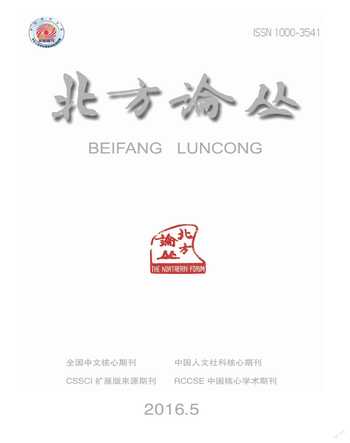莱布尼茨与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比较
郭菁
[摘 要]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指出了两条通向他者的道路。莱布尼茨强调知识,列维纳斯强调责任。具体体现在利他的前提、效果、动因、方法、程度等五个方面。神学背景、哲学基础和社会时代的不同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两条道路也是可调和的。两条道路都以独立的他者为前提,反对从自我中心的视角看待他者,倡导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以此为前提,可以建立起众多他者的超越性共在关系,其中责任和知识相辅相成,责任不仅构成了知识的前提,知识也促使“我”担负起回应他者的责任,成为“为他”的存在。
[关键词]莱布尼茨;列维纳斯;他者;责任;知识
[中图分类号]B51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109-05
“我”如何克服利己主义成为利他的主体?莱布尼茨认为,知识铺垫了通向他者的道路。列维纳斯反对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添加知识这一中介,认为,是责任使我担负起回应他者的使命。究竟是知识还是责任促使“我”成为“为他”的存在?
一、知识与责任:通向他者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指出了两条不同的通向他者的道路。莱布尼茨强调知识,认为,利他基于自我对他者的认知;列维纳斯强调责任,认为,利他基于自我对他者的责任,而不是对他者的认知,“这是他者分派给我的,责任所关涉的那个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1] (p.90)。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利他的形而上学前提不同
首要的不同体现在利他的形而上学前提下。莱布尼茨的利他以其关于完美的形而上学为前提,列维纳斯的回应他者奠基于第一哲学伦理学。
莱布尼茨认为利他的前提在于事物自身的完美。事物自身的完美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善。形而上学的善与道德上的善相关联。道德上的善就是去促进形而上学的善,即最大化地促进完美。只是道德善的引发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依赖于对完美的认知,如果“没有知识真正的美德不会出现”[2](p.114)。所以按照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只有认识到他者自身的完美才会产生要促进他者的善这一道德要求,正是知识铺就了通向他者的道路。
列维纳斯则认为,知识并未铺就通向他者的道路,反而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他者有三个特点使得他者不能被知识通达。第一,他者差异。他者之为他者就在于他者是不同的,不可能作为知识的对象被同一。第二,他者不可被经验。知识以经验到的对象为边界,他者不可被经验,超出了知识的边界。第三,他者超越。他者先于我的存在,知识基于我的存在,他者超越了知识。也就是说,他者的差异、不可被经验和超越,划定了知识的界限。
对于列维纳斯来说,我不能够通过知识来通达他者,只能够以责任来回应他者。因为,他者不可知的差异超越了我的存在,我只能在与他者差异的关系中生存。这就意味着我只要生存,就必须对他者的差异进行回应。回应即责任,在回应中我会听到他者拒斥我同一的命令,“你不可谋杀”[3](p.199),承担起尊重他者的责任。列维纳斯认为,正是这种回应他者的责任奠定了我的存在根基,即第一哲学伦理学。所以列维纳斯反对以知识作为通达他者的途径,而是表明,超越的他者早已在知识的边界之外,先行地向我指明了通向他者的道路。
(二)利他的效果不同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不同的形而上学造就了自我与他者的两种不同的关系。一个是基于完美的认知,另一个是回应他者的责任关系。这也导致两种不同的利他效果。
在莱布尼茨那里,利他会促进快乐。“快乐是知识或一种完美感”[4](p.109),是对完美的感知。当我认识到他者的完美并积极促进这种完美时,我便会因对完美的感知而快乐。“爱就是从他者的完美中找寻快乐”[4](p.109)。不仅如此,我在增进他人完美的同时也会增进自己的完美,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快乐。幸福就是在促进他人和自我的完美中获得的一种持久的快乐。可见,在莱布尼茨那里,利他与利己最终是一致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的快乐”[4](p.111)。这种一致以知识为前提,对完美的认知不仅促进了他者的善,也增加了自我的快乐,并导致了最终的幸福。所以“智慧是幸福的科学”[4](p.109)。
列维纳斯并没有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建立在知识基础上,而是直接诉诸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并不轻松,甚至成为不可逃避的负担。因为,责任不是我选择承担的,“责任仅仅是没有任何选择地进入到存在中并发生作用”[1](p.106)。它在我能认知、能选择之前就已经强加给了我。我不是在认知的基础上认同了他者的命令,再选择去承担回应他者的责任。恰恰相反,我是在认知失败之处,发现他者总是拒绝我的认知。这一拒绝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这缺口处,他者发出的“不可杀人”的命令照耀进来,要求我不能同一他者。也就是说,在认知失败的废墟上,列维纳斯看到了他者对我的先在要求,和我必须要回应他者的责任。这样的为他者当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反而因责任的无所逃避变得有些沉重。当然列维纳斯也不希望把自我和他者对立起来,他指出对他者负责不是摧毁自我,而是孕育着我。“成为我意味着不能去逃避责任”[5](p.97)。
可见,即使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都想协调自我与他者的關系,这两条路径确实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莱布尼茨认为求知即求善,在认识并促进他者完美的同时也促进了我的快乐。列维纳斯提出责任即伦理,要求自我在回应他者的过程中悲壮地成长。
(三)通向他者的动因不同
两条路径的不同也表现在通向他者的不同动因上。对于莱布尼茨来说,自我可以依靠自律来实现利他。一旦自我认识到,利他与利己是一致的,“人们甚至在为他人服务时会增进自己的善:因为它是理性和万物和谐的永恒法则,每个(人)的博爱都会遵守这个”[4](p.111),自我便会自觉地去促进他者的完善。当然自觉一定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的,需要我们运用理性来获取这样的知识,“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完美,因为它教会我们普遍永恒的真理(其在完美体中的存在不言自明)”[4](p.110),并最终习惯于根据理性行动。可见,莱布尼茨相信自我可以通过理性的自律实现利他。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却只能依靠他律。列维纳斯反复强调并不是我选择利他,而是在我能够选择之前,他者已经选择了我,要求我回应他者,担负起为他者的责任。这一要求并不是理性能够认识的,而是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是非理性的他律要求我回应他者。对于列维纳斯,这是真正的他律,因为“真正的他律始于服从成为一种倾向而停止去服从意识时”[6](p.16)。
(四)回应他者的方法不同
那么,具体如何回应他者?两者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莱布尼茨主张的方法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思考。“把你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仔细思考,就会让你拥有有关如何做事的知识”[7](p.108)。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试图换位思考,希望从他者角度获得对他者行善的知识,按照这样的知识利他。“和别人换位思考,假设他们都智力健全且受过启蒙;你会从他们的选择中得出结论”[8](p.76)。这就避免了仅仅从自我的角度思考问题,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者。但问题是,我们真能持有他者的视角吗?列维纳斯对此持否认态度。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我与他者相似,即当我换到他者的位置上,我能够产生和他者一样的观念。但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他者与我是不同的,我无论在何种位置都只能产生我自己的观念,他者超出了我的观念之外,我不可能真正拥有他者的视角。所以要回应这样的他者,我不能换位思考,我所能做的就是倾听。“因此,在倾听时我们不理解事物,没有概念”[9](p.5)。列维纳斯要求我们做一名倾听者。他者已向我发出了命令,我只需倾听、回应,这样就担负起了为他人的责任。
(五)利他的程度不同
莱布尼茨的向他者行善一直是以知识为条件的。换言之,利他必须符合理性的、知识的标准,而非无条件地、无限地行善。所以向他者行善,不是无限度地满足某个他者的一切意图。莱布尼茨主张站在普遍他者的角度,从每一个他者的视角去观看,然后分辨出每一个他者的利益和自我的利益,并根据理性对这些利益进行衡量,找到促进普遍善的知识,再根据这些知识合理地、适度地促进他者的善。莱布尼茨曾举了法官和罪犯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有人指出如果让法官站在罪犯的角度思考问题,会同意罪犯的要求宽恕罪犯。但莱布尼茨反驳道,“法官不仅要和罪犯换位思考,也和别人换位思考,而后者的利益可能就是凶手应该受到惩罚。善的平衡(涉及更少的恶)也要求这点”[8](p.76)。可见,莱布尼茨的向他者行善,是以理性的善的知识为前提,普遍地向每一个他者合理地行善,最终的结果就是正义,“智慧是有关善的知识,带给我们正义,也能够合理地促进别人的善”[8](p.76)。
与莱布尼茨理性、适度的行善相比,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主张的是非理性地、无限地回应他者。因为他者是我的存在根基,我只能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存在,这就意味着,只要我存在,我就必须回应他者。我似乎成为他者的人质,“正是这种由人质来承担的为他人而替代的责任,要求主体的无限服从”[10](p.84)。我只能无条件地、无限地回应他者,为他者负责成为我永远无法还清的债责。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确实指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通向他者的道路,一条是从求知中求善,另一条是直接回应的责任路径。前者认为,知识先于伦理,后者认为,伦理先于知识。为什么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会提出如此相对的主张?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观点如此不同?
二、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之所以选择不同的道路,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在于他们神学背景的不同;二是在于他们哲学基础的不同;三是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不同。
第一个方面,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不同的神学思想影响了他们对道路的选择。先看莱布尼茨的神学和其伦理学的关系。莱布尼茨的伦理学不仅与其形而上学、知识论相联系,还与其神学密切相关,是一个以理性神学为基点,以理性知识为路径,以理性道德为目标的整体图景。其中理性神学作为这个整体图景的基点,定格了要通过理性求知来求善的基调。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意味着上帝不凭借个人意志任意地创造世界,而是根据理性,在所有可能中选择最好的创造。“他的慈善(BONTE)先行地推动他去创造和造成一切可能的善者,而他的智慧(SAGESSE)在其中进行了选择,它成为他随后选择最善者的原因;最后,他的权力(PUISSANCE)为他提供了真正实施他所拟订的伟大计划的手段”[11](p.185)。上帝是遵从理性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对上帝的爱也不是任意的,同样需要理性。“人们不能在不通晓上帝的完美状态或上帝之美的时候就去爱上帝。由于我们可通过他的精神力量了解他,以下是见证上帝之美的兩种方式:永恒真理的知识[这解释了上帝精神力量的逻辑]和宇宙和谐的知识(通过把理性用于事实)”[4](p.110)。这就意味着,人们是通过知识见证到上帝的完美后才愿意爱上帝。既然上帝作为最完美的完美体,我们对其完美的爱都是基于理性的,那么对于他人的热爱和其完美的促进自然也是基于理性。正是基于理性地对完美的向往,莱布尼茨的理性神学直接指向了一种理性道德。
列维纳斯虽然一直将哲学与神学相区分,但在其哲学中始终贯穿着神学的痕迹。尤其是他的第一哲学伦理学把伦理要求置于存在之外,认为,伦理超越了认知,体现了对拉比犹太教传统的继承。从这一传统出发,列维纳斯认为,“‘超越这个术语精确地意指这样的事实,即人不能思考上帝”[12](p.77)。上帝是超越的,我不能凭借理性认识上帝,上帝却可通过伦理的方式与我发生关系,这就是在他者的面貌中留下痕迹。他者的面貌不是肉身的脸,“他者并不是上帝的肉身化,而是恰恰通过他的面貌,脱离肉体,显示了上帝在其中被揭露的高度”[3](p.79)。高度标示着存在之外的无限,无限抵制着我的同一,向我发出“不可杀人”的戒命,与我建立了最初的伦理关系。可见列维纳斯是借助我与上帝的关系,建立了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和莱布尼茨一样,他们的伦理学都受到了其神学的影响,正是神学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伦理。
第二个方面,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接受的哲学体系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伦理方面的差异。莱布尼茨于17世纪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父亲是莱比锡大学的哲学教授。利用父亲的图书馆,莱布尼茨从小便开始阅读形而上学,在大学时期接受了传统的经院哲学的教育,青年时期已经非常熟知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1672年,他作为外交使节出访巴黎,在巴黎他接触到了新的近代科学和哲学成就,在惠更斯的指导下深入钻研了数学。这些新的思想并没有让莱布尼茨放弃传统的经院哲学,反而促使他寻找一种体系把经院哲学与新的近代科学和哲学调和起来。他的老师耶拿的数学家魏格耳也使他坚定了这种信念。莱布尼茨寻求创建一套基于数学—逻辑原则的整体宇宙体系,这套体系不仅要把经院神学包容进来,也要同时容纳近代新的科学成果。莱布尼茨认为,要阐明这套体系的话,只能依赖于理性。我们可以借助理性确定这套体系的全部知识,不仅包括上帝的知识、关于事物的知识,同时还包括道德的知识。所以正是这套理性的哲学体系,确定了莱布尼茨的用知识求善的理性伦理学。
列维纳斯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但也同样被摆脱这种哲学氛围的深刻需求所左右。海德格尔从生存论上将共在置于此在在世的结构中。“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13](p.138)。这一点非常吸引列维纳斯,“因为与此在分享世界的那些他人并不被设想成我自己的反映”[14](p.31)。然而,海德格尔的共在并不是根据他人的出现而定,“即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不被感知,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且只能为一种共在而不在”[13](p.140)。也就是说,共在是此在与存在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必须被置于此在的存在结构中。列维纳斯反对的正是这一点,他认为,与他人的关系更根本的是与他者的关系,而非与存在的关系。“如果对海德格尔来说,胡塞尔的移情作用表明了未能把他者作为他者,那么对列维纳斯来说,海德格尔的共在恰恰犯了同样的错误”[14](p.32)。为了确立他者的地位,列维纳斯从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出离出来。他认为,他者超越了存在。“被海德格尔视为源初的现象则实际上被排在整体化的自我与他者的极端的、专横的他性之间的源初的超越关系之后,成为第二位的了”[15](p.12)。可见,是在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超越中,列维纳斯确立了他的第一哲学伦理学。
第三个方面,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所处的社会背景的不同也导致二者伦理学的差异。莱布尼茨所处的17世纪,正值宗教改革后的教派纷争时期,30年战争的结果直接导致德国的分裂和衰落。面对这样的形势,莱布尼茨内心渴望着和平和统一。他的哲学也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的哲学中充满了各种调和(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调和、先验论和经验论的调和等)。调和的工具就是理性,莱布尼茨希望借助于理性把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调和成一个完整的包含神学、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统一的理性体系。这一体系中,所有的方面都是统一的,而且在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理性所起的重要作用。伦理学作为这一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自然也是理性伦理,倡导通过理性的求知来求善的道路。
列维纳斯身处20世纪,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他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种族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列维纳斯来说,这个时代悲剧的根源就在于自我对他者同一的暴力,所借助的恰恰是理性的力量。理性似乎给了主体一种能力和信心,使自我认为能够理解他者、控制他者,把他者最终变成与我一样的存在,这导致对他者差异的忽视和压制,导致对他者的各种暴力,现实中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战争中对他者的屠杀。“战争不显示外在性和作为他者的他者”[3](p.21),战争促使列维纳斯反思,他者可以被屠杀吗?他者的差异可以被消除吗?对于列维纳斯来说,他者不可被消除。因为,他者揭示的是无限,超越了知识的认知,理性的理解,暴力的控制,在同一的总体之外。这无疑是非理性的,确实,列维纳斯所要表明的恰恰就是这种非理性对他者的责任构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最原初的伦理关系。
三、两条道路的调和
究竟哪一条是通向他者的道路?是莱布尼茨主张的基于理性的认知,还是列维纳斯倡导的非理性的责任?其实两条道路并不绝对冲突。二者都以独立于我的他者为前提,反对从自我中心的视角看待他者,倡导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莱布尼茨倡导换位思考,就是要去除自我中心的偏见,试图从他者的角度思考。列维纳斯更是强调他者不可被我同一的差异,以此为前提确立自我对他者的责任。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的分歧仅仅在于对待知识的态度上。莱布尼茨生活在自然科学刚刚兴起的17世纪,很容易产生对理性知识的信赖。所以莱布尼茨认为他者视角是可以通过知识获悉的。我可以借助理性的知识,克服自我的偏执,按照他者视角行为,实现对他者而言的善。但是列维纳斯生活在20世纪,人类的理性知识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并显示出一些局限。列维纳斯发现知识是有边界的,有些领域是知识不可通达的。他者就超越了知识,为知识划定了界限。
列维纳斯强调了他者的超越性。不过列维纳斯的他者是个体的他者,并非复数的他者们。尽管列维纳斯也提到过复数的他者。“在他者的逼近中,除此他者之外的所有的他者们占据了我,已然是這种占据呼求着正义,要求权衡和认知,即意识”[16](p.158)。不过列维纳斯认为:“我与作为邻居的他者的关系赋予我与所有他者们的关系的意义。”[16](p.159) 在列维纳斯那里,对个体他者的责任仍旧是在先的,复数他者的正义要以对个体他者的责任为前提。“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在这种一个对另一个的责任的控制之外”[16](p.159)。也就是说,超越指的是我直接面对的某一他者的超越性,其他的他者的超越性并不同时向我展现,是我一个一个地面对之后,通过比较而得出的。此外,我自己的超越性,即我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超越性,也是在这种比较之后间接得出的,并非直接性的共现关系。
但我并不仅仅存在于和某个邻居他者的关系中,我存在于和众多他者的共在关系中。这一点莱布尼茨的思想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莱布尼茨已指明站在他者的视角不是仅仅站在某个他者的视角,而是站在所有他者的视角。不过,莱布尼茨没有突出他者超越性的一面。实际上,在共在关系中,所有的他者不仅是对等的,也是互为超越的,是直接共现的超越关系。其中我作为他者的他者,同样具有对等的超越性。与列维纳斯只强调我与某个他者的非对等的超越关系不同,是这种对等的、直接共现的、互为超越的共在关系,成为每个人的存在条件。也是在此意义上共在先于存在。因为共在先于存在,所以,“每个人又必须承认他人的超越性以便能够共在。没有人能够反对共在,因为反对共在就等于拒绝存在”[17](p.240)。
既然我不能反对共在,就只能通过回应超越性的共在关系而存在。回应有两种方式:一是遮蔽共在关系的消极回应。我仍旧忽视每一位他者的超越性,按照自我中心的方式生存;二是敞开共在关系的积极回应。我接纳每一位他者的超越性,在与众多他者的关系中不断成长。回应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我的存在方式。我如何存在的问题就转换成我如何回应他者的问题。我可以选择消灭他者成为唯我的存在,也可以选择尊重他者成为为他的存在。列维纳斯没有对回应进行区分,认为,只要我必须以回应他者的方式存在我就是责任主体。这样的回应变成一种生存论上的被动回应。无论我做何选择都是回应,变成了无选择的回应。问题是,如果我的生存只有回应而无选择。这是否会变成他者对我的暴力。即使这种暴力产生的是我的伦理责任,但若我只能被动回应而不是自由选择的话,这种决定论的伦理意义又在哪里?所以,在回应的方式上,是自由的、有选择的。
对回应方式的选择不仅体现了我的自由,也开启了伦理的可能性。在此选择的路口,知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知识具有自反性,它可以反观自身,认识到自己的边界,并在边界处开显出他者共在的超越层次。在此边界,我认识到,我无法同一他者,我必须与众多他者的超越性同在。这时,我便会谦卑下来,尊重他者的差异,回应他者的超越,并在不断地回应中成为责任主体。
总之,知识和责任并不矛盾。知识具有这样的特性恰恰因为知识也是在回应共在的超越关系中形成的。责任构成了知识的前提,所以,真正的知识是与责任相一致的。“我”借助这种真知便能担负起回应他者的责任,在与众多他者的共在关系中,成为“为他”的存在。
[参 考 文 献]
[1]Emmanuel Levinas. Substitution[C]//eds. Seán Hand.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2][德]莱布尼茨. 诸侯众生相[C]//帕特里克·赖利编.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M]. trans. Alphonso Lingis.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4][德]莱布尼茨. 论幸福[C]//帕特里克·赖利编.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5]Emmanuel Levinas. Meaning and Sense[C]//eds. Alphonso Lingis.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6]Emmanuel Levinas. Freedom and Command[C]//eds. Alphonso Lingis.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7][德]莱布尼茨. 社会生活随笔[C]//帕特里克·赖利编.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8][德]莱布尼茨. 正义共同概念沉思录[C]//帕特里克·赖利编.莱布尼茨政治著作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9]Emmanuel Levinas. Reality and Its Shadow[C]//eds. Alphonso Lingis.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
[10]Emmanuel Levinas.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C]//eds. Seán Hand. The Levinas Read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1][德]莱布尼茨. 神义论[M]. 朱雁冰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2]Emmanuel Levinas. Ethics and Infinity: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pe Nemo[M].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4][英]柯林·戴维斯. 列维纳斯[M].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5][英]雅克·塔米尼奥克斯. 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接近现象学诸论题的一条后海德格尔式道路[C]//杨大春,等编. 列维纳斯的世纪或他者的命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6]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M].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赵汀阳. 第一哲学的支点[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張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