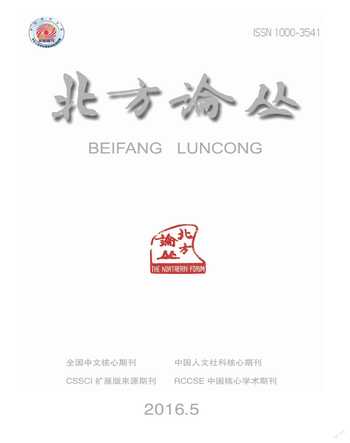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现代性
黎山峣
[摘 要]孙中山倡导国族主义,坚持文化历史意义的中华民族和政治法理意义的中国相一致相叠合;旗帜鲜明的反对分裂、反对两国论。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述,指出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中发生起来的。他认为,实业是人类文明发达之基,只有实业发达,才能救贫和救亡。对外开放,是民族主义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个人和社会、小我和大我,不是一个是非问题。在当时民族十分危急的形势下,他着重倡导国家的自由,而这又是以人为目的、为指归的。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5-0088-06
Abstract: Sun Zhongshan advocated Ethnic Nationalism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sense had the consistency with China i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ense. He opposed separatism and “two states” theory. Sun Zhongshan pointed out that no nationalism meant no cosmopolitan! In his opinion, opening up should be included in modernity of nationalism. Sun also emphasized on freedom of state, which was people-oriented.
Key words:SUN Zhongshan;Ethnic Nationalism;Opening up
一、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
严格说来,民族主义运动是从近代开始的。它有两大类型:一是西方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是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紧密联系的,例如,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革命,18世纪的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19世纪的意大利反对奥、法和教皇的三次战争,以及德国的三次民族战争等等。这类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对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西方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产生过罪恶的变种,其一是狭隘的种族主义。如沙文主义和大日耳曼主义,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浩劫,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成了这一种族主义祭坛的供品。其二是殖民主义。发达国家对非发达国家进行民族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殖民主义以血与火为先导,既强迫被压迫民族接受西方文明,又使之陷于极端悲惨的奴隶地位,从而使他们不得不起来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但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和我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启迪。他说:“俄国的主张和威尔逊的主张是不约而同的,都是主张世界上的弱小民族都能够自决,都能够自由。俄国这种主义传出以后,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赞成,共同来求自决。” [1](p.225)因而“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意到民族自决” [2](p.473),“这民族自决,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2](p.480)。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2](p.475)。作为世界潮流产物的孙中山民族主义,自然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当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又有自身民族的特点和创造。他说:“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3](p.60)这里,既显现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民族特点,又显现了其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结合。
二、反对种族主义,倡导国族主义
封建时代,中国向来“素自尊大,目无他国”[4](p.224),自以为是世界中心。这种华夏中心主义,视野狭隘,不能从世界的整体格局看待中国的地位。孙中山摈弃了“内夏外夷”“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充分意识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他早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5](p.19)正是认识到中国在当时的世界整体格局中所处的极端危险的地位,孙中山才破除了脱离实际的华夏中心主义的褊狭视野,正确地制定了民族主义的策略、任务和目的。
孙中山看到当时整个中国,而不仅是国内的某一民族处于危险和屈辱的地位,所以,他既反对种族压迫,而又没有传统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色彩。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初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5](p.20),反对清政府种族压迫的鲜明旗帜,力图“把我那悲惨的同胞从鞑靼的桎梏下解放出来”[5](p.174)。但是,反对种族压迫的口号,并非是种族主义的。虽然孙中山多次提出了恢复汉族政权的号召,但这并非目的,而为发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汉族人民起来推翻清政府的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汉族群众中,传统的种族主义排满情绪还是根深蒂固的。利用种族主义情绪,达到非种族主义的目的,是發动群众的一种革命策略。这种革命策略的运用,当然有可能导致种族主义的偏激情绪,孙中山注意到了这一点。1905年,当各革命派别合组新团体的时候,湖南学生张明夷谓既抱倾覆满洲之志,当为对象立名,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义,孙中山则认为:“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遂定为“中国同盟会”[6](p.343)。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的次年,孙中山又强调说:有人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5](p.325)。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多次重申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思想。他说:“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人人脱去奴隶圈,均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实中国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 [7](p.451)
孙中山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不是种族主义的,乃在于他认识到,清政府已堕落为取媚外国侵略者的走狗。在《驳保皇报书》中,孙中山愤然指出:“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5](p.234)辛亥革命之前,民族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反对清政府统治;二是反对列强的瓜分。在这两大任务之间,孙中山认为,“先倒满清政府”,不能不居于首要的紧迫的地位。孙中山晚年又一次指出:“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吾党之士……知非颠覆满洲,无由改造中国。”[1](p.114)上述论述表明,孙中山反对清政府的统治,是与反对列强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反对清政府,并非是满汉之间的种族斗争,而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的斗争。因此,他主要不是从汉族的种族地位,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和全中国整体出发考虑问题的。孙中山在概括民族主义之要义时说:“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p.118)民族主义前一方面的意义,是针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帝国主义不仅压迫国内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也压迫国内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所以,孙中山所说的不是国内一个民族的自求解放,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的自求解放。孙中山所说民族主义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在摧毁清王朝压迫之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 [1](p.119)。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两方面意义,都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也是从全中国的整体着眼的。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因为着眼于民族的整体和国家的整体,所以,他多次强调,要将中国造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2](p.474)。他认为,这才是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孙中山要求:“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1](p.242)所以,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p.185)。他警告说:如果再不提倡这种“国族主义”意义的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1](p.189)。所以,国族主义也可以说是救国主义。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意义十分重要,不仅和狭隘的种族主义、地方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一个国家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早在1912年1月1日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突出强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的重要性[7](p.2)。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长期陷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明确指出:“军阀本身与人民利害相反,不足以自存,故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中国之不能统一,亦此数国之利益为之梗也。”[1](pp.115-117)
孙中山严肃指出,“中国……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家”[1](p.304)。他对当时“中国将……分裂而成二国”的两国论,予以了坚决有力的批判:“中国……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为整个之单一国家。”这一国人的共识,是“正确无讹”的“事实”和“铁证”。“将来必有一伟大、统一、永久之中华民国出现”[7](p.487),“政治、产业、军事、教育及其他方面,亦当渐次进步发展,当能成一大文明国”[8](p.1852)。他强调说:“民国之幸福,以统一为主”,并对“今不幸而陷于四分五裂之混乱状态”十分痛心[8](p.1851)。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起程北上,途中在上海对新闻记者说:“这次单骑到北京去,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求和平统一。”[8](p.2068)他又说:“我这次往北方去,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8](p.2069)
孙中山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竭尽全力反对分裂,争取全国统一,争取中华民族统一,就是为了实现他所倡导的“国族主义”——文化历史意义的中华民族與政治法理意义的中国相一致相叠合的国族主义。
三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孙中山一生努力争取的,是使四万万人结成“大国族团体”[1](p.242),这不是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而是要使中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说:“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1](p.226)他又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1](p.253)这些论证,有三点重要意义:一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对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二是中国要帮助不发达的弱小国家,并和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三是在帝国主义称霸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弱国、小国可以单独发达起来。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或那一个国家,只要被压迫的或委屈的,必联合一致,去抵抗强权”[1](p.192)。从此可以看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是现代的,就在于它既是民族的,同时又超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范围,而成为牵动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世界性课题。因为一个民族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民族问题的解决,绝不可能仅仅是局部的问题。所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又具有深远的世界性,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而轻视任何一个方面,也就割裂了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完整性。
孙中山对于当时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的问题,发表了极为精辟的见解。世界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阐释。当时帝国主义所宣传的世界主义,是漠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以至否定民族利益和民族主权的欺骗伎俩。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1](pp.223-224),“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1](p.231),其目的就是否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的“自决”和“自由”[1](p.225)。所以,帝国主义所谓的世界主义是反民族主义的。
作为“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那种意义的世界主义,孙中山是坚决反对的,而对于建立在民族自决基础上,各弱小民族联合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以及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的世界主义,他则是坚决支持,并努力付诸实践的。这里的首要条件,是要各弱小民族先行自决,实现独立和自由的民族主义。所以,孙中山说:“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由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所以,不能“丢弃民族主义去讲世界主义”。现在“我们的地位连奴隶也比不上。在这个地位,还要讲世界主义,还说不要民族主义,试问诸君是讲得通不通呢?” [1](p.226)孙中山反复强调,“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1](p.231),“自己先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1](p.220)。
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二者是富于证关系的。在帝国主义已经称霸全球的条件下,不讲各弱小民族联合抵抗列强的世界主义,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现代的民族主义,不是自扫门前雪的民族利己主义;而不讲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也就失去了“民族主义做基础”[1](p.231),难免要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附庸和工具。
孙中山所说的世界主义,包括现实的和未来的两方面:一是使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二是使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所以,他说:“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4](p.56)。孙中山所说的世界主义第三个方面,就是实现世界和平。他说:“讲到世界大道德。我们四万万人也是很爱和平的。”而“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理,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1](p.231)。这里所说的“世界主义的真精神”,就是世界和平的真精神。当然,世界和平的实现,是必须而且也只能以世界各民族的平等为基础的。
四、开放主义与民族主义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抵抗列强的侵略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逐步发展的贯穿线索是十分鲜明的。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将针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的原则,作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要义的首位[1](p.118),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阐释:“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所以,“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p.119)。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民族的振兴,孙中山又力主开放主义。
反对帝国主义和实行开放主义,不是互不相容的。孙中山从全球视野出发,对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7](p.9)。孙中山认为,正是这种闭关锁国,守旧不变,才“召列强之侮”[7](p.494)。在孙中山所主张的开放主义中,最为突出的是实业经济的问题。他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发展中国实业经济的四大原则:“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5](p.8)而要实践这四大原则,就要“步武泰西,参行新法”[5](p.15),以促进实业的发展。以后他更进一步认识到实业经济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孙中山《在东京实业家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涩泽先生谓实业为国家成立之本,予谓实人类发达之基。”[9](p.18)这当然不是对涩泽之说的否定,而是从人类发展史的高度所作的更为深刻的阐释。他指出:“盖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吾国也必矣。”[7](p.492)这就说明,实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孙中山看来,实业经济的发展当然首先是经济问题,他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7](p.339)“此四万万人之中国一旦发达工商,以经济的眼光视之,何啻新辟一世界!”[4](p.252)
但是,实业经济不仅是经济问题,更“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也”[4](p.207)。孙中山举铁路建设为例说:“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7](p.490)全国“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与反对”[7](p.488),必将增进“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从而使“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7](p.490)。由此可见,铁路建设之类的实业发展,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也将极大有益于现代观念的生发、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民族发展的兴盛。所以,孙中山将实业建设提高到“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4](pp.227-228),他说:“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4](pp.248-249)这种洪钟大吕的晓示,的确是意味深长、促人猛省的。孙中山针对有人只重革命,不重建设的观点,提出了严肃批评:“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双足,鸟之双翼也。”如果只有破坏,而无建设,“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4](p.207)。这就说明,离开了实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建设,政治就不会稳定,社会也不会太平。
辛亥以后,孙中山在各路军阀热衷于权力之争的时候,以呕心沥血的极大努力,构筑了中国现代经济体系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他称此“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4](p.249)。要实现如此宏伟的发展实业的经济计划,“以一国独当之,则成功极难”,“因此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7](p.481),“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1](p.393),因此,“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材,即用外国人材;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7](p.533)。所以,“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7](p.481)。孙中山认为,在实业经济的发展上,我们持开放主义,不但需要,而且可行,因为“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此国之人可以投身于彼国之实业界,而图其发展”[9](p.19)。工业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没有什么阶级、民族、地域、国别的属性,因而可以为人类共同享有,借以增进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富强和国家的实力。当然这不仅于中国有利,对他国亦然。“中国实业之发达,固不仅中国一国之益也,而世界亦必同沾其利”[4](p.227)。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我国的实业,可以较快的时间改变我国落后的面貌。建设工业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7](p.533)。但我们采来就用,就可以“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1](p.252)。中国人的保守主义当时是相当顽固的。“虽闭关自守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4](p.224),观念远远落后于现实,落后于时代。孙中山认为,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特别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性的“世界经济之场”已经形成[4](p.249),“断非闭关自守所能自立”[7](p.530)。对外开放,已成客观必然的世界发展趋势,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于外。所以,与其被动的消极开放(如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不如主动的积极开放。近代以来,一些国家的富强,均与对外开放有关。孙中山出于“实业救国”的追求,反复鼓吹开放主义。这说明“开放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孙中山又以铁路建设为例说:“吾人须屏除一种错误之见解,勿以为外人一旦羼入此种事业,则必破坏国家之主权……盖实际上并不如是也”[7](p.490)。他认为,利用外资修筑铁路不仅不影响主权,反而有利于商业生产的发展和全国的统一,增强中国“自立以抵御外来之侵略”的实力[7](p.491)。
孫中山一方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经济和文明的多元互补。他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4](p.398)这一见识,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极富现代性的显现。
五、现代人文精神
孙中山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和根基。如果我们细加体味和分析,在其三方面的内涵和根基中,无不透示出人的追求、理想和光辉。孙中山民族主义所说的政治是人的政治,经济是人的经济,文化是人的文化。 离开了人,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成了空洞无情的东西,成了对人冷眼相视甚或与人为敌的东西。
推翻清王朝专制的斗争,既是一场政治斗争,同时也是基于人权、人道和人性的斗争。孙中山说:“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况世界潮流所趋,几于大同,若以芸芸众生,长听安危于一人,既非人道之平,抑亦放弃天职。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7](p.48)芸芸众生之安危,长听一人的封建专制,可说是对人权的轻蔑,对人道的摧残,对人性的压抑。清王朝统治的颠覆,当然可说是人权、人道和人性的胜利,是人的解放的胜利。
孙中山讲解民族主义问题时,深感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他以强烈的悲愤情感说:“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1](p.201),这种比殖民地更为低下更为耻辱的民族地位,不应称为“半殖民地”,而应称为“次殖民地”[1](p.202)。在这些话语中,我们不仅认识到我们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而且深深体味到出自民族尊严和民族人格的崇高激情,从而对孙中山民族主义以人为本的精蕴,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1921年6月,在一次演说中,孙中山将民族主义做了消极和积极的区分。他认为:“推倒满清不过是消极的民族主义”,而“积极的民族主义”,则在于“培养四万万同胞皆有人的资格”[2](p.558)。他将民族主义做出消极和积极的区分,意在强调后者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伟大,也更为根本。他之所谓培养四万万同胞的“人的资格”,重点在于提高觉悟,树立“中国主人”的民族人格和民族精神[2](p.559)。“抱此积极民族主义做人”,遇到“有凌辱我同胞、蔑视我国权者”,将“以推倒满清之手段排之,固不论其为某国抑或任何国也” [2](p.558)。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当然,孙中山所说的人,重点是合群的人、民族的人、国家的人。这为何呢,他说:“国与己之关系如身体之于发肤,刻不可无。”“须知救国即是救破舟一样,当舟沉之时,不图共力而补救,徒顾个人铺盖行李……不顾大局之观念,卒之自身亦不能保。”[5](p.523)正因为此,孙中山首先强调民族自由、国家自由的优先地位。他说:“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 [1](p.283),因此,我们要“组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即水泥——引者注)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1](p.281)。在孙中山看来,没有民族的自由、国家的自由,也就不会有现实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所以,孙中山更看重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自由,是四万万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他对人的这一重点的强调,固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迫于当时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而不得不然的。许多学者谈中国20世纪初叶人的意识的觉醒,只提个人本位意识,不提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现代较之传统要深刻和丰富得多),在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尽相符的。因为人不仅是个体的人,而且也是社会的人、民族的人、国家的人,这二者是不能分割的。
孙中山虽在人的问题上更着重地强调人的民族性、社会性,但并未将社会和个人置于互不相容的对立之中,因而在本质上不同于极权主义,也不同于极端个人主义。他说:“个人、社会,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发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7](p.507)这里,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个人与社会、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可从不同角度作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阐释,而不可对二者以是非论之。换言之,二者的关系,不是一种肯定和否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依互补的关系,是在人的有机整体结构中互依互补的关系。
正是从互依性、互补性这一人的整体出发,孙中山将三民主义定义为“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1](p.177)。三民主义的三个方面——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四万万人民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种根本需要[4](p.3)。这些需要既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又有先后重点之分。
对此,孙中山多次作过精神一致的表述:“从发生的次序”来说,“先由民族主义进到民权主义,再由民权主义进到民生主义”[4](p.3)。他还说:“那个时候满虏正盘踞中原,革命家只致力于民族主义,而于民权、民生二主义都未置意……要知道民权、民生两个主义不贯彻,民族主义虽达目的,亦不能稳固,何况今日民族主义还没有完全达目的呢?”[2](p.473)1924年6月,孙中山又做了更为完整的阐释:“吾党主义,析言之固为民族、民权、民生,至其致用,实是一个整的,而非三个分的。不过因时机的关系,有时仅实现其一部,而未能施及全体。如往者萃全力以排满,似吾党主义专在民族,而不知吾党之实行民族主义,即欲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且民族主義亦不止推翻满清而已,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而后可告完成。顾欲臻此,即非以三民主义整个的进行不可。推类言之,则欲达民权、民生两目的,亦不能置民族主义于不顾。”[1](pp.540-541)这里,孙中山既揭示了现实生活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揭示了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进程,从而使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获得了有机的统一。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的阐发,十分有助于我们对民族主义内蕴的现代人文精神的更深理解。不推翻清王朝专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根本谈不到为实现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治、民享创造起码条件的。正因如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而民族革命的完成和稳定,又必须以实现和完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基础,借以充实和增强民族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这又是孙中山反复鼓吹民主建设和实业发展的内在动因。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不停留于自身之内,而是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这种相互联系、渗透和转化的本身,也就说明民族主义从归根结底的意义来说,是以人民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为目的、为指归的。这是作为孙中山民族主义灵魂的现代人文精神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1]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1.
[7]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1.
[9]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