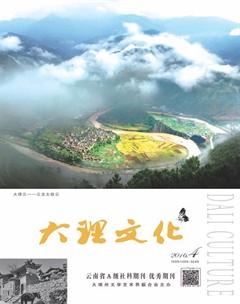凤羽河畔
河流孕育着生命,孕育着文化,因为河流,民族生生不息。
故乡的凤羽河,没有史诗般的辉煌,没有绚丽动人的乐章,甚至没有一个足以让人流连的转折,但它自有它的沉静与坚守,自有它独特的诗行。河流如血脉,没有哪一段因渺小而多余,浅浅凤羽河,因为打上故乡的烙印,带着童年的记忆,瞬间便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慰藉着思乡的心。
我是命定与故土相守一生的人,却也会生出乡愁,仿佛自己还在回家的路上。漫步凤羽河畔,溯流到时光深处,而家一直在那里。
关于凤羽河,最早的记忆是幼时跟在三老(爷爷)的后面,到蛤蟆塘给集体出工的人们送饭。那个年代,大人们都要挣工分,小孩则被随意放养。三老年轻时读过黄埔军校,解放后回到队里孤人一个,便被派去守打场。我家在打场旁,年已六十岁的好心人三老,便顺便带我,当孙儿一般疼。三四岁的我眼中,凤羽河宽阔而辽远,仿佛没有尽头。河埂上,一老一小,一担饭食,一段远路。正在挖地的大叔大妈从土里刨出几个灰褐的“土个儿”(样子像蟋蟀而个头更大的一种土虫,我至今没弄明白是什么),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钵头里再罩上碗,让我带回去油炸,算是对我的奖励。送饭路一来一回,几乎耗掉一个下午,河堤上有很多树,阴森森的,我常常要拽着三老的衣襟,生怕自己丢失在那段神秘而漫长的路上。
洱源坝子广阔的田野是少年的乐园,我常常跟在更大的孩子后面去探险,下河捉鱼,上山摘果,甚至还到珍珠涧去洗澡。而更多的岁月却与桥有关。
出小桥,过东门大石桥,再穿过田野,漫长的“跋涉”只为到九台村大澡堂洗澡。东门大石桥,是圆形的拱桥,桥的两边都给人踩出便道下到河底,就着河水洗洗菜,洗洗衣服。今天,站在霓虹闪烁的大桥上,我真难想象,那时的河为什么特别宽,河底的沙石为什么那么透亮?
青昌大桥则是解放后修的。家在西面山下。田在桥东坝子中央。一座朴素的水泥桥,贯穿了四季,也牵扯出烟火人家,根植于泥土,所有的悲欢也种在土里。那些年月,水利设施匮乏,所有的耕种灌溉都要等凤羽河水下来,上游的栽插完了才轮到下游,为了水,经常要半夜去闸。虽然是夏天,半夜也是冷的,打着电筒,走三四里才能到田头,夜风寒凉,青蛙叫累了睡去。看着水汩汩流进田里,仿佛看见了丰收的景象。若干年后一个蚕豆成熟的夜,我在暮春的晚风里走上凤羽河,绕过南山小桥,绕过福寿桥,走进青昌大桥荒凉的夜色里,坐在儿时常坐的河堤上,洱周路上的夜灯像一粒粒明珠,璀璨了远处的新城,田坝里混杂着水薄荷小秧苗蚕豆叶的香味清新了静静的夜,夜空里一颗颗星子遥远而亲切。潺潺的凤羽河水,把我带回劳作的过去。
割豆尖、背豆秆,在打场里扬起的豆糠把整个人染成墨绿色。我家准备的箩筐要比别家的小,捆谷子用的草绳要比别家多,母亲不能减少我们的劳作,只能减轻我们的劳动。背着一捆谷子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身后,她背着两大捆像一面厚厚的墙,只有两截小腿艰难地在地上移动,每一步都能在沙地上踩出个深深的脚印。三四里的路,能休息的一站便是青昌大桥边的四个石墩。可是,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很多时候,只能在河堤边歇一下,放下背子容易,再站起来就难。往往是我先在后面推母亲的背子,母亲跪在地上用手拄着地使力地站起。有时,背子太重,单推站不起,还得请旁边的人拉一把。好在,路上都是乡亲,大家就在你推我拉里把谷子背回家。后来渐渐多了手推车,拖拉机,活路才渐渐轻了些。
星光之下的石墩早已积满厚厚的灰尘。河东的土地大半已经被征用,那个忙碌奔波的耕种季,那个热闹而辛苦的收获季都淹没在河堤深深的草丛问。那个背谷子的我,背着箩筐送饭的我,在河堤下打一罐翻砂水的我,踩着沙石洗脚的我远去了;那个枕着蓑衣躺在田埂上看护篾箩里的弟弟的我,那个在沆泥潭的水沟里捞到许多大贝壳的我,那个在田边土灶上做锣锅饭的我也远去了。凤羽河,我童年的河,教会我勤快,教给我艰难,教会我珍惜的河,依旧在风雨里悄然流淌,从不吝啬。
凤羽河东与劳作有关,凤羽河西,与生活相连。外婆家在大埂村,又在村尾,一出门就是凤羽河支流的一条大沟,算是消水河的上游了,这条沟曾承载过多少茈碧渔船逆流而上,贩卖瓜果粮食换取生活必需?而我,几乎有十五年的时光都在这沟边度过,跟在表姐后面一起洗衣,洗菜,甚至渡到沟里玩水,更多的是每天都要跟着外婆或是小姨去凤羽河边的井里挑水,来来回回几趟,挑满一大缸也仅仅够一大家子一天用。外婆总会把桶里桶外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会在初一十五到井边点香,感谢水井龙王的馈赠。那是一条乡间最普通的田埂小路,那是凤羽河众多翻砂井里普通的一眼,但是,这路这井却养活了一代代人,直到自来水取代了水井,矿泉水代替了山泉水。废弃的井像一只幽深的眼,终于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和清澈,被荒草掩盖。
走过童年少年的青昌大桥,走到青年的南山小桥。凤羽河边读书三年教书十三年。我人生中最灿烂的季节都写在了这里。黄昏,大家走出校园,到河边读书,一条寂静的河便在夕阳的余晖里沸腾起来,放牛的老爹悠然地抽一竿旱烟。牛儿自在地啃着细草,绿油油的田野在风里掠过一道道波浪,那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和谐恬静。再后来,和很多老师饭后散步,大家一路热烈地讨论,交流,迎着晚风,是另一条文化之河。现在,这一段读书走廊是彻底沉寂了,即使没有封闭式管理,学子们也更愿意把所剩无多的时间割让给手机。虽然老师们还可以去河边散步,但大家更习惯于回到霓虹深处的家,集体的时代已经终结,集体出工的时代也属于历史。
逆流而上,上村水库树影依依,上村湿地虽不及茈碧湖的规模,但风车草美人蕉芦苇丛与水相携,确实增色不少。走在湿地的荫凉道上,我怀念起清源洞,怀念起白石江,也怀念起凤羽坝子来。
农历六月十三,清源洞会,那一年,我们一家心血来潮,要去赴会。因为不识路,在凤河村下了车,沿着天马山脚一路向南。山路的辛苦自不必说,走到一个山坳处,听闻一阵巨大的水声,走近,竟然是一道湍急的溪流从山里直泻而出。大家倒掉带着的水,几乎要跳到溪流里,水出奇地甘甜冷冽,水杯上都冒着冷气。都说凤羽水好,总算是眼见了。遇到村中一个老爹,说起有这样好的水真享福,他只淡淡一笑。而真到清源洞,水却安静如玉带,四周幽深,未进洞而冷气扑面,凤羽河的灵秀该是源自于此的。清源洞系苍山北麓,是凤羽河之源,也就是洱海之源。这样看,苍山十八溪是洱海的山水之源,清源洞则是把苍山脏腑里的水绕了一个大湾又送回它的面前,地面之上河流星罗棋布,地表深处,则又是一脉相连的。
凤羽河滋养了两岸的白子白女。罗坪山的浑厚又提携着坝子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如果说凤羽河是洱源的母亲河,罗坪山则是洱源的父亲山了。白石江水清清凉凉地流淌,罗坪山深处的溪流瀑布带着山的精灵传递着大地的生命,也造就了白族儿女的勤劳质朴与深深的文化底蕴。
早春三月,听说上寺村有个荒废的山村大涧。便急匆匆赶去看,大涧依着罗坪山,虽是旱季,但山涧里溪水潺潺,别有一番意趣,据说,沿着山路,能翻越罗坪山去到炼铁。而大涧朝南,就是苍山西北麓,远望过去,层峦耸翠,高拔而深远,谷底宽阔,沙石硕大,可见,雨季时这里有何等的水势。向北张望,凤羽坝子美如锦缎,透过上龙门的隘口,可以看到洱源坝子的一角了。山水相连,从不曾疏离。大涧水顺流而东汇入凤羽河,苍山水罗坪雪,共同滋养着这清浅悠长的河流,也把大理山水的情怀沿路播撒。
黄昏时分,我像往常一样,漫步凤羽河的文化走廊上,从消水河绕道鹅墩桥,再回到温泉小区边的凉亭,儿时漫长崎岖的路现在却只感觉安谧闲适。河堤上的青石路在傍晚的霞光里泛出暖暖的光,早春的樱花已经凋谢,新叶浓绿了枝头,河中的风车草美人蕉在水的滋润里旺盛地长着,三三两两的人踱着悠闲的步子享受惬意的时光。再过两年,整个凤羽河生态工程完工后,这古朴的青石路便径直延伸到茈碧湖,凤羽河也将成为一条花草的香径了。我坐在小亭子里,忽然想起关于河流的种种碎片……
生命之河,生生不息。清清凤羽河,带着它的故事,奔流向前。
编辑手记:
作为国内“新散文”的运动践行者之一,石岸以其个性敏锐的感觉和体悟,使其作品流动着深沉苍茫的生命意识,充满着对时光、人生的思考与回味,交融着对美好与沧桑生活的矛盾与平衡。《在时光中打捞》显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叙事风格,文字在世俗与超越中自由游走,忧郁理性的思考,展现了一个真诚、炽热、理性的个体,舒缓自由的内在节奏,伤感中透着对善良美好的追求,整体发散着忧思而又优美的情怀。张旗的《苦楝子》把记录祖母生平、哀思祖母的情怀寄寓在小小的苦楝子上,文章写得很有功底,平静、自然的笔调,对生活的经历不褒扬,不贬斥,以情动人,显出厚实与深度。李智红的《神树》语言老道沉稳、极具语境,充满着对那棵古老的黄连树的敬畏感,一种原始、古老的信仰萦绕其间,精炼短小的文字却让读者为这样朴素、纯粹的情怀感动。徐汝义的《凤羽河畔》写得柔美、安然,文字内敛、天然,让人充满想象,可谓笔到情到,温暖朴实间让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