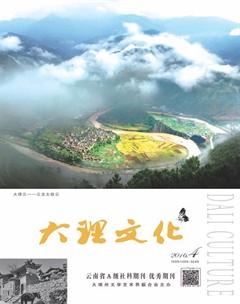苦楝子
张旗
献给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题记
苦楝子树虽说可以栽培,但我所见到的苦楝子树,都是野生的。
我家老屋庭院的围墙外。就有两株苦楝子树,一株在东面水沟边,一株在西北面废弃的旧屋基上,都是自己长出来的。至于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它们为什么要长在这里而不长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确切地说是没有人关注。树不是想长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的,一切都很偶然,然而又都自然而然。
没有谁家愿意在庭院里栽一株苦楝子树,如果庭院里不期长出了一株苦楝子树,是会被铲除的。这和有的人家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插柳,庭院里不栽缅桂的忌讳一样。桑与“丧”同音,出门见“丧”不吉;柳与“流”谐音,说法则是家中财物因此而有流失之嫌:同样的说法,缅桂则有“免贵”之忌。就因这名字愁眉苦脸的。带了个“苦”字,苦楝子树也是不被人待见的。“苦”,总会让人联想到苦命,那是人生不幸的遭遇,有谁心甘情愿与之相依为命呢?避之唯恐不及。
往昔民间的这些禁忌风习,原本没有什么道理。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求吉心理,对不可知命运的敬畏。
苦楝子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树根、枝干、树皮、叶子和果实,一整个都是苦透了的。我之所以记得这两株苦楝子树,是每年的春天,粉白浅紫的小花朵,似雪似雾,铺天盖地开满在灰绿的叶丛之上,芬芳四溢,把个庭院熏得香喷喷的,丝丝缕缕的幽香又被春风送往远方。秋天,苦楝子成熟了。枯黄的树叶,在秋末冬初的寒风里四下里飘飞,落到大门外的过道上,落到了庭院里,三天两头要我们打扫。双手握着山竹扎的老笤帚,划船桨似地,一下一下扫过去。树叶落尽,剩下成熟了的苦楝子,饱满圆润,金黄可人,圆嘟噜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若要采收,须爬到树上用竹竿敲打。祖母是绝不让我们爬树的,怕我们从树上跌下来。只等开春,在呼呼的春风中,青黑的光溜溜的枝干摇来摆去,把风干的苦楝子摇落了,祖母才去捡拾回来,放在床下的一个竹箩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供销社收购土产,除了蓖麻子、小桐子,还有苦楝子。平时采收积攒下来,赶街顺便把它们背到供销社去交售,虽说块把几毛钱,却可以买点盐巴、火柴、煤油、肥皂什么的,给那时本来就乏味枯燥的日子增添点滋味,抹些亮色。
交售苦楝子,每次祖母都要留下一些。老家的传统,妇女们就是用它来打裱布做鞋穿的。剥了皮的苦楝子,淡黄的面团似的果肉黏乎乎的。用它时,先将它盛在个木盆或铁盆里,用开水烫了,泡软,再剥去皮,轻轻搓揉,直到把它搓揉成糨糊一样浓稠的浆子。那浆子有股酸苦刺鼻的气味,一般人可闻不惯。好处是放置时间长了,不会像糨糊一样变质馊臭。苦楝子本来就是一剂驱虫良药,能杀菌抗腐败。
祖母打裱布,就是把苦楝子浆子,用棕刷涂抹在一块木板上,粘上一层层旧布片。这些旧布片,是她平时从家人穿破了的旧衣服上拆下来,洗干净了,一块一块收藏着的。就这样,在木板上抹一层浆子,粘一层布片,抹一层,再粘一层。直到整块木板都抹满粘满,厚度半厘米左右,才拿到阳光下晾晒,使其干透,才从木板上撕下来收好。一块裱布就做成了。
母亲就是用祖母打的裱布,按各人脚的大小裁剪鞋帮鞋底,做一家老小穿的布鞋。鞋帮里要夹一层裱布,鞋底两面夹裱布,夹一层,包上一层新白布。做一双三合底布鞋,鞋底至少要夹三四层裱布,然后才用抹过蜂蜡的麻线来纳鞋底。做一家人穿的鞋,一年下来,祖母至少要打两三块裱布。
那时的乡村,老式的土木建筑的瓦屋茅舍,家家都是在方格窗棂上糊上层白棉纸,挡风御寒,遮蔽隐私:在楼檩上打个竹篾顶棚,糊上旧报纸当天花板,挡挡尘灰;还有过春节贴春联、贴门神,用的都是苦楝子浆子。用面粉搅成的糨糊当然方便省事,但那是口粮,那年月常有缺粮吃不饱饭的日子,谁敢糟蹋粮食!用苦楝子浆子,除了节约粮食,还有个糨糊没有的好处,鼠不咬,虫不蛀。
记得每年的春节,除夕那天。贴春联、贴门神之前,父亲领着我和弟弟,拿根长竹竿绑上把老笤帚,先扫除屋顶楼檩上的蛛网积尘,再填好墙角隐蔽的鼠洞,把堂屋卧室灶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后,又在庭院和大门外的过道里洒上水,彻底清扫。那些平时打扫不到的角落旮旯里,总会扫出些捡拾遗漏的苦楝子,没打扫干净的叶子叶柄。我们把苦楝子捡起来收回家,把那些细长的光溜溜的叶柄和叶子堆在一起烧掉。本来可以倒进畜圈里沤成肥料,苦楝子树的叶柄叶子却沤不烂,味道太苦了,是不是也太坚强了!
天黑下来了,在合家团聚围坐八仙桌旁吃团年饭之前,祖母照例每年都要先祭祀天地祖宗,然后在大门外泼一碗浆水饭。
在岁末年底的寒风中,庭院里摆放了一张矮脚的圆桌,香烟袅袅,热气腾腾,桌上一个白瓷香炉里焚着香,红漆托盘里摆放着供品,还有酒和茶。过年我们吃什么就供什么,没有特供。祖母跪在桌前,嘴里叽叽咕咕做着长久而热烈的祝赞祈祷。听不清她说些什么,但可以想见,是祈愿天地大神和列祖列宗,保佑全家老幼来年清吉平安之类。这时,我就站在她的身后,等她祝赞完毕,也要磕一个头。这是她交待过的。我是长孙,她特别地疼爱我,她的心意不言而喻。
祭祀过天地祖宗,祖母就在一个盛了半碗水的饭碗里,把供献的大米饭和菜肴放一些进去,泼在大门外的两边,酒和茶水也泼一些。其实不止过年,就是过节。吃饭前祖母也要在大门外泼浆水饭。而且,街坊邻里,家家如此。这是老家民间逢年过节传统的仪式之一。她说,过年了,那些没有子孙后代的孤魂野鬼也要过年,家里有门神把守着,他们进不去,泼碗浆水饭给他们过年。
我一直跟在祖母身后,按她的吩咐,帮着她把这些传统的仪式一一做完。这一切,祖母总是做得不慌不忙的,总觉得有一种不知哪来宗教精神在支持着她。她很虔诚。
此时,村巷里有零星的鞭炮声,空气中弥散着幽微的火药香。看看天,深邃无垠的天穹已布满繁星:四下里,围墙外高过屋脊的两株苦楝子树的剪影,映衬着闪烁的星光,黑魃魃地贴在暗蓝的天幕上,成熟了的苦楝子成串成坨地还挂在枝头,在寒风中丢溜丢溜地摇晃。想着祖母年复一年的这一番美好祈愿,想着好不容易才过去了的这一年,有多少的烦难和艰辛:想到明年不定又会遇上怎样的不幸和艰难,谁知道呢!在这个新年旧岁交替的时刻,在祖母叽叽咕咕的祝赞祈祷声中,对命运这个神秘的不可知的问题,每年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叩问,直到祖母去世。
祖母去世后,每年的除夕,大扫除、贴春联门神,一如既往,唯有吃团年饭前祭祀天地这个仪式,没有谁来继承举行了。家庭屡屡遭遇的种种不幸与磨难,让我们对神明的护佑心存疑虑,信仰之心慢慢瓦解。但无论在哪里,每年的除夕,总会让我想起祖母,想起她祭祀天地祖宗的种种情景。老家那两株苦楝子树,枝桠张牙舞爪酷似鬼魅的阴影,贴在星光闪烁的天幕上,还有自己彼时触景生情对不堪命运的思考,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冥冥之中,神明之事究竟也不可知。每当遭遇不幸与磨难的时候,却总会让我想到人的命运。想到命运,每每让我想到我的祖母,想到她非常不幸的一生。
祖母是1982年去世的。这一年,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土地下户”的那一年。据县志记载,这一年,全县1270多个生产队都实行了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这是宾川历史性的大事件,堪比三十年前的土地改革,农民的好日子才开头啊!
祖母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是火把节后的第二天,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五荒六月,青黄不接,正是年年闹缺粮的日子。刚下户的责任田里,栽插的水稻才抽穗扬花,开镰收割还要一个多月。承包责任田的头一年,自家的稻谷还没收上来,吃上新米饭,祖母就去世了。
祖母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却没过上才开了头的好日子,很遗憾!我想,唯一能让祖母欣慰的,应该是她临终前终于看到我成了“公家人”。1979年10月,我已转正,脱去“农袍”,由拿生产队工分报酬的民办教师,成了拿国家工资的公办教师,国家还供应口粮。让她寄托了一生希望的父亲不“成材”,她把希望又寄托在了我这个长孙身上。这可是花了她一生的心血,家庭才有了这一小点点变化,而且来得太迟了。
祖母十九岁守寡,人生对她来说,可是太残酷了。在她父母的眼里,不就还是个父母疼爱的孩子吗?她才十九岁呵!成亲未满三年,我的祖父就不幸去世了,而我的父亲才一岁零九个月。祖母说,尚不知人事的父亲,路还走不稳,柞跛着脚,踉踉跄跄走到停放祖父遗体的尸床前,一迭连声地喊:“爹!爹!爹!”以为父亲是睡着了呢!就为了守这个独子,她付出了一生的幸福。这是一场单恋,是一个人无条件地为对方付出,甚至是付出了未必幸福的苦恋。
有谁想过,为人之母的她,柔软的内心深处,仍渴求父母亲人温情的抚慰!谁来给她这个关爱?任何坚强的人,即如所谓的男子汉大丈夫,也会脆弱无助,也需要人保护,何况一个十九岁的弱女子,在漆黑长夜品味人生无边的孤寂!她也是一个普通人!
我想,祖母之所以能够超越痛失亲人的巨大悲哀,走完了她这艰难的一生,是爱给了她宗教般的意志。爱就是她的宗教。为人之母,爱儿爱女,谁不是一厢情愿无私无悔!正是内心有了这份强烈的爱,一位十九岁的弱女子,才能抗御不断入侵的痛苦,有责任有担当地直面人生。被爱的抚慰消融了的绝望,就是一种蕴藏着绝望的希望。祖母一生的爱和苦,拯救了这个极有可能倾覆的单亲家庭,延续了这一脉濒于绝断的血缘。独子多孙,二十多年后,她有了四个孙子。她去世时,四个孙子都已长成林,不用她担心独木不成林了。老话说,一代人的媳妇,几代人的祖婆呵!
如果说,有个让自己珍视并愿意为之活一遭,乃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东西就是人生价值,那么,这是不是就是祖母的人生价值!至于她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做出如此决绝的人生选择。没有人知道。“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而她却从来没讲过人生,非常年代里她的非常人生。
一位西哲说,一个人应当做他能做的事: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这位西哲所说的英雄,并不是走遍天下无敌手的江湖豪杰,也不一定是功盖千秋的大伟人,甚至不一定是一个胜利者,而是芸芸众生中那些了解生命而且热爱生命的人。这种平民英雄观的价值伦理,对我心灵的撞击和震撼是前所未有的。我的祖母。平凡的一生,她所做的,就是她能做的,不就是平常人不大容易做得到的吗?
祖母去世前,一点征兆迹象都没有,她是不声不响地就走了。那些日子,她只是牙痛,到大队医疗站和公社医院看过几次,她还能喝大米熬的稀饭,总以为牙痛不是什么大病。
几天前,我请岳母在州城集市上买了一百多斤大米。那时,买这一百多斤大米。要花我将近两个月的工资。除了给祖母熬稀饭,我们吃的则要掺上大半国家供应的杂粮。不晓得是从什么国家进口的苞谷和高粱,人家做饲料的陈粮,太难吃了。幼稚的大女儿,当时曾说:“什么时候能让我吃上净米饭,不吃菜我也吃得饱!”许多年后,我们还拿她的这句傻话取笑她。
那天,我要去把这一百多斤大米运回家。一大早,骑上自行车,我就去了离家二十来里的岳母家。吃过午饭,把两袋大米装上一辆小马车就往回走。出城两里,刚转过南门外水街箐那个大弯,就遇上家族中的一个侄子,急匆匆骑着车来找我。一见面就说:“老太不在了!今天上午。”老家人把曾祖母叫做“老太”:说“不在了”是避讳,是说人死了。事情来得突兀,但容不得我多想,当即请侄子把小马车上的两袋大米送回家。我返回州城,跟岳母商量了治丧出殡诸事宜,随后才回家。
祖母入殓,没有谁安排我,我含着泪,上前抱起祖母的头,二弟跟着抱起祖母的脚,把她的遗体从漏阁屋里移出来。抬到堂屋里。家族中的几个长辈在一旁帮着,安放在棺木里。盖棺之前,我又抚摸了她皮包骨头的脸,深陷的眼窝。看清她的眼睛闭上了。并没有“死不瞑目”。虽然她这一生有不少让人感喟的遗憾!祖母是我至今唯一亲自装殓的亲人。
祖母临终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其实,她的遗言二十多年前就留给我们了。
1960年,是“大跃进”后接踵而至的大饥饿最严重的一年。不少人患了水肿病。祖母的双脚肿得亮堂堂的,像发面馒头,已卧床多日。
一天,她把家人叫到床前交代后事。其时,我才是个16岁的中学生,也站在一旁听着。祖母非常安详。她知道,她患的这个病并非不可救药,也知道近邻已有人先她而去了,有比她年长的,也有比她年轻的。她反而解脱淡定了。眼见她的四个孙子,虽然还是四棵嫩苗苗,但是一天天长大起来了。看到她的付出有了结果,无论在家族亲戚中,还是在街坊邻里间,她还是相当有脸面的。为人钦佩。她也很有成就感。离开这个世界固然可悲,但人生价值已如愿以偿,她知足了。她还能怨谁呢?她平静地说,她死后,一定要把她埋到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这不用她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接着她又说:“那里,离我家不远。做鬼也可以多得吃碗浆水饭呵!”却让人心痛不已。这些年,她是饿怕了啊,我的祖母!新庄张家山的祖坟墓地,在古镇州城西面:纳溪河从山下平旷的田野上蜿蜒流过,河东就是她出生的村庄大罗城,她的娘家。
从后来官方公布的资料得知,那一年,宾川县患水肿病肝病的有5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的有百余人(是大理州死亡人数最少的县,还有死亡上千的,甚至几千的县)。所幸祖母终于熬过了这一关,活了下来。面对过死亡,又逃过了这一劫,能够活着直至改革开放,不就是一种幸存?然而,祖母的这份口头遗嘱,像铁锤敲钉,一字一字砸在我的心上,留给我的却是永远的痛。
二十二年后,依照祖母的遗嘱,我把她安葬在新庄张家山祖坟墓地里。竖墓碑,碑文里又特意书写并刻上“大罗城黄氏人也”字样。此地距大罗城不过三四里。新庄与大罗城同属一村公所。山川田野相连,人们在这一隅土地上聚族而居,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乃至世代相守,知根知底。平常平静的日子,当然要由行政来维持,殊不知,这世道人间,还有亲情、人情和乡情,还有经年累月积淀起来的风俗和文化的潜规则的维系。
在收拾祖母的遗物里,我竟意外地发现,她的床下,一个稻草编的草箩里,竟还有不知什么时候用剩的半箩苦楝子。久违了,苦楝子!已有好多年,供销社不再收购这类土产:也有好多年,祖母没用它打裱布来做布鞋穿了。
苦楝子,完成了它的使命;苦命的祖母,苦恋一生,也完成了她的使命。
祖母去世已三十多年,一直想写她却没能写,原因我是一个性格懦弱、感情脆弱的人,一想到祖母一生的苦情,就有一种撕心裂肺之痛,让我受不了。将之诉诸文字袒露在众人面前。更需要有一种勇气。还有,那样的岁月,那样的日子,那一代人的情感、观念和精神,或许也不是今日的人们能够理解接受的。如果,今天有人像这样甘愿默默地坚守一份人间的骨肉情义,很难说会被人视作陈腐可笑。但是,什么是人性,什么有违人性,基本的判断应该不是很难。
1982年,祖母去世一个多月后,我家承包的责任田里,栽插的良种水稻“桂朝二号”,亩产达700多公斤,竟比生产队集体栽种的老品种稻谷产量翻了一番多。而邻村一农民栽插的“桂朝二号”水稻,亩产获1070.65公斤,被《云南日报》誉之为“全国籼稻单产之冠”,闻名全国。也就是自那一年始,家里不再缺粮了。这当然不止我们一家。而老家的好日子就是从那一年从吃饱了饭开始的。
那一年,祖母才76岁。好日子才开了头,她却走了。
想起祖母,每每就会想起她的苦楝子,想起她无条件的亲情大爱的“苦恋子”——那是人生无法预测也不可抗拒的天灾和人祸、饥饿和死亡,都不能剥夺和磨灭的真正珍贵的品质。
我的眼角一下子就泛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