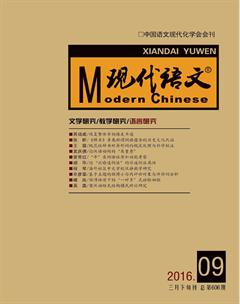翻译理论的革新:语用学的引入——语用翻译浅谈
□李梓嫣
翻译理论的革新:语用学的引入——语用翻译浅谈
□李梓嫣
摘 要:社会的需求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然而翻译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如“语言和文化”的矛盾问题。我们认为,“语用翻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本文简要介绍了翻译学中的两对矛盾,对目前翻译学中比较新的领域——“语用翻译”及其观点作了分析和说明,并指出它的优势和不足。
关键词:翻译理论 语用学 语用翻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外事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起着重要作用,只要涉及到跨语言的交流就不可能离开翻译。
目前,国际社会对翻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际需求和翻译实践的积累促进了翻译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以此为背景,翻译也由最初单纯的实践活动发展为如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我们知道,脱离了理论的实践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翻译理论的更新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本文将对翻译学中新的理论“语用翻译”作简要的介绍。
一、翻译学理论的碰撞
20世纪是翻译学蓬勃发展的世纪,社会需求催生出许多翻译学理论,各种翻译理论激烈地碰撞,从而形成许多翻译学派。尽管目前翻译学派的划分还没有定论,但总的来说,翻译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和文化学等学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学科中新观点的出现不断为翻译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
翻译学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几个学派:以语言为核心,认为翻译要使语言各要素“对等”的语言学派;把目光转向目标文本,解除了语言学派“对等论”束缚的功能目的学派;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现象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要结合文本的时代背景及作者精神的阐释学派;否定传统翻译观,突出译者作用的解构学派;认为翻译是殖民的工具,对翻译在殖民活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以唤醒民族意识为己任的后殖民学派。
除了强调作用和结果胜于强调过程和手段的后殖民学派以外,其他翻译学派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原文和译文以何种方式互相连接”的问题以及“处在连接两极的两种文本及其连接过程中诸多要素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即“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和“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
对于“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现在翻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有人提出“在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直译意译论争并非都是在同一层面上的,针对同一翻译问题或翻译现象所产生的。”[1]我们在进行文本翻译的时候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必自始至终维持同样的准则。事实上,“翻译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常常迫使译者跨越直译和意译的分界线……难以始终坚持单一的方法,结果往往是兼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2]这种融合的取向被更多的翻译学者接受,很好地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的矛盾。
但是,在“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上,学界仍有较大分歧。“语言派”吸收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立足于语言本身,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语码的转换”,强调语言的客观性,回避了不确定的心理因素。“文化派”否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存在“意义”,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这两种观点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双方的支持者至今仍然各执一词。
二、翻译的语用学转向
我们认为,解决“语言还是文化”这一问题,不妨采取类似解决前一问题的方法——引入新的理论,吸收双方的优点、摒弃二者的不足,从而推动两种观点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翻译学中引入语用学理论,以语用学的理论成果推动翻译理论的革新。
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语用翻译”。
(一)语用翻译的主要观点
要引入语用学的观点,就要先明确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语用学也关心语言符号的意义,过去曾经出现了语用学和语义学互争上位学科的现象,甚至在语用学与语义学互相独立之后,有人将语用学视为“废物箱”,把不属于语义学的内容全纳入语用学的研究范畴。现在则普遍认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词语之类的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3](P11),是一种在特定的语境下呈现出来的语言意义。然而,从定义来看,语用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语言现象几乎都和语用有关。
同语用学一样,翻译学也是一门和语言有关而又具有一定的内部复杂性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说,翻译学也需要研究具体语境下语言的运用及其意义;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上说,这两门学科都要受到几乎所有与语言、心理、文化相关的学科的影响;从时间域上来说,他们研究的重点都是共时层面的“当下”的语言。如果说语用学的优点在于它在语言现象研究中的“广泛”,那么翻译所需要的也是一种“广泛”的语言知识。因此,翻译的语用学转向也是一种必然。
“语用翻译是指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翻译操作中所涉及的理解和重构、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原作语用意义(pragmatic force)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方面的问题。”[4]受到语用学观点的影响,语用翻译理论认为:“我们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交际情景、原文的文化背景既读者的推理习惯来理解原文意义,在重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译入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读者的推理习惯来重构原作者的意图。”[5]但这并不是说语用翻译更偏向于“文化派”。恰恰相反,语用翻译在强调“建立在文化背景上的重构”的同时,也指出“语言是翻译理论体系的主干,翻译研究倘若脱离了语言,就好似空中楼阁”[6]。使翻译深深根植在原文本身,翻译过程也不失文本本意。
所以,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看,翻译并不是如“语言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受制于语言事实的客观过程,也不是如“文化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受制于主体与文化的主观过程,而是“理性基础上的重建”,即用原有的建筑材料,依照新的蓝本,重新进行构建。翻译应当关心的既不是文本的对译,也不是文本意义、艺术感的对译或作者思想的对译,而是在相同而又具体的语境下具有相同语用效果的表达方式的对译。
(二)语用学影响下的翻译实践
语用现象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译的时候不考虑语用因素是不切实际的。将语用学的观点引入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就可以避免总是以“中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肤浅的论断作为汉外表达方式差异的理由,使我们可以有理据地分析差异表达式的对应规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解决翻译中“中式外语”和“过度泛化”的问题。下面,我们举例简要说明:
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之一就是主动句和被动句使用情况的差异。有些翻译教材虽然指出了“英语使用被动语态的情况比汉语多”这一事实,却没有指明制约英语被动语态使用的因素。事实上,英语也并不是随性地使用被动语态,翻译中过度使用被动句也会让英国人觉得“不地道”。如果我们引入语用学观点,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刘明东分析了英语被动语态,认为“在语用上,它是由话题确立、语篇连贯、礼貌原则、句子结构、客观表达等方面的因素所致”[7],而陈冰飞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影响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用因素分成三类,并以大量例证对这些语用动机和它们的对被动语态的制约机制以论证描述”[8]。
在非通用语领域,有学者着眼于日语中的省略现象,运用利奇的会话原则理论探讨“日语会话中句子后半部分省略现象以及它的语用条件和语用作用”[9];有学者区分了汉语“离”和日语“から”“まで”的认知模式和语用特征[10];还有学者分析了日语中制约寒暄语使用的因素[11]。
上述成果虽然大多数偏重于语用学和语言习得,但是它们都很好地解决了从语言本体和文化角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莫爱屏的《语用与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对语用和翻译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证,引用很多翻译实例,将语用学中语境、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等概念、理论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如果我们能在翻译过程中将它们巧妙地运用,则可以避开“概率说”产生的不确定性,更理性地进行句型选择。
(三)语用学影响下的翻译学指导思想
上文我们讲到了语用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其实它还属于语用翻译中最基础的部分。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实践,就连翻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用学理论的影响。
虽然语用学被引入到翻译领域的时间并不长,但语用翻译的指导思想却经历了“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表现为从单纯的关联理论与翻译学的结合到广义认知语用学作为一个整体与翻译学的结合。这一过程与认知语用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因为国内的认知语用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关联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到基于认知科学或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广义认知语用学’研究。”[12]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要传递的是说话人的意图……说话人说话时不仅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而且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意图。”[13]以关联理论为指导,我们可以将翻译视为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即“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convergence)。”[14]
关联理论不仅能指导翻译过程,还能作为判断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达到翻译的效度,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相吻合”[15],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翻译成功的标准是译文和原文的“语用等效(pragmatic equivalence)”。(何自然,1994)
然而“语用推理和认知分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两者无法分开”[16],翻译学与关联理论结合的加深必然导致这种联系发展到认知学领域,从而引发了语用翻译原则的一次发展,即与广义认知语用学的结合。
认知语用学认为,“为了尽可能让合作者识别自己的交际意向,行动者必须构建一个关于合作者的心智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寻找策略。策略模式越具体,交际效果实现的可能就越大。”[17](P119)由于人类的认知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认知语用学可以从心理层面解释人类认知与语言使用上的普遍联系。因此,与认知语用学的结合可以大大增强翻译的创造性,尤其是在涉及到没有现存的表达方式时。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科学报告,特定的文本都会受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影响,因而总是会存在一些单从认知的角度无法解决的问题。用认知语言学指导翻译实践重在审视“心理过程”,难免会忽视社会环境对译入文本的作用。王寅倡导认知、社会和语用学的结合,认为认知语用学应考虑社会因素,以此提出“新认知语用学”这一概念。[18]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把社会因素纳入到认知语用学范围内,弥补了过去重“心理”而轻“社会”的不足,扩大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使过去的认知语用学发展为“广义认知语用学”,也让认知语用学更契合翻译学的需求。
三、语用翻译的意义及不足
读者可以是感性的,然而翻译过程一定要以理性为指导。只有避免感性的盲动对翻译过程产生的干扰,译者才有可能将最“忠实”的译文呈现在听者、读者的面前。我们所说的“语用翻译”,恰恰可以提供这种理性的指导。但是,语用翻译发展至今,不仅有它的价值,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语用翻译的意义
我们认为,语用翻译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克服了“语言派”和“文化派”的不足。
前文已经提到过,语言派的不足在于把翻译视为简单的“符号转化”,忽略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感。文化派的不足在于过分注重译入语的习惯,过分关注主题,忽视客观规律,最终陷入相对主义。
语用翻译为这对矛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化解方式,但它对矛盾的化解并不是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与前两种理论“三足鼎立”,而是积极促进两种理论的融合,这使得语用翻译的观点更有普适性。因此,有学者说:“这一转向使翻译学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向语言行为理论转向,也阐释了解构泛滥的怀疑主义重新回归理性,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才能明确语言背后的意向性,才能明白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19]
(二)语用翻译的不足
语用翻译并非完美无瑕。由于两种理论的交融需要两个学科共同努力,而现在语用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有许多理论有待完善。我们认为,语用翻译的不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用学近些年才兴盛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升。另外,即使语用学持续不断地发展,我们也无法做到穷尽一切语言现象背后的意义。
其次,如果使用不当,语用翻译“过度的语用适应”反而会给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造成困扰,让读者误以为对方的语用习惯与本民族相似。有学者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这些差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许一些人读译文的目的之一正是想了解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同与异究竟在什么地方”[20]。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此,语用翻译还涉及到“度”的考量。
最后,目前的语用学侧重于研究同一文化内部的语用现象,而翻译更关心的却是跨文化的语用对比,这导致了目前语用学的很多结论都无法直接指导翻译实践。我们认为,进行“对比语用学”或“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对这个新领域的发展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总的来说,虽然目前语用翻译领域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去寻找答案,但是翻译学和语用学的结合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相信,今后的语用翻译会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语用翻译的理论成果也会被越来越多的翻译专家所接受。并且,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流,语用翻译的理论必将不断革新,引导一个崭新的翻译学流派。
参考文献:
[1]方仪力.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策略与元理论向度探讨[J].上海翻译,2012,(3).
[2]穆诗雄.以直译为主还是以意译为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
[3]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莫爱屏.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路径[J].中国外语,2011,(3).
[5]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季刊),2001,(3).
[6]李菁.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7]刘明东.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用分析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1,(1).
[8]陈冰飞.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用理据[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马安东,王维贞.日语会话中省略现象的语用分析——利奇会话原则的运用研究之一[J].外语教学,2002,(1).
[10]周刚.汉语“离”和日语“から”“まで”的认知模式和语用特征之对比[J].对外汉语研究,2005,(1).
[11]崔昆.日语寒暄语的语用研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2).
[12]胡璇.从关联理论到“广义认知语用学”——近20年国内认知语用学研究回顾与思考[J]. 外语学刊,2013,(3).
[13]何自然.推理和关联——认知语用学原理撮要[J].外语教学,1997,(4).
[14]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3).
[15]孟建钢.关联理论对翻译标准的解释力[J].中国科技翻译,2001,(1).
[16]郭鸿.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同源和互补性——从现代西方哲学和符号学角度作出的解释[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1).
[17]巴拉.认知语用学:交际的心智过程[M].范振强,邱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18]王寅.新认知语用学——语言的认知-社会研究取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1).
[19]曾文雄.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J].社会科学家,2006,(5).
[20]黄家修,谢宝瑜.翻译的原则与词语的引进——从语言学角度谈翻译中的表现法选择[J]. 现代外语,1990,(2).
(李梓嫣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