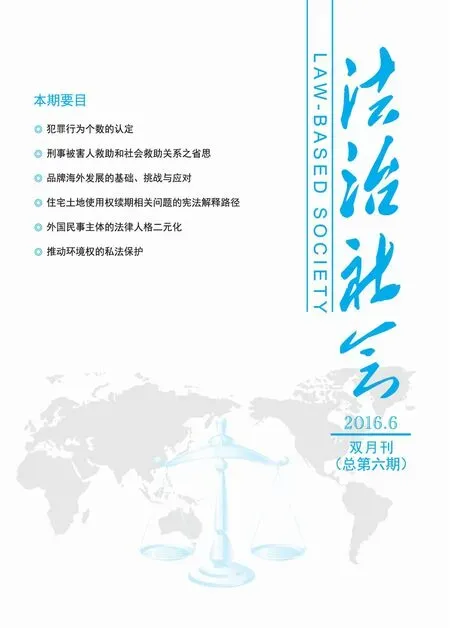施塔姆勒对编写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启示
——评《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新译本
姚 远
施塔姆勒对编写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启示
——评《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新译本
姚 远*
《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在课程设置的自我证成和融会贯通的叙述方式两方面,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的编写带来重要启示。以罗马法继受过程及其在法律实务中引发的(有时显得颇为琐碎的)新问题作为全书切入点,从而建立起法律思想史叙事的本土经验基础以及当代相关性;提示我们完全可能且有必要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学与西方法律思想之间的详细互动、彼此传承和深度辩驳;暗示西方法律思想史要与法理学乃至部门法课程形成“由史入论·史论结合”的内在关联。全书叙述对象虽然始于启蒙时代,但在各章节有机整合了古希腊、古罗马和《圣经》支配时代的法律思想,能够从核心问题意识的视野,将每个流派及其社会制度背景呈现为某种可加以把握的文化整体,做到“简约而不简单”。
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
施塔姆勒(Rudolf Stamm ler,1856-1938)是新康德主义法学派宗师,亦被视为二十世纪自然法复兴运动的重要源头,塑造了欧陆法哲学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面貌。拉斯克(Emil Lask)、康特洛维茨(Hermann U.Kantorowicz)、德尔·韦基奥(Giorgio del Vecchio)、拉德布鲁赫、凯尔森、吴经熊等人,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承袭了施塔姆勒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要素。施塔姆勒的学术成果蔚为大观,既有偏重实务方面的,例如《学说汇纂实务训练入门》《法学阶梯实务训练入门》(后更名为《罗马法课题》)《债法总论》《民法训练入门》《民法实务进阶》等,也有偏重哲理层面的,例如《论历史法学的方法》《从唯物史观论经济与法》《正义法的理论》《体系性的法律科学》《法律科学的理论》《现代的法理论与国家理论》《法与教会》《法哲学教科书》《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等。其中,《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是施塔姆勒晚年代表作之一,笔者应邀在民国学者张季忻的译本基础上重译此书,①参见[德]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收入吴彦主编“自然法名著译丛”。民国译本参见[德]司丹木拉:《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张季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期待它成为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重要教学参考资料。本文主要关心这部著作因其自身特色而带给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编写的两点关键启示。
一、课程设置的自我证成
西方法律思想史教学活动在当代中国的开展,始终伴随着一个时而凸显、时而又被遮蔽起来的根本难题,即课程设置的自我证成。换言之,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去教授和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产生该难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我国法学界如今越来越强调鲜明的“中国问题导向”和“本土经验导向”,即所谓经世致用,因而纯粹抱持文化比较兴趣、历史考古兴趣和抽象思辨兴趣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学空间受到严重冲击和挑战;(2)西方法律思想史因为打着“西方”的旗号——在课程设置上,“西方”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因此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一般不讨论马克思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家——在意识形态色彩尚未足够淡化的时代自然承载着某种异端身份,进而遭到政治漠视甚或政治排挤;(3)我国主流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学内容设计和教材编写模式,不仅严重脱离日新月异的法律实务和令法科学生魂牵梦绕的司法考试,也严重脱离宪法、民商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国际法等专业核心课程,甚至与同属理论法学阵营的法理学之间亦欠缺清晰可辨的内在关联。现有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虽然经常在引言或概论环节触及上述难题,但诸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之类的口号恐怕不能使这门课程获得足够的正当性。
相形之下,《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似乎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提供了自我证成的崭新可能性。首先,施塔姆勒并没有从古希腊哲学乃至荷马史诗开始书写,相反,全书开篇第一句话是:“罗马法之继受,向法学提出了若干新问题。”②[德]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页。他进而明确主张:“我们这里联系启蒙时代的实务法学所考虑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以及一切时代都有重要意义……当时的精神态度尤其在司法案件的处理方面表现出两种动向:(1)尽管表面上得到公认权威意见的支持,案件的判决却造就了新的法律制度;(2)各法院对旧法的规定作出解释,使其意思契合于当时的法律创制。”③参见前引②,第2页。在第一章的结尾他又提到:“批判地考察启蒙运动时代以来各地法院实践中出现的那种根本趋势,引出了为数众多的有趣问题,但我们若要在这些问题上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务必更加入木三分地探究这些问题。在阐发我们主题的过程中,有必要藉着法哲学的省思刨根问底。”④参见前引②,第12页。他以罗马法继受过程及其在法律实务中引发的(有时显得颇为琐碎的)新问题作为全书切入点,既为了屏蔽罗马法在中世纪欧洲数百年间的衰颓以及由此造成的法律发展断裂,也为了建立法律思想史叙事的本土经验基础以及当代相关性。诚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言:“把法律单纯视作伟大的人类学文件并按此立场研究法律,完全恰如其分。我们不妨通过法律来查明如下事情:哪些社会理想强盛到足以达成其最终表达形式的地步?各种主流理想随着时代更迭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在研究法律时,不妨将之视为关于人类观念的形态学演练和转型过程演练。”⑤参见OliverWendell Holmes,“Law in Science and Science in Law”,in Harvard Law Review,Vol.12,No.7,1899,p.444-445.
其次,施塔姆勒把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学法学”的前奏,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纳入西方思想大传统,并根据新康德主义者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在《唯物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批判》(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und Kritik seiner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中的观点审视马克思的方法论预设,认为唯物史观没有深入探究“法的概念”这一核心要素,因而在理应投以关注的“根本正义”问题上没有足够发言权。这样的商榷颇有一厢情愿的味道,似乎不以新康德主义偏好地方式关注正义就约等于没有关注正义,但其中透露的动向值得我们深思。由于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暂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法学视为西方智识发展历程中的普通环节,但我们完全可能且有必要在考察西方法律思想的每个阶段、每个流派、每个人物时,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它们之间的详细互动、彼此传承和深度辩驳,而非在话语体系和论证进路上各说各话,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对西方法律思想做出大而化之的粗糙批判。这实际上对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的编写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保持我们意识形态活力的必然要求。
最后,施塔姆勒将法律思想史视作法哲学(含部门法哲学)的历史引言,具有某种软化和先导的旨趣,其效果是使得自己的法哲学体系(包括方法和问题)不至于给读者带来横空出世的唐突感,可比之于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和《逻辑学》的关系。⑥施塔姆勒的写法当然难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那些不符合法理学逻辑的东西往往也就成为不在场的、被遮蔽的东西。这是哲人的思想史,不是史家的思想史。这样的思想史是否可取、在什么意义上可取,直接涉及思想史本身的元问题,学术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笔者倾向于将施塔姆勒的叙事手法视为法哲学思维的自我规训术和助产术。这就提示我们,西方法律思想史不是自给自足的研究领域,而要与法理学乃至部门法课程形成“由史入论·史论结合”的内在关联。我国学界已有这种课程定位的成功先例。同属具备教材性质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作品,张文显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拥有相对深远的学术影响力,⑦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下篇分为“法的模式(要素)”“法律与道德”“法的效力”“守法与违法”“责任与惩罚”“权利和人权”“自由、平等与法律”“表达自由”“正义”“法治”等章节。试比较关于相似主题的另一部名著,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笔者看来一个主要原因是该书“下篇·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重大理论热点”部分在国内率先将法理学的问题意识明确注入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从而使得二者相得益彰,令法理学体系的主要知识点获得直接的思想史支撑,令西方法律思想史成为法理学的鲜活历史注解。
二、融会贯通的叙述方式
如前所述,《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的讨论范围始于“启蒙时代的德意志法学家”,乍看之下,古希腊、古罗马和《圣经》支配时代(尤其中世纪)共计两千余年的法律思想进化都被排除在外,显示出漠不关心本源的态度。但实际上,施塔姆勒并不忽视这些基本思想源泉,而是采用了融会贯通的叙述方式。就古希腊而言,施塔姆勒结合“自然法”谈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vs实定正义”二元论,谈到斯多葛学派关于一切皆顺应自然的哲学信条;结合“理性法”谈到“概念”和“理念”这对基本思想范畴要追溯到希腊哲学,谈到莫尔构思的“乌托邦”不可能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以及该论断的文本依据;结合“法律经验主义”谈到皮浪的怀疑主义,谈到卡尔涅阿德斯以正义为主题的两场自相矛盾的公共演说,谈到苏格拉底所发现的对特殊具体经验进行一致处理和把握的观念;结合“自由法运动”谈到柏拉图《政治家篇》和《法律篇》都告诉我们既要创设强行性规则,又要把对于根本正当原则的选择留给当事人自己,谈到柏拉图所言的勇毅美德实为追求正义的决心;结合“批判的法理论”谈到希腊人虽然掌握了“科学的概念”但未能进行充分阐发,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广义的伦理学,谈到他们那几乎不值一提的“技术性法学”,谈到柏拉图终究没有准确得体地界定何谓正义之本质;结合“法哲学的问题与方法”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客观正当的概念实为质的概念而非量的概念,谈到质料概念的古希腊渊源,谈到苏格拉底的劝诫“认识你自己”的真正用意。⑧[德]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14、25-27、80、100-101、104、107-108、124、127-128页。
就古罗马而言,施塔姆勒结合“启蒙时代的德意志法学家”谈到罗马法关于请求权让与、代理和情势不变条款的原初规定;结合“自然法”谈到罗马人具有把法律难题解析为简单要素并据以展开精辟分析的杰出禀赋,谈到古典时期的法学家能够在处理个案时始终关注基本法律概念,但他们的哲学完全承袭希腊,未能精益求精;结合“社会学法学”,以墨涅尼乌斯·阿格里帕(Mennenius Agrippa)在平民撤到圣山之际的演讲内容为例,认为自然科学至多只能为合目的性行动领域提供一种未必可资借鉴的比喻;结合“自由法运动”谈到罗马裁判官的职能、使命和运作方式,认为它并不构成现代自由法运动的样板,谈到罗马法所规定的免除欺诈责任之约定无效,还以罗马法向未成年人授予“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为例,谈到我们在法定时间问题上通常需要创设一般的拘束性规则,以便在特殊情形下允许例外,此外又谈到《十二表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认可,谈到几位特定法学家的法律解答权;结合“批判的法理论”谈到罗马人致力于建立实定法学,清晰地洞察无限繁多的法律素材,并凭借异乎寻常的直觉在法律论证中追求根本的正当性。①参见前引⑧,第4、14-15、53、94-100、104、108页。
关于《圣经》支配时代,施塔姆勒结合“启蒙时代的德意志法学家”谈到一所撒克逊法院在失踪者的宣告死亡问题上,参考《诗篇》里面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主张假设失踪者年满七十岁且尚在人世,则分三次传唤,若最终仍未到案则宣告其死亡;结合“自然法”谈到托马斯·阿奎那将实定法与自然法对立起来,自然法是永恒的神法藉以示人的形式;结合“社会学法学”谈到滕尼斯关于中世纪城市和现代都市的结构性质差异的经典论述;结合“法律否定说”谈到围绕基督徒法庭宣誓义务的争议,谈到先知以赛亚对正义的溢美称颂和对法律生活中投机取巧之人的严正谴责,谈到保罗关于顺服有权柄者的观念;结合“自由法运动”谈到《哥林多前书》以来关于不得侵犯善良风俗的古老风范;结合“法哲学的问题与方法”谈到《诗篇》的“法必将重归于法”,谈到《旧约》借助直接的神启来解说律法的实定内容。②参见前引⑧,第3、51-52、56-57、133、135-136页。
施塔姆勒叙述方式的融会贯通之处,也表现在他冲破了原子式的点对点思想史人物书写,③值得一提的是,韦恩·莫里森虽然表面上也大都采用原子式的点对点思想史写法,但各章之间其实具有非常鲜明且彼此渗透的核心问题意识。参见[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按照流派来安排写作体例。不仅如此,他还能够从核心问题意识(crucial question-awareness)的视野,将每个流派及其社会制度背景呈现为某种可加以把握的文化整体(“点”“面”相结合④要真正做到思想史的“点”“面”结合是极其困难的,不仅要兼顾同时代的次要法律思想家、制定法和判例,甚至要兼顾神话、诗歌、民谣、传奇、小说、戏剧、史书、日记、笔记、书信、铭文、演说甚至器物、服饰、仪式、风俗等直接或间接传达出来的法观念。就此而言,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堪为楷模,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于是,流派内部的纷争体现为回应核心问题意识的不同方式,流派之间的差异则体现为所设定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差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施塔姆勒不是单纯地为思想史而思想史,他开篇即确立了属于自己的始终如一的核心问题意识,凭此澄清每个流派、每位思想家的立论前提并划定其适用限度,此正是一切新康德主义者的敏锐和精微之处。⑤例如凯尔森纯粹法学对埃利希法社会学的批判,参见[荷]科林克:《法律、国家与社会:埃利希vs凯尔森》,姚远译,载《民间法》2011年卷,济南出版社2011年版。施塔姆勒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如何科学地界定何谓根本的正义,以及如何达成应对具体法律问题时的方法一致性。“但凡哲学的讨论,都要求准确考察正确的提问方式和根本的论述方法。”①[德]施塔姆勒:《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2页。亦参见姚远:《施塔姆勒是自然法学家吗?》,载《人大法律评论》总第2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这种掷地有声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在当代流行的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中不甚明显和充分,时而被一种同情的理解姿态所掩盖。
当然,这里面的功过得失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我们用了至少20年的时间,才从原来那种纵横捭阖、难免失之笼统的、所谓“脸谱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方式,推进到年轻一代之中方兴未艾的紧贴文本、凭靠细致梳理和驾驭庞大史料的精深考据。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所限,后者又极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乏味境地。施塔姆勒汇积一甲子之功,凭借由此铸就的深厚学养撰写《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或许更臻于“简约而不简单”的境界,堪为未来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编写之典范。毕竟问题和方法相对于细碎的知识点而言,更加令人受益终生。
(责任编辑:卢护锋)
《法治社会》约稿函
《法治社会》是广东省法学会在长期编辑出版《广东法学》内刊基础上创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理论刊物,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广东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广东省法学会主办。《法治社会》国内统一刊号:CN 44-1722/D,双月刊。办刊宗旨为: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及时报道广东及全国法学法律界最新研究成果,传播最新法治信息,交流最新学术思想,促进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为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广东服务。
欢迎广大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惠赐稿件。凡赐稿者敬请遵循以下要求:(1)杜绝抄袭,不得涉及国家机密和知识产权争议问题。(2)不得一稿多投,凡于3个月内未接到本刊采用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对来稿原则上不退还。(3)文责自负,所发表的文章仅反映作者本人的观点,并不必然反映编辑部的立场,但编辑在保持作者原稿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有权对文章作文字性修改、删节。(4)稿件正文以8000字以上为宜,重大选题稿件可适当放宽篇幅。正文前须附3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及3至5个“关键词”。(5)注释采用注脚,全文连续注码,非引用原文者,注释前加“参见”,引用资料非原始出处者,注明“转引自”。(6)稿件须有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职务)、学位、工作单位、研究领域或方向及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文稿获得研究项目资助或属于课题研究成果的,请特别注明。
本刊对所发表的文章享有两年专有使用权,包括以文集、繁体文、电子文等出版发行,其期限从稿件正式发表之日起算。作者有权使用该文章进行展览、汇编或展示在自己的网站上,可享有非专有使用权。文章在本刊发表后,凡获奖、转载、被收编的,请及时将信息反馈本刊编辑部。
投稿邮箱:fazhishehuibjb@163.com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500号广东警官学院教学楼四楼(广东省法学会《法治社会》编辑部)
邮编:510230
《法治社会》编辑部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是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