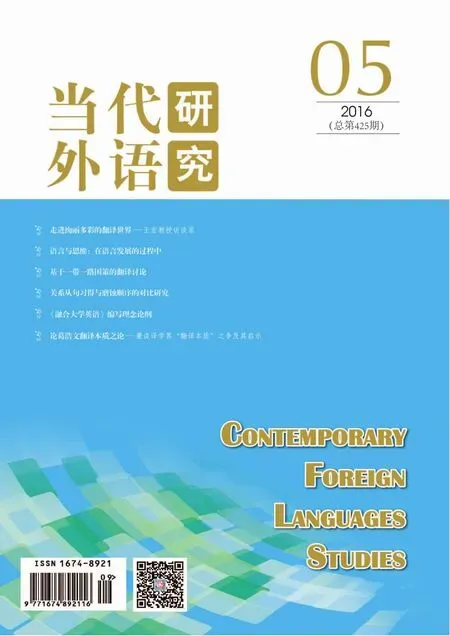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
——王宏教授访谈录
刘性峰 王 宏
(南京工程学院,南京,211167;苏州大学,苏州,215006)
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
——王宏教授访谈录
刘性峰王宏
(南京工程学院,南京,211167;苏州大学,苏州,215006)
本文是对王宏教授的访谈录。访谈从王教授与翻译的结缘谈起,并结合其翻译与治学的经历,针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典籍英译和汉译英能力等话题展开讨论。这些深刻见解对当下的翻译研究、典籍英译,以及青年译者和学者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翻译,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典籍英译,汉译英能力
刘性峰(以下简称“刘”):您好,王教授,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访谈。我们都知道,您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典籍英译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您主持翻译的多部中国典籍作品被《大中华文库》收录,有的还在国外出版,直接与海外读者“见面”,这对探索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传播途径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请问您是怎样与翻译结缘的?
王宏(以下简称“王”):我自幼喜爱文字,我母亲是一家省级报社的编辑,一辈子做文字工作,可能我的基因里也有这偏好。我最早与翻译结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武汉大学英文系的一名研究生。有一天我去武大图书馆读书,读到一本英文原版书,题目是The Art of Being A Woman,当时就觉得书的选题很好。当读到作者在“前言”里写的一句话“The sole purpose for th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s to light the fire in the darkness”(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黑暗中点燃光明的火焰),青春年少的我更是有了一种冲动,想把全书译成中文,让更多的读者读到此书。于是我复印了全书并把前言、目录和第一章译成中文投寄给国内数家出版社。没想到,果然有四川文艺出版社表示同意出版。我花了大概一年时间才译完全书。后来该书取名《女人的奥秘》,于1988年正式出版。顺便说一下,虽然出版社给的稿费只有每千字30元,但当时国内物价低,我得到的数千元稿费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从1988年到2000年,我陆续出版了九部译作,多为古典文学作品英译汉,比如《走进迷宫》、《死者为王》、《茅屋》、《大教堂》、《坚贞不屈的亲王》、《布赖顿硬糖》、《金银岛》等。此时,翻译仍是我的副业,我研究生学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后来去英国留学,学的是语言学。我曾在西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执教,教的课程都是文学和语言学。1996年我调入苏州大学,仍主讲《普通语言学》。
刘:那您是什么时候正式把翻译作为您的专业的?
王:2002年,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了加强学院的翻译队伍建设,把我正式调入翻译系和翻译研究所,翻译才正式成为我的专业。我的兴趣也转向汉译英,特别是苏州地方文化英译、中国典籍英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我最早是与汪榕培教授一起从事苏州地方文化系列英译,如《吴歌精华》(2003)、《苏州古典园林》(2004)、《昆曲精华》(2006)和《昆剧》(2004)。后来,从2004年到2012年,我参加了国家出版重大项目《大中华文库》,相继出版了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墨子》、《梦溪笔谈》、《山海经》、《国语》和《明清小品文》等。
刘:您后来的翻译作品都是汉译英吗?
王:不是。我依然从事英译汉。汉译英和英译汉我都热爱。从2006年到2016年期间,我出版的英译汉作品有《变形记》(2006)、《辛普森夫人传记》(2007)、《威廉王子的王妃》(2009)、《刺杀希特勒》(2009)、《我是麦莉》(2009)、《戈登·布朗:过去、现在和将来》(2009)、《民主与教育》(2012)、《人类的故事》(2013)、《民主与教育》(2015)、《房龙地理》(2016)。当然,翻译成为我的专业以后,我更关注翻译理论,结合所读翻译理论以及自己的翻译实践,有了一些自己对翻译研究的看法和认识,发表了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
刘:您刚才提到对于翻译的看法。我们都知道,翻译的属性、种类和过程都异常复杂。理查兹(I.A.Richards)说过,翻译“很可能是宇宙演化过程中迄今为止产生的最复杂的事件”。您既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又有深厚的理论涵养。您现在如何看待翻译?
王:翻译的确极为复杂。但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属性的语际翻译而言,其复杂性就源自原文与译文之间、译文与译文之间、作者、译文发起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译文审核者之间的多重需求和矛盾。要在诸多矛盾体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极为不易,实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刘:的确是这样的。王教授,您曾多次提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这一提法比较新颖,能请您详细谈一下您的观点吗?
王:我曾把具有跨语言、跨文化属性的翻译行为细分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王宏 2007)。我提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更多的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意图为起点,受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等所制约的语言转换。这种翻译要以原文为对照,受原文文本限制,这类译文“既要经得起读,又要经得起对”,如科技、法律文本的翻译、参赛译文等。“宽泛意义上的翻译”更多的是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等所制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与原文文本相比,此类翻译在内容、长度、文体、语气等都可能有相当的变异,如某些文学体裁、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划分,是由于我看到译界“文化学派”和“语言学派”的分歧多源于对翻译属性、范围和过程等不同理解。译界同仁都在谈翻译,而往往是各执一词,所指各不相同。
刘: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侧重于语言转换的高度对等或相似,同时兼顾原作和作者的意图、译文读者、翻译目的与译入语文化。而“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则以译文读者、翻译目的以及译入语文化为主要参照系,语言转换可以有更大的灵活度。
王:是这样的。
刘:您还提及要从哲学高度认识翻译研究,您能否谈一下为何要从哲学高度研究翻译?以及如何认识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王:好的,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有意义。其实,所有学科最终都需要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认识,翻译学也不例外。这要从哲学的主要问题谈起,柏拉图、奥威尔、笛卡尔和洪堡特等都有过疑问。柏拉图曾发问:人为啥知道得那么多?奥威尔想知道,人为啥知道得那么少?笛卡尔则问道,我们怎样解释那些超越自身认识范围的奥秘?洪堡特的疑问是:人的知识是怎样构成的?柏拉图和奥威尔的疑问看似对立,其实不然。前者是指人类的认知潜能是无限的,后者则指与浩瀚宇宙相比,人类的认知具有相对有限性。以上问题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了哲学理据,比如,翻译的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的对等与差异等。关于如何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翻译研究,这要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展开。
本体论(ontology)一词由17世纪的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Goclenius,1547~1628)首先使用。此词由ont(vt)加上表示“学问”、“学说”的词缀——ology构成,即是关于ont的学问。ont源出希腊文,是on(v)的变式,相当于英文的being;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所说的“存在”。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主要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认识论(epistemology)则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方法论(methodology)指导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如果世界观主要解决的是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
刘:听上去有些深奥!请您结合翻译研究具体谈一下好吗?
王:好的。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翻译本质属性、研究对象、特点规律与学科归属的明确与认识是开展翻译研究的基础,也是进而确立翻译研究独立学科地位的前提,这些恰恰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实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让语言文化不同的双方交流信息,沟通心灵,增进了解,促进进步,这就需要方法论提供相应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技巧。
何为翻译研究本体论?我认为,翻译之在即翻译活动,翻译活动即翻译之在,这两者原本等义。翻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人类“生命—精神”的活动中显现其身。人类“生命—精神”的活动是翻译作为一种对象存在的终极根据,对此所做的形而上学研究就是“翻译研究本体论”。本体论的定位促使翻译形成相应的研究谱系:如对翻译所做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学术视角指出了翻译活动不同的存在本质)。我们还可转入翻译活动本身,关注其生成机制、操作表现、运作方式、过程效应及其价值意义等。因此,翻译研究本体论的构建乃是把“跨语言、跨文化活动”作为翻译生态的根本性存在,并由此形成丰富的“活动研究系列”,用以完成对于翻译的最后体认。“何为译?”是所有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认为,各种有目的的翻译活动,各种形式的译本(包括全译、摘译、节译、编译、改译甚至伪译)都可以成为翻译研究的对象。翻译研究范围的扩大开拓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加深了我们对翻译本质和属性的认识。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何在译、译何为、为何译、如何译”等多个层面,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涉及翻译研究的过程认识论、主体认识论、相应方法论、目的论与批评观等。翻译研究认识论主要围绕能否认识翻译以及如何认识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问题而展开,涉及翻译的研究对象、特点要求、原则标准与认识维度等。翻译研究方法论则应为翻译理论探索与翻译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可供参考与借鉴的方法。翻译研究目的论主要解答为何要开展翻译与翻译研究,为何需要翻译的问题。
刘:您从哲学高度的阐释使我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您曾说过,翻译研究的许多课题可围绕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开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关系呢?
王: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研究很好的切入点,究其实质,翻译理论多是依据这个论题展开的,尤其是翻译定义、翻译策略、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等。许多翻译理论家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有过阐述,并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一种理论偏向于“相似说”,即译文屈就于原文,以原文为主,考察译文与它的相似度;另一种理论以描述翻译学为代表,其研究偏重于目标文本及其在目标系统中的位置。Toury(1995:136)明确建议从译文出发展开分析而不是从原文出发,并由此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单纯地比较不同的译本,或者对译本与目标系统中的非译本进行比较。Toury这种同传统研究正面抵触之举使他成了同时代惊世骇俗的革新者。
英国翻译理论家Chesterman(1998:7-23)认为,可以从相似性(similarity)的角度来理解原文和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两种相似性:第一种叫“发散式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他将其示意为:A → A’,A’’……。这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从源头导向目标的方向性,就仿佛由父母遗传给子女那样,其中蕴含的因果关系是无法颠倒过来的。第二种相似被称为 “聚合式相似(convergent similarity)”,Chesterman示意为:A ↔ B。它反映的是译本接受者观照翻译的方式,接受者都期望在A中所寻求的东西在B中同样能够找到。“Friday the thirteenth”和“martes 13”的关系就属于这种相似。
刘:除了相似之外,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是否还有对等和变异关系?
王:Kade在多年前就思考过对等问题。他认为,词或词组层级的对等有四种类型:“一对一(one-to-one)”,如固定术语的翻译;“一对多(one-to-several)”,译者须在若干备选方案之间进行选择;“一对部分(one-to-part)”,即可用的等值对象只能达到局部的匹配;“一对零(one-to-none)”,译者必须新创一个解决方案(杜撰新词或者借用外语词)。Kade将“一对一”的对等关系称为“完全对等(total equivalence)”,他认为专业术语的翻译是这类对等最典型的例子(以上转引自Gentzler 2001: 67-68)。需要说明的是,Kade所说的完全对等所涉及的决策过程与其说同翻译行为相关,不如说同术语学和措辞法相关。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显然是双向的:我们可以将A语言译入B语言再回译成A语言,它与自然对等的理想相符。然而,一对多和一对部分的情况在实践中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我们无法保证通过回译能够再回到最初的原点。显然,对等理论均以两种翻译方式的对立为基础,它体现的思维模式是二元对立的。
研究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必须要研究其彼此在意义上对等与差异,在形式和神韵上相似与变异。所谓意义对等,多数只能是相对而言。所谓形似,是指译文的表达形式和手段与原文相似。所谓神似,是指译文表达的风格、内涵、意境、气势、情调等与原文相似。对于如何处理形式和神韵的关系,古人早就表明各自不同的取向。范缜(约450~515)在《神灭论》中曾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西汉《淮南子》的“君形者论”则强调“神”对“形”的主宰作用,主张神贵于形,形受制于神。翻译中要达到神形兼备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曾提出,在形神不冲突时,应首先考虑形似,神以形存;在形神冲突时,则需要舍形求神(王宏 2012a:xvi)。我认为,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有:意似形似神似(内容忠实、形式相似、效果对等)、意离形似神似(内容不忠实、形式相似、效果对等)、意似形离神离(内容忠实、形式不相似、效果不对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刘:谢谢王教授,刚才您详细谈论了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令我受益匪浅。翻译研究关注的另一个维度是否是译者主体性?
王:翻译研究除了关注原文与译文、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之外,还需关注翻译过程中诸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所谓诸者就是原作者、译文发起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译文审核者等。译者无疑是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员。译者主体性指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之一在尊重翻译客体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创造意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主要有三种: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他们是阅读的主体。作为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对翻译的总体把握和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上,包括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语言转换的艺术、翻译目的的定位和由此带来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取舍等。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我们既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也要关注译者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传统翻译研究只注重探索语言转换层面的活动,认为翻译没有创造性,要求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并对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致使译者处于尴尬的地位。这导致译者地位的边缘化。美国翻译理论家Venuti(1998:4)撰写的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一书,就描述了当代英美译者是如何受到学术界的藐视和出版商的剥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窘境。
我曾撰文指出,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一方面,要作为肩负特殊使命的读者去理解原作和原作者;另一方面,他又必须作为阐释者,通过语言转换,让原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王宏 2011)。由此看来,翻译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译者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不少翻译理论研究者对译者的主体性加以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受重视程度大大加强。
刘:是不是我们可以说,译者主体性与您提出的“严格意义的翻译”和“宽泛意义的翻译”也有关联?
王:译者在从事严格意义的翻译时,只能有限度地彰显其主体性,有限度地去调控文本,比如,译者可以决定译文语气的轻重、译文的显形与隐形、译文词语的选择(褒贬)、译文语域的选择(雅俗)、译文的归化、异化或杂合化等。译者还可以决定译文的透明度、冗余度、结构、语域、褒贬等。只有在从事宽泛意义的翻译时,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从事严格意义的翻译时,译者需要尽量抵制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对翻译的操控,尽力向原文文本靠拢;从事宽泛意义的翻译,译者则需顺应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等对翻译的操控,与原文文本拉开距离。
刘:您能举例说明吗?
王:比如,《西游记》被亚瑟·韦利译为《猴》(Monkey),于1942年由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译本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多次再版。韦利实际上只选译了原书的第1至第15回、第18至19回、第22回、第37至39回、第44至第49回、第98至100回,共30回。其译文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等方面有明显的变异,可视为宽泛意义的翻译。再比如,林纾自己不懂英文,他的小说翻译都是先由一位懂英文的助手口述故事情节,再由他妙笔生花而成。
刘:通过您的阐释,我们对“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与“宽泛意义上的翻译”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王教授对翻译教学有何看法,也请您谈一下。
王:我认为,翻译教学必须注重学生实际翻译能力的提高。翻译能力与双语能力密切相关,但也有区别。学生对原文的理解错误以及译文表达失误均属双语能力不足,而不是真正的翻译错误。学生对翻译策略、原则、标准的应用不当,表达时的选择不当才是翻译错误。
刘:学生的翻译能力是翻译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通过翻译教学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呢?
王:是的,目前不少专家学者对翻译专业(MTI)学生的翻译能力表现出很大的担忧。我们必须对MTI的翻译教学进行反思和改革。我们(王宏、张玲 2016)提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革。首先,必须改革教学方法,适应社会对职业翻译人才的要求。其次,必须改革教学内容,变词句对比为篇章分析,把教学视角从以句子为中心的翻译模式转移到语篇翻译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对语篇整体把握的意识和能力。最后,必须重视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语料库和翻译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给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带来了挑战和变化,必须做出调整顺应这种变化。
刘:您提的这些建议很具启发意义,值得高校相关部门和教师参考。我们还想请您谈一下与中国典籍英译相关的话题。能否请您就典籍英译的定义、分类谈谈您的看法?
王:谢谢。关于中国典籍英译的定义,我在2009年主编的《中国典籍英译》一书中有过探讨。我认为,“中国典籍”可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所谓重要文献和书籍是指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典籍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典籍英译时,不但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要翻译中国古典法律、医药、经济、军事、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的作品。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长河里,其他少数民族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拥有自己的典籍作品。因此,我们不仅要翻译汉语典籍作品,也要翻译其他少数民族典籍作品。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完整地翻译中国典籍作品。中国典籍英译分类不一。根据原作的语言,可以分为汉语典籍英译和其他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依据典籍内容,又可以分为文学典籍英译、哲学典籍英译、科技典籍英译和其他题材的典籍英译;根据翻译方式,也可以分为典籍全译本、典籍节译本和典籍编译本等。
刘: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典籍英译可谓成绩斐然,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
王: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存在的一些问题,我曾撰文进行专题讨论。我认为,目前译界学者典籍英译的理论研究多为微观层面,缺乏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建构和整体观照(王宏 2012b)。当然,近十年虽有典籍英译方向的一些博士论文出版,但是数量仍然太少。典籍英译的理论探讨可以借鉴现有的翻译理论、相关学科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但必须结合典籍英译自身的属性和规律展开。其次,就中国典籍的翻译实践而言,目前选材仍比较单一,译者过多关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较少关注古代科技作品和少数民族的典籍作品。就出版发行来看,目前仍缺乏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典籍作品绝大部分在国内出版,读者对象多为国内读者,这些译作很少“走出国门”,多为“自产自销”或“自产不销”,鲜为国外读者知晓。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探索中国典籍英译的对外传播与接受的有效途径,采取直接在海外出版发行的方式,或是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的联姻,这对中国典籍作品能否走向海外有着重要影响。我翻译的《梦溪笔谈》和《明清小品文》就是由英国帕斯国际出版社购买版权,在海外成功出版发行。要符合国外出版社的出版要求,除了译文必须是高质量,典籍的选材也非常重要。我翻译的《梦溪笔谈》、《明清小品文》、《墨子》和《国语》都是首次译成英文。试想如果我去翻译已经在海外有多个译本的中国古典小说、诗歌、戏剧等,我的译本就很难受到国外出版社的青睐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典籍英译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典籍英译是一项高投入、低产出的事业。现在从事典籍英译的译者多为“老教授”,年轻译者极少,这使得典籍英译事业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建议有关部门大幅提高典籍英译稿酬支付标准,高校职称评定要认可高水平的典籍英译译作,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学子投身到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来。
刘:您提到的这些举措如能落实,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典籍英译与汉译英能力密切相关,我们还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汉译英能力的?
王:译界同仁杨晓荣(2002)、马会娟和管兴忠(2010)等曾就汉译英能力进行过探讨。我提出将汉译英能力分为:(1)双语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汉语理解能力);(2)知识能力(百科知识、相关专业知识);(3)资料查询能力(利用网络资源查询资料的能力);(4)翻译技能(转换能力、选择能力、译文修订能力)(王宏 2012c)。英语表达能力具体分为:英语词语搭配能力、英语造句能力、英语语篇能力。翻译技能具体分为:转换能力、选择能力和译文修订能力。英语表达能力是从事汉译英实践的基石,转换能力是汉译英任务能否得以完成的条件。Pym(1992)曾将翻译能力简化为:(1)从一个原文生成为一系列译文的能力;(2)从一系列译文中选择一个符合翻译目的、适合特定读者的译文的能力。Pym对翻译能力的描述对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作为非英语母语使用者来说,要具备这样从一个原文生成为一系列译文的能力绝非易事,要掌握从一系列译文中选择一个符合翻译目的、适合特定读者的译文的能力更是难上加难。由此看来,汉译英能力与英语表达能力、转换能力和选择能力密切相关。除了转换能力和选择能力,对译文的修订能力也是英译文质量高低、得体与否的关键。
刘:通过您的阐述,我们对于汉译英能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看来要提高汉译英能力,进而承担中国典籍英译的重任,非下苦功不可。
王:确实如此。翻译的确非常辛苦。但正是由于人类语言、文化、思维、社会、历史等的不同,我们才透过翻译看到一个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的人类社会。《圣经》(1611年钦定本)译者在序言中对翻译所做的一番形象比喻:“翻译好似打开窗户,让阳光进入房间;翻译好似撬开贝壳,让宝物呈现眼前;翻译好似拉开窗帘,让圣洁之处得以展现;翻译好似揭开井盖,让甘甜的水滋润心田。”翻译是如此的美好、崇高!我们唯有坚持包容、开放、合作、共生的态度才能更好地走进这如此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提升自我,惠及大众。
刘:感谢王教授与我们分享这么多精彩内容!
王:谢谢你的采访。
Chesterman,A.1998.Contrastive Functional Analysis [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Gentzler,E.2001.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Pym,A.1992.Translation error analysis and the interface with language teaching [A].In C.Dollerup & A.Loggegaard.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Talent and Experience [C].Amsterdam & Philadelphia: Benjiamins.277-288.Toury,G.1995.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Venuti,L.1998.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马会娟、管兴忠.2010.发展学习者的汉译英能力[J].中国翻译(5):39-44.
王宏、张玲.2016.中国专业翻译学位教育:成绩、问题与对策[J].上海翻译(2):13-17.
王宏.2007.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J].上海翻译(2):4-8.
王宏.2011.怎么译:是操控,还是投降?[J].外国语(2):84-89.
王宏.2012a.走进绚丽多彩的翻译世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王宏.2012b.汉英能力构成因素和发展层次[J].外语研究 (2):72-76.
王宏.2012c.中国典籍英译:成绩、问题及对策[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9-14.
杨晓荣.2002.汉英能力解析[J].中国翻译(6):16-19.
(责任编辑管新潮)
刘性峰,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电子邮箱:oliverliu@163.com
王宏,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中国典籍英译。电子邮箱:hughwang116@163.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编号13BYY034)以及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英译诠释框架构建”(编号2016SJD740008)的资助。
H319
A
1674-8921-(2016)05-0001-05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