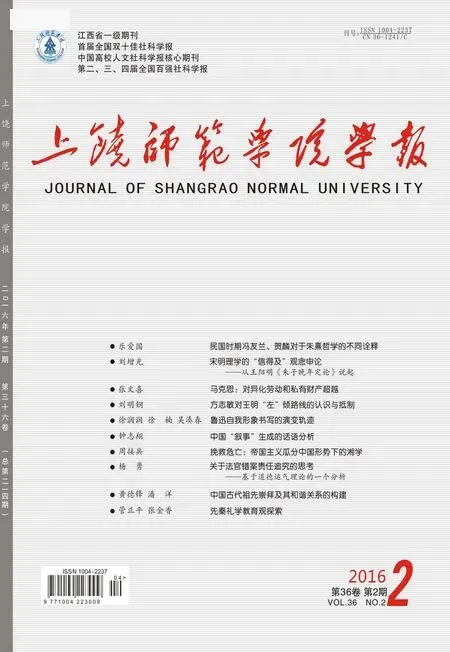论明代传记与话本中的徽商形象
张世敏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论明代传记与话本中的徽商形象
张世敏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明代的话本与传记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好名”的徽州商人形象,其徽商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天壤之异。话本中的徽商形象有好有坏,尤其是典商往往被贬为“徽狗”,与传记中的绝大多数义商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两者之间存在如此强烈的反差,除了文体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徽商到明代已出现分化。“徽狗”是对当时一部分不择手段的徽商的真实写照;提出“市义”主张,并为获利而施义,则说明徽商的经营朝着更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向在发展。
徽商;好名;义商;话本;传记
在明代社会转型与变革中,商业的发展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与明代其他方面的社会转型之间几乎都有关系,这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已形成共识。明代十大商帮中,徽商名气最大,也富有地方特色,以徽商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徽学”已成为当今的显学,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类成果之中,不乏对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徽商形象进行探讨与分析的论著。已有成果中有的以话本小说作为文献依据研究徽商形象①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令媛的《从“三言”、“二拍”、<幻影>看徽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5):34-38)、姜建设的《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南都学坛》,2003(6):70-74)、刘莉的《从“三言”“二拍”看晚明之徽商》(《山西大学学报》,2012(4):37-41)、刘艳琴的《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明清小说研究》,2004(4):142-155)、朱全福的《谈“三言”“二拍”中的徽州商人形象》(《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3):56-60)等。,有的以商人传记作为文献依据研究徽商形象②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耿传友的《汪道昆商人传记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论明清徽商传记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南京师大学报》,2012(2):129-135),王鹏的《徽州历史人物碑传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等。。
话本小说与商人传记中的徽商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文献中徽商形象截然相反的,以典当商人最为典型。两者之间的异同,值得学界给予必要的重视,其原因有二:第一,话本小说与传记中的商人形象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以“三言”与“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中的一些商人形象,便取材于文集中的商人传记。如《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义愤成家》的主人公阿寄,田汝诚在《田叔禾小集》中为其立有传记《阿寄》。又如《石点头》第4回《瞿凤奴情愆死盖》文末明言,嘉靖初年的孙汉儒为主人公孙三郎、瞿凤奴作有小传。阿寄与孙三郎的身份都是商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第二,将话本小说与传记中的徽商形象进行对比,可以使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与传记中的徽商形象成为彼此的参照,从而推进徽商形象研究。第三,通过分析不同文献中的徽商形象,可以避免研究视角的单一化,从而看到更加丰满、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徽商形象。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暂未有深入论述,故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传记与话本中“好名”的徽商
凌濛初对徽商有过一段堪称精辟的评价:“元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1]这句话点出了徽商在买官与买妾、青楼买笑时一掷千金的豪爽。不过,“其余诸事悭吝了”却不见得完全符合实情,徽商因“好名喜胜”,同样不惜一掷千金。徽商传记与话本小说对徽商的这个特点都有刻画。
1.传记的刻画
在商人传记中,徽商的好名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得到很好的说明。笔者在《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一文中,通过浏览“四库”系列丛书所收明中期的文集,共找出商人传记160篇①见笔者《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附录二《明中期文集中商人传记目录》。下文论及商人传记的篇目数量时,亦以此为据。,其中传主可确定是徽州商人的有99篇,占到总量的61.9%。在这160篇商人传记中,还有传主籍贯不明的传记10篇,若将其考虑在内,传主为徽州商人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明代中期兴起的商人传记,大多数是需要支付润笔费的请托应酬之文,徽州商人的传记占到总量的近三分之二,说明徽州商人与其他地区商人相比,明显更热衷于留名。
徽商好名喜胜除了可以用以上数据阐释外,传记中的具体文字也可以印证此说。金瑶《纪祁门李征君代偿事》一文,在开头部分即交待了李征君之子求文的过程:
万历甲申夏,予在南园楼下纪邵赠君焚券事……祁门县学诸生李子之华实,夫设帐余家川上草堂,见余纪,慨然对予曰:“予家君亦有代偿事可方邵,而数不及,予不才,未能请有纪,或遂至湮没,余愧矣。”[2]534
祁门县学李姓诸生见金瑶为邵赠君焚券之事作纪,其父李征君有代偿之事,与邵赠君焚券之事相类,李姓诸生认为如果不为其父所行善事作纪,让其父之名与善事一起湮没无闻,心中会有愧,好名之心溢于言表。以上数据与文字,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证明了徽商“好名喜胜”并非虚言。
2.话本小说的刻画
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在好名这一点上与传记中的徽商形象并无二致。前文说到,由于好名,徽商愿意支付润笔费请文人为其作传。传记中徽商形象超过一半,提高了文人对于徽商的关注度,明代的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据统计,‘三言’‘二拍’中描述的明代商人,共有63位,其中徽州商人就占19位”[3],占总数的30.2%。在“三言”“二拍”中,徽州商人所占比例虽然不如商人传记中高;但徽州地仅一州,无论是地域面积还是人口,占全国的比例都会远远低于30.2%,因此,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依然是非常高的。话本小说中徽商形象所占比重,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好名的徽商在明代文人那里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
徽商好名在话本小说也有记述,《初刻拍案惊奇》第24卷《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的入话部分,记载了一位徽州商人泊舟矶下,到弘济寺游玩,看到楼阁已颓败,徽商与寺僧聊起了修葺之事时,有一段对话:
寺僧便道:“朝奉若肯喜舍时,小僧便修葺起来不难。”徽商道:“我昨日与伙计算帐,我多出三十两一项银子来。我就舍在此处,修好了阁,一来也是佛天面上,二来也在此间留个名。”寺僧大喜称谢,下了阁到寺中来。[4]354
从徽商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愿意出30两银子修葺寺庙,一是因为看在佛面之上,二是想留名。接下来凌濛初发表了这样一段议论:“元来徽州人心性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崇信佛事。见这个万人往来去处,只要传开去,说观音阁是某个人独自修好了,他心上便快活,所以一口许了三十两。”[4]354在凌濛初看来,徽商出资修庙,最大的原因便是好胜喜名。
徽商好名,在商人传记与话本小说中,都有明确的记述;明中期的商人传记与“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在全部的商人形象中所占的比例都很高,正是徽商好名的结果。笔者认为,精明的徽州商人,为了扬名而愿意一掷千金,背后应当有进一步的商业目的,即以利换名,再以名换利,名是后文所要论到的徽商“市义”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的中介。
二、传记中的义商与与话本中的“徽狗”
在商人传记中,徽商大多以义商的形象出现,不过,从为数不多的几篇徽商传记中,未见传主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义行,但也没有恶行。在“三言”与“二拍”中,有一半左右的徽商形象是正面的,但话本小说也刻画了不少让人深恶痛绝的徽商,他们在小说中被称为“徽狗”。
1.传记中的徽州义商
明代中期文集中的商人传记中,共有99篇可以确定传主为徽州商人。这些传记中,只有盐商少有义行,其他如木商传记、丝帛商人传记等,几乎都载有义行,其中以典当商人传记最为典型,这与话本小说中让人憎恶的徽州典当商人形成鲜明对比。徽州商人施行义举的原因,主要包括积极“市义”与宗教信仰两个方面。
(1)积极“市义”
徽州文人金瑶在为徽商吴良玠所撰写的《吴畏轩君传》中,记载了传主父亲经商的事迹,言曰:“善权子母法,岁累月增,资产之富甲于东乡。然性重自爱,事从姑息。人瞰其然,有负多不偿。”[2]595由于行业的特征,经营子母钱难免会产生坏账,传主父亲又因性格之故,出现借钱之人多有不偿还债务的情况。这种现象在经营子母钱这一行业,并非个案,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关注。不过,吴良玠的父亲在临终前说过一段话,让这位商人与其他经营子母钱的商人之间,有了质的区别。他说:“取必于天,其为偿也,多矣。薛公市义而独不闻之乎。”[2]595话中的薛公,即孟尝君,其门客冯谖为孟尝君到薛地收债,焚券而归,谓之“市义”,“市义”之说可追溯到此。然而,在商人之中,将“市义”上升到经营理论的高度,就笔者所见,当自吴良玠之父始。提出“市义”,说明徽商已开始认真思考义利之间的关系,走在了其他地区商人的前面。“市义”一说,虽然仅见于《吴畏轩君传》,然而,其他徽商传记中记载的大量义行,可以说明掌握“市义”诀窍的,已非个别徽州商人。
徽商之所以愿意“市义”,是因为市义可以带来更加长久的利益,《东泉金处士传》中有一段文字对这个道理有充分的说明。典当商人金处士“出入增损,迄有定则,不为奸欺,虽五尺之童适市,而取与之数不爽也。故松人德处士甚殷,而处士之典至今不替益盛”[2]588,当其他的商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时,传主金处士仅仅是因为做到了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他所经营的典当之业因而长盛不衰。那么,如果能够主动“市义”,百姓感激商人的程度又将增加,当更有利于商业经营。在小说中,典当商人往往被刻画成贪得无厌、巧取豪夺之人,徽州的典当商人为了改变行业的不良形象,主动提出“市义”,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对此,徽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王廷元论道:“徽州典商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识到,上述昧心取利之法,固然可以称快于一时,但不能获利于长久。”[5]82
(2)宗教信仰推动的义行
徽州典当商人提出“市义”理念,并在经营中奉行此法,相对于刻剥的典当商人,无疑是进步的。但“市义”毕竟只是为了获得更加长远的利益,这两个字中透露出了商人的私欲,商人并不想把自己的义行说成是“市义”。因而,在明代中期其他的典当商人传记中,传主将施行义举的目的说透成“市义”的,除《吴畏轩传》之外,笔者不曾再见。
除了“市义”这一目的之外,徽商为义,往往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推动,徽商传记中的不少传主行义,与佛教、道教有密切关系。比如《汪处士传》中记传主汪通保所行义事时说道:
处士善施予,务振人之穷。举宗或不能丧,则置封域予葬地;不能举火,则置田予之租。出入遇僵尸,则属佣人瘗之,予之直。嘉靖中岁大旱,太守议发仓,处士则以不便于民,乃以策干太守……请易粟为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各输金以助,不足某请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民大称便。既而又就里中设糜粥饭饥人,上海亦如里中,中外多所全活。吴会洞经桥坏,费百缗新之。归则碣田、由溪各为桥,处士皆出百缗以倡义举。处士尝梦三羽人就舍,旦日得绘事,与梦符,则以为神,事之谨。其后几中他人毒,赖覆毒乃免灾。尝出丹阳,车人将不利处士,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觉之,处士自谓幸保余年,莫非神助,乃就狮山建三元庙,费数千金。[6]
汪通保梦到三羽人来就他家,早上获得一幅图画,与梦境相印证,使得他相信世间有神,并“事之谨”,由此可知汪通保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商人。此后在丹阳道中侥幸脱难,在汪通保的眼中,是有神相助,故舍数千金的巨款,在狮子山建三元庙。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汪通保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他所行义举,包括赈灾饭饥、棺敛尸殍、修桥铺路、修建寺庙等,“与《佛说诸德福经》中所谓‘七法广施福田’基本相合”[7]。
汪通保信奉宗教,其义举与佛教所倡义举相合,说明他施行义举正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推动。其他徽商传记中,不乏传主有与汪通保的义行相类者。如徽州商人王毓,王世贞在为他所撰写的《王樵云公传》载其义行曰:
公又好施予,以躯赴人之急,比邻火,数十百家皆烬。公指廪而予之俾,称力自取给。其它孤窭毋论疏戚,以指计衣食,视公若库庾也。[8]
传记中虽然没有说清楚,传主王樵云所行之义举,是否与佛教或道教信仰相关,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其所行之义举,与汪通保大致相当,而且与佛教的慈悲教义相合,因此也可视为佛教式义举。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知商人传记中所记载的徽州商人行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市义”,二是因为宗教信仰的推动。无论徽商行义的目的是什么,为传主的义行找到了可信的动机,就足以说明传记中所载传主的义行,基本是真实可靠的。传记中所刻画的徽商形象,至少在一定程度或者某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历史真实。
2.话本小说中的“徽狗”
“三言”与“二拍”中徽商形象,有将近一半是反面的,尤其是典当商人形象,几乎都是反面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卫朝奉是一名徽商,在南京开典当铺,小说描写卫朝奉之刻剥时写道:
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4]208小说讲述卫朝奉与陈秀才之间的故事时,卫朝奉表现出来的贪婪,基本上就是对这段文字的注解,难怪陈秀才会称其为“徽狗”。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薄》中有两位典当商人,一位是在浙江天台县城开典当铺的徽商金朝奉,一位是金朝奉的舅子程朝奉,两人同样让人厌恶。小说中,金朝奉因谣传选秀女,把女儿朝霞许配给穷秀才韩子文。得知选秀女是讹传后,嫌韩子文贫穷,有意悔婚。其舅子程朝奉来到浙江天台后,两人设计悔婚:
程朝奉道:“姊夫若是情愿把甥女与他,再也休题。若不情愿时,只须用个计策,要官府断离,有何难处?”金朝奉道:“计将安出?”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台州府举一状词,告着姊夫。只说从幼中表约为婚姻,近因我羁滞徽州,妹夫就赖婚改适,要官府断与我儿便了。犬子虽则不才,也强如那穷酸饿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亲笔婚书及女儿头发在彼为证,官府如何就肯断与你儿?况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姊夫真是不惯衙门事体!我与你同是徽州人,又是亲眷,说道从幼结儿女姻,也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钱使得鬼推磨。’我们不少的是银子,匡得将来买上买下。再央一个乡官,在太守处说了人情,婚约一纸,只须一笔勾消。剪下的头发,知道是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愿。既有银子使用,你也自然不到得吃亏的。”[4]143
程朝奉与金朝奉之间的对话,将典当商人的手腕显露无遗。知识的积累与智力的提升,使得他们可以自如地设计;巨额财富的积累,使得他们相信用银子可以“买上买下”,打赢官司。这两位财智兼具的典当商人,却无法赢得人们的好感,作者在故事末尾特意安排韩子文对程朝奉说“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来是不痛的”[4]148,当是有意安排的羞辱。
三、传记与话本中徽商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
商人传记与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截然相反的地方。话本小说与商人传记对于徽州商人“好名”记载完全一致,两种性质不同的文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本身就可以说明两者的记录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为义这一点上,商人传记与话本小说中对徽商的书写则有很大的差别。商人传记与其他传记一样,继承了史传贵信的原则,且在叙述传主义行时,部分篇章也交待了为义的动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其真实性作过多的怀疑。话本小说中的“徽狗”虽然只是虚构出的文学形象,但也能够从文学角度反映当时人们对于徽州商人的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种不同的文献中出现截然不同的徽商形象呢?
两者之间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原因之一是文体的差异。商人传记的作者在收取了传主后人的润笔费之后,理所当然地会为了钱财而在传记中为传主大唱赞歌,根本没有再把传主称为“徽狗”的可能。而话本小说与商人传记的最大差别是,话本小说并没有收取商人的润笔费,其所讲述的故事也只是艺术的真实,并不针对某一具体的商人,因此,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便可以塑造“徽狗”形象。
除了文体的差异之外,最根本的差异应当是徽州商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是非常复杂的,其丰富性难以被话本小说或商人传记某一种文体真实地、全面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与商人传记中的徽商形象,都只展现了历史中的徽商的某一个方面。话本小说中令人憎恶的“徽狗”,反映的是徽商落后的一面,清人程址祥就对徽州商人商人中的典商有过相似的评价,其言曰:“近来业典当者最多徽人,其掌柜者,则谓之朝奉。若辈最为势利,观其形容,不啻官长自居。言之令人痛恨。”[9]据此可知,话本小说中令人憎恶的徽州典当商人形象,大致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商人传记中所载商人的义行可分为两种,其中商人“碑传文中记录的义行绝大部分是在佛教信仰的推动下,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实,而不是为了‘谀墓’而杜撰的”[7]。为了“市义”而行义,其目的在于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其真实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商人传记展现了徽商进步的一面。
总而言之,话本与传记中的徽州典当商人形象都不是完全杜撰的,这说明徽州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出现分化。话本小说中的反面徽州商人形象是对大多数徽州商人的真实写照,传记中有义行的徽州典当商人的出现,尤其是基于“市义”理念所施行的义举,代表着徽州商人经营的新方向。
[1]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中华书局,2014:273.
[2]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的徽州商人形象[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8(3):56-60.
[4]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北京:中华书局,2014.
[5]王廷元,王世华.徽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82.
[6]汪道昆.太函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9.
[7]张三夕,张世敏.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与义举的关系[J].江汉论坛,2013(6):118-121.
[8]王世贞.弇州四部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8.
[9]曲彦斌.典当研究文献选汇[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032.
[责任编辑 邱忠善]
On the Images of Hui Merchants in the Biographies and Storyteller’s Scripts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Shi-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The biographies and storyteller’s scripts in the Ming Dynasty successfully depicted a lot of“well-reputed”images of Hui merchants.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among these images.In the scripts,the images of Hui merchants were good or bad,esp.,one called“Hui dog”,which wa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most images of honest Hui merchants.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images was attributed to the polarization of Hui merchants in the Ming Dynasties,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style.“Hui dog”was then a real portraiture of some unscrupulous Hui merchants.And the proposition of“market justice”and doing justice for benefit indicated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Hui merchants in accordance with economic laws.
Hui merchants;well-reputed;honest Hui merchants;storyteller’s scripts;biographies
I207
A
1004-2237(2016)02-0062-05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10
2016-03-30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WX23)
张世敏(1982-),男,湖南邵东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思想史文献研究。E-mail:zsmwz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