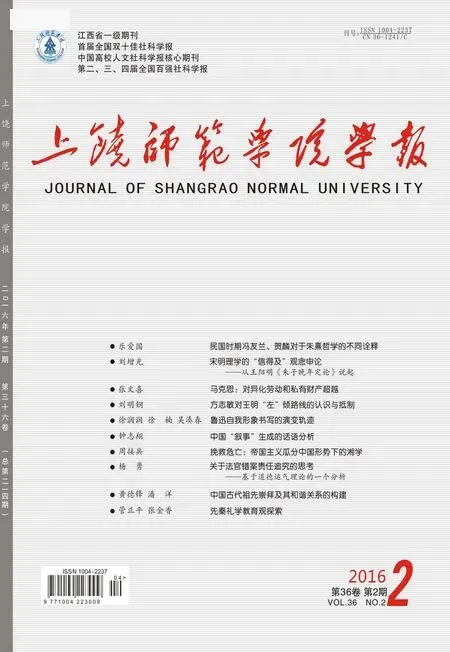宋明理学的“信得及”观念申论
——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说起
刘增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宋明理学的“信得及”观念申论
——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说起
刘增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信得及”是阳明学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构成了阳明学中最具特色的语丛。但是这一阳明学最具特色的思想命题实则发源于朱子理学,其文本证据就是王阳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此观念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做一探讨,正可作为阳明学以朱子学为基础而加以转进创新之一例证。同时,亦对理解宋明理学乃至儒家的“宗教性”不无裨益。
信得及;王阳明;朱熹;祁克果;宗教性
“信得及”是阳明学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在阳明学中又有“自信良知”“信得本体”“信得良知过”“信得性善及”等多种表述,其反面的表述则是“信不及良知”。与中国哲学史上的其他各家思想相较,这一观念可以说构成了阳明学中最具特色的语丛。虽然信得及良知的观念肇始于王阳明,但却并非为其后学各派所尽数认同,认同肯信者主要在现成良知一系,包括以王龙溪为主的浙中王学、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①关于阳明学中的“信得及”观念之研究,可参看任文利《“性善”作为信念——罗近溪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诠释》(见:吴光主编《阳明学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2-258页);吴震《传习录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131、152页);彭国翔《作为信仰对象的良知》(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80-91页)。。而归寂派、修证派儒者则对此观念多所怀疑、甚至反驳。本文欲指出的是,“信得及”这一阳明学最具特色的思想命题实则发源于朱子理学,其文本证据就是王阳明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对此观念从朱子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做一探讨,正可作为阳明学以朱子学为基础而加以转进创新之一例证。同时,亦对理解宋明理学乃至儒家的“宗教性”不无裨益。
一、《朱子晚年定论》与“信得及”观念
王阳明《传习录下》所附《朱子晚年定论》中载有朱熹《答梁文叔》一函,云:
近看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过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間見、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此外更无别法。[1]135
这段话中已有“信得及性善”(或“信得性善及”)和相对的“信不及”的说法。客观说来,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本不是在做文献学的纯粹客观的编纂工作,而是有意地“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朱子生平书信极为丰富,而他写给梁文叔的书信仅有四封,此封书信即是写于朱熹55岁时。这意味着,将这封书信视为朱子晚年所作,即使不是纯粹的“胡说”,亦是“美丽的谎言”。王阳明这样做,无非是暗示自己学说与朱熹并不相悖。而反过来说,朱子的这封书信中有王阳明所赞同的地方,或者说有可以借以阐发己说的地方。否则,朱熹之书信卷帙浩繁,他与吕子约、张栻等人之间的书信即非常多,王阳明何以独取朱熹与梁文叔之总计仅四封书信的其中一封?
《朱子晚年定论》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广泛,而受此影响最为深刻的当然属阳明后学士人。如王龙溪弟子周海门《与余太史云衢年丈》中言:“丈乔岳泰山,……惟向上一机犹然未信,昔晦翁直至晚年打破,吾丈得无有待耶?”[2]345此“向上一机”即“上达”“第一义”。龙溪的另外一位弟子张元忭称: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出,“而后考亭之学,其骨髓始透露于此。其拳拳于培本原、收放心,居然(李)延平之家法也,而后考亭之学始为质之濂洛而无疑。”[3]他取朱子《文集》中与陆学同调之诗,辑为“悟后诗”,与《朱子晚年定论》一同合刻为《朱子摘编》,说:“道一而已矣。学不会于一,非学也。是编也,岂独(朱、陆、王)三先生之学可会于一乎?千古圣学之正统,吾知其无三径矣,虽谓之儒宗‘参同契’可也。”[3]398
阐发阳明学“当下”论颇有心得的罗近溪弟子杨起元显然敏锐地看到了《朱子摘编》中《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他在评论《朱子摘编》之价值时,正是以朱熹的《答梁文叔书》为点睛之文,他说:
是编载《答梁文叔书》,云“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是第一义,若于此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引成間見、颜渊、公明仪之言教人,如此发奋,勇猛向前,此外更无别法。”此殆晦翁一生为学履历公案哉!观其平日研六籍,综百氏,强践履,勇担荷,便是何畏之間見、有为之渊,不欺之仪,胡以远过。迨其晚年翻然有觉,恍然自失,而曰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如此则知仁矣。又其诗曰:“惟应酬酢处,特达见本根”;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所谓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者非耶!然则后世尽心于圣人之道,而有始有卒者,朱子其人也,可为百世学者师矣。……盖自《定论》出而朱子之学不湮于传注,自《摘编》出而阳明之辑果得其精华,阳明有功于朱子,是编复有功于阳明……吾观是编,固可以无疑于传注之说,然所谓信得性善及为第一义者,则不可不以自考……[4]476
杨起元就将《答梁文叔书》中的说法概括为“信得性善及,直下便是”。其以此为朱熹“一生为学履历公案”“晚年翻然有觉”之语,更是与阳明“晚岁既悟之论”[1]128的说法一脉相承。逆而推之,不难想见,王阳明当初之所以重视此书,亦很可能是认识到了这一“思想的闪光点”。不妨先看看王阳明关于“信得及”“信不及”的相关论述: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1]109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1]93
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1]105
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1]116
依阳明之论述,其言“信得及良知”,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良知的遍在性和先验性。第二,良知即是圣,故而不论凡愚,既具良知,便有成为圣人的潜能。第三,从本体与工夫的角度来看,良知存在的本来性和先验性,“属于信念问题”,而良知在现实状态下被遮蔽则属于功夫问题。人只有坚定信念,则工夫问题便可随顺而解。这又被阳明称为合着本体的工夫,是“本体工夫”。在这三层含义中,不难看出,其中贯彻着“良知现成”或“见在良知”的观念。良知是每个人先天具有的,且在日用生活的时时处处都无不具有良知,圣人与凡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能以良知时时作为主宰这一点上。正因此,良知现成,也就意味着良知于当下便可呈现。若能反身体认良知,便能当下悟得良知。王阳明曾言:“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需要信得及,只是立志。”[1]32阳明的一个思路是,唯有信得及,方能真正地悟得良知,去做成为圣人的工夫。而《答梁文叔书》中所言“孟子道性善,称尧舜,是第一义,若于此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更无一毫人欲之私。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教人,如此发奋,勇猛向前,此外更无别法”[1]135一段所含之意,正可以说是:直下体认自心、自信本性之善,圣凡齐同。且不说第二节工夫,也与阳明学工夫与本体合一之说相贯通。据此可见,王阳明及其后学对于此封书信之特加留心,并非无由,实乃“于其心有戚戚焉”而然也。
那么,朱熹本人是如何理解“信得及性善”的呢?这与其天理观及格物穷理的工夫论有密切关联。
二、“知之深,方信得及”:朱子解《论语》“吾斯之未能信”
《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5]朱熹从格物穷理的角度出发,结合其知行观,对这段话“从信得及”的角度做了极为丰富又具启发性的解释。《集注》中言:“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6]
依此,朱熹之意是说,漆雕开未能信“理”,故而仍有“疑”处,因此不能出仕。那么,“此理”朱熹虽未明言,但当即是指天理。也即是说,天理是“信”的对象,是“真知”的对象。对于朱熹的这一解释,程树德《论语集释》认为《朱子语类》中说道:“斯有所指而云,若自信得及,则虽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朱子初意原以斯有所指而云,……不知何以最后定稿乃以理字释斯。然终属牵率圣言以就己说,非解经正轨也。”[7]程氏谓朱子以六经注我的方式解释此章,是“牵率圣言以就己说”,此属自然①孔安国注:“仕进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习也。”皇侃疏:“言己学业未熟,未能究习,则不为民所信,未堪仕也。一云:言时君未能信,则不可仕也。”韩愈《笔解》:“未能见信于时,未可以仕也。”可见,朱熹之前的儒者都未解以“理”字,都是从出仕之道上来说。朱熹则是以理解经。但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注释经典,是宋明时期的普遍方式,非惟朱子为然。诸家之注,载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97-298页。。而《朱子语类》中说的“乃有所指”其意也并不与《集注》相互抵牾。比如,《语类》中记载朱熹说:
或问:“‘吾斯之未能信’,如何?”曰:“‘斯’之一字甚大。漆雕开能自言‘吾斯之未能信’,则其地已高矣。‘斯’,有所指而云,非只指诚意、正心之事。事君以忠,事父以孝,皆是这个道理。若自信得及,则虽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强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须是自有所得无遗,方是信。”[8]639
曰:“‘斯’,只是这许多道理见于日用之间,君臣父子仁义忠孝之理。‘信’,是虽已见得如此,却自断当恐做不尽,不免或有过差,尚自保不过。虽是知其已然,未能决其将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8]642
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斯有所指”,正是指“道理”,如事君之忠、事亲之孝,仁义礼智信皆是。而一字以概之,便是“理”。漆雕开仕,自然涉及到了事君之理。揣摩文意,“有所指”是说,“斯”并非无意义之虚词,而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实词。而此所指又不能说是具体的事君或事亲,只能是一种本体论的指涉。宋明理学家皆谓道不可言,或性不容说。不可言、不容说,但仍然可以用形而下的词汇以有所“指”。此正犹佛教说“指月之指”一样。朱熹与弟子之间又有如下问答:
问:“格物、穷理之初,事事物物也要见到那里了。”曰:“固是要见到那里。然也约摸是见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时方信得及。”[8]640
曰:“知,只是一个知,只是有深浅。须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说道别有个不可说之知,便是释氏之所谓悟也。”②朱熹此处之辟佛,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有一段论述申发朱熹之意。其言:“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则须直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託。故实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有以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98页。
问:“张子所谓‘德性之知不萌于闻见’,是如何?”曰:“此亦只是说心中自晓会得后,又信得及耳。”[8]641
据上引两段问答可见,在朱熹看来,漆雕开之所以说“未能信”因而不去出仕,是因为他知得不深,未到物格知致处。他说:“漆雕开已见得这道理是如此,但信未及。所谓信者,真见得这道理是我底,不是问人假借将来。”[8]639因此,“斯”不仅指诚意、正心之事,也包含了格物致知之事。也就是说,漆雕开“未能信”的“斯”之所指实际上正是指体现在事君之忠、事父之孝等事上的天理。而若能信“斯”,则意味着不但真切地认识到了天理,而且也必定能够顺此天理而实行。此即朱熹所讲的“真知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真知”[1]42,真知必能行,不行只是未知。他极为强调知之真切、知之笃。所谓“德性之知”正是指对于天理的真切体会和认信。
从现存王阳明著作来看,阳明本人对于《论语·公冶长》此章内容并未有特别的关注③王阳明《传习录》上:“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孺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参看邓艾民《传习录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0页。,很可能他也没有注意到朱熹对于这一章的注释。否则,朱熹的解释与《朱子晚年定论》中所收录的《答梁文叔书》的内容何其相似,若阳明见及,当会收入其中④阳明未注意到此条,或与其对训诂之学的态度有关。他屡屡批评朱子为训诂之学。阳明很可能对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并不十分熟悉。。但阳明的后学传人却颇有人留心此章。如罗近溪高弟杨起元便说:
问: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何大乎?曰:身为大,身者天下之大本也。不知本者,见物而不见身。知本者,见身而不见物,见身者见其大,见物者见其小。暮春者,吾身之时也。春服者,吾身之物也。……舍此何以安吾身,不能安吾身,即不能有吾身。大本已失,而末治者否矣。点之见大,见身故也。开所云“斯”者,亦指此身所乘、所遇而言也。开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其曰“未能信”者,为未信者警也。二子之学同归于知本。[4]359
杨起元是以他所主张的万物一体观来理解“吾斯之未能信”。在他看来,孔子说“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正是说二人知本——身是天下国家之本,而此身是万物一体之身。因此,他与朱熹一样,也认为“斯”“有所指”,但“斯”之所指与朱熹的解释不同,应是指“身”而言。杨起元最后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既然漆雕开说“吾斯之未能信”,其中已经有“斯”字,这说明他对“斯”已有认信。之所以说“未能信”,是为未信者起警示作用。“开已信矣,不信何以取斯”的说法,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方哲学家如笛卡尔在确立“自我”作为第一原理时的思路,“我信故我在”,通过“我信”确立起了“大我”在存在论上的本体地位。杨起元解释下的“吾斯之未能信”是指人应当“自信”此身本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家国天下相联属的“大身”,不可自小了此身。此说正得阳明万物一体说之精意。
明末清初的李颙在《四书反身录》中解《论语》此章说:
学不信心,终非实学;仕不信心,经纶无本。成己而后能成物,自治而后可治人,开于斯自谓“未能信”,此正是审己量力不自欺处。……问:成己自治有素,可谓“信”乎?曰:即真能成己自治有余,而治体果尽谙乎?时务果尽识乎?经济大业果一一蕴之有素……乎?于此稍信不及,打不过,又岂可冒昧以从事乎?故必量义而后入,庶寡过;……曰:“斯”字先儒或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盖指妙道精义而言,今乃指修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义,不外修己治人;离了修己治人,何处更见妙道精义?况夫子方使开仕,……夫唯于修己治人之道,自谓未信,自觉心上打不过,所以超于天下后世昧于自知,而惟以苟位为荣者,正在于此。[9]
就《论语》此章文意而论,“斯”若不是虚词,那么李颙将“斯”解为“修己治人”还是有很大合理性的。相较而言,朱熹对于此章的注释,自然并非《论语》原意。徐复观曾对《论语》中的“信”字之含义做过简要的考察,认为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就士的操持上讲,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学而》),及“主忠信”(《学而》);二是就政治上来讲,如“信而后劳其民”(《子张》)及“敬事而信”(《学而》),这是说统治者必须使民能够信自己,此“信”是对统治者提出的要求。[10]依此,漆雕开所言“吾斯之未能信”亦应属于第二种含义。如皇侃之注释:“言己学业未熟,未能究习,则不为民所信,未堪任也。”范宁亦言:“开知其学未习究治道,以此为政,不能使民信己。”[11]此说似可视为确解。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之以“知之深,则信得及”解《论语》,亦有所本,即他所服膺的二程。朱熹所编的《二程遗书》中载: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颠沛造次必于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难为名状。[12]38
只是这个理,以上却难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12]44
这两段话皆是针对《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而发。在程颐看来,信就是信天理。而体认到天理便是觉悟,他曾说“觉悟便是信”[12]82。而体悟到天理的这种状态却难以名状,故言“只是道得如此”。宋明理学家往往谓“道不可说”“本体不可说”,正是指此。这正是朱熹解“吾斯之未能信”之“斯”为“天理”之所本。而朱熹“知之深则信得及”的说法也可在程颐那里觅得踪迹。程颐曾说:
今语小人曰不违道,则曰不违道,然卒违道;语君子曰不违道,则曰不违道,终不肯违道。……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终不肯为者,只是知之浅,信之未笃。[12]305
程颐是从知、行的角度谈论君子、小人之别,谓君子不违道,而小人则违道。二者之所以有如是之别,是因为君子对于道知之深而信之笃,而小人则虽知却知得浅,信之不笃,因此其行为会违道。朱熹与程颐一样,都认为在道德领域,人之所以知善而不行,只是因为未知,或知之不深。而若能烛理明,达于自得之境界,则能“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12]318。
此外,程颐还从圣凡之性一也的角度谈论“信得及”,他说: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日之近,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12]318
这段话是说,既然人之性一也,同禀天理而为性,那么不论凡愚,人皆能成为圣人。但世人却说自己怎么可以成为圣人呢?程颐认为这是不自信,即不自信自己之性与圣人之性是同一的。理学主张学以至圣,程颐此处之说正是在鼓励士人坚定成圣之志向,从而自信自达。朱熹《与梁文叔书》中所讲“信得及性善、为尧舜”与程颐此说相符。同时,程颐之说也与杨起元的说法相似,此正体现了心学与理学在核心义理上的一贯性。
综上,程朱关于信的论述可概括为两点:第一,从知与行的关系来看,知天理,是信天理的前提。而真知,或知之深、知之切,也就等同于信得笃。故而真知天理,也就是信得及天理①据二程的其他论述,若人真知天理,则自然不信鬼神之说。也就是说,知天理,是判定人应该信什么、不应该信什么的标准。也即,有此理,则可信。无此理,则不可信。。“知”可以涵括“信”。第二,从立志成为圣人的角度来看,凡圣之性并无差别。自信就是要信得及我之本性与圣人无别,如孟子所言:“舜人也,我亦人也。”[13]
三、“信得及”与知行观:理学宗教性的一个思考
前文曾分析了王阳明对“信得及”之解释的三层内涵,与程朱对“信得及”的论述相较,可以得知,二者的相同处在于,都认识到了信得及性善对于人之成圣的必要性;二者的说法也都蕴含了“天理”或“良知”的先验存在。二者的差别就在于知行观以及相关的工夫论上,这就涉及到对于道德知识、道德信念、道德行为三者关系的认识。
紧接上节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朱熹正是以知之深刻、信得及为真知的特点。朱熹言:“真知其如此……须是自见得这道理分明方得……漆雕开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8]639他认为,在孔子看来,漆雕开可以出仕,但是漆雕开却自认“未能信(得及)”。未能信得及,也即未达于真知。易言之,在朱熹的论述中,“信得及”是能去做的条件。“虽欲不如此做,不可得矣”的说法表明,只要是“信得及”,人就一定会去做,其中有一种不容已的践履动力。有此“信”,便有去为善进学的强大的道德意志。因此,在朱熹对知行关系的讨论中,实则已经触及“道德信念”的问题——是否相信自己之“知”足以去“行”,认识到了道德信念也是道德行为的动力,是否“信得及”也是影响“道德意志”是否坚定的因素。当然,“道德信念”已经是不同于“道德知识”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因此,朱熹将“真知”等同于“信得及”,将“道德知识”混淆于“道德信念”,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他说“知得深,便信得笃”“知之深,方信得及”[8]639,641,这一通过“以知识统摄信念”来统一二者的思路却颇有启发意义。
与朱熹不同,阳明学所主张的“满街皆是圣人”这一命题,是不可实证的,因为日常生活化的皆是常人。这一命题只能是一信念,以“信”的方式来体认,即人须确信自己能够成为圣人。王阳明曾说:
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1]93
依此,人成圣的根基就在于“人人自有,个个圆成”[1]31的无间于圣凡的良知本心。若信不及,则此良知便“自埋倒了”;若信得及,去除支离意见之蔽昧,良知便呈现出来。由此,确信自我能够成圣即在于自我要树立起良知自足、时刻完满的“信心”。换言之,道德意志的坚定与否,取决于对于自我良知完满的自信程度。程度愈高,意志愈定,则致良知之致也就愈坚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阳明学最为强调为学工夫以及为人行事,都要对良知充满‘自信’。”[14]无疑,王阳明对知而不行的探究亦已深入至“道德信念”层面。陆九渊曾批评朱熹之学说:“彼亦可受用,只是信此心未及。”[15]这正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直信本心的陆王之学与程朱之学的差异。笔者曾将这种差异归纳为两个序列[16]:
朱熹:道德知识(道德信念)→道德意志→道德行为。
王阳明:道德信念(道德知识)②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在《神圣者的观念》一书中就提出过“信念-知识”(faith-knowledge)的说法,转引自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17页。→道德意志→道德知识/道德行为。
(注:“()”为统摄之意,“/”为并列相即之意。)
简言之,虽然二人俱从道德信念、道德知识的层面触及道德意志薄弱的问题,但是,取径却近乎相反。朱熹是以道德知识统摄道德信念,而王阳明则说“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1]74,沿循的是通过树立对良知之信念从而明了本心良知即先验地具有知晓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能力的思路,以道德信念统摄道德知识。应该说,“信念”(信仰)与“知识”的关系,自古迄今都是科学家、哲学家所探讨的重大课题,而朱熹与王阳明则给出了自己的一种答案。他们对道德信念的思考尤其值得中西学人关注。
陈少明在《摆脱汉宋轮回》一文中曾概括宋明理学的特点,谓:“宋学分心、理两派,理学假定理在心外,对理的把握形式上有点认知意味……心学纳理入心,不追求外在的本体世界,但一旦把精力用于内省,其所得便与经验世界失去联系。……宋学试图确立的毕竟是信仰而非知识。”[17]他认为宋明理学的天理和良知皆不是经验的认识对象,宋学的本体论方法与具体知识方法有着截然的差别。其实,若比较汉学与宋学,似乎可以说:强调“信得及”恰恰也构成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如汉儒之所以认为成圣不可能,正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是经验性、知识性的态度①汉学重视名物制度的考证,而以圣人为生而知之的“神”,其代表即是《纬书》中的描述。,而非如宋明儒那样的信念的态度。
因此,宋明理学的宗教性意味便显得颇为浓厚,现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谈及儒学之宗教性时亦主要是以宋明理学为论说对象,这并不是偶然。为了对此“宗教性”意味做更好的说明,可以借用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以作参照。祁克果在《哲学片段》中区分了两种认识对象:直接性的和非直接性的,后者也称作“生成的”。前者是“直接的感觉与认知”的对象,如“一个苹果”之类,简单来说就是感官经验对象。对于后者,祁克果指出,“生成”是“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有”或“存在”表现为直接的“如此这般”;而“无”或“不存在”则不能在“直接的感觉与认知”中呈现,自然就不属于直接性的对象。“生成”包含了非直接的“无”,故为非直接的[18]。那么,对于“生成”该如何认识呢?“从无到有”如何进入我们的心中被我们所知呢?祁克果否认了“反思”可以承担此任。他举例说:
观察者看到一颗星星:当他努力要使自己意识到“它是生成的”时,这颗星星就立刻向他变得可疑。就好像是反思把那颗星星从他的感知中拿掉了一样。[19]210
“一颗星星”作为“直接的感觉与认知”的对象,其“如此这般”地存在着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反思”却会使这颗星星的存在变得可疑,因为“生成”是从无到有,无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故而反思并不能确定生成的是星星。如何终止怀疑呢?他说:“怀疑的终止,只可能通过一种意志行为,使自己处于自由的状态去达到”[19]211,这种意志行为就是“信仰”。“信仰所相信的是它所未见到的东西;它不相信这颗星存在,因为这颗星是它所看到的,但它相信这颗星已得以实存。”[19]210“信仰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自由行为,一种意志的表达。信仰相信趋向实存,并且实质上取消了跟那并非不存在的‘无’相对应的不确信的东西。”[19]212而且,信仰也包含着一种情感,它与怀疑是相互对立的激情②牟宗三即以良知为“本体论的觉情”,蒙培元先生亦有类似说法。清末民国时四川学者刘咸炘亦言阳明学的“良知”是一种“情意”。[19]214。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不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如此重视“立志”“信得及”的重要性了。所谓立志就是要下决心去信仰“成为圣人”。人是否能成为圣人这是不确定的,因此,人之进学修德必须终止对于能否成为圣人的怀疑。同理,天理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能不能体认到天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良知、我能否体认到良知,这都不是直接性对象,不是“物交物而知”的感官直接认识和确定的对象,而是非直接性的对象,是“生成”。宋明理学屡言“道不可言”“道无定在”“心无定体”等等,即已揭示出了这种非直接性的对象是不可以目见、不可以耳闻,亦不可以心思者。宋明儒以仁释理,又以生生释仁,亦体现了这一点。王阳明曾经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君须是信得及,只是立志。”[1]32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无中生有”即与祁克果所谓“从无到有”的寓意一致。阳明正是要人通过“信得及良知”而修学以成圣。相较而言,程颐和朱熹认为在信得及天理之前须有“格物致知”的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似乎就是混淆了直接对象与非直接对象,在认识方法上就出了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天理或良知也就是一种信念,若要将它们视为本体的话,那么也是一种“意志本体”。若严格来说,王阳明的良知才是,而程朱的天理则不是。
普兰丁格在《论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指出,人们往往忽视了“相信”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仅仅将“相信”看作持守认识结果的意志活动。而他则认为:
一般来说,我们不是先“作出决定”,然后再去坚持或形成某种信念,相反,我们直截了当地发现,我们已经具有这种信念了。[20]90
既然是“直截了当”,那么就不同于“作出决定”,因为作出决定意味着考量不同的理由和知识,这种“直截了当地发现”正近乎一种顿悟,或宋明理学家所常道的“觉”①朱熹解《论语·学而》首章就说:“学者,觉也。”而王阳明则认为圣凡同具良知,不同之处在于是否能觉。。在普兰丁格看来,信念在先,知识在后,正如研究者所分析的:“在‘适当情况’下,‘相信’的情感(‘接受这种信念的意愿程度’)越深,命题就越有资格成为知识。”[20]122换句话说,信仰才是知识的基础。而此处的基础也只能是就人本身的存在来说,因为就人的存在而言,涉及意志与情感的信念、信仰显然更为贴近人的生活。而知识则是更为外在的附加。
归根结底,宗教关涉人生,是否有信仰或信念,是人的生活方式问题,是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不论是陈少明先生对经验知识与本体知识的区分,还是祁克果对于直接对象与非直接对象的区分,都可显示出宋明理学对于“信仰”或“信念”的重视。这正表明了理学家的关心有着宗教的意味。
四、余论
张东荪在《思想与社会》中曾区分了三个方面的知识:“第一是为了当前的便利‘即实践的顺利’而得的知识,其取得则由于握住;第二是为了使用天然而得的知识,其取得则由于分析与实验;第三是为了安然生活而得的知识,其取得则由于建立信心。所以最后一种知识是为了立信而寻出理由来。在表面上讲的条条有理,而在骨子里却是志在信仰。因为没有了这样信仰人类便不能安然生活下去。人们决不乐意永久在烦闷与苦恼中,必须在这个世界中寻出一个理由来使自己得着生活下去的勇气。……这种寻找理由是为了得感情的满足,情感的满足不是仅在情感一方面,乃同时造成态度的转换,态度转换了在行为上就有变化,所以‘知’与‘行’根本上是一件事,知的影响首先及于‘性情’。宋儒所谓变化气质就是现代伦理学上所谓的铸造品格……知即是化,乃是自己化自己,使自己在性格上心理上起变化。”[21]58-59正是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将儒家的“天”“道”“理”皆视为“同时属于形而上的,又属于伦理的。这个同时属于形而上的又属于伦理的就是宗教的或‘半宗教的’(quasi-religious)”[21]62。张东荪的分析指出了信仰、情感、态度的关联性,这与祁克果、普兰丁格的分析完全一致。与西方传统对情感的排斥不同,中国传统本即重视情感。只不过宋明理学通过思辨化的方式,将心、性、情、信念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学既是哲学的,也是宗教的。故而,以西方为范式,不论是认为儒学是哲学,还是儒家是宗教,无疑又都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中国在近代遭遇鸦片和炮弹裹挟下的西学东渐潮流冲击后所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受西方科学理性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而产生“可信”与“可爱”的内在分裂。与之相应的正是对宋明理学的贬抑,因而无法洞悉传统的中国式心灵,一方面对于宗教并不热衷,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西方传入的哲学无法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这是推崇实证科学而贬抑儒家的必然结果。这种贬抑的内在结果就是在精神上的自我放逐。现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皆以“即道德即宗教”对儒家的宗教性予以阐发,正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的宗教维度。
美国哲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教授在其遗作《没有上帝的宗教》中对“宗教”做了不同于传统西方主流的解释。西方人往往会说上帝是每个人都应信奉的唯一真神,国人则往往会说“哲学是世界观”,但是德沃金在该书的开首第一章《无神论宗教》中就说:“宗教远比上帝深奥。宗教乃是一种博大精深、卓尔不群的世界观。……信仰一位神只是这种深奥世界观的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或结果。”[22]1他区分了神与神所代表的、比神更深奥的价值。“身所代表的价值是一种独立于神的存在。然而,不是教徒的人也会具有这种信念。”[20]1因此,有宗教可以无神,一个无神论者可以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在此意义上,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是相同的。似乎看起来他是宗教多元论者,其实他只是个神多元论者。这一思考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以远比上帝和各种神更深奥的、而为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最高价值来统摄了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是真实的,也是根本的”[22]12,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价值的世界是自成一体、自我论证的”[22]14。这个价值世界“与自然历史或我们的心理感知力没有关系”,并不需要科学、数学等的外部确证,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外部确证。相反,“是信心使我们相信我们有基本的科学和数学能力”,“宗教观要求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信奉价值:凭借信心”[22]15。凭借信心,亦即自信本心。“这种信念是感情化的,所以不管怎样考察其逻辑关联或内在基础,它都需要在感情上说得通。”[22]16这就印证了儒家知、情、意一体的观点。参照德沃金的论述,我们不难体会到,理学家对“吾斯之未能信”的解释,对“信得及”的强调,都一再显现出:理学家是无神论者,但却是笃信宗教的人。那么,无神论的儒家难道不是更为切近那比神和上帝更深奥的价值吗?儒家岂不就是一种宗教吗!
[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周汝登.周海门先生文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3]张阳和.不二斋文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4]杨起元.太史杨复所先生证学编[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43.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6.
[7]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98.
[8]黎靖德.朱子语类[M].长沙:岳麓书社,1997.
[9]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446.
[10]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65.
[11]皇侃.论语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
[12]程颢,程頣.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朱熹.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103.
[14]吴震.《传习录》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31.
[15]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459.
[16]刘增光.为善何以难?——宋明理学中的“道德意志”问题及其他[J].燕山大学学报,2014(2):21-27.
[17]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47.
[18]邹晓东.赋义与理解:祁克果论“信念”[J].哲学门,2010(总第20辑):113-137.
[19]祁克果.论怀疑者·哲学片段[M].北京:三联书店,1996.
[20]普兰丁格.证明与有神论[M]//当代西方宗教哲学.斯图沃德,编.周伟驰,胡自信,吴增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2]罗纳德·M.德沃金.没有上帝的宗教[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许婴]
On the Idea of“Xindeji”in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tobeginwithWANGYang-ming’sA Summary of Zhuzi’s Later Years In Life
LJUZeng-gua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Xindeji”is an important idea of Yangming studies.This idea can be said to mainly constitut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language collection of Yangming studies.However,this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proposition actually stemmed from Zhuzi’s Neo-Confucianism,and the exact textual proof is just WANG Yang-ming’s A Summary of Zhuzi’s Later Years In Life.The study on the change from Zhuzi’s Neo-Confucianism to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can provide for the exemplific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Zhuzi’s studies.Meanwhile,it helps understand the religiosity of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whoel Confucian school.
“Xindeji”;WANG Yang-ming;ZHU Xi;QI Ke-guo;religiosity
B248.2
A
1004-2237(2016)02-0007-08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02
2016-03-10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15XNF032)
刘增光(1984-),男,山西襄汾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宋明理学、《孝经》学。E-mail:zengguang0010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