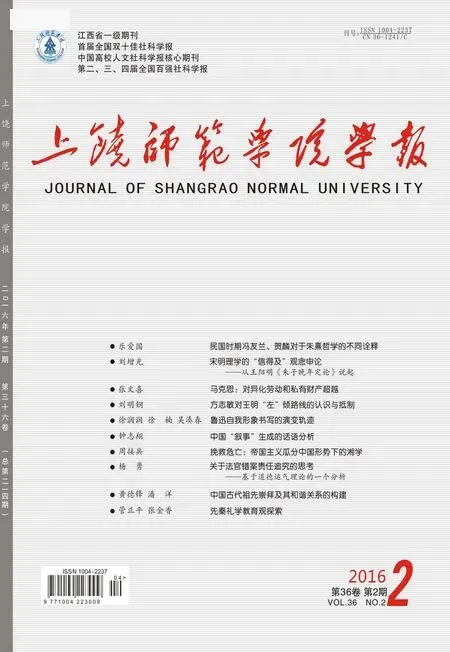神圣的社会与人造的神圣
——涂尔干与贝格尔宗教社会学思想之比较
王幼林
(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神圣的社会与人造的神圣
——涂尔干与贝格尔宗教社会学思想之比较
王幼林
(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认为社会是宗教的起源,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宗教具有维系社会的功能。贝格尔认为宗教是建立神圣宇宙的人类活动,宗教的合理化论证能够维系社会,但在现代社会里宗教的合理化论证面临着世俗化的挑战。两人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使得他们在宗教的定义、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涂尔干;贝格尔;宗教社会学;社会;神圣
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是宗教社会学的两大奠基人。然而,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涂尔干把宗教理解为与人对立的外在之物,他强调宗教的客观事实性以及宗教对人的约束作用。韦伯虽然承认宗教是社会的产物,但他更强调宗教思想对个人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影响。总的来说,涂尔干更强调社会现象,韦伯则更强调个体的思想及其行为。彼得·贝格尔是当代美国的宗教社会学家,他在方法上综合了涂尔干和韦伯的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主张人与社会互为产品,形成了一套折衷的辩证的研究方法。贝格尔用这套方法研究宗教的世俗化、多元化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旨在探讨涂尔干和贝格尔在宗教社会学思想方面的异同以及导致思想差异的原因。
一、涂尔干与贝格尔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概述
(一)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原始宗教为研究对象。他研究原始宗教的初衷是为了探索宗教的一般性或共性,而宗教的一般性之所以在原始宗教中更容易被发现和解释,是因为其社会环境单一、群体规模较小、个性没有充分发展,因此具有事实简单、关系明了、方便解释的优点。那么,到底什么宗教才是最原始的宗教呢?在涂尔干之前主要有两种看法,分别是爱德华·泰勒的泛灵论和麦克斯·缪勒的自然崇拜说。但涂尔干认为,泛灵论把宗教还原成了一套幻觉系统,而自然崇拜说不能解释宗教事物的圣俗之分,所以它们都不是最原始的宗教。在研究了大量的人类学资料之后,涂尔干认为最原始的宗教应该是图腾崇拜,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氏族是目前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初级的社会组织,而图腾乃是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教制度;其次,不需要借用其他宗教的要素,图腾制度就可以得到解释。
涂尔干接下来通过分析图腾崇拜的对象,探讨了图腾崇拜是如何产生的。他发现非人格的力具有最高的神圣性,其神圣性甚至高于图腾标记、图腾动物或植物。在北美部落有一种高于所有圣物的膜拜对象名为“瓦坎”,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意义上的力量,是其他所有圣物的神性的源泉,各种神圣力量都只是它的特殊体现。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其他部落中,如美拉尼西亚人膜拜的“曼纳”,易洛魁人的“奥伦达”,阿尔衮琴人的“玛尼托”,等等。这些事实让涂尔干相信,图腾压根儿就不是关于动物或植物的宗教,而是关于非人格的力的宗教。他说:“力的观念就是宗教的起源。”[1]279涂尔干进一步以澳洲原始人为例,分析了宗教力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澳洲原始人的生活是在两个周期中交替度过的,一个是经济生活的周期,一个是群体集会的周期。在前一个周期里,人们分散于四方,或采集或渔猎,各自为生活而劳作;在后一个周期里,人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一种叫做集体欢腾的仪典。在经济生活周期,生活单调、乏味、沉闷、枯燥,而在集体欢腾时期,人的情绪变得激动亢奋,狂热的情绪在群体中不断蔓延,使得他们毫无约束地奔跑、呼喊、尖叫、扭动身体、游戏、狂欢,每个人都感到被一种强大的神秘力量支配着。经济生活是凡俗的世界,集体欢腾是神圣的世界。“宗教的观念似乎正是诞生于这种欢腾的社会环境,诞生于这种欢腾本身。”[1]300宗教的观念产生于集体生活,正是氏族集体的力量在原始人心中唤起了神圣感,并把个人从凡俗的世界带入到神圣的世界,这种集体的力量正是他们膜拜的对象的本质。涂尔干由此把氏族的神还原成了氏族本身:“氏族的神、图腾本原,都只能是氏族本身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1]286。至此,涂尔干通过分析原始宗教揭示出了宗教的一般性,即图腾崇拜乃至一般的宗教是起源于社会的,图腾崇拜乃至一般的宗教的神灵在本质上就是社会本身。
图腾作为氏族的象征,在塑造道德共同体、加强氏族团结这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它的仪式中。图腾仪式主要包括祭祀、模仿、表现和禳解等仪式,从表面上看,这些仪式的功能在于,通过模仿神圣事物、向神圣事物供奉食物等手段来取悦神圣事物,从而在人和神圣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双向关系。但涂尔干在研究了大量的图腾仪式后发现,这些仪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在澳大利亚的阿兰达部落中,因提丘玛作为一种祭祀的仪典,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物种的繁殖,但是,这种仪典还可以用于成年礼和赎罪,甚至还可以代替葬礼。除了一个仪典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还存在多个仪典为一个目的服务的现象,甚至这些仪典之间还可以互相代替。仪式具有随意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涂尔干从这一事实中推断出,仪式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实现其特定的目的,而在于“定期地再造一种精神存在……它就是社会”[1]476。人们平时都忙于功利性的个人事务,私人利益主导着生活,对集体的情感和意识会慢慢地淡化。然而,宗教仪典会使人们聚集起来,体验同样的情感,还用同样的动作来表达情感,在这种内在的思想情感和外在的行为活动的一致性中,人人都意识到了他们属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个群体也更加团结。
涂尔干对宗教社会功能的看法,与其对宗教本质的看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既然神的本质就是社会,所以,尽管每一次宗教仪式在表面上是要强化人对神的依附关系,但在本质上却是在强化人对社会的依附关系。而社会体现的是集体的情感和意识,强化人对社会的依附关系,就意味着人应该克制动物本能,按照群体的道德规范来生活。“不管宗教生活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提升起来,使他超越自身,过一种高于仅凭一己之见而放任自流的生活。”[1]567
(二)贝格尔的宗教社会学思想
贝格尔先是阐述了他对社会的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他对宗教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他主张辩证地理解社会,即要从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这三个阶段去理解社会。所谓外在化,就是人类的本质决定了人们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来建造世界,这是一个把人类的意义倾注到世界中去的过程。客观化,即人建造的世界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会获得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性并与人相对立。内在化,是指人建造的世界又会被吸收到人的意识中去,“并且不是作为异化而是作为个体自己的意义之物从而指引个体的行动”[2]42。
外在化是人类的必然过程。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的生活世界由它们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如鸟儿翱翔于天空、鱼儿生活于水中,每一种动物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而人的生理结构不会给人设定一个特殊的生活世界,人必须为自己建造一个世界,这个建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外在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社会行动都意味着个人的意义被传导给他人,各种相互影响的社会行动则使得行动者的意义被整合成了具有共同意义的秩序,所以,建造世界的活动也就是将经验秩序化或法则化的活动。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法则,为个人提供了规范和意义,使人免受无意义和混乱的威胁。正是在秩序化这方面,宗教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3]33。换句话说,宗教可以把整个宇宙解释为一种具有神圣的秩序和意义的存在,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外在化。
贝格尔认为,人类所建造的世界正因为它是人的产物,所以它天生就是不稳定的,人类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很容易动摇这个世界的秩序。因此,对这个世界进行合理化论证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一直都是最为常见的也是最为有效的合理化论证的手段。首先,宗教可以赋予社会制度神圣性。宗教把社会制度同神圣的终极实体联系起来,于是人类社会秩序就获得了一种神圣的和持久的外表,这不仅证明了制度的合理性,还为这种合理性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撑。一旦社会秩序被宗教解释为神圣的,其人造的性质也就被掩盖了,神的烙印覆盖了人的烙印。“宗教通过赋予社会制度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即通过把它们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3]42其次,宗教可以赋予社会角色神圣性。在宗教的背景下,角色会被理解为神圣实体的模仿者,按照角色的要求履行义务,就意味着再现了神圣实体的伟大意义。如父亲这个角色,他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权威、仁爱和创造性等,只是神圣实体的力量、权威、仁爱和创造性的再现。他成功地扮演了某个角色后,不仅可以得到他人的认可,还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认可,即得到神圣实体的认可。最后,神正论思想可以利用社会中的既定法则,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边缘情境提供有意义的解释。人类社会中总是避免不了自然灾害、战争、死亡这类无秩序现象,“根据宗教合理化论证对这些现象做出的理论复杂程度或大或小的解释,都可以称为神正论”[3]63。神正论把对此世的无秩序现象的拯救投射到彼世,即彼世的神圣的裁决者会根据人们在此世的经历做出不同的安排,遭受苦难的人们将会得到安慰,有罪的人则会受到惩罚。由此一来,生前所遭受的苦难就不是毫无意义的。
贝格尔还进一步指出,宗教的合理化论证在当代面临着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严重挑战。“世俗化意味着宗教制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的丧失,以及宗教解释的可信度在人们意识中的丧失。”[2]36宗教曾经给社会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帷幕,使得社会中的一切看起来都具有终极的意义,但在世俗化的冲击之下,这层帷幕现在变得支离破碎,宗教现在只能为亚社会或社会的部分领域提供意义了。宗教丧失了它过去所拥有的垄断地位,多元化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宗教制度再也不能够声称具有核心地位,不再是意义和价值之高级秩序的唯一载体。”[2]54多元化意味着,一种宗教不仅要和其他教派争夺信徒,还要和一些非宗教对手竞争。世俗化导致了多元化,多元化又反过来加速了世俗化进程,两者一起使得宗教的地位不断衰落。
最后应该提一下,贝格尔后来否定了自己早期的世俗化理论。他在1997年曾说:“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容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是都是错误的。”[4]贝格尔修正自己理论的原因,从理论上来说,是因为他后来看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在带来世俗化影响的同时,也激起了反世俗化(counter-secularization)的运动。从现实上来说,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的事实,令他觉得自己的世俗化理论有些不合时宜了。贝格尔虽然修正了自己对宗教世俗化的早期悲观看法,但他并没有否定自己分析世俗化现象的那套宗教社会学方法。
二、对两者宗教社会学思想的比较
(一)宗教的定义
涂尔干的宗教定义是:“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1]58贝格尔的宗教定义是:“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3]33学术界往往把宗教的定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质性定义(substantive definition),一类是功能性定义(functional definition)。以此标准来看,涂尔干的定义明显是两种定义的混合物。其定义描述了神圣事物、信仰、仪式、教会这些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属于实质性定义。其定义的后一句强调宗教可以把信徒团结在一个道德共同体之内,这又属于功能性定义。而贝格尔的宗教定义则是单纯的功能性定义,即宗教可以建立神圣的宇宙秩序。在宗教的定义中,涂尔干提出了神圣概念,而贝格尔则发展了这一概念。在宗教社会学历史上,涂尔干最先强调了神圣这个概念,他指出一切宗教都把事物分为神圣与凡俗两大类,其中神圣事物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但他并没有深入阐述神圣概念。第一个充分发挥了神圣概念的学者是德国宗教学家鲁道夫·奥托,他在《论“神圣”》里说道:“神圣不只是完全、美、崇高或善,它就像这些概念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的、终极的价值……这是肯定性的神秘的价值。”[5]贝格尔的神圣概念则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浅层次含义:“神圣意指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力量之性质。”[3]33神圣在这个含义上的反面是世俗,这种理解明显是受到了涂尔干及其奥托的影响。神圣概念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宇宙秩序,其对立面是混沌,这一理解源自于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台湾被译为M.耶律亚德)的《宇宙与历史》。这部著作有个观点认为,远古时期的各个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神灵创造世界当作他们文化中最神圣的事情,后来的一切创造和仪式都是这一原初神话的重复,这个具有普遍性的事实意味着,宇宙及其秩序作为神灵的产物是非常神圣的。
(二)宗教的本质
涂尔干和贝格尔都探讨了宗教的本质问题,但两人切入这一问题的角度却不大相同。自宗教产生以来,神灵作为宗教的崇拜对象一直都是最为神秘的事物,涂尔干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揭开了神灵的神秘外衣。图腾的本质就是氏族集体,涂尔干将这个研究成果推及其他宗教的结论就是,各种宗教神灵的本质就是社会。“对社会而言,神仅仅是它的符号表达。”[1]475关于神灵的本质,涂尔干之前的宗教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宗教学之父麦克斯·缪勒认为是“无限”,爱德华·泰勒则认为是“精灵实体”,弗雷泽认为是“超人力量”。人们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竟然会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这是一个十分新颖而大胆的观点。但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使人们拥有了意识、语言、工具、技术、知识等人类文明,所以,社会凭借其巨大的权威而被神圣化是完全合理的。贝格尔认为宗教是建立神圣宇宙的人类活动,这种理解同涂尔干相比,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既然宗教说到底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包括思想观念活动、行为组织活动和情感体验活动等,那么,对宗教思想、宗教体验、宗教组织的研究都可以成为宗教学研究的切入点。从这方面来说,贝格尔把宗教看作是建立神圣宇宙的人类活动的思想,可以拓宽宗教学的研究视角。其二,贝格尔肯定了人类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贝格尔认为要完整地理解社会,需要从社会的外在化、客观化、内在化三个阶段入手。涂尔干肯定社会的权威以及社会对人的制约作用,人在社会面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这接近于贝格尔关于社会客观化、内在化阶段的思想。但贝格尔关于社会外在化阶段的思想,则肯定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即便是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也不过是人类外在化活动的产物。
(三)宗教的社会功能
涂尔干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维系社会,因为宗教仪式会强化个人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来实现社会的统一性。与大多数宗教学家都强调神圣事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神圣感、敬畏感和依赖感不同,涂尔干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仪式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在于神圣事物对人的影响,而在于仪式中群体对个人的影响。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道德共同体,每一场宗教仪式都是在强化个人对社会的依附感。贝格尔也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维系社会,但与涂尔干强调宗教仪式中群体对个人的心理影响不同,贝格尔是把社会秩序同神圣实体联系起来。宗教把社会纳入到宇宙的框架中去,社会与宇宙成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社会由此成了神圣宇宙中的一个环节,社会秩序再现了或者模仿了神圣的宇宙秩序,并且借着宇宙秩序获得了神圣性。社会秩序一旦与神圣实体联系起来,就会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帷幕,从而获得一种神圣的永恒的外表。他说:“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宗教涵括万事万物的话,将变得不可想象。”[2]31值得注意的是,涂尔干和贝格尔都只论述了宗教维系社会的积极功能,对于宗教阻碍科学进步、妨碍思想解放、延缓社会变革等方面的消极功能则完全没有提及,这说明两人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的认识都具有片面性。
(四)宗教的社会性与个体化
涂尔干非常强调宗教的社会性,他认为社会是一切宗教神圣性的源泉,宗教神灵就是人格化了的集体力量,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社会本身。在给宗教下定义时,他认为宗教是一种集体事物,因此他把教会看作是构成宗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并把教会的观念纳入到宗教的定义中去。涂尔干因为过于强调宗教的社会性并坚持宗教是一种集体事物,所以他不承认私人膜拜、个体宗教的存在。贝格尔则认为,宗教尽管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并为整个社会提供合理化论证,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宗教表现为公共领域的修辞和私人领域的德行。换言之,就宗教是共同的而言,它缺乏‘实在性’,而就其是‘实在的’而言,它又缺乏共同性。”[3]159这是因为,世俗化进程的冲击使得宗教不再具有强制性,宗教正不断地从公共领域往私人领域退缩,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的私事。涂尔干不承认个体宗教,而贝格尔则认为宗教在现代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私人化的倾向,如果联系现代社会里宗教的世俗化和多元化现象来看,涂尔干的理论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而贝格尔的理论则得到了更多宗教社会学家的响应,例如,与贝格尔进行过学术合作的托马斯·卢克曼提出了“无形的宗教”,帕森斯提出了“私人化宗教”,还有罗伯特·贝拉主张“宗教个人主义”,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宗教个体化的趋势。
三、思想差异的根源
首先,两人生活的社会时代不同,使得他们所面临的学术问题也不相同。涂尔干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科技革命推动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但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在政治方面,自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后,因为阶级矛盾和政党之间的矛盾,法国陆续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布朗热事件和德雷福斯案件等重大事件。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和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使得涂尔干极其关心社会整合的问题。《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把神灵还原为社会,认为社会是一切宗教神圣性的源泉。涂尔干如此高扬社会、强调社会统摄个人,正是要利用社会的强制性来抑制人的动物性,从而实现社会的整合。贝格尔本来从事社会学研究,后来被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宗教热所吸引,他的研究兴趣就随之转移到了宗教社会学,他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分析宗教的世俗化问题。另外,贝格尔还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学家。面对宗教世俗化浪潮的冲击,贝格尔十分担心宗教的未来,他也从神学的角度给出了应对方式,即从日常的生活体验中去感知上帝的存在。他说:“神学思想应在从经验角度给予的人类环境内,寻求可以被称为超验之表征(signals of transcendence)的东西。”[6]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使得他们自觉担负起来的学术使命也大不相同,涂尔干非常关心社会秩序,而贝格尔则更担心宗教的前途。
其次,两人的思想来源和研究方法也不大相同。在研究方法上,涂尔干受到孔德和斯宾塞实证主义的影响,并将这种实证主义推到了极致,从而使社会学从主观阶段走向了客观阶段。为了给社会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他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社会事实,并且认为“关于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的观点是全部社会学的出发点”[7]20。涂尔干笔下的社会事实是指:“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力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7]34从这个定义可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和强制性。涂尔干为了确保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他批判了个人的情感体验,认为情感只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积累起来的杂乱无章的印象和感受,因此,要保证社会学的客观性就一定要将个人的主观情感排除在外。贝格尔的思想来源和研究方法则更为复杂。在讨论宗教的本质时,他明显受到了涂尔干和奥托的影响;在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他综合了涂尔干和韦伯的思想;他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维系社会,这一观点源自于涂尔干,但在论证的时候,他把社会和宇宙的关系理解为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这又是受了韦伯的影响;他对宗教世俗化的理解,则是受到了韦伯和卢克曼的影响。贝格尔充分地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的理论成果,这也使得他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学者高师宁在《神圣的帷幕》的序言中概括说:“贝格尔的研究方法还有这么一个特征,当他论述宗教本质的时候,他是从哲学角度入手的;当他研究当代社会的世俗化问题时,他是从宗教学、社会学入手;当他讨论神学问题时,又从社会中的人的体验入手。”[3]23贝格尔因为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其他学者的思想,研究方法又十分灵活,这使得他的思想十分具有辩证性,所以,他在宗教社会学领域被视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折衷主义者。
终上所述,涂尔干所处的社会背景和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决定了,在他的学术体系中社会是一个核心概念,个人及其个人的体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把宗教的神圣光圈摘下来,然后又安置在社会上,从而把社会神圣化了。而贝格尔兼为宗教社会学家和神学家,他一直站在理解的同情和同情的理解的立场上研究宗教,所以,他明显更强调神圣概念,他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的解释都离不开这一概念。尽管贝格尔十分强调神圣概念,但他还是把宗教理解为人类外在化活动的产物,所谓神圣归根结底还是人造的。
[1]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Berger P,Luckman T.Modernity,Plu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Meaning:The Orientation of Modern Man[M].Gütersloh:Bertelsmann Foundation Publishers,1995:2.
[3]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M].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0-61.
[4]彼得·贝格尔.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M].李骏康,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鲁道夫·奥托.论“神圣”[M].成穷,周邦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6]彼得·贝格尔.天使的传言[M].高师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0.
[7]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责任编辑 邱忠善]
The Holy Society and the Artificial Holy Spirit——comparisonbetween EmileDurkheim’sand Peter Berger’sthoughtsof religioussociology
WANGYou-lin
(School of Marxism,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Peter Berger's study of religious sociology was influenced by Emile Durkheim.Durkheim thought that society is the origin of religion,religion is a symbol of society,and religion has the function of holding the society together.Berger thought that religion is the human activity to establish a holy universe andthe rational argumentation of religion can hold the society together,but the rational argumentation of religion in modern societ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secularization.They use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so they had many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the definition of religion,the essence of religion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Emile Durkheim;Peter Berger;religious sociology;society;the holy spirit
B920
A
1004-2237(2016)02-0028-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05
2014-04-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ZJ001)
王幼林(1980-),男,湖北黄冈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学。E-mail:wylwch@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