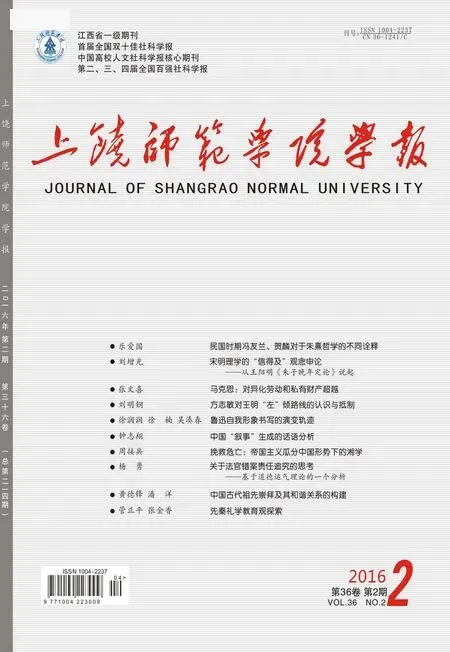性无善恶、善恶由习
——试论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吴晓东,张万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性无善恶、善恶由习
——试论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吴晓东,张万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开启了北宋儒学“非道德性命”不谈的学术风尚。作为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重要组成之一的人性论思想,围绕性与形气、性与命、性与心、性与情、性与心、性与礼乐等传统人性论的关键问题,坚持了性在体上的无善无恶和在用上的善恶相混,认为“性”所具有的为善为恶之潜能是人性善恶得以成立的内在依据,同时强调“习”是人性善恶得以成立的外在依据。这一人性论思想的历史意义,既在于其开创了宋代儒学将“外王”之功业立于“内圣”之学问之风,也在于其肯定人欲之正当性的强烈现实主义趋向。
王安石;人性;习;善恶;历史意义
王安石的心性学说在北宋儒学性理问题讨论上居有一定的开创性地位。近代以来,梁启超、贺麟等先生在推崇王安石政治和哲学思想时,也多谈及他对宋代道德性命之学的开创之功。首如,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以降的“完人”,王氏的性命学说体系既囊括了内圣的道德性命之学(“立身行己”),也涵盖了外王的经世致用之学(“施于有政”)[1]185-187。又如,贺麟极力颂扬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思想与学术思想,并称赞说王安石是“程朱以前对于人性论最有贡献,对孟子的性善说最有发挥的人”[2]298,当为陆王心学之先声。尽管如此,囿于王安石对性善恶问题的表述言出多处,且时有抵牾,先后有性不可以善恶言、性善恶混、性善诸说,这对于后世论者进一步考察王氏人性学说的基本内容、核心观点并审视其在宋代人性论史上所具有何种地位,构成了事实上的困难。鉴此,本文试图在综合王安石《性说》《性论》《扬孟》和《原性》等篇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议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王安石人性论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并探察王安石性命之说所应具有的思想史地位。
一、分析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基本进路
王安石讨论人性问题处于宋初学人皆以佛、道二教的思想作为旨归讨论养生修性问题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礼乐论》说,“天下之言养生修性者,归于浮屠、老子而已”[3]1037,显见,王安石讨论道德性命之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高扬孔、孟等历代儒家先圣先贤的人性论,以对抗当时流行的佛道二教之人性观。正是出于这一现实关怀,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更多地是在讨论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和韩愈的性三品说等思想的论议中,得以阐发的。相对而言,王安石较为推崇孟子的“性善”及扬雄的“性善恶混”二说,最为反对荀子的“性恶”论,并认为荀学的最大弊端是不知礼乐之义。从形式上看,王安石论及人性善恶问题的论议未能呈现为一个前后协调一致的有机思想体系,而是颇有些随机而发、随性而发的特质。
为救王安石人性论思想随机随性而发、缺乏有机体系的蔽失,研究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学者,也多愿以王安石讨论人性善恶问题的诸论议写作时间为轴,对王氏的人性论思想进行整合,并表述为一个有着历史和逻辑发展顺序的三阶段说。这一说法首见于《王安石的性论》一文①《王安石的性论》一文原刊载于民国30年(1941年)的《思想与时代》第43期上,后贺麟将该文与另一篇研究王安石哲学思想的大作《王安石的心学》合为一篇,即是《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该文认为,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先后经历了性情合一论,再到性善恶混,最后在《性论》中归宿于孟子的性善论[2]293。日本汉学家井泽耕一也承认了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他指出第一个阶段是《性论》中所服膺的孟子之性善说,进而发展到在《扬孟》《性情》《性说》《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诸篇中的性善恶混说,这一阶段的人性论思想主要是受到了扬雄性善恶混学说的影响,最后则回归到了《原性》篇所说的性情皆无善恶之观点[4]。胡金旺则在综合考察王安石论论及人性问题诸论议之写作年代的基础上,认为王安石的人性论经历了性善说到性有善有恶说,再到晚年的性无善无恶及佛教性空说三个阶段,第二阶段的性有善有恶、后天之善恶由习而来之说是第一阶段的性善说的逻辑发展,第三阶段则有了根本性变化[5]。
除了从三阶段说来诠释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逻辑体系外,也有论者坚持王安石人性论思想存在一个核心的观点,即性的无善无恶说,并以此来构建其人性论思想体系。如马振铎认为,王安石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性不可以善恶言,而只是具有一种为善为恶的潜能,外在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恶则是缘于外物刺激所产生的情之动所显现出来的善恶,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表现为一个由“性—物—情—理—善恶”等环节所组成的有机体系[6]122-140。张祥浩和魏福明也认为,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核心观点是,自命所出的性是人所具有的道德及智慧的良知良能,是无善无恶的,而性与后天的习相合而生的情表现为善恶相混[7]351-364。李祥俊则将王安石所论的人性视为一种兼含生理与心理的人之天赋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8]218-219。刘丰认为,尽管王安石早年所持的当是本于孟子的性善说,但他后来在人性问题上则主要是以“性情合一”说反对当时流行的“性善情恶”说,以“性善恶混”说反对“性善”和“性恶”说,并“以气言性”,将性与气、形相连,强调养生与养性的合一性[9]。要言之,这些学者在研究王安石人性论思想时,都试图构建一个以性善恶问题为中心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或纵向地以写作时间为序将其重构为一个历史地、逻辑地发展的思想体系,或横向地以某一论点为核心将其重构为一个协调的、完善的理论形态。窃以为,重构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历史与逻辑发展,并协调性善、性善恶混、性无善恶等说为一个一致的理论体系,都需进一步分析“性”概念在王安石人性论思想中所具有的涵义。
二、王安石人性论的基本内容
王安石在使用“性”时,有时仅从“生之谓性”所涵括有的自然本性的角度而言,如《礼乐论》中从形、气来讲性时,有“生而就有严父爱母之心”“嗜欲之性”“夫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等说,圣人治民理政的关键也是要“顺其性之欲”[3]1037,都肯定了人的生理欲望、情感好恶皆为性。有时又从道德性命的角度出发,专指人之异于他物的根本属性,即人心具有的性命之理,如《虔州学记》里所论,“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也……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非能夺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无”[3]1556-1557,又如《圣宋文选》所辑录的《性论》一文中将性定义为“五常”,即“性者,五常之谓也”。以下分别从自然之性和道德性命之性略说之。
王安石在论及自然之性时,主要是从性与形气的角度加以申述的。在王安石看来,性不为人所独有,万物也各有其性,万物和人所具有的“性”皆是从天地而来的天赋和秉受,即“天地无所劳于万物,而万物各得其性”[3]1061。这样一种生而具有的自然之性,要本于人的形体方才得以产生。王安石在《礼乐论》中论述这一点说:
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尽心尽诚者之所至也。故诚之所以能不测者,性也。……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3]1031
这里的“生”与“性”当可互释,都肯定了人性为人生而俱来的听、视、思、行的本能,人的形气之属是人性的根本所在。正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自然之性的认识,王安石方才强调尽性在实质上就是全形养生,而不养生亦不足以尽性,“生”与“性”互为表里而相因循。人能用以养生修性的,就是先王所制定的礼乐之义。以形气言性实际上构成了王安石人性论的第一个维度,这一维度也凸显出了王安石意欲承接先秦儒学将礼乐归本于心性的儒学传承。王安石在指出人性与狙猿之性的差异时,也能说明这一点: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育绳之以尊卑而节之以揖让,则彼有趋于深山大麓而走耳,虽畏之以威而驯之以化,岂可服邪?以谓天性无是而可以化之使伪耶,则狙猿亦可使为礼矣。故曰,礼始于天而成于人。[3]1029-1030
人与狙猿在形、气上具有相似性,但人的天性中具有接受礼乐之义的潜在可能,而狙猿之性则断无此可能。这与孟子驳告子“生之谓性”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即都认为礼乐不同于人性,但也不全然外在于人性,礼乐能得以践行的根据内在于人心人性。
除了从形气出发论述自然本性之性,王安石还着重论述了道德性命之性。围绕性之善恶问题,王安石分别从性与命、心与性、性与情、习与性等角度论述了道德性命之性。就性与命而言,王安石在《扬孟》《对难》和《性命论》中提出,“性”是“人受诸天”,“命”是“天授诸人”[3]2171,性命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关系。“命”实质上就是由性的贤与不肖而导致的外在命运之好坏,即王安石所说的“贤之所以贤,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贤而尊荣寿考,不肖而厄穷死丧,莫非命也”[3]978;同时,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性、命相分离之现实,王安石提出了“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区别,“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贤者治不贤。故贤者宜贵,不贤者宜贱,天之道也;择而行之者,人之谓也。天人之道合,则贤者贵,不肖者贱;天人之道悖,则贤者贱,而不肖者贵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则贤不肖或贵或贱”[3]1128。面对其所服膺的儒学史上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即孟子的性善说和扬雄的性善恶混说,王安石提出了“正性”与“不正之性”的划分,正性即表现出来的善性,不正之性即表现出来的恶性。孟子的性善之说主要是就正性而言,扬雄的性善恶混之说则兼就正性与不正之性而言。
王安石试图以心言性来区分开“正性”与“不正之性”。王安石将“心”定义为“气之所秉命者”[3]1031,这个承载命的形气之枢纽便是人心,人心兼有恻隐羞恶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并非全然纯善,因此既不能如孟子般以心善言性善,亦不能如荀子般以人性为恶,善为后天之“伪”。实际上,王安石承认了孟子所说的四心人皆有之、人固有之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人心也并不能全然化约为四心,心本身谈不上为善还是为恶,但却能生发出善恶。举例来说,羞恶之心是人皆有之、人固有之,若羞恶之心的对象是善行的不够,则能使人扩充善性而为君子;若羞恶之心的对象是财利的不足,则能使人的善性得不到扩充而为小人。
性情关系是讨论人性善恶问题所不能绕开的又一话题,王安石针对“性情相分、性善情恶”说(以晚唐的李翱为代表)提出了“性本情用、性情一也”的主张。通过援引《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性”,王安石认为性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喜怒哀乐未实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情是那些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好、恶、欲等七情,“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3]1062。王安石进一步解释说,“性善情恶”说的错误根源在于“求性于君子,求情于小人”[3]1062,在于将性情相分以区别论述君子之善和小人之恶。王安石反驳道,君子之为君子,与小人之为小人,都有赖于养性和情,养性之善而导致情亦为善方为君子,养性之恶而导致情亦为恶当是小人。性是善恶混的,情与性相一致也是善恶混的。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三代之圣人,之所以为善,并非是他们去情而存性,只是他们在表现七情的过程中合乎“理”。“性”与外物相接而生“情”,情如不合乎理则为小人,合乎理则为圣人、君子。
王安石既坚持性为形气所属,并由心言性,认为性不能单纯以善恶言,且又反对性善情恶而主张“性情一也”,那么,王安石人性论思想所面对的难题之一便是如何说明现实中的善恶之所缘起。这里,王安石借用了“习”的概念加以解释。在《再答龚深父<论语>、<孟子>书》中,王安石表示,在人性问题上较为正确的当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之论,他具体解释这一点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相近之性以习而相远,则习不可以不慎,非谓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也。[3]1217
王安石解释说,夫子之言并非是在强调人性的相近乃至于同一,而重在指出相近之性,若“习”不同,则最后会表现得相去甚远,是强调“习”的至关重要性,以告诫士君子应谨慎地对待自己的“习”。王安石在《原性》中进一步解释说,“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3]1089。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善的,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性也为善,五常是习于善的结果而已,因此,并不能由五常之善推论出性善。王安石还通过“习”解释了孔子论性的另两句名言,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论语·雍也》)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曰:“习于善而已矣,所谓上智者;习于恶而已矣,所谓下愚者;一习于善,一习于恶,所谓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于此,未始为不善也,谓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为不善,然后谓之中人可也。有人于此,未始为善也,谓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为善,然后谓之中人也。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后谓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3]1091
实际上,王安石以“习”来言善恶,与区分“正性”和“不正之性”都一致地保留了人在选择为善为恶上的自由意志。在王安石看来,“性”是善恶混的,同时兼有为善与为恶的可能,“习”则具体地、现实地将人为善还是为恶落在了实处,通过“习于善为善,习于恶为恶”解释了人现实中有善与恶、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之别的具体原因。通过将性与习相联系,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一方面高度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也坚持了外在环境对人为善为恶的重要作用。一如他在《答孙长倩书》中所说及的,“《语》曰:‘涂之人皆可以为禹’。盖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9]1338意即人之性皆有善,但如不能用礼乐来养性,则善就无法实现。
此外,王安石还有“性善论”的观点。这主要见于《圣宋文选》后被辑录在《临川集补遗》中的《性论》①关于《性论》的写作时期,学界或以为是荆公晚年作品(如贺麟),或以为是早年作品(如陈植锷)。如从王安石的《淮南杂说》来考察,则以为该文为荆公早年作品更为可信。一文。王安石以为,依据儒家的道统——孔子至子思再至孟子而生发的儒学思想,在人性问题上理应持性善之论:
性者,生之质也,五常是也,虽上智与下愚,均有之矣。盖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生之有五常也,犹水之趋乎下,而木之渐乎上也。[10]1064-1065
自《性论》观之,王安石持“性善”说与上文所述之大不同处,一是将“性”视作“五常”,因五常为善,所以性亦当为善;二是在一贯地反对荀子性恶说、韩愈性三品说的同时,贬斥了扬雄的性善恶混说,认为扬雄与荀、韩一样,都将性、才相混,因此不能明了性善之旨。
但如从上文所述及的王安石人性论思想之基本内容来看,性善论当为王氏人性论思想的一个“边角料”,也或可作为其人性论思想的一个前期铺垫。此外,王安石晚年(二次罢相之后)在《答蒋颍叔书》一文中,将佛教所说的“四大”(地、水、火、风)也视为性,同时将人的身体视为性,性为无善无恶[3]1418-1422。性善说与性无善无恶之说,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能视作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人性论实际上坚持的是性不可以善恶言,或者说性既有为善也有为恶的潜能。作为性之用的情也与性一样,也只是具有为善为恶的可能,而不可以断之以善恶。性为何不能以善恶言,则在于作为人之形气所秉受天命的枢纽“心”同时含有恻隐羞恶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且即使是为善的羞恶之心,也会随着羞恶之外在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或为善或为恶的不同。人在现实中所表现出的善、恶,主要是由于习的不同产生的,习于善则为善,认为人性善或人性恶都是未将“习”与“性”分开,误将“习”看作了“性”。可见,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围绕着性与形气、性与命、性与心、性与情和性与心等角度,坚持性在体上的无善无恶和在用上的善恶相混,意即性是外在之善恶之所以成立的内在依据,性具有的是为善为恶之潜能,性、情之间的关系是二而一的体用关系,“习”则是外在之善恶得以成立的外在依据。
三、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历史意义
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作为其新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开宋代读书人“非道德性命之学不谈”的学术风尚。同时,随着新学派在政治上的得势,荆公新学也霸科场约达半个世纪,对其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当与张载、二程子甚至后来的朱子、陆九渊等对性命的认识存在互相启迪之处,这一点也为研究荆公人性论思想的学人所认识。如贺麟先生就指出,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以“建立自我”作为出发点,当为理学体系中陆王心学的先河,所提出的“正性”与“不正之性”之分也几于程颐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2]293-298。还有论者令人信服地指出,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对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有启发作用,王、张二人的人性论思想具有内容上的同构性,即都在认可先天之性善的基础上,王用“习”来解释后天之性的善恶,张则用“气质之性”界定后天之性,后天之性的善恶是由于气质之变化。从张子《正蒙》写作的时间与王安石论性之论议的写作时间而言,和王、张二人在京城曾有过对于新政看法的交往来说,当是王对张的人性论思想有所启发[5]。窃以为,指出王安石人性论思想与其他儒者人性论思想在内容上的一致或相似,确能证明荆公人性论思想在儒学人性论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在宋代儒学的复归努力中所具有的开创性贡献何在,其与理学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可能会对儒学发展产生何样的后果。唯有深入理解这两点,也才能对王安石人性论的历史意义作相对客观的回答。
(一)王安石人性论开宋代儒学将“外王”之功业立于“内圣”之学问风气之先
一般来说,儒学被规定为“内圣外王”之学。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一个极大贡献,首先是承接了上自先秦的孔、孟之道统,强调用以“内圣”的道德性命之学为“外王”的事功之学之前提条件。余英时正确地指出这一点说,在宋代儒家政治文化中,强调“外王”必须具备“内圣”(即道德性命之理)的精神基础,首开于王安石,这也是王安石新学思想意趣的极大贡献[11]56。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士人非“道德性命不谈”的风尚,从而开了宋代儒学从章句注疏之学转到义理性命之学的风气。恰如侯外庐指出的,“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12]423。具体说来,王安石是通过将性与礼乐联系起来,构建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同一关系的。
王安石将心性与礼乐联系起来,认为“一道德同风俗”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尽性”,即他在《洪范传》中所说的“同天下之德在尽性”[3]1029。在王安石看来,性与礼乐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和交互的,“性”是礼乐之所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先天基础,礼乐是始于天而成于人;礼乐反过来则通过制性之欲来养性,习于礼乐是保持善性的根本理据。从礼乐的起源来说,礼乐是圣王根据人的天性所创作的,先王“体天下之性而为之礼,和天下之性而为之乐”[3]1031。从礼乐的作用来说,礼乐的目的是养人之性和使人不失其性,即“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3]1031,在《虔州学记》中,王安石再次对性与礼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
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也。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尝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说,颂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3]1556。
这里的性命之理即涵括了包括人性论思想在内的心性学说,“俎豆、钟鼓、管弦之间”则主要指的是礼乐制度,“度数”则说明了在王安石看来,礼乐制度是性命学说的一种外在表现。恰如人之身体需要衣食来养,人之性则需要礼乐来养,人习于礼乐则自然扩充性之善。
王安石试图将“外王”的事功建立在“内圣”的道德性命基础上的另一表现,体现在他的育才观和王霸之辨上。王安石在其治国规划书《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特别强调政府为天下育才的重要,强调了人才的教之、养之、取之和任之之道,其中的教之道和养之道都依赖于性与习、性与礼乐,即以礼乐教人、养人,使人习于礼乐而全人之善性,而非如《伤仲永》一文中所述的仲永那样,不注重后天的习善养性而“泯然与众人同”。在王霸之辨上,王安石一如大多数儒者,尊王而贱霸。在王安石看来,王霸都要遵循“仁、义、礼、信”,其区别仅在于人主治理天下之“心异”,即心性是王霸之辨的理论基础。扩而言之,君子之德行也是若此,如心中存着安人之善念,则并不会因其屡事不同之君而致德行有亏。王安石曾论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其能屈身以安人,如佛菩萨之行”[13]99。这一论述避免了以是否忠于某一君王而论臣,而是将“心安”作为第一位。
将实现“外王”功业的礼乐之教立于“内圣”的道德性命之说的基础上,并以心性作为王天下的最终依据,是王安石对于儒学、儒者所应肩负之使命的自觉。王安石曾明确表示道,“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3]1323。显见,王安石的这种使命的自觉构成了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贡献。
(二)现实主义趋向是王安石人性论的又一特点
荆公新学与程朱理学都试图将外王之事业立足于内圣之学问,而心性问题则又是内圣之学问的核心。综合后来理学家对王安石道德性命之说的评价,和比较王安石人性论思想与同期的张载、二程之人性论,则反能说明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又一特征,即强烈的现实主义趋向。
实际上,无论是与荆公同时的张载、二程,还是后来的朱、陆,对其道德性命之学都持否定态度。王安石曾问及张载对新政的看法,张载回应说,“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可见,在张载看来,荆公的道德性命之说与其所推行之新政,是不与人为善的。程颢与荆公在道德性命之学上的冲突则更为激烈,程颢认为荆公之学为“捉风”,荆公认为程颢性命之学难行。荆公与程颢争论各自之学的是非时说:
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14]255
程颢还评价王安石的道德性命之学为佛、老之学,非是儒学之道:
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他说道时,已与道离。他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阴阳、刚柔、仁义;只是此一个道理。[14]5-6
相比程颢,程颐更是激烈地否定了荆公道德性命之学,直以“全不识也”[14]251否定荆公未明儒家之道①“全不识”语出程颐对王安石解《易经》的“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时说“只是不识理。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全不识也”。“全不识”表明了程颐对王安石论性的激烈否定态度。。朱子也评价王安石说“德行,学则非”[15]3097,“学非”具体表现在荆公道德性命之学见道的不透彻,即: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15]3097-3098
与朱子一样,陆九渊也如是评价王安石说:
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负斯义也。[16]232
上述诸子对荆公新学的否定性评价,要在两点,一是荆公心性论未明儒学之道,而更近于佛、老之道;二是荆公心性思想甚少关注工夫论,具有随时随事而变的现实主义趋向,即明道先生所谓的“捉风”之意。
王安石人性论的现实主义趋向的另一表现,是肯定了人欲的正当性。与王安石大约同时的理学家中,张载区分了“太虚湛一之性”与“攻取之性”,前者即仁义礼智的天地之性,后者即饮食男女、刚柔缓急的气质之性。程颢则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的气秉有善有恶,善恶皆为人性。程颐则区分开“天命之性”与“生之性”,前者即为所有人所共有的天理,后者即为人生而就有的性格之刚柔缓急等,前者无不善,后者有善有不善,并特别强调“论气”与“论性”相结合,以解释人性善恶问题。将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其他诸子的人性论加以比较,不难发现,王安石的人性论更为重视形气的重要性,也更为强调养性即全生和性情一致的观点,认为人生而就有的情感与欲望无所谓过分与不过分,皆具有正当性,人性善恶在根本上是人能否习于善、习于礼乐的结果,而礼乐的重要功用在于养性、移风易俗和治民。尽管王安石区分了正性与不正之性,但他并未将二者对立而论,而是将之合二为一以说明自己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的看法。
要而言之,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最大历史意义,不止在于其首开了宋儒“非道德性命不谈”的思想风气,还在于他在个人修行之外看到了外在熏染对人性善恶养成的重要性。早在金人赵秉文时,就认为正是王安石首开了宋代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不知笃厚力行之实”之思想风尚[17]3。实际上,认为王安石首开“非道德性命不谈”之风尚当可为公论,但说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则显有失公允。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王安石的人性论思想强调个人的善性养成,既需重视内在之“性”,也需重视外在之“习”,“习于礼乐方为善”也正体现了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笃厚力行之实”,也恰说明了王安石人性论思想的重要历史意义。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王安石.王荆公文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5.
[4]井泽耕一.王安石的性情命论[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7-11.
[5]胡金旺.王安石人性论的发展阶段及其意义[J].孔子研究,2012(2):22-28.
[6]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7]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李祥俊.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9]刘丰.王安石的礼乐论与心性论[J].中国哲学史,2010(2):93-100.
[10]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临川集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1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魏泰.东轩笔录: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程颢,程颐.二程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黎靖德.朱子语类: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十九记[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许婴]
No Good or Evil Nature,But Good or Evil Way——onthebasiccontentandsignificanceofWANGAn-shi’sideaofhumannature
WUXiao-dong,ZHANGWan-q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WANG An-shi’s study of ethic life actually initiated an academic style of“Only Ethic Life”in Northern Song’s Confucian Study.The idea of human nature,an important part of WANG’s study of ethic life,centering on the key issues concerning traditional ideas of man’s nature,such as nature and physical condition,nature and life,nature and heart,nature and temper,nature and ritual music,insisted that man’s nature be neither good nor evil in substance,but good or evil in practice,which was always confused.The idea held that the good or evil potential in man’s nature w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good or evil human nature and it also stressed the way that people behave was the extern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good or evil human nature.The historic significance of this idea lies in two aspects:it initiated the style of“external success based on internal cultivation”in the Confucian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it confirmed the strong realistic tendency of human desire’s justification.
WANG An-shi;man’s nature;way;good or evil;historic significance
B244.5
A
1004-2237(2016)02-0015-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6.02.003
2016-03-03
吴晓东(1975-),男,安徽铜陵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知识社会学、文化哲学研究。E-mail:2012000759@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