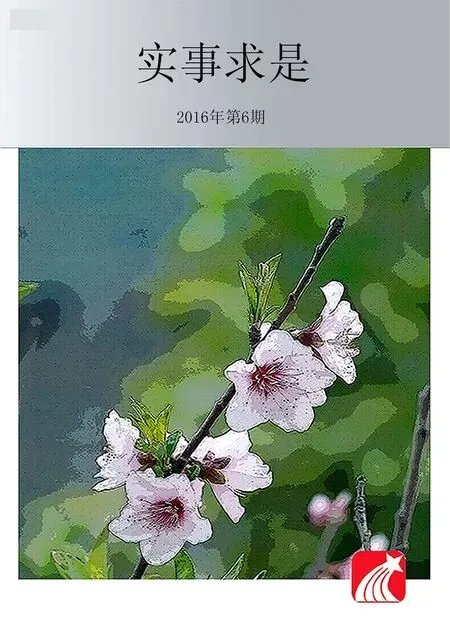追寻自然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德性之维
钱圆媛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 北京 100091)
追寻自然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德性之维
钱圆媛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部 北京 100091)
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维度并需澄清其在伦理政治领域的多重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可谓人之自然功能的实现,德性生活是一种内在化的生活。在精神生活日趋多元化、碎片化的当下,精神世界塑造、道德生活重建似乎亟待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推进:自然不仅为德性塑造提供起点和终点,更亟需在道德生活中提倡一种“自然的方式”、一种内在化的德性、一种伴随着德性选择活动而自然流露的道德情操,能够“见孺子入井”而自有“恻隐”,能够“自然而然”地向善为善。
亚里士多德 德性伦理学 自然 功能 内在性
今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道德生活日益碎片化,甚而表现出情与理的倒错,言与行的冲突,以及善与乐的断裂:理性沦为追逐情感和欲望的“万能”工具,情和欲几成心灵之主人;众人面对道德徒好“围观”,有“善言”之华而无善行之实;即若行善事,内心往往无有道德之乐,而时有禁受仆街老者的“扶”与“不扶”之困苦。美德本该体现人的卓越性且“自然而然地”为人所追求,然而当今追求善似乎日益变为一件困难的、“不自然”的事。如何能在道德和精神生活上情理和谐、知行不悖并以善为乐,部分学者转向古代哲学,试图为失落了德性之源的现代人重寻精神的源头活水,这在东方带来的是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复兴,在西方兴起的则是以“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旗帜的德性伦理学思潮。[1](P2)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又被称为“德性幸福论”——幸福是伦理学关注的人生总目的,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德性指卓越性(包含道德),是人生幸福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着眼人生整体的善而非功利或义务,注重品格、道德情操而非行为规范,关注选择和实践智慧而非道德律令,为今日伦理学带来了新面向。然而在欣喜于这些令人鼓舞的观点之前,正如安娜斯(J.Annas)所提示的那样,我们需要对其伦理学的结构和根基进行一番探讨,以更好判断其对我们今天的道德问题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所助益。[2](PP4~5)安娜斯以自然为着眼点,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如何诉诸自然来论证其德性伦理学思想。她的结论认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著作中的“自然”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初始质料、天生的、“中性的”自然,二是作为伦理目的的理想性自然。[2](PP142~158)据此可认为,自然在德性论中的根基作用体现在:一是德性之所以可能的起点,无自然则无德性;二是德性朝向的目的,其依据自然而得到规定。
这一洞见部分呼应了艾文(Irwin)的观点,[2](P147)她认为自然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大致有两方面重要含义:第一,不受人影响的事物初始构造(Con⁃stitution)或倾向;第二,指示事物之功能及所趋向的目的因(Final Cause)。[3](PP339~340)同时,尼科斯(Nich⁃ols)也认为,伦理学中的自然有初始自然和目的自然的区分;[4](P18)而米勒(Milller)则划分了严格意义上的自然和目的性的理想自然。[5](PP44~45)
自然作为德性论证的重要根基,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考察辨析:故笔者试图探讨亚里士多德德性思想中自然的多重含义及其关联,并指出其在德性论中的意义与作用。笔者试图说明,自然除了是德性的初始要素与理想目的之外,还关涉德性的“作用机制”和形式要素。德性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使人行善,在精神生活日趋多元的当下,精神世界塑造、道德生活重建似乎亟待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来推进:尽管初始自然和目的性自然一直为德性塑造提供起点和终点,但今天亦亟需在道德生活中提倡并“模仿”一种“自然的方式”、一种内在化的德性、
一种伴随着德性选择活动而自然流露的道德情操,能够“见孺子入井”而自有“恻隐”,能够“自然而然地”为善。
一、自然的多重含义之辨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并未专门探讨自然,更多是将其直接用在相关表述中。对此,诚如安娜斯所言,伦理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要通过《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的自然概念来理解。[2](PP145~147)
《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中有对自然的集中专门探讨,“自然”的总含义体现在其定义中,指自然物内在的、自身性的运动原因:“自然是依据自身而非依据偶性、首要地属于自然事物的运动和静止的本原和原因(192b21-23)。”①同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自然被确立为四类具内在统一性的原因:质料、形式(自然物的是其所是)、动因以及运动所趋之目的。上述含义(尤其形式含义)是自然概念的核心,在《形而上学》“哲学辞典卷”之“自然”的六种含义[6](PP295~296)中被再次罗列和强调(1014b16-1015a19),增加了自然的生成及其过程这两个含义。此外,作为四因含义的自然均能从潜能、现实两方面理解。
若比照自然的上述含义,我们会发现伦理学中的“自然”很少被作为“四因”而有完整指涉。在论述德性相关内容时,“自然”一词较为清晰可辨的含义是初始材料和目的,而较少直接意指其形式和动因含义:如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03a14-25)认为,品德德性来自“习惯”一词,德性既不通过自然,也不相反于自然而产生,而是在初始自然基础上予以完善之。相对于初始材料含义,目的意义上的自然是德性发展追求的理想: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252b30-53a1)指出,自然说的是事物的目的,当事物完善发展的时候,我们称其为自然,我们这样指称一个人、一匹马或一个家庭。然而就德性而言,似乎我们并非依据内在的自然动力即可作出德行,而是通过习惯,似乎习惯才是德行的动因;类似的,亚里士多德只说人依据自然而求知,人依据自然而是城邦动物,却未直言人依据自然而有美德。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被清晰界定的自然概念到了伦理政治领域,其运用似乎变得狭窄和模糊。安娜斯甚至指出,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清晰区分自然的“初始材料”和“理想目的”这两重含义。[11](P147)
伦理政治领域中自然的多重含义是否以及为何具有此种模糊性?我们需要重新溯及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主题、性质和进路:
首先,直接就“自然”谈善行之原因是困难的。伦理知识探问活动的善的原因,而善的活动和行为有很大变动性和人为性,“善行被认为可能更来自习俗而非自然”(1094b13-16)。
其次,形而上学、物理学中自然的四因含义研究旨在求得相关的精确知识,但伦理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善的活动,伦理知识的精确度不及形而上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求知意味着寻找原因,而伦理知识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原因,故精确含义的四因“自然”不能直接对应于善活动的解释——物理学中的“自然”意味着“总是如此”,但伦理学能求得的原因知识,只是“大多情况下如此”而非“总是如此”(1094b20-21)。
再次,伦理学追求活动的善,包括实体意义的善如神和努斯(Nous),以及偶性意义的善如诸德性(1096a23-27)。而“自然”在物理学领域主要涉及自然物的实体性,故很难说作为实体原则的自然能直接解释非实体的、偶性的诸德性活动。
最后,“自然”是自然活动的第一本原,却非伦理活动的第一本原,故不易直接解释伦理政治活动。伦理活动的主题和第一本原是幸福,我们并非首先因为自然而行善,而是因为幸福而行善。
二、幸福与自然
那么,伦理政治领域是否还需要“自然”?若人之德性的善不以某种方式关联于自然以及万有的存在结构和价值,在当时则有陷于智者关于Nomos 和Phusis之争的危险——其认为人的善、道德不过是习俗的结果而非来自自然;道德习俗和城邦法律终是人为设计而非有不可改变的终极价值。
亚里士多德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在伦理和政治领域仍是倾向自然主义的——自然内在地关联于善和价值:依据自然的城邦制度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和最好的(1135a3-5);依据自然的东西就其自身就是好的(1099b20-21)。不过,伦理学探究自然并非直接将其作为四类原因性的善知识来解释善活动,并不直接追问活动的善如何直接由诸自然原因“引起”,而是先设立并界定善活动的第一本原(幸福),自然的多重含义则相关于此第一本原而得以呈现。
幸福是善的活动的第一本原和原因。幸福有两个定义,一是活得好和做得好(1095a17-18),而
这里的“好”或“善”有三类(1098b11-15):外在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其中,根据自然的定义(即自然物自身动静的内在本原),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都可谓出于自然的善。而如果德性行为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善、特别是追求主要的善,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1097b22-1098a18),主要的善就是灵魂的善,也即灵魂的功能的善。此即幸福的第二个也是最核心定义:幸福是“灵魂依据并展现完全的德性的活动”(1102a5-6)据此,作为人之自然的灵魂又继而被确定为善的活动的第一本原,其联结了自然作为功能、初始材料、目的以及被习惯模仿、由理性选择而达成的动因这四重含义。
灵魂意味着功能,而人的灵魂有营养、运动、感知、情绪、欲望、理性功能,其中理性是人独有的、展现人之“是其所是”的灵魂功能。故灵魂的卓越性及其展现主要在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以及能听从理性的部分(情绪和欲望)。灵魂是人自身运动静止的第一内在本原,灵魂功能的卓越性可谓属于人之自然的卓越性。但问题在于,人的灵魂也如其他生物的灵魂一样,能自然地生成并达至其本质功能的卓越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在追求善方面是不自足的,无人能仅凭自身而自发展现出作为人之自然的灵魂中的德性。那么,灵魂的德性还需依靠何者而能实现?
关于德性的古老问题之一即是追问德性来自教授、习惯养成抑或自然形成。亚里士多德认为,能使人向善的东西有三种:理性、自然和习惯(1332a39-b1),而灵魂的德性展现需三者共同作用。其中,“自然”指向的是自己就足以形成并达至的善,是进一步的善的初始材料;欲望和情感上的卓越则较难自己形成,离不开基于初始自然的习惯化培养;理性的卓越性则需教授来引发。
可以说,灵魂的功能区分暗示着其发展方式的不同,而人之自然中愈高贵卓越者,则需愈多条件才能达至。那么,人之自然的卓越性在此被分析为初始自然、被习惯化的自然以及作为理性的自然,这就绝非概念模糊的表现,而是提示了非道德、道德以及道德之上者的界限和进路——自行即可生成的初始自然是非道德的,其是道德的基础,伦理德性依据的是实践理性和品格习惯的良好实现;在此之上则是理智德性的领域。
三、德性发展与自然功能
如前所述在伦理领域中,一方面实践理性这一自然功能离不开教授的引发,一方面习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二自然”[7](P254)(1152a31-b1)。习惯属于那些我们自己能做到、可为亦可不为之事,故道德褒贬意义上的道德责任始于习惯。习惯有一个非道德的自然基础,这种“初始自然”的非道德性有多处表述:如人不该因天生丑陋而受斥责,但要对恶习带来的丑负道德责任(1114a25-30)。
伦理所涉的习惯是一种稳定的倾向,其固定下来就形成一种品格。习惯或习性(Hexis)指Diathe⁃sis(Disposition,状态、品质)的一种特殊形式;Diathe⁃sis的字面意思是“根据地点、潜能或形式的对具有部分的东西的安排(《形而上学》1022b1-5)。在亚里士多德那里,hexis属于“质”(Quality)这一范畴(《范畴篇》8b27-9a12),是一种稳定持久,不轻易变化的Diathesis,是“要经长时间形成的人的本性(Na⁃ture)的一部分且很难改变”(9a2-5);因此,hexis属于知识和德性的范围(8b30),是一事物所具有的、只要遇到适当环境和条件即会显露的内在倾向或势态。这种倾向相当稳定,并且是可预期的。
所谓“习惯成自然”(1152a30),可谓外在价值目标的内在化。自然说到底是自然物内在的运动本原,关涉到自然物能否保持自身同一。就伦理德性而言的内在性则意味着诸自然功能即情感、欲望和实践理性的内在统一。其中,习惯作为稳定的内在倾向,本身要依赖初始自然功能,其是对初始情感、欲望进行伦理化“安排”的结果:一方面这些外在价值和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被“合理”限定为初始自然可接受的,或者与初始情感、欲望的目标同质或接近;一方面是通过习惯化训练,使欲望、情感能正确导向那些从其初始自然目标中“筛选”出来的特定目标,而这种训练大致要依靠苦乐刺激来强化或弱化某些特定目标和动因(即情感和欲望)的自然联结。这样,习惯化训练实则是加强或减弱自然情感欲望的、导向某些特定目标的自然动力,试图使这些外在价值目标与情感、欲望以及理性本身的内在作用机制保持同一。
这种习惯化有别于技艺:如工匠造一张木床,其形式、质料、目的和动因没有自然的内在统一性——木床的形式是外在的,由工匠的蓝图注入木头中,该形式既非事物自身目的,也不作为动因引导事物实现自身,换言之,床自身无能于保持床之质料中的自然动力,床中之木的自然力(比如生长)及其自然目的与床本身无关,其自然力也不受外在置入的床的形式或目的之统摄,因而木床难以自行保
持自身同一。然而,习性所运用的自然是初始情感和欲望,此二者在既成习性中仍是习性自身发挥作用乃至自我维持的动因,其与限定习性的形式和价值目标有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通过练习和实践得以完成,是理性、情感、欲望的内在统一而能自行持守和保有美德。因此,愈是模仿和跟从自然的内在统一而培养、践行习惯,则习惯愈为稳固持久和“出色”;背离自然而培养习惯则是非常困难且难以长久保持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336b40-1337a3)所言,“诗人划分7岁为受教育年龄这大体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应该考察自然的划分,因为技艺和教育要补足自然所缺失的。”德性教育亦复如是,需要根据自然、模仿自然来保有并强化伦理德性的自然动力与内在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习惯的关键之一就是一方面合理筛选自然情感和欲望所联结的自然目的,一方面考虑如何最好地保有并强化自然情绪和欲望中的“自然动力”,从而将习惯塑造得像自然力那样起作用,使特定情感和欲望在特定条件下自行发挥其特定功能,并达至最佳状态。而衡量习惯优良与否的标准之一亦在于其内在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良好的习惯总能自然而然地起作用并以快乐的伴随为标志,这种快乐在根本上源于对自然状态下无阻碍地发挥功能的内在机制之“模仿”(1099a5-15)。
伦理德性不仅是情感和欲望功能得到良好“安排”,更意味着此二者与理性功能的内在统一。理性既使得德性领域中的情绪和欲望总能为人所知,同时总在德性领域作为命令者来规范情绪、欲望并统一于此二者的活动中:首先,根据功能论证(1097b22-1098a18),[1](PP50~58)人的德性在于灵魂诸功能的优秀发挥,其中的理性功能是人的本质功能,定义了人是什么(390a10-12),是人之自然中的形式;故德性活动必然首要地依据并展现理性功能。换言之,德性及其活动必然要求理性作为形式因起作用。其次,理性作为形式因“规范”德性及其活动,表现为,德性是一种由理性选择决定的中庸状态(1106b35-a2)。中庸常被界定为“正确的”——如“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对于正确的人、出于正确的原因、以正确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中庸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特征”(1106b21-23)。若根据余纪元先生的解释,中庸意味着“命中”,那么这种“命中”就是由理性决定的。[1](P95)仅凭重复的习惯,很难在具体情况下因时因地制宜地命中德性的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习惯养成的品格在发挥作用时,由于最初是从外在引入的本原(外在价值的内化),其不可能具备准确无误且“总是如此”地达到内在目的的能力,因此需要理智(尤其是实践理性)的命令和引导。实践理性是人之理性中专司照管欲望和情感的功能,此功能的优秀发挥则称之为实践智慧。
可以说在伦理德性活动的具体施行中,实践理性一方面要发挥工具理性作用:“伦理德性使目的正确,实践智慧则达到之”(1144a7-9)。实践理性提供达到目的的形式规范,使习惯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对于正确的人、出于正确的原因、以正确的方式”命中目标。同时,在伦理德性形成的关键,即外在价值的内在化过程中,理性也提供形式因,体现为对特定价值及德性活动的理解和认知,这是具有该品德德性的最首要标志。
另一方面,实践理性作为决定德性的形式因,还发挥目的理性作用,即习惯、初始自然都要根据理性来调整和选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1332b5-10)指出,当理性告诉我们要有悖于习惯和自然而为的时候,应该听从理性。实践理性的良好实现本身就是人性最好部分的实现,因而具有内在价值;同时,实践理性对习惯的引导是为了导向完善的道德德性(1144b16-17)。完善的道德德性有别于天生的某些伦理德性如勤劳、大方等,其指向幸福这个人生总目的和最高善、主善。若没有对诸具体德性在幸福这个总目的中不同地位及相互关系的知识,我们就无法形成完满德性并拥有幸福人生——德性发展可能极不均衡,有人可能会大方却胆小,勇敢但极吝啬。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在政治实践中也要用到实践智慧,这种智慧并不仅仅考虑达到目的的手段,更需对善有总的知识和考虑,才能为城邦的善的培养和塑造制定目标。
可以说,实践理性为德性活动提供形式规范并表现为慎思,其在《形而上学》(1013a30-31)中被认为是行为的一种动因;而德性选择即是慎思的结果,意味着情、欲、理的统一,是自愿的、其伴随着快乐和对具体情况的清楚知晓,并构成行为的起点。同时,伦理习惯中的动因机制依据并模仿自然的情感和欲望起作用,试图使得被“安排”的诸情感和欲望在特定情境下发挥出特定功能,为特定行为活动提供动因。
四、结论
人的灵魂功能是人的自然,而愈首要之功能愈
难凭自身达至完满,故人之自然的实现可谓一方面表现为伦理德性,其依赖于实践智慧调谐下的、情绪和欲望的“习惯成自然”;一方面表现为依靠教授引发的理智德性(尤其是思辩智慧)。
德性之实现指向善和幸福,而正因人的自然功能包含理性、欲望和情感,才要求人所追求的幸福必然涉及道德善和理智善的统一,涉及情理欲的内在和谐,这是人所追求的作为人的幸福。其中,道德是人独有的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野兽因其无有理性、神因其唯有理性,故皆无道德德性;而第一好的幸福是理智德性的善,以模仿神的思辩活动为终点。
在这里,理性虽始于人的自然功能且在有生灭的自然中,却指向了自然之上的永恒思辨领域。理性作为人之自然的发展终点,其本身的完善可谓走向了对自然的超越。故可以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理性是“非自然者”的说法,[8]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切自然始终是潜在和可变的(1134b25-a5),理性(Nous)则是自足、完满和永恒的;故“当理性告诉我们要有悖于习惯和自然的时候,我们应该听从理性(1332b5-10),”伦理道德虽是人性卓越性的体现,却不能让人分享永恒,我们不应根据“有死”的本性来生活,而应该依据人之自然中的神性来生活(1177b31-a5)。
自然,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重要维度之一:除了自然的初始含义和理想目的含义,自然还涉及动因和形式因:习惯通过对人的情和欲进行良好“安排”而强化特定的情感和欲望的自然功能,从而塑造出“第二自然”;同时理性亦是德性及其活动的形式和动因,一方面规范习惯而形成伦理德性,一方面导向自然的终极理想,即模仿永恒之神的思辩活动。
在追求人的自然功能之善的过程中,我们发展了习俗、制度、各种工具和手段,正如尼科斯所言,那些原本用于发展和保存人的东西逐渐有了自身价值而被作为善来追求,人们似乎在追求自然的过程中越来越运用了非自然的方式。[4](P18)以至于今天愈是追求人的发展,人愈有被工具理性奴役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由于理性的滥觞,而在于没有正确地追寻自然,我们在追寻人之自然的过程中忽视了自然概念最核心的“内在化”。而假若工具理性不为追求人的诸自然能力和功能之发展,而旨在取代或“命令”人的自然能力和功能,则必然沦为一种典型的外在化生存方式。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医术不能命令健康而只能促进健康(1145a6-8);人的发展应依据人的自然,追求一种内在化的人的生活。这种德性生活应重视情理欲的统一,因而绝不忽视品格和道德情操培养;这种生活也应重视“天然”和“人为”的结合,如黑格尔所言,一方面要反对认为天生高贵是最好的,一方面也需反对纯粹义务是最善的。[9](P364)
向善是困难的,子曰从善如登;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理性要基于好的习惯才能得到发展,而没有好的法律就不可能有好的习惯(1179b20-a5)。但从亚里士多德独特的“自然”之视角来看,也许今天追求德性可以安排得更“自然”一些——理智教育可以是更具启发而非外在灌输的;道德培养可以是更自然而快乐的,可以是情理欲圆融而所为即所欲的,更可以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
[注释]
①参照Barnes,J.ed.,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Princeton,1995并标注Bekker页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引文均由笔者据此自行翻译并参照希腊文,希腊文参照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1999并作拉丁化转写。
[1]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Annas,Julia.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Aristotle,Terence H.Irwin.Nicomachean Ethics[M].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9.
[4]Nichols,M.Citizens and Statesmen:A Study of Aristotle's Politics[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
[5]Miller,F.Nature,Justice and Rights in Aristotle Politics[M]. Oxford,1995.
[6]Ross,W.Aristotle’s Metaphysics[M].Oxford,1953.
[7]参见Randall,J.,Aristot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
[8]参见1032a11以下,1071b5以下.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责任编辑:洪美云
B502.233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