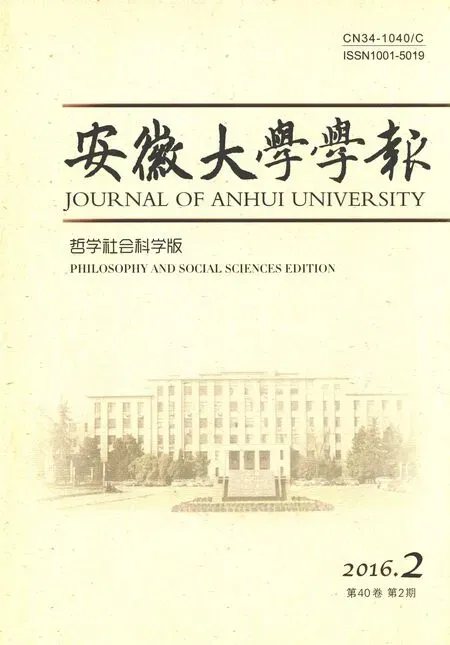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魏耕原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魏耕原
摘要:杜甫白话七律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盛唐七律高华典丽风格的变革与发展。首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其次在华州正式拉开了白话七律的序幕,成都草堂七律进入了对田园生活的叙写;复次草堂、夔州七律大量口语虚词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使白话七律趋于精熟。这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白话七律;日常生活;口语虚词
诗至盛唐,诸体大备,最后晚成者是七言律诗。初唐七律大约72首,盛唐发展到300首,而杜甫拥有151首,竟然占到盛唐的一半。“初唐英华乍启,门户未开”,杜甫“胸次闳阔,议论开辟,一时尽掩诸家”*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第4页。,而为大成,把七律的发展推向高峰。而且影响中、晚唐得以长足进展,下及宋元明清,沾溉百代。前人论述几乎汗牛充栋,然多从体制艺术着眼。如果结合内容、语言与风格,就会发现对盛唐七律高华伟丽和畅达温厚风格的扭转,而形成雄壮悲凉、凝重坚实、博大深沉等多种风格,特别是质朴自然的白话七律,向来注意者无多,或偶有微词。就其发展变化,尚待进一步讨论。
一、走向日常生活的白话七律
杜甫先从个人的情怀入手,用七律发抒心中的种种郁闷与不快。作于早年的三首,有题咏、宴饮、山水,虽与王维等人无别,似乎是对这一新体的尝试,然在风格的凝重与句式的打锻上已与上四家显然有别,似乎为将来的创变作了准备。天宝末年两首寄赠厚重雄博,已逗漏出后来主体风格的端倪,其中《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的结联“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若与李颀《寄司勋卢员外》结联“早晚荐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赋长杨”比较,貌离而神似,然高朗流畅却高出七律圣手李颀若许。这些均可看作汲纳与试验的准备期之作。
回到收复后的长安,杜甫仍任左拾遗,但肃宗视他与房琯为父党。虽身居谏官,然并不得志,实质没有多少发言权,因而郁郁不欢,他用《曲江二首》抒发了当时苦闷的心情。望着飘落的春花,其一说:“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把一叶落而知秋变作对春去的怅然。时局和时令都进入春天,然而正如同时所作《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说的“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看来他属于新朝“多余的人”。既然政治上的春天不属于他,他只能说:“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这种用动荡的单笔白描式的叙写,感觉不出偶对,甚至很有些不像律诗。出句与其说是描写,还不如说是议论——春天眼看就要完了——这才是实际要说的。对句的“伤多”,又是流播百姓口头间的俚语俗词。如此原汁原味的口语,原本与庄重的律诗是风马牛不相及,却用来“装饰”作定语,而表达“过多”的意思。以之与“欲尽”偶对,这是少与多的对偶,句法为上五下二,亦为新奇。只有读到颈联“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噢!这才是偶对,这才是七律呀!所以,我们不能小觑“伤多”一词,它预示了杜甫要向民间口语汲取活泼的语料,换句话说,他对七律的堂皇将要进行词汇上的、也是彻底的革命。这在其二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显得更到位了,干脆以口语句进入七律,而且形成偶对。我们习惯欣赏下联“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式的偶对,而“寻常”“七十”的口语习见词,用之于七律则换上了不经人道“新面孔”。这种“陌生美”有待于人们继续地再认识,杜甫向日常的白话律诗愈加走近了。
作于同时的《曲江对酒》的“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桃花小而轻故曰“细逐”,“黄鸟” “白鸟”则语如童稚,而“时兼”则为精约的雅言,如此写景与对偶,似乎在进行文白交杂的试验,亦属七律革新的范畴。句式亦带民歌特色,开宋人一大法门。杨慎云:“梅圣俞诗‘南陇鸟过北陇叫,高田水入低田流’,山谷诗‘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换雨鸠来’,李若水诗‘近村得雨远村同,上圳波流下圳通’,其句法皆自杜……来。”*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九“梅圣俞诗条”,见《丹铅馀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66页。颔联“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判”亦俗词,仇注说:“《方言》:‘楚人凡挥弃物谓之判。’俗作‘拼’。”此谓拼命,不要命。这种俗义也是杜甫最早用之入诗,劈开一条通道,在中晚唐诗与宋词即成为习见词*参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判”字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第641页。。如此议论,可谓“色相俱空”,然非雅言,以粗语发泄牢骚,愈见心中郁懑。还有《题郑县亭子》中四句:“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清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峰远趁人。”前两句,高腔大调,为大景;后两句转入小景,且不说其中寓意,“趁”为追逐义,亦为口语俗词,亦为杜甫最早入诗*《汉语大词典》“趁”字条,首列诗例为于鹄《题美人》:“秦女窥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墙头”,其实是宗法杜诗。杜诗《催宗文树鸡栅》:“驱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趁”为“驱”的同义词,驱逐义。。总上三诗可以看出,杜甫在语料与句式上向民间口语撷取,不仅施于古体诗,而且用于七律,欲建设一套新的话语的努力端然可见。语料与语序是他构筑白话律诗最基础的工序。有了这些准备,全新面貌的白话七律不久将会呈现。
二、白话七律的创建
有了白话词汇语料与民歌句式的准备,杜甫准备背离盛唐高华流美的浑厚风调,除了建立雄沉博大、厚重凝练、质苍老健的主体风格,另外放手创作全新的陌生风貌的白话七律。对他来说,既是日常生活抒情言志的需要,也是为了扭转盛唐诗歌颂升平、风华温丽的趋向,具有表现日常生活琐事与审美选择的双向追求。这种追求,在他与肃宗、代宗政治中心愈远的时候,追求愈强烈。当他被排挤出中枢机构,而被贬放到华州司功参军之时,论者以为这既是他在政治上一个转捩点,也是创作上一大关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也标志着他的七律,尤其是白话律诗,将要迈入新的进程。
作于华州的《望岳》就是用白话写的七律山水诗,其中“诸峰罗立如儿孙”的比喻,“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流水对,都体现白话修辞与句式的功能,显得生动活泼,还有几分可爱与幽默。黄生说:“‘玉女洗头盆’五字本俗,先用‘仙人九节杖’引起,能化俗为妍,而句法更觉森挺,真有掷米丹砂之巧。”*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六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册486页。似对这种俗语有所察觉,然却未发现企图建设白话律诗的努力。《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白话律诗的序幕,也是尽力拨转盛唐伟丽风格的亮点: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单看每一句,俨然是七言古诗的句式,疏质野放,不加任何修饰。连此前七古从来都不上的“蝎”与“蝇”,都派入了偶对。全用白话,更不用雅言作陪衬或缓冲。它来自生活,又走向生活,鲜活的力量,饱满的张力,生动的刻画,全方位地呈现了白话律诗的全新面孔。它的陌生是对盛唐七律正格极具强力的反拨,以致有人惊呼:“此必赝作也。命题既蠢,而全诗亦无一句可取。纵云发狂大叫时戏作俳谐,恐万不至此!风雅果安在乎!”*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六引朱瀚语,第488页。若依盛唐七律正格,确实“无一句可取”,然而这正是杜甫所追求的变格变调,也正是朝着“风雅备极”温和高华风格的逆向运进,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冲击。他的五、七古的大段议论,后来七绝的排列直硬,莫不是创新驱动所形成的。所谓“老杜每有此粗糙语”(浦起龙语),还说得较靠谱。由送郑虔诗至此,经过不懈的努力,正式的白话七律终于形成。有趣的是,高适的《封丘作》与此题材与语言均有相近处,然出之以七古,而用此“粗糙语”作七律,只能由才力雄厚、立意创新的杜甫来完成。时为乾元元年(758),杜甫47岁,诗作正处于创作的第一高潮中。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口语纯净得没有任何“杂质”,就是唯一的雅言“兼味”,也被融化掉,因用于真诚的开释,显得更为亲切。起联村舍之景话外有话,言草堂寂静,世情冷淡而无人来,只有群鸥不弃,亦为下面喜客来作陪衬。“喜客来,先说无人来,是用逆笔”(何焯《义门读书记》语)。次联把客至而有空谷足音与蓬门生辉一类的话说得极为自然亲切的原因,不仅因用了流水对,而且互文见义。黄生说:“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扫;蓬门不曾缘客开,今始为君开。上下两意,交互成对。”*黄生:《唐诗评》卷三,见《唐诗评三种》,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214页。如此看就更热情了。从平日接客的絮语烦言中提炼得如此鲜明简洁,而又不失口语风味,想见柴门迎客一言一语的意态神情,足见杜诗对白话揣摩冶炼之功夫。颔联说菜少酒薄,不成敬意;又抱歉“市远”而又“家贫”,忙乎不过来,也没有能力置办,只好如此将就。这一大堆客气话,解释的话,希望谅解的话,只这两句就交代得周详备至,而且热情洋溢。就是因了在“盘飧无兼味”与“樽酒只旧醅”中间插入了“市远”与“家贫”。就把许多话融入到只有两句就够了,而且杯盘间频频致意与殷勤款待的情状宛然如见。末联就客生情,提议邻翁对饮,亦见宾主相欢无隔,平添了不少热闹气氛,而且“隔篱”显明田夫野老身份,“呼取”见出与农夫的亲密无间,犹如陶渊明《移居》其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那样的真率。如与《宾至》合观,亲与疏、热与冷、开诚与傲岸的差异就不能以道里计,然而都是用日常的用语来表达,真让人赞叹他的说话本领,不,以白话为七律真是到了叹为观止的化境。
经过“一年四行役”,从大乱中漂泊到成都卜居以后,很有点陶渊明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弃官归里的意思,身心得到安息,咀嚼幽静居所与闲适的生活,像陶渊明集中写起田园诗,杜甫也安下心来,写起久蓄于胸时断时续的白话七律。除了以上几首以外,还有一首《江村》说:“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反复与叠用的对偶手法,轻松流动的语调,使饱受战乱创伤的心理得到安宁与静息,观赏起卜居的江村,注视屋内屋外的燕子与水鸥,同样感到一种自适与亲近。同样像陶渊明端详“方宅十余亩,茅屋八九间”,看他在同时的《为农》所说的“江村八九间”,甚至有了“卜宅从兹老”的想法。此诗的下半说:“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和丧乱的奔波相比,一家人都有了闲暇,确实感到满足。以嬉戏琐事入律诗,此前是没有的。王维七律《辋川别业》《积雨辋川庄作》描写田园风光,伛偻丈人与争席野老也只是画面上的点缀,犹如山水画中的人物,远人无目,更不会有其个性。张谓七律《春园家宴》按理该有家人日常的生活了,然而看到的是“大妇同行少妇随”,说的只是“竹里登楼人不见,花间觅路鸟先知”,仅是把场景由屋外移到园内。孟浩然的田园诗里更看不到自家人的活动,七律更付阙如。杜甫以老妻稚子的一举一动入诗,只有在初唐王籍诗里依稀可见,但那时七律尚未出现。所以杜甫描写村居的这些诗,自然要用“家常语”与日常话。用质朴的白话来写日常平凡生活的七律,确实属于创举,带出一种新风格新面貌。王孟与储光羲用五古追踪陶诗,杜甫却用七律,这本身有极大的距离,然而他与陶诗走得似乎更近,更亲切。
就在作这些村居的白话七律的同时,杜甫看到春水猛涨,由此而联想到作诗的进境。《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所谓“性僻”,是说诗学审美趋向与人有异。观其所论,出语务必惊人,此为其一;所谓“漫与”的自谦,实即“纵心所欲不愈矩”,此其二;其三则尚友古人,以陶谢为法。此以七律论诗,所论以七律为主当无疑。此诗作于一系列白话七律之后,应当也包括对这些诗在内的总结。而且可以肯定,是以白话七律为主而言。不然,何以当头即言“性僻”;既然语须惊人而又何言“漫与”?正因为如此,故以陶谢为法。他的《发秦州》《发同谷》两组24首即取法大谢,即使在草堂所作的白话律诗也可看到这种痕迹,如《狂夫》的“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渠冉冉香”。不过对陶诗最为倾心,只要看看《王十七待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前半说的“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就可知与陶诗可谓息息相通,至于其余是不消说的。所以,这诗既可以看作白话律诗的总结,也可看作为此而发的“宣言书”。因而宋人杨大年说他是“村夫子”,犹如谓陶诗为“田家语”,然而这对集大成的杜甫来说,正是所极力追求的“惊人”境界。
三、口语虚词的魅力
陶诗无论田园还是咏怀,都有不少的议论,议论则需要以虚词表达其间的转折、递进等思理的变化,所用虚词竟达五十多个,然而不失为一流的诗*魏耕原:《陶渊明诗的散文美》,《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又见《陶渊明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杜诗亦好议论,又好陶诗,虚词见多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实词如果似骨骼,虚词则如血气性情,用于言情,则更是不可或缺的。在杜甫的白话七律里虚词主要用于复杂情意的表达,如《有客》名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打头两虚词就对发抒傲岸与嘲讽起了绝大的作用。杜诗的虚词如同他对民间语料的采撷,也很注意汲取日常口语的虚词。如口语表示“同样”义的“也”,相当于文言的“亦”,就见于七律《野人送朱樱》的“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一起首就用了“也”字,看了前四句,很难清楚它的意思。下半说:“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原来首句的“也”字有个比照的前提,那就是后四句所说的皇家苑林樱桃是那样的红:昔日以金盘玉箸赐给门下省,自己高高兴兴地“擎出大明宫”,今日漂泊转蓬之际得到农夫赠送,而京都无有音讯,所以顿生“西蜀樱桃也自红”的感慨。首句从百转千回的回忆中先倒折出来,“也自红”力量就显得很重。吴汝纶说这句:“倒摄后半,章法奇警,所谓‘笔所未到气已吞’也。”*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576页。方东树说:“此小题也,前半细则极细,后发大议论则极其壮阔。……而后半妙处即在首句‘也自’二字根出,所谓律诗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如果与王维题材相近的《敕赐百官樱桃》一经比较,杜诗虚词特色就更显明了。
至于白话律诗,所用虚词就更为增多。广德元年(763)春史朝义部将田承嗣、李怀仙先后归降,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终告结束。杜甫闻喜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兴奋地手舞足蹈,也像平常人一样,要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和自己欢快的心情迅速转告别人。故诗如热烈激动的口语,八个虚词分布在每句里。首句表达消息出人意料,因安史之乱长达八年,不知蔓延到何时。诗人又在偏远的西南,故用“忽”表达闻讯惊讶之感。次句见出乍闻的惊喜振奋与喜极而悲的瞬间心理的动荡。《羌村三首》其一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的悲喜交集的惊疑——发愣——喜极——流泪的过程,以及《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二的“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均与此相似。首联的“忽”与“初”起了一定作用。次联的“却看”犹言再看,此句要把欣喜传递给妻子,然妻子“愁何在”——已不复愁矣,故对句有“漫卷诗书”的狂喜。千回百转的喜而不愁,喜极而狂的喜悦欢跳,借“却”“何”与“欲”表达得千回百折,曲尽其情。颔联急促的“须”与兴奋的“好”——恰好,时在春天回乡,正好赶上“青春作伴”,以助行色,“放歌纵酒”“青春还乡”,一气旋转。末联预想还乡路线,“即从”与“穿”配合,“便”与“向”呼应,打头两虚词又呼应一气,使四个带有重字的地名立即流动起来,大有飞流直下之势,甚至感觉不出还是对偶句。王嗣奭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愈朴愈真,他人绝不敢道。”顾宸曰:“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促间写出欲哭欲歌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顾所言,俱见《杜诗详注》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册第968页。前者所言的“朴真”,即如白话;“他人绝不敢道”,即谓七律没有如此作法。后者则指出这些虚词在此诗中表情功能与艺术魅力,其实,这些都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范围。
有时把虚词与口语实词结合,更能发抒一种特殊的情感,使语言充满情感的弹性与张力,同年所作《送路六待御入朝》便是虚实两种俗词合构的名作。先追怀以往的悬隔:“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以下从此生发说到现在: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
中两联打头的“更为”“忽漫”为虚词;“不分”“生憎”为虚词与动词的结合,便有若许曲折,种种遗憾与不顺心。颔联为倒置句,故用“更为”先伸进一层,表示再再的怅然。然后以“忽漫”领起说到忽逢即别的遗憾。“不分”即不满、讨厌,与表最讨厌的“生憎”为同义词,后者见于卢照邻与骆宾王诗。而“不分”则为杜诗首用其义,沿用到现在,二者均为当时口语。王嗣奭说:“‘桃花’‘柳絮’,寻常景物,句头添两虚字,桃柳遂为我用。”*王嗣奭:《杜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1~162页。末联的“无赖”亦为口语词,则与“生憎”与“不分”呼应为一片,而前置之虚词“还”进一步引出别易会难的黯然伤神。另外“知何地”“是别筳”“白于绵”中的虚词,与“还”字位置都处于句末的三字中,而与句首虚词呼应极为紧密。这些虚词对表达“始而相亲,继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别”(朱瀚语),都平添了无限悲伤与惆怅。如果换作实词,情感恐怕不会有如此的感人力量。此诗前四句言送别之情,“一气滚注,只如说话”(清人李子德语),说话说成七律,确为老杜绝大本领!
杜甫自许“晚节渐于律诗细”,如果从白话七律看,越作越精到。后期此类诗虚词见多,运用从心所欲,亦见一端。而且此类诗往往即成名作,《又呈吴郎》即为著例。此前因己事有《简吴郎法司》,此则为邻说情,故曰“又呈”,则又是以诗代简。既是用作书信,措辞则应如“说话”;且为人说情,更需措辞委婉。实词多则骨硬,虚词多则语活。故以贴近谈心的素朴语说起先前“任西邻”打枣,因熟知邻妇“无食无儿”之孤苦。中四句简直不是偶对,不是律诗应有的模样,百转千层,莫非劝导。看它四种句式全用虚词斡旋,八面出锋,彼此开释,极为用心:1.“不为……宁……”;2.“只缘……转须……”;3.“即……虽……”;4.“便……却甚……”。散文里的因果、转折、假设、递进四种复句,全派上用场,而且凝缩复句为单句,而变为杂糅的复合句。“不为”句虽开释邻妇,亦是对吴郎的开导。“只缘”句双双说到。“即防”句回护邻妇,亦暗含劝慰吴郎。“便插”句似专就吴郎而邻妇的“恐惧”亦包孕其内。四句如水之容器而随圆就方,无处不到。既关照邻妇,又开脱邻妇;既示意吴郎,又回护吴郎,句句处处语关彼此,无不体贴入微。末尾又变密为疏,把“已诉”“正思”分置两句,又是一递进复句。浦起龙说:“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徵求’,‘徵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有民社者告焉,而恤怜之义,自悠然言外。”*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册671页。如此深长之用意,却用如此写话之语言,真如对人面语,句句打动人心。特别是十四五个虚词使语言之委婉入微,真情至性,动人心扉,渗入心底,把语言的弹性与张力发挥到极致。回头看这又是一首七律,确有“唐人无此格调”(仇兆鳌语)之同感。
胡适为了张扬白话文学,为此专作了一部《白话文学史》。对本来矜持而讲究的七律,他自然极为反感:“律诗本来是一种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但他的作品与风格却替律诗添了不少声价,因此便无形之中替律诗延长了不少寿命。”这实在是因矫枉过正而激生的一种偏见,甚至推及到他所尊重的杜甫,说他的律诗是“消遣的玩艺儿”。偏见往往扭曲理智,而有违心之论。不过,他还说:“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然中求自然。”*以上胡适两段话,见所著《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0、213页。这确实是一种敏锐颖透的卓见,值得深长思之。但他所说的“特别长处”,却又有些走调。所谓用说话作律诗,在杜诗中并不见多,只不过是相题制宜,根据内容与感情的需要,只能是追求变调中的一种,而且亦非主体,否则他就不能成为集大成者。
总之,七律在杜甫手里完全成熟起来,发展成为盛唐诗的重要诗体。他也有盛唐正宗正格之作,如在任左拾遗作的《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紫宸殿退朝口号》《题省中壁》等,比起王维、岑参并不逊色。但他意识到这种颂美文学已时过境迁,只不过是收复长安时的一度兴奋与不久即为幻灭的期望。万方多难的时代,艰难漂泊的坎坷,促使他对律诗进行了长期的思索,也激增变革律诗的创新欲望。当他一旦远离朝廷,定居草堂,此前在关中试作的说话般的白话七律,就成了最感兴趣的话题。他尝试用来叙写安宁的日常生活,也用来抒写最常见的送别,甚至重大的政治新闻。这时期的成功,使他留下不少此类名作,为他声价极高的七律增添了新的品种。这些诗的创作意识带着审美上明显的“性僻”观念,他以“浑漫与”的精神吸纳口语俗词与民歌句式,以及大量运用习见易懂的虚词,加上内容的日常生活化,使他的七律发生了巨变,以全新的陌生面孔,显示了七律变格变调最鲜明的亮调。虽然白话七律在后期创作中,特别是夔州七律中,占不到主体,但在变调中却显出生动活泼亲切感人的艺术力量。前人对此每有微词,今人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夔州所作的关于白帝城诸诗,以及《登高》《登楼》《宿府》等,特别是大型组诗《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甚至包括《诸将五首》,使他的七律异彩纷呈,千变万化,博大、沉雄、深厚、质苍、伟丽、苍凉、老健,纵横捭阖,不可一世,而达到了七律的巅峰。充斥郁愤不平与苦闷焦虑,以及厚重坚硬甚或阻涩的风调,显然与温润安和婉丽高亢的盛唐正宗七律格格不入,同样体现了变革创新的精神。然而即使此时杜甫也没有舍弃曾经倾心的白话七律,如有《九日》等。只有把久被忽视的白话七律予以重视,也才能进一步发现草堂和夔州七律变格的趋向,以及存乎不少的文白夹杂的七律。三者合观,更能全方位把握杜律的多种风格,以及与盛唐七律有所变异的本质。
WEI Gengyuan, professor & Ph. D. supervi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责任编校:刘云
The Evolution of Du Fu’s Vernacular Poem with Seven Characters
WEI Gengyuan
Abstract:Du Fu’s vernacular poems with seven characters ar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legant poetic styles prevalent in the prime of the Tang Dynasty. First, those poems are taken from daily life, adopting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sentence structure of folk songs; Second, his vernacular poems with seven characters were first composed in Huazhou and later went on to describe the idyllic life of Thatched Cottage in Chengdu; Third, Fuci Thatched Cottage and Kuizhou vernacular poems further employed colloquial function words, which made the poetic form more mature. Granted these are not main features of his poems with seven characters, vernacular poems certainly opened up a new dimension by exerting influence over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poetic writings.
Key Words:Du Fu; vernacular poems with seven characters; daily life; colloquial function words
作者简介:魏耕原,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06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W059)
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2-0046-07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