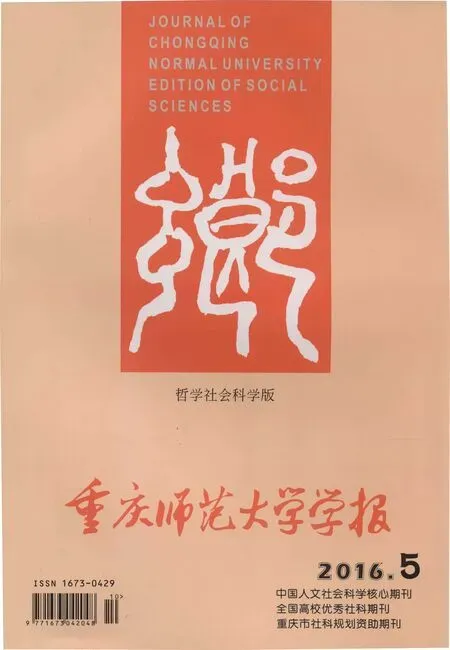王船山太极学说中的有无建构
田 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王船山太极学说中的有无建构
田 丰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3)
王船山对佛老以及在他看来儒学内部的异端之学多有批判,这种批判根植于他对有无关系的阐发,及其对真实存有的重新建构,本文以其太极学说为核心分析其有无概念的建构与意义。
太极;总计无;别计无;体
王船山作为明末遗老,痛于天下之亡而深恶晚明轻狂士风,其著述对佛老以及在他看来儒学内部的异端之学多有批判,与此批判相应的是正学之重建。这都根植于他对有无关系的阐发,及其对真实存有的重新建构,本文以其太极学说为核心分析其有无概念的建构与意义。
一、太极概念
船山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对此“全体”有数种称谓,如“太极”“无极”“天”“浑天”“道体”“阴阳”等,大致说来,它们所指皆同,即宇宙一气流行之大全。仔细分殊的话,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概念又各自描述了这个“全体”的不同面向。台湾学者陈祺助对此做过精当总结:
船山的本体论是一元实有的本体。对于此一本体,言道者可以根据对其诠释之不同,而赋予不同之名……例如:
以其为超绝无对之全体,则谓之天。“其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则谓之天。”
就其为浑沦为一,“大而无尚”,“语道至此而尽”,自具主宰之天则,则谓之太极。
就其为使万物出形入象,出象入形,“众著而共由”之大路,且为万化的主持分剂者而言,则谓之道。
就其为资始资生万物之本体,乃实有而非虚无,则谓之诚。“阴阳有实之谓诚”[1]70
这些概念中,“太极”在宋明道学中具有比较重要的本体意义,本文主要从“太极”概念切入讨论,但在讨论中请读者不要忘记的是,就船山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太极”与天、道、诚等概念所指无二。
“太极”概念出自《周易·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及《庄子·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对庄子“太极”可见最早的解释当数唐成玄英疏:“太极,五气也。六极,六合也。”这种以气解释的思路与孔颖达注《周易》类似,其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只是孔注《系辞》以为“太极”乃先天地之混元一气,成玄英则对应于六极将“太极”解释为五行之气。而俞樾考证则以为庄子“太极”之义当为“天”,并引《释文》对《系辞》的解读:“太极,天也”。此外,《淮南子·览冥篇》曰:“引类于太极之上”,高注:“太极,天地始形之时也”。
以五行之气解释“太极”的思路仅见于《庄子》注疏,且在后世影响甚小,姑且不论。以混元之气解释“太极”则成为后世思想的主要径路之一,虽然在此混元之气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多有分歧。这种思路多倾向于以时空中的某种质料运动解释天地万物之存在来源。此种意态在唐代较为盛行,从孔疏中即可窥见端倪。降至宋明理学,以张横渠为代表的气学一脉对其多有吸收发挥。
另一方面,解释“太极”还有自玄学以降的形而上思路,所谓形而上思路这里指的是认为天地万物之存在根据皆为某最高存在者,至于此最高存在者是有还是无,是外在于万物还是内在于万物的发挥作用,诸家看法皆不同,又可分为不同流派。以此本体论思路解释“太极”,肇端始自王弼,明确提出则为韩康伯,其注《系辞》曰:“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后理学家将“太极”从无转有,重归儒家立场,而其形而上意味却保留下来,程子以一阴一阳者为形而下气,所以一阴一阳者为形而上之道,即天理是也。此种理气二分思路至朱子而大成,朱子思想虽多有变化,其晚年定论仍以“太极”为天理,逻辑上先于气[2]94-99,因于气而显现发用。然而这样做的困难前文已述,不管是在本体论层面还是心性论层面都会造成“一用两体”的尴尬。船山以清算心学与异端为己任,归本于横渠程朱,他的“太极”学说是对前述两条道路的融合,批评了作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超越性本体。
笔者这里所谓超越指的是在变动不居现象之背后另有一更真实的不变存在者,有些思想将此不变存在者理解为外在于现象界之本体,现象界一切事物都是由此本体所生,我们可以称之为外在本体,这种对世界根据的解释往往偏于宇宙论方向。还有些思想强调本体不可离于现象,内在于现象并且对事物具有规定作用,此之谓内在本体,其理路往往偏于本体论方向(此处所谓本体论并非西方ontology的存在论意义,而是对存在者之存在根据或曰存在本质的探讨,更加接近于西方所谓“第一哲学”意义)。船山对这两种本体都做出了批判。我们将从“无”“有”两方面来解读船山的批判。
二、异端批判
要理解船山对佛老二氏本体说之批判,必须从他们的“有无”之分歧入手。我们先来从老氏“虚能生气”这个船山批判之典型切入问题。船山认为“太极”是一切变化与实有的整全大体,而非某种让变化得以在其中发生的虚或无。
绘太极图,无已而绘一圆圈尔,非有匡郭也。如绘珠之与绘环无以异,实则珠环悬殊矣。珠无中边之别,太极虽虚而理气充凝,亦无内外虚实之异。从来说者,竟作圆圈,围二殊五行于中,悖矣。此理气遇方则方,遇圆则圆,或大或小,缊变化,初无定质;无已而以圆写之者,取其不滞而已。王充谓从远观火,但见其圆,亦此理也。[3]12册430
人要画圆珠并不能将其内在的充实画出,就其所绘之图而言,和想要画圆圈者无异,皆画一圆圈,而其所指则迥异。圆珠不是一个中空的场所,所以没有中间和边缘的虚实之别。太极也不是一个虚空之场所,阴阳五行被包裹其中运行。此外,严格来说,太极也不能理解为一个充实的圆球,因为当我们想象一个圆球之时,其前提仍然是在一个已有的空间之中,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作为空间整体的圆球,如果这样的话,太极仍然是在一个已有空间中的存在者。而在船山看来,太极是一切我们能够想象、言说、感知的存在全体,时间与空间也都是基于太极而得以可能,所以太极根本来说不能够以广延意义描述,方圆等广延性都是理气统一体在具体场所中的显现,太极本身是无滞无形无定的。人们之所以要用圆圈来描画太极,只是取圆这个意象的无滞性。
船山针对老子天地橐龠之说,他认为以天地为橐龠之说根本的问题源自其认有为无,无能生有:
视之而见,听之而闻,则谓之有;目穷于视,耳穷于德,则谓之无;功效可居,则谓之实;顽然寂静,则谓之虚,故老氏以两间为橐龠,释氏以法界为梦幻,知有之有,而不知无之有;知虚之虚,而不知虚之实,因谓实不可居而有为妄。[3]12册361
老氏以天地如橐龠,动而生风,是虚能于无生有,变幻无穷;而气不鼓动则无,是有限矣,然则孰鼓其橐龠令生气乎?有无混一者,可见谓之有,不可见遂谓之无,其实动静有时而阴阳常在,有无无异也。[3]12册2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所谓的有与老氏之有意义不同,这种差别就字面意思来看,在于船山指出的,老氏徇耳目之见,穷于耳目之时,便以有为无。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要展开讨论还需要对有无概念意义做进一步分殊。
宇宙太极之“有”与具体事物“有无”之“有”,虽然同为“有”字,意义却不在同一层面。具体事物之有乃是一种与无相对待的有,一切具体事物必然有其生灭,其生是从无到有,其灭是从有到无。其作为“有”是偶然,并不必然而“有”,“有”终将化为“无”,故尔可称为相对待之有无,也就是具体存在者之存在。而宇宙太极之“有”乃是无对待之“有”,是绝对之“有”,也就是存在本身。任何一“物”都是气之暂时凝聚所成,“太极”即是气化流行本身,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物”,不能被理解为最高存在者、全体存在者,或唯一存在者;而是一切存在者得以可能之根据。此处只是一个简要论断,在深入分析“有”之前,我们先来探讨“无”的意义,因为在船山看来“无”是相对的,“有”是绝对的,“无”总是依赖于“有”的。
“无”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的意义,即“无待之无”与“有待之无”。熊十力曾在其《体用论》中将此二者区分为“总计无”与“别计无”,剖分殊为清晰,引用于此:
且世间计无,约分二种:曰别计无,曰总计无。总计无者,如计太虚,空空洞洞,是谓之无。……别计无者,谓于一一事理,或时计为无。……如某书纵在他处是有,而克就我手边说确实是无……所以别计无,是有其所谓无,未可斥以无据。唯总计无,即以为有所谓太虚,本来空洞无物。而从无生有之幻想每原于此,……魏晋玄学之徒多属于此派,其说盖自老子启之也。张横渠以太虚名天,气化依之起,亦有生于无之论。[4]10
熊公以为“总计无”或曰“体之无”为妄说,“别计无”虽则未尝无据,归根结底仍是俗人之浅见,此思想承自大易横渠船山一系。下面的分析将会展示,此两种“无”之义皆为船山所反对。首先是具体事物的“有待之无”,船山继承横渠思想,认为事物之生灭其实乃是一气之聚散归伸,故曰:
明有所以为明,幽有所以为幽;其在幽者,耳目见闻之力穷,而非理气之本无也。老、庄之徒,于所不能见闻而决言之曰无,陋甚矣。……屈伸者,非理气之生灭也;自明而之幽为屈,自幽而之明为伸;运于两间者恒伸,而成乎形色者有屈。彼以无名为天地之始,灭尽为真空之藏。犹瞽者不见有物而遂谓无物,其愚不可瘳已言。[3]12册272
幽明不言有无(张子),至矣。谓有生于无,无生于有(皆戏论)。不得谓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论至则戏论绝。幽明者,阖辟之影也。[3]12册410
就具体一物而言,其有为气之所聚,其无为气散于幽玄,复归太虚。此太虚并非虚无之义,而是无形之气:“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5]如果不是有一个根本在先的气之“有”,就不可能有具体事物之有,无者亦然。将气之聚散幽明理解为具体事物之有无,是将视域局限束缚于当下之一事一物,斤斤于一事一物之生灭得失,此乃俗人之浅见,不知气有聚散而无生灭:“因耳目不可得而见闻,遂躁言之曰无,从其小体而蔽也”[3]12册415。所以“有待之无”其实是人之俗见。
然而,怀持“有待之无”的俗谛不仅仅会使人执着于物,还会造成更加严重后果。如果不是将“有待之无”理解为存在者存在方式的转变,即由聚而散,由显入隐;而是将“有待之无”理解为一个存在者就其自身——而非就变为他者而言——由存在变为“不存在”,有无便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中的有无双方是不可共存的关系,也就意味着“有待之无”已经被理解为可以不依赖于有而存在,即“无待之无”: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免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3]12册411
船山此段话多为引用,其所说的不待立者而言之“无”显然是“无待之无”。其大义为,人所讨论的“无”一定针对某种具体存在者,如毛、角这样的有所立者,对于绝对不存在的对象,我们连谈论它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无”一定是“有待之无”,“无待之无”只是人为构造之幻象。[6]18-43宇宙被理解为一个为万物实存与运动提供场所的虚空也是此幻象之产物。
此外,“无”成为“无待之无”同时也就意味着存有之物和“无”的不相待,这样一来,“体无用有”思路下的体用关系就不再是一物之不同侧面,成为两物之外在关系。是以横渠批评其体用殊绝:“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船山前文对橐龠之说的批判便是基于对横渠此言之注释。
以上所论船山与异端的差别是从“无”的角度而谈,如果我们认同船山之意,即所有对“无”的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基于对“有”的理解,那么显然,儒家与异端更根本性的差别必然来自他们对“有”,或曰何为更真实存在的理解分歧上。佛老二氏所理解的真正的有或真实存在的要义在于不随境而迁者方为真实存在,所以会认为具体事物之生灭变迁证明了“有”的不真实性,并试图去寻找更加真实不变的存在。所以道家所说的“无”之究竟义并非“不存在”,反倒是更加真实无妄之存在,所谓“无”固然有敞空虚空之义,但那只是“道”的显现方式之一。“道”之所以被称为“无”更根本的意义是在于它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故尔无以名之,只能称其为“无”。老子所谓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常无名”,以及王弼所说“无形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欲言无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不可得而定也”,都昭然若揭地指向此义。此种更真实的“无”或“道”无所不通地贯注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中,使其能够获得其具体规定性从而发用,这才是道家所论“无”之意义。佛家在对待现象与本体的思路上与道家有相似之处,因诸行诸色皆为因缘和合而生,缘起性空故万法皆无自性,也即是说,凡变动者皆为不真之现象,唯有不变真如为世间唯一真实存在。虽然佛老二氏,尤其是佛家各宗派对具体事物是否真实存在的判断有所不同,对本体是内在于现象还是外在于世界的理解也有各家分歧,但他们以不变为更真实无妄之存有,且以不变为变化之根基的思路如出一辙。
还需要补充的是,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横渠对佛老的批评并非完全公允,“体用殊绝”“物与虚不相资”的主要指向在于体外于用、用外于体。显然,老氏之“无”的丰富意义非此一言可断,即便是后来的王弼韩康伯诸家所论之“无”体,也不是外在于现象的本体。其实,就中国自身的思想资源来看,从来都是反对外在于现象之本体。张岱年先生也指出,儒道两家本体观念“不以‘实在’与‘幻象’的区别来讲体用……强调体用的统一。即体离不开用,用离不开体”[7],此种外在本体说恐非中国本土资源,而乃来自佛教小乘之论。其传入中土数代之后已遭大乘诸家批驳,如华严宗便是以“理事圆融”立体用不离之说。理学诸儒更是不能同意外在之体,相应地对“太极”之理解也是内在于现象世界的。台湾学者陈祺助对理学诸儒有精要总结:“就太极之生阴阳而言。各家都有一基本共同点:即认为阴阳并不等于太极,但太极也并非在阴阳之外,别为一体,而与阴阳对立者。太极即在阴阳之中与之为体,所以运之、动之,以生之者。”[1]18船山作为横渠的服膺者,其批评固然多有直接继承之处,但更多的则是更加深入的发展。这不仅仅是思想本身的发展趋势所致。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宋初儒者们更多面对的是来自外部异学的压力与挑战;而明末儒者们所要面临的思想症结更多地来自儒家在扬弃佛老之学后,其内部受到所谓禅学空疏之学的浸染影响,所以力图正本清源。对船山而言,需要的是更加精细地分殊清楚儒家内部诸多倾向的正学异端之别,这一点由其《读四书大全说》的精细风格即可略见一斑。故尔,船山之论虽然大多数时候看起来是针对佛老而发,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些批评总也潜在地指向着诸多儒学内部流派。这样我们就不能停留于简单的“体用殊绝”或“物与虚不相资”这样对外在本体说之批判,而要从船山对“有”或曰真实存在的论述出发才能真正正本清源,看清其标举之大旨所在。
三、真实存在
我们从船山对老庄之学的理解入手,从这里可以更好地分殊清楚船山在本体问题上对真实存在之理解。船山专门对《老子》《庄子》做过注疏,而意态颇有不同,其《老子衍》旨归在于“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3]13册15。船山他书对庄子虽多有批判,然而其于庄学专门作《庄子通》《庄子解》严肃疏解,且曰:“凡庄生之说,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3]13册493那么在船山看来老庄之道差别何在呢?
船山认为,庄子之所以不同于老氏异端,而能够引而入君子之道,便在于庄子对浑天全体之理解:
观于此,而庄子之道所从出,尽见矣。盖于浑天而得悟者也。……天之体,浑然一环而已。春非始,冬非终,相禅相承者至密而无畛域。其浑然一气流动充满……物化其中,自日月、星辰、风霆、雨露,与土石、山陵、原隰、江河、草木、人兽,随运而成,有者非实,无者非虚,庄生以此见道之大圜,流通以成化,而不可以形气名义滞之于小成。……皆浑天无内无外之环也……其言较老氏橐龠之说,特为当理。周子太极图,张子‘清虚一大’之说,亦未尝非环中之旨。[3]12册395
所谓“浑天”在船山看来与“太极”无异:“太极一浑天之全体”[3]1册661。而这里的“环”并非前文所批判之空心圆圈,而指一气之浑然流动无始无终。船山明确认为,庄子、周子、张子思想的根本要义,都是此“浑天无内无外之环”。此环中任何一物都是此气“随运而成”的暂时聚合,很快又会回归大化流行,此之谓物化其中,所以“有者非实”。然而,正因一切物皆为气所构成,所以物之成毁有无只是此气之聚合分离,是以“无者非虚”。这样一来,有无之间既非体用关系,也不存在何者更加真实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天地之常并非“无”,而是“有无混一之常”。有无归根结底是气之隐显聚散,此气方为最真实之大有。
不过,这种非虚非实思路初看起来极像佛家缘起性空之论,朱子也曾因此批评横渠为“大轮回”之说。对此还需深入辨析以看清船山学说特出之处。朱子认为:
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8]17册3335
释氏所谓轮回者乃一切有生命者虽然肉体躯壳会坏灭死亡,却皆有某种主体不灭,以另一种生命形式重生于六道中另一躯壳。所以朱子说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他以为横渠之说为大轮回指的是,一切存在事物都由太虚之气聚合而成,散而复归于太虚,归根结底是一气流转,即前文船山所言浑天之环,故尔称其为大轮回。这个说法其实甚不妥当,因为释氏之所以称轮回,其精要乃是一不变主体在变动现象中的穿梭往来,好似一人不断换衣服,却仍是此人,本体与现象两无相待。故横渠批评其“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3]12册25,横渠之要乃在于,性形并非二物,只是一气之清浊而已,本体的流行絪缊即是现象,所以并无一不变本体,生死也不过是气之屈伸往来,自然也就无甚轮回之说。此意船山阐之甚明,他这样诠释《易经系辞》“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原”,有本而生也。“反”,归诸其故也。……《易》言往来,不言生灭,“原”与“反”之义著矣。以此知人物之生,一原于二气至足之化;其死也,反于絪缊之和,以待时而复,特变不测而不仍其故尔。生非创有,而死非消灭,阴阳自然之理也。朱子讥张子为大轮回,而谓死则消散无有,何其与夫子此言异也。[3]1册520
朱子的指责归根结底是因其理解太极为不变之天理,并以此理解横渠之说,自然扞格难入,这在其对“太和”之理解上犹为见出:
问:“横渠说‘太和所谓道’一段,考索许多亦好。其后乃云:‘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却说倒了。”曰:“彼以太和状道体,与发而中节之和何异?”[10]17册3329
横渠“太和”之原义此处姑不论,在朱子门生看来,“太和”如果指的是“道”,就应当是形而上之天理,是体;而“野马絪缊”显然指的是气化流行,是用,故尔“说倒了”。前文朱子部分已有对其“道体”概念的解读,应当理解为太极之理,那么此处朱子的回答就应当被理解为质疑横渠之语气,可以解释为一种反问,大致可以翻译为:他以“太和”来描述道体,这与发用之和还有什么区别?言下之意即为:两者应当是有区别的,这样运用“太和”概念的确如其弟子所言,是“说倒了”。
而在船山看来,“太和”本身就是包括形上形下,体用合一的整体:“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3]12册15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倒是朱子执守一不变本体贯穿于现象的思想更像是释氏轮回之说。这就涉及到了船山对第二种内在本体的批评,显然,这种批评更多的是针对儒家自身思想中的派别倾向。
船山对内在本体之批评的要义在于太极是否是宇宙内在的不变本体,广义来说,也就是世界本身是否有某种不变的根基。船山在解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时对朱子不变本体有明确批评。朱子之说如下:
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9]53
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枢纽,中间些子不动处,缘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谓之极星。天之枢纽,似轮藏心,藏在外面动,心都不动。”问:“极星动不动?”曰:“也动,只他近那辰,虽动不觉,如射糖盘子,北辰便是中央桩子,极星便是近桩点子,虽也随盘转,缘近桩子便转得不觉。……辰非星,只是中间界分。极星亦微动,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之心也。”[10]350
船山批评如下:
北辰之说,唯程氏复心之言为精当(笔者按:程复心曰:“枢,门簨也。天常转动,北辰却是天之北极中间不动处,如门簨相似,故为天之枢也。仍不是不动,只动时还在元处。”)。朱子轮藏心、射糖盘子之喻,俱不似,其云“极似一物横亘于中”,尤为疏矣。使天之有枢,如车之有轴,毂动而轴不动,则自南极至北极,中间有一贯串不动的物事在。其为物也,气耶?抑形耶?气,则安能积而不散,凝而不流?若夫形,则天地之间未有此一物审矣。且形,固能运形而不能运气者也。天枢之于天,原无异体。天之运行,一气俱转,初不与枢相脱,既与同体,动则俱动。特二十八宿、三垣在广处动,北辰在微处动,其动不可见耳。……抑于北辰立一不动之义,既于天象不合,且陷入于老氏“轻为重君,静为躁根”之说。毫厘千里,其可谬与?[3]6册595
二人之差异并非仅只是对天枢北辰这个天象问题,正如船山所言,北辰运动与否归根结底是一个对天道本体的理解问题,对这个问题如果理解不当,就可能陷入老氏重静轻动的无为之学。在朱子来说,任何事物表面的运动背后一定有永恒不变之道枢,否则天地将无常而变乱,所以其所理解之天象亦有一北辰作为天枢,而且此辰并非具体形气所成之星,“只是中间界分”,也即是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之点,所以在此意义上,船山以形气论辩对朱子所作的批评是无效的。船山批评真正的意义是从“天枢之于天,原无异体”这句话开始的,天枢与天并不是一则为抽象本质,一则为形体现象的两种存在形式,而是“一气俱转”。这里的“转”并不是物体围绕某个抽象圆心的运动,而是前面所说的浑天之环,即一气流行,是以虽曰“枢”,而实不殊于天也。所以船山认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根据并非不变之本体,不变者并不比变化者要更加接近真实本质,并进一步阐明,世间万有动为原始样态,静乃相对,动才是绝对:
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至诚无息’,况天地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何静之有![3]12册402
这样一来,世间万有便不再需要一个静止不动本体作为它们存在之根据,或者说万有之本体便是万有自身。那么“太极”实际上并无一核心之“极”,故可曰“无极”:
“太极”之名,始见于此,抑仅见于此,圣人之所难言也。“太”者极其大而无尚之辞。“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已,而不可名之为阴阳,则但赞其极至而无以加,曰太极。“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其实阴阳之浑合者而己,而不可名之为阴阳,则但赞其极至而无以加,曰太极。太极者,无有不极也,无有一极也。唯无有一极,则无所不极。故周子又从而赞之曰:“无极而太极”。阴阳之本体,絪缊相得,合同而化,充塞于两间,此所谓太极也,张子谓之“太和”……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3]1册561
圣人慎言难言太极,因单论“太极”容易造成形而上误解,以其为一切存在者的最高顶点或最核心本质,这样理解的话,便会拘于一隅而失全体。“无有一极”意味着没有一个离于事物的本体,没有一个离于天下之用的天下之体。“无有不极”意味着本体不仅与事物不可分离,更是充盈于事物整体,直可谓事物本身(后详)。“太极”本即浑天全体,并无一极可言,故“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本身即是阴阳全体,因其极大极至而无以加,故曰“太极”。关于“太极”与“阴阳”之关系,陈祺助有细密精审之研究,其结论曰:“阴阳乃太极本然之体,太极是阴阳浑合不分的状态,太极是对阴阳为无所不极、至足无缺之体的赞词,太极是阴阳之气中的主宰分剂之理。”(此处“主宰之理”不能理解为朱子意义上的形而上之体,而应当理解为“理气虽有异名而实则相与为一。”参看陈祺助:《王船山“阴阳理论”之诠释》P27。船山“理”之意义已多有人论之甚详,如曾昭旭《王船山哲学》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陈来《诠释与重建》第三章,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第三章第二节)“太极和阴阳所指之实都是同一内容,然而却各有其不同的义界:阴阳着重其实际存在之材质或气,太极则强调其主宰生化之性或理。阴阳和太极从其实质来说,两者可书上等号。”[1]23-31
那么如果说“太极”作为整全大体绝非“无”,而乃包含万有之大有;“太极”“浑天”乃是永不停息之动,并因此动而成其为真实无妄。那么“太极”是否能理解为一切存在者之集合,或者作为质料之气的运动呢?“太极”作为“大有”与具体事物之有无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四、太极之有
船山如此论述太极之有:
太极之在两间,无初无终而不可间也,无彼无此而不可破也,自大至细而象皆其象,自一至万而数皆其数。故空不流而实不窒,灵不私而顽不遗,亦静不先而动不后矣。夫惟从无至有者,先静后动而静非其静;从有益有,则无有先后而动要以先。……要此太极者混沦皆备,不可析也,不可聚也。以其成天下之聚,不可析也;以其入天下之析,不可聚也。[3]1册1016
船山这里连续用了几组对反的概念来破除将其理解为现成存在者集合的思路,又批评了主张无中生有静为躁根的思路。船山自然不会料到百年之后会有国人以唯物论解释其哲学,他这样强调,是试图避免一些对“太极”的可能误解。
张学智先生指出:“说它(太极)是超时空的绝对体,并非说它是现世之外主宰现世界的‘第一推动者’,而是说它是世界大全本身。它是有,永远存在,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时间空间不足以形容它,规范它。”[11]553船山强调这个是为了说明宇宙全体从来皆有,未尝有一个阶段为无。船山说“空不流”“实不窒”“不可析”“不可聚”,则是要避免将“太极”理解为具体之物的思路,不管是所有物的集合,还是唯一的整全大物。因为如果“太极”是一物,那么它便会实而窒、不可析,且必定有始终可间;如果“太极”是所有物的集合,此集合中诸物必定需要某种虚空处所方能聚合运动,便会空而流、不可聚,可分彼此而可破。由此可见,“太极”全体之“有”,并不能等同于具体事物之“有”。我们需要先讨论“太极”作为整全大体的意义,然后才能够处理其与具体事物之关系。
所谓整全,一般理解是与部分相对,不过整全与部分的关系也可以有许多方式,在船山这里,部分应当被理解为整全的显现,船山主张“由用见体”,这种显现必定是在“用”中的显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
“太极”整全义集中体现在船山易学之中,限于主题所限,这里仅就船山著名命题“太极有于易以有易”略微展开,其曰:
“易有太极”,固有之也,同有之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有之则生,同有之则俱生矣。故曰“是生”。“是生”者,立于此而生,非待推于彼而生之,则明魄同轮,而源流一水也。……故不知其固有,则绌有以崇无;不知其同有,则奖无以治有。无不可崇,有不待治。故曰“太极有于易以有易”,不相为离之谓也。[3]1册1023
“易”在这里并非指《周易》一书,而是指包括乾坤阴阳,变易无方的大化全体。“易有太极”之所以说“固有之也”,是因为太极不是外于宇宙全体的现象外之本体。所以,如果不明了这一点,就会贬低现实世界而崇尚外在虚空本体。“同有之也”指的是太极就是此大化全体,而非其中的某种支配性规范性本体,理解此意,才不会依赖那个飘渺之体去限制有的意义。不过,“易”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太极”,因为“是生两仪”,“易”还包含乾坤两仪以及由此生而出的卦爻。这里的“生”不是由此生彼之生,而是“立于此而生”的“是生”。陈祺助解释说:“太极和仪象卦爻并不是互相外在、对立的不同之物,以致太极之生两仪等,乃必须太极先立于此……即在此太极之体上而生之,所以称为‘是生’者;是者,此也。”[1] 32“魄”在此指月初生或圆而始缺时不明亮处,魄与明便如同阴与阳,不是月亮生出两种不同东西,是同一月亮因时而显现或隐藏自身之别。源头与下游也是同一水之不同样态。理解此两譬喻,便能理解船山所谓“固有”“同有”之生,也就是同一者在其自身内部原本就蕴含有的差异性与丰富性之显现,是全体与其自身的关系,即全体之大用。对于此“生”船山有多处论述:
生者,非所生者为子,生之者为父之谓。使然,则是有太极无两仪,有两仪无四象,有四象无八卦之日矣。生者,于上生也。如人面生耳目口鼻,自然赅具,分而言之谓之生耳。……要而言之,太极即两仪,两仪即四象,四象即八卦,犹人面即耳目口鼻,特于其上所生而固有者分言之,则为两,为四,为八耳。邵子之术,繁冗而实浅,固其不足从,以经考之自见。故读易者以不用先天图说为正,以其杂用京房、魏伯阳、吕岩、陈抟之说也。[3]1册789
所自生者肇生,所已生者成所生。无子,叟不名为父也。[3]1册1024
非太极为父,两仪为子之谓也。阴阳无始者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3]1册562
固合两仪、四象、八卦而为太极,其非别有一太极以为仪、象、卦、爻之父明矣![3]1册1024
这几则论述不约而同地反对父子譬喻,因为父子为二体,“若太极为父,阴阳为子,则有父无子之时,亦等于承认有有太极而无阴阳之时。本无阴阳之太极却因动静生出阴阳,这又回到船山所批判的‘虚能生气’‘无能生有’之‘体用殊绝’的二元论。所以太极不能孤立于阴阳之上之外,以做为仪象卦爻之父。”[1]32邵雍之说所以浅陋,正因其将“生”外在机械地理解,好似有一本体不断破成两片,如此便会造成有太极而无阴阳之时,船山以为其说及先天易云云皆为外于现象之本体学说,来自道家影响,故尔不可遵从(这里船山的批评也隐含地指向朱子。《朱子语类》: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义……”曰:“是如此。”参看《朱子全书》P3130)。耳目口鼻之于人面,是其本来自然就有之物,合而言之则曰人面,分而言之则曰耳目口鼻,这才是太极与两仪卦爻之关系。所谓分而言之,固然是人言,但人之所以能够分言阴阳两仪,并不是人妄自命名,而是源自太极自身之发用流行,所以太极之生阴阳两仪除了自然本有之义,还有显现之义,此显现用船山的话说是“功用发生之谓也”。
周子曰:“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生者、其功用发见之谓也。动则阳之化行、静则阴之体定尔!非初无阴阳,因动静而始有也。”[3]1册659
周子太极图说通常被理解为宇宙在时间中生成阶段的描述,在船山的阐释中,周子之论与其说是宇宙论毋宁说是本体论,而且是本体作为全体在其自身之内功用发生的描述。按照前面船山对“生”的理解,阴阳与太极同在固有,绝非因于动静而有,所以这里的“生”便必须理解为显现。显现的意思是说:“阴阳虽先于动静而有,但其性情功效却必须因动静之用才能彰着发见。”[1] 34“阴阳虽非因动静而有,却因动静而始发见,由动静之用而彰着两者判然相异之性情功能。”[12]97
“两仪”,太极中所具足之阴阳也。“仪”者,自有其恒度,自成其规范,秩然表见之谓。“两”者,自各为一物,森然迥别而不紊。……乃自一画以至八卦,自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极于三百八十四爻,无一非太极之全体,乘时而利用其出入。其为仪、为象、为卦者显矣;其原于太极至足之和以起变化者密也,非圣人莫能洗心而与者也。[3]1册561
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些都是太极全体之显现,都是原于太极之和原本即具有的,它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因“时”不同,显现出的方式以及显密程度有异。
结 语
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船山之“太极”作为“大有”之“全体”的两个特点。
其一,“太极”之“体”必定是能动能生成之体,而非静态规范性之体,而且其能动性并非不变质料之机械运动,那样必然若非“实窒”便需要一虚空之橐龠以供质料运动,终将导致有一物“鼓其橐龠令生气”的思路。所以此“动”应当结合“生”来理解,却又不能理解为父生子,此生彼之生,而是具体规定性从“大有”中显现之义。具体规定性的显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鸟兽草木直接从大化流行中跃然而出,“大有”或曰“太极”必须首先显现为阴阳两仪这样的几乎无任何具体规定性的两体,然后才能逐步由此两体交相作用,从而进一步分化呈现为杂多乃至万物。但这个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在时间之中的宇宙形成过程,这是王船山与德国古典哲学“绝对精神”在历史中自我展开的道路非常不同之处。在船山看来,至少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不能直接理解为在时间之中的自然历史进程。
船山“太极”之“体”的第二个特点是,此“体”之展开即是其“用”,“用”不外于“体”并与“体”相函,也就是说其体用关系在最原初意义上不是两物之关系,或者一物与世界之关系,而是整全大体与其自身之关系,此即“体用相函”。此与其“生”之义相关,如果“生”是由此全体生彼个体,那么体用关系的原初意义就是两物之间的关系。体用关系如果被理解成为两物之关系,不管此关系是逻辑的先后环节,还是因果链条,都将最终走上超越本体的道路。船山虽然没有明确道出此意,但其思想内在地力图避免此种道路乃是不争事实,这也是明末诸公在本体论建构上的常见倾向,这一点从宗主心学的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亦可获得旁证。
[1] 陈祺助.王船山“阴阳理论”之诠释[M].高雄:复文图书公司出版社,2003.
[2] 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 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熊十力.体用论[M].上海:上海书店,2009.
[5]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船山全书 [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 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J].安徽大学学报,1983,(3).
[8] 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 (明)胡广等纂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1]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2] 曾春海.王船山易学阐微[D].台北辅仁大学哲学研究所,1978.
[责任编辑:左福生]
Wang ChuanShan’s Ontology of Being and Nihility in his Tai Ji Theory
Tian 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bei Wuhan 430063, China)
Wang Chuanshan gave much criticism to the heresy in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This criticism was based his explic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and nihility and his reconstruction for the real Be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his ontology of being and nihility in his Tai Ji theory.
Tai Ji; nihility; not being; body
2016-07-12
田丰(1977-),男,河南信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61319003)阶段性成果。
B2
A
1673—0429(2016)05—0051—09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