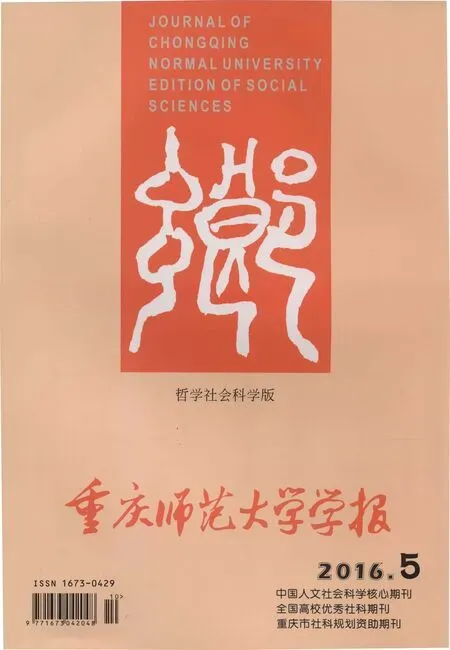《金瓶梅》的食色书写与人生迷失
岳 立 松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金瓶梅》的食色书写与人生迷失
岳 立 松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金瓶梅》在食馔品类、饮食方式、欢饮情节等丰富多彩的饮食描写中,饱含情色意味并具有深刻文学寓意。《金瓶梅》体现出由食传情的文字蕴意,将角色对食物的享用引向身体欲望层面。食、色是西门庆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以此建构小说的线索指引与价值导向,形成食色相融的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展开,预示人物命运。饮食中蕴含着对情欲的贪恋、显现出欲望的膨胀。饮食也是妻妾争宠的工具,是一种权力媒介与情色媒介,带有鲜明的男权社会特色。西门庆在食色狂欢中陷入迷失,走向自我欲望的膨胀,这是一种感官的迷失,也是人生的迷失。
《金瓶梅》;食色;情色媒介;欲望;人生迷失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饮食描写,既有对食物种类、食品制作的精细描绘,亦有对日常饮食、筵宴场面的铺陈缕述。小说重点展现了西门庆一家的饮食生活,尤其突出西门庆与妻妾、妓女的日常宴饮,无论是食物描述、抑或饮食场面往往与情色相关联,在食色书写之中潜隐着丰富内涵。目前学界在《金瓶梅》饮食种类、所反映的社会风俗等方面成果颇丰,但对于小说饮食与情欲这一重要表现层面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由食传情的文字蕴意
《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916饮食与男女是人类的自然天性,也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必备条件。在晚明追求享乐的文化背景中,“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糜为高”[2]123,富豪之家的饮食更是铺张繁富,呈现世俗文化精神的缩影。《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的吃穿住行等日常消费极尽奢华,有意僭越传统礼制,而饮食凸显了豪奢富贵与情色意味,透露出时代风貌。《金瓶梅》描写的饮食极为丰富:有荷花饼、顶皮酥果馅饼之类的糕点,有梅汤、银丝鲜汤等汤品,有金华酒、葡萄酒等酒水,有六安茶、果仁泡茶等茶品,更有蒸鲥鱼、腌螃蟹等繁多菜肴。上述饮食品类并不在于追求文人饮食的精细雅致与文化品味,而是较多展现出世俗的饮馔之丰、宴集之盛,折射出晚明时代特色与社会文化意蕴,正如学者指出《金瓶梅》如此频繁、细致、广泛地描写饮食,“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独特的时代氛围使然”[3]。
《金瓶梅》中的饮食书写具有鲜明的文化隐喻功能,除了权钱交易的权力指向外,其描写直指家庭生活,饱含情色意味。“食、色,性也”,食与色作为人类的两种基本需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常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笑笑生亦将食物与情色紧密相连,惯以饮食比喻男女欢爱。
《金瓶梅》在鸡鸭鱼肉、茶汤酒品、煎炸腌煮等食物描写中反映了日常的口腹之欲,也衬托出庸俗的男女情事,有着极为丰富的情色意指和文学寓意。《金瓶梅》中的食物或以谐音、或以形象来代指身体,尤其是喻指带有色情或性欲指向的身体,从而超越食物本身的固有定义。如西门庆与应伯爵在妓女李桂姐处调笑言欢,《朝天子》一曲即借用食物传递情色意指:“这细茶的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偢不采叶儿楂,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原来一篓儿千金价。”(12回)[4]122“一篓儿”谐音“一搂儿”喻指搂抱这一暧昧动作,“嫩芽”喻指女子娇柔身体,这支曲子形象地利用谐音和事物性状引发隐喻,烘托男女欢情的气氛。
《金瓶梅》的俗语中也常出现以食物喻身体、以饮食喻情色的情况,具有民间俗语惯以食物作喻的特征。如六十一回西门庆与韩道国老婆云雨后返回家中,被眼尖心细的潘金莲察知异常,可西门庆矢口否认,于是潘金莲扯开其裤子一探究竟,道:“可又来,你‘腊鸭子煮到锅里,身子儿烂了,嘴头儿还硬’”(61回)。潘金莲用煮腊鸭子这一食物制作的形象幽默比喻来形容身体,有力揭穿了西门庆的谎言,使西门庆无言应对,从而为自己进一步行动争取了主动权。当宋惠莲成为西门庆姘头时,被人打趣道:“我听见五娘教你腌螃蟹——说你会劈的好腿儿。”(23回)螃蟹经盐渍时会伸展开腿,此处巧用螃蟹身形,以腌螃蟹这一食物制作来比喻宋惠莲与西门庆的偷情,呈现出以食语寄情色的表达方式。
小说中的饮食书写并非单纯物象,常具有双重寓意,能发挥故事预示效应。食物书写构建起情色弥散的氛围,推动情节发展,如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情事即在茶酒饮食之中展开。潘金莲偶然邂逅西门庆,而王婆则在他们眉目传情中发现端倪,遂一意撮合。王婆为前来打探消息的西门庆做了个“梅汤”,第二次又做了个“和合汤”,梅与媒同音,“梅汤”意味着作媒之意,“和合汤”亦有玉成之意。小说借助这两道汤品显现了西门庆猎取美色的意图,同时也点明王婆欲作男女私会中间人的意图,于是在此情境中食物代替语言成为一种表意媒介,发挥着语言所不能直接表明的妙意,鲜明流露出色情意味并传递故事发展的预兆。
《金瓶梅》中的食与色相互勾连,常常在饮食阶段即先行展开情色意指,具有明确的暗示意蕴。身体、饮食与情色紧密关联,鞋杯即是这一类情欲之物。鞋杯又称金莲杯,是将酒置于小脚女子的弓鞋之内,以代替酒具。此一物件将女子身体部位及其修饰品与饮食相结合,将杯皿酒器与女性躯体的想象视作一体。小脚是明清时衡量女性美的重要标准之一,构成一种性爱的象征,“它的产生、维持以及人们对它的狂热都是因为它与性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5]227套在小脚上的鞋也成为饱含身体意味与情欲诱惑之物,用这一物事来盛装美酒极具情欲暧昧。潘金莲的小脚是其引以为傲的资本,她的绣花鞋也成为取悦西门庆的工具,鞋杯成为情欲想象的诱引。第六回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两个殢雨尤云,调笑顽耍。少顷,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第6回)在酒浓意蜜的情色氛围中,二人进入情爱交欢,在具有性爱意旨的小脚促进中,美色与饮酒交融,创造了更为情色化的欢愉场景。
《金瓶梅》善于将饮食与身体相连,借用文字间的关联暗示由身体引发的情色信息,传递出情色旨意。饮食在小说中不仅指向具体的食物层面,还被抽象、提取、赋予了更多隐晦的含义。小说通过对食物的色、味、形等特征具体而形象的描绘,使食物承载了情色意涵,将人的口腹之欲由食物引向更深层的身体欲望之中。《金瓶梅》通过食物书写将情色与性爱形象化,在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的印象与感触中,带人进入更为形象也颇具意味的情境之中,食物也成为一种话语呈现、意向表达,展现出食物——身体——情色的旨意关联。
二、食色相通的叙事线索
食与色体现人类的原始欲望、生存需要,《金瓶梅》中频繁而又细致的食、色描写,显现出西门庆对两者的极度追求与无限欲望。食,早已超越裹腹需求而有着豪奢展现、权力追寻、情色调剂等更丰富的意义,形成小说外在追求的线索;色,是西门庆追逐的目标、生活的乐趣,也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构筑小说内在隐含的导引,因此食色相通构成小说的叙事线索。食、色是西门庆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两者密切相关,或是先食后色、或是食色相交,食与色融汇勾连,如若离开了食之诱引与激发,《金瓶梅》中的色则少了氛围与情调。兰陵笑笑生将食与色这两个生存必需上升至欲望层面来观照,勾勒出无节制的获取欲望而终将导致家败人亡的结局。
《金瓶梅》中饮食场面常与男女调情、欢爱相结合,食与色的有机融合将饮食的物质层面导向身体的欲望层面。小说中饮食与欢爱的盛宴,并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随地皆可展开。这些酒宴多有调情暗示之用,饮食并非是为了满足食欲,而是为增添色欲。食物的色香味,使人受到味觉刺激,感官刺激遂贯穿于身体,激发身体欲望的膨胀,进而在饮食的盛宴中上演一场情欲盛宴。
《金瓶梅》的饮食书写不只停留在吃的层面,在对食物色香味的精细描述后存有丰富意蕴,它将男女在饮食场景中的暧昧之意,发展到男女的欢爱,身体的交合。小说描写的很多场合中,酒食是作为礼节性接待之必需品,但酒食往往仅是前奏,饮食宴请终将走向世俗的男女欢爱。潘金莲、李瓶儿、林太太等人与西门庆暗通款曲皆是借助于酒食:男女双方会面在看似恭敬有礼的宴饮场合中展开,却又暗指情爱层面;女子往往精心准备茶点肴膳,流露出对西门庆到来的企盼与欣喜,男女最终在传杯递酒中发展至情色的缠绵。在饮宴中身体是被注视的身体,视觉冲击与味觉感受相交融,小说人物从饮食美味和秀色可餐角度达至身体的亲密接触,进而发展至云雨欢爱。
《金瓶梅》警戒人们注意“酒色财气”之害,可酒与色两者往往交融,正可谓“三杯花作合,两盏色媒人”。日常宴饮少不了酒之助兴,小说中的酒更成为色之先行与诱导。潘金莲与西门庆两相有意之时,就少不了酒这个“色媒人”。在西门庆的酒食相劝下,潘金莲早已是情欲荡漾,身体正是在酒的刺激下受到感官诱惑,从而“哄动春心”勾起自身欲望。当潘金莲因西门庆家中繁忙而被冷落,在相思煎熬中终于盼到西门庆时,“妇人教迎儿执壶,斟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飏,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那西门庆连忙拖起来,两个并肩而坐,交杯换盏饮酒”(第8回)。一场情感期盼在交杯换盏中展开,进而是情欲的释放。
《金瓶梅》中的饮食盛宴表面上颇合人情往来之礼,实际的关注视角却从宴饮引向欲望,逾越礼法约束走向情欲盛宴,也将小说引向情色叙述。李瓶儿与西门庆初次偷期密约即是在一场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讲究礼尚往来的答谢宴中展开。李瓶儿为感谢西门庆照顾其丈夫花子虚,特设酒摆宴,“看见西门庆过来,欢喜无尽,迎接进房中。掌着灯烛,早已安排一桌齐齐整整酒肴果菜,小壶内满贮香醪。妇人双手高擎玉斝……吃得酒浓时,锦帐中香熏鸳被,设放珊枕……两人上床交欢。”(第13回)这次由李瓶儿亲自操持的礼节性宴请,不过是两人进一步走向情色的借口。李瓶儿在饮食的准备与呈递中融入了对欲求的渴望,宴饮过程与情色传递相结合。西门庆初会林太太也是在躬身施礼、叙礼相还的礼仪形式中展开。林太太早已安排宴饮来盛情款待西门庆,将对西门庆的情意融入酒食之中。“须臾大盘大碗,就是十六碗热腾腾美味佳肴,熬烂下饭,煎炸鸡鱼,烹炮鹅鸭,细巧菜蔬,新奇果品。旁边绛烛高烧,下边金炉添火。交杯换盏,行令猜枚,笑雨嘲云,酒为色胆。”(第69回)二人的再次相会亦在宴饮中展开,七十八回描写林太太于房中安放酒食,“丫鬟拿酒菜上来,杯盘罗列,肴馔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妇人锦裙绣袄,皓齿明眸,玉手传杯,秋波送意。猜枚掷骰,笑语烘春。话良久,意洽情浓;饮多时,目邪心荡。……酒酣之际,两个共入里间房内。”(第78回)林太太宴请西门庆的意图在于借助饮食的引导与先行,将表面出于感恩、答谢层面的礼节性交往推向更深层次,带向身体与欲望的浪潮之中,成为一种危险的逾越。《金瓶梅》虽有对食物种类、品相的描绘,但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男女欢爱。饮食作为情欲媒介,成为性爱的前奏。酒食的色味诱发情欲与身体的多重感受,如此策略即可推进此前假意的礼仪交往,使之从一种貌似端庄的境况转至暧昧情境,直至情欲泛滥,达到超越规范、僭越伦理、突破道德等目的。
饮食不仅是男女性爱的前奏,也常常作为欢爱的曲终,小说突出始于食、行于色、终于食的叙事模式。《金瓶梅》常有身体交欢后又重整杯盘,再次享受酒食的描写。如七十七回西门庆与郑爱月云雨之后,即“整衣理鬓,丫鬟复酾美酒,重整佳肴,又饮勾几杯”。七十九回西门庆与王六儿偷欢后,也是“再添美馔,复饮香醪,满斟暖酒”,西门庆又吃了十数杯酒,乘马返家后迎接他的是另一场情欲之战,也是其人生的终结。黄霖先生指出:“在整部小说的结构中,作者有意将一些情节安排成食与色的互动:常常是一场饮食活动的结束,即是一场男女之事的开始;当一场淫戏收场,又一场酒宴即开局。周而复始,故事就在食与色的互动中拓展。结果,西门庆的生命也就在这食欲与性欲的交攻中消竭。”[6]173-174饮食与享用食物时暧昧亲密的情调相连结,《金瓶梅》对饮食活动反复、细致的描写显现出人们对食物、酒品的过度追求及其所传递的情色意指。情色隐含于食物准备与享用之时,在一场场饮食之中蕴含着对情欲的贪恋,显现出欲望的膨胀。饮食与情色也形成食色相通的叙事线索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推动着情节的展开,预示着人物的命运。
三、食色欲望与人生迷失
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金瓶梅》将饮食背景多集中于家室之中,叙写由围绕家室所发生的一系列生活情景,以家庭视角诠释日常行为与人物心态。《金瓶梅》中的饮食不仅体现着对食色之欲的过度追求,也是妻妾争宠的工具,是一种带有鲜明男权社会特色的权力媒介。男女共同分享饮食,在饮食之中充分调动着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各感官,其意义不重饮馔而在于其所透视出的性别与权力的深层内涵。
《金瓶梅》通过饮食关联着男女行为、情感、关系、权力,结构成一张张家庭男女、社会关系的网络。西门庆重视通过饮食结交官吏、扩展利益,其在府宅中宴请新任巡盐御史,极度铺张的一次筵宴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特权,这是一次官商联盟与权力寻求。晚明社会好货好色,人的自然本性得到肯定与张扬,但也过度放纵了人的欲望,将人基本的两种需要——食色的追求放大到极致,表现为极端的欲望,如袁宏道《觞政》倡言:“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7]205市井之人放纵声色、追求享受、膨胀欲望,无论是风俗节令、筵宴交往等活动中饮食极尽铺张,日常情欲追逐,体现的是权力与欲望。
饮食于西门庆而言,是其身份标志、富有地位的显现,是其在官场、商场结交的工具,也是其情色放荡的诱引,妻妾争宠的媒介,于此可照射出他的家庭生活及整个人生。日常饮食在生活化的氛围中展开,遂为情色媒介,在西门府中演绎着一场场食色交欢的图景。女子利用饮食控制男子的口腹之欲,诱发情色暧昧,又基于家庭成员的结构因素而演变为妻妾争风吃醋、争宠夺爱的工具与手段,于是围绕家室的饮食与情色体现出欢愉与沉溺,占有与征服,暗含权力的意义。饮食不仅是情色媒介,也发挥着权力媒介的作用。
基于饮食本身具有的取悦功能,《金瓶梅》中女子所制饮食体现出女子争宠的策略与手段。小说中的女子并不经常亲手制作饮食,而一旦亲自制作便在此中寄寓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她们将饮食作为笼络男子、捕获男子之心的工具。女子所制饮食融合食、色元素,其意义恰在于经过女子纤手调制的食物所具有的女性色彩,既承载男性的欲望,又通过染有女性温热和情色诱惑的方式,最终演变为情色与夺宠的媒介。
《金瓶梅》中女性所制饮食最有特色者当属蚫螺,拣制酥油泡螺当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制作工艺,只有李瓶儿、郑爱月才有烹制这一令人百般回味美食的高超技艺。李瓶儿亲手拣制泡螺儿,令西门庆倾心不已。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看见酥油蚫螺,道:“我见此物不免又使伤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会拣。他没了,如今家中谁会弄他!”这一奶油类甜食外形精美、入口甜香,“浑白与粉红两样,上面都沾着飞金,就先拣一个放在口内,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第58回)这一美味让人如此享受,引发与人物密切相连的美好回忆。即使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也因此睹物思人。妓女郑爱月亦将其作为争取西门庆爱宠的手段,特意让郑春给西门庆捎去一盒果馅顶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儿。经女子之手所精心制作的食物上烙有女性身体的色彩,传情达意,成为女性争取爱宠的一种策略。
众女子亲自洗手剔甲调制日常食物以表对西门庆的心意,争宠献爱。李瓶儿曾“亲自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儿”;潘金莲在期盼西门庆时,也曾亲手制作一笼裹馅肉角儿,等西门庆来吃。潘金莲还曾亲点茶品,“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泼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欣喜。”(第72回)出于金莲之手的泡制香茗,让西门庆获得美色诱引下的味觉享受。韩道国老婆王六儿为迎接西门庆剥下果仁,顿下好茶;奶妈如意在李瓶儿死后也亲手剥果仁,挑拣几碟精味果菜,斟酒,亲剥炒栗;郑爱月不但亲手拣制点心,还将亲口磕的瓜仁儿递呈给西门庆。
小说中烹制手艺最高者非宋惠莲莫属,其精处在于平常之中见功夫:当家手艺是会烧好猪头,火侯把控极佳,“只用的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着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第23回)。宋惠莲卖力烹制猪头是要讨好潘金莲,希望获得潘氏允诺而继续与西门庆来往。饮食可向男子示爱,也可向女子示好,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争宠,具有指向情色的终极旨意。
女子手中的食物易博得男子欢心,而经过女子口中浸润的香饼、果仁则更具情色意味。《金瓶梅》中屡屡出现香茶饼,此物将茶叶与香料等压制而成饼状,可直接放入口中以增加唇齿香气。口递香饼传递的不仅是食物,还是一个明显的调情过程。男女在传递食物的吸吮中传情达意,展开具有性爱意指的情色探索。香饼所激发的嗅觉与口唇所激发的触觉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浓厚的情绪渲染,引发感官世界的刺激。饮食与情色结合,颇具性指向之意。《金瓶梅》十九回描写潘金莲与西门庆“两个一递一口儿饮酒咂舌……妇人一面搂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里……口中噙了一粒鲜核桃仁儿,送与他,才罢了。”宋惠莲噙酒哺与西门庆吃的食色交欢中,关心能否获取香茶、银钱等更实际的物质利益。在口传食物的亲密接触间,换取实利。西门庆与郑爱月交欢前也是亲手将细果奉与西门庆下酒,“又用舌尖噙凤香蜜饼送入他口中”(第77回)。女子以口噙食物获取西门庆宠爱,而男宠书童也如法炮制“口噙香茶桂花饼,身上薰的喷鼻香”(第34回),增强其举动的色情成分。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更极端地体现着食色纠葛,流露男性权力心理的膨胀。李子转变为情色道具,成为西门应实施性虐待的工具,它让潘金莲在受虐中、在恐惧状态中既有享受又有刺激。醉闹葡萄架正是对潘金莲此前嫉妒李瓶儿有孕一事的惩罚,这是男性权力的一次胜利。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妻妾争宠、家庭争斗的背后隐藏着男性权力的掌控。女子以各种手段向西门庆示爱,从而获取物质的享用及欲望的满足,巩固加强她们的地位与受宠爱的程度。女性争夺权力最有效的手段即是食色,食是色之预热,色是食之满足。女性围绕西门庆才能获得物质与欲望欢愉,这加强了男性对自身能力的炫耀及地位优越性的认可,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征服。女子的仇怨、烦闷、喜乐、欢愉,乃至对生活的态度与自我生存的肯定与追寻都在男性身上实现,凸显男性权力的权威性。
在以家庭为故事发生地的饮食活动中,弥漫着争宠的气味。孙雪娥在西门府中虽排行第四,但在家中并不得宠,遭受得到西门庆偏宠的春梅之欺凌。十一回中因西门庆晨起出门等着吃荷花饼、银丝鲊汤,却被春梅一番挑唆,于是围绕早餐问题向雪娥踢了几脚,大骂起来。一场权力与地位的争斗即因饮食而上演。已是周守备夫人的春梅私通陈经济,借机报复深知其偷情底细的厨娘孙雪娥。九十四回春梅分付雪娥做鸡尖汤儿,孙雪娥尽其所能,然而春梅却嫌寡淡,重作一碗后,又嫌忒咸,借此由头,把孙雪娥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开肉绽,领出去办卖。春梅为达到男女偷情之目的,即将饮食作为报复的手段和工具,从而排除异己,获取情欲的满足。饮食成为一种手段与工具,成为夺取宠爱的策略,饮食背后彰显出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男性的权力。
《金瓶梅》食色、欲望与权力相纠葛的鲜明旨意尤为突出的体现在西门庆身上。西门庆的人生缘于对食物、欲望与权力的追寻,尤其是对性欲的狂热与征服。词话本中西门庆出场与死亡皆是与食色相连,其出场是在领略潘金莲帘下风情后到王婆处吃茶,西门庆之死亦是在美食醉酒后纵欲而亡:先是与王六儿饮食之后纵欲,又连饮十数杯大醉而卧,接着被潘金莲送服过量胡僧药,纵乐直至身亡。《素女经》曾指出“醉饱而交接”的危害,西门庆恰恰死于过度饮食后纵欲,因食色而亡身。食欲和性欲是人最基本的欲望,而西门庆恰恰突破了常人所需,表现出极端的欲望追求,欲望的膨胀最终导致死亡结局,这一结尾也是作者对酒色财气而亡身的最好写照。
《金瓶梅》中食与色相纠缠,饮食及其宴饮场面中体现着男女关系及人物心理。食色也建构着小说的结构,推动情节的发展,预示人物命运走向,揭示出小说的深层主题。《金瓶梅》丰富而频繁的饮食书写所绘制的饮食与男女,饮食与欲望场景,体现着晚明社会的世态人情,此中蕴含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男性权力。西门庆在食色的狂欢中、在饮食的盛宴中陷入迷失,走向自我欲望的膨胀,这是一种感官的迷失,也是人生的迷失。
[1]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张瀚.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王平.《金瓶梅》饮食文化描写的当代解读[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6).
[4] 兰陵笑笑生,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 黄霖.黄霖说金瓶梅[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袁宏道著,钱伯诚笺注.袁宏道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左福生]
Diet Writing and Life Lose oftheGoldenLotus
Yue Lisong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127, China)
TheGoldenLotushas rich and colorful diet on category of food delicious, diet and drinking. The writing has full of erotic and profound literary meaning.TheGoldenLotusreflects text information and direct role for food for the body desire. Food and sex are important part of Xi Menqing in daily life, to construct novel clues guidance and value guidance, form the food hue melting narrative clue, plot and character destiny. Diet contains of erotic desire, showing the expansion of the desire. Diet is also a harem rivalry tools, is a kind of media of power and erotic medium,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Xi Menqing get lost in food carnival,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desire, this is a kind of sense of lost, is lost in life.
theGoldenLotus; food and sex; erotic medium; desire; life lose
2016-08-12
岳立松(1979-),女,文学博士,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园林文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世文学中的两性观念研究”(编号:10BZW069)的阶段性成果。
I24
A
1673—0429(2016)05—00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