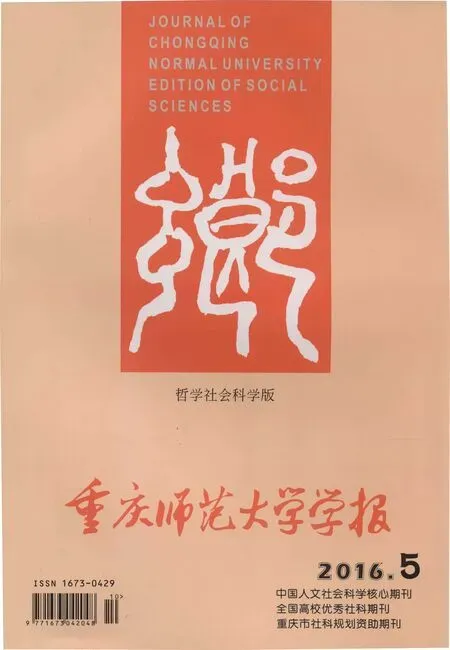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
——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吴 国 杰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
——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吴 国 杰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爱尔兰移民小说;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记忆场;口述历史
在英语小说中,有一个为数众多的作家群共同描写的题材——爱尔兰人外出移民。这些作家或者亲历了移民过程,或者作为移民后代从父辈或祖父辈那里亲闻了这一历史事件,或者对这一段历史尤感兴趣,查阅了大量史料,他(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素材,创作出了一大批以 “爱尔兰移民”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有描写作者自己的移民经历的半自传和自传体小说,也有基于作者见闻和史料查阅进行创作的纯虚构小说(共多达四十余部,部分作品将在文中提到),这一批数量可观的作品作为记忆的媒介,生动、细致地叙述了小说中每一个移民的个体切身经历;由于爱尔兰移民是一个历时长、规模大、次数多、在人类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历史现象,这一批作品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忆场”,担负着唤醒、存储并传递爱尔兰移民们的集体记忆的功能;从叙述个体记忆到承载集体记忆,以“爱尔兰移民”为题材的这一批文学作品作为一部部“口述历史”例证了从记忆中的历史到历史的记忆场所的转化。
一、叙述个体记忆
作品数量丰富的“爱尔兰移民小说”(“The Irish Emigration Fiction”)叙述了众多在不同历史时期移出爱尔兰的移民们的个体生活体验,由于作者精确、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每一部作品展开的是每一个移民的“图像化”的鲜活的个体记忆。无论是自传体小说,还是基于见闻之上的纯虚构小说,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批作品皆以写实见长,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小说主人公移民经历中的某些重要细节进行了生动详细的描写。以海上历程为例,乘船横渡大西洋的经历是每一个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的重要记忆,从登上远洋轮船的那一刻起,爱尔兰移民开始了从身体到心理的双重流亡之旅,也许是因为生命中重要时刻的记忆总是让人无法割舍、难以忘却,所以无论时间相隔多么久远,每一个爱尔兰移民总能清晰而准确地回忆起海上的日日夜夜。在爱尔兰移民小说中,很多作品都对远洋海轮上的场景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写,比如,在《暮色》(TheLightofEvening, 2006)中,叙述者蒂丽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回忆了她那个时代移民的船上亲身经历,蒂丽于20世纪10年代中期移民美国,该时期移民乘坐的远洋海轮环境恶劣,小说对当时的场景进行了摄像机般的回忆:
我们被安排在拥挤的下等船舱里,里面经常弥漫着浓烈难闻的烟,有生火做饭冒出的烟,也有燃着的煤油灯里冒出的烟,船舱里所有煤油灯即使在白天也得全天候的燃着。每天我们都在为抢占炉子吵架打架,当你拿着自己的食品好不容易挤到一个炉子旁边,却发现这个炉子已经被一个人占有了,手里还拿着长柄杓或其他烹饪器具,警告你不许靠近,这是她的炉子,她的领地。我们大多数人的主食是饼干和咸鱼。我差一点就被渴死了,口渴是所有糟糕事情中最糟糕的事,我一直想着家里的水井,想象着把一个水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一满桶干净的水,一股脑把它喝了下去。……船上的工作人员每天从楼上下来两次,骂骂咧咧地吼叫着要我们收拾好我们的残羹剩饭,归整好我们脏乱的东西。[1]
由于移民船上移民们饮用水和食物的缺乏,以及恶劣的居住环境导致的疾病的侵袭,很多移民在航程中丧生,《暮色》中船上经历的这一章中,作者用无限痛楚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新生婴儿的夭折。蒂丽的回忆跟相关历史史料的叙述是一致的:
移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不幸,使爱尔兰人受尽辛苦。大部分爱尔兰移民,是搭乘货船到美国,这些货船设备相当简陋,例如,由于船舱中没有厕所的设置,因此秽物、臭味和疾病相当普遍。每一移民分到一个3×6尺长的搁板,供他们睡觉。这些搁板,留着前一次的航程中的移民所留下来的无法消除的恶臭。每一个搁板之间,只有2寸宽。约有一半的船取用不干净且充满泥沙的河水,作为饮用的水。船上的医护人员比例不到2%。船上的移民男性与女性并不分开。……不良的食物、饮水及卫生设备使远渡重洋的移民,在航行过程中,对健康及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2]
个体记忆的鲜活性除了体现在作品中清晰而准确的细节描写和与相关史料记载相符的描写之外,还体现在作品中的描写与时代相符。尽管描写对象相同,都是在回忆海轮上的场景,但《暮色》中与《就是这儿》(’Tis, 1999)和《布鲁克林》(Brooklyn, 2009)中迥异的描写明显体现出了时代的差异性。《就是这儿》和《布鲁克林》中的麦考特和艾丽丝都于20世纪50年代初移民美国,尽管就个人经济状况而言,三人相差不大,都是爱尔兰社会底层贫民,但是,由于此时造船技术和经济水平都远远超过40年前,麦考特和艾丽丝乘坐的轮船在硬件设施、船内环境以及航海技术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从爱尔兰出发到抵达美国,蒂丽在船上艰难地度过了两周(1845-1852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们乘坐帆船,她们需在海上度过六至八周),而仅一周时间,麦考特和艾丽丝就抵达美国,除了在航行时间上缩减了一半之外,40年后的轮船在硬件、软件设施上也与40年前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由于时代的不同,同样的场景呈现出千态万状,正是这种差别性,这一批同一主题的文学作品中的每一部小说描写的是每一个移民的个体生命体验,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每一个移民的个体记忆。由于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史料相符)和时代性(与时代相符),这一批作品呈现出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记忆。
二、承载集体记忆
尽管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叙述单个移民的个体回忆,但所有作家都在避免让读者将每一部作品当成某一特定个人的过往回忆,这体现在大部分小说都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由于叙述者不参与整个叙述故事,作者与整个事件之间有了一个距离感,读者不易将作品里的叙述当作是作者本人对过去亲身经历的回忆。即使在自传体小说中,五位作家也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来避免读者把小说里的叙述当成作者本人的回忆。在《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Ashes, 1996)和《就是这儿》这两部作品里,尽管作者在作品封面上注明了“回忆录”字样,但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却采用了现在时态来讲述发生在40多年前的往事,而且,作者在写这两本“回忆录”时已是年近古稀之年的老人,尽管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但是叙述者却是从一个儿童和青少年的视角来讲述整个事件,于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错觉,误把它当成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小男孩身上正在进行的故事,而不是将小说里的叙述当成作家本人的过往回忆。《暮色》和《为流浪者祈祷》(PrayfortheWanderer, 1938)也为自传体小说,尽管作品里描写的内容都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相符,但读者也难以将作品里的叙述当成作者本人的个体回忆,在《暮色》中,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的多重叙述视角,而且,在采用第一人叙述时,叙述者为作者母亲而非作者本人。《为流浪者祈祷》不仅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而且身为女性的作者却以男性身份出现在作品中。在爱尔兰移民小说中,无论是人称的刻意采用还是叙述者在年龄和性别上所做的有意变换,作者都是为了避免让读者将作品里的叙述当成某个特定个人(小说主人公或作者本人)的个体回忆,而是为了突出一个写作意图——每一部作品讲述的是“任何”一个移民的个体生命体验,承载的是“任何”一个移民的个体记忆,因此,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个体具有“类型”意义。
个体记忆总是与集体记忆相关联的,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认为,个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依托和基础,他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有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3]“集体记忆”一词是哈布瓦赫在推翻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对主观时间和个体主义意识的强调之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最原初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才有记忆,同时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回忆,因此记忆总是集体的,个体记忆只有在集体的框架下才能形成。[3]随后,哈布瓦赫又顺理成章地推而论之,“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3]因此,“集体记忆”一词也有望文生义层面的含义,即一个群体的记忆。
爱尔兰移民是一个能用特定时空、特定属性来界定的巨大的群体。遭受被殖民统治长达八百多年之久的爱尔兰国内长期的政治冲突、宗教纷争、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期爆发的“大饥荒” (“The Great Famine”)使得爱尔兰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历时长、次数多、规模大的向外移民潮。仅以某一阶段移民去美国的人数为例,“1820-1920的正式记录表明,这期间来美国的爱尔兰移民为4,578,941名,19世纪40、50年代是爱尔兰移民到达的高峰,40年代有780,719名爱尔兰移民,50年代有914,119名爱尔兰移民” 。[4]历史文献提供的是抽象、单调的数据,爱尔兰移民小说用具体的家庭为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直观、更易理解的数据。《安琪拉的灰烬》里麦考特一家三代人都曾在不同时期向外移民,外祖父在母亲出生之前移民澳大利亚,父母两人都曾移民去美国并在美国相识,之后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举家搬回爱尔兰,麦考特于18岁又移民美国,两个弟弟和母亲随后也移民来到美国。《布鲁克林》里的艾丽丝一家共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哥哥都移民英国,艾丽丝移民美国,只有姐姐一人留在爱尔兰照顾年迈的母亲。《暮色》中的两代人母亲蒂丽和女儿伊丽劳拉都有移民经历,母亲蒂丽20世纪10年代移民去了美国,后来在祖母的一再要求下回到爱尔兰并结婚生子,女儿伊丽劳拉在20世纪50年代移民英国,并一直居住在英国。爱尔兰移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爱尔兰移民小说里叙述的个体记忆是每一个具有移民经历的爱尔兰人的共同记忆。当作品出版之后,作为一个纸质的记忆媒介,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这一批文学作品实施了存储、唤醒和传递集体记忆的功能。
哈布瓦赫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记忆会趋于淡化或渐趋丧失,除非通过与具有共同过去经历的人相接触,来周期性地强化这种记忆,或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3]爱尔兰移民们在移居国生活稳定下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在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中,移民的记忆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消失。然而,由于一些承载了集体记忆的东西(比如现在每年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定期举行的圣·帕特里克纪念日庆祝活动等)的周期性出现,移民们的个体记忆一次次被唤醒。爱尔兰移民小说这一批作品具有节日纪念庆典同样的功能,它们通过在文学作品中保存移民的个体记忆,并经作品被广泛阅读,来唤醒移民们的集体记忆。除了唤醒移民的集体记忆之外,文学作品还发挥了将集体记忆传递给移民后代的功能。米歇尔·K·雷诺兹(Michael K. Reynolds)的《伯爵们的逃离》(FlightoftheEarls, 2013)以史诗般的表现形式讲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的传奇故事,美国多产畅销书作家垂西亚·高尔(Tricia Goyer)在看完这部小说后, 写下书评:“我祖父的祖先在大饥荒时期从爱尔兰移民到了美国,我一直知道这个事实,但是直到我看了《伯爵们的逃离》,我才真正了解了祖辈们的移民是怎么一回事。”[5]
移民经历是爱尔兰移民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被唤醒和被传递给移民后代的过程,也是爱尔兰移民寻找归属感、认同爱尔兰身份的过程。民族身份认同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强制力,能驱使移民们回忆起即将毁灭的共同记忆。也许正是因为承载着爱尔兰移民共同记忆的爱尔兰移民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作为原因之一),散居世界各国的爱尔兰人才有那么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正如学者陈静瑜在美国所观察到的那样,爱尔兰裔美国人族群总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2]“记忆场”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 1931-)把某一个地理场所、纪念碑、艺术品、甚至一个历史人物、某个纪念日等等都纳入了“记忆场”,随后,德国文化记忆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对“记忆场”这一概念做了总结,他认为:“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无论物质的、社会的或精神的)都被称作为‘记忆场’。”[6]根据诺拉和埃尔对“记忆场”所做的定义,沉淀了所有爱尔兰移民的集体记忆的爱尔兰移民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一个记忆场,它跟国旗、纪念庆典、历史遗址、地标建筑物等一样,是一个能够唤醒民族记忆的意象,能促使爱尔兰移民进行民族身份认同。如果如诺拉所说,“记忆场是记忆与历史的相互交替”,[7]那么,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链接的是爱尔兰移民的个体/集体记忆和爱尔兰移民史这两个页面,每一部爱尔兰移民小说展示的是移民个体/集体记忆中的历史,而爱尔兰移民小说群作为一个整体记载的是爱尔兰移民史这一整段历史的记忆。
三、历史的“记忆场”
大规模向外移民是爱尔兰历史上一件特殊的事件,它对爱尔兰和移民移入国 (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前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估计流散在全世界的爱尔兰人及后裔有七千万人,超过四千万美国人宣称有爱尔兰血统,[8]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爱尔兰、美国和加拿大都有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博物馆,而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爱尔兰移民们的故事的这一批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当爱尔兰移民史这段历史以移民们的个体/集体记忆为具体内容,以口述历史为讲述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爱尔兰移民小说作为一个“记忆场”将历史凝固在了文学作品中,这也正是诺拉的“记忆场”的功能,她曾说过,“记忆场所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让时间停止,阻止遗忘。”[7]
作品数量可观、主题覆盖面宽的爱尔兰移民小说群中被凝固的是一段多棱镜透视的、时间跨度长的历史,在这一批作品中,读者看见的是一幅恢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画面上既有历史浩劫下大饥荒年代爱尔兰农村的社会全景,也有二十世纪初爱尔兰城市地图手绘;既有远洋海轮遭遇暴风雨时的海上惊魂,又有在移居国日常生活的风平浪静;既有挥泪告别家乡亲友的依依不舍,又有他乡遇同乡的相扶相携;既有在移居国生存艰难而回归故里的无奈,又有再次移民时的满怀憧憬;既有笃定的爱尔兰天主教信仰,又有为能在移居国提升社会地位皈依新教的动摇;既有移民前在爱尔兰的田园生活以及土地斗争,又有移民后代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小城市中所体验的悲欢离合;既有一代移民的浓浓乡愁,又有二代移民的族群认同和回归移民的身份危机;既有会简单读写只能在移民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十九世纪移民,又有受到良好教育在移民国从事白领工作的二十世纪移民,等等。由于作品的写实主义风格,小说家们带着读者穿越时间隧道回到了移民时代,历史跃然于纸上,昨日得以重现,移民时代的社会全貌、移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体验一览无遗地在读者面前犹如画卷般展开。……除此之外,爱尔兰移民小说这批作品还凝固了诸多历史细节。
以“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小说为例,由于该时期就该主题进行创作并出版作品的小说家们自己都是移民,她们亲历了这一历史事件,因此,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她们在创作小说时,非刻意间就能将读者带入了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爱尔兰,在她们的作品中,无论是人名、地名、实物还是社会经济现状等等都得到了真实再现。以小说《遗失的念珠》(TheLostRosary,1870) 为例,小说中的人物大都采用爱尔兰人典型化的姓,该小说中的人物有 Mr. /Mrs. O’Meara, Mrs. McGlone, Berney McAnley, Alick McSweeney, Mary O’Donnell 等,O’ 和 Mc (即“孙”和“子”的意思)是爱尔兰人普遍采用的姓氏。除了人名,小说也真实再现了地名,大饥荒时代爱尔兰移民小说几乎全采用真实地名,在小说中常被提到的地名都为爱尔兰中、西部农村地区,如克雷尔(Clare)、蒂珀雷里(Tipperary)、罗斯康芒(Roscommon)和梅奥(Mayo),这是因为当时移民几乎全来自这些中西部贫穷地区,目前爱尔兰最大的大饥荒博物馆(National Irish Famine Museum)就建立在罗斯康芒。在梅奥的一些地方,当时出现了村子里所有人要么饿死,要么背井离乡外出移民,整个村子空无人烟的局面。这些地区的爱尔兰农民的大量出走对爱尔兰本族语言——盖尔语(Gaelic)也具有致命的打击,由于英国对爱尔兰长达八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英语是爱尔兰优势阶层、佩尔(the Pale)区以及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居民的日常使用语言,而古老的盖尔语只在爱尔兰西部贫穷地区的农民之间使用,随着大饥荒时期该地区大量爱尔兰人饿死或移民海外,在爱尔兰盛行了两千年的盖尔语当时像潮水一样突然衰落下去。另外,当时的实物也在小说中得到了真实再现,比如在小说《安妮·赖利》中,作者特意提到了移民们离开爱尔兰时行李包裹里的亚麻布(安妮为邻居南希几年前移民美国的女儿捎带亚麻布匹;跟安妮乘坐同船的杜菲太太带着儿子和亚麻布匹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这些细节能唤醒爱尔兰移民们对亚麻生产的历史记忆,自18世纪后20年到19世纪前30年亚麻纺织是爱尔兰主要的农村经济,当时,即使在西部最贫穷的Mayo, 也有亚麻家庭纺织作坊,1830年后由于受到贝尔法斯特亚麻机械纺织生产的冲击,爱尔兰西部农村家庭作坊纺织的亚麻没有了市场,之后她们纺织亚麻几乎仅为自己使用。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充斥在小说文本中,由于真实再现历史细节,以及文本中体现出的历史真实感,爱尔兰移民小说这一批文学作品作为 “记忆场”,真实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爱尔兰。
结语
由于时代背景是重大历史事件,再加上以爱尔兰移民为题材的小说数量多,作品内容涉及面宽,故事来源为作者亲历、亲闻或史料,加之作品采用了有助于加强故事可信度的叙述元素和结构,从这一批爱尔兰移民小说中,读者看到的是一段涵盖了众多历史细节的完整、延续、立体的历史。由于文学自身固有的属性——虚构性,一直以来,文学都被认为是对现实进行的诗意的呈现,但是,当一大批量作品描写的是历史上数以近千万人之多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且绝大多数作者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时,那么,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应该能被认为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现实进行的如实呈现了。如果把爱尔兰移民小说中所有作者当作亲历事件或亲闻、所知事件的讲述者,所有读者当作听众,那么爱尔兰移民小说就是一部部内容丰富的爱尔兰移民“口述历史”,如此,爱尔兰移民小说也就有了史料意义,这一批大格局、大气象的文学作品完全有理由被拿来做社会学、历史学的参考资料。难怪爱尔兰历史研究学者玛格丽特·麦考顿(Margaret MacCurtain)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宝贵资源,她曾在学术文章中明确表示:“没有文学作品的帮助,历史研究很难完成让社会思考其自身特征这一任务……爱尔兰历史上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总是在爱尔兰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9]当新历史主义者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时候,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历史的记忆载体。
[1] O’brien, Edna.TheLightofEvening[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6.
[2]陈静瑜. 美国族群史 [M].台北:国立编译馆,2006.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Daniels, Roger.ComingtoAmerica[M]. New York: Harper Perenial, 1990.
[5] Reynolds, Michael K.FlightoftheEarls[M].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Group, 2013.
[6] 阿斯特莉特·埃尔.什么是文化记忆研究?[A].冯亚琳等主编.中外文化第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7]皮埃尔·诺拉.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场[A]. 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 Laxton, Edward.TheFamineShips[M]. London: Bloomsury, 1997.
[9] MacCurtain, Margaret. The Historical Image [A].Ariadne’sThread:WritingWomenintoIrishHistory. Ed. Margaret MacCurtain. Galway: Arlen House, 2008.
[责任编辑:陈 忻]
Fresh Memory and Frozen History: the Irish Emigration Novels Functioning as the Site of Memory
Wu Guo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Each one of the Irish emigration novels narrates the fresh and alive memory of each individual emigrant; however, when they are read by the readers who share the same experience as the protagonists and accordingl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ir ethnic group, Irish emigration novels turn into the medium of certain parts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site of memory” convey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When the history in the form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is written into the literary works, in literature can be found the frozen historical facts and historical truth which has dissolved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under the challenge of the new-historicism. Apart from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census and the museums, the literary works with the Irish emigration as the theme is another materialized form of memory of the history of that period.
Irish emigration novel; individu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sites of memory; oral history
2016-06-19
吴国杰 (1974-),女,重庆奉节人,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爱尔兰文学和英国文学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爱尔兰移民小说研究”(13CWW027)。
I106
A
1673—0429(2016)05—003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