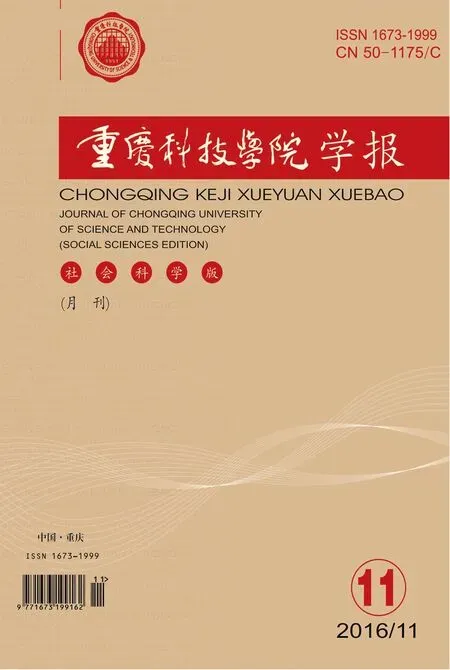《文心雕龙》的“情”“志”矛盾辨
——兼与归青先生商榷
冯艳梅
《文心雕龙》的“情”“志”矛盾辨
——兼与归青先生商榷
冯艳梅
《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巨著,历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其的研究成果更是不可胜数。近来,归青先生发表了《刘勰诗学观中的内在矛盾》一文,引发了学者们又一轮思考。对文中“刘勰诗歌性质观中的矛盾”论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从古代诗歌“言志”与“缘情”关系,《文心雕龙》的“情”“志”细说,刘勰的“情志观”三个方面,论证了“情”与“志”二而一的不可分割关系。
《文心雕龙》;“情”;“志”;“情志”;二而一
《文心雕龙》自成书以来,对它的研究便一直不断。从国内来看,研究者唐代有刘知几,宋元之际有王应麟,明代有杨慎,清代有纪昀,近代有李祥和黄侃,现当代有范文澜、周振甫、杨明照、王元化等人;从国外来看,研究者美国有汉学家休斯和宇文所安,日本有户田浩晓、兴膳宏和斯波次郎等人。可见,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都非常广泛。迄今为止,笔者搜索的有关研究文章达1 000余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2015年第2期刊载了归青先生的《刘勰诗学观中的内在矛盾》一文,文中论述了刘勰诗歌性质观中的矛盾,认为刘勰在理论上高举言志说而实际上则是一个缘情论者。笔者认为刘勰的言志说与缘情论看似矛盾,实则对立统一、不可分割。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历史问题的延续
归青先生认为,就《文心雕龙》中关于诗歌“言志”与“缘情”的论述来看,刘勰的诗学观念存在矛盾之处,但这并不是刘勰本人诗学观的矛盾,而是言志说与缘情论历来就没有明确的区分。“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诗论的传统。朱光潜先生认为,“‘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1]6,这对中国诗论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诗言志”一语作为文学术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2]30。“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在这方面的作用。”[3]2所以,古人在此基础上,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认为诗作为言志之诗,要教化人们的思想,引导道德的走向。由此,很多学者把“诗言志”中的“志”限定在教化人伦、改造人心的意义上。
据《论语》记载,孔子常与弟子论“志”。孔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4]82孔子与弟子言志,其志都是从修身、治国来谈的,故“志”是有政治倾向的“怀抱、志向”。
《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63郭绍虞先生在此篇后的说明中指出,“志”与“情”是二而一的东西。《毛诗序》将“志”与“情”相结合,为缘情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原来“情”隐藏在“志”下。而陆机的《文赋》则使缘情论浮出了水面。然而,过去的一些批评家将“情”与“志”分开,割断了二者,未免偏狭。唐代的孔颖达明确指出二者不可分割。《春秋左传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5]1455《毛诗正义》云:“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5]6明清亦有学者将二者混用。可以说,“缘情”是在“言志”的基础上提出的,之前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只能从教化功能来理解“志”,但“志”中也含有“情”,只是当时人们无法撼动这棵文坛古树,陆机的《文赋》才将“情”的成分从“志”中提炼出来。可见,区分“言志”与“缘情”是很困难的,二者有同有异,但不能就此认为二者是矛盾的。
二、《文心雕龙》的“情”“志”细说:刘勰的二者混用
笔者统计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中“情”“志”二字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49次和82次。在全书50篇章目中,“情”字的出现率高达80%,“志”字为68%,相对较低,但绝对比率依然很高,可见刘勰对“情”“志”的重视。不同的比率说明,“情”与“志”是不能划上等号的,但二者是否是矛盾的呢?刘勰对此作出了回答。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次将“情”“志”进行对举、并举和连用。《辨骚篇》云:“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7]47,将“情”“志”二者进行对举;“这是称赞《楚辞》中的篇章抒发哀伤之情,写得美丽动人。‘哀志’就是‘伤情’,‘志’和‘情’在这儿都是‘怀抱’即心中所存想之意”[8]42,用对偶的形式,将“情”“志”相对举出,二者在刘勰这里是可以当同义词来使用的。《明诗篇》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引用朱自清的话为此句进行了义证:“这个‘志’明指‘七情’,‘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缘情’作用也就包在其中。”[1]37情志并举在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证。刘勰在《明诗》中将顺美匡恶与惆怅切情并提,并将二者进行了融合。《养气篇》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7]647认为文章是顺随情志与绞尽脑汁所作,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悦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将顺随情志与逆向操作情志进行对比,突出“养气”是保持旺盛创作精力的必要因素。《附会篇》云:“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7]650刘勰将“情”“志”联结为“情志”一词,以此来概括文学的内容与思想感情。
“情志”作为一个词并不仅仅出现在《文心雕龙》中,还出现在其他文章中。例如,《尹文子大道下》云:“乐者所以和情志”[9]8;《文赋》云:“颐情志于典坟”[3]170;《文章流别论》云:“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3]191。而“情志”一词虽不是刘勰首创,但在其作品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陆侃如、牟世金在《文心雕龙译注》中将“情”“志”译注为“情志”,分别为9次和27次。例如:
《杂文篇》云:“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7]255译注:“东晋郭璞的《客傲》,情志鲜明而文采丰富。”[10]222
《章表篇》云:“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7]408译注:“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10]313
《情采篇》云:“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7]538译注:“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信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10]406詹锳先生对此义证:“在《情采》篇中,‘情志’是统一的,只是‘志’更偏重于思想因素而已。”[11]1146
《原道篇》云:“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7]2译注:“大舜作歌,已是抒写自己的情志了。”[10]100
《明诗篇》云:“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7]65译注:“所以,‘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10]138在心中就是志,发而为言就是诗,诗即抒心中愤懑。此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写:“《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3]88并无差别。
《神思篇》云:“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7]493译注:“志气:作者主观的情志、气质。”[10]360
像这种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不管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还是历代研究者的译注都没有明确将二者进行区分,这足以说明刘勰将二者看成是一个统一体而非归青先生所说的矛盾论。
三、刘勰的“情志”论:二者互为补充
既然把“情志”作为一个词,那么,怎样对其进行定义才比较恰当呢?王元化认为“情志”是“表明构成文学内容的思想感情”[12]206。而思想感情作为“情”“志”的内涵,二者又是如何统一的呢?
第一,从诗歌的性质来说,“志”是对《诗三百》总体风貌的概括,“情”是对《离骚》创作路线的总结。而《诗三百》以“思无邪”著称,文章雅正,符合国家的政教要求,但若干篇目中的“志”不仅有政教内容,还有其他意思。《诗经·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6]304“按毛、郑的解释,此诗歌颂文王夫人,有政教意义,但‘志’字本身只是心思之意。‘志在于女功之事’,即用心于女功,与政教无干。”[8]43《诗经·郑风·狡童》云:“昭公有壮狡之志。”[6]140“壮狡之志,谓童心、不成熟的心思。”[8]43可见,仅从政教来理解“志”就将其含义缩小了。而“情”在《离骚》中作为一般抒情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但它也可以用于政教。屈原在《九章·惜诵》中多次谈“情”,如发愤以抒情、情与貌其不变、又莫察余之中情、恐情质之不信等。这种种“情”,谁又敢说其无关教化,不含忠君讽谏之情,而以此来否定屈原的爱国之心呢?所以,从文学性质和功能来看,“情”“志”是可以相通的。
《文心雕龙》中的《乐府篇》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7]102其中的“志”就是情感;《征圣篇》云:“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7]15刘勰在这里提到的圣人之情,也是有关教化的。
第二,就“情”“志”作为文学内容的要素来看,《文心雕龙》中有“性情”“七情”“世情”“任情”“五情”“情性”“情趣”“才情”“情源”“情貌”“闲情”等,这些词中的“情”都是一种感性因素。而“志”是文学中的理性因素,如《文心雕龙》中的“志足而言文”“强志足以成务”“志思蓄愤”等,“志”都有思想意志的意思。后代的部分学者从此义出发,狭义地理解二者的意思,走入了极端。例如:程廷祚承袭诗教说推崇义理,着重强调其思想意义;袁枚提倡性灵说,标举其感情抒发,他们都把自己的文学视角局限在狭小的一隅而丢失了广袤的天地。
刘勰从这种文人各执一端的圈子中跳出,将二者二而一,认为二者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因此将“情志”并举,经常将各为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概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辞海》对“情志”的解释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术语,最早见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谓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基本的理性内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种本身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是属于感性范畴的感情和属于理性范畴的思想互相渗透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情志是冲突激起人物行动起来的内在要求。这也相当于希腊文中的‘情致’、‘激情’、‘动情力’等词所蕴含的意义。”[13]2276《宗经篇》云:“义既极乎性情。”[7]21《诠赋篇》云:“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7]136《章句篇》云:“明情者总义以包体。”[7]570《辨骚篇》云:“山川无极,情理实劳。”[7]48《诠赋篇》云:“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7]135这些都充分表明,“情”在一定情况下是包含着“义”“理”成分的。因此,刘勰在文章中既提倡“圣因文而明道”,又赞赏“为情造文”,他把二者作为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的条件。
综上所述,归青先生所言刘勰的诗歌性质观中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四、结语
关于“言志”与“缘情”的讨论已久,这可以说是中国文论的基本问题。本研究从《文心雕龙》文本出发,重新梳理了刘勰对“情”“志”关系的看法。这个问题可以用“复杂”二字来描述,因为从古代到现当代,从国内到国外,至今学界对二者的界限都没有划清。缘情论在言志说的基础上提出来,就确定了二者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情”“志”确实有相通之处,故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经常将“情志”作为一个词语来运用。有的学者只看到了二者的差别,而忽略了二者的联系,因此形成了比较偏执的观点。笔者认为“情”“志”的差别是存在的,但并不代表二者是矛盾的。
[1]朱自清.诗言志辨序[M].上海:开明书店,1947.
[2]尚书[M].慕平,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杨明.文心雕龙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尹文.尹文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1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编辑:文汝)
I022
A
1673-1999(2016)11-0080-03
冯艳梅(1991-),女,西南大学(重庆400715)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诗学。
2016-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