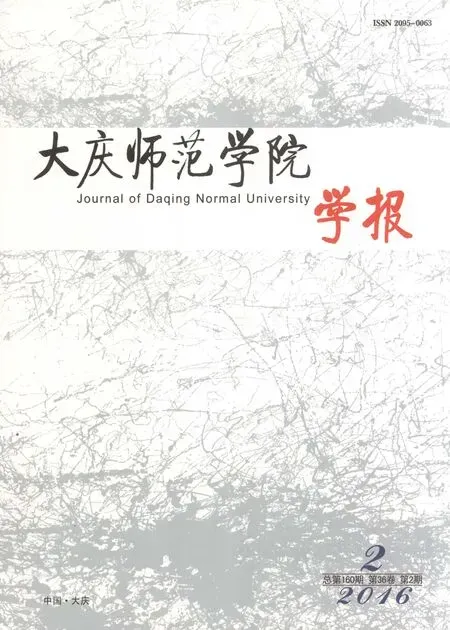“好歹”的词汇化、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
周晓彦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好歹”的词汇化、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
周晓彦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好歹”一词形成于宋元时期,本是由语义相反的“好”和“歹”构成的并列式短语,在句中充当主语、宾语或定语。在发展过程中意义逐步泛化,其整体意义不再是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这时候“好歹”初步实现其词汇化。在使用过程中其句法位置更加自由,可以用于谓语动词之前充当状语,甚至可以位于主语之前起到一定的篇章连接功能,再加上其构成成分本身具有评判性的语义基础,在使用过程中说话者的主观情态凸显,“好歹”最终虚化为表情态的语气副词。
关键词:好歹;词汇化;语法化;动因
“好歹”是现代汉语口语中较常用的一个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张谊生(2004)列举了8个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反正、高低、横竖、左右、死活、好歹、早晚、迟早。其中“反正”的语法化程度最高,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全面、透彻。而对于“好歹”的研究还比较欠缺,一些专著在谈到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但并未对其作详细的论述,目前对其进行的专文研究也只有两篇:方一新、曾丹(2007)认为“好歹”有名词和副词两类,认为副词“好歹”即可表时间又可以表语气,并且论述了“好歹”的主观化问题;闫文文(2009)认为通过重新分析,“好歹”语义虚化,使用频率的提高使其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句法环境的改变也是其语法化的一个动因。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涉及“好歹”的语法化问题,但未对其语法化过程做一个系统的分析、论述,方、曾文中认为“好歹”作副词可以表时间,这一点值得商榷。另外,“好歹”语法化的动因除了闫文提到的三个因素之外,其构成成分本身的语源义以及发展过程中词义的融合是其能够实现语法化的先决条件;语音的组块化也是其词汇化、语法化的一个推动因素。
一、“好歹”的词汇化历程
(一)临时组合阶段
“好歹”形成于宋元时期,在组合之初“好”和“歹”之间分界十分明确,各自的意义也很实在。如:
(1)一时间价钱腾贵起来,只买得有就是,好歹不论。(明《二刻拍案惊奇》)
(2)但是爹娘的说话,不论好歹真假,多应在骨里的信从。(明《初刻拍案惊奇》)
(3)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元《窦娥冤》)
(4)婆婆道:“不知好歹的贱货!(明《二刻拍案惊奇》)
(5)妇人家不认得银子好歹,是个白晃晃的,说是还得官了。(明《二刻拍案惊奇》)
以上例子中,“好”“歹”各自的意义都很实在,即“好”“坏”。(1)—(4)中“好歹”即“好坏”:“不论好歹”,即不管货物好坏,“不知好歹”即“不知道好坏”;(2)中“好歹”相当于“对错”,(5)中“好歹”相当于“真假”。虽然(2)(5)中所表示的语义与“好”“歹”本义有些许差别,但上例句中“好”和“歹”各自意义都很明确,在句中分别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好”“歹”之间界限分明,各自保持自身的意义。这时“好”和“歹”只是处于临时组合阶段。
“好歹”在使用过程逐步演变为“偏义复词”,如:
(6)颇奈大耳汉无礼,酒筵间搬调俺父亲,论俺弟兄好歹。(元高文秀《襄阳会》一折)
(7)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姓名也便休了。(明《水浒传》)
(8)吴氏见了达生,有心与他寻事,骂道:“你床醉了,不知好歹,倒在我床里了,却叫我一夜没处安身。”(明《初刻拍案惊奇》)
这几例中,“好歹”其中一个词的词义脱落,例(6)中“论俺弟兄好歹”根据文意可知是“论俺兄弟歹”其中“好”的语义脱落。(7)同(6)。例(8)“不知好歹”语义有“好”来承担,其中“歹”的语义消失,在这里只是起到陪衬音节的作用。这两例中“好歹”所表达的语义并不是“好”和“歹”语义的组合,而是由其中一个来承担,这时“好”与“歹”之间的分界并没有消失,只是选择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来承担整个词的意义,而摒弃了另一个构词语素的意义,从而形成“偏义复词”。这时“好歹”还不是词,是短语义的偏指而已,偏向哪个语素义也不是固定的,而是由语境决定的。因此,本文赞同雷冬平(2006)的观点:“好歹”的语法化与其发展为偏义复词这个阶段没有关系。
(二)意义融合、分界消失的词化阶段
随着“好”与“歹”并列连用的频率逐渐提高,“好歹”整体所表示的意义不再是“好”与“歹”意义的简单相加,其构成语素之间的分界逐步消失,“好歹”整体表示一个新的概念,其所表示的意义也更加泛化。董秀芳指出:“当一个形式在意义上发生了抽象或转指的转变,它的整体意义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的较为直接的联系就被割断了,前者不能再由后者得到直接索解,一个原本可以切分的意义组合变成了一个不能清晰切分的记忆单位,这就表明这一形式在意义构成上已经词化。”[1]59随着“好歹”使用范围的扩大,它所表示的意义也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泛化的过程。如:
(9)就烦与我除了根罢。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时,就见好歹。”(《西游记》)
(10)将明,他怯战而走,把洞门紧闭不出。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西游记》)
(11)大汉见个男子在房里走出,不问好歹,一手揪住妇人头发,喊道:“干得好事!”(明《二刻拍案惊奇》)
这几例中“好歹”意义明显不只是“好”与“歹”意义的简单相加,(9)(10)两例,“好歹”表示“结果”,例(11)表原因、事情的原委 。“好”“歹”两个词本身就带有对事物的评判性,而事情的结果往往也有好坏之分,因此用“好歹”来指结果。“好歹”这种语义的发展是通过“转喻”实现的。这时“好”与“歹”之间的界限已经完全消失,凝固为一个词,“好歹”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词汇化。
二、“好歹”的语法化过程
并列词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整体的句法功能与构成成分的句法功能一致,称为向心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一旦发生了转类(conversation),即整体上从一种词类范畴转化为另一种词类范畴,其整体功能与构成成分的功能变得不一致,就变为离心结构。相应的,整体意义与组成成分之间的意义也有了较大距离,词义的分析性减弱,综合性增强,其词汇化程度最高[1]60。“好歹”是由“好”和“歹”两个形容词语素组合而成的反义并列式复合词,在其临时组合阶段,“好歹”与其构成成分“好”“歹”的语法性质保持一致,仍然是形容词。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语义的引申和句法环境的综合作用,“好歹”逐渐由形容词演变为副词,词义进一步虚化,进而实现其语法化。如:
(12)自古木杓火杖儿短,强如手拨刺,爹好歹看我分上,留下这丫头罢。(明《金瓶梅》)
(13)夏主簿见说得蹊跷,晓得要赖他的,只得到州里告一状,林家得知告了,笑道:“我家将猫儿尾拌猫饭吃,拼得将你家利钱折去一半,官司好歹是我赢的。”(明《二刻拍案惊奇》)
(14)明日请姑娘众位,好歹往我那里坐坐,晚夕走百病儿家来。(明《金瓶梅》
(15)西门庆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儿那奴才收拾起来,牵了来我瞧瞧。(明《金瓶梅》)
以上句子中,“好歹”已经从形容词转为副词,实现其语法化。原因在于:第一,出现的句法环境发生了改变,位置由原来位于谓语动词之后移于谓语动词之前,获得与普通副词相同的句法位置,从而发生结构上的重新分析,获得了副词的功用;第二,语义融合,不再是构成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表示一个新的概念,语义上接近“无论如何,不管怎样”,而且衍生出人际交往功用,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但例(12)(13)与例(14)(15)还有些许不同:前两例“好歹”位于主语之后、谓语动词之前,更多的表示说话人的主观情态,而后两例“好歹”位于主语之前,在表达说话人主观情态的同时也凸显了其篇章衔接功能。
方一新,曾丹(2007)认为“好歹”除了作语气副词之外,还可以作时间副词,语义上相当于“早晚、迟早”,其举例为:
(1)今夜好歹来也,则管里作念的眼前活现。(元白朴《墙头马上》二折)
(2)兄弟拿他作甚么?他吃了酒好歹去也(元李文蔚《燕青博鱼》三折)
(3)如今那老婆子害病,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药死那老婆子,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元关汉卿《窦娥冤》二折)
(4)兀那妇人,你放心,等你孩儿长大成人,我着你子母每好歹有厮见的日子哩。(元关汉卿《五候宴》二折)
(5)姐姐省烦恼,俺好歹有一日见玄德公也。(元无名氏《千里独行》二折)
其实,细究这些例子,其中的“好歹”理解为语气副词更为恰当。(1)(2)中“今晚好歹来也”“他吃了酒好歹去也”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更凸显说话人对事件的看法、态度,方一新、曾丹所说的“指临近某个时间点”未免有些欠妥。后三例,都是说话者对未来事件的推测,在表示未然事件时更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结合语境这三例中的“好歹”语义上更接近于语气副词“肯定、必然”,表现说话人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持坚信不疑的态度。如果理解为时间副词“或早或晚”在语义上勉强符合文意,但是“好歹”如何发展出时间副词的用法,是缺乏语义基础的。根据张谊生(2004)对反义对立式语气副词的语义分类,“好歹”属于事理义场类,其构成语素本身只包含对事物、事件评价,不包含表时间的语义特征,因此“好歹”不可能在没有语义基础的情况下凭空产生时间副词的功用,因此,这里的“好歹”只能理解为表情态的语气副词。
那么“好歹”是如何在语源义的基础上衍生出语气副词“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义项呢?张谊生指出:反素词都处于一个语义场的两个顶端或两面,肯定或否定一个语义场的两端或两面也就确定或排除了一切前提,所以都会自然而然走上主观化的道路。[2]343除此之外,“好歹”由形容词转变为副词实现语法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短语“好歹”本身就具有价值评判的语义基础。“好歹”的构成语素“好”与“歹”本身就带有评价性,又处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两端,从认知角度来说,很容易被推向极端,来概括整个语义场。再加上其具体义素脱落,主观情感凸显,“好歹”的语义进一步泛化和虚化,进而发展为表情态义的副词,语义大致相当于“不管怎样,无论如何”。又由于所处位置的灵活性:既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又可以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做状语,甚至可以用于主语之前,扩展出篇章衔接的功用,其语法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要之,“好歹”语法化的过程为:“好歹”构成语素的概念义逐步消失,两个语素的意义融合而演变出周遍义,进一步虚化为情态义,最后发展出关连义,这是一个由实到虚,逐步发展的过程。
三、语气副词“好歹”语法化的动因
“好歹”经历了“好”“歹”的临时组合阶段,到意义融合、分界消失实现其词汇化,再到意义的进一步虚化实现其语法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自身价值评判的语义基础以及“好”“歹”语义的融合
语法化理论认为语义相宜性和句法环境是诱发一个词语语法化的必要条件。“好歹”之所以能够实现其语法化、具备语气副词的功用,与其构成要素自身的语源义密不可分。根据张谊生(2004)对对立式语气副词语义的分类,“好歹”属于事理义场类,也就是说“好”和“歹”本身就具有价值评判的语义特征,这是“好歹”能够实现语法化的语义基础。“好歹”最初只是“好”和“歹”的临时组合,由于“好”和“歹”处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两个极端,从而很容易被用来否定或概括整个义场,从而发生意义的转指、泛化,两者之间的分界逐渐消失,实现词汇化。张谊生认为,“好歹”本身具有评判性的语义基础,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具体义素脱落,主观情感凸显,自然就会转向情态化语气副词[2]344,从而实现其语法化。
(二)句法位置的改变
语义基础是“好歹”能够实现语法化的先决条件,而其语法化的最主要诱因是其所处句法环境的变化。张谊生(2000)也强调:“结构形式的变化是实词虚化的基础,由于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的改变,一些实词由表核心功能转变为表辅助功能,词的意义也随之变得抽象空灵,从而导致副词的产生。”[3]344“好歹”最初出现的句法位置多数是位于谓语动词之后充当宾语,也有少数充当主语或定语,在这样的句法位置上“好歹”缺乏语法化所需要的句法环境,不可能实现向语气副词的转变。随着其进一步发展,“好歹”逐渐可以进入状位,获得与普通副词同样的句法位置:位于谓语动词之前,修饰谓语动词。这是“好歹”演变为语气副词,实现其语法化最重要的句法环境。如:
(1)我好歹劝化你伯娘转意,你只要时节边勤勤到坟头上去看看,只一两年间,我着你做个大大的财主。(明《初刻拍案惊奇》)
这里“好歹”位于主语之后,谓语动词之前,获得了副词的功用,是对句子的述题部分进行评注,突出说话人的主观情态。
(2)好歹我替闺女报了仇来。 (明《醒世姻缘》)
句子中“好歹”位于主语之前,是对整个句子的评述。
以上两例由于出现的句法位置的不同,所评注的辖域也不同。前者属于半幅评注,后者属于全幅评注。可见,“好歹”所处句法位置的不同,其语法功用也不尽相同。
(三)语音上的组块化
汉民族人们习惯用处于同一语义场两个极端的词语,来概括一个事件的整体。这是“好歹”产生的民族心理基础。“好歹”产生后“好”与“歹”就经常并列使用,再加上它们在线性顺序上邻近,在汉语双音化的大背景下,“好歹”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而实现由句法单位向词汇单位的转变。丁喜霞(2006)也指出:当两个类义或反义关系的单音词连用在一起高频使用时,容易被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又加上韵律的制约和双音步的“梏化作用”并连在一起的成分语义发生抽象、概括或脱落,最终演变为一个双音词。[4]141“好”与“歹”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语法单位,但由于“好”“歹”经常成对邻近出现,人们习惯将其看作是一个音步,这也是“好歹”实现其词汇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四)使用频率的提高
词汇的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一个语法单位从产生到为人们所广泛使用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其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在发展中才能被保存下来。而且随着其使用频率的提高,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义项逐步增多,位置更加灵活,功能得到扩展,从而完成由实到虚的语法化进程。“Bybee曾强调语法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重复,促使一个词语语法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就是它具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使用频率越高的实词,就越容易作为语法化的始源,也就越容易虚化为语法标记,其结果反过来又提高了该形式的使用频率。”[5]181“好歹”产生宋元时期,元明时期使用频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在《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金瓶梅》等近代口语作品中使用非常普遍。我们对国家语委语料库包含“好歹”的词条按年代进行统计发现:宋代包含“好歹”的词条仅有2例,而到元明时代,包含“好歹”的词条竟有431条。由此可见,由宋到元明“好歹”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了。随着其使用使用频率的提高,其意义逐步融合、虚化,最终成为表说话者主观情态、语义接近“不管怎样、无论如何”的情态副词。
四、结语
文章系统地分析了“好歹”词汇化、语法化的历程,“好歹”经历了一个“好”和“歹”的临时组合到词义的逐步融合、分界的消失实现其词汇化,再进一步虚化为表达说话者主观情态的语气副词的过程,最终实现其语法化。推动其语法化的动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好歹”构成要素的语源义以及发展过程中词义的融合;第二,“好歹”所在句法位置的变化;第三,语音组块化的推动;第四,使用频率的提高。“好歹”虽然已经实现其语法化,但与同为反义并列式副词“反正”相比,其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其使用频率的进一步提高、篇章衔接功能的进一步凸显,我们有理由相信其语法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董秀芳.动词性并列式复合词的历时发展特点与词化程度的等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1).
[2]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3]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 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
[5] 陈全静.汉语并列式双音时间副词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责任编辑:金颖男]
中图分类号:H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094-04
收稿日期:2015-11-17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YY113)阶段性成果之一;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Y201409)阶段性成果之一;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091)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周晓彦(1992-),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