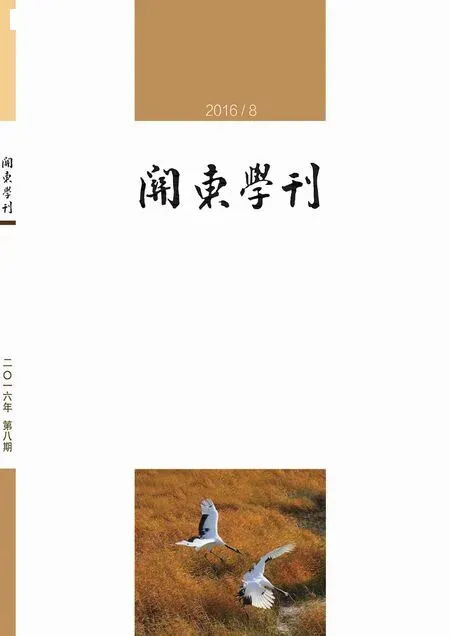看风吹过山岗
——熊培云诗中的意义世界
马 烨
看风吹过山岗
——熊培云诗中的意义世界
马 烨
再当下这个逃离文学的时代,学者型诗人熊培云却逆向而动,逃向文学,以诗歌的方式来展现对这个时代的关注与感悟。其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中的诗篇,并未致力于辞藻的堆砌与意象的建构,而是通过白描与叙事的手法,以质疑与批判的眼光,以节制而幽默的语言,来审视和再现生活世界后的意义世界,诗行间充满着一种超然的同情。
诗歌;感悟;白描;批判;意义世界;同情
这也许不是文学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依旧写诗和吟诵,诗歌依旧带给我们快乐和安慰。对此,波兰的精神守护者辛波斯卡说:“我偏爱线条细致的老式插画。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很多人像北岛一样,怀念有梦的八十年代。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经历了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势利与粗鄙的放逐,似乎只剩下梦破碎的声音。事实上,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正如星星没有离开天空,种子曾经埋在泥里。”很多人心中还怀有文学梦想和文字情结,但面对“文学已死”的断言时,或焦虑、沉默或隐遁逃离。熊培云直言,他也在逃。不同的是方向相反,他要逃向文学。他希望能够回归文学,重拾诗歌,搭建能够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的意义世界。诗歌对他而言,更像是一次试验式的文体私奔。
与传统意义上很多诗歌略有区别,作为非专业诗人,熊培云的诗取材通俗且没有太多华丽辞藻的装饰,大多直截了当地叙事论理或白描。他的诗沿袭了评论文章中节制而幽默的语言风格,诗歌主体并不沉迷于意象的构建,更关注意义世界。他喜欢用质疑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便触及爱情的主题,也有理性的批判与反思。他企图在诗作中对世间万物表达出一种超然的同情。
在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中,熊培云以春、夏、秋、冬、春五部分,涉及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等方面的思考,大多都与存在和意义有关。在四季轮回与时间流转之中,作者以独到的眼光审视社会和人性,用宽容慈悲的心去体悟人生和天命。
如果用存在主义哲学的眼光看待生活和生命,人不过是生活在没有意义的宇宙空间之中的沧海一粟,外界的一切都与你无关,自我的思想活动才是你能够感知到的世界的本质,你即你世界:“除了人,我别无身份/除了美,我一无所知”(《除了美,我一无所知》)。存在主义哲学先驱克尔凯郭尔说,你我活着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对自己而言是真理的真理罢了。而熊培云在诗中这样理解存在:
你感受,生命从此有了时间
你思想,大地从此万物奔流
你归于寂静,世界再无消息
——《存在》
熊培云的诗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他为万物写诗,向蝼蚁致歉,于生命本身充满着同情和怜悯。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除了更深的怜悯/还能说什么/每一个人都将不久于人世/每一次微笑都是临终关怀”(《幸福大街》)。
只是,在悲悯中还有希望。作者所期许的美好人生是“寻得一个人或一件事/愿意为之勇敢地死/更愿意为之勇敢地活”(《这是我想要的美好人生》)。对于这种生死以之的追寻,作者一以贯之用“天命”一词来解释。除了序言和后记,最有力量的是诗经体的《天命昭昭》: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万念俱灰,一念永抱。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无可限量,无可求告。
余生摇摇,天命昭昭。
子兮予兮,不负同牢。
这种一念永抱的天命,在熊培云那里便是永不停歇的思考与写作。在诗集第五季(春)开篇,他便给出了这样诗性的答案:“我的写作还没有开始/我的生命仍有奇迹/山枕孤星,风吹黎明/我也在悄然生长/静静地等待我的时令”(《下雪天》)。即使远方如同海子所说“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作者既不沉沦悲观,不假装欢乐,而是用心生活:“我愿意跟随自己的心/带上所有的诚实与自由/在时间的山谷里生长/无论世界向好,还是向坏/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在送往迎来的一生中,追寻并坚持自己的天命。
在寄语年轻人的诗中,作者同样希望年轻人能够不要被生活的压力所击倒,不必为与自己无关的日子而慌张,“只需找到自己的天命/其他一切交给命运”(《Being Present》)。找到天命并为之勇敢的一往无前,就是在这场告别的旅程中使自己变得完整所最应该做的事情。这是诗人心中的美好人生,也是彷徨迷茫中的人所可以找到方向的指引。他逃离了人群,他追随着理想,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逃兵。
相较于评论或小说,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是轻灵而柔和的。然而在只言片语之间,她却既可以承载“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磅礴,又能尽“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百千柔肠——诗歌能够在片刻间直抵人的灵魂深处。熊培云将自己的这次写作称为“文体私奔”,其实是文体解放。他偶尔展示诗歌的意象,但更多是对社会与人性的反思,乃至批判。
地铁里
我看见
每个人都在
向手机低头
做信息时代的弥撒
——《手机》
不着太多的笔墨,不用例证,二十余字就将信息时代为每个人所熟悉的个体被物化和异化的场景展现,这比一篇两千字的评论来得更有力,更触动人心。
文学的语言是有力的。寓言故事一般的短诗《偷生》则将人群与个体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刻的反思:“可是,危险的不是小偷/而是加害于人群的饥饿/小偷想部分消灭人群中的饥饿/人群却完整地消灭了他”。对于人群,作者称其为“因人之名而合成的庞大机器”,“它让你胆小如鼠又给你勇气横冲直撞/它为你站岗放哨又将你带入悬崖/它成群结队高举火把,而你却行进在黑暗里”(《我时时畏惧人群》)。在人群中,个体的自我意识被消减,跟着人群走终将迷失自我,用作者的话说是,人群能让他找得到方向,却找不到美。
同样是寓言体短章,在《寻牛》一诗中,作者将复仇这个文学母题升华,借以探讨人性中隐藏的比坏这个阴暗面:
寻牛的时候
他学会了偷窃
每个邻居都是嫌疑犯
他要报复所有人
世人只偷走了他的一头牛
他却剜去了自己的一颗心
——《寻牛》
回到文学的问题上,熊培云在万余字长序《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中做了解答。他不仅为在八十年代风靡一时又在如今略显颓态的诗歌正名,也为文学做辩护。他说:“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是人首先病了,才反映在文学上,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尽管我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担起理性和心灵的责任,但我相信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文学有问题,那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熊培云用诗作为载体,记录思想的片段,最终达到自己与世界和内心的和解: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不用紧张,暴雨将至
我还有一天的时间
看风吹过山岗
你花一天的时间遇见我
我花一天的时间来向你告别
剩下的一天,我想和自己谈谈
看风吹过山岗
一半的生命在水底里
一半的生命在阳光下
我是污泥,也是莲花
我以我的卑污,孕育我的美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
暴雨将至,不用紧张
我还有一天的时间
看风吹过山岗
——《看风吹过山岗》
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文字都是内心的流淌。当我们将文学束之高阁,让诗篇蒙上尘土,抛却典雅的措辞,脱口而出的是粗鄙或玩世不恭的网络语言,你可以说文学已死,是死于未受高贵的人心的滋养和礼遇。
无论读者是否赞同作者在诗中所阐述的关于爱、关于美、关于人生、关于意义的表达,我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对文字心存敬畏,对文学怀有感恩,对人生有所思考,对社会有着担当的知识分子用心去写的一部心灵笔记。对其中的观点可以有所质疑和抵触,但那种温暖与悲悯之心却是令人动容且无法抗拒的。
马烨(1989-),女,腾讯大燕网新闻编辑(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