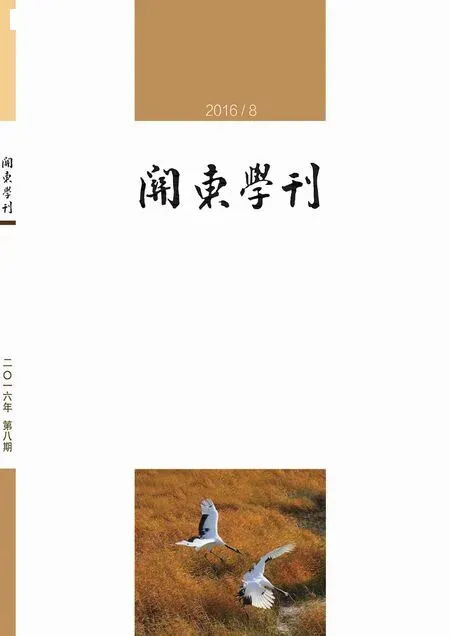傅斯年三题
羽 戈
傅斯年三题
羽 戈
一、傅斯年之怒
我对傅斯年先生的印象,可归结于两个字。一是胖。他不是矮而胖,而是高而胖,故而看起来非常威风。因其胖,容易出汗,遂有温梓川所描绘的经典一幕:“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二是怒。其绰号傅大炮,尽管别有出处,我则情愿认为,这是形容他的火气之盛(近世人物,还有一尊著名大炮,即孙大炮,不同于傅斯年,孙中山被称作大炮,则因他好说大话,正应了粤语“车大炮”之意)。
傅斯年脾气大,发作起来,不止暴躁,甚至近乎霸道。胡适曾为其得意门生辩解,称傅斯年的性格不是暴躁,“而是感情最热,往往带有爆炸性”。不过这番话,说服力不大,因为傅斯年非常尊敬胡适,虽也常与胡适争论,却不至气急败坏,大发雷霆。罗尔纲记录了傅斯年与胡适讨论问题的情形,说傅斯年“左一句‘先生’,右一句‘先生’”,其声音“恭敬顺从”,足见敬意之深。胡适未受伤害,缺乏发言权。像傅斯年的好朋友罗家伦,大概时常承受傅斯年的坏脾气,其纪念文章《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便不乏“气得孟真直跳”“孟真气得要上前来打我”“他为之大怒,要来扑我”等字样,使得傅斯年横眉立目、七窍生烟的情态,跃然纸上。

傅斯年1947年送给胡适的照片
对于自己的暴脾气,傅斯年倒也不缺自知之明。曾任傅斯年秘书达十二年之久的那廉君说过一段趣事:傅斯年对一个人发完脾气,如果余怒未消,第二人进来,还得碰一鼻子灰,甚至会殃及第三、四人。对此,傅斯年告诉那廉君:
“叫我不二过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由此可见傅斯年明知自己脾气太大,偏偏控制不了。
傅斯年的脾气,应与其身体状况有关。他患有高血压病(一是遗传,二是肥胖),1941年3月曾严重发作,后来专程赴美治疗。高血压病人大都容易激动,爱发脾气,是以有一个说法叫“高血压性格”。此外还有一大原因,如罗家伦所言,“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这后一点,尤其值得说道。
关于傅斯年“是非观念太强”所导致的功过,我们不急评判,且说一些故事。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我的老师王人博教授(山东莱西人)谈到山东人,曾与湖南人对比,称湖南人造反的目的在于当皇帝,山东人造反的目的在于受招安(所谓杀人放火受招安),他认为山东人的特点是认同合法性,素怀忠义之心。以地域论人,强调的是概率,不可能全部言中。不过傅斯年恰在概率之内,他便是王人博所描述的那种山东人,不仅忠于国家和民族,还惯于以忠诚以及相应的气节为标尺,知人论事。
据程沧波回忆,有一次,傅斯年看见他临大书法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说道:“虞世南写不得。”他停笔问其缘故,傅斯年答:“虞世南是一位变相的贰臣。”诚然,虞世南历仕陈、隋、唐三朝,其间还效忠窦建德,以忠诚而论,的确是贰臣,堪称三姓家奴,只不过,政治是一码事,书法则是另一码事,傅斯年以政治取舍书法,持论未免过苛。这已经不是是非观太强,而是成见太深。后来沈尹默听说此事,十分生气,说傅孟真该打屁股。程沧波则感慨道:“孟真这一类话,自有其偏激与过正,然也正可窥见他的真性情。”
据傅乐成(傅斯年的侄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一文所述,明末人物,傅斯年最尊重黄道周,最鄙视钱谦益;景仰顾炎武,却讥责与之齐名的黄宗羲。他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上题道:“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书中批道:“献谀东胡,可耻可恨”“此篇主旨,是毁谤明朝,以劝人归顺清室也。”钱谦益先仕明而后降清,而且是带头投降的南明大臣之一,不过清朝的皇帝并不怎么待见他,乾隆编《贰臣传》,将他纳入乙编,此之谓两头不讨好,这样的人物,纵使仕清以后,重又反清,却无补于早已失陷的大节,傅斯年看他不起,不难想见。说到黄宗羲,则有争议。黄宗羲晚年,思想成熟,对清朝政权的态度有所改观,譬如自己不出山,派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与明史编撰,可是,这并非妥协或献媚,而因黄宗羲的眼光,已经超出了一家一姓之兴亡,借用顾炎武的名言,即从“国家”进化到“天下”。傅斯年忽略了这一点而苛责黄宗羲,未免有些遗憾。
对同时代人的鲜明态度,愈发可见傅斯年“是非观念太强”。譬如他提到罗振玉,必称“老贼”,因为罗振玉与日本人合作,在满洲国做官,当然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他并不完全否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严令不再聘用那些“落水”的北大教授,包括周作人、容庚等人。容庚前来求情,他则当面斥责:“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时陈雪屏在北平接收北大校产,同时奉教育部之命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飞抵北平,见到前来迎接的陈雪屏,劈头便问:“与伪教授有无交往?”陈雪屏答:“有。”傅斯年很是不满:“‘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尽管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此后每每谈到这个问题,傅斯年还要发脾气。
傅斯年的言行,常常令我想起一个成语:爱憎分明。他的憎,甚至不避亲,连其祖宗傅以渐都不放过,只因傅以渐效忠于清朝(傅以渐比黄宗羲大一岁,系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且是帝师,教过康熙)。然而爱憎过于分明,不尽是好事,有时失之专断,有时失之寡情,最要命的是,爱与憎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致使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紧绷的弓弦,一刻不得放松,哪怕这根弦被轻轻碰一下,都要大动肝火。这般爱憎分明,大抵便是罗家伦所强调的“是非观念太强”,成就了傅斯年激切、易怒、好斗的气性。
说到气性,且来谈谈傅斯年的气。毛子水说:“孟真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沛然莫之能御。这是最伟大的一种气,不过需要“养”。罗家伦则认为,傅斯年恰恰最不善于养气(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信傅斯年,劝他读孔孟以养气:“……老兄病中读《老》《庄》,未必是对症下药。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似乎比那似达观而实偏激的庄生,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事后来看,傅斯年似未接受胡适的建议),故而他认为“孟真所代表的是天地间一种混茫浩瀚的元气”,“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这一评语,我非常喜欢,只是有时觉得,未免空疏。要我来说,傅斯年代表的则是一种火气与怒气,他的怒,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精神;不是“免冠徒跣,以头抢地”的布衣之怒,而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之怒,而是自比田横、不与专制共舞、立志蹈海而死的志士之怒,而是道之所在、义之所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之怒。他的形象,正接近一头愤怒的狮子。他为今人所铭记、所津津乐道,大都与其怒气有关,譬如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那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简直用烈火写就。
1940年8月14日,在致胡适信中,傅斯年解释了他炮轰孔祥熙的怒气之由来:
“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出(初)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侮)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
“士人之节”四字,几乎可以诠释傅斯年平生行事。他虽生于近代,接受西方教育,其一大学术贡献,即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然而究其本质,终究还是士人、士大夫,而非今天的知识分子(当然他兼顾了这两种身份,一定要分高下,我觉得士所占的成分更重一些)。他的道是士之道,他的怒是士之怒。他的时代,内忧外患,礼崩乐坏,士风沦丧,不知名节为何物,以他的性情,只能采用一种愤怒的方式维护摇摇欲坠的“士人之节”,支撑一个国家的精神苍穹。愤怒成就了他,同时禁锢了他,肝火太盛、气性太强所导致的偏激与霸道,最是为人诟病;甚至摧毁了他,他的身体之虚弱,以及他的死因(脑溢血),与其易激动、易怒的脾性不无关系。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猝死于台湾省参议会。国士死在议坛,可谓死得其所。自此之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没有傅孟真的假时代”(王小明语)。
二、傅斯年与曹操
傅斯年去世之后,师友撰文纪念,常把他比作一些先贤。程沧波说,傅斯年的言行,像东汉末年李膺、范滂一流人物,其命运则似郭泰(林宗)。李膺、范滂是中国最早的清流,把郭泰与傅斯年并论,大概缘于二人皆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罗家伦认为,论号召力与攻击精神,傅斯年像伏尔泰,“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伏尔泰)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他还开玩笑,说傅斯年像塞缪尔·约翰逊,因为这二人都是大胖子。当然,如果能把伏尔泰的精神,装在约翰逊的躯壳里面,比作傅斯年,再也合适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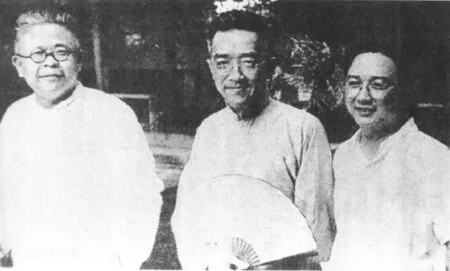
傅斯年与胡适、胡祖望
最好玩的一个说法,则是将傅斯年比作曹操,甚至称他为学术界的曹操。我读此说,起初在叶兆言书中,其次在温梓川书中,不过他们都未交代出处,愈发令我好奇:把傅斯年与曹操联系起来,到底基于什么呢,形象、性情、才略,还是命运?后来读到那廉君的回忆文章,其中引用社会学家陶孟和之言:“傅孟真要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这是在形容傅斯年白而胖。倘若以此为出处,未免有些阴差阳错:傅斯年只是与平剧里的曹操相仿。
叶兆言说傅斯年像曹操,后面有个注脚:“……是一代枭雄,很会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这属于从性情和才略而论,比以形象为标尺,显然说服力强一些。不过对此解释,我一点都不认同:第一,无论曹操还是傅斯年,皆非枭雄,而是英雄(视曹操为枭雄,大概还是以《三国演义》为底本,这不是严谨的读法);第二,傅斯年这一生,何时玩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呢,挟过何人,令过何人?
对于这些问题,叶兆言的文章并无说明,我们只好从他处寻踪觅迹。1950年,周作人撰文忆《新潮》,谈及罗家伦和傅斯年这两位创刊者。不知出于政治压力,还是往昔过节,知堂此文,相当失态。文中说傅斯年是伪君子,“他始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作特务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例,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傅斯年为了帮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忙,替他说话,以至在会上“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料吃力不讨好,沦为众矢之的,引来骂声如潮,蒋廷黻综合流言,称傅斯年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这自然是朋友间的玩笑,不过恰可见傅斯年任事之勇,以及做事的风格。
结合这两例,以及傅斯年的生平来看,要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谓“天子”,只能是蔡元培与胡适(朱家骅这样的政客,只可能挟他人,而不可能被他人所挟)。
傅斯年与蔡元培的交谊,可分北大时期与中央研究院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傅斯年还是学生,权力体系之下,二人相距甚远。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其下辖历史语言研究所,即由傅斯年亲自筹建,并任所长。中央研究院的权力,一向操于院长与总干事之手。在蔡元培任上,的确有一段时间,院长与总干事不司其职,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主持工作,然而细究起来,可知这与“挟”无关:1936年12月,总干事朱家骅兼任浙江省主席,分身乏术,其时院长蔡元培年老体衰,病魔缠身,一应院事,都落在傅斯年肩上,据朱家骅回忆,“七七”事变之后,“在这一年余之中,院内诸事,无论巨细,悉承孟真照料,甚至全院西迁,也都由他一手办理”,还得注意,1938年2月,蔡元培隐居香港,直至老死,对于院务,只能遥领。要言之,此间傅斯年权力再大,哪怕正应了“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讽,那也是授权与协作的结果,倘视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则小觑了这一干当事人的胸怀和友情。
相比蔡元培,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显然更近,交集更多,故而“挟天子”的概率更大。譬如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本来属意傅斯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推荐了胡适,在胡适回国就职之前,由他代理。此后一年,傅斯年所行之事,大多与胡适有关,甚至高举胡适的名头。这是不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挟胡适以令学界?
1946年5月,邓广铭受傅斯年邀请,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帮忙。据其回忆,他曾问傅斯年,为什么要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道出一个原因:假如别人代理,可能会设法转正,不让胡适就任,他来代理,则可一心一意为胡适到来做准备,打头阵,扫平前路。这些话不是虚辞,1946年7月5日,胡适归国,傅斯年立即让位,可为明证。而且这也证明,傅斯年并不贪恋权力。一个本可当“天子”的人,何必去挟“天子”呢?
傅斯年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最著名的一项决策,即“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所谓伪北大之教职员,包括周作人、容庚等名流(傅斯年与周作人的梁子,就此结下)。此事争议极大,最是授人以柄,叶兆言便借此嘲讽傅斯年霸道,欺负容庚。傅斯年自己怎么想呢?试看他给妻子俞大綵的信:“……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1947年1月7日)质言之,他要唱白脸,留给胡适唱红脸,他来干脏活,留给胡适当圣人,用他致胡适信中的话讲:“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与此相应,傅斯年告诉邓广铭:“各学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尽量聘定,因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义者,对人没有严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请,那可能会弄得很糟糕的。”他还对陈雪屏说:“关于行政上的业务,我们应先替胡先生办好,将来不劳他操心,即以校产为言,他断不愿和别人抢东西的。”
这些话说得毫不客气,然而对胡适来讲,却是知己之言,必定不以为忤。事实上,从胡适谈傅斯年的文字来看,他对这个学生,唯有欣赏和感激,如罗尔纲所云,胡适最钦佩的前辈是蔡元培,同辈是丁文江,后辈便是傅斯年。他们之间,是师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同道的关系,无论哪种关系,都无关“挟”字。
我曾想,如果没有胡适,傅斯年也许还会成为傅斯年,如果没有傅斯年,胡适还能不能成为胡适呢?只怕难说得紧。因为我一贯以为,胡适对傅斯年的依赖,远过于傅斯年对胡适的借重。尤其与政治的关系、对政局的判断,胡适偶尔糊涂、犹疑,傅斯年则帮他决断,以至全权代理。譬如1947年前后,蒋介石有意请胡适出头组党,以及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有一次约傅斯年吃午饭,与之商量,傅斯年则“力陈其不便”“反复陈说其不便”,替胡适一概回绝。随后他给胡适写信,决然道:“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1947年2月4日)从胡适的复信来看,他完全采纳了傅斯年的意见。可作对照的是,1948年3月,蒋介石请胡适参选总统,胡适明显动心了,从而表现为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最后固然还是拒绝,其心态之游移,不免为人所笑。当时傅斯年正在美国养病,假如他留在胡适身边帮忙谋划,想必胡适便不会这么纠结。
顺道说一点。胡适与蔡元培一样,皆非干才,他们适合生产理念,理念的落实,还得另请高明。蒋梦麟与傅斯年,正扮演了“高明”的角色。据蒋梦麟回忆,1950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发表演说,谈到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的学问不如胡适之,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蒋梦麟听后笑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功狗”一说,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夸奖萧何:“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蒋梦麟自称功狗,可视为谦逊;就傅斯年而论,他既是功狗,也是功人。不说其他,单是创办史语所,足见其“发踪指示”的能力之强。
傅斯年死后,胡适在致毛子水的信中大放悲声:“孟真真是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又最高,一不可及。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而又最能组织,能治事,二不可及。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三不可及。今日国内领袖人才缺乏,世间领袖人才也缺乏;像孟真的大胆小心,真有眼中人物谁与比数的感叹!”这“三不可及”,可谓盖棺论定之语。近世人物,能做学问,能做事情,两方面都在第一流,前有丁文江,后有傅斯年。这二人,甚至都称得上文武双全。我们常常讥笑文人纸上谈兵,陈之迈却说,民国文人,有三位精通军事,一是张季鸾,二是丁文江,三即傅斯年。1932年,傅斯年便隐约提出了持久战的想法:“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日寇与热河平津》)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曹操。先贤论人,好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后二者,正对应文章与事功,所谓下马草军书,上马击狂胡。以此为标准,秦皇汉武,唐宗清祖,略输文采;萧衍萧纲,李煜赵佶,事功则一塌糊涂。二者兼具,文武兼资,首推曹操。就允文允武这一点而论,傅斯年的确堪称“学术界的曹操”——叶兆言使用这个说法,皮里阳秋,暗含讥嘲,我则愿意从正面理解。
三、傅斯年的死志
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8年底,“似是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在南京共度岁末,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萧条异代不同时。“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云云,穿越千载,仿佛为现实而作。师徒二人感时伤怀,潸然泪下。

傅斯年在处理公务
半个月前,胡适已经哭过一次。1948年12月15日,他从北平飞到南京。两天后,到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发表致辞云:“我是一不名誉之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雪屏在会后致电北大同人:“今日校庆,此间校友集会,校长讲话,痛哭失声,会场凄然断绝。”(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校长”即胡适。
此时此刻,相比胡适,傅斯年的心境更加悲怆。胡适只是痛哭流涕,傅斯年则徘徊于自杀的边缘,精神濒临崩溃。
1947年6月下旬,傅斯年赴美治病。1948年8月回国。归国前夕,有人从北京致信其夫人俞大綵,“谓大厦将倾,傅先生欲于此时遄归,非计之得”。傅斯年读后叹道:“此君乃不知吾心。余绝不托庇异国……余已无可奈何,则亦不辞更适他省。又不得已则退居穷乡。最后穷乡亦不保,则蹈海而死已矣。”(陈槃《师门识录》)他规划了三条退路:首先更适他省、其次退居穷乡、最终蹈海而死。
然而局势变化之迅疾,远远超出了他的预计。当他尚未“更适他省”,还在南京的时候,便萌生自杀之意。师友回忆傅斯年,皆提到这一节。如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云:“在徐蚌战事(按,即淮海战役,结束于1949年1月10日)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里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屈万里说:“在这个非常紧急的关头,傅先生他身上经常放着安眠药,预备随时吞药自杀。”
除了战事失利,傅斯年起意自杀,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陈布雷、段锡朋之死。据陈槃《师门识录》:“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念头。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师”即傅斯年。
陈槃是傅斯年的学生兼属下,追随傅斯年达数十年之久。他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读书期间,傅斯年任文学院长兼国文、历史二系主任;他读三年级的时候,“为奸人诬构罪名入狱”,幸得傅斯年营救,捡回了一条命。毕业之后,他先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是创办者和所长;后到台湾大学,傅斯年是校长,他能进这两个单位,皆受傅斯年青眼提携,故而终身感怀师恩。傅斯年死后,他依旧念念不忘,有一次,他的学生登门拜谒,他正在吃粥,餐桌之上,供傅斯年遗照一帧,后来偶入他的寝室,再次见此遗照。生死相依,可见深情。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于南京;1948年12月26日,段锡朋病逝于上海(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云:“听到他的两个老朋友陈布雷和段锡朋自杀的消息后,傅斯年决定为‘旧朝’献身。”这里有一错谬,段锡朋并非自杀)。傅斯年与段锡朋曾一同发起新潮社,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加上罗家伦,号称“三驾马车”,三人互为至交。据罗家伦回忆,朋友当中,傅斯年最佩服的便是段锡朋。1947年,傅斯年到南京看罗家伦,谈到段锡朋,慨然叹息:“书诒(段锡朋字)是天下才,而始终不能一展他的抱负,使我有‘才大难为用’之感。”为段锡朋抱不平,也是为他自己抱不平,他的一生何尝不是“才大难为用”呢,如沈刚伯《追年傅故校长孟真先生》所感慨的那样:“有其才,有其遇,而无其时,可悲亦可叹矣!”
陈布雷和段锡朋的死讯,为什么对傅斯年刺激这么深,已经无法探究。需要注意的是,陈、段二氏都是国民党员,他们与国民党政权患难与共,捐生殉节,属于本分;傅斯年则系党外人士,他与国民党,谈不上是同道,只能说他不看好共产党。这一点与胡适一样。对于国民党与共产党,胡适哪个都不认同。不过,胡适可以为国民党和蒋介石站台,却不会为其陪葬,可以牺牲名誉,却不会牺牲性命。傅斯年则不然,他的性情,不像胡适那般温和、通达,而是暴烈、决绝,其终点,必然是“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大体可以推断,傅斯年的自杀之念,起于1948年秋,即从美国归来前后。“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这则关系另一节史事,可参俞大綵回忆:“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
在俞大綵的监护之下,傅斯年未能自杀,不过此后一直踯躅于死神的魔影之下,难得解脱。尤其到台湾之后,“更想尽办法,送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出国,而自己却誓死不离国门一步,连到华盛顿开会,也拒不出席。愤慨之至,乃至不自珍惜,故违医嘱,糟蹋身体,不觉遂演成了慢性的自杀!说他求仁得仁,固然不错;说他赍志以殁,也未始不可。”(沈刚伯《追年傅故校长孟真先生》)。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5日,与傅斯年素有交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催其赴台履任:“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有一情节,不知可信与否,称傅斯年接到陈诚的电报,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拟古》第九首。这三天的天人交战,终于使他做出了赴台执掌台湾大学的决定。
1月19日,傅斯年飞往台湾,次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题字留念,他挥毫写道:“归骨于田横之岛”。不论无意偶得还是有意为之,这无比凄怆的七字,足见傅斯年心志之坚。他最重士人之节,自比田横,守义不辱,“盖久有蹈海之意矣”。正如后来他对陶希圣说:“希圣!你以为我是来做校长,我死在这里。”
据陈槃记述,史语所迁往台湾,由傅斯年提出,“或言台湾民情隔阂,二二八事件可为前鉴。师决然曰: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有之!”
由此可知,为什么傅斯年做出赴台的决定,竟需绕屋三日。这关乎死志的确立。一旦去往台湾,再无退路。他不是没有生路可选,譬如像胡适那样流亡美国。
我对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最感兴趣。如陈寅恪、储安平、胡思杜等留在大陆,是何心理;胡适赴美,是何心理;傅斯年赴台,是何心理。综合我所见的史料,傅斯年赴台,心理十分决绝,视死如归,绝无苟活、幸存之理,这正应了古人写田横的诗:“穷岛至今多义骨,汉廷未许有降王。”
傅斯年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赴死的决心,无损于他工作的激情;死志已明,反而有助于他在激荡的局势之中安心定志。
彼时之台湾,形同孤岛,朝不保夕。在共和国的压力与美国的犹疑之下,没有多少人相信台湾能守住,其命运早已脱缰,不由自主,而取决于冷战形势的风云变幻。岛内一面是恐怖,一面是苦闷和绝望,人心丧乱,惶惶不可终日。不要说知识分子,就连胡宗南这样的百战骁将,都感觉“这里真没有意思”,问随从“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
傅斯年曾谈及时势:“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会动荡之下,不特‘高调’无从谈起,即此‘低调’,若努力担负起来,也是极其吃力的。……究竟大局与环境能允许我们做到几成,总在未知之数”,然而他的行事,一贯坚毅果敢,做一成,便是一成,借用胡适之言,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傅斯年在台大不足两年,其工作并非尽如人意,譬如他自己便不满意,认为来台大“真正上当”,感慨“办一新大学容易,改革一个旧大学难”。但是,他对台大的贡献,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这其中,相对制度,他对台大风气与风骨的改造,意义更为重大。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冷战时代,他治下的台大,依然具有“民主国家之自由传统”,依然享受北大自由学风的余韵。如拒绝三民主义、联保制度进校园,“学校不兼警察任务”等。今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例,则是1949年“四六事件”前夜,傅斯年横眉冷对前往台大搜捕匪谍的警总副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这句话,如今常常出现在社会运动的海报之上,历经数十年时光磨洗,却未褪色一分,字字如血,历历在目。
傅斯年在台湾的最后岁月,变成了一场与死亡竞逐的冲刺,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诚可谓用“拼命”形容。他不是被气死,而是被活活累死。当时陈雪屏担任台湾省教育厅长,据其回忆:“这时候他的健康情形已颇可虑,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平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
傅斯年死于1950年12月20日。这一天,他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参议员郭国基提出的“台大招生放宽尺度及教育部存放台大的器材处理问题”。陈雪屏说,本来五分钟便可了事,傅斯年足足回答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待他走下发言台,一头倒在陈雪屏身上,立即昏迷,抢救无效,当晚十一时二十分以脑溢血病逝。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傅斯年被郭国基气死,傅斯年绰号“傅大炮”,郭国基绰号“郭大炮”,二炮相争,必有一失。这么说,非但没有抬高傅斯年,而且丑化了郭国基。郭国基是台湾屏东人,生于1900年,无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还是国民党统治期间,他都是著名的异议者,直言无忌,不避斧钺,故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的迫害。质言之,此人绝非龌蹉鼠辈,而是一条铁骨铮铮的好汉。傅斯年之死,虽与他有关,却无甚罪责可言。此后不久,他对媒体说: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这番话沉郁顿挫,掷地有声,堪比傅斯年警告彭孟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1970年,郭国基死在立法委员任上,正应了“赐我光荣死在议坛”。
傅斯年死于议坛,而非蹈海,对比自刎的田横,勉强可称善终,死得其所。曾任傅斯年秘书的屈万里,建议将“归骨于田横之岛”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之上。不过这七个字,虽见傅斯年的凛凛之节,拳拳之忠,却无以匹配他的志向和才具。罗家伦称傅斯年“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陈槃称傅斯年“天马行空,顾瞻无匹。魄力沉雄,才气横溢”,朱家骅称傅斯年“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这些赞誉绝非虚辞。所以,对此一代霸才,我以为更合适的碑铭,应是陈寅恪《寄傅斯年》的诗句:
天下英雄独使君!
补记:
“天下英雄独使君”一语,出自陈寅恪《寄傅斯年》(1927年):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
陈寅恪平生不善作虚词,凡推许人,必有所本。以傅斯年之才,完全当得起这一评价,傅斯年死后,胡适致毛子水信中有“眼中人物谁与比数”之叹(1951年1月7日),可视为“天下英雄独使君”的回声。
听闻傅斯年死讯,陈寅恪曾作《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1951年1月):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霜红龛集》系明清之际的傅山(青主)之作,“望海诗”原题《东海倒座崖》,这是一首五古: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一灯续日月”,日月即明,傅山以此诗怀念前朝,陈寅恪“感题”,则以傅山喻傅斯年(当然这只是一说,谢泳认为此诗写俞大维,胡文辉认为此诗写郑成功与台湾政权)。“望望田横岛”云云,令人想起傅斯年那句“归骨于田横之岛”,道义所在,气节所系,冥冥之中,自有呼应。
羽戈(1982-),男,青年学者,作家(宁波 3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