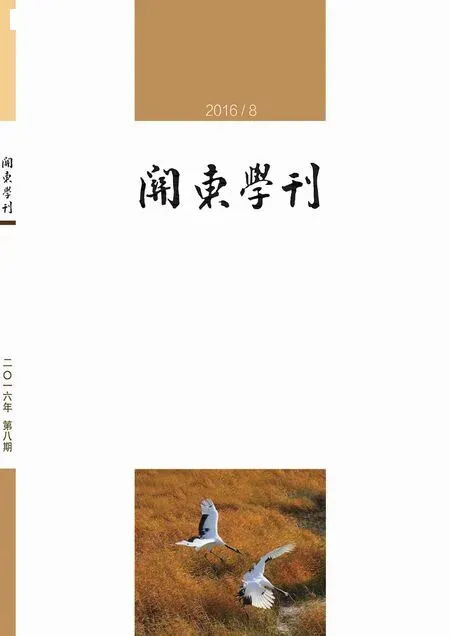“翁不死时书不死”
——郑振铎上海沦陷时期的书痴生涯
何 况
“翁不死时书不死”
——郑振铎上海沦陷时期的书痴生涯
何 况
吾生亦晚,无缘面见郑振铎先生,但我见过与郑先生颇有交谊的苏州文学山房旧书店老板江澄波老先生。江老先生知道我从福建来,特意告诉我,祖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先生曾是他店里的常客,有一次他听江先生在信里说书店收到一套道教仪式画像,立马赶来,展看画像后惊叹:“这样的画像很少能流传下来,更别说集结成册了。”当即联系国家图书馆购藏。江老先生还跟我说了许多郑振铎先生与书有关的趣事,触发了我想写写郑先生的念头。
写郑振铎先生可以有多种角度。诚如台湾学者苏精在《郑振铎玄览堂》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郑振铎是一个“中外不拘、新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齐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页。本文只取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与书有关的材料,描摹藏书家郑振铎先生的一个侧影。
一、 上海沦陷
郑振铎,字西谛,福建长乐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七日生于浙江永嘉。民国六年(1917)他从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因受到新文学运动影响,开始写作白话文, 并勤读西洋文学名著。 五四运动时期, 他作为学生代表之一表现活跃,由此认识了瞿秋白、许地山、瞿世英、耿继之等人,并先后担任《新社会》周刊、《人道》月刊的编辑,又因投稿于《新青年》及《晨报》,而在新文坛斩露头角。民国九年(1920),他与友人发起组织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翌年五月南下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两年后接替沈雁冰主编文学研究会的代用会刊之一《小说月报》,直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因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炸毁而停刊。

1948年12月19日郑振铎在书斋中留影
在此后的抗战前六年中,郑振铎先生主要从事文学教育、编辑刊物、个人创作和旧文学的整理研究等项工作,同时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文化团体的活动,与学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看法》《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等宣言主张,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1937年7月7日夜,蓄谋已久的日军悍然挑起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开始奋起进行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上海是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虽然五年前蒋介石对十九路军发起的淞沪抗战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但这次他出于多种考虑调整了策略,决心坚守上海,于是积极调集兵力,组织淞沪会战。从9月11日开始到11月初,扬言三个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长江以南潘泾以西这条战线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但中国军队却为此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11月11日,日军以死伤5万余的代价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致书告别上海市民,宣告上海沦陷。
郑振铎先生日后在《蛰居散记》一书开头写道:“‘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人们“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郑振铎:《蛰居散记》,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郑振铎先生怀着异样的心情,“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他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准备着随时离开家”。*郑振铎:《蛰居散记》,第2页。
形势越来越恶化:“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郑振铎不敢在家里继续住下去了,有天晚上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即便如此,他“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郑振铎:《蛰居散记》,第2页。他有他的打算。
二、烧书
郑振铎先生最著名的书话集叫《西谛书话》,此书收录的都是郑振铎买书、读书、研究书的文章,其中原载《劫中得书记》的《清代文集目录跋》一文中,他谈到了自己爱书的形态:“予素志怡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得之往往大喜数日,如大将之克名城;失之,则每形之梦寐,耿耿不忘者数年数月。如此书癖难除,积习不销,思之每自笑,亦复时时觉自苦也。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则区区苦辛营求之劳,诚不足道也。”*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
这么一个“书痴”,在上海“孤岛”时期,却不得不硬着心肠烧掉一些“敏感”的书。
据郑振铎先生在《蛰居散记》一书中记述,“八一三”以后,古书、新书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他个人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他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到处飘坠。“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郑振铎:《蛰居散记》,第42页。
这是兵火之劫,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未被劫的还安全保存着。但到了“一二·八”日寇占领旧租界后,情形却是大不同了。
有一天,郑振铎先生听到日军要按家搜查的消息,还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尤其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郑振铎的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这部书会有问题么?”“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人们互相询问着,打听着,夜里关上门把一些自认为“敏感”的书偷偷烧掉。
郑振铎先生忙着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郑振铎先生后来在《蛰居散记》中回忆道,“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郑振铎:《蛰居散记》,第43-44页。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狠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懊悔,不该把它们烧掉。“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郑振铎:《废纸劫》,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书整整烧了三天。郑振铎先生事后回忆说,烧书的时候,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我的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惟日抱残余书,祈其不复更罹劫运耳”。*郑振铎:《废纸劫》,第9页。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整个上海不知有多少先民之宝贵文献瞬间成了灰烬。郑振铎先生愤然道: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这是最彻底的愚民之计。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郑振铎:《蛰居散记》,第41-42页。
三、收书
抗战八年中,郑振铎先生留在了“孤岛”上海,这引起一些揣测,向来刻薄的苏雪林在战后多年写成的《坠机丧生的郑振铎》一文中,还坚持认为郑振铎先生是对抗战没有信心才未去后方。然而,正如台湾学者苏精所言:“战时留在陷区的人不少,而到后方者立场也未必全和政府一致。就郑振铎而言,留在上海也许是因为他担任文学院长的暨南大学一时并未撤退,也许是多达十口的家累,也许是舍不得视如生命的庞大藏书,甚或这几个也许都是。”*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7页。其实,与其揣测郑振铎先生为何没去后方,不如梳理一下他在抗战中都做了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也更能理解他曾说过的话:“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

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与友人合影(右一为郑振铎)
战时的上海,情形是这样不堪:“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第4页。
有家不能回的郑振铎先生,这时在做什么呢?且听他在《蛰居散记》中说:“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
有一天,郑振铎先生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进来找伙计们问话,说是想见见郑振铎先生。郑先生知道这日本人是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郑先生:“要见他吗?”郑振铎先生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日本人走后,郑振铎先生马上过去交代伙计们:“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自己常去的各书店嘱咐一过。*郑振铎:《蛰居散记》,第6页。
又有一天,郑振铎先生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店去。已望见店铺的门了,“突然的叫笛乱吹,一队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书店里熟悉郑先生的伙计向他招手,他准备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拿在手上。汉奸们逐个检查盘问,发现没带市民证的,提到一边严厉盘诘,态度稍为倔强的,便要挨耳刮子或拳打脚踢。郑振铎先生“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好想手上有支枪,干掉这些可恶可恨的汉奸们。
好容易审诘完毕,人们吐了口长气,如释重负。郑振铎先生走进那家古书店时,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郑振铎:《蛰居散记》,第51-52页。
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恶劣环境下,郑振铎先生还不忘搜集保存先民之文献。他的《劫中得书记》一书,便是简要叙述了炮火下一个本性难移的书痴生涯。当时,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郑振铎先生虽然“栖身之地,日缩日小”,但“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
这就是“孤岛”时期郑振铎先生居留上海的真正原因。因着这份强烈的使命感,虽然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掌的巨大阴影里生活着,并且还“受过若干的诬蔑者的无端造谣”,但他没有逃避责任。“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有一个时期,郑振铎先生关门闭户,一个朋友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人们后来才知道,郑先生在家里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早到晚,他的时间全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我还不曾早餐,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带了消息来,他们带了‘头本’来,他们来借款,他们来算账。我为了求书,不能不一一的款待他们。”*郑振铎:《蛰居散记》,第127-128页。
这些书商有的来自杭州,有的来自苏州,有的来自徽州,有的来自绍兴、宁波,有的来自平津,最多的当然是上海本地人。郑振铎先生深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书方法的影响,对于书商找上门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他们失望,以后自会于无意中有惊奇的收获。这个方法果然有效。什么样的书都有送来,常常在许多平常书里夹杂着一二种好书、奇书。郑振铎先生摩挲着一部久佚的古书,一部欲见不得的名著,一部重要的未刻的稿本,心里无比兴奋、紧张、喜悦,以至于连饭都吃不下去。他在战后写作《蛰居散记》时,还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是办好了一件事了!我是得到并保存一部好书了!我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我们的民族文献,历经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读到这铿锵的誓言,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郑振铎:《蛰居散记》,第127-128页。
郑振铎先生在非常时期访得之书中殊难见者,可以查看《劫中得书记》一书。但题跋收入该书的近两百部珍贵文献,“实未尽所得之十一也”。读这些简述访书经过、简介文献版本等信息的题跋,郑先生的艰辛与喜悦跃然纸上。
然而,无论是写于战后的《劫中得书记》还是《蛰居散记》,郑振铎先生当时都没有提到他冒险参加政府在“孤岛”上海抢救古书的事,当时参与的其他人事后也未有一字旁及。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第200页。
郑振铎先生为公抢救古籍的行动,以1938年中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开端。原本郑先生早就梦想着要读到钱遵王《也是园书目》里所载许多元明杂剧。后来读到丁芝孙先生发表的《也是园所藏元明杂剧跋》,惊喜地发现这些剧本果真尚在人间。他到处访求,还曾托人向丁芝孙先生打听,都不得要领。郑先生不死心,继续不懈寻访,终于在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从陈乃乾先生处得悉,苏州书商贾某曾发现三十余册元剧,其中有刻本,有抄本。郑先生欣喜若狂,当即请丁先生代觅代购。当时郑先生一贫如洗,绝对无法筹措书款,但他相信总有办法的。第二天,郑先生到来青阁书庄,从杨寿祺先生那里听到了更详实的消息:有三十多册在唐某处,估计千金可以购得;还有三十余册在古董商人孙某处,大约一千五百金可以入手。“这恐怕是近百年来关于古剧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罢!”郑先生高兴得一夜未眠,“几与克复一座名城无殊”。
就在郑振铎先生四处筹款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来青阁的杨寿祺先生告诉他,现在六十多册书已全归古董商人孙伯渊,非万金不谈。这么一笔巨款,郑先生无力筹措,便一边和孙伯渊继续商谈,一边打电报给教育部。教育部立即回了电来,说决定购买。郑先生看到了希望,再与孙伯渊接洽,最后以九千金成交,并要求在十几天内交割,不然就另作打算。
郑先生焦急万分,连着给教育部打了好几个电报去,但书款迟迟没有汇来。离约定的时间只有三天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国宝”再度流散吗?“只有一条路,向程瑞霖先生告贷。”程先生居然一口答应下来,还笑着说:“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你此款罢。”郑先生拿了支票,立即赶到孙伯渊处付款取书,“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个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书痴得意忘形时不曾想到,如果教育部反悔了,他如何偿还巨款?好在教育部总算在半年之后把书款汇来了,而“债主”程瑞霖先生竟也不曾催促过一声。
后来印行的《孤本元明杂剧》一百余剧,便是这部归于公藏的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中的精华,内含大量过去元曲研究未曾一见的史料,郑振铎先生为它写了一篇长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学界普遍认为,这部《古今杂剧》的获得,虽然尚不至于如郑先生自己所说不下于甲骨文字或敦煌写本的重要,但确是近数十年来戏曲资料一次最可观的发现。*郑振铎:《蛰居散记》,第123-125页。
此后,郑振铎先生继续与政府合作,参与了更大规模的抢救民族文献行动。“我替国家收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是偶然的事;但这‘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为什么在这时候非有计划、有组织“抢救”不可呢?“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极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南陵徐氏书,亦有一部分出而易米,一时上海书市,颇有可观”。于是,“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为此必须抢救,不让好书跑到他们那里去。
个人的经济能力有限,郑振铎先生为此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他和当时留沪的关心文献的人士,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诸先生,商谈了好几次。他们都觉得,必须立刻着手做“抢救”的工作!他们联名打了几个电报到重庆,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不过,在郑振铎等先生的力争下,政府相关部门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此后,他们便开始以国家的力量来做这“抢救”的工作。他们既以国家的力量来做“抢救”文献的工作,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他们用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个学校,像暨大和光华大学的名义购书。江南若干大藏书家的收藏有散出的消息,他们便设法为国家收购下来,不令其落于书贾们和敌伪们的手中。与郑振铎先生共同负责上海方面抢救文献工作的何炳松、张寿镛隐于幕后负责保管经费,由郑振铎先生到第一线抛头露面搜书,每天往返各书店间奔走看书,甚至赶到听说要售书的藏家去直接洽购。虽说他本来就是书店的常客,但是像这种突然进行的大手笔搜购,很难掩人耳目,日本秘探曾到各书店查访他的行踪。他有时不得不躲到朋友处避风头。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郑振铎先生为民族保留书种的决心和毅力在写给张寿镛先生的信中表露无遗: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
“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
郑振铎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却忘记了为自己收书。他解释说:“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像郑振铎先生这样的书痴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的。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先生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在此期间,郑振铎先生还编辑印行了《中国版画史图录》和一百二十本的《应览堂丛书》、十二本的《长乐郑氏影印传奇第一集》、十二本的《明季史科丛书》,真是奇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也不再安全,加上负责上海方面收购文献工作的三人中,何炳松先生奉命暨南大学迁校,并去福建筹办国立东南联合大学,张寿镛则维持光华大学转入地下的秘密上课事宜,他们两人已无暇兼顾,因此收书工作奉命停止。这时候,大批得来不易的古籍保管工作,就落到了郑振铎先生身上。
上海的局面一天天变坏,郑振铎先生不敢担保收得的图书的安全,“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籍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其余的明刊本、抄校本等,计三千二百余部,陆续从邮局寄到香港大学,由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再装箱运到美国暂行保存。这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耗费了郑先生两个月的时间。留在上海的还有大约一千六百部精善本、一万一千部较次的善本,包括刚刚才以七十万元购进的张氏适园珍藏在内,都分藏在法宝馆和外商银行中,郑振铎先生随时照顾它们的安全。抗战胜利后,这大批藏匿在上海由郑振铎先生保管的珍贵古书,陆续由中央图书馆起运到南京,郑振铎先生肩上的重担才得以卸下来。令人费解的是,《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序文,却只提“得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两先生之赞助”,而不及于郑振铎先生。台湾学者苏精不无遗憾地说,郑振铎先生的巨大付出,被后来的公私记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这是不公正的!*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第198-200页。
四、售书
“孤岛”时期,郑振铎先生一边冒险为国家抢救民族文献,一边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一些私藏。
郑先生那些年东躲西藏的生活过得可是艰难。他在《蛰居散记》中这样描述:“我绝早的起来,自己生火,自己烧水,烧饭,起初是吃着罐头食物,后来,买不起了,只好自己买菜来烧。”郑先生就这样学会了生火、烧饭、做菜,而在过去,“柴米油盐的问题”是“从来不会上口的”。
郑先生生活如此拮据的原因,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失业了,没有收入来源;二是买书费资太多。战时,一度上海纸商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大盛,许多旧书店为了换几个现钱,论担称斤售出教科书、滞销的古书、洋装皮脊的百科全书、人名录等,甚至石印的《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的《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郑振铎先生心痛不已,语之书店不能如此糟塌图书,但收效甚微。有一次,他见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郑振铎先生曾看过书目,都是有用的古书,如《五十唐人小集》《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计有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郑振铎力劝店主留售,店主却“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郑先生火大,慨然道:“归予得之可也!”一番讨价还价后,“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问题是,那个时候,郑先生“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好在几日后,有朋友得之详情,出手接济,“乃得免于家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
但朋友只能救急于一时。一家十口每天张嘴要吃饭,不得已时,郑振铎先生只能忍痛“售书易米”。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郑振铎先生在《蛰居散记》中写道:“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哪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本,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巨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
郑先生如数家珍,是想说每一部书得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每一本私藏的书都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是,哪一个书痴买书时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来,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吗?
虽然痛彻心腑,虽然觉得自己收藏的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拿出去卖的,但是生活所迫,又不能不割售。灯下挑书时,郑振铎先生“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心,把它放到出售的一堆。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形,多么令人同情!
郑振铎先生在《蛰居散记》中记下了他的售书所得:《四部丛刊》,连二三编,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一部实在舍不得卖的石印本《学海类编》,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而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后来,又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郑先生说,最后一批拟好编目要卖的,便是一批版画书。他庆幸抗战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才让他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卖的版画书。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因为读书人除了书,实在没什么别的可卖。
郑振铎先生曾无奈地说:“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他说,那时候他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他想告诉世人,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因为,“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他实在是受够了,不想让其他爱书人再来受一遍!
尽管如此,郑振铎先生还是不忘感谢书,因为“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如果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一条路走”!依他读书人的高洁品格,他是不会选择向敌伪靠拢而换取“五斗米”的。*郑振铎:《废纸劫》,第15-18页;郑振铎:《蛰居散记》,第100-104页。
写到这里,我突然记起缘督庐主人叶昌炽咏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诗句:“得书图共祭己时,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461页。这不也正是郑振铎先生的写照吗?
何况(1961-),男,学者,作家(厦门 3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