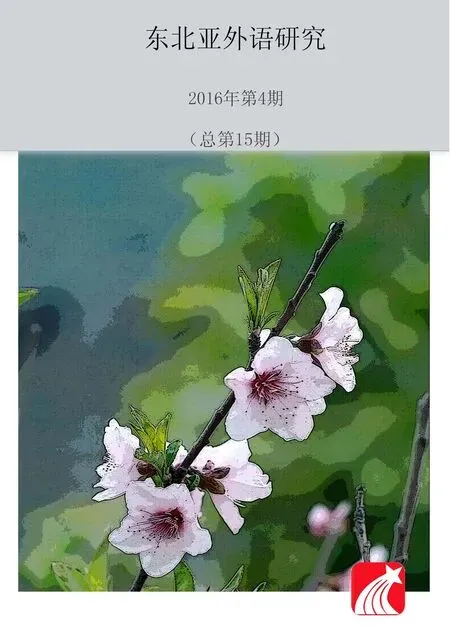“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
——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①
吴光辉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
——以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中心①
吴光辉1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之中,“中国形象”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与其说是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倒不如说是“中国形象”内在的一种张力、即“形象张力”的问题。就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之下,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自中国的外部表象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家族或国民性、美术或宗教、风俗习性、文学志趣、文化性格、地域风土等一系列领域,逐渐地构建起有别于日本的、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现代性理论(Modernism)成为日本知识分子“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与想象空间的理论基础。
中国形象;话语建构;想象空间; 日本人;中国游记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主编张明杰(2007∶9)指出:“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②自敬仰而变为蔑视,不仅意味着日本认识中国文明的一种情感变迁,乃至蔑视中国论、蔑视亚洲论的形成;同时也带有以日本为媒介的东西方文明比较、且站在日本主义立场下的通过“自我—他者”的镜像设定,赋予中国以文化他者的身分之内涵。
不过在此,借助台湾学者黄俊杰(2004∶281)的一段话,“日本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时,常不免感受到现实中国与文化中国之间的落差及其所引发的张力”这样的张力或者一种紧张关系,绝不仅仅是来自现实的认识与文化的想象之间,或者通过“敬仰”、“蔑视”这样的情感性描述可以完全概括的。我们必须看到,日本针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本身是多元性的结构,即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自中国的外部表象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家族或国民性、美术或宗教、风俗习性、文学志趣、文化性格、地域风土等一系列领域,逐渐地构建起有别于日本的、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不仅如此,这样的形象之背后亦存在着中国与日本、东方与西方的宏大叙事与力学结构。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张力或者紧张关系所演绎出来的话语模式,使中国形象呈现出一个多样性的、多元化的系谱。
本论以一部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考察为对象,通过阐述他们考察中国的核心内容,勾勒出他们的中国文明想象空间,或者说以这一知识与想象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中国形象,并进而站在东方与西方的比较文明论、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他者化的双重立场来剖析他们认识中国的视角,推演出日本知识分子重建“中国”话语、并赋予中国以“文化他者化”的逻辑或者方法,并力图挖掘出隐藏在它背后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这一根源。
一、“文明母国”传统下的中国形象
中国哲学研究者宇野哲人(1875-1974)的《中国文明记》(著者注:原标题为《清国文明记》,1918年出版)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中国游记的代表作之一,亦被美国学者佛果尔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转自黄俊杰,2004∶281)。在其《序》之中,宇野哲人(1999∶序)提到:“读古代圣贤经传,并以此来认识中国者,皆以为中国圣人并起,贤良如云,实是世界上理想之国。中国果真是理想之国耶?世人又往往以自己缺乏之经验,动辄谩骂中国人忘恩背德,不可理喻。中国国民果然应得如此谩骂,不可交往耶?”出于这样的疑惑,宇野哲人对“文明母国”的中国进行了考察,以风俗习惯、社会人文、名胜古迹为对象,试图向世人“介绍中国国情之一斑”。
宇野哲人1906年第一次来华,而后在1912年再度来华留学。宇野的中国第一印象留在了登陆地点——塘沽。矮陋的泥屋,满目的荒凉,作为北清之门户,宇野哲人(1999∶3)认为“此绝非中国之名誉所在也”,故而生“遗憾”之感,且这样的遗憾一直贯穿整个中国纪行。北京,是宇野哲人考察的一个重要对象。宇野详细记载了北京的城楼、房屋、道路;北京的露店摊贩、叫卖小吃、饮食货币;北京的祭祀活动、民间信仰、名胜古迹。之所以把北京作为重点对象,是因为其确认“北京可谓是中国之模型,了解北京,亦即了解中国之大半。……而后遍历各地,中国之真相则愈加明了。”(宇野哲人,1999∶5)但是,接下来的中国纪行却与他自身的“想象”极为“乖戾”,截然不同。“予在北京之日,见人情惟利,不知有义,浮薄而背信。北京之地,或是与外国人接触而误染此恶习耶。以北京一地而论中国,恐亦是群盲评鼎,不游中国广阔之内地,则无法遽断。”(宇野哲人,1999∶80)而后,宇野哲人入长安,过长沙、武汉,经南京、镇江、抵达杭州,足迹遍布了中国南北。由此,宇野哲人深切感到中国地域广博,文化宏大,不可一言蔽之,轻言侮之,并指出“作为国家之中国,现时虽无势力可言,而作为民众之中国,则是有势力之民族,对之绝对不能加以轻蔑。……作为国家,中国今日之所以不振,或起因于彼国自古以来民主主义思想发达,由此而形成易姓革命之风,缺乏在一定之主权下统一团结之性格。而作为民族,之所以称之为具有大势力之民族……其一大理由,即在于彼等所采取之家族主义。”(宇野哲人,1999∶182)由此,宇野哲人将中国人的国民性作为了自身重点考察与研究的对象。
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不仅是其考察与认识中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他确立自身作为中国思想研究者之地位的标志。就中国的国民性,宇野哲人(1999∶182-205)列举了民主性、家族主义、利己性、迷信、夸张性、附和雷同、社交性、同化作用、保守性、服从性、和平性、社会性、从容不迫之性格等一系列要素,并指出:中国国民自古以来就是民主性国民,因而也具有了地方性的自治精神;中国人注重家族主义,且与日本人的以皇室为核心的大家族主义截然不同;中国人追求独自享乐,上下惟利,故而商业极为发达;中国人迷信观念极强,且极为夸张;中国人是天生的社交家,善于应对,礼貌周全,至于是否真心诚实,则未为可知;中国强大的同化力使之对“外番”之信仰悉加包容;中国之保守,即便政府之法令力求改革,而社会风气却依旧如故;中国人善于服从,只要采取威力压制,则无不屈从者;中国人是和平之国民,同时也是文弱之国民;会馆公所慈善设备,体现了中国人的社会性;中国人之从容不迫,或泰山崩于前而临危不惧,或坚韧持久之顽强。这样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的评价,或褒或贬,或善或恶,应该说确实勾勒出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客观的近代中国形象,即便是到了现在也具有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宇野哲人通过中国纪行而展开的中国国民性之考察,应该说具有了三大意义或者特征。首先,这一研究应该说与那一时期日本的国民性研究保持了同步。以1907年国文学者芳贺矢一(1867-1927)的《国民性十论》、1914年野田毅夫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为代表,国民性研究成为了东亚思想研究的一个热潮③,这一研究同时也影响到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中国思想先驱,从而形成了一种围绕中国国民性考察的共通性话语;其次,宇野哲人的中国国民性考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即便是针对1912年之后的中国乱象,宇野也将根源归结为了中国的“易姓革命”,“打倒清王朝以后,又有谁人能够取而代之。每年至此,吾人感谢我日本国体之尊,又转而哀悯中国国体易姓革命之不幸”(宇野哲人,1999∶194)。也就是说,宇野是站在日本·中国的文明比较的立场来考察与审视中国。第三,宇野哲人(1999∶182)指出,考察中国的国民性或者说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在于“中国自古是我日本文化之根源”,日本需要探索自身文化的发展轨迹,找到自身的主体性。但是与此同时,失去了“主体性”的“中国表面上是君主专制国家,而实际上是民主性自治国民”——尽管缺乏“国民之协调一致性”,因此谏言中国之先觉者注意唤醒中国的国民性,“对之加以善导,而进入文明之域”(宇野哲人,1999∶191)。也就是感慨于古代与现代的“中国形象”之紧张关系,要站在一个西方式的“文明进步”的立场来唤醒中国的国民性。
二、“西方文明”暗影下的中国形象
日本近代文学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亦是积极呼应“中国情趣”这一热潮的代表人物。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现“日本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至7月访问中国,游历了上海、苏州、南京、北京等十多个城市,撰写了随行笔谈——《中国游记》并于1925年由改造社出版。与谷崎润一郎创作《西湖之月》、《鲛人》、《鹤唳》等一批小说一样,中国旅行也成为芥川文学创作的源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即是这一主题下的代表作品。
芥川抵达上海的次日,大阪每日新闻社就以《新人眼中的新中国》为醒目标题报道称:“中国作为世界之谜,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国度。旧的中国尚如老树横斜,新的中国已如嫩草吐绿,在政治、风俗、思想等所有方面,中国的固有文化无不与新兴势力犬牙交错。这正是其魅力所在”。“芥川氏为现代文坛第一人,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情趣的爱好者,氏今携笔赴上海,猎尽江南美景后,将北上探访北京春色,寄自然风物抒发沿途所感。同时结交彼地新人,竭力观察年青中国的风貌。”(芥川龙之介,2007∶4)一段介绍,可谓是确立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基调。究其基点,第一是新旧势力、新旧文化交织在一起的中国之“不可确认”的魅力,也就是中国会留下无穷的幻想;其次则是“中国情趣”这一术语。这样的中国情趣,并非是谷崎润一郎所主张的日本人的汉诗文素养,而是指中国的文学文物,即所谓“中国情趣”的第一层内涵;第三,结交“新人”、观察“年青中国”。是否是新人,是否可以观察到中国的新的发展,或许也不过是一个幻想。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有意识地与清末的中国形象——老大的衰败帝国相区别开来,为日本人展现一个“年青的”、或许可以想象着是否蕴含了无穷的“奇迹”的中国形象。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第一瞥”,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让他忘却痛苦的愉快新奇之事。一走出码头,芥川就被一群“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的中国车夫所包围。夜晚酒吧外的卖花的老太太“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个乞丐一样朝我们伸着手。老太太在得到了我们的银币之后,好像还期待着我们再一次慷慨解囊”(芥川龙之介,2007∶5)。对于这样一个亲身体验,芥川提到:“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芥川龙之介,2007∶11)在此,中国情趣的幻想一下子就破灭了。之所以令他感到遗憾,不仅因为上海的西洋化——或许这也就是日本媒体宣扬的“新”的中国,令他感受到中国的“不伦不类”,更是因为他自身“讨厌低俗的东西”(芥川龙之介,2007∶30-31)。中国的第一印象不是高雅古朴的“中国情趣”,而是经历了西洋化洗礼的“低俗”,亦是西洋文明暗影下的中国形象。
即便是对于谷崎润一郎极力赞美的杭州西湖,芥川写到:“不知何时起,我已对西湖起了反感。西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漂亮,至少现在的西湖完全没有让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的姿容。……这位中国美人(西湖)已经被岸边随处修建的那些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西式建筑)植下了足以令其垂死的病根。”(芥川龙之介,2007∶72)或许谷崎润一郎所想象的是日本与中国江南的“割舍不了”的“故乡”之感,但是芥川并不是一个“流几滴为旅途而感伤的眼泪”或者“摆出一副游子般的架势,深深陶醉于美丽的风景”的“绅士”(芥川龙之介,2007∶58),而是一个严肃的、执着的寻找着“异国情调”的人。但是,经历了西洋化冲击的“俗恶无比”的中国现实并没有满足其满怀憧憬的中国想象,从而留下了“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的惆怅情怀。
中国纪行并没有给芥川带来新奇的感受,反而令他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沉重。“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是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幼,都在唱着太平曲。当然,在年轻的国民中,或许多少还能看到一些活力。但事实上,他们的呼声中,尚缺少那种足以传达给全体国民的激昂的热情。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着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情趣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介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芥川龙之介,2007∶136)粉饰的太平、国民的堕落、缺乏激昂的热情,也正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的真实写照。在批判颓废的“感官主义者”与浅薄的“中国情趣”的崇尚者的话语之背后,也反映出芥川的“中国幻想”的彻底破灭。
芥川应该说是抱着一种“中国情趣”的观念开始旅行,并由此来认识现实中国。但是,中国的现实并没有满足个人的中国想象,或者说个人的幻想最终也只是归结为一个幻想,芥川试图发现中国“大陆”的沧桑历史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魅力究竟所在,但是却是极为失望地认识到中国人的骨子里丝毫没有什么改变,其文化情结依旧是“将重视自我的人,变为传统的奴隶”(芥川龙之介,2007∶144)。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与谷崎的“回归”式的中国情趣、即希望由此找到日本传统文化的渊源的思维方式不同,芥川之所以贬低江南,对于中国北方的雄浑博大加以赞美,乃是因为他的“中国情趣”是为了发现与岛国日本截然不同的“大陆式的气氛”(芥川龙之介,2007∶164-165)。对于芥川而言,这样的一种气氛正是打动他自己的中国希望之所在。
三、“风土人文”环境下的中国形象
日本现代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曾经于1935年第一次出版《风土》,后于1949年改版。该书将世界的“风土”归结为季风、沙漠、牧场三大类型进行了一个地域性考察(和辻哲郎,2006)。中国不仅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西方、印度、乃至日本也是其风土考察与比较的重要对象。严格地说,和辻哲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洲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文化论的亚洲主义的提倡者。但是,审视其风土考察的文化地域性特征,应该说由此而出现的文化论带有了突出日本“中心”地位的内涵。
根据1949年改版的《风土》一书,和辻的中国考察以长江、黄河为主要对象,并附加了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力图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的形象。和辻指出:“泥海”之长江君临在整个流域的平原之上,但是与唐人杜甫《旅夜书怀》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广阔伟大不同,它留下来的只是“单调和广漠,茫茫的泥海没有给我们以大海翻腾跃动的生命感”,“也缺乏大江特有的漫然流动之感”,“中国大陆的广袤给我们的感觉是缺少变化,广漠而单调”(和辻哲郎,2006∶107),而且,这样的因素也影响到了日本。不仅如此,和辻还指出:“我并不是认为只有长江能代表中国的风土。中国大陆的另一半是由黄河来表现的。”(和辻哲郎,2006∶108)黄河尽管深受沙漠之影响,但是中国人的特征之中几乎看不到沙漠人所特有的绝对服从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正是“不甘于服从,……他们不肯受任何其他的拘束。……尽管表面上唯唯诺诺,露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决不会轻易认输。……这样的决不低头的忍受与他们无动于衷的性格密切相关,只有无动于衷才能做得到这一步,而同时在这种态度中又培养了无动于衷的性格。”(和辻哲郎,2006∶108)
和辻哲郎(2006∶106-107)认为:中国文明是季风型文明的代表之一,它的地理特征在于“单调与空漠”,它的文明特征是“接受与忍从”。这一文明性格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意志的持续、感情的放纵,固守传统,历史意识的发达”。中国人的基本特征,一言蔽之,即“无感动性”,也就是对于一切皆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毫无激情可言。为了进一步证实中国人“无动于衷”的性格,和辻讲述了自身体验到的香港人的生活。尽管沦落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生活在香港这一“异域”的中国人,却依旧保持着一种重视血缘关系和乡土关系的观念,过着一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活。无论是对于艰难的生活还是面对战争的危险,他们总是“泰然处之”,从而令其感慨“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民呢?”无疑,这样的人民是执着于自己生活的“无动于衷”的人(和辻哲郎,2006∶112)。
所谓“风土”,并不仅仅只是自然环境,同时也是一个人文艺术的风土。和辻对于中国风土的考察并没有局限在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性格这一方面的描述,也涉及到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人文艺术。和辻指出:中国艺术气势宏大而内容空疏、统领大局而不重细微。汉代、唐代、宋代的文物之中,也不乏纤细入微之作——日本艺术理念深受这一纤细之影响,但是到了明清至近现代的中国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这样的文化性格也体现在了典籍编撰,国家治理等一系列方面,从而养成了崇尚宏大气魄而流于空虚、追求外观之完善而不注重局部之精华、探求形式之体面而忽视内心之感动的文化性格,“无动于衷”、“感情平淡”也正是贯穿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和辻哲郎,2006∶112-113)。在此,地理的单调而广漠的“空”、性格的“无动于衷”或者“无感动性”、文化的“无动于衷”、“感情平淡”,三者被置于了一个同一性的框架之内,构成了统一性的“中国形象”。
不过,是否中国的地理就决定了中国人的性格乃至中国的文化呢?对此,恰如日本学者藤田正胜所指出的,和辻哲郎所强调的“风土”尽管存在了风土决定性格,也就是环境决定论的一面,但是就风土乃是“我们日常性的直接的事实”,我们必须“在风土之中找到自己”这一视角而言,和辻哲郎的基本立场并不是所谓的“环境决定论”。他所强调的是一个在风土之中进行自我确认的立场,自然与文化、环境与个人,社会与自我这样的结构性的二元要素在“风土”之中得以成立,得以“互生互动”,不断地交往推演下去的立场(藤田正勝,2003∶7)。因此,对于中国人的“无动于衷”或者“从容不迫”,和辻哲郎(2006∶112)并不是直接地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而是抱着一个“身份”确认的立场指出:“中国人的无动于衷并不是说他们缺少感情生活,而是感情生活的形态之一就表现为了无动于衷。”而且,这并不伴随什么人格的褒贬评价或者价值判断,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样的态度“甚至是一个修炼的目标”。但是,正是这样的“无动于衷”,中国人最终是“将自己引向了不幸的深渊”,沦落为外国势力的殖民地。
和辻哲郎之所以考察中国的风土,恰如其中国部分的原标题——“中国人的特性”④所示,是为了探讨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究其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考察中国,倒不如说是借助中国来阐明与确认日本人的国民性。正如其所叙述的,“认清自己,就是超越自己,摸索一条前进的道路。理解与己不同之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就会开拓新的路子”(和辻哲郎,2006∶115)。因此,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强调日本崇尚的中国文化实际上与日本后来形成的文化截然不同,日本需要正确地理解自己;另一方面,中国人借助这样的考察,可以“重新认识到自己失去的、过去的辉煌灿烂的文化的伟大力量,而且可以从中找出探出一条路子,打开现在停滞不前的状况”,寻找到“文化复兴”的道路(和辻哲郎,2006∶116)就此而言,和辻的中国认识,可谓是处在“辉煌的传统,停滞的现实”这样一个认识的视角,也带有了西方式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本质内涵。
四、结论
概而言之,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纪行或是中国古都的考察,或是中国内陆的旅行,或是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的描述,或是名人逸事、访书见闻,最为生动而直接地再现了近代中国的风土人文,亦对日本人的“中国形象”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其之所以得以树立起来,其根本首先在于排斥江户时代以来的汉学式的、观念性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研究,而是要将中国的现实、尤其是中国人的现实拉入到自身的考察视野之中。在这样一个考察的变迁之中,中国从宇野哲人笔下的“文明母国”一直跌落为西方文明标准下的“文明的落伍者”,中国被赶下了亚洲的领导者的地位,沦落为被排斥的文化他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化他者化”的话语建构,中国成为一个被解剖的、支离破碎的纯粹客体。
其次,他者的想象乃是自我意识的延续。不过,自我意识不断延续下去,或者是完全走向文化的独我主义,成为吞噬他者、贬低他者的话语霸权;或者是走向一个基本立场或者观念下的、将自我加以相对化的文化多元共生主义。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与中国纪行,实质上潜藏着一个多样化的契机。但是,日本的目的却在于通过再现中国,解剖中国、批判中国,来确立日本近代化发展的一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考察不仅是中国的话语建构的重要媒介,同时也是日本树立自身形象的一个工具或者方法。而且,这样的考察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力图赋予近代日本的“同一性”的话语模式,构成了一个彼此“共谋”或者“互动”的关系。
第三,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考察,不管是将中国视为文明母国,期待中国的觉醒,期待亚洲的一体化;或者是将中国还原为中国,强调自身与中国之间的割裂或者分离,究其结果,基本上是屈从在西方现代性理论(Modernism)的话语霸权之下,从而将中国与他自身皆放在西方价值体系的内部或者延长线上来加以把握,东西方彼此互为他者的外部对抗性逐渐消弭,而转化为了一种内在的“力”的逻辑支撑下的进步与野蛮的竞争或者同化。由此可见,所谓“中国考察”,不过是日本屈服在西方的中国认识之下,且进一步通过实证考察来突出、论证“中国停滞论”这一西方近代以来的话语结构的工具而已。反过来说,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进一步论证了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或者“普遍性”⑤。
在此,谨以汉学家重野安绎(1927-1910)的一段话作为本论的主旨,或许是认为以欧美为标准来鄙视中国实乃为“褊狭”之态度,在为金子东山编撰的《支那总说》(1883年)而作的序言中,重野指出:“吾故以谓,所观于支那,以观欧美;所观于欧美,以观支那,则美疵互发,而益乎我多矣。”(转自陶德民,2002∶220)也就是站在日本的立场,希望更为多元性地输入外来的文明,而不是偏执一端,以此来谋求国家的进步。这样一来,站在欧美、日本、中国的“三点测量”的立场,日本可以展开自身充分的想象,既可以偏执一端,亦可以允厥其中,日本可以在这样的立场之下来充分地、动态地呈现自身的主体意识。
注释:
① 本文是基于拙著《日本的中国形象》的文本脉络,通过梳理近代以来的“文化他者化”理论框架整理而成,其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形象背后的日本“主体性”的动态思维,在此予以解释,敬请诸位批评指导。(吴光辉.2010.日本的中国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 张明杰《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转自内藤湖南,2007)作为参考,在此列举出张明杰博士主持翻译编撰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包括了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与《清国漫游志》、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殷野琢《苇杭游记》、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夏目漱石《满韩游记》、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德富苏峰《中国漫游记》与《七十八日游记》。这一系列书籍的出版,无疑为近代日本人中国考察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文献资料,也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内藤湖南.2007.吴卫峰译.燕山楚水[M].北京:中华书局.)
③ 芳贺矢一将日本人的国民性归结为:忠君爱国、崇敬祖先重视家名、现世实际、喜欢草木热爱自然、乐天洒脱、淡泊潇洒、美丽纤巧、清静洁白、彬彬有礼、温和宽恕(转自刘建辉,2004∶91)。和辻哲郎1935年出版的《风土》一书的原标题也是“国民性的研究”(转自和辻哲郎,2006:导读)。(刘建辉.2004.产生自日本的中国“自画像”[A].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 《风土》一书的中国考察,最初是以“中国人的特性”为标题发表于1929年《思想》杂志,1944年曾进行大幅度修改,1949年出版之际附加了香港见闻(和辻哲郎,2006:导读)。
⑤ 这一问题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日本的“欧洲性”的问题,也就是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之中的欧洲观念的问题(黄佳甯 石之瑜,2009∶197-198)。(黄佳甯 石之瑜.2009.不是东方——日本中国认识中的自我与欧洲性[M].台北:台大政治系中国中心.)
[1] 藤田正勝.2003.和辻哲郎「風土」論の可能性と問題性[J].日本哲学史研究,(1)∶1-15.
[2] 和辻哲郎.2006.陈力卫译.风土[M].北京:商务印书馆.
[3] 黄佳甯 石之瑜.2009.不是东方——日本中国认识中的自我与欧洲性[M].台北:台大政治系中国中心.
[4] 黄俊杰.2004.二十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A].张宝三 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C].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5] 芥川龙之介.2007.秦刚译.中国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
[6] 陶德民.2002.简论明治时代汉学家的多元主义文明观[A].卞崇道 藤田正胜 高坂史朗编.东亚近代哲学的意义[C].辽宁∶沈阳出版社.
[7] 宇野哲人.1999.张学峰译.中国文明记[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Imaginary Space of “China’s Image”——Focusing on the Modern Japanese Investigations of China
In the modern Japanese investigations of China, the greatest problem that “China’s image” encountered was not so mu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s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China’s image”, namely the problem of “image’s tension”. With such a strained relation, the modern Japanese investigations of China’s image were, from the superf cial level of external imagery, deepened to the study of a series of domains such as the Chinese society’s families or nationality, arts or religion, customs and habits, literary interests, cultural characters and regional customs, which have gradually constructed the China’s image as a “cultural other”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apan. In this process, the western modernism becam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imaginary space of “China’s image”.
China’s imag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maginary space; Japanese; travels in China
I106
A
2095-4948(2016)04-0028-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日本知识分子认识与重构中国形象的研究”(15BWW022)、福建省社会科学
“现代日本‘中国形象’嬗变与回归的研究”(2013B088)的阶段性成果。
吴光辉,男,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