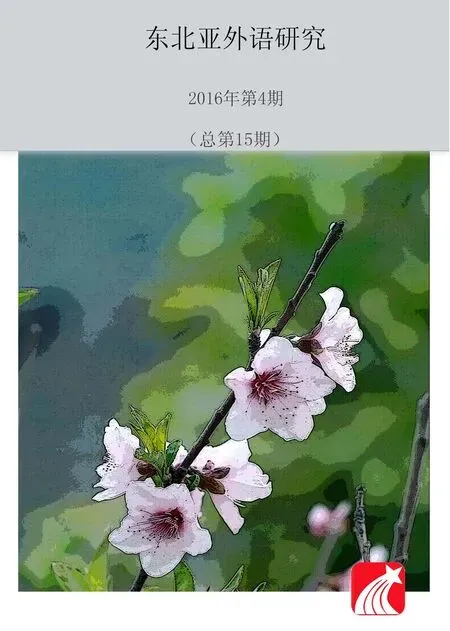俄罗斯白银时代生态创作思想探析
赵雪华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俄罗斯白银时代生态创作思想探析
赵雪华1
(兰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当代俄罗斯生态文学研究热潮是对“人与自然”这一古老主题的延展研究,回溯经典,白银时代的生态文学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其创作思想由以下三个维度构成:生态情感维度、生态危机意识维度和生态伦理道德维度。生态作家的创作思想并未止于此,从深层次讲,“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树立,精神生态危机的解决是俄罗斯生态文学创作的最终使命。
白银时代;生态思想;生态道德;精神生态
文学的发展存于此消彼长的思潮更迭,然而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一些传统主题与创作倾向在历史发展的激流中固若磐石,历久弥新。从古罗斯《伊戈尔远征记》中携带“敬畏自然”之意的多神教元素的大量使用到19世纪风景诗和自然小说中风花雪月、山河草木的意象塑造,自然的主题稳固地流传下来。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与自然主题紧密相连的生态文学创作已先于生态文学理论在文学发展进程中被践行。“俄罗斯人心目中的‘自然’,可能的确不单单是土地山川,森林湖海,而且还包括被意识到了的自然、被改造的自然、人本身的自然等等。‘自然’所具有的多重含义,也就决定了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俄罗斯生态文学具有多重维度”(刘文飞,2006∶118),那么,如果从创作思想方面来看,白银时代的生态文学可分为以下三个维度:生态情感维度、生态危机意识维度和生态伦理道德维度。
一、自然情结:白银时代生态文学的生态情感维度
人文科学的生态书写与自然科学的生态书写有所不同,尤其在文学领域自然意象、文化涵义和作家情感之间的共鸣与回应式的依存体系贯穿于生态作品中。回眸经典,艺海拾贝,茹科夫斯基笔下的落日余晖、费特笔下白夜里天边颤动的星光、丘特切夫笔下晚风携细雨的早春、叶赛宁笔下的婷婷白桦等等,自然的美丽画卷与人类的细腻感悟和珍爱自然之情紧密融合,自然意象情感化,作品富有感染力。这一时期的生态作品往往诗情画意,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乡村自然景色的歌者布宁善于将自己对大自然瞬息万变的感悟通过细致的语言创作成美文,如《在露天下》(1898年)、《乡村草图》(1894年)、《田野的花》和《落叶》(1901年)、《松树》(1902年)等。在布宁的自然世界里春天的元素是蓝天、暖阳、绿苗、薄雾、麦田;初夏的景象是果园屏息敛气准备迎接雷雨的瓢泼(《夜莺》);《落叶》里描写了秋冬会际之时的唯美景色;而冬季时节松林里散发着新雪和松汁混合的幽香,兔子悠闲地啃食着云杉的嫩枝(《松树》)。早期象征代表之一巴尔蒙特也是“风景随笔”大师,充满动感且富有生命力的自然见于诗集《在北方的天空下》(1894年)和诗集《仙女的童话》(1905年),诗人以平和的诗韵及纯朴的笔触描绘了自然给予人的亲切印象:
越桔正慢慢成熟,
白天已越来越冷,
听到鸟儿的鸣叫,
心里平添了愁情。
太阳已经很少欢笑,
花朵失去了芳香。
秋天就快要睡醒,
哭泣得眼泪汪汪。
《秋》(1905年)
(转自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06a∶16)
对祖国自然景观的热爱与赞美之情同样溢于其他作家的笔端,别雷在《蔚蓝中的金黄》(1904年)中描绘了朝霞和晚霞辉映下自然景象;恰佩金创作了描写泰加森林的短篇小说《白色隐修院》(1912年)和《天鹅湖畔》(1918年);克雷奇科夫心中的春天森林胜过荣誉:
万叶千声的春天树林,
和高空的雁鸣,
还有家乡广阔的草原,
我觉得都比荣誉更可亲。
《阔叶林妈妈》(1918年)
(转自许贤绪,1997∶136)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广袤森林、丰富的民间传说和传统的民族,许多树种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四月新绿的白桦树被喻为春天使者,如同今天象征着新年到来的十二月的枞树。“在古老的东正教节日‘三圣日’来临之际,室内外饰以白桦嫩枝,姑娘们头戴白桦花环,围绕着系有彩带的白桦树载歌载舞,庆祝春回大地”(Афанасьев А.Н.,1995∶156)。白桦树在生态文学中是最主要的意象,其次是橡树、杨树、松树和花楸树等。白桦树意象的使用尤其在叶赛宁的诗歌中达到了顶峰,在诗人心中白桦树本身就犹如一位佳丽:
一棵白桦树
伫立在我的窗前,
白雪覆盖着它,
犹如身披银色的华装。
《白桦树》(1913年)
(转自周立新,2012∶281)
1914年叶赛宁创作了另一首极为优美的白桦之歌——《晨曦》:
金色的星辰睡意朦胧,
明镜般的水面荡起涟漪,
晨曦绽放在一个个河湾
也抹红了遥远的天边。
醒的白桦轻展笑颜,
丝绸般的发辫在风中飘散。
绿色的耳环在簌簌作响,
银色的露珠散发着光芒。
栅栏旁的簇簇荨麻
身披缀满明珠的衣衫
淘气地摇摆着,轻声唱道:
“早安!”
《晨曦》(1914年)
(转自周立新,2012∶298)
金星红霞,白桦银露,诗人依据“炎绯绿碧,随类赋彩”的绘画美学原则用语言创作了一幅着意用色的风景诗。不仅如此,“自然人化”也是叶赛宁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诗人将自然提高到人的位置上,赋予了白桦以人的生命、思想、灵性,一句“早安”,一声问候构建了人与自然之间平等温馨的画面。
白银时代自然抒情诗中还常常混合东正教思想和信仰,因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在新农民诗人的风景抒情诗里是固定不变的……他们创造了兼有神圣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二元空间”(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2006b∶281),克柳耶夫诗集《松林呼啸》(1912年)和《森林往事》(1913年)中自然主题混合了东正教救赎思想和“灵魂不朽”的复活思想,而叶赛宁的风景诗里钟声齐鸣,充满了弥撒的气氛。
在斯拉夫民间传说中有“宇宙树”的提法,“树”是宇宙的时空坐标,连接了天与地,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触景起情,在许多诗歌里自然意象蕴含了诗人对过往的缅怀、对现实的期望和对未来的忧虑。象征派诗人勃洛克将这一思想体现在《在库里科沃战场》组诗中,组诗的每一个意象都像是一个特殊的符号和象征,联系着历史与现在。诗人借诗抒情歌颂了俄罗斯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以及没有随时间流变的传统和信仰,表达了对俄罗斯民族的珍视之情。1905年革命无法使勃洛克透过浪漫棱镜来观赏自然,而是实景实描,大自然的冷暖明暗与对祖国未来的担忧和期盼在诗人内心深处相逢:
卑微的穷乡僻壤啊
无以计数,难以胜数,
在渐暗的天光里
只有篝火在远方的草地上闪烁……
《秋日》(1909年)
(转自周立新,2012∶264)
文明高度发展的古埃及和古印度的文化是动物中心主义文化,近现代人们对动物的评价可能低于人类,也可能高于人类,无论怎样,动物在人类的世界观里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熊、马、狗、狼、蛇、羊等动物在生态作家笔下被创造性重现,如库普林在短篇小说《巴拉特卡》(1895年)、《巴尔斯和朱立卡》(1897年)和《白哈巴狗》(1904年)刻画了有情有义的狗的世界。叶赛宁在《冬天在歌唱,在呼呼作响》(1910年)、《狗之歌》(1915年)、《我不想再欺骗自己……》(1923年)中表达了对动物的真挚情感。
尽管白银时代是一段复杂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骤变,但是祖国仍是诗人和作家的挚爱,俄罗斯森林、田园、树林、动物在诗人和作家心中的地位依旧,对祖国的热爱渗透于生态文学创作里。“文学领域的生态学研究的是语言艺术与自然和社会相互影响的条件和规律”(Лаврентьев М.И. , 2007),生态文学在文学与生态学的相互碰撞中生发,生态文学促进了人们对自然和生态的认识,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珍视,而任何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也触动着诗人和作家的内心。
二、乌托邦追寻:白银时代生态文学的生态危机意识维度
人类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改变很慢,或者基本没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和古代人几乎没有区别,可是人类智力却取得了极高成就,可惜用在了破坏出生和生活的家园——自然上。十月革命前后是苏俄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重要转型期,资本主义在苏俄发展的利弊迅速反映在文学领域中,生态文学创作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突起也是源于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的思考。库普林的《儿童花园》(1897年)里身患重病的小女孩儿萨什尼卡的最好疗剂是新鲜空气和绿荫;布宁的《新路》(1901年)里象征着资本主义工业的铁路贯穿俄罗斯森林草原,沿途古老宁静的生活被打破,小说充满了对自然资源无节制掠夺式开发的忧虑;无独有偶,契诃夫在《樱桃园》(1904年)里同样表达了对“诗意栖居地”的摧毁的感叹和对势不可挡的新生力量的唏嘘。
经济飞速发展基于对自然肆意攫取,科技进步的副产品是不可控的生态灾难,人类开始反思追求经济增长的过激行为。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1896年)中通过阿斯特洛夫医生之口表达了利用自然的态度:出于需要砍伐树木,而不是乱砍乱伐和过渡消费自然。类似作品还有库普林的《森林之夜》(1890年)、《摩洛》(1896年)和《黑色的闪电》(1913年)等等。爱普施泰因指出,“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将对本地区的生态整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明智而慎重的态度更为可取”(Эпштейн М.Н.,2007∶322),可是在利益和本能的驱使下,外在的呼吁对于生态意识的形成收效甚微。
人对自然过渡侵略,自然对人无情报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生态文学就是批判这种失衡,并分析失衡的因果,同时构建生态乌托邦,构建和谐的生态文明”(陈少红,2013∶7)。自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以来,几百年对峙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在构建和谐生态的宗旨上取得共识。众所周知,乌托邦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代名词,指人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布宁的《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年)里乌托邦模式体现为前工业文明时期明亮欢畅的社会形态。布宁借用果园、落日、炊烟、狩猎等现实主义元素试图复原沙皇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叶赛宁的美好家园是鸟语花香、淳朴欢愉的乡村:
苹果和蜂蜜散发着清香
你的救世主在每个教堂。
草地上拉古多克琴声悠扬
人们 在欢快地跳舞歌唱。
《你好,罗斯,我亲爱的罗斯》(1914年)
(转自周立新,2012∶288)
无论是“隐遁乡村”还是“追忆似水流年”均不可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俄罗斯的迅速发展体现了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性,布宁客观剖析和批判了中篇小说《苏霍多尔》(1911年)中娜塔莉娅对苏霍多尔庄园的依恋中所附带的固执封闭与视野狭隘的一面。勃洛克将世外桃源置于穷困潦倒的采石工人的梦境中:
又高又长的围墙上,
玫瑰花蜿蜒交错,
夜莺在婉转歌唱,
小溪和树叶在低语什么。
《夜莺园》(1914-1915年)
(转自郑体武,1996∶182)
这个树影婆娑、小溪潺潺、夜莺轻唱的世外桃源与采石工人平淡贫困的生活境况构成了鲜明对比,诗人理性地以梦境否定了采石工人虚幻的乌托邦世界。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诗人和作家们清楚地知道,“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返回与中世纪甚至原始时代同样的生存状态中,但他们还是要写出他们的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激发人们不懈地探索在当今的发展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王诺,2013∶219),于是在乌托邦追寻之路上生态文学分流,科幻小说创作兴起。
标榜美好未来的科技乌托邦世界的建构是科幻小说的中心思想,如勃留索夫的《南十字架共和国》(1904年)、奥谢多夫斯基的《未来战争》(1907年)、博格丹诺夫的《红星》(1908年)和世界著名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之一的《我们》(1921年)。科幻小说的显著特点是技术统治论(технократизм)傲视一切,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乌托邦因其负面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为实现乌托邦所付出的代价巨大而被世人诟病。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它的负面因素,乌托邦思想是一种高超的奇思异想,没有它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科技创新”(Лесков Л.B.,1998∶66),旧时代不应也不会回归,探索新的文明发展之路已成必然。我国先秦法家思想家管子(2010∶253)有名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意指世人应具有创新精神和改革意识。传统观念需要适时改变,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作用和地位,科幻小说家意识到科幻小说的激进性,提出了自然与社会“共同进化”(коэволюция)的妥协思想,将人从自然的崇拜者和征服者转换为生态共同体的一员。但是科幻小说通常因缺乏细节描写,无法给出具体的实现和谐发展的可行性方法,在实践上也往往遭遇社会政治经济阻碍,无法实施而成为“幻想”。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列斯科夫(1998∶67)认为乌托邦不只是理想或幻想,乌托邦的价值在于它预示了一个长远前景中事情有可能发展的趋势,所以不能简单地称科幻小说是异想天开之作。科幻小说通过科幻创作把现实和科技文明发展模式结合起来,探讨自然生态危机成因与解决之法,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发展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的美好设想。
反映自然生态危机和世界末日的生态文学引发人类反思,生态批评家布伊尔称这类生态预警性文学为“生态启示录文学”(转自王诺,2013∶220),但将自然灾难和生态危机完全归咎于科技现代化似乎不妥,“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不是科技的危机、经济的危机、工业的危机、发展的危机,而是思想文化的危机”(王诺,2011∶ 16)。生态文化可解释为一种伦理学,道德规范和戒条体系。自然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道德危机,道德探索是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传统,也是白银时代生态文学创作思想的主要维度。
三、灵魂风景画:白银时代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道德维度
如果说世界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自然生态灾难的思潮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是文学家对地球及其所有地球生物命运的忧虑在文学创作上的必然反映,那么俄罗斯生态文学则超越了对自然生态层面的观照。对自然情有独钟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心中自然不仅仅是创作素材,情节展开的介质,或是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和情感的载体,“俄罗斯作家总是将大自然作为检验人性的尺度,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自然’和人性密不可分。俄罗斯文学中常常根据主人公对待大自然、对待动物的态度来判断他的精神和灵魂品格”(周湘鲁,2009∶56)。俄罗斯作家善于通过对动物的塑造来对人性的善恶、美丑进行哲理性思考,极具灵性的狗一直是世界各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钟爱的创作对象,库普林在短篇小说《皮拉特卡》(1895年)中以感伤语调叙述了艰难岁月里流浪狗皮拉特卡和老乞丐饥寒交迫、相依为命的感人故事。被欺凌与被凌辱,人狗无异,“整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依恋着他,那就是皮拉特卡”(库普林,1987∶101),在老乞丐的深刻感悟中饱含了世间冷暖。库普林通过物种界线的打破,暗示了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法则中爱的缺乏。人狗在相互慰藉和相依为命中缔结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皮拉特卡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被库普林“有意提升”和夸张地赋予现实中的人所匮乏的美好品行和高尚情感,作家意在充满真情的人狗关系和冷酷的人人关系之间构建强烈反差和对比,表达了对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的生态关系的热切向往。
冷酷的人际关系更体现在女性的物化现象中,库普林的短篇小说《ALLEZ!》(1897年)里当杂技女演员诺拉摔落马下时得到的不是关爱,而是“那对人、对马和对受过训练会表演特别技能的狗一视同仁的喊叫:‘ALLEZ!……’”(库普林,1987∶239)。《ALLEZ!》的悲剧结局也不禁使人追问,19世纪古典文学中,女性被欺凌被凌辱的角色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不曾改变,女性生态危机缘何而来?女性又该如何摆脱生态困境?女性严重物化一方面由于父权社会男性具有主体地位的优越感,女性成为男性任由支配的客体。麦诺季是马戏团一流演员,获奖如此之多以至于“金质奖章都串成沉甸甸的链子”(库普林,1987∶241),而诺拉仅仅是他的一个普通助手,两者社会地位悬殊,助长了麦诺季的嚣张。麦诺季的国家级驯兽师的身份无疑是具有隐喻意义的,训练动物的口令“ALLEZ!”直截了当地用于诺拉的行为锁定了诺拉的动物角色。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自身对男性过渡依附,唯命是从,牺牲自尊自爱,将自身置于男性意识遵从者的地位,成为男性附属品,诺拉“把他看作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至高无上的人物,几乎就是上帝……如果他心血来潮命令她做什么,她会赴汤蹈火去执行”(库普林,1987∶239)。女性的自我物化导致了自身价值与独立人格逐步失去,最终走向毁灭。
女性生态危机的存在有其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我国学者郑永旺提出“有些观点在时间的长河中演变成文化元素,进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郑永旺,2015∶3),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男强女弱”和“男尊女卑”观念俨然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父权社会男性凌驾女性之上,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划为弱势群体。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赫拉利在2012年出版了《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迅速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20多个国家出版。赫拉利(2014∶57)从历史学和生态学角度诠释了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并对父权社会的“肌肉理论”给予了批判。以力量判断人的价值是对人的贬低,人类登上食物链的顶端凭借的是聪明才智。力量的悬殊是浅表性原因,“男尊女卑”思想根源于女性在精神上的逊色,女性的精神贫困引起男性对女性价值的否定,将女性物化。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是伦理学中的永恒议题,库普林在《阿列霞》(1898年)中给读者呈现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自然之女,吉卜赛姑娘阿列霞与自然的融合正是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的颠覆,燕雀在阿列霞的围裙里探头探脑,阿列霞俨然成了大自然“真正的”一部分,实现了卢梭的“回归自然”的理念。阿列霞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里,“谈吐优雅,并不比真正的小姐差”(库普林,1981∶182),“缺乏教育,却有着惊人的才智”(库普林,1981∶184),穷乡僻壤、自然条件恶劣、野兽的攻击对阿列霞构不上任何威胁,几乎“不需要别人”、“任何人都可以不见”(库普林,1981∶166),不仅如此,阿列霞和外婆还可以帮助别人。善良、勤劳、独立、骄傲、强烈的自尊自信,“社会的人”具有的品格阿列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自然中阿列霞“实现了”女性自身价值。但是人类能否真正融于自然,返朴归真,库普林给阿列霞设置了试金石——“社会的人”瓦尼亚。渴望美好爱情的本能使阿列霞克服重重障碍走上了重返社会的回归之路,对自己信仰的突破是阿列霞超越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自然之女贝拉的地方,也反射了阿列霞回归自然的真诚度。阿列霞和外婆最终不辞而别,离开波列西耶森林的结局是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证伪;离开瓦尼亚是对“社会的人”的生存环境存在冷酷无情、道德严重缺失等巨大问题的证实。
要实现真正的平等,人类需从内心真正意识到自然万物有灵有情,肯定万物的自身价值是首要条件。1949年美国出版了享有国际声望的科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美国新环境理论创始者”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在这本著作中利奥波德(2011∶199)首次推出“群体”(也译“土地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土地不仅是土壤,它还包括气候、水、植物、动物和人等等,而土地伦理规范则是要把人类从以土地征服者自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对任何成员的恶性掠夺行为都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与自然认同的过程,它的前提就是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高建华,2012∶93),对大自然的身份认同尚没有形成,现在只是通过道德命令或伦理规范来外在地肯定自然万物的主体性。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树立平等和谐的生态意识被更多的人文科学领域专家学者所关注和思虑。
四、结论
生态问题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意义,文学不可能对这个触及每个人的问题袖手旁观,社会意识转向生态,文学也力图完成自己的使命:以文学形式捕捉和传达时代的深刻转变,预示未来,“俄罗斯民族更善于通过文学来传达其世界感受和各种观点”(郑永旺,2015∶6)。白银时代生态文学中,自然抒情诗无论是浪漫主义风格、现实主义风格还是现代主义风格,于诗文间描绘自然之秀丽,于秀丽间洋溢爱国之情怀。同时,开发自然也使对大自然情有独钟的俄罗斯人民纠结于社会发展和保护自然之间,因此,反映生态危机的作品充满了痛惜、忧虑和无奈。但是人们将自然生态危机的解决依托于科技改进和社会管理的日臻完善,甚至提出终止文明进程,结果收效不尽人意,甚至是缘木求鱼。自然生态危机的症结究竟何在?生态解困需要思维转向。
对道德的精神探索是俄罗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俄罗斯文学中,俄罗斯人的道德和精神经常被放在对自然的态度中去考量。人自诩是高于一切的宇宙主宰,恃强凌弱,然而冷酷换来的是悲剧。陈望衡提出人类的强势具有局限性,“人是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人的生存发展不能不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甚至决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不是无限性的、绝对的,相比于自然自身的生态平衡功能,人还只能处于被限制、被决定的地位”(陈望衡,2011∶124)。爱普施泰因以叶赛宁自然诗为例强调了万物相互依存关系:“在叶赛宁诗歌中自然万物不是独立存在的,而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如天空之于大地、无机物之于有机物、自然之于人类,乌云能带走人的忧郁,人的双眸里存有晴空闪电”(Эпштейн М.Н., 2007∶120)。人与自然万物不仅是依存关系,而且是平等关系,无所谓主体或双主体,“在布宁的‘生态生存观’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谁为主体’抑或‘双位主体’的关系,而是在人的实际存在中紧密结缘成一个整体:自然作为人实际生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包含在人生存的此在之中,而非此在之外”(叶琳,2012∶116)。
平等和谐的生态意识的树立是生态文化建设内容之一,雅尼茨基(Яницкий О.Н.)提出“生态文化”的概念:“某一个社会主体(个体、群体、团体)与周围环境(区域环境、国际环境、全球环境)的整体关系”(Яницкий О.Н., 2005∶136),所以生态文学的文化使命可以归为“平等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生态意识的树立。我国学者鲁枢元认为,“精神在现象之上的超越将取代精神在物欲之中的沉沦,精神的进化将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鲁枢元,2011∶10),挖掘自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精神根源,树立平等和谐的生态意识,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精神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在。
[1] Афанасьев А.Н. 1995. Поэ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славян на природу[M]. В трёх томах.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
[2] Лаврентьев М.И. 2007. Эколог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N]. ЛГ., 2007-10-24.
[3] Лесков Л.B. 1998. Циолковский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я[J]. Земля и вселеннaя,(4):62-67.
[4] Эпштейн М.Н. 2007. Стихи и стихии. Природа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ХVIII-ХХ вв.[M]. Самар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Бахрах-М».
[5] Яницкий О.Н. 2005.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а[J].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136-161.
[6] 陈少红. 2013. 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判[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7] 陈望衡. 2011. 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A]. 党圣元 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2006a. 谷羽 王亚民等译.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三卷)[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9] 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2006b. 谷羽 王亚民等译.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四卷)[M].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0] 高建华. 2012.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库普林小说[J].俄罗斯文艺,(1)∶91-96.
[11] 管子. 2010. 李山译注. 管子[M]. 北京:中华书局.
[12] 赫拉利. 2014. 林俊宏译.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 北京:中信出版社.
[13] 库普林.1981. 蓝英年译. 库普林选集第一卷·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4] 库普林. 1987. 杨骅等译.萍水相逢的人·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5] 刘文飞. 2006.“道德的”生态文学——序《俄罗斯生态文学论》[J].俄罗斯文艺,(3)∶116-118.
[16] 利奥波德. 2011. 郭丹妮译. 沙乡年鉴[M].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7] 鲁枢元. 2011. 地球“精神圈”与生态内源调节机制[A].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C]. 上海:学林出版社.
[18] 王诺. 2011.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王诺. 2013.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 许贤绪. 1997. 20世纪俄罗斯诗歌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1] 叶琳. 2012. 布宁创作的生态诗学特征[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2] 郑体武. 1996. 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3] 郑永旺. 2015. 论俄罗斯文学的思想维度与文化使命[J].东北亚外语研究,(1)∶2-7.
[24] 周立新. 2012. 流淌的心声 哲思的殿堂:俄罗斯19-20世纪初浪漫主义抒情诗情感诠释与评论[M].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5] 周湘鲁. 2009. 俄罗斯生态文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
Research on Creative Thoughts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Silver Age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 upsurge of Russian ecological literature is an eхtens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theme “man and nature”. Looking back upon classics, we f nd that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Russian Silver Age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and its ecological thoughts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emotion, the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consciousness and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 ecology. To go deeper,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harmonious coeхistence”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crisis of spiritual ecology are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key that can justify the valu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eхis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The Silver Age, ecological thoughts, ecological ethics, spiritual ecology
I106
A
2095-4948(2016)04-0016-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13&ZD126)的阶段性成果。
赵雪华,女,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