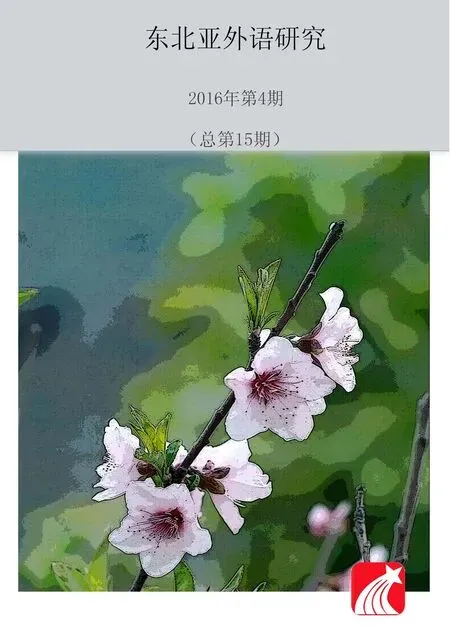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宋羽竹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宋羽竹1
(黑龙江大学 俄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拉斯普京被誉为“俄罗斯社会的良心”,他在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通过自然与女性的悲剧呈现出俄罗斯自然生态与道德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世界图景。将自然与女性置于“他者”地位的行为,剥夺了二者作为主体的话语权,实质上是违背二者自然本性的表现。拉斯普京在这部作品中对于社会弊端的诸多探讨体现了他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同时也契合了“道法自然”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即道不违自然,尊重万物之本性的主体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道法自然;拉斯普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
拉斯普京(Валентин Григориевич Распутин, 1937-2015年)是俄罗斯“乡村散文”的代表作家,女性主人公常常用来表现作家独特的审美趣味,她们勤劳、朴实、善良、亲近自然,大多来自景色优美的西伯利亚家园,同时也从这里汲取精神力量。自然是拉斯普京笔下的另一位重要主人公,具有独立的生命、灵魂和意志,是能够给予人类驱动力的角色。然而,这两位具有主体性质的主人公往往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中沦为 “他者”,作家针对生态破坏和道德沦丧的探讨体现出反对压迫女性与破坏自然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进而引发我们对道法自然的思考,即道不违自然,遵循和顺应万物本身的法则。
“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ecofeminism,又译作“生态女权主义”)这一术语“首先出现于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发表于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金莉,2006∶475)。德奥博纳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下人类的生存秩序:“人类将最终被视为人,而不是首先是男人或女人。一个更接近于女性的地球将变得对于所有人都更加郁郁葱葱。”(转自金莉,2006∶475)“生态”与“女性”两个概念分别指涉物质世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社会”。生态(eco-)源于希腊语最初用来指“栖息地、房屋、住所、家园”,换言之,生态不等于自然,而是指生物体在自然界中栖息的状态,其对应主体是生物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人类对自然不断“征服”的历史,人类误将自身作为自然的主体,进而走进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女性”是社会中相对“男性”而言的性别概念,然而在社会发展史中,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和地位。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存在诸多分支,其界限也不尽分明,但是“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郑湘萍,2005∶45),注重女性主体地位的观点是更具合理性和价值性的。根据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自然与女性之间存在天然的亲缘,对自然的破坏和对女性的压迫有直接联系,人类应致力于充分发挥男性和女性的才能,保持生态的完整性。拉斯普京既不是生物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同时也没有明确地针对生态女性主义发表过见解与著作,但他的作品(如《告别马焦拉》、《农家木屋》、《火灾》等),尤其是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Дочь Ивана, Мать Ивана»,2004年),蕴含着复杂的生态观和女性观,二者通过各自的“他者”地位和俄罗斯的社会弊端相联系,引发我们对工业发展出路的思考。如果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引入这部作品的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考量,那么回归自然与女性本性的探讨将是作家奉献给俄罗斯道德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自然与女性
(一)自然与女性——俄罗斯文化的代言者
在生物学上,女性的各项体征较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作家苏珊·格雷芬(Susan Griffin)用诗意的语言诠释了这一现象:“女人与大自然共语……她能聆听来自地球深处的心声……微风在她耳畔吹拂,树叶向她喃喃低语。”(转自纳什,2005∶168)女性与月球、地球上水文系统相关联,月亮的盈亏周期为30天,女性的生理变化周期约为30天,地球上水文系统的潮汐也随着月亮的盈亏变化在30天内分为大潮小潮,此外,女性的子宫在孕育生命的时期也有月亮盈亏的规律性,但这种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的观点难逃集体无意识的羁绊。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一部潜藏着俄罗斯文化渊源的文学文本,其中的自然与女性除了存在天然的联系之外,还被俄罗斯的历史、宗教等文化语境赋予了独特俄罗斯文化身份,因此,对俄罗斯文化的认知是确定拉斯普京生态女性主义观点的前逻辑。
古罗斯早期多神教的保护神均为女性,弗拉基米尔万神殿供奉了与农业相关的女神玛卡什(макошь),在一些童话中常常显示出比雷神庇隆更加尊贵的地位,“这是因为макошь中的ма与俄文中的мать有关”(郑永旺,2009∶75)。将女性与大地比同,将母亲的乳汁与雨水比同,不仅是俄罗斯宗教神话话语,更是其民族文化的共识。俄罗斯民族将大地视为万物之母,是世间万物的支撑,古罗斯时期就有“润泽的大地母亲”的说法,人类在大地上耕种,就像是在母亲的胸怀上留下伤口,大地母亲通过受难来延续人类的生命。因此,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下,女性是易于与自然力沟通的形象,这在最早的史诗范本《伊戈尔远征记》中就有据可考:雅罗斯拉夫娜在丈夫伊戈尔大公被俘后,向风、海、太阳等哭诉,最终伊戈尔大公在波洛夫人和大自然的助力下返回祖国。她能够与超自然力沟通,从而在宗教以及社会道德层面成为救赎主体力量的象征。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999∶12)指出:“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是女性的宗教信仰……这与其说是基督的宗教,倒不如说是圣母的宗教,大地母亲的宗教,照亮肉体生活的女神的宗教。”这恰恰是俄罗斯文化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契合之处。拉斯普京笔下的女性在性格、洞察力以及社会功用方面与自然一脉相承,如《农家木屋》中的阿加菲娅将故土视作精神的良药;《告别马焦拉》中的达利亚老奶奶,她对乡土感情亲厚,反对毁掉生活的根,“Матёра(马焦拉)”一词的词源也恰恰与“мать(母亲)”,“течь(水流)”紧密相关;《活着,可要记住》使我们记住了为成全丈夫而饱受困苦的纳斯焦娜,正如俄罗斯学者利亚波夫所言:“俄罗斯因妇女而强大”(转自谢春艳:2008∶157)。在俄罗斯文化的关照下,自然与女性的深厚渊源便不难理解。《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的塔玛拉是与自然十分亲近的女性形象,塔玛拉在安加拉河畔度过了自己单纯、快乐的童年,这里塑造了一个像修女一样的她,善良、勤恳、顺从、坚强、善于忍耐,故乡的气息不仅流淌在安加拉河里,更渗透了她的身体,流淌在她的血液里。她了解自然,儿时在安加拉河畔的塔玛拉“甚至能分辨出所喝泉水的不同气味”(拉斯普京,2005∶20),就像婴儿可以通过乳汁的气味认出母亲,她与自然有着难舍难分的亲缘关系。后来她来到城市工作,但她更喜欢每天在路上的晨昏和自然的气息,这使她觉得自由轻松,“在疲乏的身体内总是涌出一种独特的,宁静而敏锐的对生活的热爱,它洞察一切,回应一切”(拉斯普京,2005∶18)。为了保护精神和肉体上饱受摧残的女儿,她杀死了检察官,虽然这逃脱不了良心的责问和牢狱之灾,但她却在用大地母亲般的受难捍卫家庭。
对自然力量的崇拜是古斯拉夫多神教信仰的核心。水是生命之源,是支撑大地的基础,因此是受特别敬仰的自然力量。此外,水因其滋养万物的功效又被赋予超自然的能力,在丰收、祭祀等仪式上,人们借以水清洁自身,除魔去病的功能,对圣水顶礼膜拜,沐浴洁身。弗拉基米尔率臣民于公元988年接受了东正教信仰,在第聂伯河进行受洗。安加拉河由贝加尔湖流出,它们是这片沃土上植物、动物、等一切生命的源泉,有民间传说称“安加拉河是贝加尔湖嫁出去的女儿”,成为西伯利亚这片沃土的母亲河。这些文化记忆都证明了,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中,自然之水具有滋养万物,洁身除魔,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持的功能。文学文本《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塔玛拉的父亲说:“我们都到河里去喝水……没有河流,没有我们的安加拉,谁都活不了。”(拉斯普京,2005∶50)在塔玛拉童年的记忆里,“他们是靠森林和安加拉河养活的”(拉斯普京,2005∶33),面对女儿被强奸失贞的悲剧,“在寻找赖以自救的坚强的过程中,塔玛拉·伊万诺夫娜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安加拉河边的家乡”(拉斯普京,2005∶48)。无论是西伯利亚的土地,还是贝加尔湖、安加拉河,都作为生态的主体具有非人类赋予的力量,人不是生态圈中唯一的主体,大自然也不应当是人类活动的默默承受者而忍受着人类活动所带来的诸多痛苦,它应该是物质和精神力量的输出者。在繁衍生命、为人类提供精神支持方面,自然更不是人类的附庸,而是在生态系统中与人类同样具有主体地位的客观存在。
相对于自然在生态圈中的主体地位,女性在社会圈中也应当与男性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因为女性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能力、主体价值的认知是女性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塔玛拉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形象,首先,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有自觉的意识:“令她激动不安的是潜藏在她体内的女性奥秘,但不是生理上的奥秘……而是另一种奥秘,那是看不见的,深层的,比生理上的感觉更加明显,被一种特殊灵性所点燃——有时它是静静的,沉寂的,微微颤动着,轻柔地触摸着胸部,有时它突然振奋起来,让原本平常的胸部发胀,让人激动得踮起脚尖。”(拉斯普京,2005∶45)潜藏于她体内的力量实质上是女性使人类文明日臻完善的愿望,是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其次,她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潜藏于她身体的力量“并非欲望,而是纯洁的被召唤的激情,令她整个人冲动而急切地想去完成给人带来幸福的功勋……她具有这种敏感的特质,这种自我参悟力”(拉斯普京,2005∶45),她具有敏锐的直觉,同时又有对于人类社会的使命感,具有东正教的圣母情结,因为,在东正教中,圣母是替人类向上帝说情的人,“她为世界的罪孽而伤痛,以自己的祈求庇护世界,在基督的最后审判中,她祈求圣子对世界的宽恕。她把自然世界神圣化,自然世界在圣母之中和通过圣母而走向自己的神圣改造”(布尔加科夫,2001∶146-147),塔玛拉将人类的福祉作为想要建立的功勋,具有大地母亲的品格,她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社会主体所应当具有的能力和价值:对人类的意义是比耶稣基督更亲近的保护者形象,希望投入到拯救人类于苦难、为社会谋求福祉的事业中。
俄罗斯文化中具有与生态女性主义契合的文化印记,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对自然与女性的叙写证明了二者作为主体在生态圈与社会圈的重要价值和救赎作用,这既是该文本的独特品格,同样也是作家的美学诉求。
(二)自然与女性——工业文明中的“他者”形象
“他者”是相对于主体性“自我”而言的哲学概念,人类将自身视作自然界中的主体,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排序:“人类就优于动物,文明就优于自然。”(金莉,2006∶479)将自然置于“他者”的地位,这必然使自然在人类手中失去独立的主体性,造成人类与自然界截然对立的局面,遁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和自然的境遇相似,伦理道德观极力推崇女性对男权的顺从,将她们变成男性的一部分或者附属品,剥夺她们的话语权,使她们处于“他者”的弱势地位。在《圣经》中,夏娃究其根源不是独立的,她本为取自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以此维护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时至今日,性别歧视依然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问题,女性像自然资源一样被开发,自然像女性一样对男权俯首帖耳。“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略等同于男性对女性肉体的侵略,这是许多参与这场运动①的女性的共识”(金莉,2006∶477),而在俄罗斯东正教话语中有对其逆命题的共识,即对女性肉体的侵犯等同于对自然母亲的侵害,这是俄罗斯文化在东正教神话视域下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补充。而事实上人类是生态主体的一员,女性与男性同为人类文明的主体。在《火灾》中,树木被砍伐殆尽,自然呈现出一片凋敝,最终迎来了自然对人类的“末日审判”;在《活着,可要记住》中,纳斯焦娜因未能怀孕而备受婆家和丈夫的欺侮,最终为掩盖丈夫逃兵的身份,带着腹中的孩子投河自尽;在《告别马焦拉》中,有着百年历史的小岛因水电站的兴建而沉没,“树神”的形象昭示了拉斯普京对自然“他者”地位的反对。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生态女性主义意识通过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地位体现得更为清晰。
塔玛拉童年的安加拉河奔流不息,“不断带走旧的生活,不断带来新的命运,在河水奔流不息的岁月,它讲述了那么让人惊讶的宝石的故事。现在一切都在沉入河底,陷入淤泥”(拉斯普京,2005∶49)。由于水电站的兴建,安加拉河流域的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许多村庄和土地被淹没,塔玛拉和弟弟作为年轻一代,离开了安家河畔的家园,进入城市生活,因为安加拉河不再奔流不息,这里已难以承载原住民们的生计。“被布拉茨克水电站拦截的安加拉河水的汹涌之势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展宽的河岸变得荒芜而稀松,沙子被水藻覆盖,本地鱼种——茴鱼和细鳞鱼灭绝了……安加拉河不再奔涌向前,它变老了”(拉斯普京,2005∶33)。随着安加拉河的老去,意味着照此下去,它在人们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过程中,终将成为“死水”,失去滋养万物、荡涤灵魂的能力。工业文明生产机器的同时创造了武器,因为恶性竞逐滋生了战争。二战后的俄罗斯女性远远多于男性,战争夺去了许多男性的生命,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生存成本。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这武器瞄准的正是人类文明自己。塔玛拉父亲的两支枪,是从安加拉河那边带过来的,曾经,在安加拉河畔,枪支是用来保护森林资源,从自然中汲取必要生产生活资料的工具,没有威胁生态和文明的秩序;可是后来,枪支变成了挑起战争,危及人类生命的武器。塔玛拉父亲的两支枪都对人开了火:一支塔玛拉的弟弟尼古拉用来自杀,想要结束离开安加拉河畔后不幸的生活;另一支,塔玛拉用它了结了检察官的性命,也造成了自己四年半的牢狱之灾。没有人能够在自然和女性沦为“他者”的灾难中幸免于难,老伊万不安的内心,丈夫阿纳托利捉襟见肘的生活,女儿斯韦特卡不幸的婚姻和神经质的性格,都着实为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如果被置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与女性失去主体性,那么失衡的人类文明终将因无法荡涤的罪恶拖垮发展的脚步。
但是,生态破坏和道德沦丧并不是拉斯普京末世图景的完结,塔玛拉面对女儿被强奸却求告无门的困境,一反俄罗斯妇女忍耐的常态,开枪杀死了检察官,对自然与女性的侵害已经不仅表现为对她们主体性的消解,更表现为二者主观能动性的异化,滋生了反噬人类文明发展的恶的力量。
二、“道法自然”的生态女性主义秩序
拉斯普京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表达了反对压迫自然与女性的题旨,提倡建立尊重万物本性的秩序,实质上这体现了老子“道法自然”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是拉斯普京的作品在中国十分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将自然与女性从“他者”困境中释放出来的有效出口,契合生态女性主义的诉求。
老子《道德经》上篇第二十五章记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和“自然”是理解其中哲学思想内涵的关键。老子的“道”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以为天地万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总原理,此总原理名之曰道。”(冯友兰,2000∶135)“道”是适应万物自身变化却不强加控制的“秩序”②,是万物共生、和谐统一的保证者,“是形而上的最高实体”(王中江,2010∶44)。《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③在西方的文化认知中,“神”也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这个抽象的方圆之中,虽然没有人真正见过上帝或聆听到神的教诲,人们却竭力按照上帝的旨意规行矩步。因此,中国的“道”与西方的“神”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下可以被阐释为形而上的最高实体,是“秩序”的化身。“自然”并非生态中的自然。曾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其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自然如此”,但是,结合句法结构来分析,未免不通。根据前三个短句的动宾结构,“道法自然”中的“法”就丢失了“效法”的语义。在中国古代汉语中,“自”可以阐释为“自身”,也就是某一主体本身,“然”意为“如此”,“自然”即强调某一主体本身的属性,因此,“自然”是指主体的本性,那么,“法自然”就是效法主体的本性。但是,“道”相对于“人”、“地”、“天”已是穷极的概念,难道还有什么主体的本性是需要“道”去效法的吗?魏晋时期的哲学家王弼(2011∶66)对“法”做了如下注释:“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既然“道”作为终极概念已没有什么可以让它效法,那么,王弼“不违”的释义更为合理,因此,综合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法自然”意为“不违主体的本性”。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哲学视域下的“道法自然”真正的内涵在于“道”作为形而上的尺度,使万物和谐共生,不违其本性。
我们能够在拉斯普京的作品《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窥视到与“道法自然”契合的思想及话语:人类所有活动都应当在“道”这种形而上最高实体的关照下遵循万物本身的规律。
一方面,破坏自然④与压迫女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表现,其后果是造成生态破坏和道德沦丧的灾难。拉斯普京已经在创作历程中用《告别马焦拉》等作品警示人们,不顾安加拉河畔的生态而修建水电站是违背自然法则和破坏民族内核的行为。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他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安加拉河停止了奔流不息,“在城里的住家拧开水龙头,那因久置而变陈的冲力十足的水流,犹如找不到出口的困兽,从地狱般的水管中喷涌而出时……哪里有什么镜子?哪里有什么保护、救治?!……身体的病来自食品和水”(拉斯普京,2005∶50),在到处充斥着对大自然利用的城市里,自然之水被积蓄、存储,人们因“死水”的不洁患上身体的疾病,也患上了对大自然甚至对人类自身不择手段的道德上的疾病。女主人公塔玛拉是承担道德沦丧所造成悲剧的核心,她的性格和在城市中的遭遇使她具有参与雄性竞争的男性气质,呈现出“双性同体”的特征,这种特征本身就是违背女性自然本性的质素。首先,在外貌方面,塔玛拉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是稍显逊色的,“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端肩膀,小腿强健,最好能再长一点”(拉斯普京,2005∶15),她不够高挑,也不丰腴,缺乏女性的魅力;第二,在性格方面,她似男性般豪爽,与父亲的亲近使她在少女时代就学会使用步枪,修理和驾驶汽车等男人做的活计;第三,在家庭中,作为妻子的她比丈夫更有威信,作为母亲的她没有教会女儿保护自己的贞洁,而是在女儿被强奸后以杀人的极端方式保护女儿,寻求公平;第四,在工作中,她喜欢当司机,开货车,然而这个职业氛围已经使除了她之外的两个女性一个没有丈夫,一个具有剽悍的男风,这种非女性的工作岗位会使其逐渐丢失自己的女性本质。塔玛拉的双性同体特征实质上是女性本性的消解和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的压制,是不符合女性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则的。而纵观整部作品,造成种种灾难的根源就是破坏自然与压迫女性的反其“道”行为。
另一方面,人们所有的活动都应当不违其“道”,建立尊重自然与女性的生态女性主义秩序才是追寻和谐共生的出口。在全书的悲剧中,两位伊万在尊重自然和女性的道路上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得以善终。塔玛拉的父亲老伊万认为,敬畏自然、在西伯利亚乡村和谐地栖息是上帝的旨意,是一种神谕,他一生都以这种形而上的信念约束自己的行为,正如他说:“我们都到河里去喝水……没有河流,没有我们的安加拉,谁都活不了。而所有河流都是从上帝眼前流过的。他注视着它们,从里面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从镜子里看一样”(拉斯普京,2005∶50)。老伊万自始至终不愿离开安加拉河畔的故乡,因为在这里人与大自然之间是共生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这种“道法自然”的和谐应当对心存道德感的人们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塔玛拉的儿子小伊万正是由于这种吸引力的召唤,在水文气象站工作,后入伍服役,“他常常梦见贝加尔湖……戴着白色羊羔皮帽子的雄伟的山岭像军人一样守卫在贝加尔湖流向安加拉河的出口处”(拉斯普京,2005∶233-234),在小伊万的梦境中,贝加尔湖和安加拉河恢复了往日的波光与活力。同时,梦境与其说是上帝和神的指引,不如说是不违万物本性的“道”的智慧的指引,在其驱动下,小伊万跟随木工队到老伊万和塔玛拉那安加拉河畔的故乡修教堂,在他心里“这条通向母亲和外祖父家乡的路,对他绝不是偶然的”(拉斯普京,2005∶234),是遵循客观规律行事的必然。教堂是当地居民做礼拜、与上帝沟通的场所,安加拉河畔的家园在荒废已久之后重新被修葺,证明确有一些如小伊万一样的青年后代们开始回归家园,迈出敬畏自然的一步。最后,拉斯普京指出了解决当下自然与女性问题的出路,即在客观规律以及道德准则的关照下,希望恢复自然与女性的本性,从而释放二者对人类文明积极的主观能动作用,建立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秩序,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文末,塔玛拉刑满出狱,路上她感受到“从小河和不远处的安加拉河那边吹来凉爽的风”(拉斯普京,2005∶243),这来自安加拉河的宜人之感正是源自小伊万一行人重建家园的力量。塔玛拉回到家后,丈夫阿纳托利笨拙而短暂地拥抱了她,虽然重逢场景的温馨程度差强人意,但与曾经冷漠的家庭气氛相比,这一下拥抱已经是丈夫作为男性关爱女性、追求两性和谐的改变。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自然与女性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弥撒亚,是维持生态圈和社会圈平衡的重要砝码。“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是俄罗斯社会基本家庭单位的缩影,也是西伯利亚地区三代人的缩影,更是人与生态关系的缩影,两性关系的缩影。作家由此“点”及俄罗斯社会的“面”,指出“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遵循事情自己的分寸”(拉斯普京,2005∶34),建立一种在客观法则范围内规行矩步、不违世界万物之本性的生态女性主义秩序。
三、结语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这一标题的灵感源自作家与一位好友玛格丽特·伊万诺夫娜·尼古拉耶娃(Маргарита Ивановна Николаева)的书信:“不要对命运心生怨怼,我这个‘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也同样是命途多舛。”(Э. Русаков,2013)其中自然与女性悲剧的根源是二者主体意识消解造成的客观世界失衡,生态女性主义倡导释放生态圈和社会圈中两个重要主体——自然与女性——的本性,使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平衡和推动作用,进而体现了“道法自然”之不违本性的哲学内涵。这一题旨是拉斯普京希望建立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和谐共荣关系的愿望的有利契机,同时也指出了寻求工业文明发展的真正出路在于尊重自然与女性,建立平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正如拉斯普京“致中国读者”时所言:“用大自然之美和人的灵魂之美,用睿智而深刻的语言,用热爱自己土地和自己传统的榜样来教育……恶是强大的,但爱和美更强大。”⑤
注释:
① 这场运动指20世纪后半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运动。
② 老子学说推崇“无为而治”,这里的“秩序”并非是人类社会规范的条框,而是指万物发生、变化所因循的自然规律。
③ 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
④ 拉斯普京作品中作为描写对象的“自然”是指大自然的自然,下文同。
⑤ 参见由石南征于2005年翻译出版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致中国读者”这部分的第三页。(瓦·拉斯普京. 2005.石南征译.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 Русаков Э. 2013. Задача писателя - помочь человеку, сделать его добрее[OL]. 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рабочий∶ http∶//regnum.ru/ news/292070.html, 2016-2-25.
[2] 别尔嘉耶夫. 1999. 陆肇明 东方珏译. 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3] 布尔加科夫. 2001. 徐凤林译. 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
[4] 冯友兰. 2000. 中国哲学史(上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 瓦·拉斯普京. 2005. 石南征译. 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6] 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 2005. 杨通进译. 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M]. 青岛:青岛出版社.
[7] 王中江. 2010. 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J].哲学研究,(8)∶37-47.
[8] 王弼. 2011.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中华书局.
[9] 谢春燕. 2008. 美拯救世界:俄罗斯文学中的圣徒式女性形象[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金莉.2006. 生态女权主义[A].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 郑湘萍. 2005.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39-45.
[12] 郑永旺. 2009. 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看俄罗斯思想的文学之维[J]. 俄罗斯文艺,(1)∶72-78.
Research on Novella Ivan’s Daughter, Ivan’s Mo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Rasputin, known as the “Conscience of Russian society”, gave a vision of Russian world, whose natural ecology and morality had been severely damaged in his last novella, Ivan’s Daughter, Ivan’s Mother, by depicting the tragedy of nature and women. The practice of placing nature and women in the “other” status deprives their discourse right. In essence, it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two. The revelation of social ills in his work ref ects his consciousness of ecofeminism. This also goes with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 “Tao Emulates What Is Spontaneously So”, which refers to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on earth.
Eco-feminism; Tao Emulates What Is Spontaneously So; Rasputin; Ivan’s Daughter; Ivan’s Mother
I106
A
2095-4948(2016)04-0022-0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研究”(13&ZD126)的阶段性成果。
宋羽竹,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