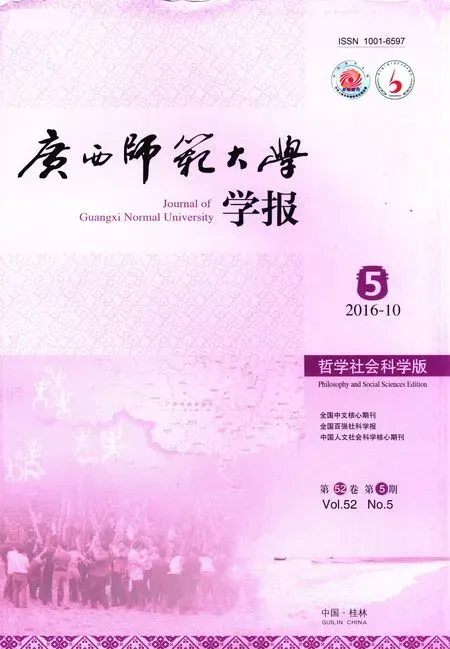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消极影响
吴全兰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消极影响
吴全兰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封建统治,对延缓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起了重要作用。但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在历史上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使专制统治合理化、合法化,使权力神圣化;使等级秩序强化和平等意识弱化;使作为学术思想的儒学庸俗化、功利化、神学化;使儒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削弱;开启了容忍和欣赏虚伪的社会风气。
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专制统治;等级秩序
西汉时形成的以儒学为主、通过对各家各派思想进行综合创新而形成的意识形态[1],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影响。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封建统治,对延缓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它的积极作用笔者已撰文论述[2],下文主要论述其消极影响。
一、使专制统治合理化、合法化,使权力神圣化
意识形态化的儒学极力宣扬“君权天授”思想,论证君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认为反抗君权是反抗“天命”。《春秋》一书是孔子编撰的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其中有不少关于天象变化的记录,为后人观察、解释、借鉴天象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经验,因此董仲舒主张后世解释各种自然灾异都要以《春秋》为根据。他运用阴阳五行学说阐释《春秋》,总结其中关于天灾与人事关系的记载,建构“天人感应”思想,“君权天授”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源,人亦由天所生:“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且“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天命”、“天志”、“天意”是存在的。不仅人是上天的产物,而且君权也是上天所授。“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君王受命于天,秉承天意行使权力、管理社会、教化民众、统治天下。因此君主在人间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臣民都应服从君主的统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君主统治天下是上天的安排,那么君主的权威自然是神圣的,君主的专制统治自然也是合理、合法的。这一思想为皇权的神圣性和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天命”成为禁止人们反抗专制统治的借口,大大削弱了人们的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
“君权天授”思想使世俗权力神圣化,既然权力是上天赋予的,那么人们对之只能敬畏、服从而不能反抗。结果权力成为人们崇拜、敬畏和服从的对象,而各级官吏是权力的拥有着,因而民众对权力的敬畏和服从又进一步演化为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的目标是入仕,认为只有当官,拥有权力,光宗耀祖,人生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也才是成功的。人们把当官作为求学的目的,甚至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以官级的高低来评价人生成就的大小,拥有权力成为最高的荣耀。这一观念从古至今已经深深渗入整个社会,植入社会成员的内心深处,流弊之大,至今难以消除。对权力的崇拜和服从也导致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很多官吏一味地敬畏、巴结、奉承上级,却很少考虑平民百姓的感受和利益。平民百姓因敬畏、崇拜权力而对官员阿谀奉承、奴颜婢膝,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二、使等级秩序强化和平等意识弱化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等级社会,人们认为区分等级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家们还从天道中寻求划分尊卑贵贱的依据,如《易传·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左传·昭公七年》亦有言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等级思想非常明显。维系这一社会等级秩序的是“礼”。“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神灵的仪式,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宗法等级制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和相应的礼节仪式。“礼”在很大程度上用以区别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等关系,“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统治者用“礼”来规定等级,并制定出不同等级所应遵循的礼节,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礼”贯穿着“亲亲”、“尊尊”、“长长”等原则。“亲亲”即爱亲人,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对血缘亲疏远近不同的亲属实施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爱;“尊尊”,即尊敬尊者,尊敬地位比自己尊贵的人,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下级尊重和服从上级,君臣、上下、贵贱都根据各自的身份和地位各司其职,不能越级;“长长”即小辈必须敬重长辈。“亲亲”、“尊尊”、“长长”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遵守“礼”所规定的行为规范和礼节仪式,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不超越自己的等级和地位,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以实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儒学在西汉被意识形态化后,儒家所推崇的“礼”成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借儒学得以强化,并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在儒学意识形态化前,中国古代社会既有等级观念,也有平等思想。强调等级是为了让人们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以维护社会秩序。先秦儒家在要求人们遵守等级秩序的同时,也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思想却被西汉意识形态化的儒学所忽略。
先秦儒家人物都有平等思想,认为君臣的关系是相对的,人臣在国君面前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孔子有“正名”思想,“正名”即事物要名实相符。齐景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即每个人做事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做国君的要像个国君,做臣子的要像个臣子,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不管什么人,处于什么地位,就要尽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孔子强调的是人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名实相符。孔子的“正名”思想包含着一种对等、平等的意识,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即君王对待臣子要符合礼的规范,臣子要以忠心侍奉君主,君臣关系是对等的。孟子说得更直接和明白: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篇下》)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反复强调,臣民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即君必须是有道之君。如果君有大过又不听劝谏,臣民可以把他赶下台;如果国君像桀纣那样残暴,臣民可以理直气壮地讨而诛之,因为暴君不配称为“君”,所以诛暴君就是杀一个普通人,即“诛一夫”,而非弑君。孟子又论“五伦”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即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妇之间,也完全是一种相对关系。
孟子还强调,交朋友不能倚仗自己年长、地位高、有兄弟,而应注重人的品德,即在品德面前人人平等。他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还强调不同等级、不同地位的人应互相尊重,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同上)这就是孟子的平等思想。
但董仲舒抛弃了先秦儒家的这种平等观念,提出了“三纲”思想。“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六纪》),后来被视为儒家的核心伦理。在《白虎通》之前,董仲舒虽然没有具体解释何为“三纲”,但已有君、父、夫贵而臣、子、妻贱之意: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 天辨在人》)
这并非先秦儒家的原意,董仲舒用阴阳家、道家、名家等学说改造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后来阳尊阴卑的不平等思想在汉代成了很普遍的观念。如西汉哀帝元寿元年正月,哀帝准备拜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帝舅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却突然发生日食。杜邺提醒哀帝曰:
臣闻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虽贱,各为其家阳;女虽贵,犹为其国阴。故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汉书·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说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阳尊阴卑,卑者随尊,并把这一观念提升到天道的高度。
在西汉,“礼”还规定卑者不能与尊者平起平坐,必须表达对尊者的尊敬,否则受到鞭打。刘向《说苑·建本》记载: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有木焉名曰桥。”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
周公制礼,首开礼教之源,而他的儿子伯禽和弟弟康叔封却未谙礼教,入见周公不懂行礼,因此几次入门都被周公鞭打。后来伯禽、康叔封得到高人指点,明白父道如高耸的桥树,子道如低俯的梓树,子弟在父兄面前应俯首谦卑。两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入见周公时,“入门而趋,登堂而跪”,表现出作子弟的谦恭,终于得到周公的慰劳。在这里,尊卑观念非常明显,周公作为父兄,是尊者,可以随意鞭打自己的子弟,子弟不敢反抗,只能有“骇色”;伯禽、康叔封明白尊卑贵贱的道理后,对周公不敢怠慢,又“趋”又“跪”,毕恭毕敬,尊者、卑者都认为理所当然。《说苑》是西汉中后期的学者刘向所编撰,上引故事亦见于汉初伏生的《尚书大传》,但刘向作了引申、补充,使这一故事所包含的尊卑等级观念更加明显。
汉以后的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地要求臣民无条件地忠君忠父,有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谬论,要求臣、子、妻绝对服从君、父、夫,已毫无平等可言。“礼”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力武器。在封建制度被推翻一百年后的今天,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某些领域,这种讲究尊卑贵贱的流弊仍难以肃清。
三、使作为学术思想的儒学庸俗化、功利化、神学化
西汉意识形态对儒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曲解了儒学的精神,扼杀了儒学的创造力,使儒学一步步地僵化。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使大部分读书人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研究儒经、弘扬儒学,结果儒学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庸俗。
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的正统哲学和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学校的教科书。学习、掌握儒家学说成为入仕的重要条件,因此只有做儒生才有机会走进仕途。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促使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争相学习儒家经典。最高学府太学以儒家“五经”为教材,以儒家思想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由于政府的推动和太学的导向,汉武帝以后民间学习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各种“经馆”、“经舍” 、“书馆”、“书舍”等私立学校开展儒学教育,并要求学生除了读五经之外,还要读《孝经》、《论语》等。西汉政府还在地方设立官学,推广儒家思想。儒家的忠孝思想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儒学变成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和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越来越功利化,失去了原始儒学的生机和活力。
汉武帝以后,很多儒生长年累月埋首经典,寻章摘句,进行繁琐的文字考证和名物训诂,并阐发微言大义。如此皓首穷经多半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和功名利禄。班固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儒者夏侯胜也曾向诸生传授经验:“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即精通儒经,获取富贵就如同俯拾地上草芥那么容易。邹鲁民间也有谚语:“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即留给儿子满箱黄金,还不如给他传授一部儒家经典,通经所能获取的富贵是“黄金满籯”所无法比拟的。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通儒家思想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社会状况。自汉武帝以后,“三公”(指辅佐天子的最高管理者。《春秋公羊传》:“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大多精通儒经,如号称邹鲁大儒的韦贤官至丞相;对鲁诗有专攻的匡衡也被元帝擢为丞相;贡禹由于精通儒经,先被征召为博士,后又升为御史大夫;薛广德也因为精通儒经而位至三公。所以《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翦伯赞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学者……把儒家哲学当做政治的敲门砖。”[3]426
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后,儒学又逐渐神学化,宣扬君权天授,神化三纲五常,失去了原始儒学的客观精神。董仲舒在前人关于“天道”、“天命”思想的基础上,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建构“天人感应”学说,开创了儒学神学化的先河。“天人感应”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帝王的权力,使帝王有所敬畏,不至于无法无天。但这一思想的恶性发展,导致了西汉末年谶纬迷信的流行。“谶”是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一种隐语、预言。“纬”与“经”相对,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一种预言。谶纬迷信的流行,使儒学进一步堕落。
思想理论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自身的生机活力就会被扼杀。西汉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在成为政治工具之后,逐渐丧失了先秦儒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变得繁琐而庸俗。到了汉末,随着专制政权的衰落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开始出现危机。但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仍然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阶级不可能抛弃儒学意识形态,而是有所损益。于是,援道入儒,用道家的自然观念来补充、改善儒家的名教思想,势在必行。
四、使儒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削弱
先秦儒家富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如郭店儒简《鲁穆公问子思》记载:“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4]85子思认为能发现并不断指出国君的缺点和错误,才算是忠臣;即忠臣并非唯唯诺诺,唯国君马首是瞻,而是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先秦儒家针对社会的不公不义,提出王道理想,强调孝悌忠恕,倡导仁政礼治,谴责暴君苛政;提倡民本,注重教化,主张改革,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社会秩序等,这些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汉武帝以后儒学意识形态化,儒学成为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很多儒生忙于寻章摘句、追逐利禄,忘记了自己作为“士”应有的社会批判精神,积极迎合统治阶层,堕落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有的儒生甚至歪曲学术,以投世俗之好,特别是投统治者所好,正如辕固生批评公孙弘说的:“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以曲学阿世!”(《史记·儒林列传》)
特别是西汉通经入仕的制度建立之后,越来越多的儒生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丧失了“士”的理想和良知,儒林风气大坏。如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宦官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奉承,欺下罔上,甚至占用田土以自肥;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依附王氏,为其党羽,生活上争田地财货,奢侈淫逸;孔光作为孔子之后,丧失儒者的正直与良知,哀帝期间善待与哀帝关系非同一般的董贤,平帝年间又唯王莽之命是从,毫无儒者的磊落之气和谏诤之风。通经入仕的制度使儒生为了保持利禄而苟合取容,曲学阿世,丧失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儒士既无权势亦无地位,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是对“道”的掌握与坚持,“道”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也是他们能够与权势抗衡的有力武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士,强调以“道” 而不是以权势和名利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士人不仅要勇于担当道义,而且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如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尽心上》) 孟子要求君王在儒士面前忘记自己的权势而仰慕儒士的道义,视之为师友而非臣下,对之致敬尽礼。
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权势高于道义,拥有道义的儒士在权势面前优势不再。如果他们不依附权势,就只能隐居、独善其身,这样可能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实现王道理想了。这就决定了儒士只能接受被权贵供养和驱使的尴尬处境。这种现象到西汉中期以后更加突出。随着专制政体的不断巩固、皇帝权力的不断强大,儒士失去了限制、引导皇权的作用,完全沦为权力的附庸,成为被帝王随用随弃的工具。《资治通鉴》载:
上(汉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云:“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资治通鉴·汉纪·世宗孝武皇帝》)
在汉武帝看来,士大夫唯一的用途就是为帝王效命,不能为帝王所用的士人无异于废物,诛杀亦不足为惜。儒家强调“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而在汉武帝眼中,士人只能算是“有用之器”,而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人,诛杀不能为帝王所用的士人就如同丢弃无用的工具,毫不足惜。士人原本自命清高,自命不凡,但在西汉专制的政治体制下,士人们都大受打击,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压抑感,很多士人都作赋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有志难伸的悲慨。如董仲舒《士不遇赋》慨叹:“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东方朔的《答客难》说战国时期因游说诸侯而加官进爵的苏秦、张仪,如果生于今世,也会像自己一样碌碌无为:“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亦感叹:“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扬雄的《解嘲》也指出士人不受重视的现实:“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和专制政体的巩固,士人发挥才干的舞台越来越小,思想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社会地位大大降低。他们的身心受到限制和压抑,只能接受并依附现有的社会制度,在现行体制中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多的儒生只能依附统治阶层,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大大削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开启了容忍和欣赏虚伪的社会风气
西汉统治者以经过改造的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应该说这种意识形态在当时符合广大民众求稳定、求发展、求和谐的愿望,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先进性,但是,为什么以这一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西汉政权最后会走向衰亡呢?
造成西汉衰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即西汉的统治阶层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上推行、遵循儒学,以儒学为指导思想,而在政策和具体做法上却违背儒家的核心价值,即仁义。正如汲黯对汉武帝的批评:“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得西汉时期为数不少的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研读儒经,名为读圣贤书,实是为了谋取利禄。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并逐渐形成容忍和欣赏虚伪的社会风气。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用儒家经典教育子民,加强道德教化,希望通过表彰忠臣、孝子,来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对忠孝仁义的过度激励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恶劣结果。过于强调忠孝、嘉奖孝廉,会诱发心术不正的人去追逐表面的道德声誉,并通过道德“造假”来骗取功名。这助长了社会的虚伪风气,破坏了社会的道德秩序,违反了道德的本意,使社会风气变得虚伪和矫情。过度提倡仁义忠孝,反而导致伪善横行。
关于西汉官场上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面目、西汉社会对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已有学者撰文揭示。[5]西汉开启了这种容忍和欣赏虚伪的社会风气之后,流弊深远。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在主张“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建议实行郡国岁举孝廉制度。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诏文中就提出“兴廉举孝”(《汉书·武帝纪》);有司奏议也说:“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可见汉武帝时已开始举孝廉。至于为什么要“举孝廉”,东汉的韦彪说:“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韦彪传》)即选举出来协助君王忧劳百姓的,一定要选对人。国家需要推举贤人,而贤人之所以是贤人,首先是有孝行,有孝行才能忠君。即提倡孝亲是为了培养忠君思想。西汉以孝廉取士,是把忠孝观念融入教育制度、道德风尚等领域,用奖励的办法促使人们行孝。这样,行孝就可以扬名、得利、封官:“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6]62因为行孝可以得官得利,所以一些人行孝的动机就不纯了,甚至为了获取名利而假行孝。这种举孝廉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但也助长了社会的虚伪风气。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指出:“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7]130可谓一针见血。但鲁迅认为历代帝王嘉奖孝廉,“从古以来,并无良效”,却说得太绝对。
孝廉可以成名,成名可以得官。有一些人为了能做官,以德行标榜,想尽办法出名,以致到东汉时,重视名节蔚然成风。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尚名节”条云:“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8]61于是,一些士人为了求得功名利禄,表面行德,口是心非,沽名钓誉,“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形成了虚伪而矛盾的价值观。一首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审举》)。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传》载,许荆的祖父许武被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许武为了让两个弟弟也成名,“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他的两个弟弟因此以“克让”之名得以举为孝廉。两个弟弟成名后,许武又将自己“理财所增,三倍于前”的财产,全部赠给两个弟弟,自己一无所留。他因此又获得广泛称誉,最终官至长乐少府。弄虚作假却可以升官加爵、名利双收,可见当时社会虚伪风气的流行。两汉以后的一两千年,这种假行德而实求名利的伪君子屡见不鲜,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虚伪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而源头正是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总之,西汉“独尊儒术”使儒学意识形态化,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西汉意识形态中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但是,儒学上升为意识形态,也使儒学被权势所利用,沦为文过饰非的工具,给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学术带来很大的流弊,值得我们反思和警省。
[1] 吴全兰.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原因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2] 吴全兰.论西汉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积极作用[J].社会科学家,2014(1).
[3] 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程念祺.西汉官场上的虚伪面目[J].人民论坛,2010(3).
[6] 吴虞.吴虞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 鲁迅. 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
[责任编辑 李长成]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U Quan-lan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ve maintained the social order to a certain extent, strengthened the feudal rule,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laying the collapse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China. However, it has also produced negative influences in history, mainly in five aspects: first, making the autocratic rule rationalized and legalized, and the power sacred; second, weakening the hierarchical 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equality; third, making Confucian thoughts as an academic school vulgar, utilitarian and theologized; fourth, weakening the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al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 fifth, starting the social atmosphere of tolerance and appreciation of hypocrisy.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ideology; autocratic rule; hierarchical order; vulgar; hypocrisy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5.011
2016-0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西汉意识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1XKS01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当代意义发掘与研究”(14MJ03)
吴全兰(1968-),女,壮族,广西上林县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
B234
A
1001-6597(2016)05-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