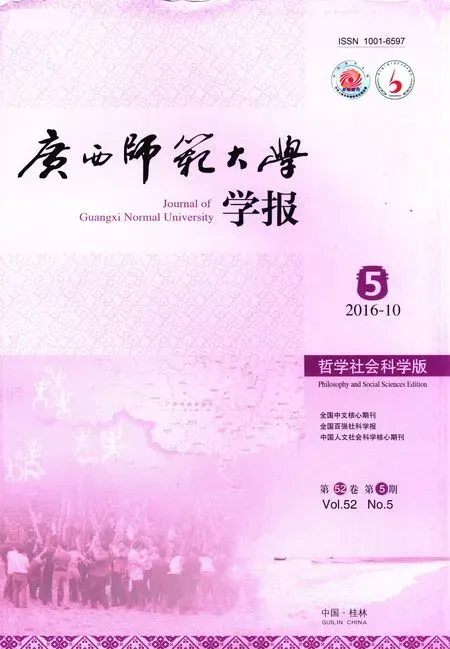论意义的定义
——兼论对自由与实践之本质的再理解
张立达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重庆401120)
论意义的定义
——兼论对自由与实践之本质的再理解
张立达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重庆401120)
对意义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通过定义才能深刻理解意义。它可以定义为人在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中建立的自我规定性。这绝非鼓吹人可以随心所欲,而是以矛盾性作为人、意义、自由和实践的本质特性,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作为解决人之生存矛盾,建立自我规定性的根本途径。这样,通过对矛盾的揭示才能深刻理解事物,并且突破哲学思辨的抽象性,敞开对现实反思和批判的空间。同时,将自我反思及批判作为人和意义的本质内涵,为人在实践中自我负责的态度奠定哲学根据。
意义;自由;实践;矛盾;自我反思
对于人而言,“意义”是最本质性的存在方式。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可以追求各种不同的目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目的,既能以德报怨,也能以怨报德,既可以苟安偷生,也可以不自由毋宁死,唯有人为赋予的意义才能为千差万别的行为提供根据。如果完全感受不到存在的意义,人将很可能发疯或自杀。因此可以说,人是唯一为了“意义”而活着的动物。
当然,这里说的“意义”只能是人的生存意义,分析哲学热衷于探讨的语词、语句的意义只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第二性的意义。人的语言活动说到底是嵌入在更广阔、更深刻的实践—生活世界的。分析哲学自身的研究重心从句法学、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变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只是这个转向不够彻底。那么,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给予意义一个严格的定义,对于更明晰地通过意义来思考人类之存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
一
但是“意义”又是最难定义的,这是一个外延极广泛、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既不是哪个大类别下的子概念,也很难说具有什么明确而具体的功能,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种加属差定义,还是功能性定义,都无法适用于它。或许与此有关,除了分析哲学在语言领域探讨意义定义之外,很少有哲学家曾给一般性的意义下过定义。不过,对于思考这种似乎无法用概念把握的存在,现象学却可以给我们重要启发,这就是悬搁起概念性的前见,让意义现象在自行展开中显示其一般形式。①*[收稿日期] 2016-02-08[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及其重构研究”(14XJC720002)[作者简介] 张立达(1978-),男,江西万安人,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① 需要说明的是,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本质上对立的两种思潮,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有去除各种遮蔽,回到事情本身的内在要求,只不过对什么是“事情本身”以及“怎样回到”的理解不同于传统现象学。现象学的核心主旨位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旨在存在论层面,因此两者核心主旨并不冲突,现象学方法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实际上马克思也已经有了人学现象学思想。国内对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见邓晓芒:《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邓晓芒:《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3期;王德峰:《论马克思哲学对现象学原则的包含与超越》,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阎孟伟:《马克思的“感性世界”理论与现象学运动》,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张艳涛:《马克思人学现象学方法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4期。然而看似吊诡的是,最关注人的生存意义问题,也恰好以现象学作为基本方法的存在主义,恰恰是反对给意义下定义的。它把通过定义来思考事物本质的方式斥为实体主义、本质主义的旧形而上学,而自居为实现了对前者超越的现代哲学。那么,对现象学这种立场的反思是本文不可回避的问题:面对现象学的挑战,给“意义”下定义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对于现象学的立场,海德格尔明确指出:“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1]41。因为只有现象的直接显现才具有自明性,而概念却是人为的经验综合、逻辑建构的产物,是间接性的存在,无法确保它在被它者中介之后不失真。尤其是非实体性的意义更具有鲜明的超概念性质,一旦对其下定义,就会使其确定化、抽象化、僵化,背离本真的现象实情。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关注的都不是意义的本质、定义,而是由人的生存体验直接显示出的实际生存意义内容。但是,现象学最容易遭到质疑的问题是:现象与本质无中介的直接统一究竟是如何可能的?揭示现象如何能达到普遍必然性而避免主观任意性?另外,对于本文探讨的“意义”而言,因为它必然包含对应然状态的自觉设定,也就需要一种超越事实性的规范性立场,那么,现象学究竟如何仅凭自身就能确保这种规范性立场,避免倒向对现实无条件辩护的虚无主义态度?
第一,我们容易看到,同样运用现象学方法,不同的哲学家所直观到的现象实情大不相同。胡塞尔从认识论角度,抓住的是意识活动的纯形式——意向性;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却从生存论角度,力图从源始的生存体验揭示生存的意义。同样从生存论角度,海德格尔直接把共在作为此在的在世结构,认为他人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需要特意揭示的问题,萨特却要通过意识到他人的注视来揭示他人的存在;对于死亡,海德格尔为其赋予了以此领悟存在的关键使命,萨特却认为死亡不过是个普通的事实,并不具备什么重要的哲学意义。这种现象学的内在分歧和冲突充分说明,现象学的无前提性乃是一个神话,每一种独特的现象学直观都离不开现象学家的价值观、兴趣、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即离不开理解的前结构。当然,现象学自己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衍生出了解释学的新形态。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前结构(成见)不但是不可消除的,而且正是实现理解的必要条件。理解的前结构限定了理解的视域,理解是与传统、与他者对话的过程,在其中可以实现视域融合,实现理解的深化和扩大。那么,理解的前结构是否真的可以像这样轻易融化于现象学、解释学的连续之流呢?同样容易看到的事实是,胡塞尔并不满意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甚至认为他转向了“人类学研究”,海德格尔则批评萨特没有摆脱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窠臼。这并不是说视域融合不可能存在,但至少上述视域不融合的现象显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无力解释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单个现象学家的直观,还是解释学家的历史性群体的共同理解,都不足以自然而然达到一种普遍真理。至于视域不融合的原因,当然直接是由于个人的价值观、兴趣等主观原因,但要追问是什么使这种主观性的差异结构化、硬化,就必然会追到概念对思维的构造上。因为只要现象学还想把握普遍性,不带理论负载的纯粹直观就是没有的,对此缺乏反思意味着哲学的失误。
第二,海德格尔等人也确实不能接受对现实无条件辩护的立场,力图使批判性奠基于现象学直观中,从实然中揭示应然。所以,《存在与时间》必须区分本真存在和非本真存在,前者是生成性的,并且是后者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后者则是现成性、给定性的。那么非本真的常人如何转变为本真能在?回答是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耐人反思之处就在这里:这一步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实际上只要“直面事情本身”就会发现,人面对死亡的感悟也有可能是及时行乐;还有可能以自欺的方式,随着自己越发衰老,就越发忌讳谈论死亡。海德格尔却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其他可能性,只是专注于阐释死亡和本真存在的本质必然联系。他在此的理论逻辑与其说是现象学,还不如说是现象学外壳包裹的辩证法:生存以死亡作为自己的内在否定环节,扬弃了自身外在的、偶然的存在形式,显示出内在必然的生存之根据。固然,现象学原则使他不得不承认有非本真的向死存在,这就是“日常沉沦着在死之前闪避”[1]297,可是马上又认定:“非本真状态以本真状态的可能性为根据”[1]298。 这正是海氏掩饰自己无力把握现实的一个遁词:因为人是自由地逃避自由,所以人是自由的,也是可能自我拯救的。这样,领悟存在、自我拯救的可能性就不是由现实的人之个体承担的,而是由抽象的人之“类”承担的。这是一种怎样的现象实情?显然这不是现实生存处境中人们的现象实情,而是抽象的、作为不是概念的概念的此在的“现象实情”。笔者认为,海氏的这个纰漏不是局部性、而是根本性的。因为现象学的立场是任现象自行显现不加干预,所以仅靠自身并没有能力打通从实然到应然的道路,进而也就难以真正克服虚无主义的危险。令人难受和不安的不一定是坏的,令人快乐的也不一定是好的,人完全可能享受沉沦而害怕勇担责任的自由,直接的生存体验并不足以说明价值论的“应当”。海德格尔要避免虚无主义的理论后果,却带来了自身理论逻辑的不融洽。再看萨特,他径直以意识的本性来论证人之自由的先验必然性、绝对性,也就是让应然(自由)直接被实然吞没,直接让实然来捍卫应然。显然较之于海德格尔,萨特在此的思考更加抽象,更明显地把意识和自由的性质单纯化,其实就是概念化,这偏离了现象学。当然,抽象的自由观会带来面对现实的困难,这也引出了萨特后来将存在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不很成功的尝试。总之,纯现象学的规范性建构已经宣告失败,如果真要另辟蹊径,从实然本身当中揭示应然,就必须立足于实然本身的辩证性、矛盾性、自否定性,那么现象学的直接性原则、非中介性原则势必会被打破。而且,为了确保辩证运动过程推演的清晰性、可靠性,避免辩证法蜕变成主观任意的“变戏法”,以明晰的概念作为辩证推演的逻辑节点也就更加必要。
综上可见,理解事物离不开概念,即使现象学也不能例外。具体而言,概念的不可取代性也有对应上文的两个方面。其一,既然明见性和普遍性往往不能直接统一,那么迂回、间接的道路是必然的。概念作为经验的普遍综合与浓缩的相对确定的形式,为认识活动的分析、综合、抽象、反思和批判提供了一个规范性的基础,从而使认识能以规范性操作迈向普遍真理。赖特指出,概念的建构是在理论和经验的双重约束下进行的。理论约束确保着概念内容的统一性、普遍性,经验约束则要求概念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这双重约束以及概念的竞争推动着概念的修正和完善化。[2]24-27虽然赖特谈的是科学概念,但是哲学不过是在不同层面解释现实,同样需要遵循客观性要求,所以哲学概念虽然是在较弱的程度上,但也仍然要受到经验约束。完全没有经验约束的概念是不可理解的。概念的明晰性足以使其成为语言交往、思想交往的公共平台,这种以普遍交往为中介向现实的开放性,正是破除概念遮蔽的利器。既然如此,只要反思性、批判性地使用概念,就不会出现现象学所担忧的后果。如果所有的叙事都以现象实情自居,排斥反思和批判的必要性,会使自身丧失通过反思和交往而得到检验、通过检验而趋近真理的可能性。
其二,概念自觉承认自身的抽象性,承认所反映之物在自身之外,显示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张力,显示了本质和存在、应然和实然的对立统一,进而蕴含了内在批判性的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辩证思想把‘是’和‘应当’之间的批判性紧张关系首先理解为存在自身结构的本体论状况。”[3]107本质既源于存在又高于存在,存在拥有某种本质是应当成为这种本质,“直言陈述因此成了绝对命令;它陈述的不是事实而是造成事实的必然性”。[3]107像婴儿、智障者、原始人都属于人的具体存在,但都不完全具备人的本质,因此婴儿需要长大成人,智障者需要康复,原始人需要进化为现代人。所以,以概念确立一个事物的本质包含了对其存在的批判,而且这是由事物自身内在地揭示的。内在批判在扬弃了现象学无中介性原则的同时拯救了它“直面事情本身”的合理内核。
二
总之,现象学擅长把握的是直接在意识领域显现的现象,对于不能充分显现于意识领域的客观事物则缺乏把握能力。不过,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之处,在于它是人实践活动的产物。一切客观事物,即使对人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制约性,也都要通过人自己的体验、理解和选择,才能使这种影响和制约具体化、现实化。所以,现象学仍然是理解人之存在的必要方法,只是不能再简单执着于意识场域内的直接现象。对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改造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改造。源始的现象实情不是意识的体验活动,而是直接投身于生存的实践活动。只有实践才能消融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的外在对立,将一切对立之物融为一个历史性生成、流变的整体,并且显示这种生成、流变的根据。其二,基于辩证法的改造。阿多诺早已指出,现象学的无中介性其实只是在意识中对现实中介性的一种抽象,“直接性总是被中介的”。[4]7因此,一种辩证的现象学不应该排斥矛盾和中介,而应立足于直接和间接的转化关系,实则是意义体验和实践处境的相互生成转化的关系,将其作为本真的现象实情。复杂的中介和矛盾因素越是具体地、如其所是地被吸纳进完整的现象之流,现象学才越能以这种迂回的,但是唯一可行的方式“直面事情本身”。
只有确立了可靠的方法论基础,探讨意义的定义才有可能。以马克思主义现象学方法揭示意义本身,而不是某种特定的意义,不能从人的在世存在或意识的显现活动出发,而只能从意义和非意义的比较,也就是人和动物(非人类)的比较出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时,正是从人和动物的比较出发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57国内学界对这一手稿多从存在论和历史观角度关注类本质和异化,却很少注意人与动物(非人类)相比较的方法论意义。首先,这显然是辩证法原理的体现,事物必须通过自身对立面来确定自身。其次,它也可以看作推至极限的胡塞尔的自由变更方法。胡塞尔指出:“自由变更作为本质直观的基础”[6]232,“一个事物的这种自由变更中,必然有一个常项作为必然的一般形式保留下来,没有这个形式,一个图像,如这个事物,作为它这一个类的例子是不可想象的”[6]233。自由变更法的意义在于让个别直接显现一般,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变更的合理范围?这其实要以对边界的预知为前提,因为边界往往并非是明显的,但是预知却是反现象学的。人与动物的比较,一方面意味人之存在的自由变更的极限状态,可以明确揭示胡塞尔想把握的“常项”;另一方面,这种做法敢于接受人与动物的分野这样一种常识观念,而不是将其悬搁,是因为它并不是认识主体个人的主观信念,而是人本身之存在的规定性,一种哪怕经过怀疑之后也会发现无可怀疑的现实性,一种即使作为意识内容也可以在生活世界中确证的实在性。这样,本质直观才能获得更现实的基础,避免胡塞尔的逻辑困难。
回到上述比较中来,显然,动物的生命同一性意味着,它的活动只能受生物本能的驱使,只能以肉体的生存和繁衍为目的;人能以自身为对象,也就意味着主我(自我意识)和客我(我的现实存在)的分化。这两个我必然是不一致的,那么我也就不会满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而是自由创造、自我超越。那么,人和动物这种区别是怎样产生的?联系人类进化史,容易看到偶然的环境变故——气候干旱化,迫使古猿下树,开辟了人猿相揖别的道路。进入一个完全陌生而不适应的新环境,人的生存之道成了一种完全不确定的东西。格伦、兰德曼、弗洛姆等人指出,存在方式的未特定化才迫使人不得不通过积极的自我创造来弥补先天不足,才得以成为人,“人在生物学上的弱点,恰是人类文化产生的条件”[7]26。 当猿人以自觉的意识打制石器,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方式包含自主决定的时候,马克思所言的“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得以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才宣告诞生。
再具体一层来看,实现这一点还必须以既不同于我又类似于我的他者为中介。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与人的差异、分歧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人才能明确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才能把自己变成反思的对象。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自主活动空间扩大,尤其是社会交往中双方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活动后果的不确定性增大。同时,随着活动越来越不局限于简单的肉体生存需要,活动也就越来越失去先天必然的根据。但是,如果任由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泛滥,人将丧失规定性,将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存,该追求什么。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它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58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不是强调实践是为了满足人具体的生存、发展需要,而是强调人要从中直观自身、证明自身。为何人还要证明自己?这是因为人之存在既缺乏先天的根据和规定性,又面对着后天的不确定性,人必须通过实践,人为建立起自我规定性,避免自身被消融于混沌的虚无。如果不是因为自我确证,人类像野兽那样活着也并无不可。人类追求各种不同的目的,说到底都是自我确证的具体方式。人的最终目的的实现方式,不是某些具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而是自我确证,确证自己是自由的类存在物。实践中的自我确证是人之存在的终极根据,是人判断事情有无意义的根本标准,也就是所谓的意义本身。具体来看,实践活动的一切具体目标都是在一定意义框架中确立的,制度、文化、道德、自我认同都是这类意义框架,都是人的自我规定的具体方式。无数意义千差万别的表现,恰恰显示了意义的一般形式,即意义的本质和定义——人在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中建立的自我规定性。
那么,意义一词的具体用法可以看作是从上述根本涵义中派生的。其具体用法有两大类,其一是指符号、语词、语句的涵义,或者是指称、用法、语言行为的效果、语义的成真条件,等等。不论意义的意思具体怎样确定,它通过表达和交往所建立的规定性毋庸置疑。同时,索绪尔的命题“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8]102已然表明了符号指称的无根据性,人类意识活动的不确定性确立语言用法及其效果的无根据性。意义的成真条件论虽看似避免了无根据性,但因此却形而上学地将成真条件封闭起来,割裂了其与实践及理解的关系,遭到达米特的激烈批判也就不奇怪了。其二,意义指事物对于人的价值、影响。价值和影响固然要通过评价而规定下来,但是,不仅事物本身是在未预定结果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而且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这同样属于上述根本涵义的一个具体表现。
由此我们得到了意义的定义。存在主义反对给意义下定义,但并没有证明自己贴近现实,反倒暴露了自己的不够深刻。意义内容的多样性并不排斥意义形式的统一性。只要这种辩证结构在概念内涵中确定下来,即使给意义下定义也并不会造成思维的僵化和抽象化,因为辩证法已经敞开了向现实开放的空间。我们的意义定义,既不是通过概念分析,也不是通过经验归纳,而是通过对人类实践—生存活动的本质直观得出的,只不过这里直观到的现象实情是已包容了中介性、矛盾性的实践活动和直接的生命体验的相互转化、相互生成。内在于实践的意义体验过程消融了从外部汇入实践的诸客观因素的外在关系,这是在扬弃中介性后,得到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直接性,相对于复杂的实践总体、社会历史总体而言的直接性。这种方法是一种辩证的现象学、实践—生存现象学,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而实现的现象学和辩证法的辩证统一。
三
这样一个关于意义的定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意义是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中的自我规定性,那岂不是人的各种作为都是有意义的?我们还能够确立什么价值标准、道德标准?这岂不会倒向虚无主义?
笔者的回答是,如果只把某种“好的”事情当作有意义的,把“坏的”事情当作没有意义的,会使我们丧失理解那些“坏事情”的可能性,无力解释它们何以在现实中存在,难以找到克服它们的途径。将意义看作人的自我规定性,绝非鼓吹随心所欲,恰恰是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和责任赋予人,将其看作人的理想本质(自由)和现实本质(实践)的本质内涵。
意义固然是人自我规定的,但之所以必须自我规定,正是因为人之存在已经超越了抽象空洞的同一律,投身于自身之外的世界中。无论人怎样自我规定,这种存在方式有不能被主观任意扭曲的客观内容,无论阿Q之流如何娴熟地运用精神胜利法,都不会改变自己实际的遭遇。寻求对自己最合理的规定方式是对自己负有的绝对责任。同时,由于没有先天根据,由于意识与客观实在绝对的非同一性,生存中必然无法完全摆脱无知和迷误状态,这与绝对责任构成永恒矛盾。既然人以自由同动物相区别,而人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又永远是有限的,那么人只能以自由的自我否定方式,即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方式,逐渐扬弃纯粹自我的主观性而不断充实、修正自我的规定性。唯此,人才得以在实践中获得生存内容的充实,进而可以历史性地克服无知、摆脱迷误,实现自身存在向类本质的趋近。
为什么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是人之存在的绝对命令?康德将绝对命令表述为:“要只按照你同时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而行动。”[9]38-39笔者认为首要的普遍法则不应该是实践哲学、道德哲学层面的,而必须是人学本体论层面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正是将人本质之“是”和本质之“应当”统一起来的普遍法则。首先在本体论层面,意识的自由意向性先验地*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的影响,我们往往习惯于把“先验”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而加以贬斥。但是,作为先于经验且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先验性存在恰恰是哲学必须探究的主题,否则它将难以同科学、常识相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不在于抛弃先验性,而在于打破先验演绎的封闭性,力求揭示先验性和经验性的相互转化、相互诠释。就人类存在而言,自由这一类本质必然具有先验性,但如果放到生物进化史这一更大范围来看,它又会转化为经验性的、历史性生成的事实。否则,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何而来,生产力发展为什么又非得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不可,都无法仅仅从经验事实中获得完满的回答。如果没有先验性的范导原则,彼此歧异但平等的经验事实将相互拆台,使得任何普遍性的理论都无法建立。决定了人不能永远满足一种固定的、有限的生存状态,唯有自我反思和批判才能使人通过实践告别动物界。没有反思,人便只能像动物一样和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屈从于自然给定的自身定在,这正是最大的不自由、最大的无创造。其次在历史观层面,人固然可以用相对于他人的优势来维系自我认同和生存意义,为避免既得利益损失全身心投入利益算计而排斥生存意义的自我批判,但是无论以康德还是马克思的标准来衡量,不平等、损人利己都不可能成为普遍规律。充斥压迫和奴役的世界里不会有最终的赢家,从这个困境摆脱出来终将成为人的必然要求。剥削阶级虽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垄断自己的剥削地位,但是人类的根本利益毕竟是自身幸福而不是迫害他者。为了自身根本利益,人类必然要发展出不依赖迫害他者就能满足自身的手段。生产力是这种根本手段。“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10]154在此基础上,生产的社会化会带来人与人利益依存度的提升。当人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尊重他者的时候,平等取代不平等,成为人实现类本质的必经之途。有平等才可能有自由,当自由获得充分的社会制度保障的时候,人不必为有限的生存目的殚精竭虑,能把自由的自我反思和意义创造作为人生目的。也就是说,与本质不相符合的存在终会被历史扬弃,此时,人的类本质——自由——便在现实中得以自我确证。
意义是人之自由和实践的自我规定形式,自由的本质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实践是自我反思和批判在客观世界中的现实化。唯有自我反思和批判才是人类解决生存矛盾、建立自我规定性的根本途径。笔者特意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自由和实践本质的理解不够深入,由此导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理解陷入了一些困境。
一种流行的传统观点把自由看作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世界的改造。这固然确保唯物主义立场,但只是把握了自由的一种外部属性,并未从自由本身揭示其本质,不能说明是什么动力推动人要去认识必然性,也不能说明改造世界的方案如何能仅仅从所认识的必然性中产生,从必然性到目的性的飞跃成了未被反思的逻辑盲点。既然目的性的根据没有得到说明,它成了非反思、非批判性的存在。以这种认识看待实践,实践隐去了精神意义的维度,仅仅表现为以工具理性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这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实践观,尊重客观规律只是为了实际的效果。对于伴随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的异化现象,它难以进行反思和批判。批判异化必须从深层反思人类整体的实践方式本身。
另一种在国内相对较新的观点,则把自由理解为不依赖于外部条件的目的性、能动性。这种理解更切近自由的本质,但如果止步于此,这种对自由的理解还是抽象的,未能深究目的性、能动性应该以何种规范形式展开。与之相应的实践观(实践本体论)借助了现象学思想,把实践看作人的根本存在方式,看作先于主客体二分的原初性、生成性、开启性的一元本体。这样的实践固然超越了狭隘功利性,但如果把它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全,如果认定“实践本身是‘不可致诘’的, 把它作为设问对象是不妥的”[11],那么会在本体论层面消解实践的内在矛盾,弱化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因为这种实践把人类生存中的矛盾当作了层次上低于自身的东西,它难以关注、反思这些矛盾。固然我们可以用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更具体的概念工具研究人的生存矛盾,但是无法破解像法兰克福学派揭露的“生产力发展同人的自由的矛盾”这类更深层次的矛盾;就算我们说最终还是要靠生产力继续发展来解决该矛盾,但这又会产生出一个“代际正义”的新问题,即当代人存在的意义是否仅仅只是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创造客观条件?当代人同后代人的利益关系究竟怎样处理?对这类不能直接由物质因素解决的生存意义问题,不但生产力概念缺乏对此反思的能力,就连实践概念也同样难以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反思框架。意义概念本身是一个矛盾性的结构,并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可以为各种具体的矛盾提供反思的框架;并且,通过对矛盾的普遍必然性、不可扬弃性的揭示,可以更好地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现实关怀。
综上可见,“实践”固然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石,但“实践”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上帝”、“理性”等的优点,乃是在于它的直接现实性、生成性和本源性,因此必须警惕抽象谈论“实践”的危险。如果不具体展开实践的内在结构、内在矛盾,实践唯物主义固有的积极意义难以充分发挥。要给实践这副骨架充实血肉,需深入挖掘实践的内在根据,意义、自由、矛盾、自我反思和批判,必须纳入本体论诠释的框架,让它们在同实践的相互解释中实现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和深化。笔者如此定义“意义”的根本意义,在于以矛盾性作为人、意义、自由和实践的本质规定性,通过对矛盾的揭示来发掘事物存在的深层根据,同时通过对矛盾运动的展开来突破哲学思辨的抽象性,敞开对现实反思和批判的空间。实践本质上乃是人在无根据性和不确定性中建立自我规定性的现实方式。它是一种矛盾,其内在根据和尺度、实践合理性的评价机制绝不可能简单给定,必须得到深入追究。由于矛盾的永恒存在,这种追究既必须突破概念思辨层面,深入具体现实,同时又必须超越具体现实,返回抽象反思层面来把捉辩证的历史总体。一个在本体论层面获得了具体丰富的规定性的实践范畴才可能转化为有能力理解、反思、批判具体社会现实的理论框架。这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足以面对具体的现实,才有力量回应现实的挑战。同时,在理论上确立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基础地位,为告别个体利益至上和小群体利益至上,为人作为社会主体、类主体而自我负责的实践态度奠定哲学根据。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赖特.阶级[M].刘磊,吕梁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4] Adorno. Against Epistemology: A Metacritique Studies i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ntinomies[M]. Trans, Willis Domingo.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7] 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8]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何中华.实践本体论若干问题再探[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责任编辑 李长成]
On the definition of significance——Pertinent to Re-comprehension on the Essence of Freedom and Praxis
ZHANG Li-da
(School of Marxism,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Seeking significance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human. Only by definition, can we gain deep understanding of significance. It can be defined as self-regulation within groundlessness and uncertainty. It means that since contradictoriness is the ultimate character of human, significance, freedom and praxis, only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can be the basic solution to resolve contradictions and gain self-regulation. Then we can understand things deeply by revealing contradictory, transcend abstract philosophy and face reality with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Furthermore, taking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as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human and significance, is to build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self-responsibility in praxis.
significance; freedom; praxis; contradiction; self-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5.009
B0-0
A
1001-6597(2016)05-00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