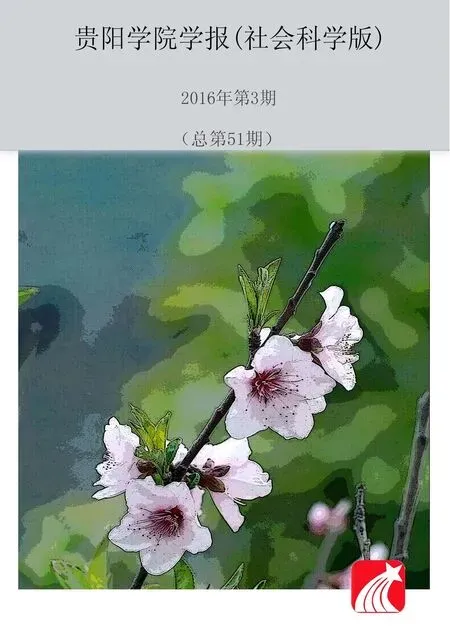合内外之道—吴澄的“知行兼赅”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
吴立群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44)
合内外之道—吴澄的“知行兼赅”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
吴立群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44)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儒家知行观以“性”与“天道”为中心论题。成圣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成圣成为知行观的关注焦点,知行问题由此而来,并因此与心性论、工夫论紧密相联。吴澄与王阳明的知行观首先从格物致知说展开。吴澄的格物致知说主要针对朱学之失而发,强调以陆学之长补朱学之失,并以内外合一为其理论前提阐发“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的观点。王阳明则明确指出,析心与理为二是朱熹错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以“心即理”观之,格物致知无内外之分。二人均以内外合一之道阐明格物致知,所见略同。关于知,吴澄以“本心之发见”为“知”,并认为知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在以“实悟为格,实践为诚”论知行关系之后,吴澄提出了“知行兼赅”的主张。王阳明则指出,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首先阐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进而提出知即行,知行合一,并以知—行—知的动态展开过程说明知行如何获得统一。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在从自在之知到自为之知,从本然之知到实然之知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在知行关系上,吴澄和王阳明均认为知行不相离,并视知行合一为动态统一的过程。
吴澄;王阳明;“知行兼赅”;“知行合一”;动态统一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对于儒家哲学而言,知行问题主要并非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而是更多地表现为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知识论),并与道德实现的根据(心性论)以及道德实现的途径(工夫论)相联系,其最终目的在于成就理想人格,完成对“道”的体认和把握,在人道与天道的贯通中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及人生意义。换言之,儒家知识论仍不离“性”与“天道”。知识论与心性论、工夫论紧密相联。
一、儒家知行观特征及宋明时期论争焦点
自《尚书》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中》)的思想以来,知行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历代儒家学者的重要论题之一。在儒家那里,“知”总是与“道”相联系(知道)。儒家的价值目标是成人,其最终目标是成圣。儒家认为,理想人格不仅表现为内在的德性,更需要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因此,成圣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成圣成为知行观的主要内容,知行问题由此而展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即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学而知之者”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对象。孔子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反对言行不一,主张“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并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等主张。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生而知之”说。孟子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又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四端”乃“仁”“义”“礼”“智”四德之端始,是天赋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能力。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孟子认为,“四端”仅为“四德”之可能,而非必然。天赋的“良知”、“良能”虽“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但须通过“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才能使其显现。在孟子那里,发现天赋的良知、良能即为“知”,亦是“行”。“知”的内容为天赋的良知、良能,“行”则是将其“扩而充之”。在孟子看来,成圣需要经历“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如其所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人的道德认知并非先验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知源于行,并最终落实到行。荀子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儒家重要典籍中,《大学》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说明了知行的统一过程。《中庸》则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环节把儒家的知行学说系统化、纲目化。《大学》、《中庸》所提出的知行观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宋代,理学家将《大学》中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之为“八条目”。“八条目”中的后七条在《大学》中都有所说明,唯有“格物”未作解释。“物”是什么?如何去“格”?后世儒者各说其是。宋儒有关知行先后、难易、轻重、分合等激烈论争亦由此而发。
程颐明确提出知难行易、知先行后,并认为能知必能行①*①程颐曾云:“须是知了方行得”,“须是识在所行之光,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故人力行,先须要知”。参见《二程遗书》卷十八【宋】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235页。。朱熹则以“知行相须”说明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生发的辩证统一过程。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至元代,许衡倡“慎思”、“践履”之“治生”之学[2];吴澄以“本心之发见”为“知”,认为知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并在以“实悟为格,实践为诚”[3]648论知行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兼赅”的主张。明初谢复首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4],王阳明则明确反对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以“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的逻辑展开,从工夫与本体,德性与知识等多个层面发前人所未发,对知行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
尽管知行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但历代儒家学者均围绕知识与德性,以及德性对行为的制约作用而展开言说。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5]就知识的内容而言,传统儒学不出“经史子集”,然究其学问宗旨,却涵盖社会与人生。儒家之“知”,既包括形而下之经世致用,更包括对形而上之“性与天道”的不懈追求。儒家治国安邦的入世态度以及以人为本的治学风格决定了儒家论“知”必与“行”相联。在回答“知”从何而来、“知”如何可能、怎样“知”、如何“行”等问题的过程中,知识论又不可避免地与心性论、工夫论交织在一起,相互阐发,相互发明。历代儒家学者正是在知识论、心性论、工夫论这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整体论域中展开论争,形成各自的知行观。其中对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分合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不仅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理论思考,也反映了历代儒者对世风时弊的现实回应。
儒家哲学在宋明时期的理论形态—理学—往往被后世学者称作“性理之学”,并理解为“希圣之学”[6]。理学家们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探讨“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本”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根本问题,对传统儒家日用伦常的“心”“性”“理”“道”等范畴重新诠释,赋予其宇宙论、本体论的意义,在精深微密,辨析毫芒的探究中建立各自的理论。宋明时期尽管学派林立,论说纷呈,但“性与天道”始终是理学的核心话题。理学将人的内在精神的规定(性)与一个外在的绝对的客观精神实体(天道)联结起来,并认为人的终极关切就是向天理的复归,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道的合一。复归天理、与天道合一亦可谓“希圣”、成圣。
论及宋明理学,不能不提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的相互诘辩和相互渗透。与此相关,朱熹与王阳明作为“理学”与“心学”的两大代表人物,始终居于理学论说的中心地位。南宋自朱熹之后,或述朱,或诤朱,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7],始终以朱熹为论说中心。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对朱熹的学术地位作了如下评价:“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8]在全祖望看来,相较同时期的江西陆象山之学、浙东叶水心之学而言,朱学更为广大精微,堪称理学之集大成者。
至明代,程朱理学的正统或曰意识形态化已基本得到实现。明中期,陈献章倡“自得之学”,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学风为之一变。此后,“理学”渐趋式微,“心学”渐兴。明清之际出现了不少有关理学发展的断代学术史专著,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明代理学家们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潮重新整理,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黄宗羲谓明代理学“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9]。此一评价可谓明儒“穷理尽性”之真实写照。自宋以来程朱理学的流弊引发了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兴起。阳明心学以其简易对治朱学之支离繁琐,别开生面,风气一新,正如顾宪成所说:“一时心目惧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10]明代自王阳明之后,或述王,或诤王,亦以王阳明为中心。
朱学与王学的异同是理学内部的分歧。探讨王阳明心学需从程朱理学谈起,理解心学与理学之异,亦需从心学与理学之同谈起。因此,论及王学必与朱学相比较,此为研究王学之必要,自无疑义。然而,由宋至明,在从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的历史演变中,元代理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它又是否为明代王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元代理学家又是如何理解知行问题的?朱熹的知行观是否就是将“知”与“行”分作两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就是模糊“知”与“行”的界限?“知行合一”与“心即理”又有怎样的联系?如何理解王学之简易而又不易?圣学之道何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上问题的讨论或可为王学研究的深入抛砖引玉。
二、“直透大义,反向自心”:朱学之失与立学宗旨
元代理学有别于宋代。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元政权推行汉法的一波三折,科举制度的行与废等诸多原因,一方面使元代理学的内容丰富多彩,另一方面又使理学在元代的发展历尽艰辛。学派间的明争暗斗以及学术与政治间的若即若离纠缠在一起,使得元代理学呈现出斑驳陆离的复杂面貌。元代著名理学家当数吴澄与许衡,时人有南吴北许之谓①*①元人揭係斯谓:“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元]揭係斯:《神道碑》,《吴文正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45页。)钱穆先生亦就元代“南吴北许”二位大儒作过一番比较。他说:“朱子后阐扬朱学,于学术史上有贡献者,宋末必举黄震东发,明代必举罗允升整庵,清初必举陆世仪桴亭。此三人虽所诣各不同,要为能得朱子学之大体及精旨所在。然元代有吴澄草庐,当时有北许南吴之称。许衡先仕于元,提倡朱学,亦不为无功。然论学问著述,惟草庐堪称巨擘。”(钱穆:《吴草庐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足见吴澄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许衡堪称元代理学的泰斗。由许衡创立的鲁斋学派是北方理学的大宗,影响了整个元代。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11]许衡推崇朱学之传注与义理,并指出治学之道需“慎思”、“践履”。所谓“慎思”,就是要审慎、精思,不可盲从。他说:“视之所见,听之所闻,一切要个思字。”[2]370“践履”意即将所学之传注义理于伦理纲常中实践运用。如果说“慎思”强调的是“知”,那么“践履”强调的则是“行”。许衡将慎思(知)与践履(行)相结合的治学之道称之为“治生”之学。他主张理学不应空谈心性,而应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相一致,如其所云:“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2]452
吴澄是元朝中期南方著名理学大师,其学术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兼综百家、弘扬心性。吴澄注重自觉。自觉意即自诚其意,自觉其心,亦即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吴澄认为,天理非外在于人心,自觉亦非外求。因此,吴澄虽于“格物致知”、“敬义夹持”处多有精论,但更注重反求诸己、“自新”、“就身上实学”[12]32。吴澄对“心学”的重视与许衡侧重“以六经如法家律令”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13]时人谓吴澄其学相较许衡而言可谓“正学真传,深造自得”[14],并称其“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考据援引,博极古今,……近世以来,未能或之先也。”[15]80元代揭傒斯认为,许衡对元代儒学有兴创之功,“其用也弘”,而吴澄则使元代儒学发扬光大,“其及也深”,相较而言,似乎吴澄的影响力更为深远②*②元人揭傒斯:“许公居王畿之内,一时用事,皆金遗老,得早以圣贤之学佐圣天子,开万世无穷之基,故其用也弘。吴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荐,强起而用之,则年已五十余矣。虽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贤之学为四方学者之依归,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实,故其及也深。……臣窃惟我国家自太祖皇帝至于宪帝,凡历四朝、五十余载,天下犹未一,法度犹未张,圣人之学犹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纵之圣,继统纂业,豪杰并用,群儒四归,武定文承,化被万国,何其盛欤!至如真儒之用,时则有若许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学,位列台辅,施教国子,是以天启昌明之运也。乃若吴公,研磨六经,疏涤百氏,纲明目张,如禹之治水,虽不获任君之政,而著书立言师表百世,又岂一材一艺所得并哉?”参见【元】揭傒斯:《神道碑》,《吴文正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946页。。
王阳明亦论及许、吴二人。在回答立志是否需要为善去恶时,王阳明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16]22儒家道德教化总是从立志谈起。志不立,则无事可成。王阳明所谓“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这样,在“立志”―“善念”―“天理”的解读中,何谓立志(是什么)的问题便转化为如何存此善念(怎样做)的问题。如果说“立志”(是什么)属“知”,那么“存此善念”(怎样做)则属“行”。既然“立志”与“存此善念”均以“天理”为其内容和目标,那么“知”与“行”便不是两件事了。具体而言,立志(知)就是要复归天理,而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向内收敛于一心方可存此善念(行);存此善念(行)即谓立志(知),立志意即复归天理。在知―行―知的展开过程中,知与行达成统一。王阳明认为,立志、存此善念等均应以收敛为主,至于发散(即向外探求),乃不得已而为之。在王阳明看来,许衡的治生之学恰恰混淆了这一主次关系、颠倒了这一先后次序。因此,王阳明指出“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16]22
许衡于元初受元世祖之命出任国子监祭酒,以朱熹理学教授弟子。其后,朱学被尊为官学,陆学衰微,而朱子后学日益流于训诂之弊③*③元人虞集有曰:“文正没,国子监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为之者大抵踵袭文正之成迹而已。然余尝观其遗书,文正之于圣贤之道、五经之学,盖所志甚重远焉,其门人之得于文正者犹未足以尽文正之心也。……而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词申义为玩物而从事于文章,谓辩疑答问为躐等而始困其师长,谓无猷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是皆假美言以深护其短,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此上负国家下负天下之大者也。而谓文正之学果出于此乎?”参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80页。。吴澄为朱学传人④*④从师承上说,吴澄为朱熹的四传弟子。吴澄初从饶鲁弟子程若庸,属朱学一系。朱子学传至黄幹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黄幹高足饶鲁即为江右斗杓,而吴澄为饶鲁再传,即为朱熹四传弟子。(朱熹→黄幹→饶鲁→程若庸→吴澄)《宋元学案》谓:“草庐出于双峰(饶鲁),固朱学也。”参见【清】黄宗羲辑:《草庐学案》,《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第641页。,受朱学影响亦深。吴澄谈及朱学之失时说:“自孟氏以来,圣传不嗣,士学靡宗,谁复知有此哉?汉唐千余年间,儒者各矜所长,奋迅弛骛,而不知其缺。……程氏四传而至朱,文义之精密,句谈而字议,又孟子以来所未有者。而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澄也钻研于文义,毫分缕析,以陈为未精,饶为未密也。堕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觉其非。……如梦之得觉,醉之得醒,而今而后而知四十四年之非也。”[17]吴澄指出,朱学之失使人“滞于此溺其心”,偏离了儒学之道。吴澄自己亦堕此窠臼四十年方如梦初醒。有见于此,吴澄力倡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以“明指本心”[18]499的心学观点对治朱学末流拘滞于文义句读而不得要领之流弊,意欲纠朱学之偏①*①朱学在元代成为官学,所谓“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90页。)自朱学被列为科场程式,成仕途捷径,原本是朱学的人,自然受官方支持而标榜其学派之正统性;有些陆学的人,也不得不打起朱学的旗号。吴澄虽师出朱门,却私淑象山。他曾作诗云:“临川捷径途,新安循堂序。本得近定慧,末朱堕训诂。”(【元】吴澄:《韻语》,《吴文正集》卷九十一,第841页。)“新安穷格功,临川修省处。三人有我师,况此众父父。”(【元】吴澄:《韻语》,《吴文正集》卷九十一,第842页。)临川即陆九渊故里,新安乃朱熹故里。在这里,吴澄暗喻陆学简捷,朱学循序,而朱学末流则流为训诂。。
在吴澄看来,陆学简易,朱学循序,而朱学末流则沦为支离。王阳明对此表示赞同。在《答刘子澄》中,王阳明大段摘录吴澄此论以示其门人②*②《答刘子澄》载:“朱子之后,如真西山、许鲁斋、吴草庐亦皆有见于此,而草庐见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备录,取草庐一说附于后。临川吴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圣传不嗣,士学靡宗,汉、唐千余年间,董、韩二子依稀数语近之,而原本竟昧也。逮夫周、程、张、邵兴,始能上通孟氏而为一。程氏四传而至朱,文义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何学哉?假而行如司马文正公,才如诸葛忠武侯,亦不免为习不著,行不察;亦不过为资器之超于人,而谓有得于圣学则未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则与彼记诵词章之俗学,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学大明于宋代,而踵其后者如此,可叹已!澄也钻研于文义,毫分缕析,每以陈为未精,饶为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觉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岁之内春而冬,常见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运转,如日月之往来,不使有须臾之间断,则于尊之之道殆庶几乎?于此有未能,则问于人,学于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首章、《订顽》终篇而自悟可也。’”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9-161页。。王阳明指出,朱学之失在元代已多有论说,其中吴澄之见尤为肯切精当。吴澄晚年著有《礼记纂言》③*③吴澄晚年著有《书纂言》、《易纂言》、《易纂言外翼》、《礼记纂言》、《五经纂言》等。其中《礼记纂言》意续朱熹未竟之志。,王阳明亦称其不拘于朱说,于《礼》多有发明④*④王阳明在为《礼记纂言》所作序中肯定了吴澄之说于《礼》多有发明:“礼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一而非仁也,无一而非性也。——后之言礼者,吾惑矣。宋儒朱仲晦氏慨礼经之芜乱,尝欲考正而删定之,——其后吴幼清氏因而为纂言,亦不数数于朱说,而于先后轻重之间,固已多所发明。”(《礼记纂言序》)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第271-272页。,并专为此书作序。可见王阳明对吴澄之学的肯定与欣赏。在王阳明看来,许衡以朱学为宗,其“治生”之学流于朱学之失,未及大本,而吴澄对朱学之训诂、条理之弊鞭辟入里,深得儒学之道。
王阳明指出,对于支离之病,朱熹晚年已有悔悟。朱学在元代被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15]490。明代同样如此。王阳明为避免引起争端,引朱熹自述其支离之病,以针砭时弊⑤*⑤王阳明在《与安之》中道:“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第194页。:“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16]146(《答吕子约》)“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16]146(《与周叔谨》)“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16]146(《答陆象山》)王阳明指出,尽管朱熹晚年对其支离之病多有悔悟,然而后世学者依然抱守朱熹中年未定之说,堕其科臼而无法自拔。王阳明叹曰:“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16]145
朱熹强调格物穷理,其后学不免趋向言语训释,流为训诂之学。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那样,朱学在宋“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桀戾、固陋,无不有之”[19]。朱门后学空谈性理,日渐偏离了儒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之传统。至明中叶,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现实社会中已丧失其在道德规范上的至高话语权。在“人欲”之常情得到公开肯定的情况下⑥*⑥宋代理学家以天理为“公”,并以公为形上本体。这一立场自明代开始遭到反对,此后,私的观念得以公开表达。详见吴立群:《从公私观念的演变看儒家价值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世俗世界的普通民众不再接受外在天理的强制与约束,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儒者也开始失去对那超越的天理的敬畏与归属。时局一时“如沉疴积萎”。如何重塑道德规范,以儒家之道统摄人心、观照现实,成为其时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王阳明对此有论:“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徒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庶几君子闻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泽。而哓哓者皆视以为狂惑丧心,诋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挤于颠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顾也,不亦悲夫!”[16]314“道之不存,我心之忧”的忧患与担当,促使王阳明“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以“正人心”,“息邪说”,“明先圣之学”。
钱穆先生在《阳明述要·序》中指出,研究王阳明心学“须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则自无不豁然解悟。”[20]在朱学成为官学的元代,吴澄摆脱朱学“训诂和条理”的束缚,以陆学之“直透大义,反向自心”纠偏救弊。至明代,朱学由于强调“格物”、“下学”、“博学”的践履笃实工夫,流为训诂之学,日见支离烦琐,昧却本体。王阳明亦以救时弊自任,倡其心学。如此看来,摆脱训诂和条理的束缚,“直透大义,反向自心”或可为元代吴澄之学与明代王学之共同特征。
三、毫厘千里之辨与简易不易之学
理学在南宋时出现朱陆分歧,后来形成门户之争。吴澄认为,朱陆后学的门户之争偏离了当年朱陆为学宗旨。吴澄任国子监丞时曾言及陆学与朱学,似有褒陆贬朱之意①*①元代以朱学为官学。吴澄却在国子监公开发表赞同陆学的言论,他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清】黄宗羲辑:《草庐学案》,《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第641页。)此语一出,便有人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因此弃职南归,抱恨深隐。。在论及为学次第时,吴澄又以“尊德性”为先,视“道问学”与“尊德性”为下学上达的关系,此说亦被人目为是陆非朱。事实上,吴澄在推崇陆九渊的同时,并未否定朱熹之学②*②吴澄一生治学行事受宋代诸儒影响颇深。其“敬义夹持”、“心”说等观点均秉朱熹而来。在元代,有人以吴澄为陆学,并非单纯的误解,而是排斥异己的口实。详见吴立群:《吴澄理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吴澄强调反求吾心,以“尊德性”为先,乃就朱门后学日益堕入训诂之流弊而发,意欲矫朱学之偏。吴澄指出,朱学有穷理格物之功,陆学有修身自省之实,二者皆有所长,并无二致,如其所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读书讲学,陆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实践。读书讲学者,固以为真知实践之地;真知实践者,亦必自读书讲学而入。二师之为教,一也。”[21]王阳明论及朱陆异同时亦云:“象山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晦庵……专以道问学为事,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而遂议其支离。”[16]890在王阳明看来,朱学陆学虽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各有侧重,然究其实质并无根本分歧,后学“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终致支离。
吴澄在提倡以“本心”之学对治朱学支离之病的同时,对陆学后学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亦保持警醒。他指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18]499。正像朱学在其后学中面临堕为“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18]499吴澄主张抛弃门户之见,以维护儒道为重,在朱陆之间取其长而避其短,将朱熹格物致知的笃实工夫与陆九渊发明本心的简易原则结合起来,避免泛滥无归、谈空说妙。王阳明亦指出,朱学之失乃君子之过,象山之学亦未及“精一”。王阳明在为《象山先生全集》所作之序中虽对陆学之简易直截给予了充分肯定,然其“庶几精一”一语亦有陆学未达“精一”之意。他说:“至宋周、程二子,始复追寻孔孟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迎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后有象山陆氏,虽其纯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传。……故吾尝断以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而世之议者,以其尝与晦翁之有同异,而遂低以为禅。”[22]在王阳明看来,朱陆之学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而世之学者厚朱薄陆,实为小人之见。
王阳明认为,世人厚朱薄陆不仅有薄于象山,更有薄于朱子。他说:“世之学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复有所谓过者,而必曲隐饰增加,务诋象山于禅学,以求伸其说,且自以为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扶之为正论。不知晦庵乃君子之过,而吾反以小人之见而文之。……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礼,是何诬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仆今者之论,非独为象山惜,实为晦庵惜也。”[16]892对于朱陆之争,王阳明指出:“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论学而务以求胜……皆失之非……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16]888是朱非陆虽已成定论,但朱陆后学囿于门户之浅见,争论胜负,“皆失之非”,“亦皆未得其所以是”。议论好胜实为学者大病。王阳明对此多有所论,他说:
先儒之学,得有浅深,则其为言亦不能无同异。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程先生云:“贤且学他是处,未须论他不是处。”此言最可以自警。……议论好胜,亦是今时学者大病。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与人言论,不待其辞之终而已先怀轻忽非笑之意,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从傍视之,方为之竦息汗颜,若无所容。而彼悍然不顾,略无省觉,斯亦可哀也已!……某之于道,虽亦略有所见,未敢尽以为是也;其于后儒之说,虽亦时有异同,未敢尽以为非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标立门户,以为能学,则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见罪之者至矣。[16]300
王阳明认为,学者治学,各有主张,自然有深浅同异,亦难免学术论争。若以求是之心、怀问道之志,则治学可得精进;若为胜负之争,抱门户之见,则无异于自筑藩蓠,自障其目,更何谈求是问道?
王阳明其时力倡心学,亦被指为禅学,为世人所非。有感于此,王阳明说:
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月新,相沿相袭,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间有觉其纰缪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则又閧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呜呼!心学何由而复明乎!……世之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既与圣人尽心之学相背而驰,日骛日远,莫知其所抵极矣。有以心性之说而招之来归者,则顾骇以为禅,而反仇雠视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为非而以非人者,是旧习之为蔽,而未可遽以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视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犹冥然不以自反者,自弃者也。[16]286
因见支离之病日甚,“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王阳明遂以“求是”为念,倡其心学,欲反本求源,阐明“道心”之“微”、“人心”之“危”,以重回儒学之正道、重塑天理之形上根据,使天理重回人心。在王阳明看来,其时学者有受旧习所蔽而不自知者,抵王学为禅,自不当怪罪(不知者不为怪),而明知支离之病仍固守其说者,则确为门户之见,王阳明称其为“自私者”;更有既知而“冥然不以自反者”,王阳明称其为“自弃者”。
面对种种抵谤,王阳明表示,因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而不为世人理解甚至遭到恶意诋毁的情形古已有之。“昔之君子”不因“一时毁誉而动其心”,皆因其内心以求真、求是为信念。正所谓学术“亦求其是而已矣”。他说:
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之故,议论方兴,吾侪可胜辩乎?惟当反求诸己,苟其言而是欤,吾斯尚有所未信欤,则当务求其是,不得辄是己而非人也。……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为说,亦将自以为卫夫道也。……乃不知圣人之学本来如是,而流传失真,先儒之论所以日益支离,则亦由后学沿习乖谬积渐所致。……虽然,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尽,则亦安可遂以人言为尽非?[16]209(《与陆原静》)
王阳明对种种抵谤表示宽容与理解。朱学之失在明代积弊已久,世人理解王阳明所倡心学确非易事。王阳明在《书汪汝成格物卷》中这样说道:“汝成于吾言,始而骇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释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16]299(《书汪汝成格物卷》)时人汪汝成对王阳明之说经历了“始而骇”、“既而疑”、“又既而大疑”、“又既而稍释”、“稍喜”、“而又疑”的辗转反复,最终似有所得,又似无所得,正如王阳明所谓“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可见王学虽以简易行世,但理解其理论逻辑并非易事。何以如此?王阳明对其简易而又不易之学作了如下说明:“真所谓大本达道,舍此更无学问可讲矣。‘随处体认天理’之说,大约未尝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风捉影,纵令鞭辟向里,亦与圣门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尘。若复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无不即有省发,只是著实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词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縻,终身不得出头。”[16]224(《寄邹谦之》)
对“道”的追问是儒家高度自觉的思想主题和致思目标。在“道”的指引下,人的生命有了意义,社会发展有了方向。宋明时期,“道”亦称为“天理”,因此便有“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王阳明认为,此说看似简易可行,却未免捕风捉影,流于空泛。正如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而其后学从杨简起,把发明本心极端地发展为以“明悟”为主,“不起意”为宗[23],以至“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24],一如全祖望所谓“一往蹈空,流于狂禅”[25]。王阳明指出,捕风捉影,流于空泛,自然无法体认天理;而“纵令鞭辟向里”,亦与王阳明所倡“致良知”隔了一尘,同样无法体认天理。在王阳明看来,即使是“著实能透徹者”亦不能从“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中寻其大本达道,更何况“世间无志之人”,既受词章之学所羁绊,又受“似是而非之学”所误导,终身不得出头,体认天理更无从谈起。可见,“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看似简易可行,实则完全行不通。这正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有见于此,王阳明对毫厘千里之辩反复论说。他说:“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至于入门下手处,则有不容于不辩者,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矣。”[16]205-206(《答方叔贤》)在王阳明看来,王学与朱学之异并非有心求异,而是因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乃不得不辩①*①《传习录》载:“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人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王阳明以诗寄怀:
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
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
屡兴还屡仆,惴息几不免。
道逢同心人,秉节倡予敢;
力争毫厘间,万里或可勉。
风波忽相失,言之泪徒泫。[16]750
又云:
毫厘何所辨?惟在公与私。
公私何所辨?天动与人为。
遗体岂不贵?践形乃无亏。
该系统为双CPU处理系统,DSP28335与STM32F103均需一套程序独立运行,二者的合理配合是整体系统性能优秀的保障。程序处理流程如图6所示。
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无为气所役,毋为物所疑,
恬淡自无欲,精专绝交驰。
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饴?
吟咏有性情,丧志非所宜。
非君爱忠告,斯语容见嗤;
试问柴墟子,吾言亦何如?[16]753
四、“订致知格物之谬”与合内外之道
王阳明的毫厘千里之辩首先从格物致知说开始。在王阳明看来,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皆为穷理尽性而分别言说,就其实质而言并无二致。他说:“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16]87在王阳明看来,天下本无性外之理,亦本无性外之物。人们将天理视为外在于我的一个超越存在,把物看作是一个外在于我的认识对象,是隔绝天人、对立物我,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早在孟子那里就被批评为“义外之说”,而世人仍陷其中而不自知。世人拘滞于此,皆因误解心与理、道与器的关系,将心与理析而为二,将道与器离而为二。对心与理、道与器的关系,王阳明再三强调:“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②*②《赴谪诗五十五首·其四》:“此心还此理,宁论己与人!千古一嘘吸,谁为叹离群?浩浩天地内,何物非同春!相思辄奋动,无为俗所分。但使心无间,万里如相亲;不见宴游交,徵逐胥以沦?”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0页。、“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③*③《赴谪诗五十五首·其五》:“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孔圣欲无言,下学徒泛应。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我诵穷索篇,于子既闻命;如何园中士,空谷以为静?”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1页。。
王阳明此论并不为当世学者所认同。与王学持不同论者认为,“心即理”之说专事反观内省,遗弃讲习讨论,沉溺于枯槁虚寂,并认为“是内非外”是王学之错误所在。王阳明对此申明,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即于此而起,故不可不辩。王阳明说:“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16]87。王阳明指出,朱熹之格物致知说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①*①《传习录上》载:“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朱熹此说“析心与理为二”,可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具体而言,朱熹所谓即物穷理,即于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如此便将“物”与“理”均视为外在于“吾心”的存在。在王阳明看来,“天理”本在吾心,如何向外求得?如其所云:“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16]50
朱熹论格物致知析心与理为二,王阳明论格物致知则以心与理为一。王阳明说:“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16]51王学所见与朱学正相反。王阳明认为,所谓致知格物,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而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所以,致知格物意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如此,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在王阳明看来,对照朱子晚年悔悟,二者孰是孰非,不言而喻。
针对与王学持不同论者的批评,王阳明予以了回应。王阳明认为,理学所学无非“性”与“理”,所谓“性理之学”是也。既然“理”无内外之分,“性”无内外之分,那么,“学”亦无内外之分。讲习讨论未尝不以性与理为题,未尝非内,反观自省自当从日用常行、事事物物中反省,亦未尝非外。世人视“反观自省”与“讲习讨论”为内外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
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徹首徹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16]86-87(《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在这里,王阳明分析了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义外”。即将性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试图通过理智分析来把握,而不思自反;其二,“有我”。即以性为内在于我,自私其心,而于身外事事物物皆无察照。
儒家向来主张内外兼修,而非二者对立。己与人、心与物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是相互构成、同为整体中不可或缺之分子。“修己以安人”、“成己为人”、“万物一体”正是内外统一,相辅相成的习惯表达。儒家以“为己之学”自称。自我在儒学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在儒家那里,自我的塑造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儒家把自我的培养和完善放到社会、国家乃至宇宙的大背景中去认识、探索。一个人若能完成自我的修身,达到与家族、社会、国家的交融,进而达到主客交融无差别的境界,就能实现人与宇宙的合一,也就完成了自我的塑造。可见,在儒家那里,内在自我的实现与外部社会、国家乃至宇宙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人们对社会、国家乃至宇宙等外部世界的关注,最终需要回到人自身。“人”又是由“己”组成的,如果抽象地谈“人”而不落实为“己”,那么,道德修养便丧失其实践性,难以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价值准则。由此可见,在儒家那里,内外统一而非矛盾,成己与成人、为己与为人,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由此可见,以内外对立的观点理解“性”“理”“学”是错误的。若以内外合一观之,《大学》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均以修身为最终目标,则无内外彼此之分。这样,“格物”不仅为入门下手处,而且贯通儒家修身成圣之始终。换言之,成圣工夫亦只此“格物”而已。王阳明指出,所谓“格物”,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所谓“正心”,即正其物之心;所谓“诚意”,即诚其物之意;所谓“致知”,即致其物之知。如此看来,“正心”“诚意”“致知”都只是“格物”;“格物”亦即“正心”“诚意”“致知”。成圣工夫只此“格物”而已。何以如此?“理一而已”。
王阳明进一步指出,“理”“性”“心”“意”“知”“物”诸范畴虽各有所名,但都是就“理”的不同表现、不同方面而分别言说,并非在“性”之外、“心”之外、“意”之外、“知”之外、“物”之外又有一“理”。与以上诸范畴相对应,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尽性”“穷理”之谓。由此可知,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则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换言之,只有在内外统一的思维框架中,才能正确理解性理之学。格物致知之学须以“心即理”为其理论前提。
吴澄的“格物致知”说同样在此框架下展开。他说:“夫闻见者,所以致其知也。……盖闻见虽得于外,而所闻见之理则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学。”[12]25所闻所见虽然是从外部世界获得,但所闻所见之理则是内在于心的。因此,“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这样,心与理、内与外便统一起来。可见,吴澄亦从内外两方面来说明格物致知,并称格物致知为儒者内外合一之学。
在对“格物致知”的阐发中,吴澄分析了朱陆之异同,并赞同陆九渊以反观自心为“致知”的观点,同时又不完全拘于陆说,在强调内心道德的自觉性上又有所发明。与此相关,吴澄又以“尊德性”与“道问学”论“正心诚意”与“格物致知”。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上,吴澄强调,为学次弟当以“尊德性”为主,同时又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予以充实。“尊德性而道问学”意即“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内外兼修。在这里,吴澄实际上是主张以陆学的“高明简易”与朱学的“笃实邃密”结合起来,在朱陆之间取其长而补其短。就陆学而言,虽然立大本之心有“头领”,但缺乏朱学“缜密”的“致知”工夫;就朱学而言,虽有笃实的“致知”工夫,但因其陷于下学而趋于烦琐,缺乏上达的“力行之效”。因此,吴澄认为,儒者应抛弃朱陆门户之见,使下学与上达统贯起来,使“格物”与“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结合起来,回到儒学正道。[13]
如此看来,吴澄与王阳明均以内外合一为理论前提阐明格物致知,所见略同。但吴澄主要针对朱学之失而发,强调以陆学之长补朱学之失,在格物致知的学理分析上不足,其理论逻辑亦不够周延。同样有见于朱学之失,王阳明则在深入分析“理”“性”“心”“意”“知”“物”诸范畴之内涵的过程中,厘清了正确理解格物致知说的重大理论障碍。
五、知行合一与知行兼赅:知与行的动态统一
前已述及,王阳明指出,析心与理为二是朱熹错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而知行分离的错误根源亦在于此。王阳明说:
理岂外于吾心邪?晦阉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16]48
朱熹以“心与理”之学概括儒家之学,并分别从心与理两方面加以说明:心为一身之主,宰万物之理;理虽散在万物,亦不外乎人心。虽然朱熹言词中并无“心非理”、“理非心”之意,但王阳明认为,“心与理”之“与”字易使学者误以为心与理为二。由于朱熹强调内外兼顾,后世便有所谓“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亦即顾此失彼之患。王阳明认为,“心与理”之说致使学者向心外求物理,必有其不达之处。“心与理”之说正是孟子所批评的“义外”之说。王阳明以“心即理”更正朱熹之“心与理”。在王阳明看来,心一而已,所谓“仁”“义”“理”之词均为就“心”的不同表现、不同方面而分别言说。正如不可于心外求“仁”、于心外求“义”一样,“理”亦不可于心外求得。将知与行一分为二的错误原因正在于向心外求理。以“心即理”观之,则可知“知行合一”方为儒家正道。
在回答门人问知行合一时,王阳明说:“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此是我立言宗旨。”[16]109-110王阳明倡知行合一,其立言宗旨即在于纠正知行分离的错误,如下文所示: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上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16]5
在王阳明看来,古人以知行言说,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知行是一个知与行统一的过程。所谓“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表达的是在知行过程中,从知开始,到行完成,即从开始到完成的一个过程。如果能理解知行本是一个由起点向终点的过程,那么,只说一个知,便知有行,只说一个行,亦行有知。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是因为人们有时不假思索而行,有时又苦思冥想而不行。因此,既要说个知,以思维省察避免冥行妄作,又要说个行,以躬行践履避免悬空揣摩。古人既说知又说行,实为补偏救弊,乃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知即行,行即知,知行二字,一言足矣。世人却以“知先行后”等字面文义误解古人言知行之宗旨,自然无法把握知行命题之真义。正是有见于此,王阳明有感而发,倡知行合一,以救时弊。王阳明指出,如果对其知行合一说之立言宗旨能有所领悟,那么,即使既说知又说行,仍然只是知行合一;反之,则即使只说一个,亦无济于事。换言之,理解其知行合一说,首先应明白其立言宗旨。其知行合一说乃针对其时之学术问题及社会弊症而发,实为补偏救弊之方。学者需切实躬行,不可只在字面文义上钻究。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16]47-48其时学者对“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一语之知与行多有困惑。王阳明以“温凊”、“奉养”为例对知行之所谓加以说明。他说:
此乃吾子自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和。温凊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后温凊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16]55(《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在这里,王阳明以“温凊”“奉养”之事为例对“意”“知”“物”与“诚意”“致知”“格物”作了明确区分。他指出,有温凊、奉养之意,不可谓之诚意。必实行温凊、奉养,然后方可谓之诚意;知温凊之节、奉养之宜不可谓之致知,必致温凊、奉养之知,然后方可谓致知;温凊之事、奉养之事可谓物,未可谓之格物,必以良知之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在温凊、奉养之事中实行,方可谓格物。此即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温凊”、“奉养”指侍奉父母之礼,每个人对此都有切身体会。王阳明以此为例说明知行关系,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自然引出如下结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16]51-52
王阳明上述就“意”非“诚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的特别区分,正是就“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一语的反向说明,意即:“知未真切笃实不可谓行,行未明觉精察不可谓知”,亦即:“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知而不行”现象并非罕见。门人徐爱即就此对知行合一说提出了疑问。[16]4徐爱的看法是:人人尽知孝悌,却有不孝不悌。可见,知孝悌并不能行孝悌,那么知与行分明就是两件,又如何说知行合一呢?换言之,知行合一又是如何达成的?
知识与德性、德性与德行、化德性为德行是儒家知行观讨论的主题。儒家学说历来重视教化问题,而又普遍认为垂教的本原在于人的心性。换言之,儒家教化的理论基础即心性论。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心性论的因素。之后,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到《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荀子》的“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荀子·正名》),到《大学》的“诚意”、“正心”,无不阐明一条由人道上达天道,以修心养性而成贤成圣的心路历程。可见儒家论修养工夫不离心性基础。至宋代,理学中有一个重要预设,即天道与人心并非彼此隔绝、无从贯连。人心中潜含着的“明德”“良知”即天道在人心的体现。朱熹说:“理在人心,是之谓之性。……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26]外在天理在人心中的体现即性。人可以通过持敬、存养、省察、正心诚意等主观意志活动,通过“尽性”的过程,体达天道,实现天人合一,获得有限人生的充实意义。儒家修养工夫的心性基础在理学那里实现了形上化。可见,在儒家那里,知识论、工夫论、心性论始终紧密相连。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亦以复归天理、成贤成圣为依归。前已述及,在回答立志是否需要为善去恶时,王阳明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16]22儒家道德教化总是从立志谈起。志不立,则无事可成。王阳明所谓“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这样,在“立志”―“善念”―“天理”的解读中,何谓立志(是什么)的问题便转化为如何存此善念(怎样做)的问题。如果说“立志”(是什么)属“知”,那么“存此善念”(怎样做)则属“行”。既然“立志”与“存此善念”均以“天理”为其内容和目标,那么“知”与“行”便不是两件事了。具体而言,立志(知)就是要复归天理,而天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向内收敛于一心方可存此善念(行);存此善念(行)即谓立志(知),立志意即复归天理。在知―行―知的展开过程中,知与行达成统一,“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时,即是“天理”。在这一回答中,“知”即“行”,并且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
王阳明认为,致知工夫展开于践履过程之中。“知行合一”即致良知的展开过程。具体而言,知行合一即展开为知—行—知①*①杨国荣指出:“知行的统一作为一个过程,以知(本然之良知)—行(践履)—知(明觉之知)为其内容。”参见杨国荣导读,【宋】陆九渊撰:《象山语录》;【明】王守仁撰:《阳明传习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的统一过程。就知—行—知而言,分而言之,前一“知”指天赋良知,即道德修养的根据,亦即心性论所谓本原或本体。它是先验的、自在的、本然的;“行”即践履,亦即工夫论所谓工夫;后一“知”指主体通过践履(行)之后而自觉其天赋良知,它是自为的、实然的。换言之,先验的道德良知只有在后天的致知活动中,才能为主体所自觉、所把握。知行在此环节获得统一,在从自在之知到自为之知,从本然之知到实然之知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首先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展开。吴澄亦认为知不离行,并强调“知”为“实践”之知,进而提出知行兼赅的思想。
在儒家那里,“知”并非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是对自我的认知;“行”亦非改造物质自然的活动,而是对“性理”的认知活动,是以自我实现为宗旨的道德实践。吴澄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他首先对“知”作了疏解。吴澄将词章记诵、政事功业归为“见闻之知”,并称其为外学。他说:“词章记诵,华学也,非实学也;政事功业,外学也,非内学也……然知其所知,孰统会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无所统会,非其要也。无所主宰,非其至也。”[27]94张载曾明确把“知”区分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见闻之知”通过耳目见闻而获得,又称“学问之知”;“德性之知”又称“明德”、“良知”,即先验的道德知识,亦即关于人性的自我认识,它通过自我反思而发明。张载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人谓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29]张载认为,见闻之知并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亦非由见闻而来,故有“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之别。吴澄以词章记诵、政事功业为“见闻之知”,并认为“见闻之知”因其外求,因其非内、非实,故不可谓真知。可见,吴澄不以“见闻之知”为真知。
吴澄认为,发见本心方可谓知。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知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12]32吴澄曾强调“尊德性”的重要性,但同时亦指出尊德性仅为“先立乎其大”,道德修养的完善仍须有“道问学”予以充实,方不致流入佛老之异端。[13]因此,吴澄在以“发见本心”为“知”的同时,提出以“固守本心”为“行”。他说:“应接酬酢,千变万化,无一而非本心之发见,于此而见天理之当然,是之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也。”[18]499-500在吴澄看来,“本心之发见”离不开行。吴澄反对“外心而求道”,并非要人们“离去事物”空谈义理。他说:“读《四书》有法,必究其理而有实,非徒诵习文句而巳,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3]648吴澄强调,“知”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如其所云:“若徒知而不行,虽知犹不知也。”[12]32可见,吴澄所谓“知”既非“见闻之知”,亦非“德性之知”,而是实践之知。吴澄以“发见本心”为知、又以“固守本心”为行,意在说明知不离行,如其所云:“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实矣,内矣。”[27]
在吴澄看来,强调真知实行的知行合一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他说:“凡学之大端有二:知必致也,行必笃也……夫子以贯之一言……朱子释曰贯通也。”[29]吴澄指出,儒家之学无非知行而已,朱熹将知行关系解释为贯通,意即知行不相离。因此,知而不行,仍是未知①*①吴澄指出,在知行的统一过程中虽有行而不知,但无知而不行。他说:“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尝真知也,果知之,岂有不行者哉?”参见【元】吴澄:《学则序》,《吴文正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228页。。换言之,知不离行。《中庸》提出了学、问、思、辩、行五个为学方法。吴澄从知行的角度对此作了发挥,他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错综之以有所疑而质诸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讲明之以发其端而反诸思……既已因其学问之所得而谨思之,则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辩,又因其思之所及者而明辩之,乃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30]吴澄把《中庸》提出的学、问、思、辩、行概括为知与行,并认为知行不相离。在吴澄看来,孔子以文、行、忠、信立教亦可以学、问、思、辩、行范围。他说:
夫子之以文、行、忠、信立教也。四者之施有先后尔,非专一偏于一而不该不遍也。……首之以学文,而诵习之、究索之,则能明其道于心矣。所明之道,我所固有,加之心学行,而修践之、持守之,则能履其道于身矣。所履之道不诚实,是欺也是诬也。尽己之诚为忠,循事之实为信。继之以学忠与信,而内外一于诚实,则践真守笃,无虚伪矣。既能明于心,又必履于身;既能履于身,又必诚于内、实于外。圣人之教人也,始终该遍如此哉![31]
文行忠信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吴澄指出,知识(文)、实践(行)、忠诚(忠)、守信(信)看似分别就书本知识、社会实践、道德修养等不同方面而言,实则彼此并无隔离。道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文以载道、体道行道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知行两方面的内涵,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儒家之知以性与天道为其主要内容,故求知即明道;明道亦即对道的躬行践履,此亦即行。换言之,知即在行中,若能知便可行。
基于对知行关系的理解,吴澄在担任太学司业时即以“多学”、“多识”为原则定“教法四条”,即“经学”“行实”“文艺”“治事”。据《神道碑》载:“仁宗即位,进司业。乃损益程淳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施行,为同列所嫉。”[32]吴澄在参考程颢、胡瑗、朱熹等人的教学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四条教法的改革方案。四条教法中的“行实”、“治事”即倡导将“知”与“行”相结合:既学以致用,又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吴澄还以“实悟为格,实践为诚”[3]648论知行关系。在他看来,知行本不相离。如果以“悟”、“诚”为“知”,以“格”、“践”为“行”,那么,“实悟为格”意即真知即是行,“实践为诚”意即实行即是知。此说似与前论王阳明所谓“意非诚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之意若合符节。
在吴澄那里,知行以德性的完善为目标,知行统一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吴澄援引《周礼》中的至德、敏德、孝德三德[33],将知行统一的程度分为递进的三个层次。他说:“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能行,明诚两尽,德之极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偏,行无不笃,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于孝,庸德之行专务其本者也……盖知行兼赅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则笃于行,而知未逮者,亦其似也。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苟未能一一纯备,先务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34]在这里,至德、敏德、孝德分别对应“知行兼赅”“行而未知”“行而不备”等知行统一的三种情形:一为“至德”,此为上。若能知能行,则可达儒家道德修养中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自明诚”而“自诚明”、内外兼备的至德境界。能知能行亦即知行兼赅;二为“敏德”,为其次。虽在知的方面未达完备,但在行的方面却无有不达。如此亦可增进道德修养;三为“孝德”。在行的方面,笃于“孝行”。虽于孝行之外的其他方面未有所达,但仍不失为“百善孝为先”之阐扬,为善行之始。如此亦可进德。通过对“进德”层次的划分,吴澄给出了切实可行的为学目标:若知行兼赅,可达“至德”;若笃于“行”,可得“敏德”;若仅笃行于孝,可进“孝德”。如此看来,知行合一非“能”与“不能”,乃“为”与“不为”。知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统一。概而言之,在知行关系上,吴澄明确提出了“知行兼赅”的思想,并将知行视为动态统一之过程。
六、结语
综上所述,吴澄与王阳明的知行观首先从格物致知说展开。吴澄的格物致知说主要针对朱学之失而发,强调以陆学之长补朱学之失,并以内外合一为其理论前提阐发“外之物格则内之知致”。王阳明则明确指出,析心与理为二是朱熹错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王阳明认为,以“心即理”观之,“理”“性”“心”“意”“知”“物”诸范畴虽各有所名,但都是就“理”的不同表现、不同方面而分别言说,并非在“性”之外、“心”之外、“意”之外、“知”之外、“物”之外又有一“理”。与以上诸范畴相对应,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尽性”“穷理”之谓。由此可知,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则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因此,格物致知无内外之分。可见,二人均以内外合一之道阐明格物致知,所见略同。
关于知,吴澄以“本心之发见”为“知”,认为知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在阐明知行不相离的观点之后,吴澄又以“实悟为格,实践为诚”[3]648论知行关系。如果以“悟”、“诚”为“知”,以“格”、“践”为“行”,那么,“实悟为格”意即真知即是行,“实践为诚”意即实行即是知。此说与王阳明所谓“意非诚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之意若合符节。在此基础上,吴澄提出了“知行兼赅”的主张。吴澄以《周礼》中的孝德、敏德、至德分别对应“行而不备”、“行而未知”、“知行兼赅”,即知行统一的三个递进程度。知行兼赅意即将“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结合,“自明诚”与“自诚明”相结合,内外兼修。王阳明则指出,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他首先以“意”非“诚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的观点阐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进而提出知即行,知行合一。接着,王阳明以知—行—知的动态展开过程说明了知行如何获得统一。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在从自在之知到自为之知,从本然之知到实然之知的过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可见,在知行关系上,吴澄和王阳明均认为知行不相离,并视知行合一为一动态统一。
如何重塑道德规范,以儒家之道统摄人心、观照现实是吴澄和王阳明在各自的时代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二人均以辟门户之见、倡求是新风为其立言宗旨。自宋以来,朱陆后学各立门户,相互排斥,使学术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朱学成为官学的元代,吴澄对章句之学予以大胆批判,以陆学之简易补朱学之支离,并使陆学借朱学得以薪传。陆学不仅在陆学系统中延续下来,而且也渗入朱学系统,为朱学所兼取。吴澄立足于学术发展,客观理性地看待朱陆分歧,冲破了狭隘的道统藩篱,使理学在元代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3]。吴澄强调朱、陆之学的根本一致,不仅体现了元代理学的学术特色,也预示着理学演变的方向。明代王学的出现并非偶然。尽管阳明心学是否就是对吴澄心学的继承和发挥尚有待考察,但吴澄兼综百家、弘扬心性、以道自任、独立省察的治学态度确实有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从中亦可窥见理学发展演变的端倪。至明中期,朱门后学空谈性理,日渐偏离了儒家修齐治平、经世致用之道。王阳明亦以救时弊自任,倡其心学。在王阳明看来,王学与朱学之异并非有心求异,而是因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而不得不辩。王阳明以求是为本,意欲重返儒家之道、重塑天理之形上根据,使天理重回人心。
对“道”的追问是吴澄和王阳明高度自觉的思想主题和致思目标。以此为依归,二人指出,人们将道、天理视为外在于我的超越存在及认识对象的这一观念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即在于视心与理、道与器为内外对立的矛盾关系。在以合内外之道对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知行观基本问题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疏解之后,二人均提出了知行不离、知行合一的主张,并均视知行为一动态的统一过程,建立了各自的知行观。就其理论体系而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其“心即理”、“致良知”的思想融会贯通,其知识论与心性论、工夫论互为阐发,理论逻辑较为周延。相较而言,吴澄的理论建构则较为粗糙。
吴澄的“知行兼赅”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表现出的理论思考亦表明儒学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是儒学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如当代学人所指出的那样:“儒学历来都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既表现在对世俗社会风气,当然还表现在对儒学内部不同传统的批判方面。儒学正因为自己传统内部充满着批判性,因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批判儒学,从而推动儒学向前发展”[35]。
[1]朱熹.朱子全书·二十二[M].朱杰人,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8.
[2]许衡.鲁斋遗书[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十二[M]//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648.
[4]吴雁南.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J].贵州社会科学,1995(2).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6]钱穆.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47.
[7]黄宗羲.姚江学案·叙录[M]//明儒学案·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179.
[8]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95.
[9]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M]//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5.
[10]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M].[万历间刻本].
[11]黄宗羲.鲁斋学案[M]//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622.
[12]吴澄.吴文正集·卷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2.
[13]吴立群.吴澄理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14]虞集.吴文正集附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45.
[15]虞集.道园学古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80.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21-422.
[18]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八[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9]黄宗羲.东发学案[M]//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567.
[20]钱穆.阳明学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
[21]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五[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57.
[22]陆九渊.陆九渊集[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538.
[23]黄宗羲. 慈湖学案[M]//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376.
[24]陈淳.北溪文集大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86.
[25]黄宗羲.絜斋学案[M]//续修四库全书:第5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404.
[26]黎靖德.朱子语类(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2.
[27]吴澄.吴文正集·卷七[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8]张载.汤勤福导读:张子正蒙[M]. 王夫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4.
[29]吴澄.吴文正集·卷九[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6.
[30]吴澄.杂识四[M]//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外集. [清]万璜,编.[清乾隆丙子年临川吴氏刊本].
[31]吴澄.吴文正集·卷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19.
[32]揭傒斯.吴文正集(附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44.
[33]钱玄.周礼[M].长沙:岳麓书社,2001:125.
[34]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一[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28.
[35]吴根友.儒学的批判性与批判儒学[J].孔子研究,2013(2).
责任编辑 何志玉
The idea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Compare Wu-Cheng’s“knowledge and behavior” with Wang-Yangming’s“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U Li-qun
(Shanghai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200044,China)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he central thesis of it is “character” and “natural law”. Will it be possible to be sanctified, and how to be sanctified has been the focus-set of this theory. Accordingly, the resulting questions of knowing and doing closely connect to the temperamen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Ontology. Both Wu Cheng and Wang Yang-ming’s theory begin with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Wu-Cheng’s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wa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lack of Zhu Xi’s study by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 of Lu school to cover the shortage of Zhu Xi’s theory, and illustrating the unity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 by taking the idea as its premise. Wang Yang-ming pointed out that Zhu Xi misunderstood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because he put the reason and mind second, and in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ind is principle”,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was neither internal nor external. They both had similar views on explaining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As to knowing, Wu-Cheng regarded the innate mind as knowing. He also believed that knowing only came from practice. Wu Cheng promote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fter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in the aspect of “enlightenment is investigation, practice is truth”. But Wang Yang-ming claimed that knowing and doing and Ontology were inseparable from one another. First he explained that “knowing without doing is nothing”, and he further theorized that “knowing is practice”. Then he explained how knowing and doing came up with the unity based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knowing-doing-knowing. In Wang Yang-ming’s opini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as a dynamic process. From self-knowledge to things-in-itsel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on can be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actual knowledge.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Wu and Wang both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a dynamic process and never took apart.
Wu Cheng; Wang Yang-ming; knowledge and behavior;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dynamic unity
2016-03-22
吴立群(1968-),女,江西崇仁人,上海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
B244;B248.2
A
1673-6133(2016)03-0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