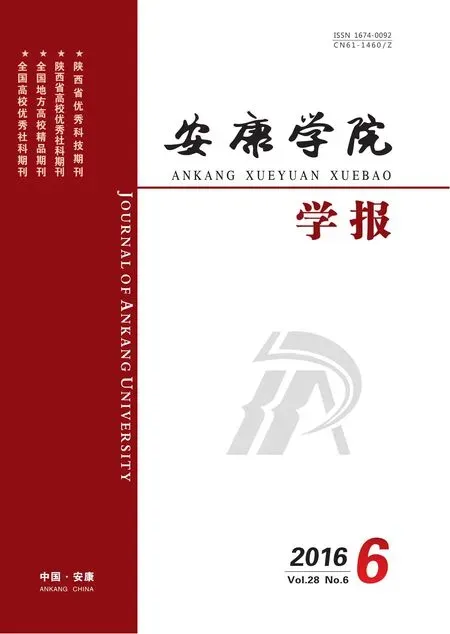“理欲之辨”与清代前中期的女性婚姻道德生活
——以“贞节观”及其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为探讨对象
施文斐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中文系,宁夏 银川 751400)
“理欲之辨”与清代前中期的女性婚姻道德生活
——以“贞节观”及其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为探讨对象
施文斐
(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 中文系,宁夏 银川 751400)
相较于对宋儒理学的照单全收,清人更趋向于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对宋儒之“理”加以辩证审视,并试图于“理”之外寻求新的道德标准,原始儒学那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关怀于是成了这一意图的重要指向。这一富于人性化的思考维度在清人论及“贞节观”的相关问题以及由“贞节观”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中体现出了“以理顺情”的道德情感化倾向。
情感化道德;以理顺情;从一而终;寡妇再嫁;未嫁守贞
就宋明以来“理欲之辨”的总体走向而言,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与晚明的“好货、好色”论无疑都具有极端化色彩,宋儒对理的异常偏执自不必说,其对欲的过度恐慌亦与晚明对欲的过度放纵一样不可取,但宋明两代之于理、欲问题所做的丰富论述与实践毕竟还是为清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使其能够对这一问题作出更加客观、全面且兼顾人情的把握。尤其在历经了鼎革之痛以及清初的实学思潮后,以“理”为衡量标准的道学家们对人情的过分苛责往往招致开明之士的强烈不满,清中期出现的以“礼”代“理”的学术思潮在相当程度上也正代表了人们试图于“理”之外寻求新的道德标准的意图,而原始儒学那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关怀无疑成了这一意图的重要指向。尽管学术思潮乃至社会思想在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会伴随着保守主义的惰性,但相较于对宋儒理学的照单接受,清人显然更愿意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对宋儒之“理”加以辩证审视,其以原始儒学的情感化道德来取代宋儒语境下的理念性道德这一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这无疑使得清人对理、欲问题的思考不同于宋儒的偏执而更富于人性化。这一充满人情味的思考维度在清人论及“贞节观”的相关问题以及由“贞节观”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从一而终与通奸行为
在正统的伦理道德中,“从一而终”是女性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礼记·郊特性》中有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汉代《女诫·夫妇》更进一步地通过对天地阴阳的比附论证了“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并认为“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1]。也就是说,按照正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女性并没有自主改嫁的权力。只有在她的丈夫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如“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做妻子的才可以“义绝,乃得去也”[2]467。否则,即便“夫虽有恶,(妻子)不得去也”,因为“地无去天之义也”[2]467。
毫无疑问,“从一而终”的道德观念严重地限制了女性的婚姻选择权。即便对自己的丈夫心存不满,她们也没有权力自主改嫁,而只能继续忍耐下去。但事实上,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结成的婚姻往往都是低质量的。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从来都是以家族利益为考量,当事人双方是否情投意合反而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尽管一场由父母包办的婚姻从家族利益的角度出发,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情感层面来衡量的话,则很可能是一场有着严重情感缺陷的低质量婚姻。
在女性没有权力通过改嫁的方式结束低质量婚姻的情况之下,通奸行为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据有关学者考证,通奸行为在清代中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3]。以清代中期的女性犯罪情况为例,30岁—50岁是女性犯罪的集中年龄段,这也就是说已婚妇女是女性犯罪的主要群体,而其中又尤以奸情犯罪数量为最。据郭松义先生统计,在婚姻类中,因通奸而引发纠纷甚至于命案的,占到女性犯罪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同时,据郭先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奸情类”档案统计,乾隆年间,各省区每年上报朝廷批决的婚姻奸情类命案要案平均在800件左右。在这800件中,因通奸引发的约为250—530件。从通奸和奸杀案件的频发可以看出,男女私通在清中期可谓相当普遍[4]。
从女性的情感诉求这一角度而言,清代女性奸情犯罪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晚明盛行的情欲观对女性婚姻观产生的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当时的封建婚姻制度下,这种原本应有益于个体解放的影响却往往以奸情类命案等负面新闻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如果换个角度的话,就会发现通奸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极大地补偿了女性在低质量婚姻中所无法获得满足的情感需求乃至欲望需求。当然从维护正统家庭秩序的角度出发,女性的通奸行为就如同改嫁行为一样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它们显然对身为丈夫的男性尊严以及整个家庭秩序造成了伤害。
二、守节与寡妇再嫁
明朝尚烈、清代尚节,明清两代对于女性最高道德标准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明史·列女传》中论及了寡妇的三条出路:“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5]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人以女性死烈为尚、以守节为次的道德价值取向。不仅如此,中晚明以后明人普遍表现出来的好奇尚异也同样体现在了女性的节烈观上。节得越苦越好,死得越烈越好,“盖挽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国制所褒,志乘所录,与夫里巷所称道,流俗所震骇,以至奇至苦为难能”(《明史·列女传》前言)。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为道;不如此,就不足以为人所传扬。据有关学者统计,以王鸿绪在雍正元年进呈的《明史·列女传》中记载的女性事迹为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孝义与节烈。其中,以孝入传者有17人,义妇有3人,其余78人皆是因坚贞如冰雪而入选,“节妇”与“烈女”的比例竟为2∶39。《明史·列女传》中烈女事迹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说明了编撰者的价值取舍受到了明代尚烈风气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明代确实存有数量庞大的烈女事迹。
明代的尚烈风气到了清代发生了重大转关,雍正六年三月(1728)壬子颁行的上谕可视为这一转关的重要标志。在这份上谕中,清廷之于女性的最高道德标准做出了重新界定,“妇人从一之义,(再婚)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然烈妇难,节妇尤难。夫亡之后,妇职之当尽者更多,上有翁姑,则当代为奉养。他如修治苹蘩,经理家业,其事难以悉数,安得以一死毕其责乎?朕今特颁训谕,有司广为宣示,俾知孝子节妇,自有常经,伦常之地,皆合中庸,以毋负国家教养矜全之德。尚训谕之后,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清史稿·忠义·李盛山传》)。这份上谕表明,清廷之于女性守节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死烈。在丈夫过世之后,赡养舅姑、抚育幼孤、维持家业等等一系列的家庭重担就全都落到了寡妇身上。如果寡妇此时执意殉夫而去,那么原本就已濒临解体的家庭也将会家破人亡、走向毁灭,其后留下的诸多问题必将给整个社会造成负担。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为全国的统治核心,清廷当然希望能将问题消化在家庭内部,这就需要必须有一个人能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将夫家从濒临解体的边缘拯救出来。这个颇具殉道意味的角色就自然地落在了寡妇身上。
正是从巩固家庭秩序进而维系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清廷才大力提倡寡妇应忍辱负重地守节下去而非一死了之。当然,在完成养亲、抚孤、持家等一系列任务后,寡妇是死是活就不在清廷的干预范围内了。在更具理性精神的清人看来,明人所崇尚的夫死立即殉死实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们更崇尚的是所谓的“节而后烈”,即在履行了之于夫家的一系列义务后再死也不迟。这样“知大义,明大礼”的妇人才会得到清人毫不吝惜地赞美,清人笔记中就大量记载了此类事迹。陈康琪在其笔记中记载的“林节妇”事迹就非常全面地体现出了在死节这一问题上,女性自身、官方以及文人等多方面的不同态度[6]677。
就林节妇的个人意愿而言,她是很希望能在丈夫死后立刻殉死的,但从官方以及文人阶层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推崇的是“先节后烈”这一情理兼容的做法。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女性生命的尊重,但这显然又是以承担起维系夫家的重任为前提的,而非出自于对女性自身权益的考虑。正因为如此,夫死后立刻殉死的行为被视为是对夫家责任的逃避而遭到了否定,至于那些夫死之后就急于改嫁的女性则更易受到强烈的舆论谴责。这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她既没有为夫殉死,更没有替夫持家,而是在夫死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另结新欢。尽管这种做法在今人看来似乎无可厚非,但既不能为夫殉死,又不能替夫守节,置夫家责任于不顾而纯然追求个体幸福的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无法令人接受的。那些逃避夫家责任而急于改嫁的寡妇们往往会遭到男性社会的痛恨与唾弃,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舆论之于寡妇的道德要求,即既不可立刻殉死,也不可改嫁他人,而要继续留在夫家,并代替死去的丈夫承担起维系一家生计的重任。这样一来,除了为夫守节外,社会舆论并没有为寡妇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当然,对寡妇守节以及“先节后烈”行为的提倡是完全符合清廷意图的,作为统治核心的皇权显然发挥了舆论导向的重大作用。
尽管如此,当我们在翻检明清史料时却又发现寡妇再嫁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陈剩勇先生曾以图表形式例举了明代的浙江诸府县、南直隶有关府县、江西诸府县、福建、湖南诸府县等江南地区的人口及男女性别比率情况,并通过大量统计数字表明,“在明代中叶以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以南一带,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资源空前稀缺,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7]。清代情况亦大致如此。究其原因,有许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做了分析,认为明清两代寡妇再嫁在民间社会之所以盛行,主要是源于溺杀女婴的陋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适婚女性资源的严重稀缺等原因。其中,溺杀女婴这一恶习虽然有着原始文化遗留的一面,不过更多地则是根源于明清两代婚嫁论财且彩礼偏高这一社会现实。
郭松义先生根据清代地方志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做过统计,在清代十六个省份,一百五十余个府州县厅中都有过溺女行为的记载,其中最严重的是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省。这些记载中有三分之一都提到溺杀女婴与婚嫁论财的关系。而谈到某地无溺女现象的原因时,也常常将其与妆奁不厚相联系。在传统社会,男性能否适时婚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受制于经济上的困窘而无法及时婚配的往往都是中下层的男性,那些经济富足的上层社会男性仍有充足的女性资源可供选择,他们在成亲、纳妾以及蓄婢上几乎很少受困于经济因素。不过这样一来,女性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使得原本就十分紧张的资源供应变得更为紧张。在适婚女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许多中下层社会的男子便将目光更多地转移到寡妇身上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许多清人笔记中甚至还记载了某位女性刚刚丧偶,就立刻有许多人前来提亲之类的事情。由此可见,寡妇在清代的婚姻市场,尤其在中下层社会的婚姻市场上还是十分抢手的。
于是,围绕着“寡妇改嫁”这一问题便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以清廷、官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希望寡妇守节,但在另一方面,以中下层庶民为主的婚姻市场又对寡妇有着极大的需求量。这也就是说,国家意志,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下行到基层社会,官方的主流观念与民间的具体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脱节。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明清、尤其是清代的贞节牌坊林立本身就足以说明国家意志已然极大地贯彻到了民间社会。应该说,这一观点基本上也是成立的,但相较于前面几个朝代(其中也包括节烈风气盛行的明代),清代贞节烈女的陡然剧增也与清廷不断地降低旌表标准等措施有关。但无论如何,清代民间社会的节烈风气极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笔者并不想否认。只是想进一步明确的是,即便如此,在清代民间社会节烈风气极盛的情况之下,寡妇改嫁的现象也同样盛行于民间社会。
与这一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是,尽管我们在上文中论及到了一些文人之于寡妇再嫁问题的强烈批判,但也应看到还有一部分文人的持论其实是相当宽容的。他们往往能从人情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体察守寡对女性造成的种种痛苦。虽然清廷倡导寡妇守节的主要意图在于维护家庭秩序,而并不是主观上要控制女性的情感诉求以及生理欲望,但不可否认的是,守寡,即替死去的丈夫守住自己的贞操,在其实际效果上确实对女性的情、欲诉求造成了强烈的压制。对于经历了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以及情欲观洗礼的清代文人而言,这一点就显得格外不近人情。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对“寡妇再嫁”持肯定态度的文人总是会从人情的角度出发着重表现守节生活对女性的摧残。
沈起凤在其笔记《谐铎》“节母死时箴”条中就写到了一个以坚韧的意志力压制住自己的情欲需求并最终成为“良家节妇”的“励志”故事,但这位节妇在临终前却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诫子孙“知守寡之难,勿勉强而行之也”[8]。某种道德教条的实现往往是以对个体欲望、情感甚至是生命的戕害为代价的。正是因为一些开明文人较为敏锐地感受到了寡妇的苦楚,因此,他们才会更倾向于认为守节与否应当出于寡妇自愿,不可勉强为之。如汪辉祖就认为如果孀妇“或性非坚定,不愿守贞,或势逼饥寒,万难终志”,那么,“不妨听其自便,以通人纪之穷”,否则,“强为之制,必有出于常理外者,转非美事”(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无志秉节者不可强”条)。作为一个崇高的道德标准,对于“节操”的完美实践心向往之即可,但不必人人勉强为之。
三、未嫁守贞
有一点须明确的是,尽管清人围绕着“贞节”问题进行的探讨多从人情的角度出发,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以理顺情”的情感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清人将会就此滑向“弃理纵情”的极端,就如同晚明时期所犯的错误那样。事实上,清人在对正常的情、欲诉求持宽容态度的同时,更对那些能够以极大的意志力克制住人情、人欲,并最终成就完美道德的人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如在针对“未嫁守贞”这一问题的探讨上,许多清人对归有光、汪中的论调都持反对态度。“明归熙甫著论,极言女未嫁夫死守节之非,近时汪容甫亦主此说。余颇不谓然。”[9]35“女子未嫁守贞,归震川以为非礼,作论辨之,后儒往往信其说,此一言而有乖名教者也,今以诸家之说正之。”[10]311“女子未嫁守义,归震川氏谓不合于礼经。近代文人,又多引据经传,与归氏相诘难。余谓朝廷有旌典,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论。”[6]677在清人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贞女、节妇、烈女光辉事迹的大量书写。在迫于家庭压力而无法完成守节志愿时,许多女子还会以自残甚至自戕方式来明志。在清人笔记中,诸如“女断发自誓,因亦不强也”[6]354,“有强之者,至截耳自明”[11],“剪发断一指以拒”[12],“微闻亲戚有欲夺其志者,辄不食,凡二十日,呕血至尽死”[13]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为了坚守住自己的道德节操,这些未婚贞女承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肉体痛苦,并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虽其情可悯、其志可叹,但她们由此而表现出的崇高的道德品质理应得到社会的肯定。
当然,为了实践某种道德规范而对身体实施的自残、自戕并不会得到清人的赞同。虽然清人对死节之烈时常表现出一种赞叹之情,并往往神化之,但在清人的普遍观念中,终究还是有着一种“尊身重生”的强烈愿望。能以一己之身完美地实践某种伦理道德固然令人钦佩,但由此而自残身体甚至于自戕生命则诚不可取。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借一个等待替身的吊死鬼之口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按照这位吊死鬼的说法,“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尽节,烈妇完贞,是虽横夭,与正命无异,不必待替”。至于那些原本“有一线可生”,并非一定要去死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或小忿不忍,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气,率尔投缳”,因此,“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罚”[14]58。不当死则不必死,道德的实践并非一定要以自我生命的消解为代价,“成仁”未必一定要以“杀身”的方式才能实现。通过这种颇具神异色彩的言说,纪昀同样表达了“尊身重生”的强烈愿望,这也是清人比秉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化观念,动辄以自我毁灭来成就道德理想的宋儒更为开明、更为变通的地方。当然,纵观整个封建历史,清代是女性死节数量最多的朝代,但其中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并不能由此而抹杀清人“尊身重生”观念的存在。
四、对由“守贞”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的讨论
围绕着“女性贞节”这一问题,清人又对由“守贞”而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道德冲突进行了探讨,诸如守贞与抚孤、守贞与全孝等道德困境是清人时常探讨的话题。在清人笔记记载的大量事件中,女性往往都在经历了一番挣扎与权衡后,暂时放弃了守贞或死节的志愿,而忍辱负重地承担起抚孤、全孝、养亲等家庭责任。当家庭责任的履行最终得以圆满实现后,这些女性仍会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残生,借以实现当初的守节志愿。
对多重伦理道德的实践往往最终都集中到了女子身上,尤其是抚孤、全孝、养亲等群体性伦理道德时常不得不以女子舍身为妓、或自鬻为他人妻等方式,即以牺牲个体性道德操守为代价才能实现。对于这些在多重伦理道德的冲突下不得不舍身取义的“失节”女子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更加令人踌躇。在对此类问题的探讨中,充分显示出了清人重视精神操守,而并不苛责于“肉体贞洁”与否的开明态度。
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了一位乔氏女在丈夫死后,为了完成抚孤的重任而暂时放弃死节的志愿,待将儿子养育成人后才自杀以明志的事迹。值得探讨的是,以抚孤为己任的乔氏女虽然不幸地落入贼人之手,其后更沦落为娼,但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乔氏女依然坚持抚育幼子并为其延师授业,使其娶妻成家。她的执着、忍耐与坚韧确实令人肃然起敬。然而,群体性道德的完美实践丝毫不能减少个体性道德,即失节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倡,尚何面目复生人世乎?”[9]84带着失节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痛苦,这位乔氏女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如果从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角度来看,这位妇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以“节妇”目之,但相较于宋儒的决绝与苛责,清人却更倾向于以区分出孰为“大义”、孰为“小节”的变通方式来灵活地处理这一问题,俞樾对这位乔氏女的评论就很好地印证了清人的这一思考模式。俞樾认为“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因此,“不必徇沟渎之小节”。相较于肉体上的“贞洁”与否,精神层面的“贞节”才更为重要,而此妇能“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故仍“不失为完人”[9]84。但是,对伦理道德冲突的灵活处理总是会与僵化、刻板的道德教条发生冲突,因而又时常会遭到道学家们的谴责。对此,以纪昀为代表的开明之士也总是予以猛烈的回击,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曾多次针对道学家们动辄以理责人的道学言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
纪昀在其笔记中曾记载过一位丐妇弃子救姑的事情。这位“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的丐妇在涉水过程中,“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但获救的婆婆并不领情,而是对着儿媳破口大骂,“我七十老妪,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后“竟以哭孙不食死”[14]275-276。这件事在当时似乎引起了道学家们的广泛讨论,纪昀将此事记载于笔记中,同时亦将道学家们对此事发表的言论同时记录了下来。“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纪昀对此类道学言论甚为不满,认为“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并就当时的危急情况以及丐妇由此而陷入的道德困境进行了深入剖析,“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终身宁不耿耿耶?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而道学家们则往往置纷繁复杂的情、理冲突于不顾,“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如果以道学家们的苛责为据,那么,“三代以下无完人”[14]276。在另一则类似事例的论述中,纪昀也同样表达了对“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的强烈不满。
综上所述,围绕“贞节观”问题以及由“守贞”而引发的诸种道德困境而展开的讨论很能体现出清人在情、理间反复权衡的复杂态度。他们一方面对贞女、节妇们那崇高的道德操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贞也者,后世之所难。虽过于礼焉,苟合乎从一之义,是则君子之所深取耳”[10]312,但在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循理窒情”对人性的戕害。因此,尽管清儒亦同宋儒那样将守贞、守节视为女性所应秉持的道德品性,但他们并没有像有严重精神洁癖的宋儒那样要求人人都要成为贞女、节妇、烈女。对于那些出于人性的软弱与人欲的诱惑而未能坚守住节操的女子们,清人也很少表现出严厉的苛责,而总是予以一定的同情与谅解。即便对那些坚定地表示出守贞志愿的女子们,清人也还是希望她们能更多地从自身实际的情感诉求出发做出慎之又慎的考量,而不要出于“一时激烈之所为”的道德冲动,至于“矫立名义”以邀取虚名则更不可取,出于此类行为动机的所谓“守贞”“守节”皆“君子所不愿见也”[15],“圣人固不以守义强人,亦不禁人弗为,殆欲人之自尽其道焉耳,此圣人之深心也”[10]312。能守则守,如若不能,亦不必勉强,更不必苛责。在清人的观念中,希望尽量从顺乎人情的角度出发解决情、理间的冲突。相较于对某种道德教条的一味恪守,更推崇发乎自然人情的情感化道德。虽仍对贞女、节妇、烈女事迹普遍致敬,但又对道学家们置具体的人情实际于不顾而对贞、节妄加苛求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这些以“重理尚情”为特征的清人言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清人对情、理、欲三者关系的深入思考,体现了清人在这一问题上力求情理兼容。这种以人情为尚的人道主义情怀,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对缘情制礼的原始儒学精神的复归。
[1]裘毓芳.女诫注释[M].上海:上海医学书籍出版社,1916:10.
[2]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杨晓辉.清代中期妇女犯罪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4]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7.
[5]蔡东藩.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33-7734.
[6]陈康祺.郎潜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陈剩勇.理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J].史林,2001(2):22-43.
[8]沈起凤.谐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6.
[9]俞樾.右台仙馆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陆以湉.冷庐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龚炜.巢林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3.
[12]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274.
[13]王晫.今世说[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82.
[1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5]朱翊清.埋忧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87.
【责任编校 杨明贵】
The Chastity and The Moral Dilemmas Arouse from It in the Qing Dynasty
SHI Wenfei
(DepartmentofChinese,ChinaUniversityofMiningInstituteofYinchuan,Ningxia751400,Yinchuan,China)
Compared tosign on thedotted lineof a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in theSong Dynasty,Qing Peopletend torefer totheoriginal Confucianismas thereferenceand havedialectical reviewon“Li”of confucian intellectuals in theSongDynasty,attempttoseekingnewmoral standardsinadditionto“Li”,thehumanitariancarefull of tenderfeelingsof theoriginal Confucianism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point of this intention.This thinking dimension full of humanistic human nature represent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therelatedissues of“chastity”andmoral dilemmatriggeredby the“chastity”of QingPeople,andreflects thetendencyofmoral feelingof“makingLi conformtofeeling”.
emotional morality;makingLi conformtofeeling;befaithful toone’shusbanduntodeath;remarryafterone’shusband’s death;unmarriedchastity
B249.9;B823
A
1674-0092(2016)06-0022-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6.004
2016-04-27
施文斐,女,满族,辽宁沈阳人,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中文系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世白话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