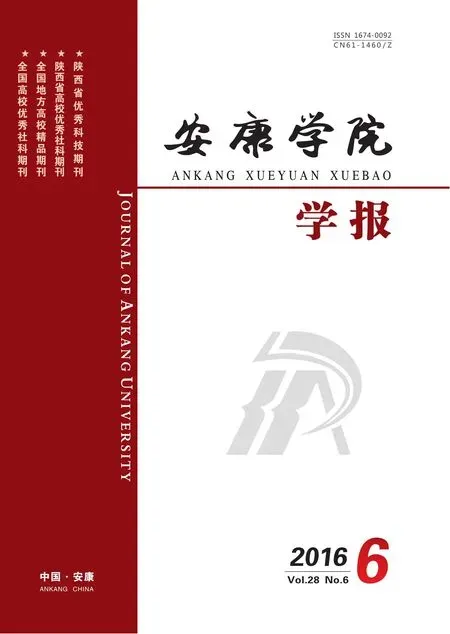《极花》:《盲山》之后,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极花》:《盲山》之后,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虽然与电影《盲山》有着较为相似的故事框架,但贾平凹的新作《极花》却并非对拐卖妇女故事的重复书写。通过与《盲山》的对比,从叙述视角、叙述立场以及大量的细节描写方面论述了《极花》的创作目的:作家希望借助胡蝶的眼光与经历向我们展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西北农村的凋敝与悲凉。
《极花》;《盲山》;叙述视角;叙述立场;创作目的
一、作为拐卖妇女的故事
贾平凹肯定看过电影《盲山》。
虽然他在《极花》的后记中告诉我们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1]91,但我们还是觉得从开头到结尾,以致故事的整个框架,胡蝶与白雪梅都是那么相像。从外出打工被骗到被拐卖西北农村,从一次次逃跑失败到被强暴怀孕,尤其是对解救女主人公的方式和结局的想象,都让人觉得《极花》不过是对电影《盲山》的文字性转述。在此,我们并不是要怀疑胡蝶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想借此讨论小说创新的可能性。
讲故事的能力对于小说家而言至关重要。虽然我们毫不怀疑胡蝶的故事来自于“十年前”那个无雨的夏天,来自于作家老乡的亲身经历,但是如何讲述一个与以往书写拐卖妇女的作品不同的故事,显然应该成为作家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当胡蝶的故事与白雪梅几无差别时,我们是否可以说作家创新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或许,贾平凹也只是从老乡的口中听到了他女儿被拐卖的梗概,因为生活经验的阙如,他只能借助于以往的作品来展开叙事。
即使把它仅仅作为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极花》也有它的自身价值。
鲁迅的高明之处在于当别人都在呼吁中国女性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时候,他却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发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作为当代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贾平凹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没有仅仅停留在人云亦云的层面。《极花》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胡蝶被解救之后生活的想象上:即便胡蝶被成功解救,她的生活还能回到从前吗?
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胡蝶做了一个梦。在被成功解救回到城市之后,她所面对的一切并不比在圪梁村时幸福多少,那情景甚至更糟:以社会良知的面目出现在她生活中的新闻采访给她带来的羞辱和伤害让她无法忍受,“我反感着他们的提问,我觉得他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个精光而让我羞辱”。当年自己以辍学为代价供应他继续读书的弟弟此刻非但不同情姐姐的悲惨遭遇,反而觉得她被拐卖非常“丢人”,“你丢人了也让我丢人!”周围的人群看她的眼光也发生了残酷的变化:“巷子里人来来往往,猛地看见了我,都是一愣,给我一个无声的笑,却又停下来回头目送。”这一切不由地让人想到五四时期的启蒙小说,对人性的批判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可贵的切入口。如果作家真的希望“在中国城与乡的轮回之中,写出一部人性深处自我搏战与修复的信史”,写出“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2],那么,上面的内容就不应该被仅仅处理成一个梦境,而应该花费比它多得多的篇幅进行详尽的刻画与书写。但是,贾平凹确实是把它作为一个梦境处理掉了。可见,作者的创作目标并不在此。
二、西北农村的凋敝与悲凉
既然作者讲述胡蝶的故事,本意不是要通过拐卖妇女揭露人性的黑暗,那作者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按说,《极花》的篇幅不长,不过十五万字,故事也不复杂,几乎如《盲山》一样,讲了一个女孩被拐卖到西北农村的故事。这样一篇小说,对于其主题的解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分歧。而事实上,虽然《极花》发表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关于它的主题解读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所引用过的,认为它是在揭露人性的黑暗。这种观点把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胡蝶被拐卖这件事上,把小说对西北农村的细节描写视为与主题无关的“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在借用这种特殊的逆城市化向度,表达作者对城乡夹缝中的人群的关切。”[3]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因为过于执著于思想启蒙的理论预设而误读了作者对乡土民俗的书写,那么,后一种观点则可能因为太过关注胡蝶“农村—城市—农村”的“逆城市化向度”而忽略了胡蝶在圪梁村的所见所闻,而这些内容在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它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胡蝶本身的故事。这一点,我们通过《极花》与《盲山》的对比可以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要拿《极花》与《盲山》进行对比?这不仅是因为二者在很多故事的讲述上十分相似,而且它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极花》的创作目标。如果说《极花》是想借助胡蝶的“逆城市化向度”关注“城乡夹缝中的人群”,或者通过胡蝶的人生经历揭露人性的黑暗,那么在《盲山》之后,《极花》的创作就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因为,就“逆城市化向度”而言,初中辍学到城市打工的胡蝶的意义远不如通过借债到城市读大学毕业后又被骗到西北农村的白雪梅典型;在揭露人性的黑暗上,《盲山》也远比《极花》来的更为直观和全面。
那么,《盲山》之后,贾平凹为什么还要创作一部与其故事框架十分相似的长篇小说呢?其实,与其说《极花》的关注重心在胡蝶身上,倒不如说作家更希望借助胡蝶的眼光与经历向我们展示西北农村的凋敝与悲凉。
三、投向自身之外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
《极花》使用的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述视角,它通过胡蝶的眼光不仅讲述了一个女孩被骗到西北农村的悲惨遭遇,更为我们展示了西北农村的落后与艰难。一般来讲,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述视角更侧重于讲述主人公自己的故事,具体到胡蝶而言更应如此。当一个花季少女的人生遭遇发生了巨大转折,美丽的人生梦想一夜之间被禁锢在昏暗逼仄的农舍中时,她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来关注自己命运的变化和下一步逃跑的可能,就像《盲山》中的白雪梅。然而,从小说的内容来讲,胡蝶讲述的更多的不是自己的故事,而是圪梁村民众令人心酸、心疼的日常生活。就是通过胡蝶的眼睛,我们看到了黑亮一家一日三餐的单调乏味、生活起居的艰难重复,看到了村民经济来源的贫乏、男人娶妻的困难、日常生活的无聊、自然灾害的严重、生活环境的恶劣,看到了老老爷的神秘威严、麻子婶的悲惨命运、訾米等人的可怜而又可悲……可以说,胡蝶对外在环境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从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述视角和胡蝶的人生遭遇来讲,这些关注都是难以理解的。如果要给这种从叙事逻辑上难以得到解释的现象提供一个理由,那只能是作者的叙述立场。贾平凹自己说“我实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1]92。在这篇小说中,他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想讲述一个拐卖妇女的故事,他还想甚至更想借助于胡蝶的眼光从一种民间的立场上讲述一个西北农村的故事。
四、民间化的叙述立场
《盲山》的叙述立场是精英知识分子式的,里面充满了思想启蒙的冲动和批判现实的眼光。黄德贵以及周围村民的愚昧与落后、与白雪梅一样被拐卖到这里的其他妇女的软弱与认命、整个乡村对教育的忽视甚至偏见……都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五四时期的启蒙小说。除了思想启蒙之外,《盲山》还在讲述白雪梅故事的同时,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严厉的批判。黄德贵的野蛮暴力、邮递员的丧失良知、周围群众的人情冷漠、基层政府的毫无作为、警察的解救不力、吴经理的丧尽天良等等都是白雪梅人生悲剧形成的帮凶。“对城乡夹缝中的人群的关切”以及“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用来概括《盲山》的主题似乎更为合适。
《极花》的叙事立场是民间的。如果说《盲山》是想通过白雪梅的人生悲剧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和批判现实的力量,那么《极花》则是希望通过胡蝶的眼睛为我们呈现中国快速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世界的凋敝与衰败。如果说《盲山》基调是悲愤的、批判的,那么《极花》则是一个站在农民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的心酸眼泪和无奈喟叹。
《极花》民间化的叙述立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叙事主人公胡蝶的视角不是投向自身,而是更多地投向了外在的民间世界。从叙事逻辑自身的矛盾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他并不想将拐卖妇女的故事如前人一样再重复一遍,而是希望借助于这样的故事框架去讲述西北民间的生命诉求。
其次,《极花》中的农民不是被启蒙、被批判的愚昧的一群,而是值得同情、值得帮助的善良而可怜的乡民。无论是黑亮一家,还是老老爷、麻子婶、訾米等人,他们都是善良的,对胡蝶充满善意、充满关心,他们在圪梁村这样一块生于斯也终将老于斯的穷山恶水中卑微地生存。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物质极度缺乏,仅有的极花也因为过度的挖掘而濒于灭绝,訾米等几个女人为了挖掘极花不得不攀爬崎岖坎坷的雪山。乡民一日三餐的主食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为了改善胡蝶的伙食,黑亮也只能到镇上购买白面馒头。这种极度困难的生活环境自然难以吸引外面的女人,圪梁村的男人为了结婚成家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努力的结果依然没有回报,娶不上媳妇的男人依然是大多数,“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连做了媳妇的也往外跑”,“这些年来,村里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光棍却越来越多”。面对现实的无奈,光棍们请黑亮爹给做石头女人,希望以此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最不济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那孤苦的灵魂。“那些还没有媳妇的光棍,就给村里的石头女人都起了名,以大小、高低、胖瘦认定是谁谁谁的媳妇了,谁谁谁就常去用手抚摸,抚摸得石头女人的脸全成了黑的,黑明超亮。”这些让人唏嘘无奈的细节描写绝不是什么“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而是饱含着作者辛酸和眼泪的深切同情和现实控诉。
再次,胡蝶逐渐在圪梁村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在电影《盲山》中,白雪梅自始至终都对她被拐卖的农村充满敌意。在电影的结尾,当前来解救她的警察问她想不想回去时,白雪梅充满愤怒地回答:“我死都要回去!他们都是畜生,不是人!”其间充斥的依然是批判与控诉。与白雪梅不同,胡蝶逐渐在圪梁村实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刚开始的时候,胡蝶就是另一个白雪梅,她对自己被拐卖的现实也充满了愤怒与反抗。“我要回去”“我要回城市去”的呼喊表达着胡蝶对命运的抗争。但是,越到后来,胡蝶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少,到最后,她甚至自觉放弃了对前来寻找自己的母亲的等待,而一步一回头地又回到了村中。当然,这中间有着太多的无奈,对逃离的放弃让她失掉了身上所有的水分,“我没有了重量,没有了身子,越走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的窑的墙上”。这种对命运的无奈认同与《盲山》的奋力抗争有着极大的不同。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在小说的前几部分,胡蝶还在讲述她用指甲在窑壁上刻痕的细节,这是为了计算她被拐卖到黑亮家的日子,比如说“差不多六个月前的晚上”她刻下了第一道痕迹,第三节她还在讲述“第二百零五天的傍晚”和“第三百零三天发生的事”,但是从第四节开始,这种有关刻痕和计算天数的讲述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思想意识的变化来讲,我们认为越到后来胡蝶打算逃离圪梁村的意识越是淡薄。反过来说,越到后来她越是认可了自己在圪梁村的身份,这在她自己的内心自问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在儿子出生之后,她曾经对着襁褓中的儿子喃喃自语:“我在这村里无法说,你来投奔我,我又怎么说呀。这可能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么”。面对胡蝶的这种心理变化,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贾平凹的一厢情愿而已,或者更尖锐一点,说这是贾平凹对女性反抗意识的一种可耻的腐蚀。一厢情愿也罢,思想腐蚀也好,贾平凹那种对农村世界凋敝与衰败的残酷现实,同情与不甘的民间立场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
胡蝶的这种身份认同是真实的吗?从其人物原型和小说的内在逻辑来看,这种真实性都是存在的。在这部小说的故事原型中,贾平凹老乡的女儿在被解救之后无法忍受社会舆论的压力,给家人留下张字条,“说她还是回那个村子去了”[1]91。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离家出走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离家之后为什么还要回到自己曾经极力试图逃离的那个村子呢?或许,我们只能说她在那里找到了温暖和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小说中,这种身份认同也有着坚实的逻辑基础。首先,胡蝶生于农村,而且初中辍学(《盲山》中的白雪梅大学毕业),从成长环境和文化层次上讲,她与黑亮并没有太大的悬殊,这就为她接受黑亮提供了可能,也为她在圪梁村找到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其次,黑亮一家对她都很友善,甚至可以说把她视若珍宝,虽然为了留住她而强行与之发生了性关系,但并没有把她看作生育的机器和劳动的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黑亮都尊重着她的意愿,让她睡在炕上,而自己则在方桌下铺了席睡。虽然她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将房间中的东西砸了个稀烂,但黑亮却并不打她,还为她提便桶、送饭食。因为油价太贵,黑亮一家都不舍得点灯,她的房间却日夜灯亮。虽然自己一日三餐都是土豆,黑亮却因为担心她吃不惯这里的饭食而经常到镇上为她买来白面馒头,黑亮爹也想尽办法变换花样,为她提供可口的饭菜。因为水很金贵,黑亮等人洗脸的时候都是一个洗过一个再洗,但每次给她打来的洗脸水却都是新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胡蝶讲给我们听的,这也就说明她从这些点滴中感受到了黑亮一家以及周围村民对她的善意,给她带来的温暖,而这些又都为她在圪梁村的身份认同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最后一个能够体现作者叙述立场的是小说的结尾。《盲山》以白雪梅砍杀黄德贵作结,明显的是一种悲剧性的批判与警示:这里没有大团圆式的解决方式,不是白雪梅被解救出去,而是双方的毁灭,电影希望以这样一种西方式的悲剧引起震撼,达到批判现实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但是,《极花》不同。在小说的结尾,胡蝶一半是无奈一半是自觉地放弃了对前来寻找她的母亲的等待。这种结尾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大团圆,虽然放弃了离开的努力,但是,从她那逐渐失去重量变成纸张的身体上,我们不难读出胡蝶内心的痛苦。它显然不同于《盲山》那种精英知识分子式的悲剧精神,当作者在后记中悲情地喊出“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的时候,作家的灵魂与西北农村的乡民贴得是那样紧,从内心深处来讲,我们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希望胡蝶能够留下来啊!
多少年来,深深植根于西北农村的贾平凹一直用自己的笔墨勤勤恳恳地书写着自己父老乡亲的生老病死,《秦腔》如此,《古炉》如此,《带灯》如此,《老生》如此,《极花》亦如此。虽然与电影《盲山》有着较为相似的故事框架,但是,《盲山》之后,《极花》讲的却是一个并不一样的故事。
[1]贾平凹.极花·后记[J].人民文学,2016(1).
[2]丁帆.贾平凹长篇小说《极花》: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N].文艺报,2016-02-03.
[3]顾超.贾平凹《极花》:沉重的现实关切[N].人民日报,2016-01-29.
【责任编校 曹 刚】
It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in the Composition—Ji Hua
XU Hongjun
(CollegeofLiberal Arts,XinyangNormal University,Xinyang464000,Henan,China)
JiaPingwa’slatestnovelJi Huaisnottorepeatthestory ofwomentrafficking,althoughitsstory framework issosimilartothe filmMangShan.ThispaperdiscussedthepurposeofJi Huaby comparedtoMangShaninthenarrativeperspective,thenarrativeposition andalotofdetailsofthedescription:thewriterwanttoshowusthedestitutionanddesolationofthenorthwestrural intheprocessof China’surbanizationwithHuDie’svisionandexperience.
Ji Hua;MangShan;thenarrativeperspective;thenarrativeposition;thepurpose
I207.42
A
1674-0092(2016)06-0018-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6.003
2016-05-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ZD089);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信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徐洪军,男,河南宁陵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