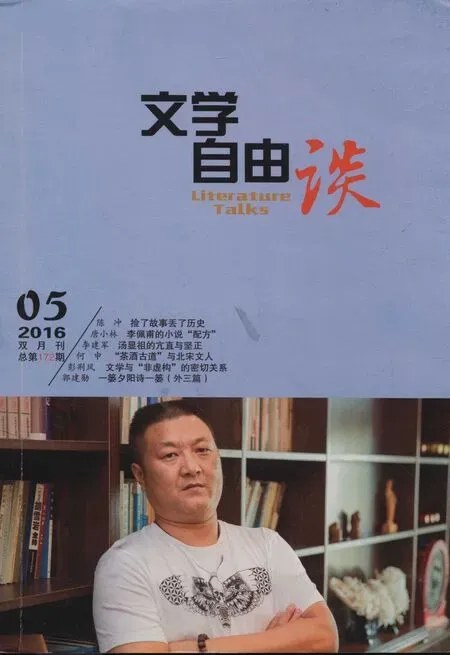文学与“非虚构”的密切关系
□彭荆风
文学与“非虚构”的密切关系
□彭荆风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945年,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入侵东南亚之时,中国政府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后派出了20余万军队,以“中国远征军”的名义前往缅甸作战。那不仅是中国近当代史上的伟大壮举,在当时更是事关中华民族安危的战略举措,也使得世界各国真切地感受到了积弱已久的中国正在奋起,并在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云南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组建、出征、进攻、败退、再进攻,并最后夺取胜利的基地(怒江以西还是重要战场),存留的史实也就很多。
我在1950年初,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后,60余年来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各地行走,接触了不少当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战后流落于滇西南边地的官兵;出于多年从事新闻、文学工作的职业敏感,对当年远征缅甸的往事也就有着较浓厚的兴趣,只是那段史实从前还是写作的禁区,从而一拖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了与这方面题材有关的写作,并于1999年7月在北京出版了以腾冲之战和慰安妇的悲惨命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孤城日落》。但是小说与纪实文学不同,即使是字数较多的长篇小说也只能围绕着一条较完整的主线构成的故事和几个虚构的人物来写;如果要全面、具体、真实地反映战争的全过程,还得采用非虚构文学体裁,严格依照战争的进程来描述众多参与了那场大战的各式人物在战争中的得失,才能够较翔实地再现那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战。
于是我又经历了近10年的思考、补充素材,2009年8月在上海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但是那部作品的题材仅仅局限于在国内的滇西战场,远在缅甸的作战、印度的屯兵,却因为涉及的人物、事件更多,战场也更广阔,而迟迟没有动笔。
我也明白,只有把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前后历时三年半的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事件写出来,才能较完整、深刻地反映中国远征军的征战全貌。于是又在2005年12月1日开始了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的写作。近十年间,前后经过七次大的修改,才在2015年2月定稿。
纪实文学虽然排除了小说的虚构与想象,但是仍然属于文学的范畴,如何读来生动、感人?作家仍然要在写作的过程中运用文学技巧来安排大至全书,小至章、节的结构,寻找、筛选能够丰富人物、事件、情节的素材。
我从多年的写作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任何文学作品中的感人情节,都是来自于生活;如果能在生活中用心寻找,同样能把非虚构性作品写得既真实又感人。所以这些年,我对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时断时续的写作,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不单纯是对文字的精心修饰,更多的是对史料的补充与核实,由于史料的增删而带来的结构的调整,行文的变化……
这虽然很麻烦,很累人,但是写作重大历史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又不得不如此。忙累之后,见书稿内容日益丰富、厚重,却是很愉快。
过去对文学作品分门别类时,还没有“非虚构文学”这一提法,而是把描述真人真事的作品,笼统地列入“报告文学”这一范畴。文学辞典的编撰者们是这样阐述“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新闻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文学体裁。是叙事性散文的一种。也是文艺性的通讯、速写、特写的总称。它要求选择真人真事的新闻材料,迅速及时地反映生活,而又必须用文学的方法形象生动地予以描述。
但是,我从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实践中来看,用“报告文学”来概括写真人真事的一切作品,是不够准确的;那些过去了许多年,并不具有新闻性,又必须是真实地书写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作品,怎么能列入“报告文学”中?而且那些重大事件中,众多性格复杂的人物,生动、丰富的情节,也不是文艺性的通讯、速写、特写式的简捷手法所能承载的。
因此,我也在不断地思考:一部长达四五十万字的纪实性作品,怎样才能不陷入冗长、啰嗦、枯燥的叙述中?作品的篇幅越长,越要具有可读性,才能吸引人们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这就要求作家在掌握了大量素材以后,在既不违背人物、事件的真实性的同时,多方寻觅、选取最能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细节、故事,并注重作品的结构,以求能统揽全局。
一提到塑造人物、描述故事,就会使那些习惯于通讯、速写、特写式写作的人联想到这是否在用小说的手法来虚构?甚至指责敢于在非虚构文学中使用文学技巧的作家涉嫌编造。但是生活中又确实是充满了有个性有特点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时间长、跨度大,人物众多,过程复杂的重大事件,更是故事多、人物性格复杂。所以作为纪实文学作家虽然不能虚构人物、编造故事,却要擅于发现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围绕着他们产生的故事。
在我国古典文学中,那些从事非虚构文学写作的前辈,早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发掘,并卓有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应该是中国早期“非虚构文学”中,既“以年为经”又“以人为经”的文学经典;那130篇、55万余字的作品,从五帝至汉初,写了那样多的人与事,多数是精品。如《项羽本纪》,通过项羽这个个性鲜明的风云人物,使读者对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争的形势、战争的残酷有了深刻了解。楚霸王项羽叱咤风云一生,可写者很多,但是司马迁只是选择其重要情节、细节、故事,来突出项羽的特异个性。例如项羽少年时代,学书不成,学剑也不成,他的理由是“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他要学万人敌——兵法。路遇巡游的秦始皇,虽然声势逼人,他不仅没有敬畏之心,反而说出了:“彼可取而代也!”从这两个细节,就鲜明地突出了当时还是个少年、未来的西楚霸王与众不同的霸气。项羽身经70余战,每一场战斗都是动辄歼敌数万、数十万,极其激烈、残酷,但是,司马迁只选取了几场有代表性的战斗来描写。例如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引领楚军渡河,从劣势转败为胜,大败秦军的“巨鹿之战”,是那样有声有色。本来是陷于失败的 “垓下之围”,却用“霸王别姬”“不肯过江东”几个情节,把一个在历史上属于失败的人物写得比胜利者刘邦还动人,使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魄能传之久远。
这是司马迁在掌握了大量素材后,运用他的文学技巧来对历史事件、人物进行结构、剪裁、抒写的作用。
远在秦、汉之际,还没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但是我们的文学先辈,就在“非虚构文学”中,熟练地使用情节、细节来塑造人物,选择故事了,并影响了后来的小说的出现与发展。
如今一些对“非虚构文学”所知不多的人,把情节、细节、塑造人物、结构故事,看成是小说家的创举、专利,那是本末倒置。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约翰·霍洛韦尔也提出了“小说家的技巧和如实客观报道的新融合”的“非虚构小说”。名为“非虚构小说”,但是有一条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作者只能是“综合了小说和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从而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
从《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古典作品开始,在写作手法上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以年为经”到“以人为经”的写作过程。“以年为经”时,条理分明,时代的发展进程清晰;“以人为经”时,那些个性鲜明、事迹突出、叱咤风云,甚至影响千古的人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发展到宋代,袁枢编著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后来陆续出现的《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等又在写作手法上有了新的开拓,进入了“以事为经而始末具载”的非虚构文学新领域。
这“始末具载”的写作手法,融合了前人编年、写传的特色,把事件充分展开来写,也就使得所写的题材中的情节、人物、故事都能更加详尽地得到体现。那些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精心描述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人物,选取既真实又生动的故事来感染读者,引领读者进入深层次思考的历代“纪事本末”,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司马迁以来,优秀的“非虚构文学”,我们应该认真研读,定可从中得到启示。
我在1987年至2009年写作、修改那部55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时,就是采用了中国古典纪实文学和约翰·霍洛韦尔提出的“增加‘非虚构文学’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的写作手法,才引起了众多读者的浓厚兴趣。但是也有人,对我运用小说技巧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一位评论家就武断地认为:“有过度想象或虚构之嫌,如大量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而缺少相应的注释或引文说明,似为历史小说之作法,令人有编造、杜撰之嫌。”
他对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的要求,可以理解。但是我确实是信守“非虚构文学”必须遵守的“拒绝创造非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原则,根据史实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
例如对于《解放大西南》中用了较大篇幅描写的领导云南起义的卢汉将军,就有人在既承认这位重要人物描述得真实、性格鲜明的同时,又提出怀疑:“他起义前后的犹豫、彷徨心态,与一些人的对话,是从哪里得来的?这在当时都应是绝对机密,你怎么知道得那样详细?何况你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当时还远在几千里外的赣粤边境。是否有所虚构?”
我告诉他们,那都有出处。有的是采访他从前的部下得来的,有的来自他们的回忆录;特别是最接近卢汉将军的两个警卫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当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卢汉那一阶段的言行,都被秘密监视并每天写成报告送与中共地下党领导,如今还留存于有关云南起义的历史档案中。别人写到有关西南的解放时,只能粗略地写个大概,更无力表现卢汉这位重要人物在起义前后的复杂心态,是他们没有深入采访、寻取。我却是用了许多年时间上下求索。
我当然也可以把《解放大西南》中那些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如那个评论家所要求的,每一段都加以相应的注释或引文说明。但是这不是一篇仅有几千字的学术论文,而是一部长达55万字、有着600多个人物的长篇纪实文学,如果把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注明引文出处,又将要增加三五十万字的篇幅。“附属品”那样多,出版社愿意出版吗?读者愿意买吗?
我们再看看《左传》《史记》《汉书》《宋史纪事本末》……那些古典纪实类作品,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也没有逐一注明引文出处。《史记·留侯世家》中,写张良在袭击秦始皇后,亡命下邳,在一座桥上遇见黄石公,黄石公三次把鞋子丢往桥下,要张良给他捡起来,再给他穿上,又三次约会,以考验张良的真诚,最后才满意地认为“孺子可教”,赠予《太公兵法》。前后几天,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那是谁把这段奇遇告诉后人的呢?没有注明。《项羽本纪》中,项羽在乌江边与乌江亭长那场充满英雄气概的“不肯过江东”的对话,是谁传下来的?是乌江亭长?是项羽立有遗嘱?司马迁也没有注明。再如《史记·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多次与田光、荆轲分别密室长谈;《汉书·苏武传》写李陵去北海与被流放在那里的苏武见面,都是左右无人,几十年后的司马迁、班固,却写得很翔实,肯定有事实为依据。我们能因为他们没有在文章之后注明是谁传播出来的,就说是他们在编造、杜撰?
如今我写作这部《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也是因为自感掌握了大量素材后,在情节、细节的运用,人物个性的抒写,故事的铺陈等方面能够比较从容地描绘,从而促使我这个写作小说多年的作家,再次放弃小说的体裁去写作这部非虚构文学。
在坚持史实的真实性的同时,充分运用文学技巧把所写题材中的人物、事件写好,写得动人,既具有文学性又有可读性,应该是我们从事“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作家不懈的追求!
(本文系作者《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一书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