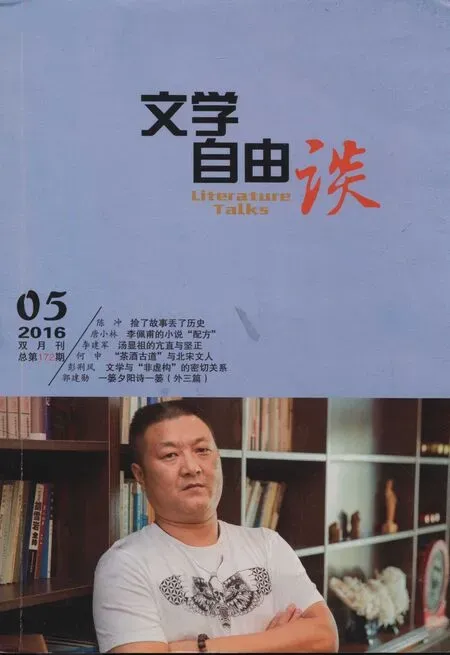在龚自珍与鲁迅之间“扯扯淡”
□陈歆耕
在龚自珍与鲁迅之间“扯扯淡”
□陈歆耕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但恐怕没有人会记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思想启蒙大家和诗文大家龚自珍逝世175周年。因为陈漱渝先生和我今年分别出版了两部历史文化名人传记 《搏击暗夜:鲁迅传》和《剑魂箫韵:龚自珍传》,在上海书展上,作家出版社总编辑黄宾堂出了个题目,请陈先生和我座谈,这个题目叫——从龚自珍到鲁迅:串起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
这篇“命题作文”犹如一个庞然大物,再长的手臂恐也难以将她拥入怀中。仅仅是一个龚自珍,或一个鲁迅,即使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能理出一个头绪来,更何况将两个人“串”到一起?再加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时必须结束,还得留半个小时签售,因此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只能在10分钟内。如此这般,除了“扯扯淡”,还能干什么呢?记得曾有美国学者写过论著《论扯淡》,非常畅销;接着又有人写了《论为何要扯淡》,也畅销。可见“扯淡”是个世界级的现象,非本国特色,因此用不着为此而感到有什么不安。高官们在主席台上“扯淡”,学者、评论家、作家在各类论坛、研讨会上“扯淡”,因此常有这样的尴尬,参加一个什么研讨会,扯了半天或一天,过二日竟想不起究竟“扯”了些啥。
出版社出了咱的书,既然有此要求,就得配合,抡起胳膊使劲地“扯”。这是一个宏大而非常有深度的话题。我想,虽然有人写过关于龚自珍和鲁迅比较研究的博士论著,但要梳理清楚这两座思想高峰之间的精神脉络,可能写多部专著,怕也难以说清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部中国近代史拉开序幕,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开,中国进入了痛苦而痉挛的历史转型期。在此多年前,龚自珍曾发出过忧心如焚的醒世预言和嘶喊,可是他的剑气箫音,无法激活大清王朝昏庸的睡眼。一部近代思想史,是从龚自珍的嘶喊开始的。发人深思的是,一个多世纪后的鲁迅,同样也身处重大的历史转型期,他拿来许多别国的理念,同时也承续了龚自珍等许多前人的启蒙思想,成为另一座思想、文学的高峰。这个高峰,至今无人能超越。
当我们在思考当代文学为何缺少像龚自珍、鲁迅这样的大师级别的作家时,让我再次坚定一个想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未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定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思想的贫乏和缺失,正是当代文学最大的软肋。当代文学要从高原走向高峰,首要的就是为创造者注入有温度的血液和有硬度的钙质。
我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因偶然的机遇,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1974年底,我从苏北农村参军到东海舰队后勤俱乐部。那是一个书荒的年代。正好俱乐部图书馆里有一套《鲁迅全集》,我那时几乎是囫囵吞枣般看了其中10卷鲁迅创作的文字和部分翻译的文字。毫无疑问,在写作龚自珍传记之前,我对鲁迅的了解要多于龚自珍。在2012年我开始接触龚自珍的史料时,常常有如同梁启超所说的“若受电然”的感觉。为何经历两个多世纪,龚自珍的思想仍然还能撞击我们的神经?这是我常常要思考的问题。另外,我发现,鲁迅的很多思想确实熔铸了龚自珍的启蒙思想元素。从龚自珍到鲁迅,这两位思想和文学大家,有太多可以对接、关联、相融的地方。
虽然,从现有的史料看,鲁迅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及龚自珍的文字。王元化先生曾撰文对此提出疑问,他的揣测是,章太炎当过鲁迅的老师,而章太炎因与龚自珍分属不同的学派而骂过龚自珍,因此,鲁迅对龚自珍的评介保持沉默。但这也仅仅是揣测而已。在鲁迅多位友人的诗和文章中,曾提到鲁迅对龚自珍诗文的喜爱,如沈尹默在怀念鲁迅的诗中说鲁迅“少年喜读定庵诗”,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提到鲁迅的一首纪念杨杏佛的诗“才气纵横……无异龚自珍”,唐弢在《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中说:“先生好定庵诗。”
其实,从这些考据式的史料中,我们并不能清晰梳理出龚自珍与鲁迅之间的思想脉络。这里,我从他们的诗文以及生平形迹中寻丝觅迹,来提供几点我的个人感悟——从思维方式、重要思想关注点、思想资源的异同,来看两位巨人相通、相融的地方。
首先是思维方式。我曾在《龚自珍传》中写过类似的文字,认为龚自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和整个诗文。在龚自珍的诗文中,当然也有纯粹写情感的部分,比如他在辞官南返后写的大型组诗《己亥杂诗》中,有不少是写他与一位青楼女子灵箫之间的情感。但他的主要代表作品,都是充满批判力量的。他批判整个士人阶层良知的缺失:“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他批判整个时代人才的平庸,平庸到不仅朝廷无贤臣良将,就连偷技高明的盗贼也没有;他批评扼杀人才的文字狱,使得“万马齐喑”,士人们“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他批判官场普遍存在狮子猫人格,他们不会捉老鼠,但非常擅长讨主人的欢心;他批判封建专制集权制度使得士人们一个个都成了扭曲的“病梅”……
至于鲁迅,他一生也都在进行社会批判,无论他的杂文、散文、小说等,都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林语堂先生在鲁迅逝世后写的不算悼文的“悼文”《鲁迅之死》中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这里,语堂先生用酸溜溜的口吻,无疑是说:“这个鲁迅呀,无非就是一个好斗的人。如果找不到可斗的对手,就是捡块石头打打狗,也是很快活的。至于是不是文人,是可疑的。”我这里想说的是,语堂先生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文人的,即使像你这般的大作家等级的文人也是不缺的,哪个朝代都可以抓出一大把,而缺的偏偏就是有热血、有心肝、有豪气、敢亮剑的“战士”,更缺的是战士型的文人。语堂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的差距恰恰就在这里。龚自珍与鲁迅同属战士型的文人。
龚自珍与鲁迅在思想关注点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在梳理龚自珍的思想脉络时发现,龚自珍的思想是有一个主要聚焦点的,那就是人,人才,人格。他的所有批判性思维皆围绕此轴心展开。他衡量一个朝代盛衰的标准是什么?是这个朝代拥有什么样层级的人才;他考量一个朝代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准是什么?是能否让真正的优秀人才尽其所能;他测量一个社会是否充满活力的标准是什么?是这个社会国民是否具有理想的人格。龚自珍的那些著名的诗文,如“九州生气恃风雷”,以及《明良论》《山中之民》《病梅馆记》等,其题旨谈的都是人,或是批判扼杀人才的机制,或是呼唤身心健全具有理想人格的国民,从山野间涌现。至于鲁迅,读者都非常熟悉,我只是稍稍点到为止。他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揭示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吃人”。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主人吃奴才,奴才相互间也在“吃”,被“吃”的“人”,也在“吃人”。狂人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他一生都在用笔致力于掀翻这“吃人的宴席”。鲁迅先生对麻木不仁的“看客”痛心疾首,正是因为“看客”现象的刺激,导致他弃医从文,致力于从精神上疗治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他认定,中国的问题,“其首在立人,人立然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再次,龚自珍与鲁迅的精神思想资源有相同之处。由于他们所处时代各异,他们汲取的精神营养的来源自然也有所不同。龚自珍自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实,他是以“古时丹”来做挡箭牌,他的思想主要还是来自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过人的洞察力。他批判的所有社会痼疾,他发出的“衰世”信号,均有现实的依据。他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始终充溢在他心中。我听到当下有学人说,伟大的思想家只有一种,那就是忧天下,而非忧君王。这样的划界,似乎过于绝对了。所谓忧天下是“忧”什么?具象化地说就是“忧苍生”。如果一个君王,“不问苍生问鬼神”,那他的社稷还能存活多长时间呢?这时有诸如龚自珍这样的智者提醒他,请“圣上”不要整天沉醉在三宫六院中、酒池肉宴上,看看老百姓已经饿殍千里,尸横遍野了,老百姓一造反,就要天下大乱啦!你说这样的智者,是忧天下,还是忧君王呢?因此,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中有非常复杂的元素,需要我们仔细甄别,而不是做看似斩钉截铁,其实并不周严的判断。鲁迅的精神思想资源中,除了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外,他与龚自珍不同的是,透过洞开的中国大门,有许多外来思想可以引进,面对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大量优秀思想成果,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最可贵之处也是,甭管是“古时丹”还是“拿来”的火种,与龚自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力。他的杂文、散文、小说,都是针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因此能够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其独立思考的人格。这使得他的思想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闪烁不灭的光亮。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文学家,一旦丧失了对现实的洞察力,他的精神力量必然弱化,他的人格形象必然矮化,他被读者边缘化也就是必然的了。
有记者问,将龚自珍和鲁迅串到一起,对于当下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今天又应该以怎样的眼光和立场来读龚自珍的作品?
说到“现实意义”,很多人常常到此就戛然而止了,至于这“现实意义”的内涵,就留给读者去感悟了。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思想启蒙大家,他发出诸多醒世嘶喊,曾经开风气之先,为驱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动力;而鲁迅身处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激荡的时代,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的一生也在从事唤起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当我们在梳理龚自珍到鲁迅的启蒙思想的脉络时,就会发现,他们最为忧心的许多问题,仍然在困扰着当下。因此,有专家在研讨《龚自珍传》时认为,启蒙问题在中国始终是一个未能解决好的问题。
龚自珍自称“药方只贩古时丹”,我是不赞成照搬“古时丹”来解决当下现实问题的。先贤的智慧、思想要借鉴,但解决当下的种种困扰,需要从实际出发,寻求新的路径。即使在写龚自珍传记时,我也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借古人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一切评析、论断、感悟,都必须有坚实的史料做依据。只要你的心中有“现实感”,文字、史料的背后自然就会有充沛的“现实感”在流动。
至于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读龚自珍的诗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千个人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读《红楼梦》,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会从中读出不同的“符号”来。当代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当代人的眼光当然也就因人而异。你能从龚自珍的诗文中读出什么来,也就与自身的学识、修养、人格境界等等有关——有的人读出启蒙思想,有的人读出“丁香花绯闻”、猎艳高手,有的人读出“哀艳杂雄奇”的诗词才情,有的人读出“怪魁”的荒诞行止……不管怎么读,我都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读龚自珍,这样才有可能有更多的人走进龚自珍浩瀚博大的精神世界,让龚自珍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在更多的人心中矗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