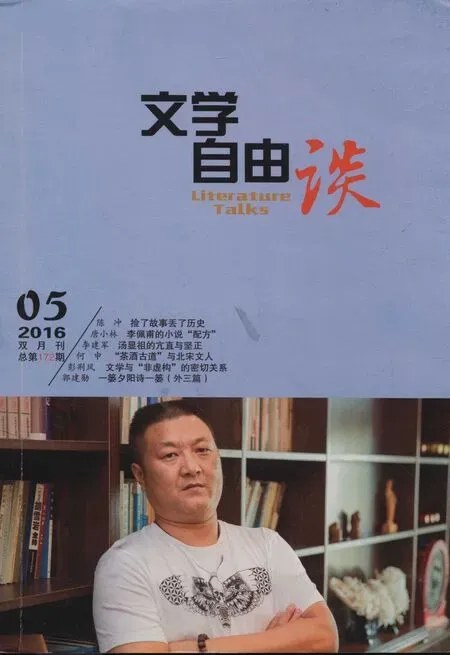名居(外一篇)
□李更
名居(外一篇)
□李更
如今,余秀华已经非常习惯村干部笑嘻嘻地来她家问寒问暖了——她靠在依旧破旧的旧屋廊柱,想必心态也是非常轻松的。
其实不光是村干部,乡干部也经常来,还有钟祥市的干部。有人说,钟祥人都有十分强烈的出名欲望,而且有十分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倔强性格。从建制上讲,钟祥市是荆门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是钟祥人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荆门人,因为无论经济、历史还是文化、教育,荆门对比钟祥都乏善可陈,而且,钟祥是出过皇帝的地方——明朝嘉靖皇帝就是钟祥人。
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人士余秀华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倔强的性格。她谁也不服,颇有“一言不合就开骂”的劲头儿。十里八村,一些下乡干部也知道那里有个喜欢骂人的 “苕”女人——湖北话,“苕”是傻子的意思——见到她就绕道走。不过,也有村民说,她一点都不“苕”,“贼”得很——贼,湖北话,狡猾。
以前,余秀华多少年都出不了横店。每天她走得最远的路,是从家里磨蹭到村头,看别人下象棋。但她比别人知道的多。那个时候,北京、上海,于她就像火星、土星于我们,她知道,但也仅只是知道有那么个地方。
现在,她已经成为空中飞人,可能上午还在北京,下午却在上海,前天才离开广州,今天又来广州了。我说你还没走吧?她说昨天回了一下横店——武汉人从武昌到汉口好像也没有她那么快捷随意,尤其是,她的出发地是横店。
忽然觉得,余秀华就像《北京折叠》中的人物,穿越在不同的城市空间。她属于完全不同的阶级,并且代表不同的阶级出席不同的场面。荆门出去不少农民,在武汉发达以后,回来就不习惯农村生活了,甚至一些人在武汉文坛混出名堂成为了诗人,整天就往文豪的地步打扮自己,头发怎么留,胡子怎么剪,做派怎么样,以为这就是城市人的范儿。
余秀华一回到自家的院子,就和横店浑然一体,特别舒服。
最重要的是,她不装样儿——不是不会,而是没有必要。不像那些在武汉混出来的农民作家诗人,首先要声明自己不是湖北人,而是哪里哪里大码头的人,甚至是上海人。你以为你穿了马甲别人就不认识你了?余秀华最讨厌数典忘祖的人。
所以,当地的文化人觉得余秀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个一说喝酒就手舞足蹈的余秀华。在余秀华那里,省作协领导的面子绝对没有当地干部的面子大。
不过,从贫困中过来的余秀华,把钱看得非常重。一说到钱,她就严肃了,就认真了。我给她算了一下版税,说,你可以在武汉买房子了。她眼睛一瞪,你给我钱?她现在经常来往武汉,主要还是因为母亲在武汉某医院住院,前几天还为费用的事情与医院发生了摩擦,她为此发了微信圈。
但是,她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笑她现在是纸醉金迷了。她经常形容自己,才下五粮液,又上二锅头。我说,才下灶台,又上茅台。
表情就是那么夸张,瞬息万变,一波三折,令人悲欣交集。什么傅园慧?她是表演好不好?她只适合低级别喜剧。余秀华才是原汁原味与生俱来。傅园慧才有几个表情包?余秀华一分钟一个,步移景换,并且,天然去雕饰。
关于担任钟祥作协副主席,余秀华给了个无所谓的表情包。但是现在正值荆门市作协换届,分管的宣传部副部长说,秀华,还是来个副主席吧。她马上问,有编制没有?领导笑,何必在意这个呢。怎么不在意?有工资啊。又是一种表情包。
我插一句,就给个主席吧。领导说,秀华那个身体,怎么能干具体事情?我说,主席都是挂帅的,另外找办事员嘛。领导说,你别看我们这个地方小,全国性的著名文人可不少,你要不信,上网查查。
既生瑜何生亮,已经有不少诗人悲叹自己的命运:怎么和余秀华生在同一个时代?本来,他们和其他诗人只是竞争关系,现在,他们和余秀华竟然是遥望关系,都不是被甩几条街的问题了。他们现在唯一思考的是,她的风头什么时候过去?就像等待台风过去一样,台风过去了,他们再上路。因为不管他们怎么折腾——搞什么现场裸诵啊,对名人故居罗嗦自己的诗歌啊,对诗歌进行新的定义啊——余秀华一概嗤之以鼻:什么鬼截句,酒不好,换什么瓶子也没有用。
现在的问题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余秀华这个中国诗歌的魔头放出来了,还想让她回去吗?
有人开始拿她和当年的舒婷类比。已经可以确定的是,余秀华的诗集是近20年以来大陆卖得最多的诗集,这对今天门可罗雀的诗坛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要知道,当年舒婷诗歌大卖时节,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十年”,诗歌成为一种群众运动,狂飙突进,而且,当时也不是舒婷一人,北岛、顾城比舒婷更火。之后的海子就差了很多。而今天,余秀华是一家独大,虽然那些报刊,那些宣传平台还是掌握在打油者的手中,但是,话语权已经开始转移了。
认真分析,舒婷在短暂的爆发期以后,很快呈断崖式下降。再然后,诗歌完全不行了,写散文,流水账一般。现在,只能靠吃老本。
余秀华却还是穿越中国的态势。她居然也可以批判现实主义。她的那些时评类诗歌,甚至比她个人化写作更有时代痕迹。她的写作已经开始多元化发展。她的散文,我觉得比诗歌更有语言张力,内容更为丰富丰满,并且仍然锋芒毕露。
现在,当地一个公司专门给她成立了余秀华工作室。
那天遇到一个发了大财的老板,重新开始年轻时的文学梦想,要把自己当年送外卖时住过的楼买下——当时,他只是蜗居其中的一个农民工。他说,那是我的故居,要保留,说不定哪天我也诺贝尔了呢。
故居保留的前提,好像应该是独栋、平层,还要有原生态。看余秀华的家,这个院子倒合适。城市那些高楼大厦,几十上百家的,怎么会因为你住过就保留?当然,除非你自己买下来。
不管怎样,荆门钟祥的旅游,已经开通两个点,一个是嘉靖皇帝为他爹做的显陵,一个是文学青年喜欢的余秀华的家,横店村。
关于黄春炳的小说
我喜欢旅行,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让我高兴,这种高兴源自在当地认识的朋友。好像是一种习惯,无论到哪里,都会下意识地想到这个地方的文化人、文人。因为我旅游的目的,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地理的。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看一个地方的综合指标,经济、政治、民生都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的痕迹都容易清除,但是文化不会,因为文化是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即使文化的物质形态灭失了,也还会形成一种口碑,一种传说。所以,文化的意义永远大于物质的意义,虽然文化是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当年的扬州,曾经因为盐商的作用而经济繁盛一时,而同时,也是凭借盐商的雅好,带动了文化的风生水起,汇聚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今天,盐商已去,杳如黄鹤,而扬州八怪却永远留存下来,成为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符号。
什么叫文以人传?一个地方的文化是靠人传播的,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传承的。所以我到了斗门,就会自然地想到两个人:邝金鼻、黄春炳。
斗门是珠海的一个区,这是行政区划的概念;实际上,我认为从文化的意义上讲,斗门的独立性是很强的,甚至强到可以独立于珠海的文化板块之外。别的不说,单说语言。我到珠海一年,就把广东的白话学会了,但是,三十年过去,我仍然搞不懂斗门话。斗门的方言是自成一体的,仅仅离开香洲二十公里吧,已经让我感慨“十里不同天”了。那种混杂着客家话的白话,甚至我感觉还有点桂柳方言的痕迹,甚至每一条村(斗门的村子以“条”论)的方言都有明显区别。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斗门给我的陌生感就像是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区。那里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没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就像一个过于固执的人,其不可改变性恰恰在今天表现为个性鲜明的识别性。我曾经为了认识斗门,专门去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住在当时的县委招待所、长途汽车站旅馆,甚至住到村住到组——在偏远的六乡镇小托村,我在那里驻点扶贫一年,被成千上万的蚊子咬得浑身是包。当时的扶贫有个名称:农村基层组织改造工作。我经常组织村干部开会,而大家全部用土话交流,这真让我欲哭无泪。
后来我认识了斗门大文豪邝金鼻。他的鼻子永远是酒后那种红彤彤的,有时在夕阳下,真的带有金子的闪光。他笑眯眯地教导我:你还要继续在斗门呆下去,因为你还不了解斗门。
斗门人有北方人的性格,粗犷、直爽。后来我忽然发现,老邝的创作居然都是以中国北方为题材背景的,写了大量的阿凡提寓言。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广东农民,居然蒙蔽了如我这样的大批北方人,匪夷所思吧?我在来珠海之前,就读过大量的阿凡提寓言,可以说,阿凡提寓言是中国孩子基本的启蒙读本;而在我们读到的关于阿凡提的传说中,就有邝金鼻的贡献。走到今天,老邝的创作仍然是唯一代表珠海文学在中国北方被认可的成就。
后来,我认真读了邝金鼻的寓言作品,才发现,他的作品里其实包含了许多斗门人的智慧和民风,是了解当地人性格的地图。应他再三要求,我写了一篇读邝金鼻阿凡提寓言的心得体会,没有想到交卷以后他就去世了,成为斗门的文化先贤。
邝金鼻生前曾经跟我特别提到他看好的一位斗门作家——黄春炳,一位地道的乡土作家,也是他多年老友。
我做副刊编辑几十年,最大的乐趣是读到一篇好稿,最大的好处是在乐趣中还能发现民风民情。黄春炳的写作恰好在这方面有着比较完美的体现。
和邝金鼻的创作完全不同,黄春炳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写小说。他的作品饱含了斗门的地气,我甚至是在他的小说中重新发现了斗门,认识了一个个鲜活的当地人物,了解了一件件当地的事物,品尝了一种种当地的食物。
黄春炳的小说,以短篇为主,更有不少小小说。一些篇什,我认为还有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遗风。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黄金十年时期的文学青年,一直到现在,仍然固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读黄春炳的小说时,我常常与其呼吸相通。我觉得他也是现实主义,而且对于今天社会的腐败现象,还持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读他的小说,让我不自觉地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写作手法承继传统,没有那么多天马行空,没有那么多现代后现代的花里胡哨的文学概念,就是写实,甚至就是扎扎实实的白描。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一下,小说创作的基本功就是白描,这个写作基础就像绘画中的素描和速写。离开基本功去追求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首先你得把人画得像吧?可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急功近利,具象的还没有过关,就开始抽象了,结果邯郸学步,爬都爬不回去。
所以,有时我就拿黄春炳的小说当教材,看看同样是生活在珠海、生活在斗门的黄春炳,是怎样写生自己所面对的农村、城市。他笔下有善良的妇孺,有奸诈的贪官,有泼皮的牛二,有转型为城市人的“农二代”……这些人物呼之欲出,栩栩如生。
特别接地气的,还有他对语言的运用。他的叙述经常巧妙地夹杂着斗门方言,不多,一点点,就像纽扣缝在衣服的关键部位,恰到好处地承上启下,呼应此时此刻的语言环境,实用,并且闪闪发光。语言是文学的载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是语言的发展。在生活中发现民间口语,并且适当应用到文学创作中,是丰富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很多文学大师,其实也是语言大师,一个名词,一句俚语,如果因为你的文学创作而流行社会,甚至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你就是文化的成功人士。
年逾花甲的黄春炳第一次出版自己的著作——《春暖花开》,就和盘托出自己的小说,我想是十分有意义的。这本小说出版的意义不光是黄春炳的,同时也是属于斗门的,对我们体会斗门的文学、斗门的文化,套用一句老话,是开卷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