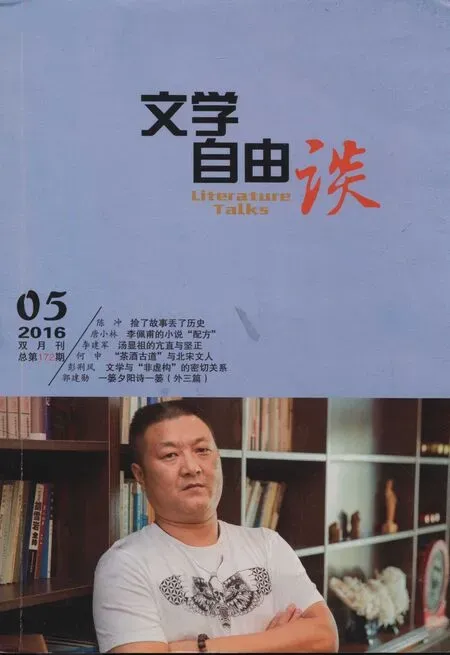捡了故事丢了历史
□陈冲
捡了故事丢了历史
□陈冲
我省文学院实行导师制,将我也定为导师之一,从此便被一个问题困扰。过去自己写小说,怎样才能往好里写,自个儿慢慢琢磨就是了,现在却要跟别人说怎样把小说写好,怎样才能写出好小说,这、这、这却从何说起?直到前不久,这个问题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似乎有了一个标准答案。在各种的文件、新闻、报道、座谈、论坛乃至绝对符合学术标准的论文中,都频繁而反复地出现了一种说法:讲好中国故事。晚近则更有新发展,即如我的已故太太的老家,最近开了一个“峰会”——敢称“峰会”,到会的自然都是各路的顶尖高手,大家不远千里万里地聚到一起,据报道“探讨”的问题就包括“怎样讲好宁波故事”。如此看来,问题真是变得简单了,再有人来问我怎样写好小说,答之曰讲好中国故事、本省故事便是了。
问题在于:这样真的就能交差吗?
而新近出现的一些故事,则让我更加心存疑虑:这样只着眼于故事,会不会捡了故事却丢了历史?
故事之一,是前不久看到,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在一次讲座中说:“高薪养廉是个伪命题。”他举北宋为例,说北宋官员的俸禄很优厚,但贪腐盛行。为此他讲了个故事,说“包拯的年薪——折合人民币650万元”,然后问:“一个副省级官员,如果拿包公的工资,那税收得有多少?老百姓能否承受?”于是得出结论:“高薪未必能养廉,低薪肯定不养廉”,“反腐倡廉的教育是学习历史”。
一条很长的逻辑链,最后落在了“学习历史”上,绝对突出了历史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我的逻辑感觉告诉我,“故事”和“历史”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同一。如果在逻辑推导中用前者“顶替”了后者,那就很容易发生“捡了故事丢了历史”之类的安全责任事故。如果那个“故事”再是虚构的,或假装非虚构的,那就很可能酿成一次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捡了一个靠不住的故事,却丢了一大片历史。
包拯的年薪到底有多少?真能折合人民币650万元吗?不知您知道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可以上网查。以前得查文献,这类的活儿,没有十天半月查不清;现在上网查,虽然不如查文献严谨,不能算是做学问,但要把事情整明白,一个小时足够了。不料这一查,又查出了另外一个小故事。原来早在一年前即2015年,就有人引用一篇二十年前的旧文,批驳了二月河的类似说法。然则二月河这回的讲座,只是将已被批驳过的老调又重弹了一次。当然,著名作家一般都不怎么拿批评当回事儿,压根儿不知道亦未可知。
还是回到故事的核儿——包拯的年薪。从网上提供的资料看,当年包拯的工资单并没有保存下来,只能以他的级别去套当时的工资标准。流传下来的这个工资标准又并不“标准”,只能算个大概。包爷的官,最大当到枢密副使,略相当于今之国防部副部长,即二月河所说的副省级。可是在那个工资标准里,没有枢密副使的,只有枢密使的,而且不一致,有说月俸四百千钱的,有说三百千钱的。为了往高里说,且取其高者,再以“副”取其低,定包爷的月俸为三百千钱。虽然这里面已经有了若干个猜测和假设,不管你认不认,反正我认了。无论如何,这还是比较靠谱的。从逻辑上说,就拿它当作一个无需证明或不证自明的前提吧,往下就是换算了,即,它是怎样经过一回回折算,折合成年薪人民币650万元的。
首先得把铜钱折算成银子。按史书中的官方说法,是一千钱兑白银一两。这个好算,三百千钱,就等于白银三百两。对于一般读者,即不懂经济学,不了解古代经济学,或者说认为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读者来说,这儿不存在任何歧义;但是如果我们动动脑筋,问题就来了。铜钱是一种货币,它在流通中体现的交换价值,是人为赋予的,与它的实物(铜)的价值两码事。而白银却是一种贵金属。按史书的记载,中国发行货币实行银本位制是从元朝开始的,那么在之前的宋朝,白银就是一种纯粹的,或者说与货币完全不挂钩的贵金属,它的价格是由自身的供需关系决定的。按史书记载,正是在包爷每月领取三百千钱俸钱的那段时间里,由于白银的产量跟不上需求的增加,价格不断上涨,涨到了两千钱才能买到一两白银。如果依实按此折算,包爷的年薪立刻就只能折合人民币325万元了。
折算成白银以后,再按其购买能力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需要一个中间物;从网上提供的换算资料来看,这个中间物被选定为“米”。我对此无异议。此物为那时的人和现在的人同样不可或缺的生存必需品,自然那时和现在也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因而也有一定可比性的价格。可是尽管如此,这个折算还是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在去掉一些不确定因素后,资料显示宋时一两银子可购买米4至8石。问题是现在已经不以“石”为计量单位了,我们给出的数据只能是1斤米价为人民币1.5元至2元。问题就出在如何将宋时的“石”折算为现在的“斤”,出在了存在两种并行的说法——一说一石为96斤,一说为132斤。按前者算,一两银子折人民币672至1344元;按后者算,折人民币924至1848元。您圣明,最低值与最高值相差近三倍——这意味着包爷的年薪又有可能只折合人民币不到150万元,即还不如现在的某些央企高管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折算法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而且看上去也是比较靠谱的。可是按这同一个折算法折算出来的结果,竟然是在唐朝时一两银子折合人民币高达2000至4000元,明朝时降为600至800元,而到了清朝只有150至220元。这跟我们看武侠小说所得到的印象相差太大了。看《射雕英雄传》,郭靖向怀里一摸,就掏出二十两银子;看《三侠剑》,胜英向怀里一摸,掏出的银子也是二十两。谁也不会去想,这胜英的二十两竟值不到那郭靖的二两。可是遍查史书,又找不到不断大量发现银矿,致使白银越来越不值钱的记载。
在中国的历史里,各时期的消费品价格水平,各种流通货币间的折算,就是这样一笔“大概其”的糊涂账,而在各种“中国故事”里,这笔账却是相当清楚的,不然怎么会有“包拯的年薪——折合人民币650万元”这种“非虚构”?捡到这个靠不住的小故事之后,我们就丢掉了一大片历史。首先,我们丢掉了中国古代长时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经济学的历史。那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在制订相关政策时,都是只考虑如何搜刮民财以充实国库,从来不觉得还需要什么“学”。与此同时,我们也丢掉了这个漫长历史中的一次短暂的例外,丢掉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伟大(没有之一)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叫阿合马。他在七百五十多年前的元初,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早发行纸币的成功先例。与南宋发行的纸币总是迅速大幅贬值不同,他发行的纸币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建立了银本位制,即为纸币的发行建立了足够的白银储备。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要到四百年后,西方人才明白发行纸币必须有足够的贵金属储备的道理,而阿合马是怎样提前四百年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史书即付阙如。从后来的事实看,要保持纸币的币值稳定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正确计算货币的总需求量和总发行量。阿合马显然会算,但他是怎样算出来的,现在已无人知道。不过,二月河这个小故事最直接地丢掉的历史,则是中国古代的历代统治者从来不肯实行高薪养廉的历史。时至今日,高薪养廉几乎已是全世界公共政策制订者的共识,唯独咱们有些人持怀疑态度,说“未必”。什么叫“未必”?所有拿高薪的人中没有一个贪污受贿的才叫“必”,出了几个贪官就“未必”了?就是这种逻辑。而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高薪能不能养廉,而是过去历代统治者愿不愿意用高薪去养廉。他们不愿意。给官员们发高薪,那个钱是要从国库里支出的,而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是他们自己的钱,多花了心疼,万不得已时给有限的高官多发一点,大量的中下级官员绝不多发,不够用时自己去想办法,也就是去向民间搜刮。这个他们不心疼。不仅是这些官员的家用,即便是办公的开销,甚至办事的人员,也是只给一部分。你看那些衙门里,不仅有吃官饷的在编制的“公务员”——称为“属吏”,往往还得有一帮由主官出钱聘用的 “编外人员”——称为“幕僚”或“宾客”,这才能把该办的事办好。捡拾起这些历史,你才能明白那些“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是怎么来的,才能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总是置疑高薪养廉了。
时势造英雄,一批讲故事的能手正在应运而生,把故事讲得越来越让人痴迷。
但时势同时也会造出取巧者。在越来越多的让人痴迷的故事里,不见了历史。
这也是一个中国故事,里面充盈着中国的特别国情。特别在哪里?在这种“叙事”里,故事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历史的生命力在于“真相”。这个嘛,看上去也还挺靠谱是不是?麻烦在于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里,“真实”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在近百年来的文学理论中,现实主义是无可置疑的主流,而至少在其中的后七十年里,作家们的现实主义书写,却几乎总是得不到理论上的认可。这个相当离奇的故事情节,让人不能不想到,在不同的人那里,存在着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完全不同的定义。这中间还涉及另一个猴皮筋概念:“生活”。此类离奇情节中往往会有一个高潮,就是向作家厉声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对于作家来说,这种问题基本上是毁灭性的,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有段时间,很明确地提出来,创作要上去,作家先得下去。就是得深入生活。还不是一般的深入,而是要“三同”,和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才能了解到现实。近读《阿城文集》,阅至内中说到有一种“指定现实主义”,不觉哑然失笑,颇觉是一种生动、精准的描述。虽说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并不是要把你看到、听到即亲身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而是要去发现那些“指定”的现实。最近在纪念柳青,我觉得很有必要。柳青的经典性就在于,他没有去“三同”,而是干脆把家搬到农村去,并且特别擅长于把亲身感受到的东西,揉合到指定的现实中去。等到那个指定的现实失去了指定的合法性以后,那些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仍能保持一定的审美价值。另几位有天赋的作家,例如李准、浩然,也有类似的情况,只可惜还没人把这个编成故事讲一讲。现在时过境迁,那个“指定”的所指和能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没有变。不过这儿又有一个故事情节上的留白。人们几乎都以为“深入生活”是毛泽东倡导的,其实“未必”。为了慎重,写到这一段时,我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仔仔细细重读了一遍,所以可以负责任地跟您汇报,在这篇相当长的讲话里,“深入生活”这个词并没有出现过。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能读到的这个讲话,是在多年以后,经过多次修改,包括毛主席本人亲自修改后的定稿,应该可以判断他没有讲过这个词。不过,这个词究竟是谁的原创,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现在这个词虽然还在用,但在实践上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大概两年前吧,上海一位女作家出版了一部新长篇小说,在接受采访谈到新作的写作时说:“我一直都在生活里。”能说出这个话,是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的,但这个话却没有任何理论上的价值。它就是一个常识,常识到趋近于一句废话。你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不屑一顾”:废话!谁不是一直都在生活里?但问题又不像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的那么简单。这位作家毕竟上了点年纪,眼睛还在盯着她那个“一直都在”里面的自己的“生活”。新一代作家多半都不这么傻了。他们洞察事物的本质,知道那个指定的现实在哪里,所以既不用深入他者的生活,也不必动用自己的生活,最多跟着一伙人出去采采风就行了,尽管回来以后讲的也不是采风采来的故事。重要的是这些故事都讲得很好,好就好在它们不是直奔那个指定的现实的所指,而是周旋于那些能指的附近。于是就有了一个又一个或者很有趣、或者很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里什么都可能有,唯一不可能有的只是历史。它们或者看上去很真实,或者让人很难确定它是否真实,可以确定的只是它不会把真相告诉你。
我承认上面这个故事讲得有点乱——不,相当乱。即便是它本来就乱,并不是我把它讲乱的,终归也不好。所以下面有错即改,讲一个清楚的故事。
这是一个抗洪故事。
今年我国多省遭遇洪灾,敝省也是其中之一。与南方各省相比较,因为成灾原因不同,所以虽然历时较短,但损失也相当惨重,尤其是人员伤亡方面。洪水退去,便有一个指定的现实浮出地面。有人去深入抗洪一线,不料却发现并不存在这个“线”。敝省这次的洪水特别不讲道理,它本身就是因短时间内降雨量超大引起的山洪暴发,所以忽喇喇一下子就来了,淹死、冲走一些人,毁坏了一些建筑、农田、财物,然后忽喇喇就走了,没给当地军民留下任何跟它抗一抗的机会。不过这只是现实之一种。没过多久,该有的还是都有了,例如有张对开大报,就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抗洪斗争诗歌专辑,包括若干位诗人的若干首诗,全都激情四射地讴歌了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虽然不一定都有上佳的意象,但肯定都是好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小的支流。没错,它肯定是支流。讲故事的是一个外省的记者。对不起,为什么是外地记者,以及这个外地记者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之类的问题,咱们就跳过去吧,否则又要把故事讲乱了。总之他没有深入到抗洪一线,而是直接就去找这次灾难中那个漂浮在最最表层的人群——那些有亲人被洪水冲走的家庭。然后,他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些人在洪水退去以后都做了些什么。我是在微信上看到这个故事的,已经无法引述了,但我想我还是能够凭记忆大略复述一下这个故事。这些人,即有亲人被洪水冲走且尚无下落的人,有的还邀集了更多的亲友,便开始沿着洪水退去的方向向下游行进,一路之上,一面向每一个遇到的人打听有没有看见过怎样怎样一个人,一面仔细地察看着沿途的每一个河湾,每一堆淤泥,每一片草丛。即使这些地方已经被前面的人无数次地仔细察看过,他们还是不会放过。中间,他们会听说某处发现了一具遗体,他们总会立即抽人过去辨认。会不会扑空,大略就纯粹是个概率分布的问题了,但还是出了一些戏剧性事件。有人辨认出那正是亲人的遗体,却被管理者告之这具遗体已经有人认领了。于是就有了争议。但是没有争吵,因为很快就形成了共识:DNA说了算!就留下一两个人等待DNA鉴定结果,而其余的人则继续向下游搜寻。陆续有人退出了这支队伍,那是因为他们或者确认了亲人的下落,或者找到了亲人的遗体,但直到最后,还是有一支规模可观的队伍到达了一座大型水库。退去的山洪就泄入了这座水库。这座水库的设计库容超过12亿立方米,可以想象它的水面有多大。然而,即使到了这地步,他们还是不肯回归指定的现实,化悲痛为力量,投入重建家园的战斗,而是滞留在水库附近,甚至干脆在当地县城住下,有空就到水库边上转悠,甚至雇条船到水库里面转悠。他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说,老话说了,总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是?他们的信心也是不可动摇的——他们说,那人只要是到了这里,总得有一天漂上来不是?不怕您笑话,看到这里时我流泪了。以我现有的识见,我确实没把握判断这种故事的真实性。假如突然爆出一声断喝: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我确实不会感到特别意外。不过我还是确信,这种故事会成为历史,因为它是真相。
我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弄文学批评的人,恐怕仍会陷在某种困境里,在故事和历史之间,在真实和真相之间,被抛过来扔过去。但迎难而上的人总会有的。比如最近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70后”: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作者叫曹霞。对于这位作者,除了可以从名讳上猜测可能是一位女性,我一无所知,甚至都没能从网上搜到简历,倒是由此觉得她应该是一位新锐吧。文章读下来,明显感到了她的聪慧,但我还是要首先向她的理论勇气致敬。按我的理解,一个批评家的理论勇气,是最容易从其立论上体现出来的。您瞧瞧这文章的标题,开宗明义,就冲着“去历史化的历史写作”而去,绝对是一种迎难而上的气概。换了我,脑子就简单多了:“去历史化”之后,就没有“历史写作”了。
这种评论文章是可以当作故事来看的,你可以从中很容易地找到某种历时性的过程。这篇文章的议论对象是70后作家,所以它的第一个情节就是把70后作家,去和50后、60后作家做对比,并且在没有做什么真正的对比的情况下,就“清晰地辨认出”了70后作家的“异质性”与“陌生性”,和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写作中“正在呈现出新的维度与格局”。这正好适合于当作故事中的一个情节,而不是逻辑推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并不影响论证。既然论者所要论证的是她立论的可信性,也就是70后作家的“历史写作”是“去历史化的”,那么他们和50后、60后的差别并不是最重要的,何况我们从其他地方还有可能得知,这两个“后”绝非全都是历史化的历史写作,甚至还有相当不少的伪历史写作。于是,下一个情节就是检视70后作家的历史写作实践了。这个情节又被分成了五个小情节,分别代表着这种历史写作的四个特点,即“短历史”,“镜像”里的历史,“旁观者”的历史,“非亲历者”的历史,然后再把这四种历史写作混装为“一代人的历史写作”。在这些情节的展开过程中,曹霞充分展示了她不俗的理论表达能力。按我粗略的统计,这里一共提到了十六部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句话概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一个更出彩的地方,是在用四句话概括了四部长篇小说之后,又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四句话以及它们所概括的那四部长篇小说。这儿得说句公道话。对于作家来说,自己的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被人家一句话就说完了,其切身感受很可能不是被概括而是被宰割,但对于批评家来说,这还真是一种必备的基本功。如果要我说这儿是不是还有某些不足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在把这十六句话放在一起之后,虽然确实可以证明其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作品,确实是“去历史化”的写作,但是并没有证明这种“去历史化”的写作仍然是历史写作,反倒是近似于证明了我那个很简单的担心——“去历史化”之后,就成了没有历史的写作了。其实曹霞挺冤的。读她的文章,常可感到她识文的“眼光”准确而敏锐。这是一个合格批评家不可或缺的秉赋。比如她在谈到某部作品时说:“(该作)讲述了‘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却化解了历史的沉重与恐惧,而填塞进了热闹、嬉戏、歪打正着的友谊、温暖细小的私情。”如果颠倒一下顺序再略改几个字,变成“(该作)讲述的是‘文革’中的武斗场景,却填塞进了种种热闹、嬉戏、歪打正着的友谊、温暖细小的私情,从而化解了历史的沉重与恐惧”,岂不是刚好用来描述“去历史化”是怎样把历史丢掉的?我尤其赞赏文中的一句话,道是“这一代作家比‘50后’、‘60后’都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历史真空”。看得、说得多准啊!当然,得把“认识到”改为“表现出”。表现出了不等于认识到了,浑然不觉者所在多有,甚至曹霞也是其中一位。同样也是在这篇文章里,她还说了一句很糟糕的话,道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也是‘70后’的成长和成熟期)并无多少别开生面的政治运动和重大的战争动荡,堪称风雨沧桑的近现代中国以来难得的‘无事’时光”。这甚至让我想起一个传说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回目叫“丁某怒斥张某某”。初听之下颇为错愕。以我的印象,张某某原是个不错的新锐批评家,怎么就会被我一向景仰的丁教授怒斥呢?原来张某某确实说了一番糊涂话,道是不该总是跟年轻人说“文革”怎么怎么样,“文革”那点事,谁不知道?就算不知道,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若按这个,也该斥。曹霞的这个三十多年的“‘无事’时光”,亦此类也。不过我又想,错便错了,其情可原,其因可悯。他们确实有很多事不知道,但那是因为一些本该把这些告诉他们的人,却将其瞒过了。这等讲时,倒是丁教授这辈人更应该反躬自省,为什么您老们教出来的学生会这样?
是不是都热衷于讲故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