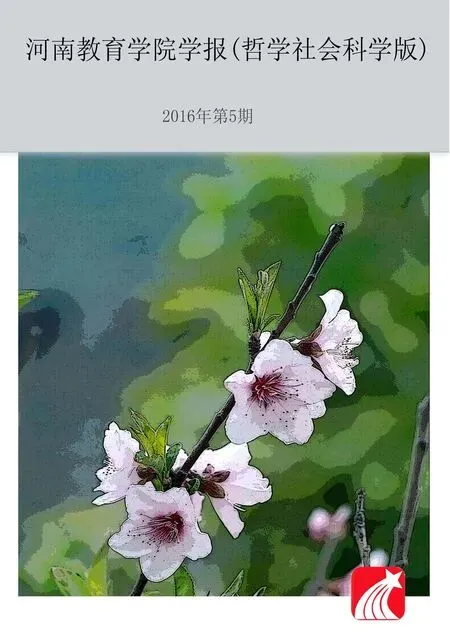毛泽东红学文献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
董志新
毛泽东红学文献的现状及其未来展望
董志新
毛泽东红学文献现在可以说比较丰富,人们能够研究,能够说清楚不少曾经迷惑不解的学术难题。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和现行的档案管理制度,这类文献的披露有其独特方式及特殊历程:依赖于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开,依赖于专门机构人员的研究成果,依赖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的展示;它的出现呈波浪起伏状,有一定周期性;一般人或一般研究者很难接触到第一手材料。这就必然存在文献不足的问题,如文献来源不明、传闻异词、披露缓慢和散佚难寻等,使毛泽东红学有些议题,乃至重要课题“不足征也”,制约、迟延了现当代红学史中这门专科的生长和发展。所以,要使毛泽东红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首要任务仍然是搜集、挖掘、考证和整合毛泽东红学文献史料,以夯实学科基础。
毛泽东红学文献;披露缓慢;夯实学科基础
提起毛泽东红学文献这个话题,使我联想到《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谈历史文献的情况:“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69
孔子的意思是说,夏代的制度,我能够言说;但它的后裔封国——杞国的现存文献不足以证明我的言说。商(殷)代的制度,我能够言说;但它的后裔封国——宋国的现存文献不足以证明我的言说。是文献不足以证明的原因啊;如果文献充足,那么我就能够证明夏代的制度和商代的制度。孔子的话,说明了文献的重要性,说明了文献与“言之”“征之”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他也有“文献不足”的苦恼。放在今天,“言之”大概就是学术研究,“证之”大概就是利用文献史料给予证明。
套用孔子的话来说,毛泽东红学文献这个大题目,我们现在可以说,文献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比较丰富,人们能够研究,能够言说,能够撰写论文和专著,能够说清楚不少人们曾经迷惑不解的学术难题,但仍存在“文献不足”的问题。这就使得毛泽东红学有些议题,乃至重要课题“不足征也”,无法进行,只好被搁浅、被冷冻、被滞碍,这制约、迟延了现当代红学史中这门专科的生长和发展。所以,要使毛泽东红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首要任务仍然是搜集、挖掘、考证和整合毛泽东红学文献史料,以夯实学科基础。
一、从零星披露到集中提供:毛泽东红学文献的呈现方式和特殊历程
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都必须掌握这门学科的全部文献或主要文献。从事毛泽东红学研究也不例外。解决毛泽东红学每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都需要搜集、整理、阅读毛泽东红学文献。
毛泽东红学的研究对象与毛泽东红学文献的内容是对应的。毛泽东红学包括: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红楼梦》阅读史,评论《红楼梦》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引证运用《红楼梦》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组织指导红学活动和红学学科建设,以及毛泽东身后研究毛泽东红学的论文和专著。这六方面构成了毛泽东红学和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整体框架。
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也由于现行的档案管理制度,这类文献虽然为数不少,可是有些并不能轻易见到,甚至至今没有披露。一般研究者想在一个较短时段内将它们全部找到基本上不可能。如果要一一地加以仔细研究,那就更不容易。毛泽东生前,有关他的红学文献面世的并不多,毛泽东逝世后至今的40年(1976~2016)内才渐渐多起来。这就产生了种种与众不同的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披露现象与过程。
涉及这种现象与过程的著述不少,笔者选择40年期间有代表性者做个案介绍,以斑窥豹,探析毛泽东红学文献披露的独特方式及特殊历程。
(一)《“红学”一家言》的披露
1986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生活》一书,收入了龚育之、宋贵仑的研究文章《“红学”一家言》(以下简称“龚宋文”)。这篇文章在毛泽东红学研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首次做出了毛泽东红学是“一家之言”这样评价其历史地位的判断,而且以毛泽东研究专家的权威身份(龚育之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公布了毛泽东评红谈话、批文、引语等红学文献18条。这篇文章显然具有毛泽东红学文献价值。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依据每一条文献的主题,拟出它们的标题:(1)与哲学工作者谈《红楼梦》研究与红学(1964);(2)中国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1956);(3)曹雪芹的生活时代(1962);(4)曹雪芹的民主文学(1958);(5)《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1961);(6)《红楼梦》写得有点希望(1962);(7)贾家就是那么垮下来的(1963);(8)曹雪芹还是想“补天”(1964);(9)不读《红楼梦》不懂什么是封建社会(1965);(10)《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961);(11)《红楼梦》的描写说明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1959.12~1960.2);(12)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出家长制的不断分裂(1959.12~1960.2);(13)“三反”时用“贾政做官”的故事(1952);(14)用“大有大的难处”说明大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1957.3);(15)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志士仁人(1957);(16)用“东风压倒西风”比喻国际形势(1957);(17)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1958);(18)在李希凡、兰翎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上的批注(1954)。
这18条文献资料,可以分为四目。第一条是总论,即谈《红楼梦》研究,谈红学发展史;第二条到第十二条,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整体评价;第十三条到第十七条,是对《红楼梦》故事典故和词语典故的生活运用;第十八条是1954年“批俞评红”大讨论中毛泽东对李、兰批评文章的激赏。
这组资料的出处和来源是:(1)毛泽东的谈话。如已经注明的,第一条就出自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也是出自毛泽东与不同对象的谈话。(2)毛泽东的讲话。如第三条出自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第七条、第十三至第十七条则源自毛泽东在不同会议上的讲话。(3)毛泽东的著作。如第二条出自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4)毛泽东批语。如第四条出自1958年8月毛泽东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修改时的批语。第十八条则是对李、兰文章的批语。由于作者出自权威研究机构,占有第一手档案资料,因此其公布的18条毛泽东红学文献无疑是权威的、精准的,并在之后的毛泽东红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组资料呈现出如下特点: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1965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和“文革”开始后的文献不涉及,均未披露;内容方面,涉及《红楼梦》研究的多而博,涉及红学及红学史的则少而薄。它的长处是把毛泽东红学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主要资料、精华资料呈现出来了,不足之处是囿于当时的文化氛围和认识程度,某些该给予肯定并阐释的毛泽东红学文献资料被搁置甚至误判,比如所谓“掩盖说”,即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毛泽东与许世友谈阅读《红楼梦》(1973),就被视为“偏颇之论”放弃不录。新中国成立前与“文革”中的毛泽东红学文献的缺席,也使红学界深怀“文献不足”之忧。
(二)《毛泽东论〈红楼梦〉》的披露
边彦军在1993年《红楼梦学刊》第四辑上,以《毛泽东论〈红楼梦〉》(以下简称“边文”)为题,梳理公布了29条毛泽东论曹评红文献。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和人民的领袖,确实也很重视我国古典文学,特别与《红楼梦》这部小说有很密切的关系。当此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际,本刊特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边彦军同志,将毛泽东有关《红楼梦》的谈话、批文等整理成文。这里发表的是毛泽东自1954~1964年的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谈话及批文。”[2]编辑部所以这样做,显然有明显的针对性,诚如“编者按”所指出:“过去,有人曾传抄或私下传讲这些谈话,因无文献资料根据,纷说不一,有时弄得很混乱。”[2]作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研究组的研究人员,边彦军的文献整理思路,与同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人员的龚育之有共同点,如他在“题记”中所说:“这个材料汇集了毛泽东1954年3月至1964年8月十年间读《红楼梦》、谈《红楼梦》、评论红学研究的主要大事。为什么只选择这十年?理由也简单:主要是材料的原因。因为在这之前,有文字记载的很少”,“抗战时期有点材料,仍然不多”,“‘文化大革命’后期……传出一些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若干说法……不能表达毛泽东对《红楼梦》的一贯看法”。[2]如“掩盖”说显然是“偏颇之论”。
虽然同样是选择大致1954~1964年这个时间段,“边文”比“龚宋文”的资料更丰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14条资料。增加最多的是1954年“批俞评红”大讨论的材料,如毛泽东在李希凡、兰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文艺报》编者按上的全部批语(此条在“龚宋文”也有,但不全),在李希凡、兰翎《评〈红楼梦研究〉》和《光明日报》编者按上的全部批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批判的报告》上的批语,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上加写的一段话,在冯雪峰检讨文章上的批注,在周扬《关于批判胡适组织计划的报告》上的批语,给李达的复信(信中主要谈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陆定一在阐述“双百”方针报告中评价俞平伯“政治上是好人”,对他批评是有错误和缺点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批准)。这9条资料,把毛泽东在1954年“批俞评红”大讨论中的红学实践活动的基本面貌都反映出来了。新增加的文献还有:《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1954),“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1958),读吴世昌《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源〉的?》(1962),“《红楼梦》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1963),“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1963)。这5条资料,有4条属于《红楼梦》文本研究,一条属于红学史范畴。
二是对“龚宋文”已有的资料补充了缺文和背景材料。如“龚宋文”中提到毛泽东对《红楼梦》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五次运用,只是点个题目,而“边文”不仅补足了毛泽东的涉红议论,而且补充了事件全貌和时代背景。这样,读者、研究者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毛泽东的引红目的和用红价值。
三是除了毛泽东谈话、讲话、著作、批语,也从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和学术专著中摘录毛泽东的谈红片断。如第一条就是从毛泽东卫士张仙朋的回忆录《为了人民……》中摘出的。再如,有9条文献资料出自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为适应阅读期待和研究需求,“边文”对毛泽东红学文献的寻求搜集,选材范围有扩大。
(三)《毛泽东文艺论集》的披露
《毛泽东文艺论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书中《谈〈红楼梦〉》一文,是首次以专题集纳的形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论红著述。共收8条资料,时间跨度从1959年到1973年。从毛泽东谈《红楼梦》说明了封建社会中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和家族的瓦解崩溃(1959.12~1960.2),到“文革”中毛泽东与许世友谈红(1973),都是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红楼梦》的经典个案。前7条在“龚宋文”和“边文”中都有介绍,已为人们所熟知,第八条关于毛泽东与许世友谈红则更具价值。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其中与许世友谈论要阅读《红楼梦》。毛泽东此段谈话共有四层意思:《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曹雪芹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吊膀子”是掩盖政治斗争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红楼梦》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3]209-210毛泽东与许世友谈红,尤其是其中的“掩盖说”,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偏颇之论”。此次入选《毛泽东文艺论集》,等于说权威研究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已认为毛泽东此段谈话是正确的或者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毛泽东文艺论集》选文时遵循的原则。另外,《毛泽东文艺论集》还选入了《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文。这是1975年7月毛泽东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谈话的整理稿,其中谈到繁荣文艺、谈到解放周扬、谈到《红楼梦》和《水浒传》的出版。[3]233这两篇文章为历史地、正确地评价“文革”时期红学活动(如“‘文革’评红热”)的是非功过,提供了信实的文献依据。
(四)《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的披露
徐中远撰著的《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由华文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该书第一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1~71页),是专讲毛泽东阅读《红楼梦》的情况的。此文最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阅读批注《红楼梦》的史料文献:(1)从1958年到1973年毛泽东索要25种《红楼梦》。如1972~1973年要4部新版《红楼梦》(4~8页)。(2)中南海故居藏线装本《红楼梦》20种,是毛泽东主动要读的(9~12页)。(3)“用铅笔圈划过”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两部书(43~44页)。(4)对俞平伯《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何其芳《论红楼梦》“毛泽东圈划批注都比较多”(52~65页),对周汝昌考证“胭脂米”一段“一一作了圈划”(36~40页)。(5)要读吴世昌《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源〉的?》全文(66~67页)。徐中远“是为晚年的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4]327,他在毛泽东逝世后,整理毛泽东所遗藏书,记载的毛泽东阅读批注《红楼梦》的情况为其亲历亲见,颇具文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五)《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等书的披露
陈晋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他从文化角度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较多:如《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读毛泽东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版)、《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毛泽东文艺生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这些书是对毛泽东新文化建设和思想理路的专题研究。毛泽东长期钟情喜爱古典文学名著,这些书中的记述和引证中包含着不少新披露的红学文献。前面已经提到,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中,仅反映1954年“批俞评红”大讨论的文献就有9条之多,既全且细。再如,《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书,其《文学篇》中有6篇论红文章:《〈红楼梦〉的老祖宗》《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就讲不通》《第一次向红学权威错误观点开火》《没有实际经验写不出马鞍之微的事》。每篇文章又连类而及引证多条资料。陈晋在书中也常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如1954年毛泽东曾经组织人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抄一部善本《红楼梦》,就是陈晋在《〈红楼梦〉:小说怎样成为历史?》一文中记载透露的。[5]278-279由于上述诸书引述的文献多数出自档案,真实确凿,可以校正传闻、传抄中的毛泽东谈红语录,使之准确规范。
(六)盛巽昌对《毛泽东与红楼梦》的编辑集纳
盛巽昌编著的《毛泽东与红楼梦》(以下简称“盛著”)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是一部毛泽东红学文献专题资料集成式的著作。编著者在《后记》中说:“本书所采撷文字,均源自国家公开出版物所发表的毛泽东和《红楼梦》的评述、介绍。……为便利阅读,正文按年月顺序排列,且稍作简注,梳理成册。”[6]148全书共收资料146条,起止时间从1913年到1976年。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取材范围广泛。除毛泽东本人著作外,举凡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论文,涉及毛泽东生平、交往、行为、生活琐事、重大事件的回忆录,纪实体传记的实录,报刊纪念或研究文章,国史、党史、军史和地方志的记载等,都在其搜集范围之内。如取材于萧克、刘英、王炳南、何其芳、吴冷西、邓绍基、李锐、陶鲁笳、许世友等回忆录中的红学文献,均系原作者首次披露,具有时新性,为研究者提供了原始资料。
第二,规模相对完备。从毛泽东1913年在湖南师范(先是四师,后是一师)读书时开始阅读《红楼梦》,到1976年逝世为止,毛泽东阅、评、用《红楼梦》的红学实践和红学思想,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13~1949年9月为酝酿发生期,1949年10月~1965年为体系成熟期,1966~1976年为曲折发展期。以往对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侧重于第二个时期。“盛著”辑第一个时期资料达44条,辑第三个时期资料也有15条。从整体上说,这使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披露和整理趋向系统化,初具学科文献规模。
第三,系年考核准确。文献逐年编排,注明出处,不仅查阅方便,而且很容易使读者了解毛泽东红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整体面貌。对毛泽东评说或引证《红楼梦》的内容,又对应查阅文本,摘出原句,附上简注,免去读者翻查之苦,能充分发挥文献的作用。
当然,这部专题资料书的考校也有瑕疵。如曹雪芹在小说中运用的成语,“坐卧不宁”“诚心诚意”“无缘无故”等,俗语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坐山观虎斗”等,毛泽东在著作中也使用过。编著者将这些作为毛泽东征引《红楼梦》的例子,似不妥当。因为这些成语和俗语的原始出处,远比《红楼梦》出现得要早。毛泽东学习、熟识并随手运用这些成语和俗语,很可能是受到别的典籍的启迪,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毛泽东引用《红楼梦》。
(七)各种毛泽东著作、传记和年谱中的披露
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传记和年谱很多。这里主要指权威研究机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或编撰的此类出版物。综合类毛泽东著作有一卷本《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修订版,1991)、八卷本《毛泽东文集》(1993~1999)、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87~1998),专题类毛泽东著作有一卷本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99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8)、《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毛泽东书信选集》(198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995)、《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2001)。毛泽东传记类著作如一卷本《毛泽东传(1893~1949)》(1996),上下卷《毛泽东传(1949~1976)》(2003)。年谱类著作有三卷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1993)、六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2013)、一卷本《毛泽东经济年谱》(1993)。各种毛泽东著作、传记和年谱大都有毛泽东红学资料的披露,只是多少不同,尤以《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这五种为多。例如,毛泽东说《红楼梦》“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就出现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时间为1938年的抗战初期。[7]124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的思想源头即在此。再如,毛泽东引证小说人物性格特征以比喻宣传工作中“软”与“硬”时说“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就出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8]120这五部书其中有三部书的时间跨度是毛泽东一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又选编了“文革”时期较为正确的篇章。它们不仅提供了以往人们知晓的某些红学文献的原生态,而且披露了不少世人前所不知的新材料。例如,毛泽东说“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唱的小曲是《红楼梦》的主题歌”,就出现在《毛泽东年谱》1959年7月的谱条中。[9]100再如,毛泽东评论“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则出现在《毛泽东年谱》1973年5月的谱条中。[10]480这些资料几十年后才公布出来为人所知,虽然有点晚,但也难能可贵!
综上,毛泽东红学文献面世的大致情况可以基本了然。从中可以发现,能够披露文献者,如龚育之、边彦军、陈晋、徐中远等,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者或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著作、传记、年谱的整理撰写,也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承担。盛巽昌编著的集成之作,只是集纳已发表之资料,无力披露新材料。普通作者、研究者难于做出贡献。再者,有些评红材料等到毛泽东身后几十年才公布,实在“供不应求”,令研究者徒唤奈何。
文献整理有自己的规律。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其红学文献的披露,依赖于档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开,依赖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的展示;它的出现呈波浪起伏状,有一定周期性,如1993、2003、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隆重纪念之年,此时有关毛泽东的出版物或载体中,会批量出现毛泽东红学文献资料;由于一般人或一般研究者很难接触到高层领袖人物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权威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公布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情形占绝大比例。
二、从传闻异词到散佚难寻:毛泽东红学文献传播渠道的症结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40周年。经过40年努力,毛泽东红学文献可谓丰富矣。但仔细想想,其间不尽如人意之处还为数不少。梳理一下,曾经存在的和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大致有来源不明、传闻异词、披露缓慢和散佚难寻四端。
(一)来源不明
红学界都知道,“总纲”说、“掩盖”说、“阶级斗争”说、“历史小说”说这著名的评红四说,本来都是毛泽东的评红观点,而且它们产生的年代都在1965年以前,如“阶级斗争”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54年春天,“掩盖”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62年以前。但是,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评红谈话大都是“内部”传达,“私下”传播。即使写阐述文章的人,也往往只知“有来头”,并不确知是谁的观点。毛泽东逝世后揭批“四人帮”时,不少文章竟把这“四说”当成“帮红学”的“靶子”来批判,如说“掩盖”说的实质是“掩盖”了“四人帮”的夺权斗争。这实在是前后错位、张冠李戴的胡乱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后,“四说”的原始出处逐渐真相大白,可直到21世纪初期出版的某些红学史著作仍以讹传讹,沿袭这个错误判断。文献来源不明,危害大矣。
(二)传闻异词
传闻异词与红学文献的特殊生成环境有关,如会议讲话记录,与会者各有所记,侧重点不一样;又往往事隔多年才回忆整理,难免大同小异,同中有异。毛泽东的评红谈话或讲话,许多当年并未录音,当事者记录时各有取舍,因此导致传闻异词。
如毛泽东与王海容1965年的评红谈话,“文革”期间传播广泛,广为人知。《毛泽东传》中有摘引,王海容回忆录中有节录,可见确有此事此论。这个谈话的“全文本”,笔者见到两处,文字出入很大。
一处是董学文、魏国英著作《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以下简称“董魏书”)的记载:
《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凤姐这个人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这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里说的是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说的是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宝钗家)。[11]231-232
一处是胡小林、于云才著作《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以下简称“胡于书”)的引证:
王:现在谁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的那个干部子弟,尽看些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本好书。读《红楼梦》不是坏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个,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红楼梦》,你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说贾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说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12]384
毛、王谈红的思想可分为四个层次,即分为四段。两相比较,有多处异文。第一层,谈读红的必要性,“董魏书”删掉了毛、王对话71字,又有“部”与“本”、“读故”与“坏”的差异,异文共74字。“胡于书”的“读《红楼梦》不是坏事”显然是毛泽东针对王海容模糊认识而发,“董魏书”的“不是读故事”没有前者意长。第二层,谈小说语言美兼及人物塑造,“胡于书”把谈语言的三句话删削掉19字,缩为一句话,保留文字又有“部”与“个”的不同。谈凤姐描写有“那个”“都”“物”“很”5个字的差别。异文共25字。第三层,谈读《红楼楼》的目的,有“一点”“会”3字的异文。第四层,讲读《红楼梦》要领,即“要了解四句话”(护官符)。有“这”“这里的是”“的是”“宝钗”9个字的异文。“胡于书”中四大家族排序错位,与小说描写的贾、史、王、薛顺序不符,令读者会产生毛泽东记混了、背错了的感觉。毛、王谈红的两个“文本”,文字差异共111字。文献传闻异词,也会使研究者首鼠两端莫衷一是,不得不用时只能“两个版本”同时录入,并加以说明,降低了文献的可信度,影响了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准确把握。
(三)披露缓慢
从本文第一节介绍的情况看,某些毛泽东红学文献披露的速度相当缓慢。以毛泽东与许世友谈红(1973)为例,早在“‘文革’评红热”时,毛泽东要求许世友“《红楼梦》要读五遍”的“指示”就举国皆知,“文革”后许世友在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和自己的回忆录中有摘要透露[13]143;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一些书中,也是部分摘发;2002年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则以语录体形式全文发表,但受体例限制,没有背景材料;2003年和201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120周年)而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14]1676《毛泽东年谱(1949~1976)》[10]514,不仅用对话体公布了毛许谈红全文,而且介绍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全部背景材料。至此,毛许谈红文献才“全景式”地公之于世。从部分透露到“全景”公布,历时三四十年(1973~2003、2013),对随着信息时代而节奏加快的红学研究来说,这速度太慢了。红学史研究表明,毛许谈红这条文献史料,对考证“‘文革’评红热”的缘起、对判断“文革”时期红学活动的性质,十分重要。它被披露的速与慢、全与残,确实影响着当代红学史一些大是大非的分辨,速与全则明,慢与残则惑;速与全则成,慢与残则殆。当然,某些毛泽东红学文献 “披露缓慢”,与档案管理制度有关,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有关,与毛泽东著作出版的目的和编辑体例有关,我们不能一味指责具体承办人。
(四)散佚难寻
在长年累月的辗转流徙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毛泽东红学文献遭逢变故,偶然失落,去向不明。有两个典型个案:一个据说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评论《红楼梦》的长文,被编辑在一本小册子中,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天津一带见到过这本小册子,而且尚记忆编排位置和主题内容。丁玲和周汝昌等人曾提及此事。[15]200-201[16]另一个据说在1954年秋季,毛泽东曾点评过一部《红楼梦》,批语达五六千字。1995年,有名季学原者在《羊城晚报》上披露批语数条。又有人撰文说,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将批本《红楼梦》赠给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柯让文教书记石西民保存,“文革”中石家被抄,从此毛批本《红楼梦》下落不明。又有消息说,康生借阅毛批《红楼梦》时,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曾借机录副一部,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毛批”即源自路工的录副本。[17][18][19]192-195目前,关于毛泽东评红的一书一文是否存世,仍无结论。
毛泽东红学资料佚失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毛泽东的谈红对象(当事人)事久淡忘,没有记录,疏于保存。如1940年6月在延安,毛泽东与茅盾先生谈话,“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20],具体是什么“精辟见解”,茅盾先生没有讲明。丁玲女士的回忆也有类似情况,她说毛泽东于延安红军大学讲哲学时,“在露天广场上,他常常引用《红楼梦》中的人、事为例,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听课的人都非常有兴趣”[21]49。惜乎丁玲没有讲出“常常引用”的具体人和事。再如,据保健医生徐涛回忆,1954年以后,毛泽东“经常和我及身边工作人员谈《红楼梦》,几乎天天谈,对许多章节字句都细致分析,正面评论”[22]234。可惜,徐涛回忆中把“对许多章节字句都细致分析,正面评论”的具体内容省略了,难得其详。还如,1959年在庐山,毛泽东与水静谈《红楼梦》的反封建主题时,“毛泽东又举出了一些情节,并一一作了分析”[23]195。毛泽东举了哪些情节?他是怎样分析的?水静没讲到。上述这些例子说明,毛泽东评红谈话,有不少被无意淹没了,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红学文献搜集整理中的憾事。
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寻求,收集文献仍是毛泽东红学研究刻不容缓的工作
毛泽东在1975年谈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时说:“缺少文艺评论”,“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3]233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对于繁荣当时的文艺评论有指导价值,而对于今天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来说,也是这个道理,也可启迪思想:没有文献,就无法研究毛泽东红学;文献较少,文献不全,也都会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对毛泽东红学文献来说,目前红学界知之者虽然不少,但远没有穷尽,甚至有的重要史料仍然无处可觅,至今有些学术难题无法求解。如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这是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第二次红学大潮。这次红学实践活动持续两年(1962~1963),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胡乔木、周扬、王昆仑、何其芳等都有评红论红活动,毛泽东的活动和评论却只有少许披露,不能反映他在这次红学大潮中的全部实践和理论贡献。以往,红学界对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收集整理是被动地接受,就是公布多少接受多少,公布多少研究多少。现在,要在遵循其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主动作为,以热烈、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搜求红学文献,积极建设这门红学分支学科。当前可以考虑从考证、挖掘、整合三个方面推进收集整理文献的工作。
(一)考证
毛泽东红学文献的真实性、确定性和完整性,有些在文献披露之时,就已经具备了这些属性。比如,依据档案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集和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年谱中公布的文献,就有这个特质。有些文献真实却不完整,有些文献则传闻异词。比如前举“龚宋文”中有毛泽东在“三反”时讲“贾政做官”的故事,这条资料真实可信,可惜这条资料只是一个提纲,或是一个题目,没有具体内容。毛泽东在“三反”的什么具体背景下讲的,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讲的,故事是详讲还是略讲,针对什么社会问题讲的,都不清楚。“龚宋文”指出的毛泽东拿《红楼梦》说事的共5条,后出的“边文”对其中的4条做了补充完善,唯独没提“贾政做官”,可见“边文”作者也没查到相关史料。这就要考证,在考证中恢复文献的原貌。
再举一个例子,邓绍基先生提供这样一条线索:“我曾听一位看过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写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和附件的同志说起,毛泽东主席的批语中对当时《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认为可以进行讨论,只是这个在附件上的批语至今没有公开发表。”[24]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毛泽东红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它是确定1954年“批俞评红”大讨论性质、作用、地位诸问题的主要历史文献。这封信的“附件”,有“当时《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有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可以进行讨论”的批语。如果这个“附件”和“批语”能够披露出来,那将更加丰富红学界对“批俞评红”大讨论的认识,甚至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二)挖掘
事实上,毛泽东红学文献呈现两种状态:显文献与潜文献。显文献是已经公开披露,并为众人所知的文献;潜文献是已经客观存在,但没有整理,没有公开发表,还以档案等状态存放而不为众人所知的文献。潜文献还有一种表现形态,甚至暂时还不能称之为“文献”,因为它们还只是深藏在当事人脑中的记忆。所谓挖掘,即是把潜文献转化为显文献。首先,这种潜文献存在于未曾整理、未曾发表的毛泽东各类著作(包括讲话、谈话记录稿,也包括书信、文件、批语等等)中。现在,还没有《毛泽东全集》,也没有权威机构在掌握全部文献、档案、资料基础上编辑的“毛泽东红学文献集成”式著作,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都是“选集”,暂时因各种原因未入选的毛泽东著作中存在一定数量的红学文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流传出来的一些毛泽东评红谈话录,至今未被正式公布,未被证实。战争年代的著述出版情况,也存在类似现象。其次,潜文献还存在于当事人(如毛泽东谈红对象)的记忆里。毛泽东一生交往甚众,喜欢与高层领导、与身边人员、与亲人友人、与有文化的人谈红,这是他文化生活中一大嗜好。有人写有回忆录,也有人未做文字记载。这两种红学潜文献都要下力挖掘。即使已经公开的毛泽东评红谈话中,也有删节取舍,需要补全配齐。研究毛泽东的各类专著,尤其是从文史方面、从传统文化方面研究毛泽东的专著,也偶有红学文献线索,成为查找新文献的起点。我们还要看到:毛泽东红学文献中,有正面文献,思想观点正确,实践效果积极;也有负面文献,思想观点片面,甚至错误,实践效果消极。从红学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只有全面掌握正面和负面文献,综合分析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毛泽东红学文献,又可分为记载其思想观点的文献和承载其实践活动的文献。以往研究重视前者而忽略后者。后者如给毛泽东专门印制的“大字本”红学专著、毛泽东赠送他人的《红楼梦》文本、毛泽东手书《红楼梦》诗词传世书品、毛泽东调阅过的各种版本《红楼梦》、长时间累计存放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的线装《红楼梦》、批注圈画过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补图石头记》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手书原件,等等,都有深入挖掘的必要。
(三)整合
从多年来的实际运作看,毛泽东红学文献的披露是分散的、零星的、不定期的。它们被淹没在著作集中,被淹没在回忆录中,被淹没在学术论文中,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载体中……如果无人搜集,无人整理,无人集纳,即使公布再多,也是“散落满天的星”,难于被红学家及时纳入视野,进入研究过程。边彦军、盛巽昌等人做过很好的集纳整合工作,发挥了推动毛泽东红学整体前进的作用。此后的二十多年,新出现的毛泽东红学文献为数众多。但是专家们在研究红学史的时候,在回顾“百年红学”的时候,在评价新中国毛泽东时期三次红学大潮的时候……又深感毛泽东红学文献的缺乏。现在,这样的学术任务被提上日程:全面收集、梳理已公开的文献,考证、核校不确定、有疑点的文献,尽力挖掘潜在的文献,在此基础上给予整理整合,使其系统化、条理化,给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便捷适用的文献精品。
[1]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边彦军.毛泽东论《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1993(4):13-29.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5]陈晋.毛泽东阅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盛巽昌.毛泽东与红楼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1]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12]胡小林,于云才.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3]学习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5]张晓京.中国第一人:毛泽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6]林东海.我与红楼梦研究资料[J].红楼梦学刊,2002(4):158-178.
[17]季学原.毛批《红楼梦》有意外发现[J].羊城晚报.1995-01-14.
[18]季学原.毛批《红楼梦》点滴[J].羊城晚报,1995-09-05.
[19]邸瑞平.红楼漫拾[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20]茅盾.延安行:回忆录:二十六[J].新文学史料,1985(1):4-25.
[21]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22]徐新民.在毛泽东身边[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3]许祖范.毛泽东幽默趣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4]邓绍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发言[J].红楼梦学刊,1993(4):36-39.
(责任编辑范富安)
Current Situation of MAO Zedong Redology Literatur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DONG Zhixin
(BaishanPublishingHouse,Shenyang110014,China)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MAO Zedong redology literatures, or even plenty of ones. People can study and solve academic problems that have ever puzzled.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MAO Zedong’s special identity and current archives management system, the disclosure of such a kind of literature has its unique way and special course. Basing on the decryption and disclosure of archives materials,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special agency staff, and demonstration of memory articles and memoirs of parties involved, its appearance takes a shape of wave fluctuation, with a certain periodicity. The average person or general researcher is hard to contact with the first-hand material of high level leaders. Therefore, it will inevitably caus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such as dissatisfactory aspects like unidentified sources of literature, inconsistent phrases, slow disclosure and missing and so on. Some topics for discussion of MAO Zedong redology or even important topics are insufficient, thus restricting, limiting and delaying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in current redology history. As a result, in order to make a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n MAO Zedong redology, the primary task is still to collect, excavate, textually research and integrate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AO Zedong redology literatures,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subject basis.
MAO Zedong redology literature; slow disclosure; consolidate the subject basis
1006-2920(2016)05-0001-10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5.001
董志新,白山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沈阳 11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