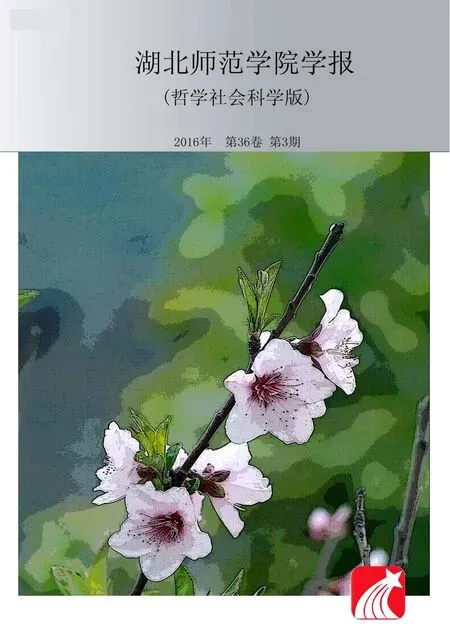李振钧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丁功谊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李振钧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丁功谊
(井冈山大学 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343009)
清代道光年间,李振钧提出论诗要从音调格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抛弃门户之见、唐宋之别,反映诗人内在的性情和寄托。在诗歌创作中,李振钧以性灵诗学为底蕴,同时转益多师,熔铸百家,表达他对纯真爱情的坚守,对科举功名的游离,以及对封建末世王朝的冷静思考,形成了深沉阔远、拗峭峻拔的独特诗风,成为嘉庆、道光诗坛的重要诗人。
李振钧;诗学思想;性灵
李振钧(1794-1849),字仲衡,号海初,安徽太湖人,道光八年(1828)状元,先后授翰林院修撰、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和功臣馆纂修、顺天乡试同考官等,著有《味灯听叶庐诗草》。
嘉庆三年(1798),李振钧五岁,开始解辨四声,接触古典诗歌。这年诗坛发生一件重大事件,性灵派领袖、随园主人袁枚去世。嘉庆年间,袁枚的弟子们和追随者依然在创作追求性灵、纤巧灵动的诗歌,并且风靡大江南北。李振钧始终关注着诗坛动态,潜心师法性灵诗歌,力主赤子情怀、天真摅写,并以真率疏狂的诗歌创作实践着性灵诗学的主张。同时,他在诗歌创作中熔铸百家,用香草美人的寄兴传统,阔大深远的识见器局,改造了性灵诗学,形成了自己深沉阔远的诗歌风貌,成为嘉庆、道光诗坛的一道亮色。
一、对性灵诗学的传承
1.乐府闲情寄托深
在《味灯听叶庐诗草》中,李振钧曾经提到袁枚,其《题<手把芙蓉朝玉京图>》组诗第一首诗云:“迢迢流水到天涯,小谪人间又若耶。毕竟随园诗谶早,生非薄命不为花。”[1]随园即诗人袁枚。这首诗写表兄顾秋碧的已故姬妾佩湘,佩湘是袁枚堂弟袁树的婢女。李振钧引用袁枚的诗句“生非薄命不为花”,大有深意。袁枚作《落花》十五首,第一首云:
江南有客惜年华,三月凭栏日易斜。春在东风原是梦,生非薄命不为花。仙云影散留香雨,故国台空剩馆娃。从古倾城好颜色,几枝零落在天涯。[2]此诗为袁枚于翰林院时因考满文不及格,而外放江南任县令自伤之作。写成后,此诗倍受时人喜爱,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十载:“余改官江南,赋《落花》诗,祁阳中丞内幕程南耕爱而和之。”[3]袁枚作此诗自伤仕途沦落,深深打动场屋不顺的李振钧,而深得诗心的李振钧自然深谙此诗颔联之精妙:以“春在东风”喻翰林院,以“薄命为花”喻外放之失落也。此等拈合,起落无端,而熨帖神奇。
如果把袁枚《落花》诗置于更广的背景下来思考,则发现《落花》诗代表的是中国古典诗词香草美人的创作传统。明人沈周因丧子而作《落花》诗三十首;唐寅因科场被黜赋《落花》诗三十首,徐祯卿因寓居京师感怀不遇而作《落花》诗十首。和袁枚同时期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作的《葬花吟》,既是黛玉红颜薄命之谶语,也是作者曹雪芹的身世写照,而袁枚因罢官江南而作《落花》十五首,自然沿袭了这一诗歌传统,而李振钧直接引用“生非薄命不为花”句,既表达对才女佩湘的同情与叹惋,也委婉传达出他对随园主人的敬重与推崇。
人们论袁枚,多认为他放浪风流、纵情逸志,论他的性灵诗论,多引其《答蕺园论诗书》中“情所最先,莫如男女”之句,把男女之情作为其性灵诗论的核心内容。其实,袁枚《答蕺园论诗书》的诗论正好相反,他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苏、李以夫妻喻友,由来尚矣。”[4]袁枚所说的借男女闲情而寄托,也就是性灵派的本质,即以温柔乡躲避或对抗现实的无奈。对此,李振钧领悟于心,他在《赠孔冶山上公姻丈即以志别》诗中说:
平生最不喜秋吟,乐府闲情寄托深。深藏石梅九仙骨,美人香草百年心。
所谓诗中的男女情爱不外是诗人境遇的曲折寄托,人生的委婉传写。寄托遥深,归趣难求,诗风深沉阔远,成为李振钧诗歌创作的特点。
2.天真摅写赤子心
关于袁枚的《落花》诗,有段饶有趣味的故事。袁枚晚年,整理《小仓山房诗集》,想把他年少时候的《落花》《残雪》等诗篇删掉。这时,他的弟子薛起凤劝老师:年少的文字,如春日繁花,保留早期诗风的特点,不可废除。事见袁枚弟子薛起凤的《小仓山房诗集序》:
(袁枚)晚年境愈高,才愈敛,欲删去《少年》《落花》《残雪》诸作。起凤争曰:“孤松苍于冬,时花繁于春,各有其时,不可废也。”先生曰:“诺。”已乃并存之。[2]
我们可以想见,李振钧向往前辈袁枚,读此诗必读其诗集,读其诗集必读此序。年少时期的文字,珍藏了青春的密码,反映了赤子之心,如春日的花雨,如冬日的融雪,是逝去年华的写照,也是最为动人的性灵诗篇。用袁枚的话来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妙在皆孩子语也”(《随园诗话》卷三)。在这种诗论启发下,李振钧提出他的诗歌主张:
尝论人之为诗,往往存门户之见。夫使李、杜在宋,不失大家;苏、陆生唐,自是初盛。夷、高抗行,巢、皓峻节,时代虽殊,情性则一,必拘拘于音调格律,以求合是,既束缚而又欲其驰骤也。虽然,余何敢言诗哉?潦倒中年,情怀萧索,转不若少时之天真摅写、音律自谐。回首当年之翦翠裁红,忽忽已成往事。古人云:情随事迁,感慨系之,良有以夫。 (《味灯听叶庐诗草》自序) 清代中叶,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人提出“格调说”,强调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而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诗人提出“肌理说”,主张师法宋诗,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相统一。在这种背景下,李振钧提出论诗要抛弃门户之见、唐宋之别,要从音调格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追求诗歌内在的核心要素,也就是情性;诗人要保留了一颗年少的赤子之心,有了赤子之心,那么诗歌自然音律自谐,优美动人。李振钧的论诗主张实际上是对格调派和肌理派的有力反拨,这和袁枚主张的“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2]、“诗真岂在分唐宋”“专主性情”(《随园诗话》卷二)的诗论是一脉相承的。
“假我韶年悦性灵,候虫时为发新声”(《检诗稿偶成》其一)李振钧始终没有忘记他最早的一篇命题作文。在清嘉庆五年(1800),山东莱州古藤书屋里,七岁孩童李振钧给老师交了份日课作业,也就是一首题画绝句诗:“水绕前村绿,山横远树青。诗人工著笔,添个小茅亭。”(《味灯听叶庐诗草》自序)上联简笔勾勒出山水之妩媚,对仗工稳流畅,下联别出心裁,宕开笔调,转写画师乐山智水之趣,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上超拔出画面空间。李振钧后来辗转奔波于贵州、江苏、云南、湖北、北京等地,深得江山之助,笔墨放纵,落想不凡,诗风阔大深远,无不暗藏童年这首诗的思维印迹。
3. 傲骨慧心见性灵
李振钧还有一首诗提到袁枚,即《赠许定生内史》组诗第二首:“随园弟子女名家,桃李新鲜那足夸。傲骨慧心真绝世,一生倾倒只梅花。”诗后有小注:“定生为梅麓第二弟子。”梅麓即李振钧的忘年交,桐城派姚鼐的高足齐彦槐(1774-1841)。年少时,齐彦槐以诗拜谒袁枚,袁枚大为赞叹,惊呼“此生乃旷世逸才!当以远大期之”。嘉庆十三年(1808年)恩赐举人,次年中进士,先任翰林院庶吉士,颇善楹对,传有《梅麓联存》。齐彦槐曾赠女弟子张襄联两副:“几生修到梅花骨,一代争传柳絮才。”“前身来自众香国,佳句朗如群玉山。”[5]从齐彦槐赠联和带有众多女弟子行迹看,齐彦槐在创作和行事两方面都追随袁枚。道光十年(1830),李振钧离家北上,拜访齐彦槐,认识齐彦槐的第二个女弟子许定生,由此写下《赠许定生内史》组诗六首。
在这组诗中,李振钧称许定生为随园弟子,尽管许定生在名分上为齐彦槐高第,但是在李振钧看来,她的才华和性情,足以纳入随园弟子中。李振钧在组诗序中高度评价这位女诗人:“工诗词,尤婉丽,无脂粉气。”可以说,李振钧对性灵诗歌的认识比较深刻,弥补了袁枚性灵说诗论的不足,那就是性灵不局限于男女艳情,也可显现在傲骨慧心和婉丽才思。联系李振钧的诗歌创作看,性灵说不仅表现于他对女性的深沉爱恋,还表现在诗人对历史人物的借古讽今,以及内心深处对科举功名的淡漠和游离,他把性灵诗作从个人的性情际遇提升到广阔的社会,实现了性灵的升华。
二、对性灵诗歌的突破
1.情到眼狂魂断处
自古以来,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也是性灵派诗人最为着力的写作题材。清代中叶,袁枚主盟性灵诗派,写尽各种情爱,唯独对自己的夫妻之情较少涉及。而李振钧以执着而深沉的情感,表达他对亡妻的思念,及对妻子的坚贞。
嘉庆十四年(1809),21岁的汪正珠(1789-1815)嫁给了16岁的李振钧。六年后,汪正珠突然病逝于福建巡抚署,享年仅二十八岁。在家乡太湖读书的李振钧惊闻岳父亲笔书信中传达的噩耗,不由心如刀绞,接连写下《悼亡(四首)》《自伤》《自解》《重谴(十首)》《魂归来歌(七首)》等诗,后来将这些悼亡诗结为《结肠集》。
李振钧在《悼亡》诗题下,以诗序和小注的方式,介绍了亡妻汪正珠的一生。她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学习女诫家训和诗词韵律之类的书籍,能写诗赋词。嫁到李家后勤俭持家,亲自下厨、纺织,很少添置衣妆奁具,而丈夫李振钧任性纵酒,夫妻之间偶有小事不合,汪正珠总是逆来顺受。母亲知道后,经常责备李振钧,这反而让汪正珠更加感到内疚。她自幼体弱多病,每当病痛不已的时候,为了不让父母忧心而总是忍住呻吟。后来在临终剧痛的时候,仍然声声提及公公、婆婆待她的恩德。这些故事,既显现汪正珠的温柔善良、知书达礼,也流露出诗人对妻子的无比怀念。而在诗中,悼亡之情显得更为感人:
年年泪向诗中洒,恶谶谁知竟属卿。情海几时惊一变,神山此去了三生。遣函犹道将归速,灵药终难与命争。最是回肠不堪忆,飘风零雨落花声。——《悼亡》其一
此诗直抒胸臆,情感沉痛真挚。字字血泪,凄楚动人。又如《重遣》其六:“巾箱为检嫁时书,记得灯前共话余。尽是阿爷亲口授,印章还刻女相如。”诗人不加任何修饰,纯用白描手法,平静叙述着亡妻的遗物和灯前共话的情景,显示出作者对往日生活的无比怀念,和对亡妻的无比哀思。
嘉庆二十五年(1820),李振钧依然哀伤不已,在梦中写下思念亡妻的四句诗:“惊回一枕江南梦,转忆前盟暗自伤。宵最可怜犹有月,魂原难返况无香。”句后有小注:“梦中句”。醒来后,他回到现实中,补上身世飘零、宿业未了的四句感怀,连缀成《续梦中句》诗。并接着写下《更得一首》以悼:“门对清溪柳影低,个侬家住板桥西。命如难续春蚕尽,谶或非真梦蝶谜。”而这时,汪正珠离开他已经五个年头了。
后来,李振钧见过一些女子,尽管他酒后内心疏狂,但没有风流放纵,而是以轻快流转的性灵诗,表达他对女子的尊重和祝福。如《醉后戏赠》组诗:“临邛昔日度琴心,十六年来断音信。老去诗人情未灭,么弦低拂海棠阴。”“我如银汉无根水,卿是巫峰未出云。艳福柔情消不得,逢人说嫁李将军。”这位年轻时疏狂任性的诗人,没有消受眼前的艳福柔情,反而为她们寻求幸福的归所。
道光九年(1829)四月,李振钧高中状元,直接选入翰林院任修撰。同年九月,诗人带着科举的荣耀,回到家里,写下《到家杂咏》:“小妻抱子笑相迎,转觉无言可慰卿。看遍长安花似锦,不曾负却旧时盟。”(其五)看到继室汪氏(1796-1876)抱着儿子出门含笑相迎,诗人无言相慰,也不愿再谈科举功名,只觉得没有辜负夫妻旧盟,也算是对妻子的莫大安慰。在诗人的心里,状元的科举功名和那些异乡花草,哪有夫妻深情重要。
在李振钧一生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亲人,那就是亡妻汪正珠的兄长汪奂之。嘉庆十一年(1806),汪奂之与李振钧的长姐成婚于李家,汪奂之也说是李振钧的内兄。这种内兄加姐夫亲上加亲的关系,以及共同的志趣追求,使他俩情如兄弟。嘉庆十五年(1810),二人初相识于武昌,这年秋天,同应顺天乡试。汪奂之感秦淮旧事,作《题李香君》诗云“为问板桥桥外月,可能描得旧眉痕”,此诗给李振钧极大启发。道光元年(1821),汪奂之寄诗并约遥唱,李振钧和诗云“三年不见奂之诗,孤馆相思风露夜”,表达他对内兄的深切思念。这年,李振钧还写下《九松水榭感旧》诗:“板桥桥外纤纤月,未必眉痕似旧时。”遥和当年秦淮诗。道光七年(1827),汪奂之逝于成都,李振钧在悲痛中写下《哭奂之诗》:
真个而今是别离,未曾白发故人稀。晴川浪拍河豚上,燕市双回塞雁飞。月下眉眼抛画笔,风前弰影挂弓衣。石湖依旧桃花水,不见汪伦送我归。(其四)
化用李白诗,把汪奂之称作汪伦,表达对内兄的深情厚谊。“月下眉眼抛画笔”句指的正是当年的《题李香君》诗句,李振钧一直没有忘怀与内兄的乡试与唱和的情景。而等到李振钧高中状元后,不由得又想起汪奂之:
女嬃话旧感酸辛,奠雁曾推第一人。怪底荣枯分两树,有才无命是汪伦。(其六)
诗下有小注:“予十七就婚武昌督署,外舅稼门先生一见以第一人相许,今奂之姊丈殂谢,内家零落,良可慨也。”在武昌督署成婚的时候,岳父汪志伊(1743-1818)初见李振钧,就极为叹赏。而现在岳父汪志伊和前妻汪正珠已经去世十余年,内兄汪奂之也已离开这个世间两年了,婚盟通好的李汪两家如今已是荣枯两分,想到这,李振钧不由叹惋,对至情至性、才华横溢的汪奂之怀以深深的念想。“情到眼狂魂断处”(《道中偶成》)对亲友的深情咏怀,成为李振钧诗歌的主题。
2.气偶不平缘咏史
在诗歌创作上,李振钧不愿流俗,他善于从咏史中观照现实,寄寓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他的咏史诗,最为出色的是《书淮阴侯列传后》等歌咏韩信的篇章。
登坛一对信奇才,钟室呼天剧可哀。爱好又将人断送,悔教丞相夜追回。
少年犹拜楚中尉,雍齿封侯意岂同。若使真王成帝业,功臣断不叹藏弓。
腐史微词托渺冥,冤含碧血化燐青。当时太息庭中语,曾有何人侧耳听。
天谴孤儿寄海南,杵婴高义尉佗堪。士官争说存韦姓,如意酖亡戚氏瘖。
组诗第一首感叹命运的吊诡。楚汉相争时,韩信登坛拜将后,向刘邦献以东征夺天下之计,刘邦听后大喜,对韩信言听计从。谁承想刘邦夺得天下后,吕后和丞相萧何谋划,在长乐宫的钟室诛杀了韩信,为刘邦解除心腹之患。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最终却毁灭了韩信。第二首诗揭露帝王权术的虚伪。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刘邦授印分封韩信为齐王,笼络住韩信,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使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夺取天下后,刘邦用张良计,把曾经背叛过他的雍齿封为什方侯,从而稳住了群臣。第三首诗对史书发出大胆的质疑。《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陈豨被任命为钜鹿郡守,向韩信辞行。淮阴侯拉着他的手避开左右侍从,在庭院里漫步,仰天叹息,说未来可以协助他反叛刘邦。李振钧质疑史书,这等绝密的庭中叹息之语,写史书的人又怎么能知晓?如果联系陈豨在战乱中被樊哙的士卒所杀,我们可以说李振钧的质疑不无道理。
第四首写的是清初以来流传甚广的“韩氏孤儿”的故事。据清初遗民作家来集之(1604-1682)《倘湖樵书》卷一载,当韩信钟室之难时,有客匿其孤子,求救于相国萧何,萧何心中愧疚,于是给南粤王赵佗写信,把韩信孤子送往南粤。在赵佗帮助下,韩信孤子以“韩”字的半边“韦”作为姓氏,得以避仇存身,并世代相传下来。[6]这个记载很像司马迁笔下的“赵氏孤儿”故事,司马迁作《史记·赵世家》写到赵氏孤儿的时候,与《左传》的大不相同,留下了很多疑问和漏洞,《左传》中的赵朔、赵婴没有被杀,更没有后来“赵氏孤儿”中最核心的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的故事,清初文人将“赵氏孤儿”转换为“韩氏孤儿”,将逃亡地点改在南粤,寄寓了那个时代遗民的情感。清初人们经常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扯起故国旗号,拥立亡皇后裔,起兵对抗朝廷。仅康熙年间来说,就发生多十多起“朱三太子”案件,例如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以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起义,他承袭明朝的制度,废除满族剃发令,将旗装脱下、长辫剪断,恢复明朝时的服装及传统汉人的发式,国号大明,年号永和,可以说,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朱三太子”已经成为一面不倒的思想旗帜。
李振钧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了解“韩氏孤儿”故事,在嘉庆十六年(1811)写下这组七言诗。他一生漂泊辗转,饱读各地诗书,接触各地风土人情。而遗民作家来集之的《倘湖樵书》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间,就有倘湖小筑刻本刊行。当然,我们无法探知李振钧阅读乃至给他思想启蒙的具体书目,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当时18岁的李振钧发唱惊挺,在官方认定的信史和民间的野史间,做出了自己的评判选择。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年轻的书生李振钧对宫廷权谋的痛恨,对人才摧残的惋惜,对英雄传后的深深欣慰。
李振钧诗集中还有一些咏韩诗作,如《漂母祠》:“君不见鸟尽弓藏良将死,皓首功名同白起。长乐受缚谁为怜,吕后何如漂母贤。”又如《吊淮阴侯》“杀信机先伏,留侯蹑足时。竖儒虚大计,腐史记微词。”这些诗也都是以议论为主,在议论中显示作者卓尔不群的识见。在其它的诗作提到历史人物的时候,李振钧都显示其独特的眼光,又如《有赠》其五:“一曲弹词蹙黛颦,马嵬遗恨袜生尘。阿环枉自为情死,万乘难生一妇人。”诗人清醒地看到,杨玉环只是皇权下的牺牲品,冤枉地为“情”而死。这些咏史诗总是出人意表,这源自诗人的心胸器局和狂放气质,正如他诗中所说:
心胸常抱百年愁,天地惊传一叶秋。半壁东南楼屹立,大江上下水中流。
——《黄鹤楼送家稼畲兄归里》
万古繁华终是梦,一年生意更无余。有人独立斜阳外,指点残红返太虚。
——《红叶》
气偶不平缘咏史,过犹可恕为多情。粗才敢问千秋事,也向旗亭浪得名。
—— 《检诗稿偶成》其一
“万古繁华终是梦”“心胸常抱百年愁”,这不正是诗人内心旷世孤单和愁苦的流露吗?尤其在那个压抑个性的封建末世。“有人独立斜阳外,指点残红返太虚”,诗人独立于风景之外,个体生命对外部世界的观照和融合,这种写法不正是他幼年“诗人工著笔,添个小茅亭”的思路延续吗?“气偶不平缘咏史,过犹可恕为多情”,正是因为心中慷慨不平,愁绪万端,诗人将其性情发露于笔端,将“性灵”内涵拓展到一个超脱于男女情爱的更高层面。
3. 踪犹萍梗性同鸥
李振钧的性格傲岸耿介,他的门生宝鋆对此有过评价。光绪十五年(1889),他在《味灯听叶庐诗草》序中指出:“顾性傲岸不羁,语言戆直,不合于时。”这时,离李振钧去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宝鋆说出了老师性格的特点,却并未走进老师的心灵世界,去真正读懂老师独立特行的思想情感。
李振钧的思想远超于那个时代,他对人们醉心的科举功名抱以深深的怀疑和否定,一直努力寻求生命自适的皈依之所。嘉庆二十二年(1817),他在《放言简振之》(其二)诗中说:“碌碌无为章句囚,狂歌醉卧碧云秋。不谙生产千金子,自立功名万户侯。末俗几曾逢笑口,古人未尽愿低头。谪仙只是能诗酒,已占人间第一流。”诗人已清醒地认识到,八股制义的文章只能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让人们碌碌无为;他宁愿在诗酒间寻求心灵慰藉,也不愿向功名利禄低头。
李振钧藐视功名,崇尚自由,这使得他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格格不入,难以和光同尘,融入到俗世中去。对此,李振钧早已感触,正如他早年在《醉里》诗中所说:
踪犹萍梗性同鸥,人世难忘旧酒楼。醉里不知身是客,夜深惟觉气如秋。最爱多情清净水,不因河曲强回头。
此诗写于嘉庆十七年(1812),诗人才19岁。这时,他已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一生萍踪不定,耿介疏狂,向往江湖白鸥之盟,不管日后际遇如何,也不会强求自己随俗俯仰。又如《叠前韵会振之》诗:“也如郊岛两诗囚,吟袂同悲宋玉秋。好丑随人初嫁女,盛衰阅世旧封侯。多才自古难青眼,好友于今渐白头。万事若能如我意,大河应亦向西流。”万事不能如意,多才难合于世,那么生命如何获得安顿呢?诗人在《奉酬竹醉兄兼以留别》诗中说:
语惊侪俗非豪气,交满人间总至情。留得蓬莱仙骨健,飘然摆脱一官轻。
此真天下奇男子,犹是当年旧性情。归来独对寒梅坐,一卷新诗信笔成。
生命的安顿、心灵的愉悦在于信笔而成的新诗,在于至情至性的亲友,更在于让人飘然归隐、像蓬莱一样的自然山水。而这三者,正是李振钧诗中反复传唱的主题。那么,到了道光九年(1829),李振钧初次参加会试和殿试,就拔得科场头筹,立即选入清显而高贵的翰林院,面对人生巨大的光环,李振钧又如何来面对呢?
让我们来看下李振钧夺得状元后的心态。道光九年(1829)九月,诗人衣锦还乡,过淮河口占云:“春风偶尔夺标回,未是凌云献赋才。一过关门争识面,何曾紫气自东来。”(《过淮河口占》其一)面对着眼前的莫大荣耀,诗人没有踌躇满志,而是收敛其往日的狂放,冷静地审视自己。回家后,写下《自题戴笠小像》:“故人若招隐,应有归来篇。”“有人笑指曾相识,春水桃花旧钓徒。”田园归隐依然是诗人心中的梦想。道光十年,诗人回京,留别同社诸君子诗云:“无语各沾巾,秋风陌上尘。故人勤赠处,我辈慎持身。高韵难谐俗,多文可济贫。儒冠容易换,不见去年人。”诗人劝谏自己立身谨慎,叮嘱朋友作文济贫,诗歌变得深沉而平和。在《题六安程芳野瘦鹤图》中,李振钧借诗明志:
独守天寒二十年,无端独占百花先。故乡消息凭谁问,梦绕空山野水边。
从17岁到顺天府参加乡试,到金殿传胪为一甲第一,整整二十年过去了。而故乡亲友,以及那里的田园山水只能在梦中萦绕了。在诗人的悲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此心付与白鸥盟的理想一直没有改变。
4.语直偏怜性最真
清代中期,以袁枚为代表的诗人大力创作性灵诗。这些诗歌多以爱情为主要题材,着重表现女子的才华、容貌及其命运,多用白描,分题吟咏,语言浅近而蕴籍,风格清新婉丽。李振钧有不少诗歌,就体现了性灵派诗歌的特点,如《临别》诗其一和其三:
漫调玉管拨银筝,踯躅离筵听不清。一样歌喉珠宛转,而今都带断肠声。
情丝难断泪丝垂,欲解卿愁倩阿谁。一法传卿牢记取,闲窗无事背侬诗。
又如《有赠》诗其三和其四:
芙蓉映水荻芦秋,旧住佳人号莫愁。一棹菱歌多感喟,西风帘卷最高楼。
闲写红笺问讯渠,已凉天气病何如。殷勤作答亲缄押,小字分明纸尾书。
这些七言白描素写,轻快流转,浅近情深,可看出李振钧对随园体诗的领悟与追随。另外,李振钧爱用七言组诗的形式,进行分题吟咏。道光四年(1824),李振钧作《美人》诗十八首,分别吟咏:塞上、楼上、马上、船上、枕上、座上、画中、曲中、镜中、醉中、梦中、病中、月下、花下、灯下、帘下、帐下、林下。这组诗无疑借鉴了随园体从各个角度分题吟咏女子形貌才艺的写法,以细腻的描写,展现诗人描摹和想象的艺术本领。道光七年(1827),李振钧作《舟行纪闻杂咏》诗十二首,分题吟咏:风声、水声、雪声、樯声、篙声、橹声、柝声、钟声、雁声、鼠声、棹歌声、梦呓声。这组诗保留了随园体分题细致刻画的写作特点,但因题材转为江河风光和船舻生活,风格显得苍凉雄浑。
随着年岁渐长,阅历越多,李振钧开始转益多师,熔铸百家,有意识地对随园体进行革新和突破。正如他在诗中所说:“潦倒敢夸能作赋,错教人当谪仙看。”“浪迹江湖追老杜,孤吟风雨似郊寒。”(《九日同人邀游龙门寺》)伴着生活的飘零转徙,李白、杜甫、孟郊等诗人都走入他的视野,使他的诗风转为苍劲雄浑。对前辈诗人,李振钧最喜欢的是苏轼。道光五年(1825),他在《夜坐感怀》其五诗中说:“一代风流能有几,千秋事业未为迟。文中飞将诗中史,俯首眉山进一卮。”眉山苏东坡的旷世才华和文采风流,深深吸引着疏狂率性的李振钧,使他有时模拟苏诗,如《题徐筱涟少尹误寻旧约第二图》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定是三生有约来”,就沿用了苏轼《狱中寄子由》(其一)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表达了对挚友的深情。在创作技法上,李振钧诗歌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多用虚词,工于起调。李振钧有意地学习杜诗,且有创新。杜甫常用以虚词入诗,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虚词的运用使诗歌痛快淋漓,自然流畅,李振钧受此启发,爱用虚词,且多置开篇。如:
可是先生宅,何如太傅墩。(《小园落成》其七)
岂独爱吾庐,还宜读我书。(《小园落成》其八)
敢以乘车日,而忘戴笠年。(《自题戴笠小像》)
也有园林一亩宽,偏逢山寺共追欢。(《九日同人遨游龙门寺》其八)
何因饱挂一江风,屹立高牙挺碧空。(《舟行纪闻杂咏·樯声》)
也曾问讯并头花,十五盈盈阿姊夸。(《莲舫强晋卿题是图》其一
这些都是开篇直接运用虚词,使得诗节起伏,气脉流转,显示出李振钧工于起调的才能。还有的诗歌全篇大量用虚词入诗,如:
何必陆居幽,浮家狎野鸥。此心原似水,不系恰同舟。叶满村前路,潮来晚渡秋。风斜兼雨细,亦自使人愁。(《谷舫小憩》)
已为云出岫,那敢问归期。石每横斜叠,花曾向背移。肯抛三径乐,不悔十年迟。惘惘将行意,东山知未知。(《留别余园》)
这些诗都大量运用虚词,如《留别余园》诗中的“已为、那敢、肯、不、将”等虚词的使用,使全诗气脉连贯,一气呵成。
二是句式拗峭,诗风峻拔。李振钧对宋诗也独会于心,对宋诗的拗峭句式揣摩学习,并时常运用于诗歌创作中。如:“石每横斜叠,花曾向背移。”(《留别余园》)“才多转不奈才何,人不能多尔独多。”(《少云作小照予题为众妙图赋赠》其二)“得原非福失犹幸,壮不如人老可知。”(《夜坐感怀》其五)这些诗句比较奇特,音节急促,使诗歌的内在情绪动荡起伏,传达出诗人内心的不平之气,诗风由此显得拗峭峻拔。
李振钧自幼起与堂兄李振翥相投,李振翥曾这样评价李振钧的诗歌:“貌肥谁信诗能瘦,语直偏怜性最真。”(《挽廉访兄》其七诗注)李振钧深以为然,他也曾自言:“黯淡秋心诗亦瘦,萧疏爽气酒余寒。”(《九日同人遨游龙门寺》其八)“瘦”字说明他性格的耿介,诗风的刚直。而李振翥“语直偏怜性最真”句说出了李振钧真率的性情,而这正是李振钧性灵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
综述,在清中期性灵派诗歌风靡诗坛的背景下,李振钧力主性情与寄托,在诗歌创作中以性灵诗学为底蕴,同时转益多师,熔铸百家,表达他对纯洁爱情的坚守,对科举功名的游离,以及对封建末世王朝的冷静思考,最终形成了深沉阔远、拗峭峻拔的诗歌风貌,成为嘉庆、道光诗坛的重要诗人。
[1][清]李振钧.味灯听叶庐诗草[M].清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2][清]袁枚.小仓山房诗集[M].清刻本.
[3][清]袁枚.随园诗话[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M].清刻本.
[5][清]齐彦槐.梅麓联存[M].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6][清]来集之.倘湖樵书[M].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责任编辑:胡光波)
2016—01—10
丁功谊,男,江西上高人,文学博士,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
I206.5
A
1009- 4733(2016)03- 0016- 06
10.3969/j.issn.1009-4733.2016.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