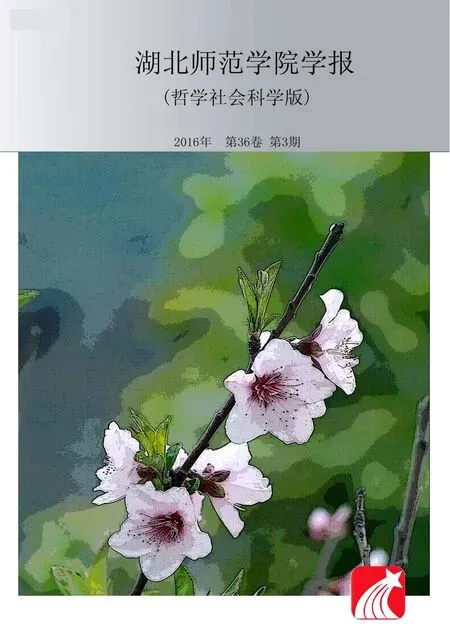“妖由人兴”
——先秦文献“妖”现象及其言说方式探析
王 静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妖由人兴”
——先秦文献“妖”现象及其言说方式探析
王静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妖,在先秦文献中多用以形容一些反常、怪异、不同寻常的现象。在神秘主义信仰之下,“妖”成为人们表达对各种不祥“征兆”的抽象理解和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因此,对于思想意识中的“妖”象的描述,重心仍在于劝谏上位者懂得“妖由人兴”之道,从而“修德从善”。这种对“妖”的言说方式和叙述表现,对后来汉魏时期“妖”现象的泛滥,以及魏晋志怪小说中“妖”形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妖;先秦;妖由人兴;言说方式
妖,在先秦文献中亦常作“訞”,或“祅”,亦通“夭”,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反常、怪异的现象。许慎《说文解字》云:“衣服歌谣草木之怪谓之妖,禽兽虫蝗之怪谓之孽。此盖统言皆为之祅。”又释“妖”字云:“地反物为妖也。”[1]《左传·宣公十五年》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所谓“地反物”,杜预注曰:“群物失性”[2],即自然界之万物失去它们的本性,出现各种反常的、通常带来灾异的现象。因此,“祅”(妖)兼指动植物类的变异,以至于“衣服歌谣”之怪也被称作“祅”。“妖”作为小说文本里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历来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小说中“妖”本体论层面的分析。本文侧重讨论“妖”的另一层面的含义,即怪异、反常之现象。这是先秦子书、史书中,人们对“妖”的普遍认识和知识信仰。此时的“妖”的意义还停留在对于一些反常、怪异、不同寻常的事物与现象的标识。笔者将通过梳理分析先秦文献所载“妖”现象的不同类例,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对上述现象的言说和评价方式,以此进一步了解古人的知识思想信仰及政治言说的特征。
一、反常为妖
“妖”作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范畴,其观念早在周时便已出现。这时期的“妖”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预示意义的反常之象,人们叙述时,多谓之“妖”或以“妖祥”连称。《周礼·春官宗伯》在记录“保章氏”的职责时已有云: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4]周代“妖”与“祥”在观念甚为接近。“祥,福也。凡统言灾亦谓之祥,析言善者谓之祥。”在这里,“妖(祥)”即是指一种以日月星辰及天气的变化来预示吉凶的现象。依周代的官制,“保章氏”乃是大宗伯的属官“太史”的一类下属。太史之官,集巫、祝、史于一身,“掌建邦之六典”,同时也广通星占、历数、卜筮之学。他们“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的权责中,就包括观“妖祥”之象来征验国家兴亡、预测社会未来命运的题中之义。又该书记录“眡祲”的职责时,云:“眡祲,掌十辉之灋,以观妖祥、辨吉凶。”[4]“眡祲”是“太卜”之下级属官,占卜预测自然在其职责范围之列。故此,在周代浓厚的巫史文化氛围之下,“妖”与卜筮系统有着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这种以四方百物的各类“妖(祥)”现象来预测人间命运的走向,其实也反映了早期原始信仰中的神秘主义自然哲学观,人们常以天上之象与地面人事相对应,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某必然之联系。以“妖”的征兆之意来预言人事的功能,正是古代“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5]传统的反映。
《左传·宣公十五年》记伯宗之言曰:“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5]《礼记·中庸》亦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耆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6]二者对于“妖”的描述,皆与国家兴亡相关,体现出一种“政事混乱——天降妖孽——国家存亡”的“天人感应”之逻辑。正所谓“天之降异,必有其故”,“妖”处于这样一个因果链条之中,其含义则为一种预示国家兴亡的反常现象。而“人”亦是此系统中决“国之存亡”的决定性因素,这从一层面揭示着“妖”与人事的关联,即“妖由人兴”意识的萌芽。
《左传·僖公十五年》:“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这里秦伯所言即是指僖公十年中,狐突梦中申生所说的“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异秦,秦将祀余”一事,故“妖梦”一词,杜预注:“狐突不寐而与神言,故谓之妖梦。”[2]这里,妖与梦占之事发生定向性的联系,所谓的“妖梦”其实指的就是一类对现实具有预兆性的梦。《左传·昭公十年》又载: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5]
郑裨灶所言的“妖星”即为“出于婺女”的那颗星辰。天以“日月星辰之异行”来预示人间即将发生的异常之事。因此,此处之“妖”所指代的就是一种具有预示意味的不祥之兆了。可见,这一时期的“妖”的涵义,乃主要是一种政治意味的、预示性的征兆。且最初多数情况下,这些“妖”与卜筮、梦占以及天文关系密切,常常并肩而行。
战国时期,谈妖说怪成为社会上普遍风气,各种“妖”象在侈谈灾异的时代氛围下异常活跃。此时,“妖”的队伍中出现了一批动物、植物性的妖,大量“妖”象,表现在有生命力的动植物,甚至人身上。如: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日月星辰,乱逆其行。赢绌逆乱,卉木亡常,是谓妖。”唯邦所□妖之行,卉木民人,以□四践之常,□□上妖,三时是行。“唯天作福,神则格之;唯天作妖,神则惠之。”[7]
“‘卉,草也’,所谓‘卉木亡常’,指草木非时而生,即后世所说的草木之妖。”[8]同样的动植物“妖”象亦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当是时也,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卉木蓁长。昔者天地之佐舜而佑善,如是状也。[9]
这条记载则从“妖祥不行”的正面表现,来说明其在政治清明中的预兆意味。而更多时候,“妖”的出现是伴随着时局动荡、国家败亡。“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作为征兆的“妖” 此时就承担起代天惩戒预警的职能。《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篇》有言:
其妖孽有生如带,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国,其音匈匈,国有游蛇西东,马牛乃言,犬彘乃连,有狼入於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而弥,鸡卵多毈,有社迁处,有豕生狗。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10]
在其中,除了日月星辰的“天降妖异”,还有像“菟生雉”、“雉生鴳”、“螟集其国”、“马牛言”、“犬彘相连”、“狼入于国”、“马有生角”,“雄鸡五足”,“豕生狗”等与人及动植物相关的妖异形态。“祅(妖)是生于乱”,这些有生命的“妖”一起大量集中出现,共同予君王以强烈警示之意,也象征着时下政治的混乱不堪。
从这些记载来看,“妖”以征兆之义出现在先秦大多数语境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这些文本叙述中,各种反常、悖理的自然事物和社会现象,均通过与人事活动相联,从而显示出的不祥之兆广泛被称为“妖”。但是,反常、怪异有时并不等同于负面、邪恶。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春秋左传正义》云:“降者,自上而下之言。当时秦人有此妖语,若似自上而下,神冯之然。”[2]这里的“妖”,是被认为附体于王室巫师的神灵,故能为秦人作出灵异的预言。这种意思,同见于僖公十五年:“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5]所谓的“妖梦”,也是指神降于狐突的梦中。由此之故,美得超越常态的人或事物,亦常以“妖”论之。如屈原《楚辞·招魂》篇:“郑卫妖玩,来杂陈些”,王逸注:“妖玩,美女也。”[11]《列子》中亦提到“妖靡盈庭,忠良满朝”[12],此“妖”有艳丽之义,用来描绘美女或女子美色,故有“妖女”、“妖冶”、“妖妍”等称谓。可能在谨严端方的正人君子眼中,“妖”所附带的艳丽妩媚之色彩,彰显着某些淫邪不正之征兆意味,这个意义上的“妖”则显示出美艳女色祸国殃民的焦虑和恐惧思想。
二、妖由人兴
先秦时期,对“妖”的解释代表了上层国家的权威定式,与“妖”相关的信仰,有着很强的实用、功利之特征。在各种历史语境中,“妖由人兴”说中的“人”很大程度上针对于最高统治者——君王,对“妖”的解释和评论则一般都是由巫官、史官以及各国中掌通古今的仁者贤人,比如申繻、师旷、子产、伯宗等。这些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知识精英,他们借“妖”来干预政治,讽谏约束当权者施行德政。“妖”与“德”常常互为其表里,内外为用,从而表达出对古代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的关注。《左传》中记载: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二厉公入。公闻之,问于申繻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3]
申繻用外蛇和内蛇的争斗来预示郑厉公将入郑之时,昭公将败,厉公必胜之象。以“蛇斗”之“妖”象,解释郑国国内政局的变动,目的在于劝谏鲁庄公深省“妖由人兴”之道进而“修善从德”。对申繻来说,“妖”作为“休咎之徵”的表现,其所预示的反常妖异现象与人类现实世界不仅仅是感应关系,更是因果关系,引发征兆和具体灾异的通常是人的行为,因此言“妖由人兴也”。可见,在“人事不修——妖异出现——灾祸降临”的程式之下,“人”是妖异出现的直接原因,更是直面“妖”象灾祸的责任人和反思者。这一点在《吕氏春秋·先识览》篇得到显著的体现:
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10]
“人事”是上天评判君主政绩德行的主要标准,它直接影响着国家、人民在未来的祸福。晋公为人“骄而无德义”,多行不义之事,导致“天妖”降临、“百姓郁怨”。因此,“人”行为失德、言语失当均会引起“妖”的产生,从而陷国家于危难。反之,如若君主勤勉执政,积极立德修身,则能“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同样,《吕氏春秋·季夏纪·制乐篇》中,记载商汤和文王事迹时,有言:
欲观至乐,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今窒闭户牖,动天地,一室也。故成汤之时,有谷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於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 “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10]
这段话中,商汤成为有“德”君主的典型,对于“有穀生於庭”的“妖”象,他主动“见妖而迎以德”反躬自省,早朝晚退,尽职尽责,故三日后“妖”消灾除。同样的,“寝疾五日”与“地动东西南北”所代表的疾病、地质灾害也被视为天示之“妖”。在文王心目中,“妖”象的出现,乃上天给予自己施政的警示与遣告,于是其深刻“罪己”,在政治上施行一系列措施来“交诸侯”、“礼豪士”、“赏群臣”,最终“妖不胜德”,文王成功“止殃翦妖”。
战国诸子百家中,最频繁引妖说妖的莫过于荀子。如《荀子·天论》篇云:“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13]”荀子作为战国时期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对妖异鬼神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批判“营于巫祝,信讥祥”等世俗迷信,认为“木鸣”“星坠”的自然“妖”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并不足以让人感到畏恐。且作为“物之罕至者”的自然妖异现象,其与人事活动并没有直接关联。而相反的,荀子认为可怕的是社会政治混乱之下的“人祅(妖)”,其《天论》篇对“人妖”进行了集中详细的阐释: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內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13]
这里荀子以客观的眼光审视自然界的怪异现象,一针见血指出在所有自然灾害掩盖下“人妖”的危害性。例如农业违背农时,政治失掉民心,米贵民饥,途有饿殍,这便是一种“人妖”;政令混乱,政事失当,这就是一种“人妖”;伦常失序,男女淫乱,父子相疑,君臣离心,引起内患外忧,这也是一种“人妖”。除此之外,荀子还将那些“口行善,身行恶”的险恶小人斥之为“国妖”[13]。这些所谓的“人妖”“国妖”,其实归根全在人祸,深刻说明了动荡时代之下“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的内涵,即“妖由人兴”。
可见,从“观妖祥,辨吉凶,求永贞”到“妖由人兴”再到“人妖”观念的提出,这是“妖”本质上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更是先秦时期“人”的力量和“德”的价值重新发掘和评估的必然结果。“妖”作为“天之意志”的表现,通过以自然之“天”为思想行为之基本依据,将“人”的生存合理性--“德”上通于“天”,这无疑将对世俗政治权力产生消解意味,尤其是对君主的权威、制度的规范以及伦理道德的依据发生影响[14]。这些富有政治意味的预言性叙述模式,强调当事人(君主)对自身责任反思和征兆的感应效果的应对,“资于人事”,以作“王事之表”的政治功用是所有“妖”之征兆背后的归结点。到了汉代,“妖”的概念被纳入阴阳五行的系统中,对于“妖”的记载多延续这样一种模式而稍作改变,即“人事不修——五行失序——妖异出现——灾害降临”。随着汉代官方神学体系的最终确立,这种由上层精英解释和评点的“妖”象越来越代表着封建国家的权威,一切违背和挑战此国家权威模式的意识和言论都无情的打上“妖”的污名化标签[15]。
三、有关“妖”的知识、信仰
春秋之前,“妖”的记载多零光片羽见于史书中,对其描述多集中在日月星辰之“妖”象。随着思想更为自由、多元的战国到来,诸子百家之学蓬勃而兴,宗教迷信和神仙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广泛交流。齐人邹衍把阴阳、五行思想结合,开创“五德终始”说,成功把“天人感应”的思想具体化。在这种神怪传闻和阴阳五行空前炽盛的环境里,大量的妖孽灾异、符命祥瑞的传闻为“妖”的内涵注入了哲理化和变异性的时代特色。
书成于魏襄王时的《竹书纪年》一书,记载有各种预示灾祸的荒诞怪异之“妖”象,如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周庄王时“玉化为蜮,射人”、“有兔舞于市”,宣王时“有马化为人”、“三十七年,有马化为狐”[16]。《荀子·王制》篇亦有述:“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13]又在《非相》篇言:“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13]可见,战国时期,对于“妖”的认知和叙述与各种实用知识相融合,通过阴阳之术、相术、卜筮、星算等具体的知识和技术来获取“吉凶妖祥”,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行为选择,“妖祥”也从另一层面表达着人们祈盼在硝烟战火中,获得生之“启示”的重要途径。此时社会,制造和传播妖祥谎言蔚然成风,以致魏文侯之相李悝还专门制定了“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的惩戒法令,以消“妖”风邪气。随着符瑞灾异、阴阳五行思想的大量增多,一些带有预示意义的妖怪故事,逐渐被一些子书、史书和杂史杂传体小说集中收录,出现了“古今纪异之祖”的《汲冢琐语》和百科全书式的《吕氏春秋》,它们对“妖”的记录,呈现出鲜明的哲理化色彩与系统化倾向。战国中前期《琐语》的性质,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云:“按汲冢书目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17]妖怪,即妖异之意,相书,则不出占筮吉凶之类。又在《华阳博议上》言:“《琐语》博于妖”[17]。该书专记妖异故事,一事一语,对“卜梦妖怪”现象的记载,多间涉鬼神,并杂以战国阴阳五行家和方术之语,使得“妖”的内涵在丰富驳杂之中哲理化色彩大大增加。而《吕氏春秋》通过“妖”象的视角来为封建统治寻找依据,其思想中亦杂糅战国百家九流之说。
战国时期,“妖”的范围和内涵获得空前拓展的同时,各种诡异反常的“草木鸟兽之妖”进一步向人类靠近,逐步具备了人的行为能力。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的《诘》篇中,就有许多鬼怪妖祥的描述,以及各种禳灾之法。如讲鬼怪,它有诱鬼、孕鬼、妖鬼等等。记妖祥,则有“虫豸断而复续”、“野兽若六畜逢人能言”、“□鸟兽能言,是夭也”。等等[18]。整理小组释“夭”为“妖”,认为这些“鸟兽之妖”都是作为灾祸异象予以记录的。类似情况在文献中同样也有记录:《开元占经》卷一一七引《吕氏春秋》曰:“乱国之妖,牛能人言。”卷一一八又引《吕氏春秋》曰:“乱国之妖,马乃言。”[19]《太平御览》卷八九九引《吕氏春秋》:“乱国之妖,有牛马能言。”[20]在这里,“鸟兽能言”、“牛马能言”的诡诞之象均成为国之将乱的预兆。
与此同时,“妖”的身上开始具有变幻异形的能力,这种“变异”能力的出现带动出一批“异形”之妖,如《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篇》中:其妖孽有生如带,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国,其音匈匈,国有游蛇西东,马牛乃言,犬彘乃连,有狼入於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而弥,鸡卵多毈,有社迁处,有豕生狗。[10]
“菟生雉”“雉生鴳”、“犬彘相连”、“豕生狗”、“马化为人”,这些“妖孽”之象中,不同种类或分属于不同种属的动物之间相互关联与彼此变异。这种细节化叙述使得“妖”所具有的隐喻性和暗示性增添了浓厚的诡谲灵异色彩。这就不仅突破了最初的巫官文化影响之下的“妖”之卜筮、梦占格局,更为两汉时期“服妖”、“诗妖”、“鼓妖”、“脂夜之妖”等“妖”象的泛滥[18],以及魏晋志怪小说中的“妖”形象塑造提供了文化背景和阐释空间。
四、结语
先秦时期,“妖”作为人们认识和表达社会秩序的方式,广泛存在人们的思想生活之中,代表着先秦时期普遍的知识背景和一般思想水平。其内涵上多指一种吉凶灾祸之兆,任何“天反时”、“群物失性”的奇异之象均可以“妖”贯之。这种在人类社会同源互感的传统观念上产生的“妖”,言说方式常以“人事不修——妖异出现——灾祸降临”的程式化形式呈现。人们通过对“妖”的记载和标识,呼唤“德”的力量和价值,进而显现古代政治社会秩序的特质。而“妖”在内容上丰富性和表现形态的多样性,也为汉魏时期的“妖”现象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73-674.
[2](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全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983-2437.
[3]罗曼玲.唐代小说中意识形态意义的“妖”[J].北京大学学报,2013(5):29.
[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1.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全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6-1315.
[6]俞仁良译注.礼记通译[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68.
[7]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
[8]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37.
[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6.
[10](战国)吕不韦撰、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0-956.
[11](汉)王逸撰.楚辞章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2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5.
[12](战国)列御寇.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68.
[13]方勇、李波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1:53-478.
[1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50.
[15]吕宗力.汉代的谣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74.
[16](梁)沈约注.竹书纪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03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30-43.
[1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160-523.
[18]王子今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339.
[19](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016-1022.
[20](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91.
[2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15-1522.
(责任编辑:王国红)
2015—11—10
王静,女,湖北大冶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I206.5
A
1009- 4733(2016)03- 0031- 05
10.3969/j.issn.1009-4733.2016.0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