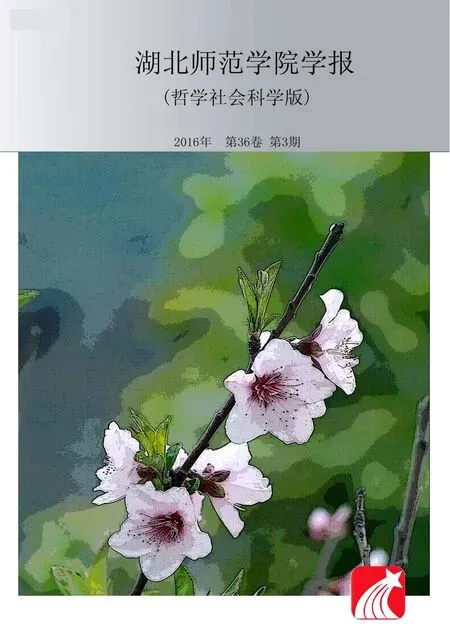落后之罪与罚:“十七年”小说的另一副面孔
柯弄璋,张园园
(1.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 430074;2.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0)
落后之罪与罚:“十七年”小说的另一副面孔
柯弄璋1,张园园2
(1.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 武汉430074;2.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435000)
“十七年”小说究竟是颂扬革命与解放的“红色经典”,还是“虚假和拙劣的”伪经典、伪小说?除开政治性与阶级性之外,它是否又保有艺术性与审美性,抑或这种审美空间到底有多大?对此,人们莫衷一是,一直缺乏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则既突破以往着眼正面形象的“红色经典”论,又不同于流行的艺术否定论,而从落后形象的读者接受来分析与评价“十七年”小说,指出它们存在从政治落后到伦理落后、情感落后呈沦漪效应的落后形态,以及围绕主体与环境两方面落后原因展开的两套惩戒策略,发现这些小说首先是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小说,形成了揭老底、看血统、分敌我、行惩戒的一系列教育方法,其次由于主客观关系认识不足等因素而造成小说叙事含混,以致它们跟时代意识形态构成同谋和越界的双重关系,同时亦折射出时代内含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十七年小说;罪与罚;政治
一、落后形态:政治、伦理、情感
什么是“落后”?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p849)。虽则他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会有“落后思想”,这些将成为“负担”阻碍他们前进,然而,哪些才算“落后”语焉未详。显然,它应该是“进步”的反面,而关于“十七年”中“进步”的内涵已有学者给出结论:“人民性”、“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立场”、“现实主义的方法”(p78-82)。按此标准,无论哪个阶级,只要他站在人民和革命的对立面,无疑就属于应当批评甚至消灭的落后者。
“十七年”小说同样坚持这种落后标准,严格以政治为中心,划分出先进与落后两大阵营,在《创业史》中是梁生宝带领的灯塔农业合作社对地富分子的斗争,在《艳阳天》中是萧长春等对地主马小辫和革命投机分子马之悦的揭发。但是由于艺术的加工,小说还为落后形象叠加了诸多条件:奸淫妇女如冯兰池(《红旗谱》),虐待妻女如王菊生(《山乡巨变》),幻想女性如马立本(《艳阳天》),丧失操守如张金龙(《新儿女英雄传》),外表丑恶如“阎王保长”周长安(《高玉宝》)。这些叠加的情节与描写不但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从伦理与情感层面强化了人物的落后。也即一旦某个人物被视作政治落后或说与正面主人公对着干,那么他必定是道德伦理的破坏者,而为了更直接地刺激读者对他的憎恶感,叙述者往往从外表、着装、行为习惯等方面进行丑化描写,以“周扒皮”、“王红眼”、“杨大剥皮”、“弯弯绕”、“把门虎”等带负面色彩的绰号代替人物称呼。与之相反,一个人政治上先进或者曾经落后而今改正,那么至少在叙述者看来,这个人对子女的暴打则是正确的(马老四说“我只认社会主义,不认儿子”(p480)),对女性的幻想是合乎情理的如陈大春与盛淑君、少剑波与白茹,像墙头草般在革命与反革命间摇摆也是能够原宥的如马连福。但其实,单就伦理与情感层面而言,这些人的行为本质上与上述马立本等人所作所为未必就不一样。
叙述者的不同态度表明了“十七年”时期的确是政治中心论,并且呈现为“政治——伦理——情感”渐次扩展的沦漪效应;也说明伦理和情感从不同角度会质询乃至解构政治,造成小说叙述的含混性。《山乡巨变》这样描写共产党员陈大春跟共青团员盛淑君的惜别:“男性的庄严和少女的矜持,通通让位给一种不由自主的火热的放纵......他用全身的气力紧紧搂住她,把她的腰子箍得她叫痛,箍得紧紧贴近自己的围身。他的宽阔的胸口感到她的柔软的胸脯里面有一个东西在剧烈地蹦跳。她用手臂缠住他颈根,把自己发烧的脸更加挨近他的脸......一种销魂夺魄的、浓浓密密的、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的传统的接触,我们的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写成为'做一个吕字'”。(p181-182)叙述者比较遵循自发情感的描写,且用词香艳,以至后来遭致“色情化”的诟病,批评的关键就在于它有悖于党员、团员纯洁和高尚的理想形象。说做“吕字”而不是接吻,说明周立波意识到可能遭到批评而有意隐晦,只是色情跟隐晦之间的分寸实在过于模糊或说太主观,而让人根本难以把握。然而,“十七年”小说却通过将读者注意力转移到对落后者的揭发与惩戒而遮蔽了这种含混,因为发掘落后者,同一切落后行为斗争是“十七年”小说的主要篇幅,也是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斗智斗勇的好看内容。那么,究竟如何惩戒?首当其冲须辨清落后原因(“看病抓药”),然后才好“对症下药”。
二、落后原因与惩戒策略
既然惩戒是个廓清的过程,那么查找落后原因也必须条理清晰。首要的是追查血统与出身,按照敌我二元逻辑明确区分落后主体的政治身份,以此确定落后的性质,因为“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p468)。虽然小说早就预设了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小资产阶级等政治身份,但它还是对之作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方法就是通过叙事者或人物回忆性的描述交待某个人物的过往生平。重述(再现)过去正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如地主过去对贫雇农的残酷剥削反映出当前斗争地主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对落后者血统和出身的追查目的之一便是确定他属于阶级敌人还是人民大众。《艳阳天》中合作社副主任马之悦对合作化的不热情开始被认为是认识没有提高(属于内部矛盾),后来追查到他曾勾结日伪出卖八路军,于是就被定性为反革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山乡巨变》中的龚子元同样如此。他们二人的狗腿子马立本、符贱庚跟着也干了不少坏事,但由于他们的过去表明他们是小知识分子、二流子农民,所以小说将他们处理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回忆性质的解释不过是将预设的观念加以具体演示,拒绝或说压制含混的叙述,绝对不允许出现像《丽莎的哀怨》中同情资产阶级贵族的叙述人,这点也是“林道静”曾受批评的关键。
对于政治身份的确认和区分其实已将落后原因归结到主体和环境两个方面。一方面,阶级敌人的落后似乎与生俱来,带有遗传特征,不仅阎王保长周长安剥削贫苦农民,其父亲周扒皮同样半夜鸡叫压榨长工,父亲叫康锡雪(吸农民血汗),儿子外号就叫“康家败”(《吕梁英雄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是阶级思维影响,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按财富积累情况将社会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呼吁后者对前者的强烈反抗,这种绝对唯一的分类标准和对过程与效果的强调,阶级敌人的落后和过错都是不言自明、长期存在的;第二,是原罪思维影响,即地主的罪恶是天生的,如《创业史》中的姚富成,这样就突出被剥削者反抗的天命色彩;第三,是本质论影响,敌人都是坏到骨子里的人,即便时代变迁,他们被党和人民打倒,却仍然延续着坏心眼、暗中搞破坏。当然,这种处理办法有失简单,缺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它也被普遍用来解释先进人物的先进性,萧长春、梁生宝们都是天生的先进分子,在陈大春身上,“一种是父亲熏陶出来的勤劳的刻苦的精神,一种是母系传来的豪勇的革命的气概”[4](p128)(其舅舅是革命烈士),他命中注定就是优秀的民兵队长和共产党员。另一方面,人民大众的落后主要是环境的制约与诱惑,如果没有马之悦、龚子元的威逼利诱,马立本、符贱庚也做不出那么多反合作化、反人民的勾当,《创业史》中的农会主任郭振山抱有单干致富思想也是受到了富农发家的刺激。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这些落后分子在政治上仍属人民群众,如今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应当歌颂的对象,他们中间虽有良莠不齐,但不能破坏这个群体的崇高地位,只能是外界环境导致的结果。这是早在40年代的延安就产生的规训方法,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老人。这种办法忽视了主体的复杂性,有失片面,是值得商榷的。
在落后主体的政治身份确定、落后原因清楚的前提下,“十七年”小说对落后者的惩戒就水到渠成了。惩戒的基本方针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的“专政”与“民主”。一是针对阶级敌人天生的落后,采取精神打压乃至肉体消灭策略。这是党对付敌人的一贯思路,在土改中就是要灭掉地主恶霸的威权,让广大农民不但翻身,更要翻心;在合作化中就是要打碎敌人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幻想,消灭个体主义气焰。在描写40年代以后的叙事中,精神打压是主要策略,即便愤怒的群众要求马上打死阶级敌人,党员们也是极力阻止而要求押送政府法办的,如马小辫、马之悦、康顺风、龚子元等,因为40年代以后党在区域性、全国性建立了政权,人民在政权下的一切行动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与制约。然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一旦在后者被党和政府拿下的时候,就熊熊烈火般燃烧,形成强烈的暴力冲动,非要毁灭掉什么不可,这就将对敌人的精神打压推向极端,即侮辱和践踏人的尊严,如“用枪托狠狠地捅”被缚住的龚子元,骂道“你他妈的,生得贱的死家伙”[4](p517)。相反地,在描写40年代以前的叙事中,如《红旗谱》中,对冯兰池这样的地主恶霸则实行了肉体消灭的策略。对阶级敌人采取这样的惩戒策略十分像延安整风时期对部分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一方面是掐灭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温情主义、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一方面是令其置身农民中间从事身体上的劳动,乃至被彻底消除。二是针对人民大众因环境促使的落后,采取党的训导、正面示范、亲友劝诫等策略。在五四时期,强调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所以需要进行个体启蒙;而延安以后,人民是赞美的对象,即使有毛病也可以耐心教育,因为他的毛病不是源于自身,而是外部环境具体地说就是旧社会被动造成的。所以,强调人民大众落后是由于环境导致,也就是突显教育的意义。对落后群众的教育主要就是党的说教如萧长春多次劝说马连福、典型示范如韩百仲和焦克礼等的模范作用、亲友动之以情理如父亲马老四和妻子孙桂英的说服。
可不论是在文本中还是在现实中,这两种惩戒策略都出现了混淆使用。如在《创业史》中,落后富农姚士杰就辩称自己的落后在于身处旧社会环境,“旧社会嘛,贪财爱利,哥地比一般庄稼人多,粮食打的吃不了,常有人借,还时给一点点利。这就是罪过,真正是罪过”[6](p145),言下之意他的落后也是旧社会的无奈之举,这当然是被作为他的一种托词,但也说明简单将阶级敌人的落后归因于环境确乎不太妥当。更值得思考的是在“十七年”及“文革”的现实生活中两种策略的混用。毛泽东在1957年就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5](p480),明确将知识分子问题视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无论是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还是反右运动,知识分子受到的却是运用在阶级敌人身上的精神打倒、肉体消除的专政策略。现实中求而不得,只好在文本中带着合法的伪装铺展,民主地或说温和地对待知识分子,也许正是“十七年”小说家们的一种期许吧。造成种种混淆的原因无疑出在对政治身份的划分和落后原因的确定上面,而这涉及到对“十七年”小说的再评价,尤其是对小说含混性与文本裂缝的深入认识。
三、“十七年”小说再评价
对于“十七年”小说人们有个普遍成见,认为它是重述民族国家神话,是起源性叙事,是国家精神与民族真理的象征。这是一种抽象化甚至抽空化的评价,并且也仅关涉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的某一方面,因为难道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就只有沉湎于过去的记忆与重新组装,它不更应该持有面向未来的积极向度吗?研究和评价“十七年”小说,不能脱离它的历史环境或说生产场域。“十七年”是向社会主义迈进、建设社会主义、艰难探索与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它被一种日渐神秘的“创造历史的动力”驱动,这种动力混合着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乌托邦激情以及最高领袖意志。“十七年”小说创作同样被这种动力驱动,成为一场浩大的、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尤其在艰难的岁月,对落后者的斗争会更加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决心与信念。如《艳阳天》将对马之悦等的斗争归结为“生活,就是战场啊”[7](p582),后来就有工农兵学员指出,“社会主义是如何得来的?是和平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吗?不是。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这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识到坚持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8](p71)。
作为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教育,“十七年”小说目标明确:以政治为中心,实现政治、伦理、情感的一元化。这主要体现在它们“政治——伦理——情感”渐次扩展的沦漪效应。政治落后者,则他的道德必定是败坏的,他的一些个人情绪必定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进步者,则他必然是道德完人,他的情感诉求被边缘化或被阉割。这是一种道德政治,也是一种情感政治。其形成原因既与乡土社会人伦传统相关,更离不开国家领袖的阐释和革命年代的实践。在毛泽东看来,“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1](p84),阶级性要高于伦理性,阶级的不同决定了伦理道德标准的差异,落后阶级的伦理必然腐朽落后,相反,先进阶级的伦理必然完美无缺。这也是为什么说“萧长春是个好人里面最好的人”[3](p54)。而政治对于人们情感的再塑造也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的事情。整风运动和讲话可以说彻底让知识分子丢弃了那种柔美的情感,延安生活也改变了从“五四”走来的女性情感与气质,“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的交际来往冲淡了”[9](p51)。在道德政治和情感政治的目标指引下,“十七年”小说发展了一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第一,揭老底。追忆每个人的过去,尤其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审查落后分子以前是否做过一些反革命、反人民的坏事。这是一场事无巨细的调查,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第二,看血统。它跟前者相辅相成,血统的好坏往往直接决定一个人是敌还是我。第三,分敌我。在经过调查和出身分析之后,挖掘出需要加以教育的落后者,并作出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判定。第四,行惩戒。对于敌我矛盾需要精神打压乃至肉体消灭,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应开展党的训导、正面示范和亲友劝诫等。这些方法并非作家在小说中的虚构与创造,而是来源于这样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此而言,“十七年”小说是它时代的共谋者,它在暗地里传播着时代的规训手段,无形中扩大这些非常规手段的影响,助长着其在下一个历史时期走向巅峰,造成全民的恐惧与癫狂。
与此同时,“十七年”小说也是时代的越界者,不仅是伦理、情感跟政治之间的张力引起的含混,更有围绕落后问题引起的主客观矛盾关系。前文引述已指出,毛泽东曾在40年代指出农民的思想“落后”会成为“负担”,而到了50年代,他却认为“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0](p238),承认落后的优越性。前后差异的原因主要由于毛泽东所在位置的改变:从在野走向执政,从革命转向建设。但共同点都强调人的意识的推动作用,相对忽视客观因素的制约,难道革命成功就真的光使用“小米加步枪”,没有工业基础的“一穷二白”就真的更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划分敌我阶层的标准也违背马克思主义,十分主观而含糊,毛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中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5](p467),是否抗日只是个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毫不涉及阶级成分,却被用来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在他眼里,“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不完全是由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等客观标准决定的,而是由更为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即对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政治觉悟'水平和政治活动的评价”[10](p364)。这种主观的划分造成政治的无理性,容易形成挟私报复的恶劣后果,而这是经历史所证明的。最后,将落后原因归结为主体与环境,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敌人的落后未必就是天生的主观意愿,而人民的落后也未必就是纯粹的外部诱惑,如郭振山的寻求发家致富除了受到富农的刺激,难道不也是小农社会中积留下来的惯习?总之,唯意识论、主观标准和机械的主客观论,这些都是“十七年”小说在对落后者的罪与罚中展露出的叙述含混,而它们同样内含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体现在大炼钢铁、红旗歌谣、雷锋精神、大寨精神等一系列国家事件与政治宣传中,同时它也预示着一个更富主观激情的时期即将到来。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寇鹏程.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进步”理念及其影响[J].北京:文艺理论研究,2015(4).
[3]浩然.艳阳天(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周立波.山乡巨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J].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26).
[6]柳青.创业史(第一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浩然.艳阳天(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杜时国.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艳阳天》读后[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2).
[9]赵超构.延安标准化生活[A].任宏、高梅主编. 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C].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
[10](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胡光波)
2016—01—12
柯弄璋,男,湖北黄石人,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张园园,女,河南鹤壁人,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I206.7
A
1009- 4733(2016)03- 0022- 04
10.3969/j.issn.1009-4733.2016.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