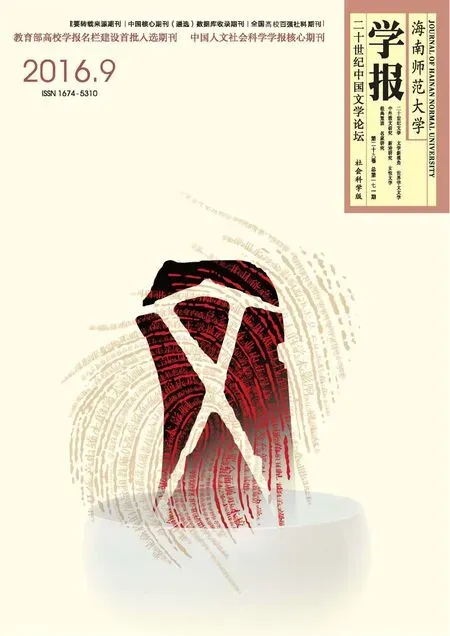家国同构:“中国梦”的民族精神认同基础
王赠怡
(四川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家国同构:“中国梦”的民族精神认同基础
王赠怡
(四川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
“中国梦”不仅是整个民族的,而且也是每个个体的。“中国梦”能达成个体全面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有机统一,就在于“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在悠久传统文化中所生成的集体精神认同的一种现代表达。这个传统文化生成的集体精神认同就是家国同构思想,它是“中国梦”将个体发展和民族复兴贯穿起来的理论基石。
中国梦;民族精神认同;家国同构
习近平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梦”不仅“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①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7日。习总书记的讲话特别注重中国梦的主体即中华民族与每个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处理,强调国家发展与个体人生出彩的一致性。这样,“中国梦”就把至伟的民族振兴和至微的个体追求置于了一个荣辱与共、相互依存的逻辑整体中,其深刻的哲学意味就在于:中国梦将民族复兴的普遍性与个别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中国梦”之所以能把民族整体和具体个人统一起来就在于其作为执政理念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认同中,这种精神认同就是深植于我们每个中国人心里的“家国同构”意识。“家国同构”的形成有着悠远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它远远早于人类文明精神有重大突破的“轴心时代”,是在各民族的不断融合中生成的。“中国民族初为炎黄二宗,始分终合,今并其名不存。于山东、江苏求夷族,不可得也。于山西、陕西求戎狄,不可得也。同化既久,界畔早失,截至今日,已伟然荟为一族。”②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58页。这“一族”就是中华民族。“家国同构”在民族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的治理、民族国家的生存等问题的探索中不断完善和强化,最终成为民族的精神信仰,这也是中国梦之所以能达成个体梦想和国家民族梦想统一的根本所在。“家国同构”能够成为中国梦的精神认同基础的合理性就体现在它的形成过程中。
一、族群社会的政治化衍变是“家国同构”的生成基础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群体社会的最突出文化表征就是有关“姓”、“氏”、“族”的身份认同体系出现。虽然血缘关系是群体社会以姓、氏、族作为组织形式的根本依据,但是这些组织形式所强调的内容又各有侧重。如“姓强调的是血统,氏突出的地域,族彰显的是武力”*张法:《中与中国审美关系的起源》,《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姓”从血缘上标明了早期社会群体的亲疏关系,具有恒常性。《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正义云:“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33页。由于姓与生相关,它就意味着种的繁衍和血脉的延续,被赋予了永恒之义。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就是从“姓”繁衍不断来理解“死而不朽”的,他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虽然穆叔认为范宣子的说法是“世祿”而不是“不朽”的体现,但是穆叔客观上也承认了“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的普遍性。不仅如此,同姓兄弟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人们衡量统治者人心向背的一条重要准则。如《左传·昭公七年》“诗曰:‘即鸟鸰在原,兄弟急难。’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兄弟之不睦,于是不吊;况远人,谁敢归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姓”就是“氏”“族”的不同称谓而已。《春秋左传·隐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云:“记谓之庶姓者,以始祖为正姓,髙祖为庶姓,亦氏族之别名也。”(《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注疏·卷三》)与“姓”相比较,“氏”突出的是地域性,在迁徙流动中“氏”是“姓”分支衍变情况的文化表征。《春秋左传·隐公八年》就有“胙之土而命之氏”之说,其正义曰:“胙训报也。有德之人必有美报,报之以土,谓封之以国名以为之氏,诸侯之氏则国名是也。周语曰:帝嘉禹德,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国,赐姓曰姜,氏曰有吕。亦与赐姓曰妫,命氏曰陈。其事同也。”*阮元:《阮刻春秋左传注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294页。由此可见“氏”的源起与地域有紧密关系。当然“氏”的含义并不仅且而此,正义又云:“《礼记·大传》云‘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是言子孙当别氏也,氏犹家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33页。从“子孙当别氏”看,“氏”是“姓”的分化延伸,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至于“族”,徐中舒《甲骨文词典》云:“从方人从矢,方人所以标众,众所以杀敌。古代同一家族或氏族即为一战斗单位,故方人矢会意为族。”*徐中舒:《甲骨文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735页。可见,族的最初产生与一个群落的安全防务相关,而其组织的划分依据可能与血缘姻亲或者地域相关。居于族内的人们往往会在生命财产方面得到保障而产生一种安全感、归属感,进而形成一种族群信仰。如《左传·僖公十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就佐证了当时人们这种信仰的专一。氏与族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正义认为氏与族是同一的,其差别在于“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言之则为族”,并举例说:“别合者若宋之华元、华喜皆出戴公,向鱼、鳞荡共出桓公。独举其人,则云华氏、向氏,并举其宗,则云戴族、桓族。是其别合之异也。”*(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33页。以姓、氏、族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建立的目的大致表现为这样几方面:其一,族类之间的相互扶助;其二,相互保险;其三,同族的繁荣。同时基于这样的目的又形成了一套伦理秩序:一是同祖者间血缘情感的唤醒,如我们对轩辕黄帝的祭拜就是通过共同的血脉深情唤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二是敬祖情感的激扬;三是依辈分、排行等世代顺序和出生先后所形成的长幼之序;四是由长老掌控的人治、道德统治。*[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91页。可以说氏族社会是国家形成的最初形式。如古文字学家唐澜先生便认为“中”最初为氏族社会中的徽帜,它有着重要的功能作用:“盖有大事,聚众于旷地,是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附。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列众为阵,建中之酋长或贵族恒居中央,而群众左之右之望见中之所在,即知为中央矣。”*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一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8页。可见先民最早的国家观念就是在氏族或者部落的“建中”之地发展而成的,而主宰国家的君王也是由居中央的酋长和贵族衍化过来的。
随着氏族社会向阶级国家的演变和确立,统治者逐渐把“姓、氏、族”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方式纳入到国家管理中去,以至于成为了安邦定国的经营谋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从现存的典籍看来,在帝尧的时期就注重家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尚书·尧典》就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的主张。《诗经·大雅·板》“大宗维翰”、“宗子维城”等语亦表明了宗族在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左传·文公二年》云:“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可见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宗族对公室完成治理国家有非常重要的裨益作用。而与公族相对的异族,就被居统治地位的阶层小心提防。《左传·成公四年》就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于统治阶级认识到宗族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安危,便自觉地参与到宗族的管理中;这种把宗族纳入邦国建构的举措事实上开启了家国之间的贯通渠道。如《左传·隐公八年》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所以“赐姓赐族”作为一种家族殊荣,并非人人可得。孔颖达正义云:“记谓之庶姓者,以始祖为正姓,髙祖为庶姓,亦氏族之别名也。姓则受之于天子,族则禀之于时君,天下之广兆民之众,非君所赐,皆有族者。人君之赐姓赐族,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赐者各从父之姓,族非复人人赐也。《晋语》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况余人哉?’”(《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春秋左传注疏·卷三》)这些以“姓、氏、族”作为组织社会的形式经过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渲染之后,亦成为了家族荣耀的文化标志。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有意识地自觉收集整理姓氏的谱系,官方也积极参与姓氏谱系的编纂和修订。宋人郑樵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述:“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篇》,又有颍川太守聊氏《万姓谱》,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故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咨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徐勉又有《百官谱》。宋何承天撰《姓苑》,与后魏河南《官氏志》,此书尤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氏录》二百卷,路敬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韵谱》,林宝有《姓纂》,邵思有《姓解》。”*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页。不过,政治因素介入也打破了主要以血缘为依据的早期社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尚书·尧典》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从《尧典》可见,宗族以外的“百姓黎民”同样重要。《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亦引用了《泰誓》该语),把民意放到了天意的高度。《尚书·洪范》就如何进行公天下的“王道”提出了要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左传·昭公三年》的“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已经从观念上超越了血缘家族的狭隘,以更博大的胸怀思考国家了。《论语》提出的“仁”的思想已经把血缘之爱升华为普天下之爱。如《论语·述而》云:“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颜渊》甚至打破血缘小家的局限,提出了四海如一家的理想主义思想:“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荀子那里,如何处理好与庶人的关系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思考天下安危的首要问题了。《荀子·王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随着大一统的天下观念的牢固树立,统治阶级在选贤任能方面更加开放。如曹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的用人机制以及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等等都对基于血缘宗族的门阀制度的削弱,宋代尤为突出:“‘士庶婚姻,浸成风俗’,即使后妃,也‘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倒是‘小官门户’。……‘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在宋代蔚为风气。那种依靠血亲门第来维系其特权的贵族势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朝闻、邓福星:《中国美术史·宋代卷(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这就使人们在由家到国的认识上更具了广泛性和普遍意义。当然最重要的是国家政权参加到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建构的举措不但打开了最基本社会组织形式——家与最高的政权组织形式——国之间联系的通道,而且使家族伦理(如尊尊、亲亲)与国家治理形成了内在的统一。如《礼记·大传》云:“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材用足,材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家族伦理的政治化演绎路径:基于血缘的家族、敬宗之爱是如何一步一步上升为国家百姓之爱,再由国家百姓之爱如何一环一环地转化为有效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
二、治国与齐家在理念上的同质是家国同构的认识依据
家国同构思想的生成还体现在治国和齐家之道在本质上相通,齐家与否通常作为治国的前提和考量准则。以舜为例,《尚书·尧典》说舜的家庭“瞽子,父顽,母嚚,象傲”,而舜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于是尧选用他作为继承人,尧启用舜的重要标准就是齐家。孔子亦赞叹舜说:“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告子章句下》)如果家都不治,何谈理国呢?!在《尚书·牧誓》里,周武王正是用这种家国同质的逻辑去声讨纣王的:“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那么,齐家何以能通向治国呢?那是因为齐家之法和治国之道在手段上同质:基于血缘的家之所以能与国这样最高的政治组织关系之间形成内在的联系,其要义就在于一个“亲”字。《孟子·尽心章句上》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礼记·中庸》还把“亲”作为君子的修身、知人和知天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齐家与治国在手段上的同构:由亲亲人到泛爱天下之众,也即是以事亲之心对待天下百姓,恰如孟子所讲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种以亲亲之心事民的治国策略早在《尚书》已经很明确了。从《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看,天子之所以能君天下,就在于他能以父母之心关爱天下百姓。《左传·昭公三年》同样认识到以亲亲之心治国的重要性:“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与《洪范》“天子作民父母”句不同的是“爱之如父母”强调的是以子女之心敬奉天下,不过,无论是“作民父母”还是“爱之如父母”都是根源于“事亲”的家庭伦理。而以“亲”作为贯通家、国关系的逻辑实践行为在本质上又最终表现为个人的伦理精神,那就是“孝”。因此,家国天下之重任实系于个人一身,在传统文化中个体价值总是被要求贯穿于家国的统一体中。《尚书·伊训》云:“立爱惟亲,立敬为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孟子亦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而考量个人对于家、国之本的价值意义则主要通过“亲”、“孝”这样的伦理精神体现出来。如《孝经·三才章》称“孝”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孝经·圣治章》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的《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还从个人的不同身份诸如“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等维度阐述了“亲”和“孝”对于家、国的建构方面所具有的社会实践意义。如《天子章》就引孔子的话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用了较多的篇幅肯定了“亲亲”与治国之间的必然联系,把基于血缘亲情之上的家族伦理之“孝”广泛纳入到国家秩序的宏大建构中,其把“孝”类化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举措已经充分彰显出家族伦理亲情与国家建构之间的互文性意义:由狭隘的亲亲之爱、敬亲之孝升华为百姓、国家之爱。这种典型思想还较丰富地体现于《孝经》其它篇章。如《广扬名章》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广至德章》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正是由于这种贯穿于家国建构的伦理精神已经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中,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把传统中的孝治天下的伦理精神创造性地转化为对人民的无私的爱。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把党对人民的这种深情提炼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邓小平同志1981年在《邓小平文集》序言中把党对人民的这种情感凝炼为:“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同志那里不仅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而且世界人民也是一个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在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通过重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来体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的深情爱戴。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各级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2015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亦以中国古人为榜样,把国家的治理纳入到传统家庭亲情伦理的考量之中,总书记动情地说:“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有学者认为考察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如何,不是看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多少范畴、原理,而是应看他们是否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就是实践的思维方式。*倪志安、杨志鹏:《“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中国梦战略”的方法论意义》,《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我们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升华,就在于能通过实践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我们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通过实践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家族伦理创造性结合起来的结果。
从中华民族的演变史看,对于个体来说“家国同构”思想中的家、国不是两个抽象的符号:一方面个体的实践贯穿于家国的建构中,个体赋予了“家国同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个体只有在家、国的关系中才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礼记·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个体作为“人君”“人臣”“人子”“人父”以及“与国人交”的行为者,使家国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统一体;同时个体价值、抱负施展的始基和依托正是家、国的存在,个体对象化的价值只有在家国统一体才能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实现。因此,传统文化总是把个体的价值成败与否纳入家国体系中进行考量,家的价值也同样需要从国家的层面予以确认。恰如《礼记·大学》所讲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故而,家国的兴衰荣辱总是与个体生存发展休戚相关。习总书记之所以自信地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就是因为家国同构的民族心理意识的广泛存在。“中国梦”也正是基于这一广泛而深刻的民族精神认同,将民族复兴的普遍性与个体发展的个别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王赠怡:《论“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美学化解读的意义和表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所以,“中国梦”的实现不仅从国家、民族的层面体现出来,亦从个体层面彰显出来。不仅如此,国家、民族梦想的实现也最终诉诸于每个个体的躬身实践。习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3月20日。当然与传统家国同构语境中所强调的个体对家国的责任和义务相比较,“中国梦”特别注重突出国家对于实现个体价值的责任和义务,充分体现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和个别差异性,而不是简单的以“类”的充分理由和口实去遮蔽个体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所以习总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
三、文人志士对“家国同构”的不断抒写强化了民族的精神认同
早在商周时期我们就有了“家国同构”的精神追求,这鲜明地体现在我们的典籍文化中。《诗经·小雅·瞻彼洛矣》:“君子万年,保其家室”、“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小雅·桑扈》:“君子乐胥,家邦之屏”;《左传·僖公十九年》引《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不仅如此,典籍中还流露出对国家生存状况的一种忧患意识。如《大雅·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瞻卬》“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甚至还涉及到民意的考量及内部关系稳定的处理:《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憂泄”;《大雅·民劳》“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在战国末期的屈原、宋玉那里这种家国同构思想已经转化成为中国文人矢志不渝的精神认同。屈原的“家国同构”情怀既见诸他那离乡去国的悲怆情感中:“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九章·哀郢》);“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远游》)。又见诸报国无门的绝望中:“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九章·哀郢》);“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九章·怀沙》)。背井离乡的悲怆裹挟着报国无门的绝望真实地呈现了屈原内心深沉的家国忧患意识。“屈原的‘深固难徙’、‘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绝不是出于‘洁身’,更不是出于‘泄愤’,而是出于他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和信念。”*董运庭:《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那么屈原的爱国思想基础是什么呢?无疑是其“家国同构”情怀的深沉坚守,正所谓“深固难徙,更一志兮”(《橘颂》)。屈原在《离骚》开篇就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来呈现自己的家族世系,其目的就是要表明他与楚国血缘上的渊源关系,屈原对这种渊源关系的重视表明楚国对他来说家国是一体的,他所眷顾的“故乡”、“旧乡”大抵是关乎家、国的双重喻指。屈原爱国思想之深切至今为中华民族所敬仰和讴歌。在宋玉那里我们同样感受到其深沉的家国同构情怀:“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九辩》)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屈原和宋玉文风“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其实屈原、宋玉特别是屈原对后代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们的文风上,更主要地还体现在他们那种强烈的家国意识上。从《礼记·大学》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国同构观念的实践路径如何在个人那里得以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随着汉代《礼》的经学地位的确立,家国同构思想就演变成为了民族精神普遍认同,个体生存与家国盛衰休戚与共,兴家立国也成为历代中国文人的共同追求,这种情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演进中愈来愈得到强化,我们从历代文人志士的诗歌创作中就可以见证到这种浓烈而深沉的情怀:六朝江淹《荐豆呈毛血歌辞》“愿灵之降,祚家佑国”;唐代刘商《金井歌》“赡国肥家在仁义”;元稹《遣兴十首》“理国如理家”,杜牧《冬至日遇京使发寄舍弟》“樽前岂解愁家国”,吕岩《赠刘方处士》“悠悠忧家复忧国”;宋代邵雍《家国吟》“邪正异心,家国同体”,冯时行《和王祖文》“忧国忧家连梦寐”,李处权《贺雨》“忧国如家愿年丰”,赵蕃《宜春道中赠邢公昭二首》“问君家在离骚国”,洪咨夔《送兴元聂帅》“忧国如忧家”;元代侯善渊《满庭芳·太古真风》“修家国,臣忠子孝,民业自安淳”,谢应芳《题杜拾遗像》“国破家何在”;明代瞿佑《旅舍书事》“平生家国萦怀抱,湿尽青山总泪痕”,韩邦靖《感事》“便因家国泪横流”,邢侗《送方胥成之蓟门塞》“纷纷家国堪垂涕”;近现代谭嗣同《戊戌入都别友人》“家国两愁绝”,梁启超《澳亚归舟杂兴》“姹女不知家国恨”,秋瑾《七律》“如许伤心家国恨”,宋教仁《晚泊梁子湖》“家国嗟何在”,郁达夫《秋兴》“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上述诸例表明,家国同构思想正是在无数文人志士的不断抒写中得到强化,并升华成为民族普遍的精神信仰和心灵家园。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投入到了惨烈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家国同构”的民族精神信仰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在求得民族独立的抗争中同仇敌忾、前赴后继。这一时期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的就是《保卫黄河》这首抗日救亡之歌了,尤以“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之词最能震撼人心,其要害就在它唤起了我们深沉的民族情操——“家国同构”。从上古到近现代,“家国同构”思想是我们民族能够生生不已、繁荣昌盛的精神法宝。所以习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15篇讲话系统阐述“中国梦”》(2013年6月1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619/c40531-21891787-3.html。正因为中国人有“家国同构”思想的普遍认同,所以每当中华民族到了危机的时刻,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信仰就会自觉转化为浩浩汤汤的精神洪流,激励仁人志士投入到民族自救的实践抗争中去。这种精神信仰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民族现象感受出来,那就是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了。每年春节期间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回家,短短几天的合家团聚折射的却是中国人的那种强烈的亲情之爱和浓烈而温馨的乡恋,正是这种信念构成了爱国主义的基石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有了它,我们就形成了由家到国的情感升化,这也是习总书记“中国梦”特别强调个体梦想价值的根源所在。“家国同构”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和发展中积累下来的最为宝贵精神财富,它依然是我们今天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法宝。一个外国学者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称之为“礼治”的社会主义:“突破宗族框架的国家规模的礼治社会,构成其物质基础的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依赖‘大公无私’的公有性而实现的重工业化,以及支撑这些新社会关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讯网络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些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才有了1987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也就是对‘私有性营利’活动的开放。”*[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91页。从其描述看,我们说这种“礼治”的社会主义正是我们党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家国同构”政治理念所做的现代转换,这对社会主义的初期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迫切要做的就是如何把“家国同构”的传统思想和当前中国深化改革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思维方式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念,而“中国梦”正是适应这一需求而生的经典范例。习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03月17日。“中国梦”之所以能将国家的梦想和中国每位老百姓的个体梦想统一起来,就在于“家国同构”根植于每位中国人的心灵中。想起佛法大师慧能有一句经典的话:“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寻菩提,恰如觅兔角。”(《坛经》)同样我们政治的现代性也万万不可离开文化母体的支撑。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可见习总书记以“中国梦”作为执政理念的举措实际上就是为中国政治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一个富有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中国模式。
四、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家国同构”是无数仁人志士几千年来为图谋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而探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和精神认同,其关键在于将个体的价值诉求与国家建构置于一种互生共荣的互为因果的统一体中,它给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理想的政治美学图景。构建于“家国同构”的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中国梦”,势必让每位中国人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体全面发展的多重福祉中充分享受政治美学所带来的生存愉悦。
(责任编辑:王学振)
Homogene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the Basis of Recognition for the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Dream
WANG Zeng-yi
(SchoolofFineArts,Sichuan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Dazhou635000,China;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The Chinese Dream” involves not only the entire nation but also individuals. The reason for the Chinese Dream to make an organic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es in its giving a modern expression to the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formed in the long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governing idea. The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refers to the view that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 are homogeneous, which is a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connect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wi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Chinese Dream; collective spirit recognition; homogene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
四川省教育厅2015年重点项目 “‘中国梦’美学化解读的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5SA0107)
2016-05-11
王赠怡(1972-),男,四川平昌人,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美学、艺术美学。
B83-02
A
1674-5310(2016)-09-0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