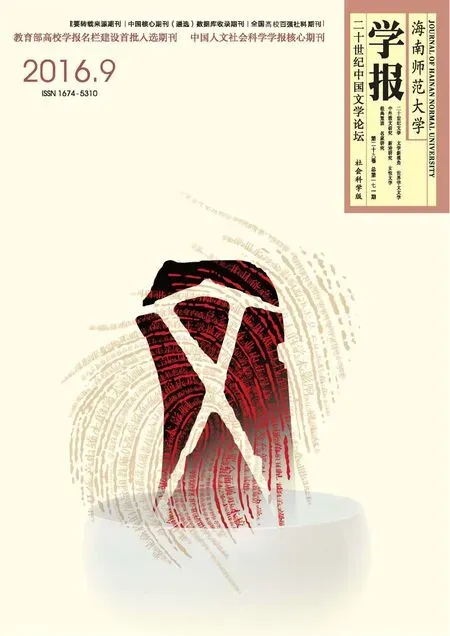时空扭曲下的“文革”镜像
——以毕飞宇小说《玉米》《平原》为中心
赵 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时空扭曲下的“文革”镜像
——以毕飞宇小说《玉米》《平原》为中心
赵斌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文革”时期为毕飞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反思极权的时间视角,王家庄等地点又提供一个绝佳的空间视角,将人物锁定在这样一个最佳的“时空”之下,能最大程度放大“文革”那段被扭曲的历史,也能放大“文革”的种种乱象。具体来说,在《玉米》《平原》等“文革”小说中,一个方面,毕飞宇有挥之不去的时间情结,他对时间、历史特别敏感,对挖掘“文革”那段被扭曲的历史更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时间、历史是通过文化地理空间、日常伦理空间和身体性空间这个“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来展现的,即用时间空间化的写作模式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来展现那段荒谬的时间、历史;反过来,时间、历史也烘托了小说的空间,从而达到了时空一体的叙事效果。
毕飞宇;《玉米》;《平原》;“文革”镜像;时空关系
学界对《玉米》(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文革”小说做了大量的阐释和解读,但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没有把毕飞宇对“文革”那种独特的洞察完全披露出来。评论家张均说,“在后革命的今天,评论家已习惯于用专制与反专制的政治权力模式去解读所有‘文革’背景的作品。”这种模式化的“文革”解读必然留下很多历史的漏洞。毕飞宇也认为,“我们的历史阐释是极其卑鄙的……它像一个盗贼,洗劫一空之后布置了一个现场……把疑点指向了一群无辜的人。”这样的历史阐释是有问题的,历史书写也是有污点的,所以,《平原》是他“‘必须’写的作品,不管你给它一个什么评价……”他必须给“内心一个交代”。因为,“七十年代的中国太重要了,也许对全人类都是重要的。”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①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换一句话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革”的亲历者,必须直面那段惨痛的历史,因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从这里下手,上溯、向下都不能撇开这样的问题。”②蔡翔、费振钟、王尧:《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4期。那么,毕飞宇是如何解密那段扭曲的历史呢?他说:“权力,或者说,极权,一直是我关注的东西。”③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当然,对极权的痴迷不是毕飞宇的专利,李佩甫、刘震云等作家也热衷其道,但毕飞宇的极权阐释却别具一格。笔者认为,“文革”时期为毕飞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反思极权的时间视角,王家庄等地点又提供一个绝佳的空间视角,将人物锁定在这样一个最佳的“时空”之下,能最大程度放大“文革”那段被扭曲的历史,也能放大“文革”的种种乱象。具体来说,在《玉米》《平原》等“文革”小说中,一个方面,毕飞宇有挥之不去的时间情结,他对时间、对历史特别敏感,对挖掘“文革”那段被扭曲的历史更是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时间、历史是通过文化地理空间、日常伦理空间和身体性空间这个“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来展现的,即用时间空间化的写作模式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来展现那段荒谬的时间、历史;反过来,时间、历史也烘托了小说的空间,这样就达到了时空一体的叙事效果。
一、挥之不去的时间情结
毕飞宇对时间、历史的书写非常痴迷,但他对众多的历史阐释极其不满,他说,“历史一是指存在,一是指阐释。对存在,我们不能说什么”,但是,那些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历史阐释”“大多是理不直而气壮的撒谎”*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在他看来,“时间是人类在深层次上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赋予的需要。”*〔奥〕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页。也就是说,历史不仅是我们的过去,它也孕育了现在。“在关于不幸事件的意识中,我们不仅倾向于了解过去个别发展的相对封闭性,而且还倾向于了解迄今正在圆满结束的整个历史过程。”*〔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307页。
毕飞宇对时间、历史一直都很迷恋。在其早期小说《叙事》里,毕飞宇采用了把历史的真相与个人生命的感悟相结合的视角去审视奶奶被强暴而众人缄默的家族秘史,这种猎奇心理让他沉醉在各种隐秘的时间、历史里,同时也激发他去解密时间、历史。对于一个“文革”亲历者,那段荒谬的历史给毕飞宇造成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革”本身,一是对“文革”的荒谬阐释。
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是说出唯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捷〕米德·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6页。《玉米》《平原》等小说可以说出“文革”历史中不一样的乱象,通过小说言说浮现那个逝去的历史酷虐,通过扭曲的时空叙事去探寻被历史烟尘蒙蔽的历史往事,去探查一个时代的真相,去探秘历史悲剧的来龙去脉。显然,反思“文革”的最好方式是直接进入那段荒谬的时间里,直接进入历史现场。在《玉米》《平原》等小说中,“1971年”、“1976年”显然都不是平常的时间,它们凝结了“文革”历史的“刀光剑影”,充满着“文革”历史的盲动和狂欢。洪治纲说,小说《平原》“不仅将叙事时间严格地控制在1976年的某些片段里,而且将空间始终锁定在王家庄的狭小天地中……”*洪治纲:《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在扭曲的历史时间里,人物也相应做了夸大的形塑,以此呈现“文革”种种乱象。例如,在小说《平原》中,端方熟稔于民间伦理的盲动中,体现了民间生存智慧的阴毒,同时也表现出虚无的生命意识;吴蔓玲则沉醉在革命伦理的乌托邦的想象中,体现出对国家权力的盲从和痴迷。同时,性别觉醒后的个体生命伦理也深深撕裂她虚无的灵魂。其他如老右派顾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信,混世魔王的小商人的投机,乡村能人兴隆对汽水制作的炫技,孔素贞对封建迷信的虔诚……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映射出1976年这个特殊时期的非理性的政治热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喜欢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时间节点上加以考察。在小说中,毛泽东逝世是一个特大的历史节点,作家把恶讯传来后的王家庄的乱象无限放大,以此来洞察动荡历史带来的人心的失衡。如小说这样写道:“王家庄的社员体现出了高贵的自觉性,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这样做不只是因为团结,骨子里是害怕。”总而言之,小说中的这种时间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但这种时间、历史是通过文化地理空间、日常伦理空间和身体性空间这个“三位一体”的空间架构来展现的。
二、文化地理空间
文化地理空间是比较宏大的一种空间,此概念借用了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的定义。克朗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这一点对本文的研究非常有用,小说具有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小说具有地理学意义,有些新鲜。“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地理空间的书写往往能够揭示一段特殊的时间、历史。
在毕飞宇的“文革”小说中,文化地理空间主要是王家庄,同时还有与王家庄相对立的潜在的文化地理空间——城市和天。在一个传统的幽僻的乡村文化地理空间——王家庄里,“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在这个幽闭、静止的文化地理空间里有一套传统的交往逻辑,此种“交往的逻辑起点在于维护时间和空间是的两个稳定性,一是时间的延长性与连贯性,二是空间上是彼此依赖性及地域认同。”*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但这一切在“文革”时期被打破,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发展,城市的五彩空间使乡村人趋之若鹜;二是来自知青下乡,知青的植入打破了乡村文化地理空间的平衡。简而言之,“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费孝通:《乡土中国》,第94页。小说《平原》具有这种文化地理学的意义,知识青年下乡打破乡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诺沃特尼说:“都市与没有沥青路面的或者没有连接国家电网的村庄之间的差距,是时间上和经济上的差距。”*〔奥〕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金梦兰等译,第15页。那也就是说城乡之别不仅仅是空间的差距,更是时间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自然促使人物进行空间位移。在《玉米》《平原》等小说中,有两个相对的空间移位:一是从城市到乡村;一是从乡村到城市。两种空间位移映射了“文革”的种种乱象,既包含物欲权欲的肆意张扬,也包含着人性的扭曲堕落。
(一)从城市到乡村
王家庄这个文化地理空间,充溢着躁动不安的狂躁气息,暗藏着破坏(指端方等)和征服(指王连方、吴蔓玲等)的欲求。毕飞宇面对这一“文革”乱象时,并没有“全盘地沿袭整体性的历史常识,而只是从历史的整体性中找到那些与人物生命相辉映的精神禀赋,使人物的存在获得细致灵动的延展空间。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空间又往往是超越客观逻辑的非理性的存在”*洪治纲:《1976:特殊历史中的乡村挽歌—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也就是说,“文革”时期的乡村文化地理空间(王家庄)给小说人物的畸形成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吴蔓玲、混世魔王、顾先生、兴隆和端方等可以看作从城市到乡村的一类人。从城市到乡村是一种被动的空间位移,蕴含很多不为人知的无奈和心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吴蔓玲、混世魔王等知青从城市来到王家庄。顾先生是老右派,属于旧知识分子思想再改造,也从城市来到王家庄。兴隆和端方归属于这一类人物似乎有些勉强。兴隆是当兵转业归乡,端方是学习毕业归乡。但总的来说,这五个人物都有着从城到乡的空间转移以及伴随着的身份转变。当然,不同身份的人物对现实的认知必然不同,也必然加剧人物心理撕裂和创伤。而最关键的是,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碰撞与扭结,衍生出种种“文革”乱象。
一般来说,城市文化地理空间隐喻着一种革命政治文化,乡村文化地理空间隐喻着一种民间传统文化。人物从城市到乡村,人物的根性里还是对政治革命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但人物毕竟回到了乡村,到不同的山上就要唱不同的歌。正如董之林所说:“即使在政治环境最为激进的年代,由于小说与其新老传统的关系,也没有被政治完全所决定',被纳入‘一体化’轨道。”*董之林:《当代小说的传统延伸》,《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2期。
吴蔓玲对民间文化有深刻的体悟,这是能够立足于王家庄这个文化地理空间的主要原因。吴蔓玲为了实现她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她掩埋自己的性别与来历,放弃“城市”身份与“女性”意识,尽量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去。因为她知道,“在政治权力话语之外,还潜藏着一条与其相对应相平衡的民间话语线索。”*张卫中:《“十七年”农村小说话语的分层与配置——以〈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中心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吴蔓玲没有忽视这一点。刚刚来到王家庄,吴曼玲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两要”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要做乡下人和要做男人。吴蔓玲一口地道的王家庄土话很甜,见到男女老少,都很平易近人,摆出“亲民”做派,尽快地拉近了“和贫下中农的距离”。因为吴蔓玲知道,“关系没有边界,会引发处于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也无法限定,它是扩散的,广泛的,可转移的以及流通的。”*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第2页。同样是知青的混世魔王对民间伦理有痛彻心扉的认知,因为“城市到处是陌生人,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与人的疏远”*〔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第50页。。混世魔王带着城市陌生人的关系逻辑莅临王家庄这个乡村文化地理空间必然会碰壁,他没有吴蔓玲那样有先知先觉,到了最后他才彻底洞察乡村熟人关系逻辑的。到了最后他才醒悟过来,即使在心里可以不把王家庄看作一个家,但是,在表面上必须把它弄成一个家的样子。
老右派顾先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很痴迷,一直在制造着各种虚无的革命神话,因为,“革命神话为乌托邦思想充当了避难所,并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神秘的、不可预测的说情者。”*〔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7页。顾先生显然沉迷于城市的那套乌托邦逻辑,对民间文化的体认与混世魔王很相似,也有着痛苦的认知。小学校那令人惊魂的一刀,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乡村文化地理空间的盲动与血腥并存,这是民间文化的一个极端方式。顾先生是端方的精神之父,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端方都会求教于他。端方和兴隆都是乡村能人,他们对乡村的民间文化和生存智慧都熟稔于心。例如,在大棒子溺水事件中,端方的民间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大棒子的身上已经飘散出很不好的气味了……实在令人揪心……但是,端方有底……裁判终于出现了,是四五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是,事件是靠民间力量解决的。这正如孟繁华所说,“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二)从乡村到城市
毕飞宇说:“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毕飞宇:《沿途的秘密》,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第22页。这是典型的中国鬼文化。“人在人上”的内鬼促使村民逃离乡村文化地理空间,向城市文化地理空间进军。从乡到城是一种主动的空间位移,蕴含很多侵蚀人心的物欲与权欲。在小说《玉米》等三部曲中,玉米的心不在乡村文化地理空间里,而是在城市及天上等文化地理空间里,天是城市的一种。和彭良国确立关系后,“天”不知不觉地融入到玉米的生命中,然而,天是漂浮的,最终抛弃了她。接着,另一片天——郭家兴出现了,郭家兴是进城的表征符号,也是城市对乡村的侵犯标记。玉秀为了进城,意外怀孕使她成为断桥镇茶余饭后的笑料。玉秧进城的代价也是毁灭性的,魏向东能够随便凌辱玉秧的肉体,更能够摧毁她反抗的精神意志。从这些可以看出,乡村人在力图走进城市文化地理空间的路途中,扭曲了人性,逐渐滑入欲望的深渊之中。这是一种“文革”乱象。
小说《平原》也是一样,小说只写到中堡镇,城市文化地理空间大都是通过一些话语暗示反衬出来的。顾先生、吴蔓玲、混世魔王、端方等人的身份转变本身就标示着城市到乡村、乡村到城市的空间游移。通过他们的叙述、他们的故事揭示出他们对城市文化地理空间的欲望。在小说《平原》中,主人公端方上学的惟一理由也是为了能够有一个“前途无量”的结局。但事与愿违,下学归乡后的失落,让他觉得“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的恐惧”。赤脚医生兴隆当过兵,和端方一样,没有留在城市,但必定见过大世面,言谈举止也不一般。兴隆也深谙“人在人上”之道,所以他“一门心思建议端方去当兵”。
“人在人上”是一种冥顽不化的“官本位”思想幽灵。作为土生土长的乡民,他们深知逃离乡村,遥望梦想中的城市是成为“人在人上”的最佳途径。端方说:“我只想到兴化去。中堡镇也行。”所以,端方见到吴蔓玲也会恭恭敬敬地说:“吴支书。”志英的妈看得更透彻,在乡村立足没有权力庇护是不行的,甚至一个女人的结婚宴会上也需要一个村干部“撑场面”,否则,“总是寒碜,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过门之后被婆家人欺负也说不定。”
毕飞宇说:“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毕飞宇:《沿途的秘密》,第24页。这话非常精辟,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对的。在小说中,吴蔓玲似乎和混世魔王不太一样。混世魔王对家乡南京这个文化地理空间非常憧憬,他的南京口音一直都没有变,南京的冰棒是他的美好记忆。吴蔓玲对混世魔王似乎很厌恶,她看不起他是一个小店员的后代,认为混世魔王投机心很重,因为,“他这样过分地卖命,目的是为了早一点离开。”其实吴蔓玲和混世魔王是一丘之貉。因为,洪主任的话让吴蔓玲萌生了很多政治野心,她感觉自己能够“前途无量”。也就是说,她前面诸多努力、种种异化行为都是想捞取政治资本,她想当更大的官,以便能够顺其自然离开王家庄,回到城市文化地理空间中去。顾先生是和吴蔓玲一样的人,他更希望自己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够早日回到城市文化地理空间去。
三、日常伦理空间
用城市和乡村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文化地理空间来揭秘“文革”乱象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小说的时空往往是融为一体的——时间空间化。例如,大队部等空间景象有着很深的“文革”印记,这种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是一种历史的诉说。换一句话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所以,我把比文化地理学空间(城市、乡村等)小而具体的诸如大队部这样具有一定的伦理意义的日常空间叫做日常伦理空间。
日常伦理空间在毕飞宇“文革”小说中其实是很多的,诸如大队部、学校、家庭、收麦场、养猪场、废旧厂库等等。这些日常伦理空间从各自角度反映出“文革”时期的施虐和无序,即“文革”乱象。
大队部无疑是最重要的“文革”的时空标签,是能够呈示乡村政治伦理的一个空间。并且,乡村喇叭是大队部的标志。到一个地方找村支书,朝着喇叭方向就能够找到。乡村喇叭是权力象征,甚至,“村里胆小的人一听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裤裆立马就湿漉漉的。”*崔东汇:《喇叭》,《杂文选刊》2010年第10期(下)。毕飞宇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村庄的高音喇叭永远在支书的家里。”*赵允芳:《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村长形象演变》,《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很显然,喇叭在王家庄是一个有意味的政治符号。小说《玉米》中,喇叭两次出场都有政治的意味,儿子王红兵的出生和彭国良的到来都表征王氏家族权力的延续与再生。另外,王连方在家里可以通过喇叭向全体村民训话,甚至,王连方的老母亲也能够用高音喇叭喊话。从中可以看出,村支书家庭空间和大队部空间往往是重叠的,换一句话说,大队部空间是可以挪移的。王连方可以把大队部移到自己家里,也同样可以把这种权力空间延伸到其他家庭,王连方与王家庄众多妇女的性事就是这种空间挪移的象征。小说《平原》中的支书吴蔓玲也是如此,她就住在大队部,家庭空间和大队部空间是叠加的,这是否寓意着“家天下”呢?这也是一种“文革”乱象。
家本来是“与人最亲密的空间”*〔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惠敏译,第28页。,是一个温馨和谐的血缘空间,是一个凸显家庭亲情伦理的一个日常空间,但毕飞宇在其“文革”小说中却赋予其血腥的一面,演变成一种“文革”乱象:家成了各种权欲争夺的场所。在小说中,没有一个“五好家庭”,家都是有问题的,充满着紧张感。王连方的家是紧张的,甚至是离心离德的,夫妻、父女和姐妹之间似乎都无亲情感。王连方夫妻在一起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延续权力;玉米和其父亲王连方也是剑拔弩张的,甚至没有话说;玉米与其妹妹们也是紧张兮兮的,“饭桌夺权”就是最好的证明。端方的家也是紧张的,破碎的,父子、母女和姐弟之间都充满着敌意。“大棒子”事件是端方获得家庭威权的最重要途径,它颠覆了父子的家庭伦理秩序。另外,其他家庭也是有问题的,王连方在王家庄可以将其行政威权任意撒播到其他家庭,王连方摇曳多姿的性就是这种权力的表征。如果说王连方只是偶尔把性延伸到其他家庭,那么,更有政治意味的是,小说《平原》中的老鱼叉对地主婆的侵入则是永久性的,对地主家的侵占更是永久性的。
和家一样,学校也是悖谬的日常空间。学校本来是一个清幽的学习空间,却被用来展现“文革”血腥的一面,展现“文革”的种种乱象。福柯认为,学校是一个纪律规训的场域,通过学校的这种监督,“规训权力变成一种‘内在’体系。”*〔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00页。毕飞宇非常反感福柯的这种空间权力观,他认为不符合中国人的特权观念,他说:“福柯这个人真的是不讲理的,在权力面前,人是不自由的,这句话等于没说。权力就是专制,这句话也等于没说。”*张均、毕飞宇:《通向“中国”的写作道路——毕飞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所以,毕飞宇从非法或者非道德的意义上考察外部权力对学校等日常伦理空间的侵犯。在小说中,学校是端方与地主女儿三丫的性浪漫的地方;学校是知识分子顾先生接受刀劈洗礼的地方;学校也是校职工魏向东凌辱、性侵学生玉秧的地方。学校本来是知识理性的空间,在“文革”中却成了展示施虐、受虐的舞台,不能不说这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日常伦理空间,目的是为了展示“文革”的种种乱像。
苏贾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21页。这是很有洞见的。在小说中,大队部、学校、收麦场、养猪场、废旧厂库和家庭等各种日常空间的寓意不是一成不变的,“‘贫苦的农民’在民间,然而,从根本上说,‘贫农’的精神却在庙堂。”*毕飞宇:《沿途的秘密》,第54页。这话一点儿不错。一般来说,乡村人不怎么过问政治大事,很多时候自得其乐。如,在大队部,王瞎子和顾先生“论辩”的严肃场合里,村民们也自顾嬉戏。因为,村民们懒得理会、评判对错,最关键的是,“谁有能力把说话的气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有意思的是,村妇们可以在收麦场等日常空间戏逗队长“蘑菇”来自娱自乐。从这些可以看出,民间伦理仍然是村民们生存的内在依据。但是,这种超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976年这样动荡的历史阶段,“国家”一有运动,人心就乱了,人就没有主意了。同样在大队部,村民们哭天抢地,“虽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门,可他天天在王家庄……”王家庄和北京无形中发生了联系,革命伦理也就深入人心了。也就是说,国家权力可以通过特定的时空撒落到每一个乡村日常伦理空间。
四、身体性空间
文化地理空间和日常伦理空间都是比较宏大的,身体性空间却是微观的。身体美学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因为,“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思想成就之一。”*〔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并且,众多学科都转向了“探讨社会生活中的身体,从而理解我们特殊历史连接的复杂性”*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与生命政治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把身体空间与历史链接起来做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且有很重要的意义。
毕飞宇一直喜欢写身体写性,在其早期作品《叙事》里,他把历史、语言与权力等宏大叙事与柔软隐秘的身体空间叙事并置链接起来,把身体作为历史“疼痛”的载体。奶奶被强暴的历史,成为了家族史上一个众人缄默的秘密,身体的重要性在这里突显。从这些可以看出,毕飞宇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种身体性空间与历史并置融合的时空书写模式。毕飞宇说:“我描写性的时候相当节制,我抱着审慎的态度写……你不可能通过‘想象’去蒙人。”*毕飞宇:《我是一个疼痛的人》,《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9期,2009年5月11日。换句话说,毕飞宇把身体性放在历史中去考察,力图捕捉身体性空间的嬗变历程,以突显身体性空间演变的历史意义。
在毕飞宇“文革”小说中,小说人物大都与身体性纠缠不休,人物往往在身体性空间中成长。王连方就是最好的例子。王连方的成长主要依赖于乡村恶性特权的滋生,而特权又是在身体性空间中培育起来的。福柯说:“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第27页。王连方身体性空间的转移是沿着“自己家”到“大队部”再到“别人家”的路线行进的。王连方身体性空间的转移是其权力成长的历史。换一句话说,王连方的乡村威权是在女性身体空间里建构出来的。因为,“人的性生活必定不能被看成一个简单数据,而是应该被看成一段历史。”*〔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页。
翟学伟说:“判定一个体是权威者还是服从者,并非由这个人的角色或相应的职权来决定,而是由该个体所处的关系状态,即社会网络来决定。”*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第115页。在王家庄,人人都怕王连方,“不是嘴上怕,而是心底里怕。”老婆施桂芳也怕他,事实上他与施桂芳的性爱,完全是为了生儿子。对王连方而言,女会计是她性权力的启蒙者,女会计把玩着他裆里的东西,意味深长地说,“就算不肯,打狗也要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这充分说明“历史会在男人的性经历中惊奇地复生”*毕飞宇:《雨天里的棉花糖·叙事》,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第52页。。王连方在艰苦卓绝的身体性斗争中“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因为,“性交本身是一种生物的、肉体的行为,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体现着具体文化的价值系统。在一个权力可以支配到人的内心的体系中,权力等于性是必然的结果。”*徐仲佳:《权力与性——〈玉米〉解读的一种可能》,《名作欣赏》2004年第7期。
王连方很多身体性空间叙事大都没有合法性依据,但却符合“文革”历史的逻辑;在《平原》中,身体性空间的错位更是离谱,但是,1976年这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却能够提供历史依据。由于历史的错位,老右派顾先生,知青吴蔓玲、混世魔王等人物都在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存在着。也许,“存在就是合理的。”在小说中,人与时空的错位和男人与女人的错位是一体的。具体说,一男一女在错误的时间(1976)和错误的空间里相遇,发生了一系列荒唐可笑而又凄惨的“爱情”故事。这里面有一个判断男女是否错位的标准——成分论。毕飞宇曾经说过:“我一听到‘民间’这个话题马上就会想起‘划成分’。”*毕飞宇:《沿途的秘密》,第53页。小说《平原》大致有三个人物系列。顾先生、吴蔓玲和混世魔王等可以归属于城市人物系列;端方、老鱼叉和老骆驼等可以归属于村民人物系列;三丫和王二虎的女人可以归属于地主遗孀人物系列。一般来说,这三个人物系列界限清晰,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发生爱情,一旦发生这种错位就是一种悲剧。
小说《平原》中的身体性叙事惊心动魄,也摇曳多姿,但仔细审视一番,其实都是畸形的性。有两个原因:男女错位和人与时空的错位。端方和三丫、顾先生和姜春花、老鱼叉和地主婆都是一种男女错位的性爱。有一个似乎是男女没有错位的性爱,那就是吴蔓玲和混世魔王的性爱。但这种性爱更不正常,那是一种裹挟着权力与利益的强奸,强奸成了计谋、策略,可谓错位得令人咋舌。而吴蔓玲和狗、老骆驼和猪之间的人与动物的错位性爱更是荒唐可笑而又令人心酸。因为,“色情是人的性欲活动,它与动物的性欲活动是相互对立的。”*〔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第17页。需要补充的是,吴蔓玲和端方的无性之爱也是错位的,最后也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相对于男女错位,人与时空的错位更是丰富多彩。具体来说,不合时宜的时空没有给男女的性提供合法性依据。端方与三丫在小学校的性是见不了光的,黑夜、学校的时空设置隐喻了他们爱情的毁灭,悲剧不仅仅是赤脚医生抢救的意外导致的。顾先生与姜春花一次体外射精更是荒唐可笑,鸭棚的时空设置预示着他们的性只是鸭蛋的交易。而这种荒谬是可以解释的,对于姜春花而言,生存伦理是压倒一切的,包括身体性。正如M.利普顿所指出的:“许多看似古怪奇特的村庄活动,实际上具有隐蔽的保险功能。”并且,“这种活着的取得,常常要以丧失身份和自主性为代价。”*〔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7页。老鱼叉与地主婆的性爱有些复杂,是一种阶级复仇的性,时空也是错位的。从表面上看,性爱发生在家里,但是房子是地主王二虎的。混世魔王是在大队部强奸村支书吴蔓玲的,他们的性更有着很深刻的政治意味。大队部作为小说的时空是政治权力、革命伦理的标志,来自“国家”的声音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小 结
文化地理空间、日常伦理空间和身体性空间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空间阐释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能够有效阐释时间、历史的“三棱镜”,用它来审视毕飞宇“文革”小说的那段秘史尤其管用。当然,“文革”的种种乱象是当代小说家喜欢书写的,然而能够抵达历史的真实——阐释的真实,毕飞宇走得远些。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段历史,毕飞宇喜欢“混沌”一词。在笔者看来,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文革”那段历史是“混沌的”;二是当下对“文革”的阐释还是“混沌的”。对第一种混沌我们无法清除,那是历史本身的存在,对第二种混沌,毕飞宇等历史阐释者正在做清淤工作。
(责任编辑:王学振)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mage under the Space-time Distortion——A Case Study of Bi Feiyu’s NovelsMaizeandThePlain
ZHAO Bi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n provide Bi Yufei with an excellent time-perspective to reflect on totalitarianism, and locations like Wangjia Village can provide for him a perfect space perspective, thus by placing characters under such an optimal “space-time structure”, Bi Yufei can maximally amplify the distorted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zoom its various chaos. Specifically, in novel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keMaizeandThePlain, Bi Feiyu has a lingering time complex for one thing, because he is extremely sensitive to time and history, and is more willing to spare no efforts to delve into the distorted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another, time and history is shown through the “trinity” spati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space, daily ethical space and physical space, namely revealing the absurd time and history of that specific period in the macroscopic to microcosmic order by way of the “time-spatialized” writing mode. And time and history also foil, in turn, the space of the novel, thereby attaining the narrative effect of time-space integration.
Bi Feiyu;Maize;ThePlain; imag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space
2016-07-22
赵斌(1982-),男,安徽霍邱人,中山大学中文系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
A
1674-5310(2016)-09-00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