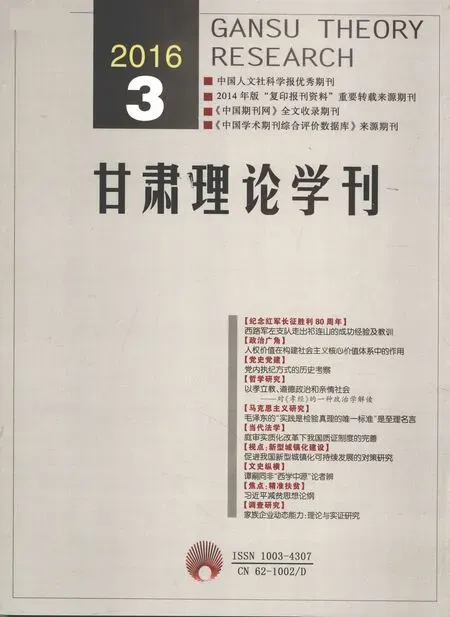钟嵘古今观与其诗学思想
李 波
(渭南师范学院 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钟嵘古今观与其诗学思想
李波
(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陕西渭南714099)
在品评古今五言诗作的过程中,钟嵘的诗学思想受其古今观念的影响较为明显。在诗学批评方法上,钟嵘采用溯源析流的方法对古今作家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较为具体而完整的阐释。而在对诗歌特征和审美标准的认识上,无论是“吟咏性情”的观点,还是“直寻”的提法乃至是“贵奇”的风格主张,都有反对拟古的本意在其中,但同时钟嵘又能在其古今兼顾的思路下对当时文坛过于求新的弊病予以严厉的批评。钟嵘这一古今观念在其对具有古今倾向的作家之品第中有更为直观的体现。
钟嵘;古今观念;诗学思想
和先秦两汉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已经相当繁荣并发生了许多新变。针对这种新变,日渐兴盛起来的文学批评也需要作出必要的回应。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稍后时期的文论家对新旧文学的总结和批评就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刘勰《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1]710把整个古今文学都纳入到考察的范围;沈约撰写中国第一篇文学史专论《宋书·谢灵运传论》时也对古今文学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汉魏以来的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批评都有论及。与同期文论家一样,钟嵘《诗品》“品古今诗为评”[2]1779对文学的古今问题也多有论及。显然,作为一种思想的预设,古今观念对牵涉古今问题的文学批评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就钟嵘而言,其《诗品》中的古今观念与其文学批评之间的联系性也是相当突出的。下面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源流意识与古今观念
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这篇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文学史专论的文章与作者的古今观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其审视古今文学时以一种古今因缘、因果的思维来理解古今文学的关联。这当是受到佛教古今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是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观的重要原因。这种审视古今文学的思维方式,除了沈约,在同期文论家刘勰、萧子显等人那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而在钟嵘这里又把这种方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钟嵘以考察源流的方式来品第作家,其实,这种批评方法与其古今观念下的思维方式也是颇有关联的。
如何认识古今文学的区别和联系,一直是文论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中国文论家很早就运用了古今联系比较的思考方法。早在《诗大序》中就有“变风”、“变雅”的说法,这是以前代的雅正之作来审视后世作品;班固在认识有着一代文学之称的汉赋时也说“赋者古诗之流也”[3]721,这也还是一种以古诗的至高标准来界定后代文学的思路;魏晋文论家在“古今同则”认识下探讨文体产生、演变的过程,也注意到后世文体兴起于前代的事实*譬如傅玄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并指出后世文章“合于古诗劝兴之义”[3]38。这些都足以说明文论家们非常善于联系古今来审视文学本身的规律性。这些认识固然是注意到了古今的联系性,但是对古今文学的具体流变关系阐述得却还不够清楚,而且在早期的古今文学关系认识中,往往是以古代为准的的。比如《诗大序》和班固说到的“变”和“流”,虽然注意到后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但是以古为尊的思想观念还是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发展的正确认识。当然这和文论家受限于所处时代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自魏晋以来,随着文学创作事业的更加繁荣,人们对文学理论的认识也必将更为深入,在认识古今文学的关系上亦是如此。故此,继沈约以文学史的眼光来考察古今文学的变迁之后,刘勰、钟嵘等人也广泛采用追源朔流的方式来考察古今文学。这是文学理论向前推进的又一具体体现,尤其是钟嵘,他在《诗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源流意识是非常突出的。
钟嵘在《诗品》中往往以后代作家“源出于”前代作家或作品为梳理方式,把跨越了前后七个朝代的文学联系起来。因此,通过历代作家之间的承袭关系,古今文学的联系性也得到了高度体现。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又说“屈平宋玉,道清流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4](297)这就是以因果关系来审视前后时代作家关系的典型范例。也就是说“源”是“流”的因,“流”是“源”的果,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因果关系又会不断的推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钟嵘《诗品》通过渊源流派来品第作家,实际上是对沈约这一理论认识的发扬光大。所以有人怀疑《南史·钟嵘传》所载沈氏与钟嵘的龌蹉*《南史》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79页。也的确有些道理,至少在文学批评的古今思路上,两者可以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钟嵘《诗品》对沈约文学史观的光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考察了前后时代的因袭关系,而且把这种关系梳理得更加细致,且源流关系更加清晰。同时,对于沈约所提到的“莫不同祖风骚”,钟嵘又给以了明确的划分。譬如《楚辞》一系:楚辞-李陵-王粲-张协-鲍照-沈约-王融。这一流派的传递在每个时期都有代表,其一脉相承的谱系是非常清楚的。这比沈约多在前后时代、阶段性地来谈古今文学的变革要更具体,也体现出更好的完整性。而对于古今作家因缘、承袭的关系,钟嵘又不限于前后紧邻的时代,并且承袭的源头也并不完全单一。前者比如曹植之于《国风》、谢灵运之于曹植,后者比如陶潜之于左思、应璩,江淹之于王微、谢朓。很明显,继沈约古今文学相承相因的认识之后,钟嵘把陆机所说的“沿波而讨源”和“因枝以振叶”两者很好结合了起来。在注意“讨源”的同时,钟嵘又是站在后代“源之流”的层面上来考察“源”的。所以,一方面,他会注意到古代对后世的源流作用、前世与后代的因缘关系;另一方面,他又能够注意到后世对源头的演变、后代对前世的因袭继承。正是这种古今相因相袭的连环关系,构成了古今文学这个完整的谱系。因此,可以说钟嵘把玄学古今观中探源溯流而求本的思维方式与佛学古今观中前后因缘相关的看法,都吸收了进来,把对古今文学关系的认识推向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毫无疑问,这种源流意识业已被后世广泛接受。当然,钟嵘在溯源析流过程中也难免有失精准,譬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道:“其论某人源出于某人,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5]2738钟嵘在溯流别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的确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一种审视古今文学的方法则是无可厚非的。
二、古今取向之下的文学认识与评价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钟嵘诗论的批评方式上探讨了其文论与古今观的联系,下面我们结合钟嵘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古今文学的认识和评价来考察其古今观与文论思想的联系。
首先来看钟嵘对诗歌的本质特征及其审美标准的认识。钟嵘在阐述诗歌生成的过程时就强调了诗歌抒发性情的特征。他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6]1曹旭先生把钟嵘的这一诗歌发生论跟《诗大序》和《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发生论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钟嵘更强调‘物感’的作用”。[7]123其实钟嵘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也就是看重诗歌的抒情感人作用,这一点和沈约等新变派论家也是相同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是这样认识文学发生的:“史臣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4]296虽后一句也是沿用《诗大序》的说法,但“喜愠分情”显然还是多指情感而言。由此可见,沈约、钟嵘都是对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延续。而钟嵘在肯定诗歌“吟咏性情”的同时,又对古代儒家文论更为重视的政教功能进行了弱化处理。无论是在《诗品序》还是在具体的品第批评中,钟嵘都较少提到诗歌的政教风化作用。这一点和刘勰强调“神理设教”有所不同,由此也看出他们对待古代传统的些许差别。但无论怎样,诗歌抒发性情也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故而也可以视作钟嵘对这一古代传统的肯定与坚持。
从吟咏性情的诗歌抒情特质出发,钟嵘对诗歌中有违此特质的内容就有清醒的认识:“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6]220显然他认为在经国、述德的文章中可以借鉴古代,但是在诗歌创作中用事、借古,则是违背“吟咏性情”的做法。这与其后萧纲等人强调文章的抒情特性也基本一致。并且,在此基础上钟嵘还提出了著名的“直寻”说: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6]220
钟嵘强调诗歌抒发内心情感的特点,当然偏好现实中有感而发的诗作。他所列举的都是抒情体物的诗歌名句。由此可见,钟嵘“直寻”一说,看重的是眼前所见、所感带来的情感体验。和萧纲所说的“寓目写心,因事而作”[4]353意思也比较相近。
陈延杰在《诗品注》中解释说:“钟意盖谓诗重在情趣,直由作者得之于内,而不贵用事。此在诗中叙事写景则然耳。若夫抒情,则非借古人成语,不足以写其胸臆。”[8]12陈说把钟嵘“直寻”限制在了“体物”方面,却忘了在主张“物感”说的钟嵘那里,抒情体物是一体的。“直寻”当然有肯定即兴之感的要求在里面,而不是借古人才能更好地抒发胸臆。钟嵘原意正是要反对刘宋时期形成的拟古诗风,若按陈氏解说钟嵘岂不是要赞同拟古?这和钟嵘诗论是完全背离的。正因为看到钟嵘“吟咏性情”的诗歌主张具有反对拟古、摹古的用意,大约一千年后,清代性灵派文论家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一诗中才会写道:“天涯有客好聆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9]691因此,从抒发情感的诗歌特征上来说钟嵘也是反对拟古的。从创作思维的角度来看,“直寻”说的提法也具有反对拟古的用意。
钟嵘又是很重视创新的,正如曹旭《诗品研究》所言,“钟嵘更有求新、求奇、求变、求独创的个性特点”[7]129,这一特点完全顺应当时诗歌创作的趋势。其实钟嵘批评任昉、王融用事过多,也主要是认为由此导致诗作不能“贵奇”。他提出的建议是“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6]228。这里的事义也是指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当然,钟嵘也绝不是对后代文学的新变都一概认可,譬如他主张“自然英旨”而反对声律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更能反映出钟嵘对古今文学态度的是他对古今时代文学的评价。相对于对汉、魏、西晋的作家批评而言,钟嵘对后代作家,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齐梁作家评价都不太高。 钟嵘评诗标准是文质兼顾的,也即他在《诗品序》中所说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样,曹植的诗歌就成了钟嵘诗歌美学的典范,即所谓“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6]117在这样的品诗标准下,他对当时的诗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文曰: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6]64-65
实际上,钟嵘批评当时诗风是有参照、比较的。他列举了作诗的几种具体情状,然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6]56而这里所列举的“凡斯种种”又无不是以古人为例。可见,他列举古人也正有批评当今之意。有人刚开始学写字就要作诗,尤其是那些贵族子弟偏偏刻意吟咏诗作,这些和不得不抒情于诗的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所以钟嵘称他们的作品是“庸音杂体”。而且对那些自身轻薄却讥笑曹植、刘桢诗作古老拙劣的人,钟嵘甚至认为他们根本不配作诗人。“古拙”的反面是轻浮,显然,钟嵘在维护其诗歌典范的同时,对当时诗坛的轻浮之风深恶痛绝。在这时候,他坚决站在了“崇古” 的一面,显然是为了纠正齐梁诗坛过度求新的风气。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说:“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10]505这是世人过度追求当前新变而摒弃古代(魏晋)诗歌风骨与丹采兼备的优良传统才导致的浮靡诗风。故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钟嵘和刘勰都是企图拯救时弊的文论家。这也正是他们在古今兼顾思路下,避免了崇古和求新的偏颇之后,才能具有的公允态度。
三、对表现出古今倾向的作家之品第
对古今作家的品第,其实在上面谈到钟嵘诗学思想时已有涉及。此处专门讨论钟嵘《诗品》对表现出古今倾向的作家的品第情况,是为了更鲜明地突出钟嵘古今观念以及对古今文学的态度。因为他对具有古今倾向各不相同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会显得更为直接一些。
首先,来看钟嵘对具有古朴风格的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品第。钟嵘虽然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但是从诗评的内容上来看其实还是肯定居多的。他说: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6]336-337
钟嵘说陶诗“笃意真古”,其实说明他的评论主要着眼于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品质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结合诗歌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考察作品也是钟嵘贯用的批评方式。因此,思想品质之后才紧接着说文辞方面的特点。但是从钟嵘后面对陶渊明品质的补充强调也可看出,他和萧统一样,很欣赏陶氏的人格品质。“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所以,钟嵘此处对陶渊明的评价,虽不乏对其文辞清新方面的赞许,但主要还是对其作品思想品质古朴而真诚的肯定。也就是说,在诗歌思想内容方面他是更欣赏古代的。其实,这也就是一般后世认为古人思想更为淳朴的古今观念的一种反映。对那些崇古的人暂且不论,就是主张今胜于古的王充、葛洪等人也无不持这种观点。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11]23今天看来依然有一定的道理,所以钟嵘持这种观点也无可厚非。因而对那些古朴、古雅的诗歌风格钟嵘都是予以肯定的。评曹操“曹公古直”[12]79,评张永“颇有古意”[12]93,说鲍令晖“拟古尤胜,唯《百愿》淫矣”[12]96,又说张欣泰、范缜“并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12]99对他们诗歌中的古雅风格都进行了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家所处品第位次都不太高,尤其是曹操和陶渊明这两位重要的作家。其实,这也就印证了钟嵘对诗歌审美标准要求的两个方面,即文质兼备,否则难居上品。
另外,也要看到钟嵘对另一类崇古方式的严厉批评。他对颜延之“喜用古事”颇有意见,认为它的毛病是:“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6]351所以在文辞方面钟嵘不主张刻意摹古,他认为这样有违自然。而且他还从求新的角度对这种用古事的作法进行了批判:
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6]419
由此可见,对于诗歌创作中因过多引用古事而落于俗套从而缺少创新的作法,钟嵘也是坚决反对的。
综而言之,无论是在诗学思维上,还是在具体的诗论内容上,钟嵘古今兼顾的观念都有所反映。正是这种古今兼顾的思想观念,使钟嵘诗学思想具有了较强的思辨性因而也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他坚持诗抒性情的传统,但又反对拟古;他认可诗歌思想内容上的古雅,但同时也反对有违自然的“用典”;他追求诗歌新奇独创,但同时也反对过于求新;他继承并发扬了沈约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以溯源析流的思路来品第古今五言诗作。钟嵘诗学思想与其古今观念的联系虽然是潜在的,但的确也是存在的。
[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郭丹.先秦两汉文论全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
[7]曹旭.诗品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9]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责任编辑:张林祥]
2016-04-05
李波(1980—),重庆永川人,文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整理与批评。
I207.22
A
1003-4307(2016)03-01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