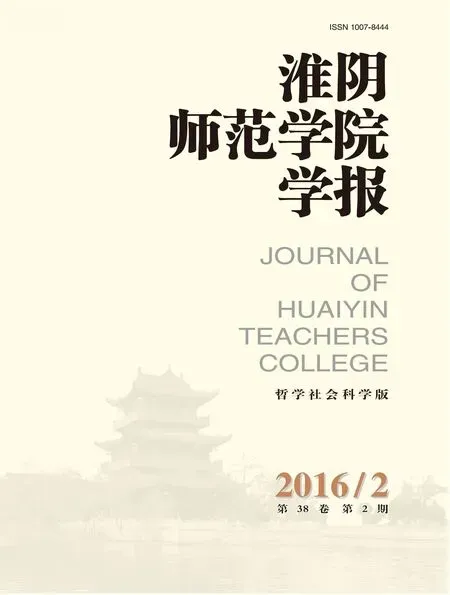重评《西游记》的“反抗”主题——以朗西埃、巴赫金的“文学—政治学说”为参照
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重评《西游记》的“反抗”主题——以朗西埃、巴赫金的“文学—政治学说”为参照
竺洪波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要:对《西游记》“反抗”主题的认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歧见。以现代“文学—政治”学说(主要选择朗西埃政治美学与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为参照,《西游记》的“反抗”主题,并非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其内涵也只是权力之争和情理相抗,反抗的途径,也以“脱冕”和“加冕”的形式体现狂欢化色彩。
关键词:《西游记》;“反抗”主题;朗西埃;政治美学;巴赫金;狂欢化诗学
一、“扬弃”的必要性
“文革”时期,《西游记》论坛流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将《西游记》的主题图解为农民起义与阶级反抗,孙悟空大闹天宫后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即是阶级立场的背叛,从而成为宣扬投降主义的“叛徒文学”[1]。这种庸俗社会学批评,完全脱离了学术的正常轨道,纯粹是其时政治斗争与极“左”思潮的附庸,其方法和结论都不足为训,理应予以抛弃。
但是,在新时期以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将问题推向极端和反面,完全割断了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抹杀了《西游记》丰富的社会政治学蕴涵,甚至谈政治而色变,一味唯精唯一,谈宗教、释文化,自觉地将《西游记》的反抗主题也一并抛弃了*这一时期,学界提出的《西游记》主题观主要有:“求放心”说、“表现理想英雄”说、“性格成长”说、“金丹大道”说、“哲学与审美自由”说、“密码”说、“将功赎罪”说、“以情抗理”说、“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善”说,等等,不一而足。参见拙著《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第十章《西游记文本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哲学普遍性说,一切事物皆处对立统一之中,对立与斗争是绝对的。有斗争就有反抗。鲁迅有过一则著名的假设:“(使)二士室处,亦有吸呼,于是生颢气之争,强肺者致胜。故杀机之昉,与有生谐,平和之名,等于无有。”[2]把反抗归结为阶级斗争是片面化,但阶级斗争本身则是一种反抗,除了阶级斗争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反抗存在。《西游记》,特别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不一定是阶级斗争,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反抗。所以,关于客观存在的《西游记》“反抗”主题,历时悠久,然而是耶非耶,然欤否欤,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歧见,值得总结、反思。
有必要引入现代性“文学—政治”学说。
在西方文论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广受关注的理论命题。从亚里士多德、斯达尔夫人、丹纳到马克思、卢卡奇、葛兰西,都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属性,列宁甚至将文学视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国家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并且由此归结出文学的“党性原则”[3]。在当下后现代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文学—政治”学说尤显丰富,巴赫金、福柯、布迪厄、朗西埃等理论大师都就文学的政治功能(或属性)发表过精辟的意见,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想潮流*对此,国内学界也有热烈反应,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如范永康《何谓“文化政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姚文放《文化政治三维度》(《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化政治”的兴起及社会意义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解读。。结合西方文论与《西游记》艺术精神的契合实际,我们将选择雅克·朗西埃政治美学与米·巴赫金狂欢化诗学为主要参照,来重评《西游记》的“反抗”主题,揭示其生成的社会政治根源。朗西埃主张政治、美学、艺术三位一体,艺术在这个整体的社会文化场域中显示张力,指出当代艺术的衰落之因即在于艺术的边缘化地位“已经无法扮演政治行动的角色”[4]。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理论内核是从民间立场出发,反抗正统与既有秩序,通过“脱冕”与“加冕”的方式,建立社会(通过文学与文化)的新理念、新秩序。在此种西方文论“他者”视野里,《西游记》的反抗主题赫然在目,并且有了老调重弹,客观评其价值、发现新问题的可能性。
二、“大闹天宫”非农民起义辨
农民起义是阶级反抗的集中体现,文学反映包括政治活动在内的整体的社会生活,当然可以反映农民起义*事实上,在中国小说中就有一类专门反映历代农民起义的作品,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施耐庵《水浒传》和罗贯中《三国演义》。。所以一种有代表性并且长期流行的意见是:《西游记》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大闹天宫”隐喻农民起义,孙悟空的形象“则是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人物性格的概括”[5]。他们说:
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至使得封建统治者不能维持或者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如果不是建立在历代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或者说其中心不是反映农民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这段话不知出于何人。转引自林庚《关于“大闹天宫”的故事情节》,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13期。收入《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但是,《西游记》是神话—神魔小说,孙悟空形象来源于唐宋以来的猴精传说(按鲁迅本土说*关于孙悟空形象原型主要有两说:一是胡适外来说,认为是印度史诗《摩罗衍那》中的哈努曼;二是鲁迅本土说,认为是唐宋以来丰富的猴精传说。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大闹天宫”故事实际上并没有“扮演政治行动(特指农民起义——引者注)的角色”,并非反映阶级斗争与农民起义。对此,著名文学史家、北大老教授林庚先生有过精辟的分析。
其一,“大闹天宫”自始至终没有涉及农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孙悟空与中国封建社会“安土重迁”的农民意识截然不同,孙悟空生活的环境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类似于“葛天氏之民”的大同世界,《西游记》美誉为“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无忧无虑,享乐天真,可是他并没有就此安居乐业,反而要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去追求所谓的长生之道,并由此引发了大闹龙宫、地狱与天宫。这与统治者的高压暴政所迫使的农民起义风马牛不相及。
其二,孙悟空作为天地化生的“自然之子”,其身份不是农民。
孙悟空由天地化生,从来不是农民。孙悟空两闹天宫时,已被玉帝招安,身份分别是未入流的弼马温和齐天大圣。虽然两者官品有高低,但都属于天庭官吏,起事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次孙悟空嫌弼马温官小,不愿为玉帝养马;第二次则是受“有官无职”阴谋论的愚弄,不能参加蟠桃盛会而愤愤不平。这也与历史上常见的因统治者强征徭役、加重赋税、兼并土地、抢夺财富而引发的农民起义截然不同。大闹天宫,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只是即使这样的理解也依然过于简单,完全不能揭示出作品“反抗”主题蕴涵的丰富性。
其三,孙悟空大闹天宫轰轰烈烈,场面火爆,直打得“扬沙走石乾坤黑,播土飞尘宇宙昏”,“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但始终是单打独斗,作为“起义”的主体只有孤身一人,没有羽翼,是一个“出色的单干户”。这也不符合农民起义的“群体性”实际。林庚指出:
我们几曾看见有农民起义是一个人单干的?农民起义所依靠的力量是群众,所谓登高一呼,揭竿而起,而孙悟空所依靠的是他七十二般变化与一根如意金箍棒,此外还有的就是一身毫毛会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若说这千百个小孙悟空就算代表起义的群众,那么在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也老带着这一身毫毛,而且随时都可以变成千百个小孙悟空,也就无时不是在起义中了。这说法也是没有人会同意的。[6]
此外,还有一处反证。那就是:如果大闹天宫属于农民起义,孙悟空身处阶级社会,那么如何解释孙悟空后来皈依佛教,“至死靡它”,一路上忠心耿耿地保护唐僧取经呢?或许只能得出“主题分裂”说,甚或“投降主义”和“叛徒文学”一类违反文学常识的荒谬结论吧。
应该说,林庚先生的分析基于“文本细读”,鞭辟入里,而且符合历史上农民起义与《西游记》描写的实际,令人心悦诚服。值得注意的是,林庚先生的此项研究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受到极“左”思潮意识形态的过分影响,完全是在艺术角度所作的客观评析,更显示出理论的公允。林庚的评论,实际上已基本宣告了所谓“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主题观的破产。
三、“反抗”主题的内涵
《西游记》的主题不是农民起义,“反抗”却是应有之义。因为在大闹天宫故事里作者明确写道:“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昨日反下天宫去了。”并且用“乱蟠桃大圣偷丹,反天宫诸神捉怪”作为回目,既是“乱蟠桃”,又是“反天宫”,“反抗”的意义十分醒目。
所谓反抗,《辞海》释义“反对并抵抗”。那么孙悟空“反抗”的对象是什么呢?当然是天庭的既有秩序,一种业已建立与存在的制度体系。他认为天庭的既有秩序和制度是不合理、不公正的。“争天拒俗”的心理渴望,演化为轰轰烈烈的“颢气之争”。
你看那个天庭,气势宏伟,整日里祥瑞飘渺,歌舞升平,各级官衙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官吏们饱食终日,奢靡无度,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尸位素餐,不思进取,只图清净,已然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合二亿二千六百八十万年)年纪,还要延请老君炼丹,“企谋与王母娘娘更愉畅地过天宫少有的夫妇生活”*在《西游记》中,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以恩爱夫妻的形象出现,在天庭诸多神灵中极为醒目,其世俗性不言而喻。参见苏兴《西游记对明世宗的隐喻批判和嘲讽》,《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他赏罚不明,不识真才,无掌控、应变能力,一旦妖猴作乱,便手足无措,只好借助外力实施镇压。——竟是个十足的颟顸昏君。对于这样的既有秩序和制度形式,天然率性的孙悟空当然要揭竿而起,一反到底。
朗西埃的政治美学为孙悟空的叛逆心理(性格)和造反行动提供了理性依据:主体的政治诉求,也即追求、实现主体的“感性的分配”,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深层诱因。朗西埃把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区分为“政治”(lapolitique)与“治安”(lapolice)两个层面。统治、治理、管理、秩序等归为“治安”,“政治”则是对于这一切管理、统治、秩序的不断消解、抵抗、重配。因为这种消解、抵抗、重配引起的变化是可以被个体所感知的,所以朗西埃称为“感性的分配”或“感性的再分配”[7]。孙悟空正是感受到天庭秩序对自由的窒息,必欲反抗来打破既有的“感觉配置”模式——被正统认可的制度与秩序,以实现个体“自由欲望的贲张”[8]。从整个《西游记》看,“反抗”主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权力之争。
孙悟空清醒地认识到,权力是维系天庭既有制度和秩序的根本保障,要打破旧秩序就必须挣得相应的权力。所以他要为自己争权、维权,首先要求做齐天大圣,并且是有名有实、有职有权,与诸般神将平起平坐,一旦不能满足就宣告与玉帝决裂“反下天宫去了”。其次,他提出了造反的纲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要求久居龙庭又与昏聩为邻的玉帝“让贤”,遭到拒绝则“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上演了一幕“闹天宫”的好戏。从现代“文学—政治”理论看,社会文化政治的核心恰是权力,那种“微观的、网状的”,也即无处不在的权力,以及凭借权力而进行的对社会资源的竞争,孙悟空上述诉求与纲领,说明了反抗(政治行动)的自觉性与合理性。
其二,情理相抗。
如果将《西游记》与明代中后期追求个性解放的心学思想和“以情反理”的文学思潮结合起来,那么《西游记》的反抗主题就表现为情理相抗。孙悟空“斗战胜佛”的封号象征了情欲反抗天理的最后胜利,而玉帝与唐僧形象(昏庸、软弱、迂腐)的意义则在于“实际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破产”。
这里,所谓“理”即是正统、秩序,所谓“情”即是在野、草根。显然,玉帝、如来、唐僧是“理”的代表,悟空、八戒是“情”的代表,后者对前者权威的不恭、挑战和背叛,就是“以情抗理”。“大闹天宫”是最激烈的反抗,其余还有多方面的反抗。如田同旭在《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一文中评论孙悟空:
孙悟空是个由一块石头造化出来的自然之子。作为猴子,他极端好动,永不安生;作为人,他“一生受不得气”;作为神,他不愿受任何束缚。一句话,孙悟空追求的是个性解放,任情随欲。在程朱理学统治的天罗地网中,孙悟空庄严地宣布,他的本性不可扼杀,人的情欲不可战胜。不受阎王束缚,不受天宫束缚,不受唐僧束缚,不受菩萨束缚,不受妖怪束缚,不受佛主束缚,可谓其主导性格;而且,不论谁束缚他,他就反抗谁,反抗成为孙悟空性格的本质[9]。
可见,他反玉帝、反佛祖、反菩萨、反师尊,反抗一切正统和既有的秩序,“反抗”的主题是全方位的,是孙悟空“性格的本质”使然。
还是用朗西埃的“无份者之分”理念来解释《西游记》“反抗”主题的发生:
我提议将“政治”这个名词,保留给与“治安”对立的一种极为特定的活动,亦即,借由一个在定义上不存在的假设,也就是“无份者之分”,来打破界定组成部分与其份额或无份者的感性配置。
即是说,政治活动的发生源于“无份者”(类似于无产者吧——引者注)对利益和权力的诉求。朗西埃以古希腊城邦的平民政治为例:那些曾以无声的沉默作为存在的平民一旦发出平等的要求,他们的话语被共同体内部的其他部听到并视为平等的声音时,政治才能发生[7]。诚如鲁迅的名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不过是爆发的前奏,爆发才是沉默合乎逻辑的结果,沉默即反抗:所谓“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如是,《西游记》“反抗”主题的发生,亦应作如是观。
四、“脱冕”与“加冕”:反抗的途径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来源于古代欧洲的狂欢节。而民间狂欢节以特殊的方式——如痛饮狂醉以后戴上面具、穿着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游行、歌舞,纵情欢乐,尽情地发泄自己的原始本能,因此狂欢化诗学就与生俱来带有反抗正统、挑战秩序、蔑视权威的特征,呈现宣泄性、颠覆性、草根性的艺术精神。美国文化学者菲斯克就此解释说,作为“对统治力量的反应”的大众草根文化存在于“社会控制之外”,其价值即在“对抗着某种霸权力量”[10]。这与《西游记》的“反抗”主题尤其吻合无间。比如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背后隐喻着“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和“无法摧毁的生命力”。孙悟空大闹天宫,把巍巍天庭打得稀巴烂,一切威严和等级秩序荡然无存,充分显现出草根生命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脱冕”与“加冕”是狂欢节的两种仪式,巴赫金用来说明文学正统与草根、高雅与低俗的互换关系,提倡不同文学体裁的平等地位。对此,朱立元界定说:“巴赫金发掘人类的狂欢化文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传统的诗学体系挑战,是要颠覆旧的诗学理论,为传统的高雅体裁‘脱冕’,而替所谓的低俗体裁‘加冕’。”[11]这里,借用这两个术语来阐释《西游记》反抗的途径。
孙悟空对正统秩序的反抗首先表现为“脱冕”,剥去其伪装,撕破其尊严,甚至将其打出原形。玉帝号称“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三界主宰,何等威严,但是面对孙猴子的搅乱,束手无策,躲在灵霄宝殿龙椅下歇斯底里地狂叫“依他依他,落得天庭太平是幸”,丑态毕露,斯文扫地。如来佛祖法力无边,却只能使诡计才能收服孙悟空,落下个“胜之不武”的诟病,顽皮的悟空在如来佛手心里撒尿,佛祖居然无法回避,无奈捏着鼻子闻了一阵“猴尿臊气”。孙悟空与观音菩萨联手降妖,悟空突发奇想引诱菩萨化身妖精,大慈大悲大智慧者观音菩萨不识猴头“诡计”,直到被讥讽为“妖精菩萨”“菩萨妖精”时才恍然大悟,真个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唐僧身为师尊,对《心经》的理解反不及徒弟,几次放下身段,自愧不如,称赞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有人说,唐僧的前身是金禅子,本是如来佛祖的第二位大弟子,因偶尔犯错(听经时瞌睡走神)被打入凡尘。他童年时代即遭受遭贬、出胎、抛江、抱怨四难,即九九八十一难的前四难,高僧出身如此不堪也是一种“脱冕”的表现。只是觉得唐僧父亲之官路上无辜遭害,母亲惨遭蹂躏,“脱冕”未免太过残忍。历代佛教徒即以“亵渎圣僧”、丑化玄奘大师为由疏远、敌视《西游记》。*如20世纪80年代,央视拍摄电视剧《西游记》,所到之处倍受欢迎,却遭到一些僧寺冷遇,佛教大师赵朴初先生甚至断然拒绝题写片名,并恳切希望电视剧“为唐僧平平反,起码不要丑化唐僧”。参见杨洁《敢问路在何方》,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4页。又,近代虚云法师也说过:“世上流传《西游记》《目连传》,都是清浊不分,是非颠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玄奘法师有《大唐西域记》,内容所说,都是真实话。惟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话。这部书的由来是这样的:北京白云寺白云和尚讲《道德经》,很多道士听了都做了和尚,长春观的道士就不愿意了。以后打官司,结果长春观改为长春寺,白云寺改为白云观。道士做了一部《西游记》小说骂佛教。看《西游记》的人要从这观点出发,就处处看出他的真相。”这段文字引自互联网,其真实性无可质言,这里仅备参考。。
最可笑的是太上老君。他信誓旦旦,要将孙悟空关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锻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结果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孙悟空不仅没有变为灰烬,反而炼成一双识辨妖邪的火眼金睛。书中写道:
那大圣双手侮(捂)着眼,正自揉搓流涕,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眼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呼啦一声,蹬倒八卦炉,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炉,与丁甲一班人来扯,被他一个个都放倒,好似癫痫的白额虎,疯狂的独角龙。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捽,捽了个倒栽葱,脱身走了。
自此之后,太上老君作为道教一代宗师,常被孙悟空冷嘲热讽,玩弄于股掌,见着悟空就心里发怵,不是作揖相迎,就是丹丸赠送,纯粹一个“宵小之徒,现世小丑”。——“脱冕”何其彻底。
再说“加冕”。
“加冕”是“脱冕”的反面,两者相反相成,一方的“脱冕”必定是另一方的“加冕”。正是在对玉帝、如来、老君、唐僧等正统人士的“脱冕”过程中,完成了悟空们人格或精神的“加冕”。
首先是身份的“加冕”。相对于上述上层人士,孙悟空没有高贵的血统,甚至无父无母,只是个天生石猴,名不见经传。然则,孙悟空果真无一字来历?否,否,不然。且看《西游记》的叙说: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兼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
原来孙悟空是一个“自然之子”,天父地母、风雨雷电等自然力是他的助产婆,血统比任何人都更高贵,来头最大,他的年岁孕育期从盘古开辟算起,玉皇大帝苦历一千七百五十劫凡二亿二千六百八十万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顺便提及,“天真地秀、日精月华”这八个大字,简直就是一部漫长的生命起源和发展史,“金猴出世”正是50亿年生命孕育、诞生史的缩影。《西游记》对孙悟空身世与诞生的描写不失为文学史上一次最宏伟的艺术构思。通过诠释孙悟空身世的秘密,即能发现其中的“加冕”意义。
其次看行动的“加冕”。孙悟空的“政治行动”分为两个方面:闹三界与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闹三界”是孙悟空的“英雄传奇”,胡适称其为“失败英雄齐天大圣传”[12]。闹龙宫抢夺东海至宝——定海神针,四海龙王凄凄惨惨;闹地狱强消猴属生死簿,十代冥王战战兢兢;闹天宫袭扰蟠桃盛会,王母娘娘花容失色,玉皇大帝手足无措。都是惊风雨、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完全可以与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大功业相媲美。西天路上,孙悟空一路斩妖杀怪,苦历九九八十一难,度尽劫波,终于保护唐僧取回三藏真经,教化东土人民,创获无上正果。唐太宗特作《圣教序》*《圣教序》,全名《大唐三藏圣教序》,收入严可均编《全唐文》卷十,《西游记》全文引录,文字有少许差异。赞誉曰:“方冀真经传布,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圣教序》虽为表彰唐僧而作,但人尽皆知取经功臣第一人实为悟空。如意金箍棒、火眼金睛、腾云驾雾、十万八千里筋斗云诸般神技异能,闹天宫、火焰山、女儿国、真假美猴王、无字真经诸般奇人奇事,《西游记》采用神话方式为孙悟空的行动“加冕”,作为艺术精神和文学风格,符合巴赫金“怪诞的现实主义”与“颠倒的世界”的理念[13]。
最后为人生命运的“加冕”。取经功德圆满以后,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与唐僧的旃檀功德佛平起平坐,甚至超越了观世音菩萨的果位*观音菩萨曾发下宏愿,要度尽天下众生,自己最后成佛。《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观音)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众悲苦无尽,观音无法成佛。所以在民间,观音崇拜远超佛祖释迦牟尼。如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说:“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唯观音大士,慈悲众生,百方度世,亦犹孟子与孔子也。”评价高于三千诸佛。《西游记》也有观音崇拜的表现,如如来镇压孙悟空的压帖“六字真言”即来自观音菩萨的大明神咒,可见在民间崇拜观音比诸释迦牟尼佛祖尤甚。。“斗战胜佛”的佛号不见于佛经,当为吴承恩游戏之笔,猜测如来佛祖因不喜悟空本不愿以佛号相赠,无奈害怕他当庭反将起来不可收拾,自己再次露丑才不得已而权矣。所以说,孙悟空“斗战胜佛”的封号象征了以情抗理的最后胜利,从“脱冕—加冕”的二重组合看,则是完成了对如来最后的一次“脱冕”和孙悟空最终人生命运的“加冕”。
总之,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反抗”的哲学。运用这一文化政治学说检视《西游记》,不仅能发现作品的“反抗”主题和浓厚的狂欢化色彩,而且还能感受到其中“脱冕—加冕”的深层结构,用巴赫金的话说就叫——“复调”。
参考文献:
[1]何满子.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J].社会科学,1982(11):56-58.
[2]鲁迅.摩罗诗力说[M]//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61.
[3]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M]//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雅克·朗西埃.艺术无法扮演政治行动的角色[N/OL].社会科学报(上海),2015-04-09.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2-293.
[6]林庚.西游记漫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3.
[7]吕峰.感性分配的政治——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8]梁归智.自由的隐喻:《西游记》的一种解读[M]//梅新林,崔小敬.20世纪《西游记》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448.
[9]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论[J].山西大学学报,1994(2).
[10]赵勇.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J].文学评论,2004(3).
[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65.
[12]胡适.西游记考证[N/OL]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15.
[13]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31.
责任编辑:孙义清
Re-evaluate the Topic of "Revolt" in "Journey to the West"—with Rancière and Bakhtin’s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s reference
ZHU Hong-bo
(Literature Colleg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topic of "revolt"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ntexts of culture. With modern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al (mainly choose Rancière’s political aesthetics and Bakhtin’s carnival poetics) as reference,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topic of "revolt" in Journey to the West are the power struggle and the revolt in sense, while not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The ways of revolt reflect carnival color through forms of "coronation" and "abdication"
Key words:Journey to the West; the Topic of "Revolt"; Rancière; Political Aesthetics; Bakhtin; Carnival Poetics
作者简介:竺洪波(1959-),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等研究。
基金项目: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ZD106);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西游记》学术史研究”(2013BWY003。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247-06
收稿日期:2015-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