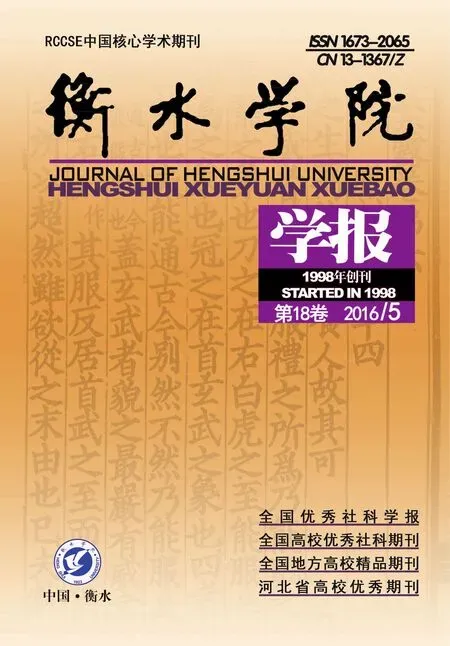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
任 蜜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董仲舒思想的“天”“元”关系
任 蜜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元”和“天”在董仲舒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元者为万物之本。”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群物之祖也。”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的关系是: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臵于比较“虚”的位臵,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董仲舒;天;元;生成论;本体论
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董仲舒一方面说:“元者,始也。”(《春秋繁露·王道》,以下引用《春秋繁露》仅注篇名)“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另一方面又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天者,群物之祖也。”(《汉书·董仲舒传》)那么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和“天”究竟是什么含义?二者究竟何为宇宙万物本体?二者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二者与人类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研究董仲舒思想中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元”之内涵
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源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元年春,王正月”乃《春秋经》语,“元年者何”以下是《公羊传》对经的解释。在《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传》对于“元”重视,《穀梁传》《左传》皆对“元”没有论述,如《穀梁传》解释说:“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左传》解释说:“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传》之所以对“元”重视,盖与其“大一统”思想有关,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董仲舒对于“元”的理解也是在公羊学背景下展开的,其说:“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玉英》)“志”乃衍字。这里的“元”为大始的思想显然取自公羊学。“元年”为君之始年,因此君主对其非常重视。以“元”为“始”的思想,是汉代春秋学比较常见的看法。如贾谊说:“《易》曰:‘ 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新书·胎教》)刘向说:“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说苑·建本》)贾谊的说法亦见于《大戴礼记·保傅》篇。从贾谊、刘向的论述来看,他们虽然非正宗公羊学传人,但也受到《公羊传》思想的影响。
在公羊学的基础上,董仲舒进一步对“元”进行了形上学的论证。他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玉英》)“终不及”之“终”,凌曙曰:“原注:终,一作故。”“生不必应四时之变”之“生不”,苏舆认为当作“生死”[1]68。刘师培认为“不”当系衍文,或“又”之讹[2]。“承天地之所为”之“地”,徐复观认为是衍文[3]218。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
对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梁启超认为,“元年”本来作“一年”,是孔子作《春秋》的时候才改的。其说:“元年春,王正月。不修《春秋》,疑当作‘一年春一月,公即位’。何以见得呢?据传发问‘元年者何……’,解诂说明‘变一为元者……’。知鲁史本作‘一年’,孔子修之,将‘一字’变为‘元字’。”[4]据上述董仲舒所说“《春秋》变一谓之元”,可知梁氏所说有理。不过“元年”的用法在《尚书》中就已经使用了,如《伊训》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苏舆说:“谓一年为元年,未修《春秋》之先,盖已有此。商称元祀是也。而序《书》称‘一年戊午’,《书传》称‘周公摄一年’,又云‘文王一年质虞芮’。意周初尚参错用之,圣人沿殷法取元,遂为定称。”[1]67由此可知,“元年”“一年”起初只是用来表示君主继位的始年,并无深意。因此,二者起初可以互用。到了孔子修《春秋》的时候,根据殷历,“元年”的用法遂在《春秋》中固定下来。《公羊传》认为“元年”与“春为岁始”一样,是表示君之始年的意思。在《春秋》和《公羊传》中,“元”虽然重要但并没有形上学的意义。董仲舒则对“元”作了形而上的论证。董仲舒认为,《春秋公羊传》言“元年”而不言“一年”大有深意,其表示“元”乃宇宙万物的本原,“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元者为万物之本”(《重政》),“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宇宙间一切事物皆由“元”生出,“天”“地”也不例外,因此他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二端》)
那么“元”在董仲舒那里是什么意思呢?以往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如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的“元”只是纯时间观念。他说:“董仲舒用之作为宇宙本原的‘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它只是纯时间的观念,不包含任何物质性的内容,似乎也不包含人的意识,只是纯粹的概念。”[5]徐复观、金春峰等则认为其是“元气”的意思。徐复观说:“在仲舒心目中元年的元,实际是视为元气之元。……仲舒认定《春秋》的元字即是元气,即是天之所自始的‘端’。”[3]219金春峰说:“从哲学上看,元可以有三种释义:1)气;2) 精神;3) 天。本文认为,释为气比较符合董仲舒思想的特点。”[6]冯友兰说:“在董仲舒的体系中,‘元’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即使把‘元’解释成‘元气’,而这个‘元气’也一定是有意识和道德性质的东西。”[7]这几种说法,哪种更符合董仲舒的思想呢?还是都不符合,另有他义。
从现有材料来看,“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以下几种含义:1) “始”义。如前面说的“谓一元者,大始也”。《王道》也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应该来说,这是“元”的最基本含义。《说文·一部》说:“元,始也”。2) “首”义。如《立元神》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深察名号》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这里的“元”与“国之元”的意思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3) 与“气”连用,指“元气”。如《王道》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天地之行》说:“布恩施惠,若元气之流皮毛腠理也。”4) 还有“元士”“黎元”等用词,这些都是古代比较通用的用法,并无特别的含义。
可以看出,“元”在董仲舒思想中有不同的含义,但能代表董仲舒独特思想的是第一种含义。除了“元气”外,其余几种含义都是董仲舒以前常用的词。如孟子说:“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元”指的是首、头。贾谊说:“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新书·过秦中》)“元元之民”,与“黎元”的含义相似,指的是百姓。
“元气”一词最早见于《鹖冠子》中,其《泰录》篇说:“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这是说天地由元气所生,万物又因天地而有。《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此中所引两“气”字,据《太平御览·天部一》所引,皆作“元气”。王念孙说:“此当为‘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下文清阳为天,重浊为地,所谓元气有涯垠也。”[8]王氏所说虽无实据,但据《淮南子》书中所说,此“气”应当理解为“元气”。《淮南子·缪称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泰族训》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按:此语亦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说:“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二者虽然皆引自“黄帝”,但表明这种思想是《淮南子》作者认同的。“与元同气”说明“元”也是一种气,因此可以称作“元气”。可以看出,在董仲舒时已经有“元气”的概念。但在董仲舒思想中,“元”与“元气”并不相等。《王道》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这里也说“元”是“始”的意思,但并没有把其当作“元气”。如果把其解释成“元气”,那么下面“王正则元气和顺”就讲不通了。“元气”在这里应指由“元”而生出来的“气”,这种气充塞宇宙,是君王与外界感应的一种中介。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元”在董仲舒思想中并不仅仅是《公羊传》说的时间观念,其还具有形上学的意义。《玉英》说:“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达其所为也。”这是说,“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
董仲舒这种以“元”为本体的思想应源于《易传》。《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两句本来分别是对《周易》“乾,元亨,利贞”和“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解释。在《周易》中,“元”本来是“大”的意思。《易传》却对其进行了形而上的解释,“乾元”是万物之始。“坤元”则作为“乾元”的辅助,也是万物生长的凭借。《文言传》则认为“元”是“善之长”,即“元”是一切“善”的来源,这是对《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元,体之长也”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而穆姜的思想也是源于《周易》的。可以看出,与《彖传》不同,《文言传》“善之长”的说法并没有将“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在《春秋繁露》中,我们能看到董仲舒对《周易》思想的论述。如《玉杯》说:“《易》《春秋》明其知。”“《易》本天地,故长于数。”《精华》说:“《易》无达占。”这些语言都非明于《易》者不能言。除此之外,董仲舒还直接引用《周易》来论证自己的思想,如《玉英》说:“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此出自小畜卦初九爻辞,原文作“复其道,何其咎,吉。”《精华》说:“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国家倾也。”此出自鼎卦九四爻辞。《基义》说:“故寒不冻,暑不暍,以其有余徐来,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此出自坤卦初六爻辞。《坤·文言》曰:“《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说文·心部》:“愻:顺也。”“愻”“逊”古通,可见董仲舒此处的论述受到《文言传》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元”的思想应受到了《易传》的影响,又借助《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的论述对“元”进行了创造性解释,从而突破了《公羊传》“元”的政治含义,把“元”推到了形上学的高度。
二、“天”义疏解
对于中国古代的“天”,冯友兰曾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之天是也。”[9]这五种含义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天”的不同含义。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主要有主宰之天、物质之天和自然之天等含义。
对于主宰之天,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郊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郊义》)这是说在所有的“神”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如果祭祀“天”的礼节不完备的话,那么祭祀其它众神礼节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众神都是由“天”决定的,那么天下万物就更不用说了。董仲舒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这是说,“天”是一切万物的根本。对于“天”来说,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日月风雨、阴阳寒暑等自然现象都是在“天”的作用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董仲舒看来,“天”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如果离开“天”,则宇宙万物就不能产生。单独的阴气和单独的阳气都不能产生宇宙万物,它们只有和“天”结合,才能生出宇宙万物。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顺命》)董仲舒还用祖先和子孙来比喻天与万物的关系。如其说:“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观德》)“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这里虽然说的是“天地”,但实际上主要是讲“天”,因为“地”是从属于“天”的。《五行对》说:“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可以看出,董仲舒说的主宰之天有着浓厚的神学意味。
对于物质之天,董仲舒说:“故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玉杯》)“传曰:天生之,地载之,圣人教之。”(《为人者天》)“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天道施》)这里的“天”都是与“地”“人”相对的物质之天。
至于自然之天,主要指天道的运行。在董仲舒思想中,其主要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阴阳、五行都是从“天地之气”分化出来的,它们的运行体现了天道的变化。《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在董仲舒看来,天道的变化,体现在阴阳二气的循环消长,与四季相配,阳气盛于春夏,阴气形于秋冬。虽然阴阳二气都体现了天道的变化,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阳气处于主要的、实在的位置,而阴气则处于辅助的、空虚的位置。因为阳主德,阴主刑,所以这种关系体现了天道的“任德不任刑”。
五行也是体现天道的一个重要内容。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义》)木、火、土、金、水五行都为“天”所有。五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相生关系,一种是相胜关系。所谓“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种次序是由“天”规定的。而“相胜”则是指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董仲舒看来,五行相生的关系就如同父子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木生火”,木为父,火为子。“火生土”,则火为父,土为子。其余依次类推。父处于支配的地位,子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在五行中,土处在居中的位置,“五行莫贵于土”。因此,在与四时相配的关系上,土与其它四行不同。其它四行都有具体对应的季节,如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土则不居于四季的任何一季,实则对四季皆发生作用。五行虽然主宰四季的运行,但其还要服从阴阳二气的支配。《天辨在人》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
除了上面三种“天”的主要含义外,在董仲舒思想中,还有运命之天、天理之天,前者如《随本消息》说:“天命成败,圣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后者如《度制》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相比其它三义,这两种含义比较次要。
在董仲舒思想中,“天”的含义虽然很多,但神灵主宰之天是最主要的,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物质之天、自然之天等不过是它的表现。《天地阴阳》说:“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因此,在董仲舒那里,物质之天、自然之天背后都参杂着神灵主宰之天。在董仲舒看来,“天”主要有十个方面,其说:“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可以看出,其中天、地、人三者是从物质之天层面讲的,而阴阳、五行则是从自然之天的层面讲的,它们合起来都是神灵主宰之天的表现。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根,而董仲舒则认为“道”也是出于“天”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样,董仲舒就在继承和改造孔子“天命”和墨子“天志”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三、“天”“元”“人”的内在关系
从上可知,董仲舒对于“元”和“天”的根本地位都有论述,那么二者究竟属于何种关系?哪一个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我们前面说过,董仲舒对于“元”的论述,是源自《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天”在其中相当于“春”的位置。《汉书·董仲舒传》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这里明确把“春”解释为“天之所为”。按照这种逻辑,“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
董仲舒对于“元”与“天”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其说:“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惟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玉英》)这段话亦见于《重政》篇。这是说,只有圣人才知道宇宙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一”,这个“一”就是“元”。做事如果不能顺承万物之所从来的“元”,那么就不能成功。因此,《春秋》把“一”改称作“元”。“元”就是本原的意思,其是与天地相始终的。人也是有始有终的,其生长与四时的变化相顺应。因此,“元”是万物的本原。人的本原也是天地产生之前的“元”。人虽然生于天气、遵奉天气,但不能直接与天之“元”相联系,而与天共同违背“元”的作为。苏舆说:“天固勿违于元,圣人亦不能违天,故云不共违其所为。元者,人与天所同本也。”[1]69因此,君王要遵奉、继承天的作为来完成自己的功业。君王之道只与天来共同实现他的功业,而与天地之本原的“元”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元”是不能直接施予人的,这是贯彻天的旨意的表现。这说明,在董仲舒思想中,“元”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因此,其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
从上可以看出,尽管“元”处于比“天”更为根本的地位。但“人”不能与“元”发生直接关系。也就是,“人”只能与“天”发生关系,而不能越过“天”直接同“元”发生关系。这实际上使“元”处于比较“虚”的位置。在生出“天”以后,“元”的任务就完成了。而“天”对于人及万物则有实际的主宰作用。因此,董仲舒又说“天”为“万物之本”“群物之祖”。在董仲舒看来,这也是《春秋》的基本要求,如其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楚庄王》)“《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玉杯》)“《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天”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与万物都是从“天”生出来的,但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能够超然于万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人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样子设计出来的,如人的骨节本于天的岁数和月数,五脏本于五行之数,四肢本于四时之数。天有昼夜,人有视瞑;天有冬夏,人有刚柔,等等。因此,可以通过人来认识天,“求天数之微,莫若与人”(《如天之为》)。
在董仲舒看来,天子即是人间的代表,也是天所任命来治理民众的。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深察名号》)“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佑)而子之,号称天子。”(《顺命》)“天子者,则天之子也。”(《郊语》)只有道德能与天地相比的人,才能称为天子。这种能行天意的天子又称作圣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威德所生》)。圣人之性是纯善无恶的,“圣人之道,同诸天地”(《基义》),“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奉本》)。因此,圣人是效法天的意旨而治理国家。如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这是说,圣人要按照天的意旨,选贤任能,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
天子对上要顺从天意,对下要为民负责。天子的作用是贯通天、地、人的。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王道通三》)古人在创造文字时,把三横画通过一竖画连接起来而称作“王”。三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人,一竖画则代表贯通天、地、人的王。董仲舒通过对“王”字的解释,意在说明只有天子才能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
天道是“任阳不任阴”“任德不任刑”的,天子治理国家也应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阴阳义》说:“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使德之厚于刑也,如阳之多于阴也。”如果“刑厚于德”或“废德而任刑”,那就是“逆天”,就会出现灾害、怪异。
综上可知,从生成论上看,“元”是一切宇宙万物的根本,“天”也是由其决定的。但从本体论上来看,则人与万物都由“天”来决定的,人与万物都是从“天”而来的。这实际上把“元”置于比较“虚”的位置,而“天”才有实际的主宰作用。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上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012.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6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5:45-46.
[5] 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9.
[6]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46.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5.
[8]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81.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n” and “Yuan”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REN Mili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Yuan” and “Tian” ha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n the one hand, he said that“Yuan” was the origin of everthing in the universe. On the other hand, he also said that “Tian” was the ancestor of everthing in the unive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an” and “Tian” in his thought could be 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pesp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mology, “Yuan” was the origin of everthing in the universe, including “Tian.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human beings and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were determinded by “Tian” and they were originated from it, which actually put “Yuan” in a more “empty” position, but “Tian” in a practical dominant one.
Dong Zhongshu; Tian; Yuan; cosmology; ontology
B234.5
A
1673-2065(2016)05-0023-06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06
2016-07-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ZX026)
任蜜林(1980-),男,山西曲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