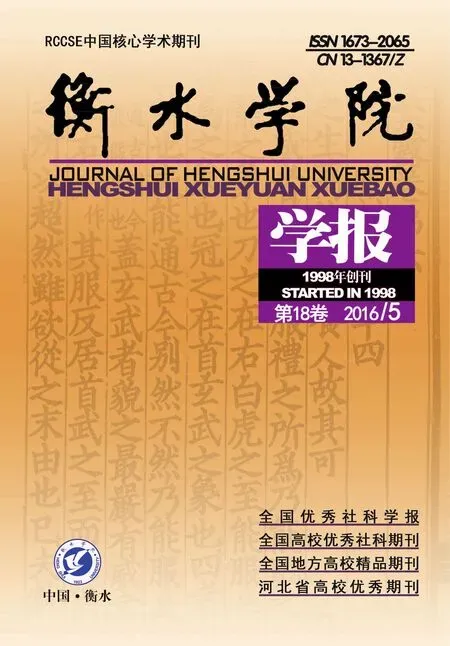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哲学
金 春 峰
(人民出版社 哲学编辑室,北京 100706)
董仲舒与汉代经学哲学
金 春 峰
(人民出版社 哲学编辑室,北京 100706)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的实际上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建立的道德目的论哲学体系,确立起“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主题,从而重新恢复与发扬了先秦儒学的人本与人文主义传统。汉代,《易》《诗》《书》《礼》《春秋》都贯彻董仲舒的这一哲学思想,从而使“经学”成为政治的指导方针与意识形态。
董仲舒;经学哲学;道德目的论;天人关系
一、时代的新问题与需要
哲学虽然是人的精神与思想自由与自由运思之产物,但社会与政治的需要,常常是刺激其产生的力量与催生剂。中国哲学,因其政教合一、天人合一的传统,与政治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因而更受政治的直接影响,其内容也与政治密切相关。它常常是围绕时代特别是政治所提出的大问题,以它为轴心而建立起来的。汉代哲学中占支配主导地位的经学哲学,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点。
从社会情况看,汉初七十多年,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生活富庶;但同时促使了新的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尖锐化。
1) 诸侯王日益壮大,坐山为王,积蓄力量,滋生了篡权夺位的政治野心与叛乱。
2) 没有文化教育、教养,没有法纪与权力的监督,许多诸侯王极度腐化、堕落。
3) 军功贵族和地方豪强,横行不法,大肆兼并田产,加剧了社会矛盾。国家权力不彰,宗族复仇与游侠之风盛行。
4) 匈奴势力壮大,边患日益严重。
黄老目光短浅,因循苟且,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缺乏进取宏图与作为,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解决上述新的社会矛盾。黄老不懂得文化教育与道德的重要性的内在弱点,也使其完全不能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新的足以担负解决新的时代任务的哲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哲学,就是为解决上述这些时代性的根本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这新哲学,用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话说,其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是讲天人关系,“通古今之变”是讲古今关系——如何借鉴前人治国平天下的历史经验教训,都有很强的现实性、政治性。两句话合起来即是讲包括时间、空间、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的最普遍也即世界观的大问题。因而,汉代哲学不仅其问题意识是哲学的,是自觉地从哲学高度提出的,它的回答与其由此建构的思想体系也真正是哲学的。
天人关系本是先秦以来各家哲学所讲的共同问题。孔、孟、荀、《易》、老、庄,其思想体系可以说莫不以天人关系为中心;“通古今之变”亦是如此,而法家尤具代表性。这两大问题在武帝即位时,都有其新的时代尖锐性、迫切性。哲学如果不想脱离生活与时代,不想成为僵死无力的经院哲学,就必须回答这两大问题。而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哲学,正是在成功地解决这两大新问题中建立起来的。它如此成功,以致支配了汉代整整四百年的时间,成为此时期学术、政治、社会伦理道德的指导思想。
就天人关系言,战国以来以至汉初,呈现一种新的危机,危机的集中表现,一是传统信仰的失落;一是人的失落,人的尊严与地位的丧失。
殷周有传统的上帝与天命信仰。王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都建立于这一神权、天命之上。经过春秋以来的理性的发展,文化的提升,人文思想的涌现,系统性的哲学思想的诞生,老子道家,上帝、天命信仰被严重打击、毁坏。
孔子制礼作乐,维护传统信仰,并把它理性化而引向人文与道德的方向,为中国文化树立起真正的基础。同时为人的尊贵与地位,从天人关系的哲学高度,提供有力的论证。但儒家思想在孟子以后迅速遭到削弱、围攻,郁而不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荀子在战国末期,成为儒学代表,但荀子的“天道”观,摒弃传统,摒弃信仰,建立在道家自然论基础上。其礼乐文教、道德伦理思想,以人性恶为前提。按荀子的学说:人之能成为人,依赖于圣王的“化性起伪”,人成为完全被动的受教育与被改造者。同时期居于显学地位的法家,源于黄老刑名,其思想体系中,人亦被视为一自然物。以至韩非认为,对人的统治,仅须赏罚两手,一如对牛马的驾驭。“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道德的教育,被认为完全是不必要的。人的尊严与地位彻底丧失。汉初流行的《黄老帛书》,对人的看法即属于韩非这一思想系统。《十六经·观》说:“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不会(交配)不继,无与守地;不食不人,无与守天。”人和禽兽一样,主要的特征被认为是生育、衣食;对人的统治被认为也只须刑德两手。所以,在汉初,文化道德蕴藏与酝酿着深刻危机,其性质、根源,不是贵族腐化堕落的问题,而是治国之指导思想、哲学思想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则是天人关系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看法与信仰之失坠的问题。
古今之变的问题,汉初亦呈现极大的尖锐性。这表现为:新的大一统的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建立了,种种人际关系、政治关系,如君臣关系、臣民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等,必须有新的思想予以规范;而旧的包括孔孟在内的传统的学说、政治思想以及秦人奉行的法家思想,或者过时了,或者失败了,都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与政治的需要。
孔孟的政治与伦理道德学说是适应宗法分封、亲亲、世袭的诸侯国家这种情况的,以宗法亲亲为基础。孔子讲“正名”,讲“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讲“子欲善而民善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庶人不议”。孟子讲“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推恩足以保四海”等等,都是以宗法亲亲制的国家关系为基础的。士与诸侯的关系,也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自愿帮忙、帮办的关系。新的大一统皇朝建立后,天子居至尊无上的地位,并掌握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君臣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完全是政治关系。“亲亲”情恩的原则已不能作为关系的基础。法家完全排斥宗法仁恩,而一律诉诸于法。实践证明,这不适合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导致了秦皇朝的兄弟骨肉相残,土崩瓦解。那么,在新的时期,仁恩宗法与法令、法治如何协调、兼顾?“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何以“定位”?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具体如何规范?如何综合先秦诸家思想,借鉴与吸收以往的经验教训以符合新政治形势的需要?这成为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春秋以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秦罢黜各家,独尊法术。秦的速亡,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新形势下,究应如何作新的选择?儒家与法家思想如何调和、折衷?如何对待各家的思想资产?这也是古今之变要解决的大问题。
董仲舒的经学哲学体系——《春秋》公羊学,其成功,即在于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答案。
二、汉代经学哲学的基本性质与内容
董仲舒建立的哲学体系,称为经学哲学,因为在其答武帝诏问的《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意见被接受了。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从此成为官学——太学博士生员的基本教材,成为大经大法,即政治、人伦、道德与天人关系的根本指导性思想,有如《圣经》、佛经之称为经,这五部著作也成了五部经书。《圣经》、佛经只解决人生之价值与归宿问题,汉代经学则不仅解决这一问题,还政教合一,解决国家之政治之根本大政方针,是所有企图进身官僚统治阶层的人所必须修习掌握的。
汉代经学,后人特别是清人称之为汉学,以为其性质、内容是名物训诂。实际上,汉代经学主要特质与特征,是义理之学与哲学,而主要是哲学。这个哲学的根本内容是天人关系,而核心是重新树立天的权威与信仰,重新确立人的尊严与地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确立皇权的性质与任务以及君臣、君民关系的性质等等。
战国后期,天人关系与古今之变这两大领域中,盛行的是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与邹衍的终始五德思想。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及《月令》《淮南子·时则训》中,它与人君的起居饮食、施政及人们的生产生活结为一体,而以神秘的天人感应为核心。秦朝的统治者信奉这一学说,汉朝的统治者也信奉这一学说。它是一巨大的思想与政治力量,是任何一个企图居于指导、主导地位的新哲学所必须面对的。由于秦的“焚书坑儒”,儒家研习的典籍中,唯一可以继续讲述的,是与占卜相结合的《周易》,故《易》学在秦与汉初亦特别流行。马王堆帛书中,除《老子》《经法》等著作,《周易》及《易传》《易说》是最有分量的部分。“《易》以道阴阳”。所以阴阳家与儒家在秦汉之际这一时期,可以说已经合流了。本来《易》讲的阴阳,就不是纯自然的范畴,而打上了“天道”“吉凶”“祸福”及道德、人文的内容,有其“天人合一”的神秘性,在与阴阳家合流以后,就更加加重了这一色彩。董仲舒的哲学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是由这一情况决定的。
但董仲舒并非简单地继承与照搬,而是把阴阴五行学说的精神与关注点,由神学的以吉凶祸福为内容的天人感应,转变为以阴阳之气有规律地运行之宇宙图式和以人为中心的道德目的论哲学体系。在古今之变的问题上,则以《公羊春秋》学为基本指导方针,古为今用,有如司马迁引董仲舒所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汉书·司马迁传》)实际上使《春秋》学由历史演变为政治哲学,演变为解决当时政治、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指导著作。
三、董仲舒的道德目的论哲学思想的主要命题
董仲舒的道德目的论哲学,围绕天人关系从各方面展开论述,其主要命题是:
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王道通三》)
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道通三》)
天地阴阳水火木金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天地阴阳》)
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祭义》)
在勃兰兑斯看来,华兹华斯是一个纯粹的英格兰人,他就像一株老橡树深深地扎根在帝国的文明沃土之上,他厌恶一切异族,如同厌恶法国一样[28]62-63。勃兰兑斯的论述略显偏颇,至少华兹华斯在对苏格兰的战争暴力的态度上表现了矛盾之情。诗人对于英苏战争的态度表征了其作为以言说世间真理、书写人间悲苦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个人情感与掺杂了政治因素的民族情感的冲突。
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万物者,莫贵于人。(《人副天数》)
仁, 天心。(《俞序》)
察於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王道通三》)
中心思想是突显人,认为只有人是目的,万物皆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人之形体化天数而咸,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由此确立起“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的主题。而人之贵,不在于其有知识,而在于有仁义道德,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所谓“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然有文以相接,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不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恢复了孔孟人为贵的人文传统;而且以开阔的胸怀与远大的视野,综合各家予以消化,而树立起儒家人文思想的权威与独尊的地位。
这里,“人为贵”的人,指的是人的“类”或作为“类”的人,而不是个人,也可以说,这里人是一集体名词。因此它并非个人尊严或与人权有关的思想,把它现代化是不对的;但在古代,在董仲舒的时代,这仍然是与人的幸福、利益密切相关的思想。董仲舒的“立太学”“兴教育”“除奴婢”“去专杀之威”“开放盐铁”、政府不与民争利及主张禅让、革命,提出立君是为了民而不是相反,要求君主行仁政,以教化民为主要责任等等,这些在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可以说都是在这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提出的。它被确立为指导思想,从而使汉代思想在经过战国至秦汉长时期的儒学衰落和混乱以后,能又一次确立起人文思想的大方向,并使儒学传统得以承传不断。
董仲舒的道德目的论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是同类的,而更具鲜明的人文思想特征。汉代大一统政权之能稳固,社会之能长治久安、生产发展、国力强盛,实有赖于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与成功。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体系,在整个汉代四百年间,覆盖与支配了《易》学、《诗》学、《尚书》学各学术思想领域,成为一时代性的思想与思潮。汉代,《易》《诗》《书》《礼》《春秋》都贯彻董仲舒的这一哲学思想,从而使“经学”成为政治的指导方针与意识形态。汉代之“独尊儒术”,独尊的实际上是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其哲学体系和由此建立的新《易》学、新《诗》学、新《书》学、新《礼》学与新《春秋》学。没有这一体系的建立,仅靠政治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五经”之能在汉以后直至清代都确立起“经学”地位,亦是由于这一点。
四、儒道对立与互补
名家兴盛于战国,以后分别为儒、道所吸收,至战国末年已不存在。董仲舒的名号理论仍是对它的继承。
法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一枝独秀。但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就被吸收,成为儒家的组成部分,为“独尊儒术”的儒学所取代。
墨家,其“上同”“尊天”“兼爱”“明鬼”的思想,完全从政治与功利上立论,缺乏天道观与人生观的根基。在战国中前期风行一阵以后,也不再独立地活跃于思想的舞台了。到汉代,它被吸收、融合于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之中。董仲舒的“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可以说亦是吸收了墨子思想的。
阴阳家命运亦与墨家类似。在汉代,成为董仲舒儒家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唯有道家,在汉代,一直以独立的思想体系存在,与儒家相互消长兴衰,既对立又互补。据杨树达统计,汉代研习老子思想者达五十余家,其中有像刘向这样的儒家学者(刘著有《说老子》),而儒道兼综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则有扬雄、王充、郑玄。
道家,在汉初,以黄老之学的特殊形态,成为政治的指导思想。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它得到最高的评价,被认为应该成为统一各家思想的指导思想,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俨然对立。但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融合各家思想的企图。《淮南子》以道家为主,兼有浓烈的杂家色彩。而这一色彩,亦反映出其企图综合各家的打算。在《河上公老子章句》和严遵的《道德指归》中,它系统地阐述“治国治身同一”的理论,希望人君世主采纳,表现出强烈的“君人南面之术”和弘扬道家政治社会理想的思想特征;但同时也吸收儒家和法家思想。《河上公老子章句》还提出了“人者,天下之神器也”的命题,和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相互呼应。在西汉哀平以后,谶纬出现,种种迷信荒诞思想盛行,思想界被弄得乌烟瘴气,此时,道家思想成为有力的清醒剂。扬雄以道入玄,造作《太玄》,企图取《周易》而代之,这是道与儒的互补和融合。王充以黄老之自然观为哲学基础,发展出批判神学与崇尚实知、知实的理性思想,亦是儒道兼综的成果。郑玄引“老”注《易》,引进自生、自长、自养、无为的思想范畴,开王弼以“老”注《易》的先河,亦开魏晋儒、道融合,形成新经学的先河。
五、抽象思辨能力的发展
《淮南子》很为武帝所欣赏。《淮南子》抽象思辨能力很强,对道之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出了系列的思辨性的论证,如:“无形者万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原道训》)“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原道训》)老子“有生于无”,有生成论与本体论的两种说法,《淮南子》这里的讲法是明确的本体论思想。在这一论述中,“无”与“虚”不是空无、虚无、一无所有,而是从本体上作的一种指谓。意思是,本体是无形无象的,但却是有形有象有名之物,如有形的某物——五声、五味、五色等等之根据与所以然。故“无”是对“有”而言的。它也是一种“有”,但含寓在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有”之中。从其不受具体的“有”的局限而言,它是“非有”,是“无”;从其作为“有”的本体根据,使“有”能成为“有”而言,它又不是“虚无”而是“有”。《淮南子》举了许多例,如:“寒不能生寒,热不能生热;不寒不热乃生寒热,故有形出于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说山训》)“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形,则得其所见矣。”(《说林训》)等等,所谓“不寒不热”,即超越于具体的寒热而又作为寒热之根据与所以然的寒热本体,它也就是温度本身。以后王弼说:“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商者,非大音也。”(《老子指略》)“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道德经》第十四章注)“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注)其对“道”为本体的论证,与《淮南子》一脉相承。
“魄问于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为体。’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说山训》)“以无为体”也就是以“无”为本体,即本体不是“有”而是“无”。此“无”即无形无名之“无”,而非虚无。
“无为者,道之宗”(《主术训》) ,“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使不化应化,千变万化而未始有极。……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也矣。化物者未尝化,其所化则化矣”(《精神训》)。以后王弼也发挥类似的观点,说:“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老子道德经》三十八章注)“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老子道德经》第五章注),与《淮南子》亦一脉相承。
《淮南子》哲学中之丰富的本体论和思辨因素,虽未形成体系,但已足够证明,汉人或汉代哲学同样有哲学的抽象思维能力,并不是只能作经验的观察和实证的分析与归纳。这种思辨式的论述,也贯穿于严遵的《道德指归》。
董仲舒哲学中,亦有出色的理性思辨与分析,这集中表现于其名实思想,其对人性问题的论证。先秦,孟子主人性善,荀子主人性恶,但两者都立足于经验的观察与归纳之上。董仲舒的方法则是从名、从定义与一般出发,从中引伸出应有与必有的结论。如谓:“性之名非生与?”“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从这样“性”的定义(名)出发,分析这个定义,指出其中不包含“善”这一后天的由教育而成的因素,由此不同意孟子人性善的结论。而这种理性分析的运用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与其《公羊春秋学》有内在的密切的关系。“《春秋》以定名分”“名号以达天意”,由此,尊名与从名出发,成为董仲舒哲学思想的一大特点。这虽然有神学的成分或神学的外衣,但董提出“名者,名其真也,名其情(实)也”的命题,理性分析也在其中发展出来。
六、汉代经学哲学之政治性及消亡
汉代经学哲学,归纳起来,它的基本特点有:
1) 政治性是其最本质、最根本的特性。经学是政治的指导思想。经学哲学成为经学的首要条件是皇权的支持,汉武帝对董仲舒天人三策的重视、采纳,是经学确立的决定性条件。以后,宣帝有石渠阁会议,裁决经义,东汉有白虎观会议,《白虎通义》成为法典式的典籍。
2) 经学哲学是载道卫道的著作,道德、教化性是其本质的根本的特性。因此《诗》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以“三百篇当谏书”。《春秋》不是历史记事,而是“礼义之大宗”。《易》不是占卜术与普通哲学,而是天道,是天人之道的根本指针。
3) 经学哲学被视为大经大法,是普遍、永恒的真理。其对各门学术之指导与统率是经学的又一特性。汉代五经,不论《易》《诗》《书》《礼》《春秋》,都由统一的经学哲学所指导,具有经学哲学的共同特性。对经学的研究不是学术考证、名物训诂,而是为政治、为伦理道德服务。“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方法,在汉代经学学者中是不存在的。
4) 经书本身的神圣化,被尊崇为“神书”,是经学成为经学的必要条件。故在汉代,孔子被认为是“素王”,负有天命,为汉制法。没有这一条件,经书本身不能超出于其它学术典籍之上,不能具有永恒性与神圣性。故“名号以达天意”“观五行之本末顺逆,所以观天意也”,亦成为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这一点,使它类如《圣经》、佛经。
5) 由于政权独尊儒学,立五经博士,设博士弟子员,到元成之际,宰相大臣皆为经学之士,一切政事以经义为准,经学之士成为新的巨大社会政治力量,形成了“士族”这一新的阶层。巨大的产业、政治权势,门生故吏结成的经学帮派,及经学知识的垄断权、解释权,使这一群人成为一新的足以取代老的军功贵族与土豪强绅而成为社会的主要基础,成为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三位一体的中坚力量。皇帝则挤身经学之中,成为经学的最高权威。这种皇权与经学、皇权与经学士族相互依存结合的情况,左右了西汉后期的政治变化。王莽,由士族拥戴而登位,又由士族的离心而垮台;东汉光武由士族拥戴而登位。灵献之际,汉代亦终于由党锢之祸迫害士族而亡于士族。袁绍集团、曹魏集团及司马氏集团,都是经学士族或依附士族的。东汉士族又世代承传而成为魏晋以后的门阀世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故经学及经学哲学之兴起及衰落,都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其学术理论方面的原因,则在东汉与谶纬结合,以及日益由经院教条而走向烦琐,如在象数易学中所表现者,从而完全堵塞了理论思维的发展。而理论思维正是哲学自身生命的灵魂。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Dong Zhongshu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JIN Chunfeng
(Editing Office of Philosoph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706, China)
“Respecting Confucianism and excluding hundreds” was advocated in the Han Dynasty. What was actually respected was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the ethical teleology established by Dong Zhongshu in his Chun Qiu Fan Lu. It established the theme of “Humans are the most valuable among all the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us resum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humanism in the Pre-Qin Dynasty. In the Han Dynasty,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Songs,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Rites,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ll carried through t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us making “Confucian classics” the political guiding principle and ideology.
Dong Zhognshu;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classics; ethical tele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Man
B234.5
A
1673-2065(2016)05-0017-06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5.005
2015-03-16
金春峰(1935-),男,湖南邵阳人,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