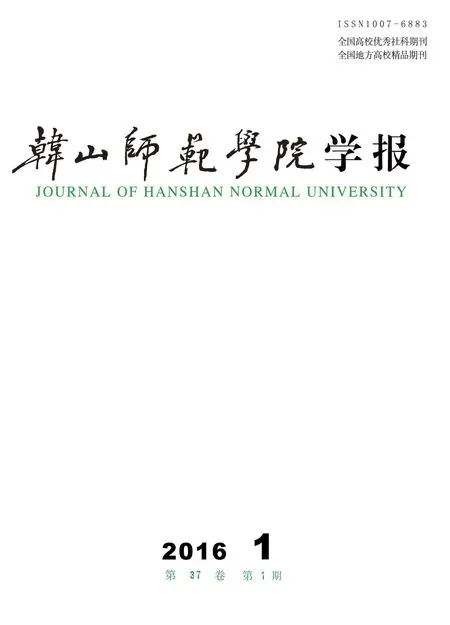论《马人》的主题和叙事模式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69)
论《马人》的主题和叙事模式
秦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1169)
摘要:从弗莱的罗曼司理论出发,分析厄普代克《马人》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回溯传统、忠实于神话原型的《马人》在主题上延续传统文学的追寻母题。与此同时,文本又多处对追寻母题进行戏仿。这是一部游离于真实和神话世界之间、横亘于以人为本的小说和以神为本的神话之间的文本罗曼司。
关键词:文本罗曼司;《马人》;追寻母题;戏仿
《马人》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第三部小说,在这部自传性小说里,厄普代克套用古希腊神话原型,讲述了人世间一个普通家庭里的悲情父爱。半个世纪以来,批评界对《马人》神话与现实的交织模式毁誉参半。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尤利西斯》的模仿,并无新意可言。[1]还有人认为,客戎神话的运用虽适于象征及叙事的目的,但却无助于凸显现实层面上故事的意义。[2]然而,在肯定派批评家看来,厄普代克采用神话与现实的融合叙述,目的在于“扩大对现实的表述可能”[3]64。那么,小说究竟表达的是怎样的主题?神话的借用具有怎样的艺术表现力?现实与神话的交融体现的是怎样的风格?本文以罗曼司理论为依托,从小说的主题模式入手,对作品的艺术内涵进行深度挖掘。
一
作为一种植根于美国文化土壤中的特殊文学样式,罗曼司是一种既关注神话、又关注小说的“边缘”文学体裁。一个多世纪以来,罗曼司辩护者们纷纷著书立说,从多个角度丰富并充实这一美国独有的文学体裁。尽管他们对个体作品的解读不同,但垂林的《自由主义的想象》、蔡司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贝尔的《美国罗曼司的发展》、费德勒的《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以及霍夫曼的《美国小说的形式和寓意》等扛鼎之作都无一例外地达成这样的共识:美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并非现实主义小说,而是罗曼司。罗曼司“是一种根植于美国文化和美国经验的小说题材,它运用的是非现实的方法,借助民间传说、寓言、神话去探究‘人心的真实’”[4]。在霍桑的《七个尖角阁的老宅》、《红字》等作品的序言里,他不止一次地抱怨新大陆上(文学)“材料匮乏”,而只有“罗曼司注定是美国式的叙事方式”[5]3,在创作中,他频繁地采用罗曼司这一文学体裁,去创造“一个中立的领域,一个界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国度”[5]6。在霍桑看来,真实与想象的并置是罗曼司文学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对罗曼司情有独钟的不止是霍桑,著名文论家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详细追溯了罗曼司的起源及发展,将其与小说、告白等并置为文学的主要题材,弗莱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罗曼司……是一种临界于关于人的小说与关于神的神话之间的边缘体裁。”[6]306随着美国文学理论的逐渐成熟,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美国罗曼司体裁的评论家。其中理查德·蔡司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被后人誉为集大成之作。在这部经典文学评论集里,蔡司写道:“自其源始之日起,本土的美国小说就清楚自己的命运,它吸纳了罗曼司的元素,并依此界定自我的特点。”[7]通过对两个世纪以来美国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蔡司又指出,美国小说的盛衰与它对非现实的罗曼司文体的传承密不可分。罗曼司并非对现实的直接表述,它更青睐神秘化、寓言化、象征化的模式。
《马人》共分九个章节,每一章的主人公和叙事角度都在变换着。第二、四、六、八章,儿子彼得以第一人称讲述发生在身边的他和父亲的故事;而在第一、三、五、七章,作家则采用第三人称从旁观者的视角补充片段之间的空缺。简言之,《马人》主要讲述的是一个父亲和其子三天的经历。父亲乔治·卡德威尔是一个普通中学的普通教师,已届中年的他在学校里毫无成就感可言,学生的戏弄、同事的嘲讽、校长的蔑视使他倍感挫败,恍惚间,他感到自己正濒临死亡。然而他不能死,尚未成年的儿子彼得需要他的供养,妻子和岳父还需要他的照顾。第二天,卡德威尔和彼得从位于郊区的家中启程,前往学校。经历了压抑沉闷的一天之后,返家时汽车抛锚,两人只好在一个破败的旅馆过夜。第三天的经历尤为艰辛,遭遇暴风雨、无法归家的父子不得不在朋友亨迈家过夜。直到第四天才得以返回家中。此外,穿插于三日历险记中的,有马人客戎和希腊诸神在奥林匹斯山的故事(第三章),有父亲卡德威尔身后的讣告(第五章),有马人客戎在石岩崖的边缘献祭生命时的内心独白(第九章),有卡德威尔与客戎的交替出现(第一章卡德威尔撞上薇拉·亨迈时)的时空置换,还有成年后的彼得与女友的絮絮私语(第八章)。纵观全作,厄普代克在神话、现实、梦境、回忆间穿插翻转,游刃有余,让故事在其间交织发展,他将三天里的平常生活延展到三代人的生活轨迹,拼绘出卡德威尔祖孙三代的人生,整个文本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张力和悲剧深度。
二
《马人》充分呼应传统神话中的“追寻”母题。它叙述了主人公卡德威尔及其子彼得三天的经历。两人踏上寻求真理的征程,一路上不断受到病痛的折磨。这三天里,他们沉沦、奋争,最终获救。因此,父子两人的三日历险记再现了传统文学的“追寻”母题。弗莱指出:“自罗曼司获得文学样式以来,它就表现为由一连串的小冒险发展至高潮期冒险的轨迹。高潮期冒险的结束便宣告了故事的终结。这个高潮期的冒险,便是成就罗曼司文学样式的要素,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追寻’。”[6]186-187冒险是罗曼司文学情节的主要成分,它由英雄式的角色来执行,分为危机四伏的旅程、狭路相逢时的拼杀以及英雄化碧三阶段。如前所述,《马人》中父子两人三天不断升级的历险记,正对应“追寻”历程的三阶段。
不同形式的病痛,自始至终折磨着卡德威尔和彼得。小说伊始,卡德威尔被刁钻的学生们用钢箭射中脚踝,钻心的疼痛,是小说开篇第一段的主要内容:“疼痛的感觉,从他胫部的狭长经络往上蹿,在他的膝部复杂组织中转悠,往外扩展,再蹿到他的肠子,疼得更凶了……疼痛已把触角伸到头上,展开湿漉漉的羽翼,沿着他的胸腔四壁扩展。”[8]4是箭伤迫使卡德威尔离开他的讲台,去亨迈的修车厂寻求治疗——开启了他的“一连串的小冒险”[3]186。第二日(小说第二章),叙述者转为儿子彼得。该章开篇,彼得一觉醒来,正听见父亲对母亲忧郁地谈到他的病症。“肚子里那东西像条毒蛇绕着我的肠子。”[8]48当天下午卡德威尔到阿波顿大夫那儿问诊、拍片、抓药。除此之外,牙痛也时时折磨着他,拔牙的疼痛同样是难以忍受的。“这疼法是空前的:是一棵花团锦簇的疼痛之树,每一朵花向灰蓝色的空气投射着一团橙绿色火花。”[8]218可以说,卡德威尔无时无刻不受到疼痛的折磨,“如果仔细找一下,他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他要找的任何类型的病痛:牙的甜滋滋的刺痛、疝气的轻微惬意的轧痛、肠子里的病毒不停地在撕搅着、翻起的脚指甲啃着挤在鞋子里旁边的脚趾令人心烦的隐痛,过去一小时用眼过度造成他鼻子上面的阵阵抽搐,以及他头顶上和这勾连起来的另外一种疼痛”[8]199,正是疼痛,让他一次次踏上寻医问药之路。而对彼得来说,他与他天生的疾病——牛皮癣同步登场,“上帝为了造就我成人,给了我这个配合他的四季消长的诅咒”[8]54,彼得对这与生俱来的诅咒痛恨不已,“这东西叫牛皮癣,我生下了就有。太可怕了,我恨它”[8]245。正如《批评的解剖》指出的:“肢体的毁损或残疾,往往是超凡智慧和力量所付出的代价。”[6]297于是,像渔王神话中追寻圣杯的骑士一样,病痛让卡德威尔父子俩踏上了追寻的征程。
在追寻模式层面,小说再现了“堕落→奋争→救赎”三部曲。弗莱指出,充满了冒险的罗曼司故事主角常常以“死亡、消失和复生的三日节奏”[6]165方式呈现,这是“原型之原型”[9]。人因原罪堕落到人世间这一隐喻,在《马人》中得以呈现。第一章以卡德威尔的痛感开篇,对疼痛的认知恰到好处地与宇宙的诞生并置在一起,暗示这是生命诞生时的痛楚:“他疼得眼睛往上一翻,目光射到黑板上他曾用粉笔写过的数字上5 000 000 000(宇宙的大致年龄)。”[8]4紧接着,主人公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降临到人世间:卡德威尔拖着流血的腿,逃出教室,一跛一跛地进入大厅。狭长而昏暗的大厅充斥了“黏乎乎的、油亮的气氛”[8]5,暗喻马人诞生时必经的产道,而一系列肌体意象的陈列正强化了这一暗喻。“他的肚肠有些抽搐”,“上百只银眼睛在闪烁”,“灰花呢上衣的下摆(英文flank双关,意指身体上的侧腹)”,“他的脑袋和肌体一起向前方冲去”,“他的高大、优美、复杂的身体向这青蓝色的光团奔去。他的五脏直翻腾”,终于,在一阵剧痛中,马人诞生了:“在箭杆撞击钢栏杆引发的一阵剧痛中,他跌跌撞撞地跑下通往水泥地面的低台阶。”诞生到人世间的马人以一副倜傥伟岸的身姿呈现在读者面前,“卡德威尔端正他的异样的身架;挺起那与他的大骨架相比有些偏窄的双肩”。[8]5-6接下来,小说的叙事中心转向父子的三日历险记。他们的历险始于一段下坡的冰路,经过火镇、教堂公墓、加利利小镇、七英里店,最终到达奥林格中学停车场。[8]72-93第二章结束,第三章开始,卡德威尔变身马人,匆匆奔驰在前往奥林匹斯山给众神授课的路上。放学后,父子俩开始逆境中的奋争。他们先下楼遇到清洁工海勒(Heller影射Hades),进而穿过亨迈的修车厂(Hummel影射Hephaestus),到迈诺的餐馆(Mi⁃nor影射Mino’s labyrinth)时,彼得遇到潘妮(Penny Pandora),而卡德威尔则去阿波顿大夫(Dr.Appleton影射Apollo)那儿看病,父子俩最终在阿波顿大夫的诊所里重逢。第三天回家的路上,大雪封道,他们只好在薇拉·亨迈(Vera Hummel影射Venus)家过夜。直到第四天父子俩才得以重返家中。第四日,终于迎来了一个“晴好、理智的天气”[8]271,父子俩开车上坡,链环断了之后,两人只得踏雪爬坡。在这段爬雪坡的路程中,两人一再地仰望星空,暗喻着堕落之后来自上苍的救赎。赶回家中的彼得回到他在楼上的卧室,从窗外望出去,看到父亲“趟过我们的庭院,走过邮筒,上坡,一直消失在我们果园的树木之中”[8]293。附加在这些现实化的描述之外的,还有最后一章对马人攀爬石岩崖的描述。父子两人都以上升的意象终结故事,暗示英雄冒险归来时上苍的救赎。在父子俩旅途中,不仅他们遭遇的重要人物的人名以及性格与希腊诸神遥相呼应,他们的冒险还有一个本质特征:对真理的追寻。“在人的世界里寻求智慧时,这种寻求往往与对死亡的焦虑和对未知世界的欲求联系在一起。这种智慧往往以谶言、谜语或神谕的方式传递出来。”[10]卡德威尔与奥林格居民的交谈中,听到了无数条箴言。岳父奉劝他,“时机不待人”[8]62;阿波顿告诉他要“了解你自己”[8]130。他追求智慧的同时伴随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意念,对“追寻”母题的模仿,证明本文是一部以描绘神的故事为中心的神话。
三
同时,《马人》追寻主体的反英雄性和追寻情节的反传统性,又是对罗曼司文学的戏仿。追寻神话的中心特征表现为英雄临危受命、请缨杀敌、一路冲杀过去,攻克所有的困难险阻。这类英雄人物无不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超人的意志力。“晦涩与复杂都不是罗曼司文学所太钟爱的。故事中的人物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追寻行为。支持的一方被理想化为勇猛而纯洁;阻扰的一方则被描绘为邪恶而怯懦。”[6]195
然而,《马人》的主角并非如此高大,表现的是一个反英雄的角色。卡德威尔在追寻途中徘徊犹豫、畏首畏尾,被无常的命运捉弄着,他身心疲惫,觉得自己生活碌碌无为。教书对他来说已不能成为精神寄托,在他看来,这是一份徒然消耗他生命的工作。他是个具有强烈失败感的角色,丝毫没有传统追寻神话中的英雄气概可言。作为教师,教学令他“压抑得要死”[8]100,学生们对他“恨得要死”,他明明白白告诉学生知识是“没有用”[8]100的,学校在他眼里是“仇恨工厂”[8]69;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收入微薄,自惭形秽。无论作为生活中哪一个角色,他都是失意的。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现代社会小人物,他自始至终都纠结于他臆想的死亡。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宇宙的形成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带一长串零的数字,告诉学生“他们让我想起死亡”[8]34;讲授天文学时,卡德威尔偏离主题,发表一通他对死亡的认知:“团藻菌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发明了死亡……它是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牺牲的。”[8]42卡德威尔表示他要“为它们脱帽致敬”[8]42,此时他将死亡誉为可歌可泣的、利他主义的献祭行为。然而,当父子俩在第四章中遭遇醉鬼时,醉鬼的诘问“你要找死吗?”[8]158一下子触动了父亲心里的意念,清醒过来的父亲谢过醉鬼,“你给我澄清了思路”[8]161,醉鬼疯癫的理智将父亲的思路带回现实,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为人父的角色和责任,他必须保护好彼得,将他培养成人。卡德威尔对死亡的最初体悟是一种利他的、英雄主义的行为,而现在,他认识到死亡是一种不光彩的逃避主义。表面上,他是一个追寻真理、得胜归来的英雄式人物,然而深究文本可以得知,他与任何一个凡人一样,都是无常命运的玩物。当听到克雷默老爹说到“时机和阿尔吞铁路不等人”[8]63时,卡德威尔反问道:“你想没想过有什么人等待时机呢?”[8]63简单的一答一问,折射出两人对人主观能动性的不同观点。然而,认为人类是“创世纪中(上帝)所做的最后一件好事”[8]54的父亲,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备受命运的嘲弄。首先,身为牧师的卡德威尔的父亲,教会了卡德威尔对人类的信仰,然而自己却丧失信仰而亡。其次,作为一位教自然科学的教师,卡德威尔清楚地知道基督教和科学对人类起源的相悖解说。再次,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卡德威尔阻力重重,生活艰辛,汽车抛锚、大雪封道、囊中羞涩的他,不再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之灵长,而是无奈地沦为命运的玩物。
除了追寻主角的反传统性,追寻行为本身也是反传统意义的,这表现在叙述视角的流动性、故事接受者的不确定性以及传统意义上追寻神话中激动人心情节的缺位。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马人》的叙事视角是流动而不确定的。第一章是第三人称视角叙述卡德威尔在学校里遭到学生的戏弄和校长的凌辱,第二章则转为彼得的第一人称叙事,第三章仍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时态却是用现在时。也许直到我们读到第八章的第一句,“我的爱,听着。”[8]266我们方才意识到,这是成年后的彼得将他对往事的回忆讲给爱人听。然而,那些从神话中马人客戎视角叙述的章节又该如何解释?明确而单一叙述者的缺位,暗示了整个文本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和模块化特征。与之相应的,我们唯一可以推知的被叙述者是成年后彼得的黑人情妇。这是一个难以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的扁平人物。当彼得回忆与父母共同生活的这段青少年时光时,他间或地会偏题,对他目前从事的“二流的抽象表现艺术”[8]81进行评论,然而,他的讲述从来没有得到听者的任何回应。这位听者的缄默使得我们无法得知她的所思所想。至于她的外貌,我们唯一能获得的信息是第八章中的寥寥数语,“你的呼吸与你的胸脯的缓慢起伏合拍。你那庄重的嘴在睡眠之中松弛了,上唇展现了那多出来的带有种族标志的一小块圆肉”[8]269。这段带有极浓主观情绪的叙述,更多的是彼得对女友梦呓般的赞美,而非客观的描绘。此外,就整个故事情节而言,它没有传统冒险故事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古罗马神话中奥德赛返家的故事,充满着惊心动魄的环节,英雄的奥德赛在归途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他矢志不渝,最终荣归故里。然而,《马人》中的卡德威尔和彼得的三日历险记,如同任何一个关于后现代小人物的故事一样,是极为平凡普通的。小说中的三天和两个主人公生命中任何一个三天都是一样的无聊沉闷。第一天选景在学校教室,卡德威尔遭到学生们的玩弄,然而作为教师的他却不敢声张,只得含羞忍辱。当天的第二节课对他来说是个噩梦般的经历。早就对他怀恨在心的校长前来听课,学生的不配合以及校长对他的成见让整个课堂一团糟。卡德威尔沮丧地回到家,自认为被解雇是迟早的事。接下来的两天见证了这一对父子从家到学校然后再返家的乏味旅程,他们自始至终囊中羞涩,意志薄弱,然而挑战却层出不穷,两人穷于应付,即便像搭乘路人这样的一桩小事,对他们来说都成了灾难——卡德威尔唯一的一双手套被偷。
综上所述,在叙事形式上,《马人》由两大泾渭分明的叙述体交叉构成,现实与神话的杂糅与共存,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模块化和开放性的特点。在主题关怀层面,《马人》既有神话的一面,又展示了人性的温情。首先,《马人》是一部描绘神或英雄历险传奇的神话。故事回溯传统,吸纳了古希腊神话的人物和情节原型。主题属于传统文学中的“追寻”母题。正如渔王神话中所描写的,病魔是促使英雄历险的诱发因素。父子两人饱受病痛的折磨,踏上寻求真理的道路,开启他们“沉沦、奋争、获救”的三日历险记。结尾处,冬的意象隐退,春的迹象来临,这暗示着神话中的一个轮回。与此同时,《马人》又是一部描绘人和人的故事的小说。在传统文学“追寻”模式下,文本多处对传统“追寻”母题进行戏仿。追寻主体卡德威尔自己就是个反英雄的现代小人物。其次,故事本身也有很多反传统的一面。为了传达人所处的“介于天国与尘世”这一边缘境地,厄普代克借用了罗曼司这一文学样式。正如游离于真实世界和神话世界、横亘于以人为本的小说和以神为本的神话中的传奇故事罗曼司,《马人》无论是在主题模式上,还是在叙述形式上,都堪称一部现代文本罗曼司。
参考文献:
[1] JOHN W. Aldridge“The Private Vice of John Updike”[M]//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 Chea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8(7): 4009.
[2] TANNER T. A Compromised Environment [M]//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hn Updike. New York: Chea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7: 51.
[3] DETWEILER R. John Updike [M].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4] BELL M 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ce: 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69.
[5] HAWTHORNE N.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M].Coloumbia: Ohio State UP, 1971.
[6] FRYE N. Anatomy of Criticism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7] CHASE R.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M].New York: Gordian Press, 1987: 19.
[8]约翰·厄普代克.马人[M],舒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9]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3.
责任编辑温优华
[10] FRYE N. The Secular Scripture [M].Cambridge: Har⁃vard, 1976: 122.
On the Thematic Mode and Narrative Patterns of The Centaur
QIN Dan-dan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Jiansu, 211169)
Abstract:In light of Northrop Frye’s theory on romance, the present thesis sets out to analyze the the⁃matic mode as well as the narrative patterns of John Updike’s The Centaur. True to the traditional quest motif, The Centaur demonstrates fidelity to God-centered myth by embodying Greek characters and plo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 parody of the quest myth. For its simultaneous treatment of both Gods in myth and men in novel, The Centaur is a typical American romance.
Key words:romance;The Centaur;quest motif;parody
作者简介:秦丹丹(1983-),女,安徽岳西人,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收稿日期:2015-09-09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6)01-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