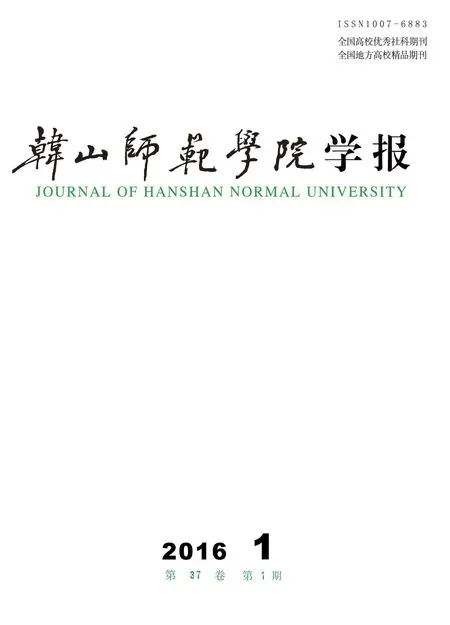环境史刍议
赵玉田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环境史刍议
赵玉田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环境史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表明当今历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反省与改革的方向选择及迫切性。在大历史视域下重构历史,注重环境与民生问题,是近十年来环境史“新史学”主要坐标。环境史要讲“自然的故事”,同时要讲“社会的故事”,要以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三者关系为依归。惟其如此,环境史才能成为真正的“环境”史。我国“环境史”有自创之实,在其研究旨趣与方法及任务等方面都应该有适合国情的独立的学术思考。
关键词:环境史;新史学;学术自信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成果斐然,它以全新的思想理论与技术方法引领史学创新及发展方向,渐成史学中显学,或将引发历史学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重新认识人的历史,重新建构历史。然而,毋庸讳言,迄今为止,有关环境史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问题尚未厘清,有些还存在明显分歧。
一、西方环境史:“救时史学”与“新史学”
一般认为,环境史研究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学开始被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1]检视西方环境史学发展轨迹,不难得出,它经历了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的发展过程。西方“环境史”首先是环境问题逼出来的历史,是西方史家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灾难而表述的一种学术诉求,也是救时举措。故而,本文称其为“救时史学”。
(一)环境危机与“救时史学”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建立起工业生产体系,煤炭与石油成为工业化主要能源。由于资本家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无视环境,工厂源源不断制造的有毒物质被肆意排放到土壤、空气、河流与地下水之中,污染惨剧接连发生。如美国纽约市曾在1963-1968年做过一项死亡率与大气污染关系调查,6年间该市每年约有1万人因大气污染而死亡,占该市总死亡人数的12%。[2]59大气污染成为民众的主要“杀手”之一,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对此“杀手”却“置若罔闻”。如美国在1969年向大气排放粉尘2830万吨,二氧化硫2500万吨,一氧化碳600万吨。[2]89在此前后,西方一些科技人员开始运用多学科知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与环境灾难关系,寻求化解环境危机良方。①如1962年,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令美国朝野上下难以“寂静”的警世科学名著——《寂静的春天》。该书首次向民众揭示了因滥用杀虫剂等农药造成的大量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案例及一个可能“死去”的世界。随之,媒体一再曝光美国石油泄漏与水污染及空气污染等问题,民众环保意识得到持续强化。其后,倡导资源保护的学术力作——斯图尔特·尤德尔著《静悄悄的危机》与塞缪尔·海斯著《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等面世,这些作品有效传播环保理念。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基本生存权,1970年4月22日,环境污染重灾区的美国,民众“首义”,约2000万美国民众发起环保运动,游行示威。与此同时,面对此起彼伏的生态灾难,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文学界亦掀起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传统价值观思潮,重新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其中,美国一些历史学者正视环境危机,在环保运动感召下,以救时为目的,撰写了一批旨在分析与应对环境危机的史学论著,西方“环境史”在美国首先冠名并发展起来。如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休斯称:“在公众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今天,环境史可以用来纠正传统史学的弊端。人们现在意识到,对地球生命系统越来越强的干预,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进理想世界,反而让人类深陷生存危机。环境史为应对这一危机或许能做点贡献,叙述何以形成当今这种状况的历史过程,阐释过去存在的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对一些重要历史遗留因素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这样的视角,可能就会因为受一些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诱惑,而造成决策失误。环境史有助于矫正当下解决环境问题过于简单的思维模式。”[3]概言之,西方环境史学在美国兴起阶段,以民生为视域,以救时为宗旨,以反思人与环境关系为重点,以解决环境问题为依归,故而,本文称其为“救时史学”。
(二)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史学发展迅速,并担负起国际史学革新者重任;近十年来,西方环境史学开启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的华丽转身,即以揭示人类与环境的复杂历史关系为主线,主张“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4]更加关注民生与现实问题,旨在重新建构历史,全面解读人的历史——这是包括欧美环境史学在内的全球性“努力”。如唐纳德·休斯所论:“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环境史家已注意到了当代这些问题。”[5]1-2国内著名环境史家王利华与梅雪芹对此亦有高论,王利华称:环境史“不仅开辟了新的史学领域,而且提出了新的历史思维,将形成新的历史知识体系”[6]。梅雪芹亦言:“环境史的根本宗旨,是要叙述一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也即人类家园变化的故事……可以说,环境史是现实关怀的历史。”[7]
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环境史学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环境问题检讨与反思,而是放眼人类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多维互动关系史,藉以重新认识人类自身与重构人的历史。凡此,环境史的救时功能并未减弱,而是增强了。史学界关于环境史“新史学”的定位及其实践,表明当今历史学重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反省与改革的发展取向及实践迫切性,环境史将成为历史学改革引擎。
二、“环境史”概念的思考
为回答“什么是环境史”?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休斯撰写一本专著——《什么是环境史》,论述极为深刻。不过,关于环境史概念,学界至今莫衷一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风趣地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转引自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其实,环境史的概念之争,本质上是环境史话语权之争。
(一)欧美“环境史”概念
欧美史学界关于环境史概念的界定,人言人殊。其中,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概念具有一定代表性。1994年,休斯在其所著《潘神的劳苦》一书中称:“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于历史学。”[8]2001年,休斯在其所著《世界环境史》中又指出:“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自古至今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以便解释影响这一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史将生态分析用作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9]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还指出:“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5]12013年,休斯又在《历史的环境维度》一文中对环境史的概念如是界定:“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evolution)”,而“作为一个领域,环境史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作为一种方法,它是指用生态分析理解人类历史。环境史家探讨地球上生物和非生物系统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种种方式,描述人类导致的环境变化,并评价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念”。[3]显然,唐纳德·休斯的“环境史概念”经历了一再“完善”的过程。除了休斯的环境史概念,西方环境史研究者亦多有界定者。如学者斯坦伯格认为:环境史是“探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塑造历史,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10]
要言之,休斯等西方环境史家主要从研究对象(即研究什么)、研究方法(即怎样研究)、研究任务及目的等四个方面界定环境史概念。笔者认为,“研究方法”不能说明环境史是什么,不能作为“环境史概念”的本质内容,也不应该以其限制处于发展阶段的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选择及创新;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的概括,则对认识“环境史”有一定指向意义。不过,唐纳德·休斯等学者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这一基本判断有待商榷,因为环境史研究二者之间“关系”不是目的,而是重新认识人的历史的手段与方法,以为现实社会借鉴。进而言之,时下,欧美环境史研究(包括概念界定)还逡巡于“救时史学”基本思维模式而向“新史学”艰难探索之中。
(二)“中国版”环境史概念
受欧美学者的“环境史”概念影响,西方环境史初来,国内学者多认同“欧美版”环境史概念。其实,欧美环境史肇端于西方环境灾难频发之际,为应对环境问题而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主要视域与研究内容。无疑,环境危机话语下的欧美“环境史”,只是一时的局部的“环境史”,不是全部的“环境史”;只是某国的“环境史”,不是它国的“环境史”。欧美一些环境史学者,未能客观理性地认识与检讨环保主义者的思维模式及其情感倾向,且以此“认同”裁量“环境史”。这种研究价值取向及思维范式,使西方环境史学陷入环保思维“窠臼”而难以自拔,故而缺少理性的学科建设。环境史是一门快速发展的新史学,是一种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环境、认识人类的相对客观的全新史学。欧美“环境史”对我国环境史研究或有裨益,但是不应成为中国环境史的“金科玉律”。
界定“环境史概念”的前提是弄清环境史的“环境”内涵。“环境”并非“生态环境”简称,“环境”应是与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总和性关系。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1]人类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环境史的“环境”应该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环境,包括生态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如果像西方学者那样仅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研究环境史,未免狭隘而有失偏颇,也不是真正的“环境史”。王先明认为:“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在历史进程中始终是同一的,而不是分离的。因此,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12]钞晓鸿也提出:“环境史中的环境一般是指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所处的环境,既包括社会,也包括自然并重视自然,但当需要探讨其中的自然环境变迁时,又以人类为环境因子之一。”[13]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不应陷于环保运动思维模式及其语境而顾此失彼,应该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创建一个体系开放的全新的环境史学。概言之,环境史要讲“自然的故事”,同时还要讲“社会的故事”,要以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三者复杂的历史关系为手段与途径,以重新认识与建构人类历史为依归。惟其如此,“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完整的历史,环境史才能成为真正的“环境”史。
三、环境史学发生的“名”与“实”
近几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生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坚持“舶来说”,有人主张“自创说”。中国环境史学是“舶来”还是自创?实则涉及环境史学发生的“名”与“实”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环境史之“实”早已有之,属于自创;中国环境史之“名”则来自欧美,属于“舶来”。
(一)美国环境史学:“名”为自创,“实”为舶来
美国环境史家唐纳德·休斯强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特分支,环境史是在美国得以冠名并首先组织起来的……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否认环境史的许多主题在欧洲史学家的著作中已经出现。”[5]36-37其实,休斯此言欠妥。
环境史学在美国首先得以冠名,这是事实。然而,“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则肇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国年鉴学派。早在1922年,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撰写了《大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费弗尔在该书中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联,实则开启“环境史”研究。其后,马克·布洛赫(1886-1944年)所著《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则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自然环境,亦表现明确的环境史旨趣。1949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年)出版了史学名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则论述了“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14]是著对地理空间、环境在地中海地区历史演变中的重要性予以认可及论证。其后,以杜拉里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在环境史研究方面贡献颇多,如其所著《丰年,饥年》(1967年)侧重于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影响的研究,而其所撰《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973年)及《危机与历史学家》(1976年)等史学论文,对14世纪以降瘟疫在欧洲和美洲横行及其引起的生态和人口危机的历史事实进行专题研究。另则,年鉴学派在《年鉴》杂志1974年的《历史与环境》专刊中,深入探讨了涉及气候、瘟疫、地震、灌溉等方面的“环境史”。笔者认为,正如马被命名为“马”之前也是“马”的道理一样,“环境史”冠名之前,年鉴学派有关环境史内容的历史研究当然属于“环境史”。就年鉴学派的研究内容而言,“年鉴学派”亦可称之为“环境史学派”。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指出:“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15]其实,唐纳德·休斯在论述“年鉴学派”的研究旨趣时亦言:“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法国的一群史学家,与其它地方的同行们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细致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作为拓展史学视野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强调了地理环境的重要性;除了对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产生广泛的影响外,他们还提供了有助于环境史的推动力。”[5]29既然如此,年鉴学派所为,亦是“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进而言之,这种“历史努力”首先在法国出现,而非发生于美国。
(二)中国环境史学:有实无名与名实俱备
中国“环境史”是不是舶来?这不仅是学术自信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历史与地理学者已就“环境史”相关问题展开研究,虽未冠以“环境史”之名,亦属“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如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了《殷人服象之南迁》;同年,蒙文通在《史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另,陈高庸于1940年出版了探讨气候变迁与历代社会动乱关系的著作《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再如,20世纪60年代,丁骕在《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发表论文《华北地形与商周的历史》、杨予六在《史学通讯》发表《地理环境对历史之影响》,等等。这些研究无疑都属于“环境史”,都是环境史成果。如环境史学家王利华先生所论:“中国环境史研究从思想方法、问题意识、目标指向等方面来说,均非完全舶来之物,而是拥有自身学术基础和社会条件的。……在西方环境史学传入之前,中国历史地理学、农林史、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已展开了不少相关研究。”[1]概言之,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环境史”舶来之前,我国学者本着经世目的与学术自觉,对“环境史”相关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是时,虽无“环境史”之名,却有环境史之实。
最近几年,“西方环境史”著作被陆续译介到国内,颇受学界推崇。其实,中国环境史家不应“妄自菲薄”而重复“邯郸学步”故事。善于向西方同行学习很重要,加强学术自信而勇于理论创新更为重要。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环境史学是一个开放的综合性的学科体系,而且处于学科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博采诸家之长。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发生文明中断的古老的文献大国、农业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与人口众多,历史内涵宏富,不同时空下的“环境”各有不同。凡此,要求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实事求是,积极开展理论与方法探索,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而不应以“欧美版”为畛域而自缚。惟其如此,才能写出真正的“中国的”环境史。
参考文献:
[1]王利华.中国环境史的发展前景和当前任务[N].人民日报,2012-10-11(023).
[2]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外公害概况[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唐纳德·休斯.历史的环境维度[J].历史研究,2013 (3):12-19.
[4]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J].南开学报,2006(2):2-13.
[5]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J].历史研究,2010 (1):10-14.
[7]梅雪芹.环境史叙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7.
[8] J DONALD HUGHES.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Creeks and Roman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3.
[9] J DONALD HUGHE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M].London: Routledge, 2001: 4.
[10] TED STEINBERG.Down to Earth: Nature,Agency,and Power in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2002 (107): 35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12]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J].历史研究,2010(1):24-29.
[13]钞晓鸿.深化环境史研究刍议[J].历史研究,2013 (3):4-12.
[14]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
责任编辑黄部兵
[15]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2003,42(4):14.
Issue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ZHAO Yu-t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Abstract: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 new historiography,which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and the urgency of the current history in the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y reconstruc⁃tion,the study of“New History”has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 and livelihood issues over the past decade. Environmental History tells stories of nature as well as stories of the society,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ac⁃quired initiative results in the study of purpose, method and mission, giving independent academic thinking ori⁃en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New Historiography;academic self-confidence
作者简介:赵玉田(1968-),男,吉林通榆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YJA770071)。
收稿日期:2015-05-25
中图分类号:K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883(2016)01-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