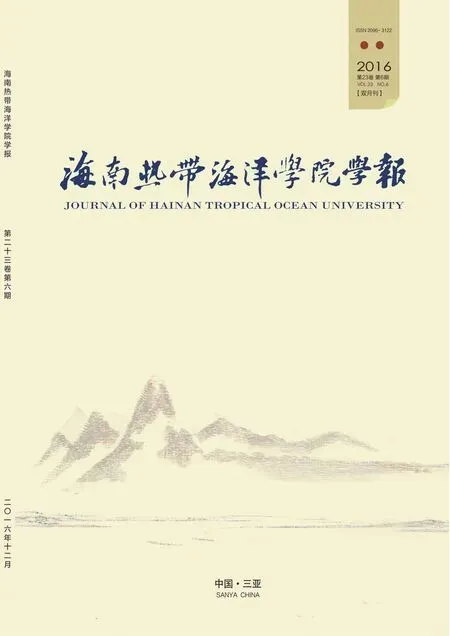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蒿 帆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心雕龙》研究
蒿 帆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其蕴含的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文学、美学、逻辑学内涵根植于中国文学悠久的历史土壤中。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对话论、阅读论、意义论、空白论)为整体参照系,具体运用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等理论要点,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将西方现代阐释学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探析有关《文心雕龙》研究走过的足迹,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有益实践,为《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开启了新的视阈。
《文心雕龙》;视域融合;效果历史;阐释范式
对《文心雕龙》阐释史的梳理,就是以文学阐释学的相关理论对一部古典文论的研究史进行再阐释。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阐释者的前理解,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有、先见和先把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讲究不是对某个现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1]8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前理解或先见是历史赋予阐释者的,是促使阐释者的积极因素,它的意义就是为阐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这种视域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孤立的,它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如果一个阐释者不能将自己置于这种历时与共时的视域中,那他将无法真正理解传承物的意义。所以,阐释者的任务就是去努力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1]9梳理《文心雕龙的》阐释史,就是以不同的阐释范式进行视域融合进而形成《文心雕龙》研究的独特效果历史。
一、《文心雕龙》研究史的现代阐释
(一)对话论
巴赫金将“对话”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在西方阐释学的文学接受理论中,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开启了阐释对象的转移,阐释不再只局限于文本之内,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文本间的关系成为对话的功能意义与阐释焦点。在对《文心雕龙》这种经典文论的诠释过程中必然存在着阐释者的前理解,阐释者这固有的“先见”依赖于以往历朝历代阐释者的视域融合。《文心雕龙》的阐释史表明“视域融合”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从隋唐至宋代,元、明时期到清代,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从新时期到当代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是视域融合在历时性上的体现。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学者在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对话和交流就体现着共时性的融合。大陆与港、台地区,中国与美、日国等不同国家关于《文心雕龙》的学术交流就毫无悬念地进入共时性融合的轨道中。“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这样,我们就达到了伽达默尔所谓‘效果历史’这一诠释学核心概念了。”[1]9效果历史,可以简单理解为与作品相关的所有阶段性研究成果都会对今后的研究产生影响,就如历史的发展必然产生现实的作用。我们将这种影响称之为“效果”,这种“效果”自身就是自我发展历史的全部要义。这种对作品产生影响的探究是由传统的过去面向当今的未来的,它并不把过去囿于某一特定的彼时彼刻,也不把现在视为不能再前进的此时此刻,它让传统向当今诉说,由一个时期的阐释者向另一个时期的阐释者开放,也就是向每一个阐释者话语的开放。伽达默尔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依赖于这种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真正的交流。“谁想听取什么,谁就彻底是开放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彼此的开放性,就不能有真正的人类联系。彼此相互隶属的同时意指彼此能够相互听取。”[2]58这种阐释者之间的“相互听取”并不是毫无主见的一味附和,这只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一种尊重和承认,即接受他人的意见与我相左。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事物一旦存在,就必然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阐释,都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例如关于《文心雕龙》整体性系统性的阐释路线就体现出这种开放式的对话、交流的效果历史意识。
(二)阅读论与意义论
我们这里借用金元浦对文学阅读论的陈述:“在我看来,阅读正是文学本质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本质即在过程中,过程彰显了本质。”[2]157以此来说明阐释《文心雕龙》的方法和意义。学者们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阐释无一不是建立在对《文心雕龙》仔细研读的基础上。在阅读的过程中,过程作为本质,体现着《文心雕龙》阐释的意义。从最早期的史学家对于《文心雕龙》的著录和评论、作家文人的征引和评论、文学家的序跋和品评到近三十年来“龙学”学者对其进行的整体化、系统性研究中,这些学者作为阅读主体,通过解释和理解《文心雕龙》去“占有”意义,占有《文心雕龙》体现出的美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意义。实现对于这部作品意义和影响的全方位把握。巴尔特认为阅读即是一种写作,而读者必须进行创作。正如“龙学”学者在阐释研究中寻找新的视点和方法,使文心雕龙研究史不断蔓延出新的光晕。这种阐释之再阐释就是一种创造,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实践。当然,这种实践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范式,即强调文学本质的共性、同一性及社会品格的批评范式。在强调共性的同时,也注重《文心雕龙》作品本身的特殊性、个性及本文特征。这种阐释方式体现着阐释学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体现着意义在“本文—读者”间的意义生成。
(三)空白论
“从人类学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意义的未定性与空白是联结艺术形式与审美感觉的中介,是审美创造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是导致审美体验、审美实践的内在动因,它在文本与感知者(接受者)之间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2]406换句话说,《文心雕龙》这部作品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会在一定时代一定个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空白”,而正是这些“空白”推动了人们参与的能动性和创新的自觉性。受历史、文化、地域、传统的限制,学者的研究和阐释总是存在着可发展性以及可改革性,这些恰恰是《文心雕龙》阐释史中可“填空”的地方,它表征着本文与阐释者相互作用的无穷建构,在这种建构下,《文心雕龙》将有更多可待发掘和阐释的地方。
二、梳理不同时代的《文心雕龙》研究
(一)隋唐至宋代的《文心雕龙》研究
“著名‘龙学’研究家王更生,对隋、唐时期《文心雕龙》研究状况,作了如下评述:隋唐去刘勰《文心雕龙》问世的时间不远,加以在内容思想,语言文字方面,彼此间的隔阂不大;而刘勰论文又只不过是当时‘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中的一份子,他本人既乏突出的家庭背景,又无不凡的生平事迹,衡情度理,一般人很难取其书作专门性的研究。”[3]44张文勋先生指出,在隋、唐时期直接谈到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多半是史学家,有的是为之写传,有的是著录书目。在史书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得到了肯定。“姚思廉撰的《梁书》和李延寿撰的《南史》,都有《刘勰传》……两传都介绍了刘勰的身世和经历,而特别突出了他的学术成就:一是写作《文心雕龙》,二是说他‘长于佛理’。可以说这是对刘勰及其著作的最早研究和评论。”[3]45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更是摹仿《文心雕龙》的体例写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本史论专著——《史通》,文风亦多似刘勰文风。张文勋先生分析了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后,他认为空海对《文心雕龙》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吸收了其中不少理论资料,并将其介绍到了日本。由此实现了跨地域的传播和交流,实现了中日学者间以不同视点的碰撞所达到的视域融合。
到了宋代,在理论领域,诗论、词论占据大壁江山,又因袭古文运动的传统,倡古反骈,《文心雕龙》的地位就不可能被看重,所以即使常常引用其理论观点,也很少公开肯定和提及。杨明照先生谈到自己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附录中对于《文心雕龙》原文的选录和引用,以及对其观点的沿袭和借用时讲到:“舍人《文心》翰苑要籍。采摭之者,莫不各取所需;多则连篇累牍,少亦寻章摘句。其奉为文论宗海,艺圃琳琅,历代诗文评中,未能或之先也。”[3]55影响的广泛和深远没有使《文心雕龙》获得文学理论史上的显著地位。《文心雕龙》甚至没有宋本,而著目则是散见于各种书籍。这种在隐性上影响之大,显性上无人标榜的尴尬局面的形成,是源于历史、文化上重政教、提倡儒家圣贤之道的限制。唐宋古文运动轻视六朝文风,而《文心雕龙》本身就是用骈体文写成的,自然被认为是六朝文风的产物。所以即使是文坛广受其影响,但它的历史地位还是不愿被抬高,反而被遮蔽了,这就是时代的选择。
《文心雕龙》研究史的开端,是以作者中心论和作品中心论为阐释范式的研究。虽然不够十分详尽,但学者们考量了《文心雕龙》与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种族、地域的关系;同时通过传记介绍了作者的生平、思想、个人经历等创作背景和创作活动。这种阐释虽然没有具体深入到强调探寻作者原意的层面,但在关注作者个人方面可以称得上周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提倡的作者中心论的表现。宋代注释家或诗论家引证《文心雕龙》者虽大有人在,但他们主要是把它作为一部文章写作的工具书而被引用的。他们不关心《文心雕龙》的作者是谁,不关心刘勰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理论,他们关注的只是《文心雕龙》这部作品的本身,摹仿这部作品的修辞手法、文本结构以及引用它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将作品作为独立本体,以作品的结构和语义为主要对象的阐释范式:本文中心论。
(二)元、明、清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
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处于大变革时期,社会文化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艺发展突破了诗词的局限,小说、戏曲、民间文学兴起并蓬勃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中新儒学的发展促使社会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发生极大变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作品,在众多流派的审美观念下被各取所需。元代的刻本和序、跋,明代的多种刻本、钞本、评点本中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强调主体意识的主导作用,所以重视刘勰文章中的性灵和体性,注重作家才性与艺术风格和境界的影响。清代盛行考据风气之下的征引、考证、序跋以及代表性的黄注和纪评将注意力转移到考证和校注的工作,所以阐释者关注文本本身,对文本的字义阐释较为重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杨慎的批点本,杨慎的批点方法将作者中心论与本文中心论推向了注重读者本身理解与阐释,以读者的理解为意义产生根源的范式之下,读者中心论初见端倪。“杨慎的批点本在明代颇有影响,起到宣传的作用……其彩笔圈点能起到在精彩之处和重要的地方唤起读者注意的作用。这就是他自己说的‘不必说破’,让个人自己去领会。”[3]77杨慎作为《文心雕龙》的研究者,以“圈点”作品的方式将《文心雕龙》以近乎素颜的状态呈现在其他读者面前,激发其理解阐释的意愿,起到引导的效果。张隆溪先生讲到:“艺术作品不仅有意义并呼唤读者去对之作出解释,而且其意义从未得到过决定性的解释和穷尽——人们可以把艺术的语言意译为另外的话语,却不能由此而穷尽其丰富的内涵。”[4]《文心雕龙》的艺术价值时刻呼唤着读者去对其做出阐释,读者才是《文心雕龙》意义阐发和价值挖掘的动力。
(三)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心雕龙》研究
民国时期是“龙学”形成的准备期,新中国成立后“龙学”迎来勃兴期。在民国时期,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把《文心雕龙》放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中评价,不再是孤立地研究,而是在和前人的比较中突出它在汉魏以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中的最高地位和广泛深刻的影响。罗根泽的《中国文学品批评史》同样注重比较研究,他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谈到了刘勰以前的批评家,在比较研究中充分肯定了刘勰的伟大和成功。这种比较研究范式虽然没有突破空间,但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为不同阐释视点的融合提供了全新的平台。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特别注意到刘勰的文学理论与佛学的关系”[3]118,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侧重点,轻“文体”重“原理”,黄侃始创了对于《文心雕龙》的分篇研究。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根据纪昀‘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名其本然’之说,把刘勰的理论作了系统的整体考察,明确树立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观念”[3]111。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是一篇研究提纲式的文章,同样体现了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观念。这种由部分到整体,由各要素到系统整体的阐释路线,体现了《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解释学循环。为了理解刘勰这整部作品的意义,则必须理解其部分篇章的意思,为了理解刘勰的整个理论体系,则必须理解刘勰的思想体系。反之亦然。在理解《文心雕龙》展现出的各要素的同时,又有必要对其整体理论有所思考。在这种解释循环之下,对文本的理解将大有裨益。“海德格尔则是这样来描述循环的: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的。在完满的理解中,整体和部分的循环不是被消除,而是相反地得到最真正的体现。”[1]415伽达默尔肯定了这种循环的本体性原则:“这样,这种循环在本质上就不是形式的,它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而是把理解活动描述为传承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1]415不仅是在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而且在哲学阐释学的观点中,人类在认识自己、探索意义的实践行为里,循环都是使其成为可能的一种条件和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整套文艺理论,这股马克思主义的浪潮在文艺界尤为猛烈,所以,研究者们都追求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去阐释《文心雕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10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在此指导下,研究首先关注刘勰的世界观是“唯物”还是“唯心”。郭绍虞、张启成等学者在《文学遗产》上展开了关于刘勰的世界观的讨论。经过一番激烈的商榷,学者们达成了一点共识“刘勰世界观中的唯物唯心的成分是交织的”[3]152。这有利于破除抽象的唯物论或唯心论,对刘勰的文论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来评价作家和作品,实际上是把文学视为社会历史和审美的辩证统一。“恩格斯从结构、情节、韵律、格言等方面,提出美学要求。”[5]13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阐释者展开了关于《文心雕龙》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讨论。刘绶松认为《文心雕龙》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宣扬了现实主义的进步文学思想,反对和驳斥了盛行于当时的颓废主义奢靡文风和唯美主义文学倾向。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文心雕龙》注重文体论,提倡“风骨”“情采”“丽辞”对于文章创作的意义,走向了形式主义的偏向,由此又引发了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价值取向是反映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趋势;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透过《文心雕龙》,我们能重新体验刘勰所生活时代的社会变革并审视现代社会转型下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龙学”勃兴之际,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价值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阐释,身在骈文盛行,骄奢浮糜的社会风气之下,刘勰却能乱中求定,写出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学理论,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提出的艺术生产的发展同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三、社会转型大环境下《文心雕龙》研究的未来走向
刘勰的《文心雕龙》经过一千多年的积淀,其文学理论得到了史学界、文学界、语言学界等各领域专家学者的积极阐释,其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进入新时期,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对于《文心雕龙》新的阐释应该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更广大受众。文论阐释该如何面向现代、面向世界?巴赫金的“对话语义”在这种文化转型之下对阐释学的发展就具有了特殊意义。沟通、对话和交流已成为社会交往的主题,文艺理论的阐释亦是如此。金元浦先生说到:“在当代哲学阐释学各学派及其他这种哲学理论的倡导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开始注意将自己先前孤立自在的学科置于人类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更为宏大的架构之中。”[2]62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及学术活动的开展实现了“龙学”在国内得到大范围的普及。《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是加快了“龙学”走向世界的脚步,实现了更为广阔的视域融合。日本、瑞典、俄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分享了自己国家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其中意大利学者珊德拉用意大利文对《文心雕龙》进行了翻译。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代表了《文心雕龙》英译的杰出成就。台湾“龙学”专家王更生先生对台湾“龙学”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展望,讲述了由艰辛起步到辉煌发展的“龙学”阐释。香港“龙学”的代表人物黄维樑将“龙学”的研究推向了现代文学阐释理论的视点之下。“黄氏的研究有两大特色:一是中西文学理论比较他把《文心》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及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作比较……和西方近代的读者反应说、解构主义、原型论等等也作了比较研究……黄氏研究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力图做到古为今用,使《文心》的理论为现在所用。”[3]257
正是因为《文心雕龙》中语言意义的开放性,使《文心雕龙》阐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文心雕龙》的研究要面向广大群众,就不得不走向阐释的多元化,以广大读者为中心,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更大范围和更好效果的传播,仅在大学课堂针对特殊受众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以周振甫、陆侃如、牟世金为代表的学者对《文心雕龙》做了今注今译,他们把骈体文翻译成白话文,帮助读者打破了阅读的障碍,提升了普通受众对刘勰文学理论的接受程度。
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仅给当代文学批评和鉴赏提供理论依据,对文学创作方法提供丰富素材,也为现代中学语文教育提供“通变”思路。以中语纪实文学的美学表达方式为例,“描写能够把作家头脑中的意象、浮雕为可感的语言意象”[6],刘勰论《夸饰》、谈《比兴》、讲《丽辞》、述《情采》,无不处处彰显刘勰自己崇尚“有韵之文”的美学心理与注重“文质彬彬”的创作要义。“描写”在刘勰的灵活运用下大放异彩,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手法影响颇深。
“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时不仅要理解西方文明,而且要努力消除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从而缩小认知差异,彼此理解认同。”[7]正如对于文化形象的认知需要消除误解一样,对于中西方文化交流而言,不必一味“西为中用”,迫使文学研究变成了“拿来主义”。我们是有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们不必生搬西方套路,我们自有《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西方现代阐释学源于西方哲学,中国阐释学发展源于中国古代诗学阐释学,只有将二者相互审视,积极融合,才能迸发新的异彩。即成就了阐释《文心雕龙》的效果历史,也促进了其视域融合。
所有这些以不同目的、不同视点、不同范式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不断形成新的效果历史,而这种效果历史正是新的理解得以发生的媒介。处于社会转型新时期的研究者将在这种“媒介”的帮助下,在中西比较诗学视野下以西方现代文学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绘制《文心雕龙》的阐释路线图,作出有益于《文心雕龙》研究发展走向的探索。这种文学实践对发掘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的精髓来说是积极的尝试,对于引导文学阐释在方法上灵活通变同样意义非凡。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金元浦.文学阐释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张文勋.文心雕龙研究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4]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42.
[5]陆贵山,周忠厚,编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姜岚.叙事与描写:中语纪实文学的美学表现[J].琼州学院学报,2014(6):65-70.
[7]朱珺,李旋.文化隐喻视角下中国龙和西方Dragon的比较[J].琼州学院学报,2015(1):111-117.
(编校:李一鸣)
Study ofWenXinDiaoLongunder the Hermeneutics Perspective
HAO Fan
(Faculty of Arts,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China)
WenXinDiaoLongas a “large and diverse”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masterwork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and profound literature, aesthetics, logic connotation which are roo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hermeneutics theory (dialogue theory, reading theory, meaning theory, blank theory) as the reference system, using fusion of horizon, effect history,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and other theoretical points, drawing the route to explainWenXinDiaoLong, comparing the thoughts of modern western hermeneutic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analyzing the study direction of theWenXinDiaoLongin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evel, are the beneficial practice for exploring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also stimulate the study of this masterwork.
WenXinDiaoLong; fusion of horizon; effect history;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2016-06-10
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SLGYCX1604)
蒿帆(1991-),女,河南南阳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阐释学和《文心雕龙》研究。
I206
A
2096-3122(2016)06-0064-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11
——关于海德格尔的“那托普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