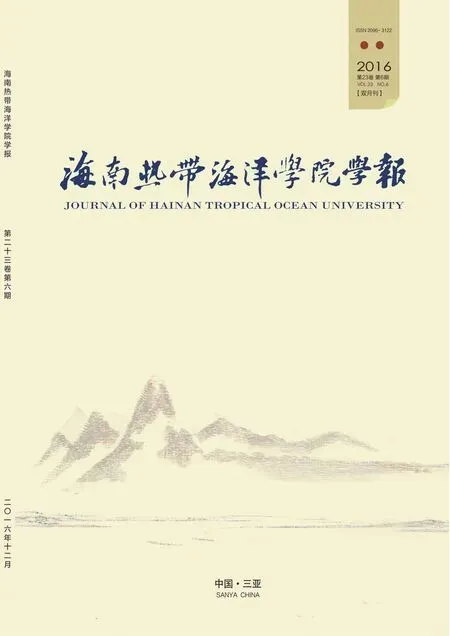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
——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严振南,王晶晶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先秦两汉天道神学观的嬗变
——兼谈汉乐府郊庙歌辞的精神转变
严振南,王晶晶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6)
德和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中国祭祀文化的核心。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天(上帝)和君主建立了以“德”为媒介的契约关系,君主受到上帝的监管,尊天重德。两汉时期,汉武帝将“太一”神与阴阳五行理论融合,将敬天演变为娱神,重视神仙方术,慕仙追仙游仙,天(上帝)独尊地位逐渐被消解。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郊祀歌辞发生了重大变化:天的崇高地位消失,人的欲望不断加强,引起了以《郊祀歌》为主的祭祀文学出现世俗化、娱乐化倾向。人与天的关系发生改变,这也是雅文学向俗文学的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德;天道;追仙;汉郊庙歌辞;雅俗
祭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背后有着一套完整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祭祀仪式和礼乐制度,衍生出成熟的祭祀文学作品。祭祀文学多以仪式乐歌的形式呈现,主要收录在郭茂倩《乐府诗集》郊庙歌辞中。
祭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祀天地,其祭祀指向的是上帝;二是祭宗庙,其祭祀指向的是祖先。《中庸》载:“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1]自商周以来,祭祀一直是国家重要的宗教活动,同时也是严肃的政治活动。商周时期,“上帝”是“天”的具象化,是天道神学观的核心;“上帝”是即天,是至上神,它是原始先民对“天”崇拜的产物。随着国家的建立和君权的不断强化,祭祀至上神“天”成为君主专属的权力,以此形成了严格的祭祀制度。
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一朝,商周以来形成的天道神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太一”神与阴阳五行说融合,天(上帝)的独尊逐渐被“太一”取代。在这一天道神学思想下,祭祀文学呈现出游仙、慕仙、追仙的特征,民间鼓舞乐、郑卫新声被引入庄重的郊祀乐章中,以《诗经》“大雅”为核心的郊祀雅文学逐渐世俗化,汉《郊祀歌》开始成为君权私欲的载体。在成仙思想与君权永久独享思想交织下,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神仙方术思想在汉代盛行一时。
这一文学思想的变化,其核心是天道神学观的变化,即天的独尊地位的消失和君王私欲膨胀的开始。“人”从“天”的监管中挣脱出来,以“天”为核心的天道神学观最终沦为以“君”为核心的皇权观的附庸。人与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君权从对天的敬畏转向与天同寿,君权失去了“天”的监管,失去了“德”制约。这正是商周与两汉时期,天道神学思想的本质区别。郊祀文学最能直接体现这一变化,郊祀乐章主要用于君主郊祀天地和祖先的活动中,因此最能体现君主的思想和治世态度。
一、商周时期以“天”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与宗法伦理观体系
君主通过祭祀,将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所作出的“德”向天和祖先陈述。天,是虚的、无形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时刻监视君主的行为。君主是天之子,代替天治理国家。天和君主建立这一关系的条件是“德”。“德”是天与君主之间契约关系维系的核心,即人唯一能成为天之子的凭借是“德”。天和君主存在“德”这一契约关系,天只认同有德行的君主,“皇天无亲,唯德是辅”[2]334。“德”是君主沟通天(上帝)的凭借和依据,即“德以配天”,唯有敬德行事,方能得到天(上帝)的托付。天(上帝)不仅具有选择君王的权力,同时还有监视君王行为的责任,天在最高位通过体察万民生存状态,以评判君主的行为,“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3]777。君主治理国家需将天的指示作为最高依据,将德作为一切行动的本源,行德以惠及子民,敬天配德保民。
“德”作为天和君主契约关系的核心,其本质内涵是生民和保民。君主只有行“德”以配天,使部族子民生活丰盈,安于生产,繁衍生息,“好生之德,洽于民心”[2]30,只有这样,天才会降福祉于君主,君主方能得到子民拥戴,继承祖先的德业。
周部族认为,其始祖后稷是感天而生,为“上帝”之子,代天行事,治理国家。在周部族的意识里,后稷与天是紧紧连在一起,是天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周公成为君主后,通过郊祀后稷达到祭天的目的,以宗祀文王于明堂达到祭祖的目的,即“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4]1357。祭祖的最终目的是要配天,郊祀后稷体现出天道神学观上的“德”,祭祀文王体现了宗法伦理上的“孝”,“德”和“孝”又统一于天。因此,郊祀天地和祭祀宗庙成为周朝时期最重要的部族大典,是周部族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的集中体现,“德”和“孝”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
德的对应目标是天,孝的对应目标是祖。“天”与“祖”辩证存在。首先,“天”与“祖”是存在区别的。古老先民的神学观念中包括“天神”和“祖宗神”,在二元的神学信仰中逐步确立了以“德”为核心的天道观和和以“孝”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形成了“德孝”并重的神学观念,即“有孝有德”[3]834。其次,“祖”最终又归于“天”。在商周时期,以“德”为核心的天道观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逐渐融合。伦理层面的宗“孝”最终要归于天道观层面的敬“天”,天道观层面上的敬天又是伦理观层面的宗孝。天道观中的“德”与伦理观上的“孝”最终统一于天,天与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3]746。最后,“德”和“孝”又贯穿于治理国家政治活动中。因此,在商周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德”和“孝”为中心的天道观和伦理观,“德以配天,孝以配祖”是先民天道神学观、宗法伦理观以及君主政治观的统一。
二、两汉时期以“太一”神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体系
商周时期,在天道神学观、宗法伦理观和君主政治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神学体系。以“德”为中心的天道神学观是三者共存的基础,以“天”为核心的天道神学观处在独尊地位,是宗法伦理观和君主政治观的归宿。汉代天道神学观中具有了强烈的帝王意志,汉武帝独尊“太一”为最高神,商周以来至上神“天”(上帝)的地位逐渐被取代。随着“天”独尊地位的消失,天道神学观也失去了至高地位,开始为皇权服务,成为君王独尊的工具,天道神学观成为政治君权独尊的手段。伴随着天道神学观地位的消失,君主对天的态度也由敬畏天演化为娱乐仙,神仙方术开始在汉代流行起来。
汉武帝时期,信奉方术尤为盛行,汉武帝启用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四位方士炼丹求仙,以祈长生,“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4]1384。李少君以炼丹著称而为汉武帝尊崇。汉武帝欲通过延年益寿之术与蓬莱神仙相见,为祈得不死,遵循方士之言,派方士到蓬莱寻找仙人,行泰山封禅大礼,欲通过封禅与仙人相见而长生不死,“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4]1385。少翁以祭祀鬼神之术而得汉武帝重用,为实现汉武帝与神相通的愿望,又造甘泉宫,“置祭具以致天神”[4]1388;栾大、公孙卿皆以能与神仙往来而为汉武帝重用。各路方士迎合了汉武帝求仙心理,通过炼制长生丹药、鬼神之术、祭祀拜天之事而得到汉武帝重用,祭祀与神仙方术结合,推动了汉代宗教神学观的发展。商周时期“天”的独尊地位逐渐被取代,汉武帝独尊“太一”神,建甘泉宫,立“太一”神祠,五帝佐之,强化了君主的集权统一和独尊地位,“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4]1386
“太一”神取代至上神“天”,将最高的神形象具形化,这便消解了人们对无形的、抽象的至上神“天”敬畏。建甘泉宫、立“太一”祠,将“太一”供于宫室之中,神权独享,神权为君权役使,强化了君权私有化、独尊化的意识。商周以来形成的“天道靡常,惟德是依”,敬天、敬德的天道神学观被君权独尊的意识取代,“天”的地位消失,“君主”成为中心。
这一天道神学观的转变强化了“君权神授”思想,强调天命,且天命不可违,弱化了君王需要有“德”行才能配得天的授权意识。商周时期,天与君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德”,天与君之间以“德”为媒介进行双线互动的结构。两汉时期,这一关系刻意强调天的选择不可逆转,弱化了君需对天负责的意识,从而消解了君也要通过“德”来对天负责的契约关系。汉武帝尊神、祭神、追神,欲通过泰山封禅与神仙相见,获得长生,永享帝王之君位,敬神的目的非为敬天、敬德,而是为了永生成仙。
三、汉《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对商周郊祀雅文学的背离
郊祀天地,是天道神学观的直接体现,祭祀宗庙,是宗法伦理观的直接体现。德对应上天,孝对应祖先。天与君主,以郊祀的形式进行沟通,“德”是二者沟通的条件,“礼”是沟通的方式。郊祀之“礼”主要包括祭祀中的歌、乐、舞。宗庙祭祀的兴盛推动了祭祀音乐的发展,天道神学观通过宗庙祭祀的形式呈现,而宗庙祭祀又以祭祀乐、歌和舞为中心。
汉乐府郊庙歌辞主要以《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为主,沈德潜《古诗源》称:“《郊庙歌》近颂,《房中歌》近雅。奥中带和平之音,不肤不庸,有典有则,是西京极大文字。”[5]《安世房中歌》共十七章,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七言,格调高古,义理精深。全章以“德”和“孝”为中心,歌祖宗神灵,向祖先陈述自己的文治武功。其中第一、二章为迎神乐章;第三章至第八章,乃君王入庙门后,对君王歌颂;第九章至十一章为君王的祷词;第十二章为神灵享用完毕祭品;第十三章至十七章,赞美神灵飨食完毕后,赐福与君王和下民。《安世房中歌》在祭祀的不同的阶段演奏,迎神用《永嘉》,皇帝进庙用《永至》,颂神奏《登歌》,飨神《修成》,礼毕用《永安》。《安世房中歌》依据祭祀流程,大致可分为迎、颂、祷、飨神几个部分。
《郊祀歌》是郊祀天地的乐章,始于汉武帝时期,由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协助而成,《汉书·礼乐志》载:“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6]1045
传统祭祀歌多是客观的,非个体主观化的意愿。王红杏和木斋先生在《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一文认为:即使以浪漫抒情著称的屈原,在创作祭祀歌时,都严格遵守祭祀歌舞辞的标准,其祭神歌《九歌》与《离骚》《抽思》《惜诵》《天问》具有明显差异。[7]35汉乐府《郊祀歌》表面看是在歌咏至上神“太一”,实则是汉武帝求仙意愿的体现。汉武帝得神马,作《太一之歌》,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4]1178后伐大宛又得千里马,复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1178当时任中尉的汲黯不满于此事,故向汉武帝谏言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於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4]1178帝王作乐,以乐向祖先陈述文治武功之德业。汲黯认为武帝将颂马之乐写入祭祀天地、宗庙的乐章之中,违背“肃雍和鸣,先祖是听”[3]961郊祀乐的宗旨。郑玄认为郊祀之乐需和且敬,如他在《诗经·周颂·有瞽》注曰“言古乐和且敬也”[3]962。汉武帝作郊祀乐不为配祖,而欲长生求仙。汉武帝将所得之“马”与天神之“龙”相配,将郊祀天地之神的“德”行乐歌演变为求仙私欲之乐,故先帝和百姓不能知其音。
《郊祀歌·日出入》曰:“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表面是在祭祀日神,然而其思想感情却是不能与日同存的悲叹,而不是敬畏日神。应劭在《汉书·礼乐志》注曰:“《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6]1060《日出入》是欲求天马,驾天马而成仙。第十章《天马》则是歌咏天马,汉武帝认为天马乃“太一”所赐。《汉书·礼乐志》载文颖曰:“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6]1061乘天马而“游阊阖,观玉台”。紧接着第十一章则是咏《天门》:天门开,众神降临祠祭,神灵德泽恩厚无私,故能成其永世长生之愿。随后,借天降祥瑞来佐证能与神同往的缘由,即天显景星,地生灵芝。《景星》言吉星出现,《齐房》言地生灵芝,《朝陇首》歌白麟,《象载瑜》歌赤雁,皆属于天降祥瑞。
司马迁对汉武帝将求仙、祥瑞之事入宗庙之乐同样持否定态度。太史公虽未直接对汉武帝进行批评,然其在《史记·乐书》一文中围绕何为“乐”展开,论述了音、乐、礼与德之关系。他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4]1191君王所作之乐应与天地同和,乐是德的外在表现,“乐者,所以象德也”[4]1200。与天地相和的大雅之乐,可安抚民心,“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4]1206。乐是德的外在表现,是德浓缩与精华,是顺应天地而产生。仁人君子深知其中的道理,“小人”则只关乎其一己之所欲,“小人乐得其欲”[4]1212。所以,古代明君帝王作乐不娱己而为治世,“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4]1236。
《郊祀歌》在内容上不述德业以示天地、宗庙,背离“德”与“孝”,在形式上不采用庄重肃穆的曲调,而采民间音乐入郊祀乐章。在《郊祀歌》中,《天地》《后皇》《五神》篇中皆采用民间鼓舞乐,“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4]1396。此外,汉武帝在《郊祀歌》中还采用新声,“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6]3725。新声,多指郑、卫之声,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后来将与雅乐相对的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在内,统称之为新声。新声入《郊祀歌》,使庄重肃穆的乐郊祀天地、宗庙之乐变为“丽而不经”“靡而非典”。《文心雕龙·乐府》载:“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8]《桂华》为《安世房中歌》篇章;《赤雁》即《象载瑜》,为《郊祀歌》篇章。刘勰对将新声入郊祀天地、宗庙的乐章明显是持否定态度的。《宋书·乐志》也记载:“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9]正因如此,才导致“雅声浸微,溺音腾沸”以及“中和之响,阒其不还”的局面,郊祀之乐被世俗化、娱乐化。
商周以来的,在以“天”为至上神的天道神学观指引下的正统雅乐具有示范和教化意义。这种教化作用是无分别的,对君王和人民是一致的。雅乐肃穆庄重,令人心生敬畏,可以安民心,固社稷。而汉乐府轻教化、重娱乐,将“乐”演变为享乐工具。因此,“乐”丧失了独立地位,成为个人私欲的附属品。后世乐府、诗歌开始脱离政治教化,走向个体生命的审美感受。沿着“享乐”这一基本主题发展,人从与天同寿、同在的神学体系中脱离,享乐主题的盛行与人生短暂的生命局限最终成为人脱离“天”之后永恒的矛盾和痛苦,慷慨悲越成为成为清商乐府和建安五言诗共同的审美特征,乐府与古诗呈现出相似的“审美风格和审美目的”[10]。
乐府,特别是郊祀乐曲的教化作用是天然形成的。这种教化作用起源于雅乐本身,它以天(上帝)为至上神,上帝临赫四方,于最高处俯察人的行为。正是这种从“天”而视的纵向空间感,让人们自觉规范自身行为,从而形成群体性的内在自觉。此外,祭祀宗庙的乐章,强调“德”的传承,通过向祖先陈述德行,以祖先之德行观照自身行为得失,体察自身行为是否“配祖”。这种横向的追溯,形成了“继承性”的时间感,通过怀念祖先德业引人自省。人与天之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德”是中介。故有“德”,天福赐,无“德”,天降祸,“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4]1235。
汉代郊祀歌的排列顺序反映的是刘邦到汉武帝宗教神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即“太一—天地—五帝”的宗教神学体系与阴阳五行说“一—阴阳—五行”对应关系[11]。《郊祀歌》主要由迎神曲、送神曲、祭祀五帝曲和歌祥瑞曲几部分构成。其作者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张强在《〈郊祀歌〉考论》一文认为,《郊祀歌》的辞作者应该有武帝、司马相如等以及宣帝和匡衡,歌(曲)作者应有李延年、邹子和民间鼓舞乐等。整个一神学体系,以阴阳五行为内理结构,以“太一”独尊为神学之宗,统一于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体系中来,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结构体系,最终将权力核心指向皇权。
这一新的宗教神学体系,将商周以来形成的天的地位取代,德以配天、敬天行德的敬天爱民意识逐渐被消解。天的意义在于敬畏,尊天而行爱民之行。两汉时期,这种敬天崇德爱民的宗教神学观开始被慕仙、追仙、游仙、成仙的思想取代,天的意义不在于敬畏,而在于向往,天成为帝王向往永世长生私欲的归宿。因此,汉武帝将求仙的私欲与庄重的祭祀和封禅结合,在祀天尊德的背后,隐藏着长生求仙的目的。因此,《郊祀歌》虽为郊祀天地的乐章,缺少“德以配天,孝以对祖”肃穆和庄重,更多的是求仙游仙的,欲与天同寿的思想。
《易经·豫卦》载:“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12]商周时期,郊祀尊天重德,将德行诉之于天。《昊天有成命》是周朝郊祀天地的乐章,颂赞成王能继承文王、武王德业,勤勉治国,兢兢业业,光大祖宗基业,安定天下。其中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3]943开篇先言“二后”(文王、武王)受天命成帝业,成王继承先祖之位,勤勉有德,安民定邦。汉代郊祀天地的歌辞则全言帝王一己成仙之事,而不言其治世之德,背离了商周以来“德以配天”的天道神学观和“孝以对祖”的宗法伦理观。
周部族郊祀天地,将对天敬畏与对祖先的敬重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从周部族史诗“大雅”中可以看出。祭祀天地之乐,是行上帝之德的体现,通过郊祀向祖先陈述自身励精图治、治理国家的德行,将对天的敬畏与对祖先孝的结合。首先,借郊祀天地之乐,审查自身德行,是否有愧于天(上帝)与祖先,“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3]754。周部族特别注重德行的继承,德是唯一能与天相配的依据和凭证,德行传承是君权传承的重要标志,是天(上帝)评判能否治理天下的重要标准,《诗经·大雅·皇矣》讲述至上神天(上帝)洞察观照天下四方,憎恶殷商失德之行而喜周王之德行,“帝迁明德,串夷载路”[3]779,王季继承周王德业,声誉清静无瑕,并将上帝之福祉传承给文王,“维此王季,帝度其心……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3]781。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敬天法祖的思想在汉代逐渐演化为游仙思想。这一演化消解了人们对天的敬畏,将威严的天神娱乐化、世俗化。这一变化趋势背离了商周以来的天道神学观和宗法伦理观。在神学思想上的世俗化,表现为将天道神学演变为政权统治的工具,在礼乐体制上的娱乐化,将俗乐新声引入庄重的祭祀雅乐之中。
德以配天、孝以对祖,天和祖先是辩证统一的存在。天道神学观的核心“德”,德的本质是生民和保民。宗法伦理观的核心是“孝”,孝的终极目标是配天。天和君主存在契约关系,这一契约关系的核心是“德”。德和孝贯穿于治理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并以“礼”的形式呈现,“礼就是社会群体所要依从的,在最初是指祭祀的仪式,后慢慢变为约定俗成的准则”[13]。商周时期,天道神学观与宗法伦理观体系得以建立和统一,将崇天和崇祖通过“德”和“孝”统一起来。天(上帝)作为至上神,具有监管君主的责任,君主替天(上帝)行治理天下之事,君主受天的监管,并形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行德以对天,行孝以对祖。
德和孝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两大重要支柱,德以配天、孝以对祖是商周天道神学观、宗法伦理观和君主政治观的统一,天处在核心位置。到汉代,天的独尊地位逐渐被帝王君主意志消解,天道神学观沦为君主独尊的统治工具。君主对天的态度从敬畏转变为娱乐,从而将敬天演变为娱神,君主失去天的监管,私欲不断膨胀,产生了与天同寿,慕仙追仙的思想,而不是敬天行德惠民。这一思想转变,打破了天与君主的契约关系,导致商周以来的以“天”为核心的神学体系瓦解,“太一—天地—五帝”的宗教神学体系与阴阳五行说“一—阴阳—五行”神学体系逐步建立,形成了以“太一”为至上神,以阴阳五行为内理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最终服务于皇权。
这一变化导致了郊祀天地的乐和歌辞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引起了文学层面的变化,即由以《诗经》“大雅”为主的雅文学到汉《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为主的世俗文学转变。人与天关系脱离,是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这种转变表现为,天(上帝)的独尊地位和人们对天的敬畏感逐渐消失,人们从对天(上帝)的文学言说方式转移到自我现世世界的言说,即雅的本质是对天(上帝)文学言说,俗的本质是人自我现世世界欲望、享乐需求的言说。人从与天的契约关系中脱离,享乐主题的盛行与人生短暂的生命局限最终成为人脱离“天”之后永恒的矛盾和痛苦,这构成了后世诗歌重要的审美主题。同时,将民间鼓舞乐用与郊祀天地、祖先的乐章中,郑卫之音混同于庄重肃穆的雅乐乐章,不述德业而写一己求仙心愿,郊祀之乐被世俗化、娱乐化。因此,汉乐府郊祀歌辞呈现出轻教化、重娱乐的特征。天的地位消失,人的欲望增强,这也正是祭祀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学者认为:“中国自秦汉中央集权以来,士人唯独在秦汉这两个时代没有和诗人这一中国历朝历代不可独缺的特殊身份挂钩。秦朝以暴政废儒而使诗人缺席,两汉则以极端经术而为诗歌荒漠。建安特别是建安十六年之后,士人方渐次成为了诗人的创作主体,反之也可以说,诗歌方才成为士人精英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两汉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何不能成为产生诗歌创作的土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所述,秦代独尊法术,焚书坑儒,毁灭儒家经典,文化荒漠上自然难有诗人存活的绿洲;继之而起的汉代政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为国家哲学,正是接受秦代极端政治的一种反拨,从而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儒家哲学的极端化,儒家思想的统治的严密化,儒家经术在士人群体中传播流布的牢笼化,从来没有像东汉时代这样的登峰造极,而这种严密的牢笼化的儒学经术统治,走到极端化的结果,就是士人群体思想的僵化。士人思想僵化投影到文学创作的领域,一方面使以讽一劝百、铺采摛文之洋洋大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就是面对诗歌写作的望而却步。”[14]作者极为细心地分析了秦汉士人作为诗人主体的诗歌创作的衰落的种种原因,而没有注意到天道神学观念的转变在雅文学到世俗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的观点正可与之互相发明。
[1]大学 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90.
[2]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38.
[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7]王红杏,木斋.论中国早期文学侍从的文学史意义:以二曹六子主从关系为中心[J].琼州学院学报,2014(4):34-43.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平:文化学社,1929-1931:101.
[9][南朝齐]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0.
[10]王立.论“古诗”类五言诗及乐府诗在传播中的变异[J].琼州学院学报,2014(4):26-33.
[11]张强.《郊祀歌》考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3):97-101.
[1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5.
[13]陈柏桥.从《左传·宣公十二年》看允文允武的楚庄王[J].琼州学院学报,2016(4):94-99.
[14]木斋.再谈原典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J].琼州学院学报,2015(4):1-4.
(编校:李一鸣)
Evolution of Theology in the Period before Qin and Han Dynasty—The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of Sacrifice Literature in Han Yue Fu
YAN Zhen-nan, WANG Jing-jing
(School of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Virtue and filial piety are the two important pillars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Virtue corresponds to heaven while filial piety is for the ancestor and is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sacrifice culture.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eaven" as the center of the theology and patriarchal ethics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and heaven (God) and the monarchy established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linked by "virtue". The monarch is supervised by God and respects heaven and virtue. In the Han Dynasty, emperor Wu integrated the Taiyi God and the theory of Yin Yang, turned respecting the heaven to entertaining God, cared immortal art, and pursued immortals, so heaven(God) was gradually degraded. This change led to the great changes ofSacrificeLyrics: the lofty status of heaven disappeared, person’s desir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SacrificeLyricsas the main sacrifice literature presented the tendency of seculariz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eave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legant literature to popular literature.
virtue; heaven; immortal pursuit; sacrificial literature; elegance and popularity
2016-09-18
严振南(1988-),男,山东临沂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王晶晶(1991-),女,河南许昌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美学。
I207
A
2096-3122(2016)06-0021-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