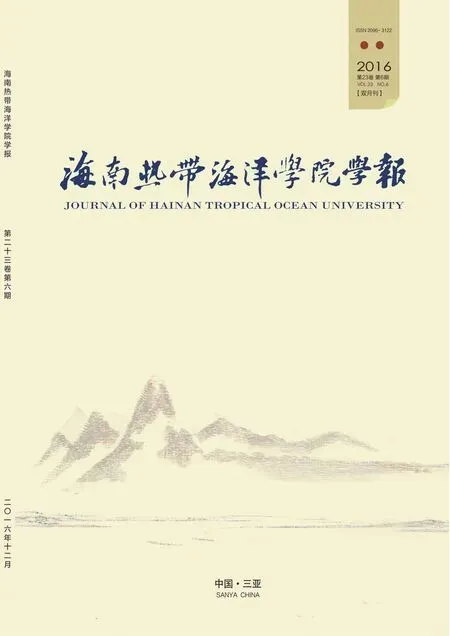先秦尊天情结述论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先秦尊天情结述论
汪韶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崇天的文化。天不是位格化的绝对实体,而是一个“如在”的神圣对象。古人借天命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或借天来约束君权,其深层都是德的观念。此时,“天”代表着正义或神圣的宇宙法则,对人构成一种道德律令。天地因其化育万物、公而不私、予而不争等德性,被古人当作人类行为的伟大典范。古人尊天、法天的主旨是以德性来配天,即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天来指引人的在世方式。如果人的德性达到了天的高度,便是“天人合一”。
先秦诸子;天;天命;德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崇天的文化。有学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天为中为极的文明。”[1]322这一论断非常恰切。“天”在古今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天”由“帝”发展而来。从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出,“帝”是殷人卜问的对象。殷人凡事必卜,“帝”可以说是他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顾问”。殷周之际,“天”取代了“帝”,成为后世尊崇的对象(后世仍有“以配上帝”的说法,但“上帝”已指天)。笔者在此先回顾学界有关“天学”的研究,之后通过地上地下文献考察诸子之前以及先秦诸子的“天论”,以揭示尊天情结背后的深层意旨。通过这种考察还可发现,学界的某些流行观点,如认为墨子所谓天是意志天、宗教性之天,认为天人感应说、灾异说、谴告说纯是宣扬迷信,认为“天人合一”指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一、“天学”研究之回顾
笔者将有关“天”的观念及其相关研究称为“天学”。学界一般认为,“天”在中国哲学中有着多重涵义。冯友兰析为五层:“物质之天”(天空)、“自然之天”(唯物主义所谓的自然)、“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运气)、“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2]89。劳思光分为三种:主宰义的“人格天或意志天”(对应于“天意”)、法则义的“形上天”(对应于“天道”)、自然义的“苍天”。[3](天道与天意的差别在于,它没有意愿性,只是一种客观规律。)研究者还认为,先秦诸家秉持不同的“天”之观念,如徐复观说:“儒家发展了道德法则性之天,墨家则继承了宗教性之天,道家则发展为自然法则性之天。”[4]张岱年认为,孔子所谓天处于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过渡中,墨子所谓天完全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老子说的天与地相对,庄子说的天与人相对。①详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又有论者认为,老子用天道取代了天命,孔子则用仁、礼淡化了天命。种种说法虽然有异,但学者大多都认定,老、孔之前的“天”主要是意志天。
张祥龙反对这类切分,更反对把老、孔之前的“天”解释为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他认为,殷人的“帝”近似于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老天爷”,而老、孔之前的“天”并非意志天,老、孔之后也没有背离之前的尊天传统:“周人同样占卜,信天命,但这天却肯定不是人格神,……尊奉人格神的宗教则一定以绝对信仰、种族或教律而非德性为识别‘上帝的选民’的首要标准”[1]236,“周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也还在对祖先社稷、天地山川等行祭祀之礼。但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人格神崇拜,而更近乎孔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237
笔者比较认同张先生的这种观点。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天”不是位格化的绝对实体,而是一个“如在”的神圣对象。《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后,孔子慨叹道:“噫!天丧予!天丧予!”*本文调用了大量原始材料,目的是更好地呈现先秦的尊天情结。但为了避免繁琐,凡从《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墨子》《老子》《庄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论衡》《越绝书》《孔子家语》等经典性古籍或常见古籍中引出的材料,文中只注明所出篇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老天爷要绝我啊”。而《宪问》篇“知我者,其天乎”,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天知地知,实际只是“我”自知。孔子未将“天”当作实际存在的人格神,就如同他并未真的认为有鬼神一样。“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给很多人的感觉似乎是,孔子只是“不语”“远之”,而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但这样理解的人,实在没有看到孔子骨子里对鬼神观念的反对。《八佾》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只是说,祭祀一定要虔诚,一定要投入,否则祭了等于没祭。“祭神如神在”是主观上权当鬼神就在身边,这样能增进祭祀者的虔诚,绝不是在客观上肯定鬼神的存在。“如”字很微妙,但实际只能理解为若有而实无。为什么要用“如”字?原因很简单,明确肯定鬼神的存在,会导致人们重视“事鬼”而忽略“事人”;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则又导致人们丧失敬畏精神。这两种情况孔子都不愿看到,故将鬼神观念“虚悬一格”。《孔子家语·致思》有段材料颇能说明问题,“子贡问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墨子·公孟》则记载了墨子与公孟子关于鬼神有无的一次辩论。公孟子是曾子弟子,他一面说“无鬼神”,一面又说“君子必学祭祀”。这里明确指出了祭祀对象没有实在性,但依然对其充满敬意,这就是“祭如在”的真正意含。
再看《诗经·小雅》中的几首诗。《节南山》斥责执政者师尹:“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无罪无辜,乱如此幠。”这里,“天”成了人们质问的对象,作为人们的“出气筒”而存在。冯友兰认为:“这些诗歌的作者,对于上帝的存在还没有怀疑,但已怀疑宗教所宣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正义性,开始向他提出质问。”[2]78笔者以为,冯先生的这种解释未必妥当。“天问”的做法在当今中国老百姓这里还普遍存在着。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人们会说“天开眼”;如果恶人得势或善良的人遭罪,人们会说“天没长眼睛”。但无论如何,老百姓并没有真的认为有那么一个人格化的“老天爷”,一会儿长了眼,一会儿又瞎了眼。
二、先秦天命论的功能
天命论的渊源甚古,而其功能有多方面。
其一,借天命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诗经·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周颂·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这是把政权的获得说成天的旨意,有点类似西方君权神授的意味,“天子”的称号即溯源于此。这种观念的另一形态便是顺天应人,替天行道。《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篇:“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国语·越语下》记载范蠡称灭吴乃“致天地之殛”:“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天予不取,反为之灾。”《黄帝四经·经·兵容》:“天固有夺有予,有祥□□□□□弗受,反随以殃。……□不飨其功,还受其殃。”[5]71这些都是说,天命的到来,不可抵挡;天命的遁去,无可挽留,应该当机促成政权的废立或更替。甚至《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述而》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子罕》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也是一种变相的替天行道,因为它们都是行为主体觉得道义在身,由此产生一种使命感、责任感。
其二,借天来约束君权,无论是为上者自我节制还是下对上的建言。《诗经·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小雅·小宛》:“各敬尔仪,天命不又。……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此时,天命论反映出一种忧患意识。它认为,人只有凭借自身的德性,才能成为天的选民。这种观念可能最先产生于统治集团内部,西周初年的周公、召公堪称代表。他们深感天下来之不易,为了维持新政权于不倒,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这在《尚书·召诰》中有突出反映。王国维极赞道:“自来言政治者,未有能高焉者也。古之圣人亦岂无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然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胥在于此。”[6]
墨子尚同,而尚同的终点是齐之以天:“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天志下》)这里明确提出以天来正天子。*西汉董仲舒也主张奉天法古。《春秋繁露·玉杯》把《春秋》大法总结为“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他想以“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篇),这与墨子的思路完全相同。墨子认为,治国必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天意是什么呢?“天欲义而恶不义”(《天志上》),“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义果自天出矣”(《天志中》),“天之志者,义之经也。”(《天志下》)而“义”是什么?《经上》:“义,利也。”可见,墨子说的“天”并不是意志天,而所谓“天意”,实即墨家所主张的兼爱兼利原则,是用以指称公而无私、民意的一个语词,即三表中的“古者圣王之事”“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法仪》篇:“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志上》:“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称天能“欲”能“恶”,能“福”能“祸”,并非真的说天有意愿性,而是说天代表着道义。因此,称墨子之天乃意志天、宗教性之天,恐是执于字面的解释。
由此推之,郭店儒简《唐虞之道》“天地佑之”[7]157,《黄帝四经·经法》“天将降央(殃)”[5]49,“天诛必至”[5]55,“不有人僇(戮),必有天刑”[5]57,《称》篇“天有环(还)刑,反受其央(殃)”[5]81,“宫室过度,上帝所亚(恶)”[5]82,都不是说天或上帝有意志。
古人认为,只有法天,才能得到福佑,才能长久。《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离娄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管子·形势》云:“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围之。”然而现实生活往往是,有德不一定能获得福佑,无德也不一定就遭到祸害。《墨子·公孟》就记载一门人问墨子:“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那么,古人为什么把一种或然性说成是必然性呢?东汉王充《论衡?福虚》在批评汉代变复之家时曾说:“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这就明确地将或然性与必然性区分了开来,同时避免了被滥俗化的灾异说。《谴告》篇又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原来,哲人言天是为了劝诫,并不真的认为自然灾异是天的谴告;其所谓“天”,实质上是“人心”。王充此见非常深刻。*荀子就曾批评灾异说。《荀子·天论》:“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灾异说、谴告说的初衷,是借天来敦促人君明心返道。庞朴也说:“律令意义的天之道,本来是说给君王听的,是大臣们挟天道以令天子,制约君王无限权力和自由意志的法宝。”[8]249这种做法“不如说把为政应有之道附会到天象上,再返回来尊作天行之道,以作为建言、谏争的根据,拉着‘天道赏善而罚淫’(《周语中》)、‘天道无亲,唯德是授’(《晋语六》)之类的虎皮作大旗,以求补救君主无上制度的缺陷。”[8]246当然,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仅借天来劝勉君主合理使用权力,是很不可靠的,所以《文子·上义》提出:“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
其三,天命论在先秦还有其他功能,如解释命运。当时许多人认为,天道是主持正义的,但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义的现象,于是就有人用命来加以解释。或者,当一个人处境恶劣而又理会不出具体缘由时,就容易在无奈之下一方面呼天,另一方面又认命。《诗经》中的几首诗就传达了这种情绪,如《小雅·小弁》:“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庄子·大宗师》末尾子桑呼天唤地,与《北门》诗很相似:“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这里的“父母”即天地。表面上看,《北门》诗作者说“天实为之”,而庄子说“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但“天实为之”之“天”实质上就是命。他们把非自身所能控制、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一些因素,姑名之为“天”,姑名之为“命”。《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与命互文。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命是尽了人力之后仍旧不能如人意,因而感受到的一种不可抗力。郭店楚简《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7]145“天”就是时命。《孟子·万章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的运作自然而然,命的形成也是自然而然。《吕氏春秋·知分》:“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需要注意的是,天命即使指命运时,也不是宣扬宿命论或命定论,认为天主宰着人间;而是把命运的自然形成机制姑且归之于天,或径以天作为命的代名词。天、命的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泄导人们的精神压力,有时还能因此培养出一种超脱、豁达的气度。《文子·上德》说得好:“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无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
就前两种功能而言,天命论的深层都是德的观念,而不是人格神。可以说,“天”代表着正义(divine justice)或宇宙法则,类似于西方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年)讲的神圣的宇宙秩序。这样的“天”,对人就构成一种道德律令。
三、天地之德——法天则地的根据
《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郭店儒简《唐虞之道》:“夫圣人上事天,……下事地。”[7]157(古人谈“天”常连带着“地”。)中国比较缺乏古希腊那种穷究宇宙起源的思辨传统,讲天道最终还是要落到人道上来。中国古代对天的尊崇塑造着人的生存形态。古人所以上考诸天,下揆诸地,乃以天地为人类行为的典范。这是中国哲学天人观的主旨。先秦天人观就认为,无论治国还是修身,人类都应该则天而行。那么,中国哲人为什么尊天、法天呢?他们从“天”那里到底获得了什么启示?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四经·经法·君正》有所谓“天地之德”,《黄帝四经·经·姓争》《礼记·中庸》都有“天德”之说。据先秦的有关叙述,天地之德可总结为*老庄这方面的言论,详见拙文《论〈老子〉之“玄德”》,载《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其一,化育万物。范蠡(前536年-前448年)是由老子到黄老学派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越绝书》卷13载其语:“圣人缘天心,助天喜,乐万物之长。”帛书《九主》也是一篇道家文献,其中说道:“天乏(范)无□,复(覆)生万物,生物不物”,“法君者,法天地之则者。……复(覆)生万物,神圣是则,以肥(配)天地。”[5]29
《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周易·彖》:“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对天地化育万物的哲学概括,故《中庸》如此称圣人以德配天:“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宇宙万物的生命都源于天地乾坤,所以天地乾坤是广义上的父母。老子所说的天道,是“万物之始”“万物之母”“万物之宗”“众妙之门”“天下母”“玄牝”“众甫”(即众之父)。《庄子·大宗师》:“阴阳于人,不翅(啻)于父母。”又《天地》篇:“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黄帝四经·经·果童》:“夫民卬(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5]66《周易·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其二,无不覆载,公而不私。季札(前576年一前484年)是与老子同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其语:“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
道家一系,《国语·越语下》载范蠡语:“惟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恶皆成,以养其生。”《黄帝四经》认为天地是无私的,并提出“刑天”“法地”。其《经法·四度》云:“周迁动作,天为之稽。”[5]51又《经法·六分》:“参之于天地,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5]49《管子·心术下》亦云:“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儒家方面,《礼记·孔子闲居》记载了子夏与孔子的一次对话。子夏问如何才算参于天地,孔子答以“三无私”:“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中庸》也把天地无不覆载、无为成物之德概括为“博厚”“高明”“悠久”。
其三,予而不争。《国语·周语中》载单襄公语:“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故《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单襄公生活年代先于老子。“先诸民”是说把民放在首位;不得民心,则政权难以稳固。在此,我们明显看到了《老子》“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的影子。老子在天地之上安了一个道,并不是要贬低天地,实际上,他对天地仍怀着一种崇敬之情,故要“配天”(68章),理由很简单,因为天地有“利而不害”(81章)、“功遂身退”(9章)之玄德。《黄帝四经·称》:“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5]83此经所谓的“雌节”相当于老子所说的“柔”,它是一种不争之德。
儒家方面,《荀子·非十二子》曰:“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儒效》篇:“争之则失,让之则至。”《修身》篇:“行乎冥冥而施乎无报。”
墨子也认为,“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墨子·兼爱下》)。《法仪》篇:“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尚贤中》称天“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天所以值得效法,在于它在施予过程中兼而不别,没有偏私,而且不会因为施予而自诩(“不德”)。
由上可见,古人尊天、法天的主旨是以德性来配天,即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天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如今,“天人合一”已成为非常时髦的用语,但几乎都被歪曲成了绿色和平的口号,其实,它的原初意义绝非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而是从德性的角度强调人去合天(人道去合天道),即法天、配天。如果人的德性达到了天的高度,就是天人合一了。
[1]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1.
[4]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86.
[5]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王国维.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二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6:474-475.
[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
(编校:王旭东)
Review on the “Zun Tian” Complex in the Pre-Qin Period
WANG Sha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 Communic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Since ancient times, Chinese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e in which “Tian (天)” is worshiped. “Tian” is not an intentional personality, but a divine object which appears to exist. Ancient Chinese demonstrated the regime’s legitimacy by “Tian Ming (天命)”, and restricted monarchical power by “Tian”. The core of such practices is the notion of virtue. Here, “Tian” stands for divine justice or universal principle. Therefore, it becomes a moral imperative for men. “Tian” is believed to have such so-called virtues as bringing up all cosmic beings, being impartial, giving but never taking, so it is regarded by ancient Chinese as a great paradigm of human behavior. The main purpose of worshiping and imitating “Tian” is to match “Tian” with virtue, that is, to act or to guide man’s way of living according to virtues of “Tian”. Once an individual’s moral realm has reached the height of “Tian”, we can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as “Tian Ren He Yi (天人合一)”.
Pre-Qin thinkers; “Tian”; “Tian Ming”; virtue
2016-10-2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X002);海南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子项目(01J1N10005003)
汪韶军(1973-),男,浙江淳安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禅宗、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B22
A
2096-3122(2016)06-0032-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6.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