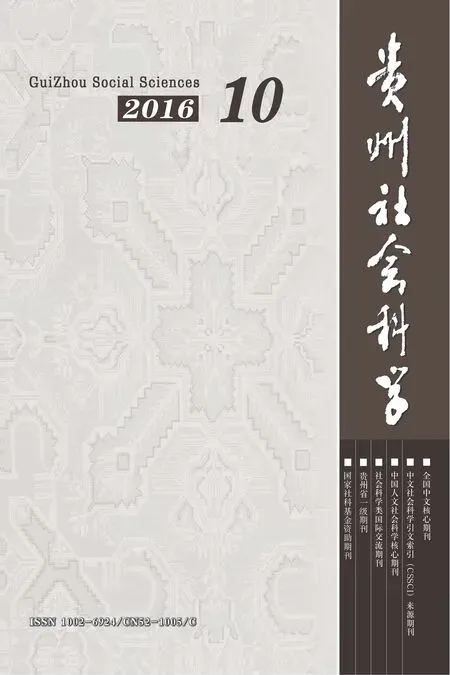地方空间与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建构
蒋建国(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1)
地方空间与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建构
蒋建国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1)
在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的全球性和统一性的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然而,网络的地方性却被淡化甚至忽略了。网络的地方空间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是彰显网民主体和网络文化差异性的基本场景。网络地方与地域相关,但更多地体现为特定的网络生活空间。回归地方,应包括地理上的地方网络文化、情感上的地方存在感、价值上的地方意义感。网络文化建设需要回到地方空间,从网民个体情感与社群活动中探寻“地方”的文化意涵,通过网络地方文化建构体现网络清朗文明。
网络文化;地方空间;建构
列斐伏尔指出: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1]同样,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网络空间,空谈网络文化也毫无意义。而“合适的空间”应该是一个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地方”,而非泛指的全球性空间。因此,网络文化并非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需要通过网络“场景”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从地方空间的角度探讨网络文化的“在地化”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全球空间与网络地方空间的生成
空间与时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而网络空间则是网络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网络空间既是抽象的虚拟空间,又与人的主体性存在相关。没有人的参与,网络空间便成为“空洞”的空间,其价值和功能便难以体现。因此,对网络空间的探讨,除了研究其技术、工具层面的意义之外,需要更多地关注其价值、精神层面的作用。
在传播全球化语境下,网络空间是统一、流动、同质的,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信息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共享、互动成为网络信息的基本特征,网络空间成为突破地理限制的无界“银河”。毫无疑问,网络技术极大地推进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进程。然而,网络是由无数个节点组成,我们在强调总体上的意义之网的同时,对网络的节点却少有从具体层面认真探讨,也就是说,在复杂的网络世界中,各个节点的“地方性”存在方式,往往被“全球性”所遮蔽。
网络文化并非完全是全球同一性的文化,“虽然全球化可算是当今的主导力量,但是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就不重要了。即便我们曾强调非本土化(delocalisation)进程,但该进程尤其与发展新的信息传播网有关,不应该把它看作是绝对的趋势,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2]由于“地方”的客观存在,我们需要用“他者”的眼光观察其差异性。正如吉尔兹所言: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3]因此,过分地强调传播全球化所导致的时空压缩,而忽略全球各地的文化特色,不符合网络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体系研究中,我们需要从民族、地域、社群等方面关注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可以说,不承认地方性网络文化的差异和个性,就难以提炼和归纳网络文化的共性。
网络空间虽然没有专属性,但是网民在虚拟空间的客观存在,却有具体的位置感。梅罗维茨用消失的地域来描述网络空间,但也强调“场景地理”对我们的影响。他认为,媒介既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给出排斥和隔离感。媒介能加强“他们与我们”的感觉,也能消除这种感觉。[4]对于处于特定空间的网民而言,他在感受到网络空间的全球性文化的同时,更多地会体会到网络空间“场景地理”的存在。因为每个网民都是网络世界中微小的主体,虽然海量的网络信息提供了平等的消费机会,但是,上网时间和选择机会限制了信息的可消费范畴。因此,全球空间更多地体现出网络整体消费的意义,对于网民而言,他在特定空间中的上网行为,是在网络节点上的行动过程。具体网站和节点是特定的“地方”和“此在”。
研究网络地方空间的意义在于,我们在承认网络全球化“可得性”的同时,更关注网民消费的“现实性”。一方面,网络虚拟空间可以提供任何公开传播的信息,另一方面,网民对公共信息的获取,是在独特空间中的个体行为。我们需要对于获取的“地点”予以特别的关注,尽管网络上的“地点”可以漂移,是流动空间中的漂浮的节点,但是,它体现了消费主体与信息的共同在场。这种具有特定消费意涵的空间,便是构成网络世界的“地方”,没有特定“地方”的存在,网络空间便是空洞的“白板”。因此,研究网络地方空间,是探讨网络文化“在地化”实践的必选选择。
当然,网络地方空间与地方性网络有着很大的区别,地方性网络一般以一定区域作为传播重心,但由于它在网络空间中具有无数的节点,任何对它感兴趣的网民都可以随意链接,在理论上它可以传播至全球任何地理空间,但它却是网络地方性的重要象征。媒体意义上所谓的“当地”,是由地域所决定的“地方社会”,其中媒介景观不可或缺。感受“地方”,便需要通过地方网络提供基本信息。通过链接地方网络,网民的知识仓库中便增加了地方性知识,而此类地方性知识虽然不同于抽象的理解性知识,却对网民增强地方感有着直接的帮助。
正如卡斯特所言,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地方乃是一个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容于物理临近性之界线内的地域(locale)。[5]然而,地方性和地方感在网络文化研究中被以种种方式忽视或淡化了,即使在部分研究中未被忽视和淡化,它与网络超地方性、去距离效果的关系也需要重新的定位审视。因此,强调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就是在普遍性基础上凸显“地方”的特别意义。只有回归地方,对网络文化的地方感觉和人文价值才能落到实处,也只有在地方空间,网络文化的具象性、可感性、消费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二、网络地方空间的生产与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呈现
瑞夫认为,地方具有物质、功能和意义三重属性,其中地方意义包含象征意义、思想感受和行为价值等等,地方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性。[6]网络地方与地方社会既有直接的联系,又可以通过网络产生空间移植。
网络技术发展对地方的观念有着直接影响,在Web1.0阶段,网民对网络地方的依赖度较强,网民通过计算机上网的方式,在固定的地点,感受物理意义上的网络位置消费,地方网络媒体提供的信息直接影响着信息消费的地理空间。因此,各地报刊媒体的网络化和中央网络媒体的地方板块,便为当地网民提供了地方消费空间。对于网民而言,在新闻消费方面最感兴趣的仍然是地方新闻,地方网络提供的各种信息和服务,具有消费上的优先地位。网民对现实地理的依赖性,决定了地方性网络在地方空间的影响力。商业网站对地方新闻的板块呈现,也为网民的地方性消费提供了指引。网络上的地方,往往为网民提供某种身份识别。虽然网络上乡土的概念并没有现实生活中那样明晰,但网民对来自何处的新闻仍然有着“地理”上的心理反射。“我从哪里来,到何处去”,不仅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追问,也是网民对自身归属感的本能反应。因此,网络的地方性就为地方社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许多网络社区以属地命名,就是瞄准某个地域的网络群体。而一些网络热贴也往往体现出网民对地方时政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由于网民可以摆脱现实空间的限制,对网络地方进行空间上的构筑,并能通过任意位置回归“地方”。在网络上与“地方”相遇,使“地方”成为自由移动的载体。网络摆脱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却必须依赖“地方”来表达主体的存在。
在Web2.0时代,地方空间是可以自我书写和交互传播的媒介景观,社交媒体的高度发达为网民的“地方”表达提供广泛的空间。与Web1.0时代对地方的阅读体认不同,社交媒体通过交互性来书写新的“地方”,“地方”既可以是一种乡土地理概念,也可以是族群和亚文化呈现的空间。作为生产型消费者的网民能够摆脱时空的局限,通过网络读写与交往行为,在网络任何“地点”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地方”。这一网络空间,可以是地缘意义的乡土概念,也可以是情缘意义上的同道概念,还可以是趣缘意义上的同好概念。以社交媒体为主导的交往方式,使网民可以发现许多新的“地方”,通过博客和社交网站,网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其网络上的自我呈现和交往诉求,很快会汇成族群聚集的“地方”。
在一定程度上看,网络族群是网民由于某些共同目标、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汇集起来的群体。如尼特族、考碗族、月光族、背包族、隐婚族、追星族、御宅族、SOHO族、99族、辣奢族、酷抠族等,不同类型的网络族群折射了当下网络生活极为丰富的样貌,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和价值多元。有人用网络56族来描写网路“族”生活的丰富多彩。作为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网络族群文化具有反叛、创造与宣泄的风格。正如赫伯迪格对亚文化风格分析的那样:“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表现出了类似于演说的姿态和行动,冒犯了‘沉默的大多数’,挑战了团结一致的原则,驳斥了共识的神话。”[7]当某一族群文化流行于网络时,势必因其鲜明的主张和强烈的行动获得网民的高度关注,由于网络族群的匿名性和随机性,族群的成员很少考虑网络行动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加入某一族群,就是要以“我发帖、故我在”为荣,敢于突破现实藩篱的种种束缚,尤其是对传统道德伦理不屑一顾,甚至敢于揭发和暴露自身的弱点和劣势,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网络族群是网络地方空间的新生力量,他们不断创造出亚文化的新样态,颠覆了传统地方社会的空间概念,使“地方”具有主观性和聚结性的意涵。网络群体缺乏组织性和紧密性,是流动的网民在无边际空间的群体活动。它打破了现实社会群体传播的时空限制,以聊天、会话、信息分享和新闻传递为主要方式。群体传播主要体现为传染病传播模型和影响力传播模型,传播的信息分为多源信息传播模型、信息竞争力传播模型。围绕着群体共同关注的信息传递、聚集、评论,以核裂变方式快速扩散,形成关注的“事件”,群体行为的匿名性、群体信息的易感染性、群体活动的变动性,使群体传播表现出较大的地方差异性。
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发展,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传播,网络地方空间与社会空间进一步交汇,媒体化社交使信息转发与浏览实现了即时化与随机性。移动终端已经完全摆脱了消费的位置局限,网络的节点可以无限制蔓延,地方的差异性对文本的影响越来越小。手机媒体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网络上的地方,微信用户也可以轻易建立一个新的地方空间。尤其是用户能通过朋友圈化身为“帮主”,在网络上构筑自己的“领地”。从理论上看,每个微信用户都可以拥有无数“地址”,通过各种微信群找到社群生活的地方,形成新的“文化部落”。这些“文化部落”成为当代都市人新的精神居所,部落人的积聚是为了消费一种意义、一种象征和一种社群感,他们更少地因为地理和工作相近而发生联系,而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链接在一起。[8]在Web3.0时代,网民通过朋友圈可以任意在网络上“圈”住一个地方,每个网民也可以同时驻扎在不同的群落中,在不同的地方发言,并表达作为社群成员的声音。地方与地理的概念已经完全撕裂,微信群文化已成为亚文化的主流方式。朋友圈是一个逐渐内爆的虚设的圈,流行性社交已经消解了“朋友”的内涵,圈内的地方舞台林立,表演者无处不在。传统的情感领地被信息“瀑布”冲刷得分崩离析,各种朋友圈也失去了私密性社交的界限,“越微信、越孤独、越无聊”成为常态。微信的泛地方化,对网络文化的再地方化提出了挑战。
三、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建构
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播全球化的进程,也对网络地方感产生极为强烈的冲击。然而,我们在谈及网络文化时,却很难用全球文化来统领网络文化。网民对网络文化的认知,既有“普适性”的一面,也有个体认知的一面。网络文化的意义之网,需要在具体的地方和环境中进行阐释。因此,没有“地方”,网络文化就无法生根,没有“地方”,网络文化就难以体认。网络文化存在民族、国家、宗教、地域、阶层等方面的差异,也意味着其内涵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强调网络文化的在地化,就是要从地方空间中凸显其独特风格,从抽象的全球性概念回到具象的文化实践和符号所指,从总体意义上的文化描述转向地方层面的客观分析。在网络文化建设中,我们通常从民族、国家层面进行宏观思考,但是,对地方层面的具体举措,却缺乏应有的关顾。这就使大众化的网络文化难以体现个性和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地方性文化的特色和主体间性的作用。因此,强调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建构,从地方空间探求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性、时代性和社会性,都有重要的价值。
重视网络文化的地方性,首先要关注地理空间上的“在场”。尽管“脱域”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特征,但是,网络文化的生成必须依赖特定的空间,承认网络文化的差异性,就必须从地方空间中寻找网络文化的“个性”。由于文化堕距、技术鸿沟、社会传统、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原因,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尽管城乡、区域之间的网络信息可以任意流动,但是,网民所处的“地方”却对网络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地方网站对本地社会的报道,势必增加本地网民的亲和力。因此,网络文化的在地化,需要地方网络媒体的形塑。
对于网民而言,全球、国家、地方的概念始终体现在行为和观念之中,尽管与1990年代都市报兴起的背景不同,但是本地民众对地方新闻的关注,并没有因为网络的普及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网民即便在浏览搜狐、新浪等商业网站时,也会对当地新闻特别关注。而地方网站尤其是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政府网站,与当地网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如何争取当地网民的认同,便是网络在地化服务的立足点。因此,网民的地方性感知和消费偏好,会对网络的地理空间产生直接影响,而强化网络地方与地方网民的多元互动,则是网络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随着网络记者证的放开,网络媒体将会获得更多的地方新闻采访权。网络内容生产和供给的模式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地方新闻的呈现方式将更为丰富。回到“地方”就是要让网民感受到地方场景的结构性存在,网站的内容供给不单纯是提供简单的信息指引,而是要活化网络作为地方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现网络地方空间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景观,为网民提供消费、社交、娱乐的综合服务,使网民能够在地方空间感受健康、理性、文明的氛围,焕发网民对地方社会的关注和热爱,并积极为地方发展献计献策,从而构建地方空间的精神家园。
其次,网络文化的地方性建构要适应网民情感上的地方性需求。在网络内容的同质化不断增强、审美趣味不断降低的背景下,如何提升网络文化的品质,满足网民日益多元的精神需求,已成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大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上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是网民经常浏览的网站,也可以是喜欢的网络社区,还可以表现为网络社群和社交圈。从可行性看,网民都能拥有自己喜爱的“地方”。地方空间是具有价值指向的栖居地,它应该满足网民的个性需求,提供某些特色的服务,具有浓烈的情感归属感,在网络世界中呈现自身的魅力和优势。因此,网络地方空间既要体现大众文化的需求,满足大众休闲娱乐和精神消费的需要,更要进行类型化、专业化、精细化型构,侧重为某些具有相似消费需求的网民服务。所以,网络地方空间的聚结,是网络社群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群体传播是网民进行自我归属和网络社会化的需要,网络族群的广泛出现,体现了网络亚文化的普遍存在。网民交往过程中的角色展演、交往报酬、资本竞争、价值导向与权力角逐,通过“在地化”的象征符号得以体现。因此,网络社群文化所形成的地方感,对网络地方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网络社交媒体出现的群体聚结现象,在地方空间的生产和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群体区别于一般社群,其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个体与“他者”之间的交往,通过在某些“地方”的交流得以实现。网络群体摆脱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使网民能够围绕各种话题建立群体关系,并进一步表达意见、分享快乐、学习交流、娱乐游戏。网络群体活动在一定的地方空间呈现,网民基于地缘、业缘、学缘、趣缘、情缘等关系而结合的族群,具有自我认同、身份区隔、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追求,对群体传播的属性、作用、功能和价值进行区分,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形成网络亚文化空间。如小清新亚文化独白式传播和逃兵主义,以及商业收编和标签化特征,展示了网络地方空间的类型化与象征作用。因此,群体传播首先就是以网民为主体的集体传播,网络群体传播是网民寻求社会归属的需要,尤其是微博、微信上的群体活动存在着严重的他人导向。一些网络谣言能够在各种群里广为传播,与群体成员的盲从与偏好有直接关系。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仇官、仇富心态,往往通过群体事件的传播得以强化。而群体极化现象一旦形成,则会演变成社会情绪,激发社会矛盾。网络上群体的非理性意见传播,是导致群体心态失衡的重要原因。加强网络群体情绪和心态调节和引导,净化网络交往环境,提升网络群体生活的精神品质,则是网络社群文化和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网络地方空间应体现网民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特色。在微时代,许多网民热衷于自我表现,沉迷于各种朋友圈和社交群,对公共价值漠不关心。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泛滥,导致了审美疲劳和社交幻化,进一步消解了网民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具有集体文化和公共精神的网络地方空间,则被广为流行的私人空间所压缩。网络上的“地方”,并非是乌合之众的汇集地,而是需要网民精神上的“还乡”。在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融合的过程中,网民的消费需求被不断放大,而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生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微博、微信中,网民通常是进行日常生活和社会新闻的内容生产,精神层面的思考和批判往往难得一见。我们在承认网络文化商业性、娱乐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作为社会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时代特征。强调网络文化的精神品质,需要网民从文化生产的源头,看到网络高品质内容缺失的现实,从个体本位和公共价值的角度,在网络地方空间中明确自己的定位,重新审视地方空间与流动空间,主体价值与客体价值的关系。
回到网络地方空间,指的是网络媒介时代对主体的地方感和深层精神结构的构建,而不是简单地回到地域。[9]这要求网民从精神层面上找到“希望的空间”。尽管全球性网络文化充满各种色调和迷乱,但是,我们需要在“希望的空间”中不断找到自信、尊严、自由和创造力,这就需要我们去伪存真,潜心修炼,不为“低俗”、“网瘾”和“物欲”所惑,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和社交圈。要求我们尽量保持独立的思辨能力,寻求适合自己生长的网络“地方”。因此,回到网络地方空间,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流动空间,而是需要在精神层面进行自我修炼和提升。对于个体而言,大同世界固然遥远,但地方空间却前景广阔。我们需要净化自己的网络环境,在一个较为晴朗的网络空间展示自身的存在。此类地方空间虽然形态多样,功能不一,但它体现了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可以成为地方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地方空间,网民不但可以开阔视野、寻求新知、广交良友,还可以各抒己见、广开言路,成为不断创意和创新的文化园地。可见,网民寻找网络地方感,更多地体现了其对网络精神和个体价值的追求。而网络地方空间的不断成熟、发展,有利于满足网民对现代文明和公共生活的多元需求。
在全球化的网络景观中,我们需要回归地方,在漫无边际的网络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就在网络的某些“地方”,它是网络人文价值、公共精神、思想资源的具体指向,也是网络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1](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C]//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王志弘,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4.
[2](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M].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7-158.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9.
[4](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
[5](美)曼纽尔·喀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94.
[6]Relph E.place and Blamelessness.London:pion,1976. pp.25-30.
[7](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
[8]朱军.略论新媒介文化与空间生产——以空间与地方二元关系为视角[J].文艺理论研究,2013(2):212-218.
[9]徐翔.回到地方:网络文化时代的地方感[J].文艺理论研究,2011(4):130-134.
[责任编辑:李 桃]
G206
A
1002-6924(2016)10-099-103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播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13AXW013)。
蒋建国,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