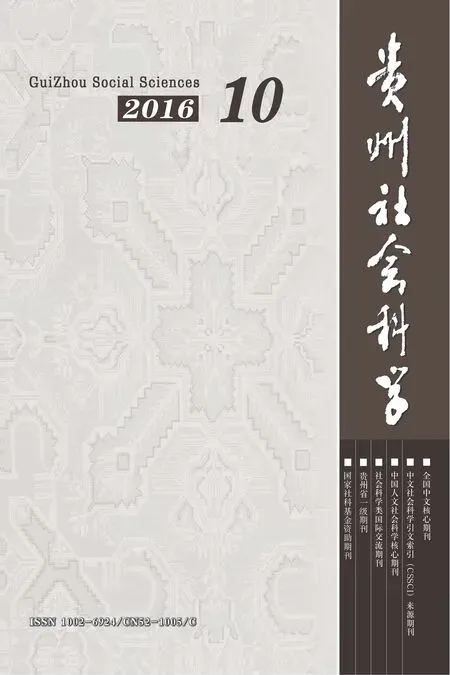中西方义利关系的对立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关系问题探析
靳红娜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中西方义利关系的对立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关系问题探析
靳红娜
(河海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中国的义利之辩在西方思想史中表现为道义与功利之争,它涉及道德与利益、公与私等关系的辩论。在中西方历史上,义与利、功利与道义是相分离的,甚至是相对抗的。而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关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超越了中西方义利关系的对立,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
义利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道义论;功利论
“义”和“利”确为中国文化的原生范畴,义利关系也是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义利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关系。“义”包括着道德责任、社会公利的内涵,而“利”则包含着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的内涵。因此,义利关系包含着道德与利益(抑或道义与功利)、公利与私利两方面的内涵,由此形成了不同思想派别。而在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义利关系中所探讨的许多问题也同样得到了重视,并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观点。中国的义利之辩在西方历史中表现为道义与功利之争,它多是针道德与利益、美德与幸福、利己与利他之间展开的,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中国传统义利关系之辩
(一)中国传统义利慨念
西周时期出现了义利思想的萌芽,但作为理论形态的义利思想则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随着春秋末年的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同的社会力量奉行不同的价值取向,义、利关系和义利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并且在不同的观点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碰撞,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义利之辩”开始正式产生。中国传统义利观所讲的“义”与“利”,是两个歧义较多的概念,其意蕴十分丰富,常常在不同的情况下被赋予不同的涵义
1.义的传统内涵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义与利这两个字很早就出现在甲骨文中。“义”的繁体为“義”,在古代羊是美善吉祥的象征,而“我”的本义是一种戈形兵器。“義”的本义就是由“我”的力量捍卫美善吉祥的事物。后来,随着“我”由兵器向第一人称的转化,“义”便被解释成“己之威仪”,这里的“威仪”,按《左传》的解释就是指人在社会生活多方面均能举止从容、合度合节,在一定的伦理道德关系中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风度和威严。由此,义便成为一种道德威慑力,具有了道德的内涵。“义”被进一步抽象和引申。《中庸》(第二十章)则这样解释:“义”原指“宜”,“义”与“宜”相通,含“应当”之义,引申为道德的当然之则。
传统义利观中的义,有二层含义:其一是指与功利相对应的道义,泛指与物质价值相对应的精神价值与道德规范;其二特指某种性质的公利,代表着以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为基础的人伦道德秩序、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2.利的传统内涵
在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利”是个会意字,意思就是指用刀割禾,意为收获。后被引申到宗教领域,在商、周之际,利字在《易经》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当时仅仅用于占卜,卜问吉凶,在此是取“吉祥安泰和顺”之义。再后又被引申到经济领域,用作“货财之利”。随后又进一步引申出利益、功利、事功之意。
传统义利观中的利有两个层次的意思,其一是泛指利益、事功、功利等,古人所说的利,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其二是特指个人的私利。儒家把“利”同个人的物欲、私心、享乐和欲望联系起来,提出了“利之所在,害之所兴”的观点。儒家的“利”所重视的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
(二)中国传统义利关系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就有义与利何者为先之争。义与利作为一对思想范畴,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自从先秦儒家提出了义、利两个对立的概念,“义利之辩”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存在。一般认为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传统文化反映出三种观点: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合一。
1.重义轻利:废义则利不立
中国自汉至明清,占统治地位的是孔孟荀儒家的重义轻利论。在处理义利关系上,儒家认为,义和利是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孔子提倡“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根本原则。孟子的义利关系的思想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仍然坚持重义轻利的主张,但孟子在义利相斥的思想道路上比孔子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主张。孟子特别推崇义的价值,不仅要求人们舍利取义,甚至要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①《孟子·告子上》。。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总结者或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以义制利”、“利统一于义”的观点。孔、孟、荀三人在义利问题上虽然观点不是完全重合,但重义轻利则是共同的基调。
汉代董仲舒把“重义轻利”的传统推至顶点,提出了“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②《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义利关系发展到宋代,程颢认为义与利不能同时并存,非义即利,非利即义,更加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和不可兼得的关系。朱熹更是认为“圣人”的境界即为“存天理,灭人欲”③《朱子语类》卷四。。其实质是一种禁欲主义。宋明理学将义利关系引申为理欲关系,使重义轻利极端化,将“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互相分离,互不相干。
2.重利轻义:惟利无义
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是重利轻义论的主要代表,此派以商鞍、韩非为代表,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利是基础,在利的基础上产生义,利是第一位的,义是第二位的。影响最大的是《管子》中的“仓廪实现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④《管子·牧民》。。它表达了没有利便没有义的思想。韩非也持此观,宋代苏洵也明确指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⑤苏洵:《利者义之和论》。
法家义利关系思想的主旨是强调功利,其思想逻辑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从人性之自然出发,认为好利、自为是一切人的本性。因而要求人们“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⑥《韩非子·六反》。。其次,法家所强调的“利“,指的是“人主之公利”或“人主之公义”,而非个人之私利,他所辩护的是如何来维护封建国家的宗法等级秩序,这与儒家重义轻利的目的是一致的。
3.义利合一:义即利
墨子“尚利”,认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①《墨子·非乐上》。,同时又提倡“贵义”,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②《墨子·耕柱》。。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及其后学不主张义利互相排斥,而主张“贵义“又”尚利“,承认义利并行,两者可相互含蕴。即所谓“义、利也”。③《墨子·经上八》。
墨子把利分为公利和私利,又特别强调公利的作用,墨子把义通约为利,强调义即利,义就是指天下之利、国家之利、百姓之利。总之,墨家把利规定为大利、公利,从而在公利基础上,把义利统一起来了。因此,他把凡是利他人利国家的行为本身看做义。这既强调二者的内在联系,又强调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墨家承认人有利己之心,但明确反对私利,认为从利己之心出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任其发展,就会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天下大乱。墨家提倡的利是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它在提倡功利的同时,也充分地重视和提倡道德,由此达到了义利统一,这也是和儒家的义利思想相区别的地方。
中国古代义利关系经历了儒家的重义轻利,法家的重利轻义和墨家的义利合一。梳理传统义利关系,不难发现各派尽管存在似乎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也有其共同之处。首先,对义与利关系都偏向于一方,而轻视另一方。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义利关系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义、利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次,儒、墨、法各家均提倡“公利为义”的思想,强调公利即社会整体利益具有至上性。第三,儒、墨、法各家的“义”表面上看是维护全社会的利益,但实质上是极力维护君主统治和家长统治的宗法等级秩序及其利益关系,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论证和辩护,反对僭礼越分、犯上作乱等。
二、西方历史上义利关系之辩
义利问题在西方历史上也一样源远流长,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着功利与道义的争论和辩难。西方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是围绕着道义与功利之争展开的,义与利、功利与道义是相分离的,甚至是相对抗的,由此形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义利观。西方义利之辨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德谟克利特开始,经历了柏拉图的“重义轻利”、色诺芬的“重利轻义”的矛盾对立;到了“以神为中心”的中世纪,其义利思想受到教会伦理的影响,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重义轻利”;随后,经过思想家们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性代替了神性,个人利益得到肯定,在义利关系上最终确立了重利轻义的思想。
(一)功利论:利高于义
功利思想萌芽于古希腊时期,最初功利是与幸福、快乐等字眼联系起来的。它起源于感性主义,从伦理史角度来看,德谟克利特应该是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他的感觉幸福论观念是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源头和内在精神实质。紧随其后的伊壁鸠鲁是一位理性快乐主义者。他们都注重道德与现实物质生活的密切联系,肯定个人的物质需要,反对把道德与物质利益对立起来。西方近代感性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霍布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以及边沁、穆勒。他们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共同见解都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质的体现,追求物质利益、满足感性欲望是人生的最大目的,功利论肯定道德依赖于人的实际生存利益,并始终强调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和来源,着重善和功利的价值。
但功利论在肯定义利之间、利益与道德之间存在着联系的同时,坚持利益对道德的优先性和决定性,使道德为利益服务,认为利要先于义、高于义,义应该服从于利。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问题上,他们主张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个人利益是更根本更现实的利益要求,主张私利高于公利。
(二)道义论:排斥利考量的义
道义论几乎伴随着功利主义成长起来。该词源于希腊语“deon”,意思是“必然性、责任”。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对义利关系的考察,主要围绕人生目的和幸福生活等问题展开。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多葛派,形成了一种德性伦理的思想传统,他们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把追求至善的理念和美德看做是真正的幸福。苏格拉底堪称古希腊道德哲学的第一人。他将人的感性欲望和物质利益从道德中排除出去,把道德看成是天赋的,完全否定道德的社会物质根源,这一思想由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继承和发展。到了近代,该学派逐渐形成以斯宾诺莎、康德等为代表的道义论,康德更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康德看来,最能体现道德价值的莫过于人的“善良意志”[1]。康德在道德与利益关系问题上是重视道德鄙弃利益,否认道德的利益基础的,认为一切道德价值的产生都是出于对物质欲望的排斥。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问题上,康德强调道德必然要求为义务而义务,认为道德的要求就在于自我牺牲,一个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不是因为他得到利益,而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道义论排斥感性的东西、物质因素,把道德提到利益之上,强调道德对利益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强调义利的对立关系,主张牺牲利来成就义。这体现了与功利主义迥然不同的“道义伦”的色彩。
功利论虽然强调利益与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但是由于不懂得人的社会性,而把人归结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他们强调感官的快乐和幸福,过分强调物质功利,贬低精神。道义论在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上,重视道德而鄙视利益,否认道德的利益基础,认为道德至高无上,一切道德价值的产生都是出于对物欲的排斥,人应该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在道德评价上强调自我牺牲的道德价值,使其道义论成为摩西十诫的道德诫命。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人的感性需求、物质欲望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功利论和道义论在对待义利关系上都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缺陷。
三、马克思恩格斯义利关系是功利论与道义论两者的统一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义利之争,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应当肯定,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伦理思想史上,一切唯心主义者总是颠倒物质和意识、利益和道德的关系。他们认识不到道德与利益的辩证统一的关系,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由来已久的义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道德和物质利益关系这一问题,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不是重义轻利论就是重利轻义论,总是执其一端,非利即义或者非义即利。结果就是终究无法找不到义与利相通的基础。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们虽然就义利关系问题提出过合理思想,但都没有触及到义利关系的本质,他们总是离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去观察和研究义利的关系,都没有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间题。一方面,思想家们不能正确认识道德的来源与本质,看不到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内在关联,把道德看成与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毫不相干的东西;另一方面,在私有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义利观,不是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就是片面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完全把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对立起来。例如,封建主义一味地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而资本主义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基于社会实践,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吸取功利论和道义伦思想精华的基础上,既批判了抽象的道义论,又批判了狭隘的功利论,超越了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利思想是人们对义利关系问题认识上的一次伟大飞跃。
(一)对抽象道义论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是道义论者,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道义论者。首先,它否定道义论离开物质利益空谈道德,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反对从单纯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去思考社会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康德等人的为义务而义务的义务论。康德不赞成英法唯物主义的道德论,认为把快乐、幸福作为道德根据的经验主义伦理学说,其原则是没有客观的普遍必然性的。道德的根源不仅不能到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中去寻找,而且恰恰是对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的征服、控制与超越。一个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不是因为他得到利益,而是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康德主张从完全超感性经验和功利幸福的纯粹理性和善良意志中去寻找道德的根源,并坚持认为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之中还是在这个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善良意志落实到人们的道德生活领域必然要求“为义务而义务”。
马克思分析批判了康德的善良意志理论,指出:“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2]211道德善良意志不能失去人类最基本的东西,如果道德失去了它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被推到了“彼岸世界”,道德就变成了神的祭坛上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影像。
(二)对狭隘功利论的扬弃
马克思早期就开始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走向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功利主义学说,他们在全面分析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之后,充分肯定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功利主义“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3]并且又说,功利主义“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2]484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之所以“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而不能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财富,就在于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论原则最为真实地揭示了人类幸福论理想,而这一理想恰恰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功利论超越了功利主义,他们在肯定功利主义的同时,批判了功利论把道德立足于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偏狭性。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是自然的人,其次才是社会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18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每个人又都有维护社会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功利主义者把道德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时指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然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5]也就是说,道德的基础在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而不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利益基础上的。
边沁宣扬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不是想得出与利己主义相对立的道德结论。因而他所宣称功利主义恰恰是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以利己主义为归宿的。恩格斯在批评边沁功利主义时深刻地指出:“边沁在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所犯过的同样错误:他在克服二者的对立时是不够认真的,他使主体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弄颠倒了”,他“不是代表全体利益的权利赋予自由的、自觉的、有创造能力的人,而是赋予了粗野的、盲目的、陷入矛盾的人”。[4]675-676在他们眼里利己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使人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6]
(三)超越中西方义利关系的对立,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利关系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了义利关系问题。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应有于义利关系的研究,而且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上考察道德现象,科学地阐明了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又对利益具有反作用的两者辩证统一关系,从而在伦理思想史上完成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中西方历史上对义利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夸大二者之间的对立。不管中国的义利之辩,还是西方的道义论与功利论之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义”“利”分离、“义”“利”对立,因而都无法科学地揭示和说明义利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上。通过对抽象道义论和狭隘功利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道德与利益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关系,既不能遵循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路径,也不能重蹈思辨唯心主义的覆辙,应当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来认识和解决这一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打破了“义”“利”的二元对立,确立了科学的义利关系。他们立足于社会物质基础把义与利、道义与利功利有机统一起来,在现实的实践中彻底摆脱抽象的义利关系,真正实现了义与利的有机统一。
[1]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5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6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3—33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9.
[责任编辑:黄 昇]
A81
A
1002-6924(2016)10-071-075
江苏省教育厅课题“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2013B28514)。
靳红娜,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